行走与他者体验
汪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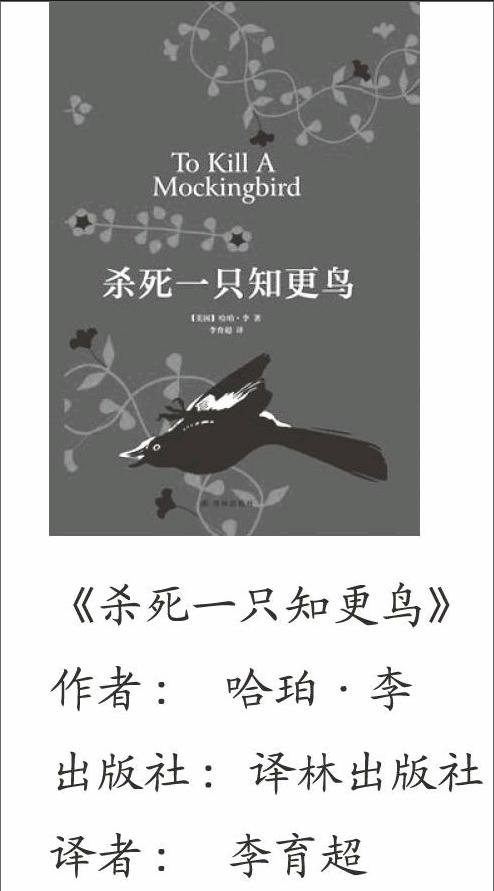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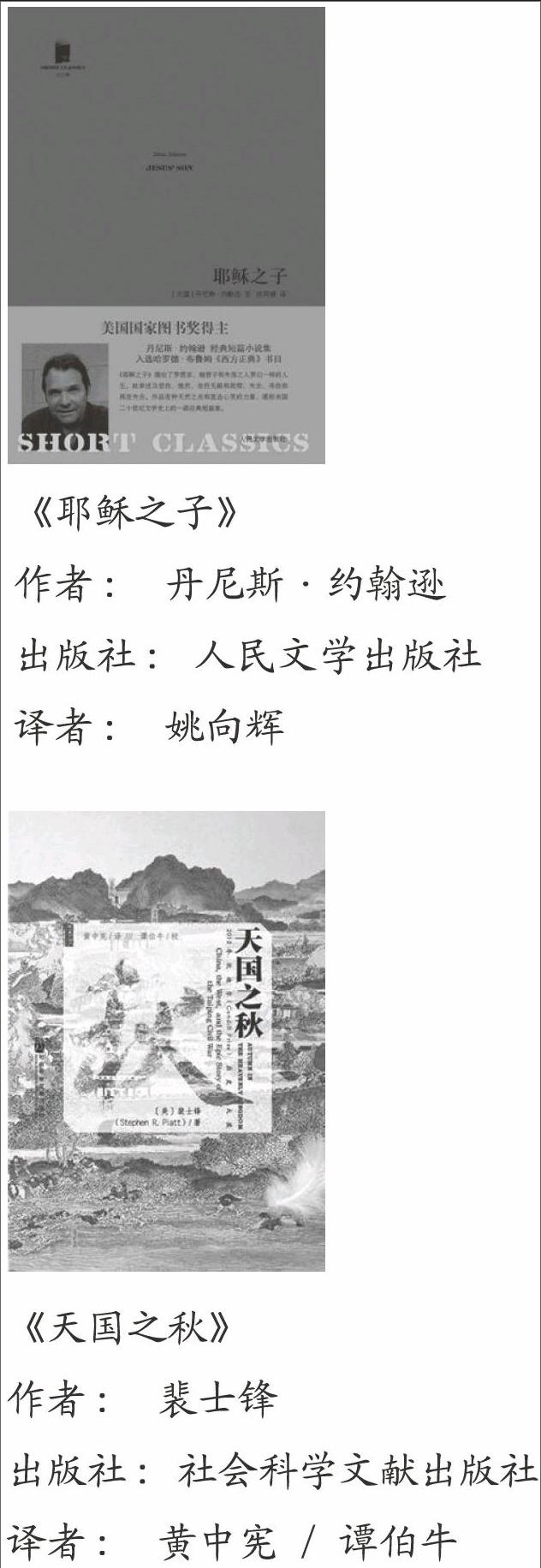

公元十六世纪,徐霞客先生环游大明三十年,从万历朝走到了崇祯朝,后世认为(或者说期望)他作为一个有价值的古人应当有些人世的抱负,所以把他说成是地理学家,博物学家,或者至少是个旅行家。不过在我看来,这些头衔或多或少都有后人的目的在里边。种种迹象表明,徐先生只是好奇心不安分又笃爱乱走而已,跟现在穷游的背包客在思想上多少有点同源,至于地理生物之类的发现都是顺带脚的事,不信你看他那句“大丈夫当朝游碧海而暮苍梧”的名言,跟现在被不安分的小青年们奉若精神领袖的海贼王那句“男子汉,去大海吧!”有没有异曲同工之处。
后人们很爱按自己对高尚的解读武装先辈,但往往会把先辈最值得尊重的部分丢掉。一个科举时代的人,能不顾功名去遍游名山大川,本身就是一件很穿越的事,对比现在社交媒体上有关房价和名校之类的遍野哀鸿酷得一塌糊涂。而且手机时代的旅游和徐霞客的旅游大为不同,徐霞客应该是不会有走到哪儿都发个照片九宫格换几十个赞的概念的,亦不会料到几百年之后官方和民间会各自把他当做科学冒险家或徒步界的祖师爷来纪念。对于他来说,行走就是一件自我的事。
随着科技的发展,自我的事越来越少是一个不得不拿到台面上来的事实。现在讲万物皆媒,好多东西的意义都是秀给他人看,别说旅行这种本就带有社会性的活动,就连读书这种原本带有充分排他性质的行为也越来越多的成了样子货。不过现代也有一点比较好,就是行走和阅读这两件事通过某个场景结合一下,就又可以成为一件自我的事。要徐霞客背着书本边走边读很不现实,现在你坐在飞机或者高铁上,速度快得完全可以把4G信号甩在后面或者下面(当然听说现在有高铁已经开通了wifi服务,如果速度有保证的话,人类好像又少了一块可以只活给自己看的地方)。
犹记得大学临毕业前第一次出远门,是从东北到北京的特快火车。那个时候倒也没有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一说,也没有各种ipad上的大小电影,只好捧着一本《杀死一只知更鸟》从头看到尾。现在大家都知道,知更鸟在这本书的书名中是一种错译,因为北美是没有这个物种的,应该叫反舌鸟才对。但是人们总觉得“知更”二字对书中的律师父亲芬奇先生是一种贴切的隐喻,也就将错就错下来。这本书如果在平等与权利这类政治的解读视角看确实有点浅显,但如果对“他者”在生活中的存在和位置而言,李·哈珀可能是写得最传神的美国人之一。鄙人之前没怎么出过远门,长达十二个小时车程坐到后来是比较容易崩溃的,所以当看到牧师在审判结束后对女儿说“斯高特小姐请起立,你的父亲要经过这里了”之时,突然觉得鼻子发酸,差点在京哈线上洒下男儿泪。
芬奇先生是一个维护常识的人,这个常识说未很简单,就是要尽量去尊重你不理解的人,起码不要歧视他们。在长途火车这种塞满了人的封闭场所,这一类体验常常出现。我曾经在浙赣线的一列火车上翻看一本丹尼斯·约翰逊的《耶稣之子》,这本薄得很的集子被称作“肮脏现实主义”的代表作,但是我个人觉得比之雷蒙德·卡佛的功利还是略逊一筹。这本书里涉及到很多嗑药的情节,我翻了一半时把它塞在前座靠背后的大口袋内去上厕所,回来发现书不见了,环视四周寻找时,一位斜后方的大哥微笑着把书还给我。他的表情没有一丝一毫的厌恶,似乎也并没有因为我在公共场合中公然阅读这样一本如此露骨地描述瘾君子日常幻觉的奇怪作品,而对我另眼相看。
另一次被乘友把书拿去的情况是在某列去上海的高铁上,我抱着一本裴士锋的《天国之秋》打了半天盹儿,醒来准备继续读的时候被过道另一端的阿叔提出要借来翻翻。他说小伙子你拿着这样厚的一本书坐车还真是够努力的,我告诉他其实这书除了读来增广见闻之外并没有什么更直观的利益收获,跟努不努力也不搭界。这本书中所描述的很大一部分历史发生或有关于上海,如果阿叔有兴趣询问书里大概写了些什么,或许我也可以斗胆和他聊一聊。不过在这列从南京直奔上海的火车中我们似乎没有交流一百六十年前沿着几乎同样的路线杀向魔都的那群“长毛”的缘分,阿叔颠了颠书的分量就还给了我,后来也没有和我再聊过什么。
相较之下,我还是更喜欢在交通工具上读历史书或小说,因为窗外转瞬而过的景象很容易为人带来一种类似电影中的长镜头的空间感和时间感,总有一点和你在家或图书馆或咖啡馆里看书不太一样的体验。我曾在北京到郑州的高铁上读《生存与命运》读到肝肠寸断。战地记者出身的瓦西里-格列兹曼写出了一本有关二战的《战争与和平》,主角换成了纳粹和苏联,文风也更加符合现代人阅读的口味。小说中,随苏共机关逃至古比雪夫的一位母亲柳德米拉突然得知自己在前线作战的儿子托利亚身负重伤,于是从当时苏联实际上的“陪都”出发,南下前往萨拉托夫寻子。我当时行进的方向和距离与这位母亲几乎一致,只不过柳德米拉是沿着伏尔加河的水路,并且在甲板上刚刚痛哭了一场。她和主旋律语境中“英雄”母亲有所不同,她离过婚,第一任丈夫是苏联红军内部大清洗的对象,第二任丈夫是科学家,却总让她觉得有些隔阂,她的母亲常常讥笑她不近人情,她与第二任丈夫的女儿秉性又有些叛逆和古怪,喜欢对她夹枪带棒,还热爱引用外祖母讽刺女儿的话来讽刺她妈。战争没有发生的时候,除了上述问题之外,生活的不如意还包括“安排丈夫出差却没有为他搞到软卧票”,如今儿子生死未卜,所有问题却都成了点燃她悲伤的引子之一。她坐在甲板上,周围人来人往,她的悲伤“如大地一般,无边无际”,他人的叹息让她觉得安慰,却无法忍耐“妇女们平静的目光”。处于重大变故状态下的个人,很容易在不冷静和无助中产生需要“周围的人与自己休戚与共”的幻想,但此时的“他人”还是“他人”,“地狱”自然也是“地狱”。
不过我当时却难过得不能自己。柳德米拉在伏尔加河的破旧轮船上似乎没什么理解她的人,我一个距离小说中的情境时隔七八十年数千公里的外国人倒恨不能为她流泪。环视左右,芸芸众生都在做着自己的事,书中人却经历着战祸带来的生死离别。窗外的田地树林山包快速的掠过,后人眼中的历史与之相似,你知道闪过了什么,但是细节如何,有多少人在其中绝望的生存或死去根本看不到。好的小说让你脱离开上帝视角靠近人,倒也是作家的慈悲心。
在乘坐交通载具行走这件事上,我是高铁的拥趸,因为我并不喜欢坐飞机。有的人终其一生也不敢坐飞机,却常常被旁人笑话。厄普代克有一短篇小说《相信我》中描写了这一类的事实,其中也包括飞机故障,而且不巧我是在某趟飞广州的航班上读到这篇文章的,也有一瞬间觉得晦气。在这个短篇中,厄普代克写了一位主人公身上发生的几个故事,都是那类“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会不在乎”的体验。写这种体验写得惟妙惟肖的另一位美国作家是理查德·耶茨。这个体验可以被表述为“孤獨”。但是孤独会不会是一定程度上的自由呢?比如行走着的徐霞客是不是孤独的?独自乘坐飞机或高铁上的你或者我呢?
当然,在多数情况下,人都是以自己的感受为大,这并没有什么可以过分非议的地方。如同你在火车或飞机上排队上厕所,很少有人会按自己和他人生理需求的轻重缓急来决定谁先进谁后进,因为主观感受只能是你的主观感受。我小的时候曾被撞坏过一只眼,至今两眼的聚焦功能于常人相异,所以看不了3D电影,这个体验在别人问我“那么你看3D和我们相比有何不同”之时,表述上便遇到了很大的障碍,因为我不知道“常人”看3D时是何种体验。类似的事情会使我想到葬礼,逝者的至亲和好友,或许会对与之永别这件事有切身的痛哭,但总有些关系一般不上不下的人,他们在葬礼当时也会流露出悲伤的表情,但一旦从那个场景中解脱,就会回到如常的生活,该饮酒饮酒该打牌打牌。你不能因此而觉得他们是无情的,这恰恰是某种人本精神的体现一一埋葬掉队的人,然后继续余下的路。毕竟与其他事,包括为他人的感受而喜怒哀乐相比,走自己的路才是此生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