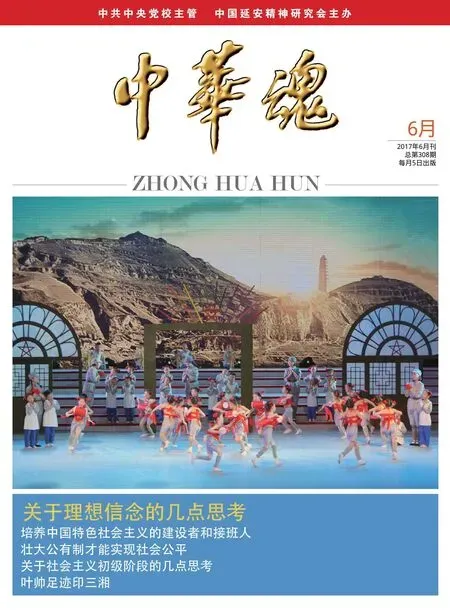忆我的父亲李振三
文/李雪松
未能忘记
忆我的父亲李振三
文/李雪松

李振三
父子情深 子承父业
父亲李振三,字子纲,陕西省米脂县桃花峁村人(现在叫桃镇),出生于 1898 年 9 月 26 日。他是中国现代史上闻名遐迩的爱国民主人士李鼎铭先生的长子。李家虽家境贫寒,却是乡里闻名的“耕读传家”。李鼎铭自幼孜孜不倦,刻苦钻研中外历史、数学、天文学、中国古代哲学及诸子百家学说。李鼎铭在青年时期受其舅父杜斗恒(杜聿明之叔父)的影响,就十分喜爱钻研医学,广览历代名家医书,阅读《本草纲目》《黄帝内经》等各种医刊(这些医书后又传给其长子,保存至今),深究医理。他这样坚持数年,自学成才,成为米脂县内外远近闻名的一名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的中医。
李鼎铭 17岁时,生下长子李振三。父亲自幼聪明好学,祖父对他很是喜爱,于是精心培育,严格要求。
李鼎铭 20岁考取廪生,但他拒绝做官,决心致力于振兴地方教育事业,1904年在桃花峁义学教私塾,后在临水寺创办完小,命振三就读于此完小直至毕业。1911 年 2 月父亲又到绥德中学学习,至 1916 年毕业。1917 年父亲受祖父之命,在家乡筹建桃花峁小学(即现在的鼎铭学校),兼任校长并任教。他把好的窑洞让给其他老师住,而他和祖父就住在教室北面的一间小房子里。他们坚持新法教学,打破了八股文的条框,使用白话文,还给学生们讲授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生们都深受教育,激发了高昂的爱国热情。他们的学生不少后来都成了共产党的领导干部。
1917年的桃花峁农村生活困难,李鼎铭父子对困难学生经常免去或半免去他们的学费。课余时间,他们带领学生参加建校劳动,种菜植树,自力更生,以减轻家长的负担。
在这段时间,父亲成为祖父创办地方公益事业不可缺少的得力助手。他们父子热心办教育,女子也要放足上学,祖父让他的女儿和儿媳(李振三之妻)带头上学。他们还常排解地方纷争,设法减轻农民的负担等等。
1922 年父亲受父命在桃花峁村试办中医实验所。父亲自幼聪慧过人,自小在给爷爷当司药的过程中就已经暗中刻苦学习中医中药。在办中医实验所后,他亲自开垦荒地,种植药材,上山采集药材,加工研制中药等,并研究试用当地的草药如宁条草(一种开黄花、有须根的草)、老才洼等,治好了不少老百姓的病。
1926 年,一生淡薄高官厚禄的祖父李鼎铭对当局彻底失望,遂称病辞官返回故乡,专心研究医学,父亲就成了祖父行医的得力助手。当时祖父坐堂行医,父亲开方取药并送医上门。父亲还经常到偏僻的农村和疾病繁多的地方为老百姓看病。据家乡老人们回忆:“当时他们父子为群众治病吃药,从未索取报酬。富家是自己赠送钱物,贫家则送给医药。”因此,深受当地群众的爱戴和称赞。一传十、十传百,不少患者闻名远道来求医,父亲则从不拒绝,随叫随到,风雨无阻,还主动负责到底。祖父对儿子的成长和医技的高超颇为赞赏。他遇到疑难病症诊治时总要与儿子共同探讨、研究。常常采纳父亲的意见下药。
听姐姐说,1943 年春天,祖父的肠胃病复发,卧床不起,我父亲立即为其号脉、开方,亲自侍奉祖父服用,并不时调理药剂。祖父的病情逐渐好起来了,饮食也一天天地正常了,家里人看到老人家的身体好起来都很高兴。祖父当着四个儿子和儿媳、女儿等的面讲起了家史,其中特别夸奖了我的父亲,称“振三学医专心,医术比我有过之无不及,医道深,对我帮助很大”,并让弟妹们好好向哥哥学习。
抗日战争中投身革命
1927 年,父亲的家贫困交加,母亲靠捡食野菜、野果,一边侍奉病瘫的祖奶奶,一边照顾幼女幼子,还要开荒种地、种树。为生计所迫,父亲忍痛告别妻儿,出外闯荡。他先在榆林陆军医院边工作边学习,以后又到西安、甘肃、内蒙古等地,以医为生,普救疾苦为乐。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父亲满怀救国之志,于 1937 年 12 月30日奔赴晋西南一带的抗日前线。在山西临汾经其弟(是共产党员)介绍,先到学生游击队工作。1938年2月初,父亲被调往决死纵队第六区专署工作(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实际是共产党领导)。当年2月底日寇进攻晋南,父亲随部队转移至汾西山区。3月初奉命组织第六区兵工修理厂。
1939 年 1 月,父亲被正式调任兵工修理厂厂长。在任职工余时间,仍坚持为群众看病。当年 12月初,晋西事变发生,工厂随军向北转移,于 12 月 22 日到达灵石孙山区后庄时,当时的负责人宣布机关向西北方向转移,工厂解散,命父亲自找安全地点隐蔽。父亲拟于晚间行动,不料被叛徒出卖,被阎锡山 208 旅415 团俘虏。其后两年中父亲边在阎军监视下干活,边组织不堪打骂的工人自救,掩护地下党工作,同时暗中寻找部队的消息。1941 年 12月中旬,祖父李鼎铭得到消息,报告党中央。延安保安处遂派地下工作者吕生文来到中部县营救父亲。为了尽快脱离险境,父亲开始装病,自制红药水含在嘴里,谎说是吐血,要求去国统区榆林治病。吕生文和我母亲拿着李鼎铭的本名“李丰功”的印记,来到父亲身边。12 月 30 日他们连夜赶过封锁线,早有我边防部队将父亲接到张村。沿途父母亲受到根据地政府亲切的慰问和照料。1942 年 1 月 6日晚,父亲终于安全到达延安,合家团聚,好不欢喜。回到延安后,父亲由其弟陪着拜见毛主席,受到亲切接见,毛主席同他做了长时间的谈话。毛主席询问父亲这两年的情况,鼓励父亲爱国的热情,赞扬父亲治病救人的精神。不久,父亲被安排在延安兵工厂(当时也叫农具厂)任副厂长。自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工作中,先后任兵工厂厂长,难民工厂厂长,毛纺厂厂长等职。解放后,父亲于1950 年又调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工业部统计处当科长。
父亲在这些繁忙的工作中,从未放松过对祖国医学的研究和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天职。他边工作,边钻研中医,阅读中医书刊,工余时间免费为领导和百姓看病。在延安的温家沟兵工厂,在难民工厂的沟横渠,还有在磨家湾,不少患者慕名前来就医。有一次,父亲看到一个人已被装在棺材中,家属痛哭流涕。父亲观察“死人”的面色,称“还有救”,立即把这人抬出来,经针灸、服药,终于从死亡线上把病人拉回来了。家属感动极了,要送东西,父亲笑着说:“救人是我的本职”。
全心全意治病救人
在延安期间,父亲常常骑着毛驴陪同祖父为首长诊病、开方。由于当时大家对中医中药认识不足或者说还有偏见,所以给首长治病就很难,必须得到组织的批准(当时连给其弟吃中药都要经组织批准)。父亲出诊总是随身带着他的针灸包,可往往派不上用场。但是,父亲诊病果断,处方大胆,所以祖父总是与之商讨后下药为首长治病。他们的高超医技得到首长的高度赞扬。
1953 年以前,父亲除了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党工作外,还一直坚持利用业余时间为群众治病。在我幼小的记忆中,几乎每天中午、晚上下班前,就见门里门外排满了看病的人群,父亲下班一进门顾不上吃饭喝水,放下包就坐下为患者诊治。父亲看病很认真仔细,号完脉总要先了解病人的思想状况,对病人十分亲切和蔼,要先讲病因,再讲治疗的道理,使病人对战胜疾病有信心(父亲称治病先治心),然后开方。他开了药方,还要告诉病人如何煎药,如何饮食起居,一一交待清楚,还要抽空亲自上门诊治,随访,负责到底。他还常常与中药堂的药剂师们切磋炮制丸散药物的方法,西安解放路原中药堂、北京同仁堂都是他常去的地方,他和这些药店的老板、药剂师们成了很好的朋友。他这样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看病从不间断,从不厌倦,也从不收费收礼,还非常高兴。我那时小,不懂事,就问他:“爸爸,你为什么要这样?”他摸着我的头说:“我懂中医,就要为病人服务。给他们治好了病,他们就能为革命多做工作,这不是很好么!”多么朴实的语言。父亲的善良,父亲废寝忘食治病救人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1956 年我还专门写了一篇作文《我的父亲》,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节目中播放了。我小学的老师和同学们对父亲的事迹称赞不已。
父亲为了救人一命,从不避嫌,不怕担风险,坦然面对。记得有一位 50多岁女性患者,突感右下腹疼痛难忍,痛苦难堪,被医院诊断为“急性阑尾炎、腹膜炎”,患者高烧不退,医院嘱立即住院手术,并让家属签字,说有生命危险。患者及家属很害怕,慕名找到我父亲,父亲立即安慰其“不要怕、能治”。他先以针灸给她止疼,然后用自家的广木香、大蒜碾碎以黄酒拌之,让病人马上服下,第二天就不疼了,连服三日即病愈起床,家属及患者感激不尽,说:“振老真是神医”。他们备了礼品送父亲,父亲坚辞不收,说:“治病救人,是我应该做的”。还有一邓姓女干部,因患“痔疮”,排便时肛门疼痛流血,被医院诊为“内痔脱出”而住院,以“枯痔散”治疗。五天后称“痔已枯干”,且无任何症状,嘱下午出院。不料出院到家才一小时,病人突然发冷高热至 40℃,头晕乏力,精神不振,嗜睡,不欲言语,食欲不振,又入院用青霉素,治疗无效。两天后邓姓女患者出现精神烦燥不安,意识模糊,呈谵妄状态,不能吞咽,须导尿及鼻饲维持,生命垂危。家属要求会诊以抢救其生命。医院即邀李振三老医师会诊。父亲为其诊脉后认为“此湿热郁蒸,身发黄疸,实为湿热发黄而湿偏重也。湿热蒙闭心窍则神昏。脉大仍为病性进展之象。”急与“茵陈五苓散”,水煎鼻饲药液后,当夜患者神志逐渐好转,一般状态改善,夜3点发现肠鸣矢气,腹胀鼓肠消失,且可进食。次晨,病人神志完全清晰,可以问答回话,能自动排尿,巩膜及皮肤之黄染减轻。继服上方第三日,患者自己能于床上坐起,并要求下床。住院十余天痊愈出院。医护人员及病人统称奇迹。
父亲独到的诊治技术,尊重并与西医合作的精神,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不避风险,直言不讳的高尚医德,使多少长年被疾病缠磨的患者恢复了健康,使多少病入膏肓,被医院判了“死刑”的病人得到了再生。他是人民的好医生。
为发扬祖国医学艰苦奋斗,呕心沥血
中国长期以来遗留下中西医不团结,不合作,互不服气,尤其看不起中医、鄙视中医的现象。在延安时期,和国统区一样,不少人主张废中医,立西医。中医被一些人认为是巫医,骗人的,不科学的。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李鼎铭父子坚持认为中医是中国世代相传的治本之术,中医也有自己的病理、医理和药理,也是科学的,而且,中西医各有所长,只有团结起来,优势互补,二者结合,才能求得进步。他们父子以自己的医疗实践证明了中医的治疗力度,片面否定中医的看法是不对的。他们常给中央首长看病,他们的疗效和意见,对中央首长全面认识中医是有影响的。从这个角度说,“中西医结合”现在成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方针,他们是作出了贡献的。父亲遵照祖父的遗愿,不遗余力,呕心沥血,始终不渝地钻研中医,解放后成为中国中医研究院的创始人之一,成为著名的国家五级中医师,为中医中药学的发扬光大作出了贡献。还在 1945 年8月,在领导的支持下,李鼎铭在延安办起了中医训练班,设立了生理、药性、汤头、诊断等课程。父亲也有时去帮助代课。他们不排斥西医,倒是满心希望能为团结新老中西医,各自发挥所长作出自己的贡献。
1947 年 3 月,胡宗南奉蒋介石之命,大举进攻延安,中共中央果断决定撤离延安。李鼎铭父子随机关、部队转战陕北,生活十分艰苦,面对当时的险恶形势,祖父心急如焚。加之祖父年高体弱,积劳成疾,1947年 12月 9日患了脑溢血。父亲赶赴祖父驻地,亲自针灸,开方服药,但为时已晚,祖父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 12 月 11 日上午 6 点带着无尽的遗憾与世长辞。父亲及全家悲痛欲绝。祖父在病逝时有三大憾事,其中第一件就是中医学未能流传后世,发扬光大。他要求振三继承父志,继续研究。父亲扶柩发誓,定将“悲痛化为力量,永远继承家父遗志,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为光大中医不懈努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到底。”
1952 年,中央专门派华北局领导到西安,命父亲到北京搞中医,筹建中医实验所。当年9月到了北京,住在华北局招待所。
在翻看父亲的遗物时,我看到了好几个笔记本(也可叫日记吧),上面详细记载了他到北京后的活动。万事起头难,但父亲横下一条心,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开始给二叔治病,同时到处奔走,经常到中央首长家中,边给他们诊病,边宣传中医中药的重要,呼吁重视中医,中西医结合。他还阅读了大量的西医书刊,学习琢研新知识以充实自己,虚心向同道学习,还与苏联、日本、朝鲜等国的同行们切磋医技,交流经验。当时慕名前来就医或联系看病的人络绎不绝,无论贫富贵贱,无论职位高低,父亲皆一视同仁,常常废寝忘食,竭尽全力。
1953 年 1 月,父亲受命在西直门内一院内成立了中医实验所,只有父亲与其助手宋抱朴大夫,还有一名女护士。当时定的方针是“团结中西医”,任务是:团结、组织、联络广大中医;收集、整理、研究中医验方,交流经验。所设的实验所只有3间平房,上午门诊,以机关干部为主,不设条框,不设病床,不收费,下午主要研究中医理论与实验的结合或组织会诊。在一年多的时间内,父亲又为不少首长治好了病,如习仲勋,朱良才等,他几乎每天或隔天去给他们看病.并和他们成了好朋友。
在繁忙的工作中,父亲受命广为联络社会上散在的中医名家,了解他们的医术、政治情况、家庭情况、历史情况等等,和他们联络感情,交流经验。他将他们的情况汇报给组织进行政审,逐渐扩大中医实验所,由3个人扩大到5个人至多人,由半天门诊改为全天门诊,并开展中医讲座学习。
1953 年 10 月,父亲李振三与岳美中大夫共同写了“我对祖国医学的认识”,这一材料是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团结中西医政策及中央卫生部第三届全国卫生会议的决议“批判地接受祖国的宝贵医学遗产,有步骤、有计划地整理中医中药”的精神而写。洋洋洒洒,长达 50多页的文章,分为中国医学基本上是科学的(还从生理、病理、诊断、治疗、方剂、药物、针灸等方面论证之);中医今后努力的方向和结论三个大的方面。它详细地论证了“中医学本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在悠久历史过程中的光辉遗产之一,于保障人民健康事业上曾经发挥了伟大的作用,与疾病做斗争的记载中,写下了不少的辉煌成绩。”父亲在文章中说:“我们相信这一份民族遗产,在毛主席和共产党正确领导下,必须得到整理和提高,使旧有的延续生命抵抗死亡的医学经验,成为科学的医学,以崭新的姿态出现,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文章最后高呼:“中西医团结起来,互相学习,互取所长互补所短,接受苏联先进医学经验,整理祖国医学遗产,发扬民族固有文化,为提高医疗技术战胜疾病保护人民健康而奋斗!”这篇文章得到了中央首长及卫生部的高度重视。
1954 年 6 月,他们正式成立了华北中医实验所。其性质定为事业单位。任务是:团结联系广大中医;收集整理实验秘方和民间单方;总结临床经验。他们研究制定了一整套如何完成这些任务的方式。父亲任该所所长。
1954 年 7 月,卫生部召开了中医座谈会,会上传达了领导对中医中药工作的指示:“中医对中华民族有极大的贡献,中医对人民的健康保障,是起了不少的作用。西医也是有贡献的。”“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反动统治下,西医歧视中医是宗派主义态度,是卑鄙的恶劣的资产阶级心理状态。”指出,当前的任务是首先“西医学中医”,并提出“好的中医应当专家待遇。”“学校里教中医课的按教授待遇。”“有科学基础的西医更应该很好地学习中医,加以研究提高,成为统一的中国医学。”“中药人员应按技术人员待遇。”“哪一级卫生部门做不好这一工作要撤职。”“要扩大中医治疗,中医要参加各大医院的工作。”“大量翻印中医医书,有重点的译成现代文。”这些指示极大地鼓舞了父亲和中医实验所的同仁们。经过反复讨论研究学习中央的精神,1954 年 9 月 29 日上午在北京中医进修学校召开了“中医研究院筹备处关于编制预算讨论会”,讨论了研究院的编制等。
1954 年 10 月,中医研究院筹备处正式成立,父亲任门诊部主任。他们首先从实际出发,逐步开展工作,逐步解决房子和人员问题,从低级到高级,从少数到多数,做好统战工作,服从国家统战工作路线,节约开支。他们的任务是以治疗为主,适当的满足患者要求,从日门诊量 300 人左右逐渐扩大,积累治疗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虚心学习。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父亲经常抽时间遍访老中医,经常和中医名家探讨医技。同时父亲的名声大振,全国各地不少人慕名前来就医,上至领导下至百姓,还有国际友人。他是有求必应,全心全意治病救人。
1956 年 11 月 29 日,在毛主席党中央的关怀下,在北京正式成立了中国中医研究院(当时叫北京中医研究院),地址设在北京广安门内。父亲任内科研究所所长。作为中医研究院的创始人之一,父亲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为之奋斗 40余年的中医终于有了自己的家,祖父的遗愿实现了,父亲的心愿实现了,他高兴啊!他如年轻人一样更加勤奋,更加刻苦学习中外医学的科学理论,更加努力地为更多的病人服务。那一年他被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从此我更难看到父亲的身影,除了正常上班,他还要奔忙于各大医院会诊,还要到许多病人家中诊病、随访,还要和国际友人交流经验(《中医》杂志 1957 年第3期上登载了朝鲜保健省药物局指导员金声屹在中研院与李振三学习内科临床诊断的照片)。1953 年1月至中医研究院成立为止,父亲已治疗了 400 余例肝硬化患者,这些患者大多系全国各大医院确诊,不少重症患者还是被判了“死刑”的,他们经人介绍到父亲那里治疗,经过 2—3年的治疗,基本痊愈者占22.4%(其中包括两例已发生肝昏迷及两例胆管性肝硬变患者都治好了),好转者占 51.7%,好转以上者 占 74.1%, 无 变 化 者 占 10.3%,仅死亡 15.6%。当一位肝病患者在父亲的治疗下起死回生后、当一位苦盼儿子的干部夫妇经他治疗生下了白白胖胖的儿子后、当一位腰腿疼痛缠磨多年经他治疗站起来后,他们对父亲感激、崇敬不知该如何表达时,父亲只是淡淡地一笑:“这是我应该做的,只要你们好了,就好嘛。”他和这些病人都成了永久的好朋友。
父亲得到了同行们的肯定,得到了领导的赞扬,得到了“国家五级医师”、“人民代表”、“中华医学会委员”、“中医学术交流会委员”等称号,可他说:“荣誉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医学有了地位,得到了发扬。重要的是我有这么多的好朋友。”
1957 年以后,父亲想到自己年事已高,开始想到了要总结一些治疗经验,该培养更多的接班人。他将自己治疗肝病(特别是肝硬化)、高血压、妇科病等等的治疗经验汇集成文,如《常山的性能及其临床应用》(发表于《中华医学》杂志1954 年第 11 期)、《高血压病临症初步观察报告》(写于 1956 年11月)、《关于门脉性肝硬化的治疗报告》、《祖国医学治疗急性肝炎和胆管性肝硬变的试验观察》等等。可惜,父亲太忙了,没有更多的时间总结材料,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倒下得那么快。1957 年下半年,一天晚上,我被父亲的咳嗽声惊醒,父亲脸色突变,从来没看见父亲有病的我吓坏了。母亲赶快叫人把父亲送往协和医院治疗,诊为“骨肉瘤”(肋骨已断,这是一种恶性度很高的肿瘤)。父亲倒下了,只知道忙啊忙,从不知道休息的他倒下了,从不知道疲倦,从不知道爱惜自己,把病人看得高于一切的父亲倒下了。他太累了,他要被迫休息了。可是,坚强的父亲并没有真正地倒下,他平静地向母亲、向姐姐、哥哥交代后事,他乐观地谈天说地。他仍然在勇敢地向癌症挑战,他和同仁们共同研究攻克癌症的办法。在当时人们还不怎么认识癌症的情况下,他大胆的给自己开方自己服用中药,使他广泛转移的癌症病体又延长了半年之久。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一天,1958 年 3 月 20 日凌晨,我被母亲的哭声喊醒(当时我因发烧未去上学),我们乘3辆车赶到了北京协和医院高干病房,我哭着大叫了一声”爸爸“,爸爸听到了,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平静地去了,那么安详、那么坦然。那个最最疼爱我的爸爸走了,他走的那么匆忙、那么早,他才 60岁呀!“爸爸太累了,他要休息一下。”幼小的我想:“父亲还会醒过来的。”
父亲的追悼会在北京平安里的一家殡仪馆举行,前来吊唁的有习仲勋等党政领导人,有一起工作过的同仁、有亲朋好友、还有他救治过的好多病人,人群络绎不绝。他们一致赞扬父亲一生忠于中医事业,赞扬他不遗余力为中医研究院的筹备成立做了大量的工作,赞扬他对病人认真负责,废寝忘食,不怕风险,勇挑重担的精神。
父亲被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医中药事业,他的精神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