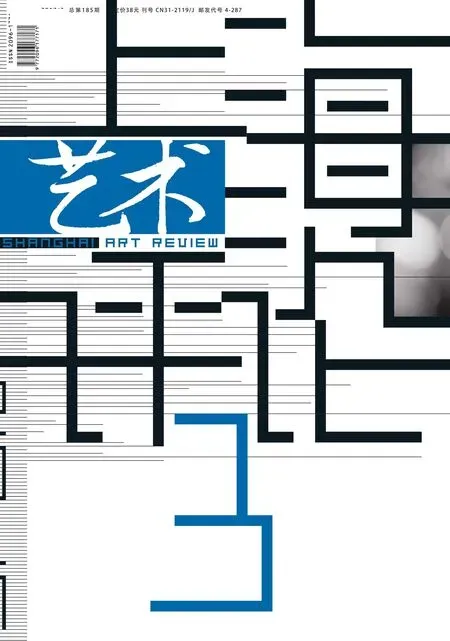创作原创音乐剧,我们还缺什么?
费元洪
创作原创音乐剧,我们还缺什么?
费元洪
一方面,原创音乐剧数量在显著增加,另一方面,品质却没有显著提升,更没有所谓的“爆款”。我们摸索的速度,似乎赶不上时代带给戏剧和观众的挑战。或者说,我们还没有找到原创音乐剧的门路。音乐剧属于世界,当然不只属于百老汇,也不只属于伦敦西区,如何在自身环境中成长出一种音乐剧的新的形态,生出具有自身文化特点的创作手法,这是我们的课题。
上海文化广场举办原创华语音乐剧展演季,已经第六个年头了。六年来,参与作品的数量逐年增加——从两部到七部,从一年两场到今年的27场。对于每年仅有一个多月时间的音乐剧展演季来说,这样的变化,是令人欣喜的。
但也存在另一个事实:这些原创音乐剧中几乎还没出现哪怕一部作品,可以完全依靠市场立足,观众认知也不高。目前,多数的原创音乐剧,还是依靠非市场因素而生存的。比如不少国有文艺院团的作品,国家提供资金、院团创作,唯独缺了市场。大多数作品演出后,便刀枪入库。中国的歌剧、交响、芭蕾也基本如此情形。但与国外成熟产业相比,音乐剧是以当代舞台艺术的姿态出现的,似乎不该这样。一方面,原创音乐剧数量在显著增加,另一方面,品质却没有显著提升,更没有所谓的“爆款”。我们摸索的速度,似乎赶不上时代带给戏剧和观众的挑战。或者说,我们还没有找到原创音乐剧的门路。
作为身处第一线的运作者和策划人,我知道,这个行业的整体提升,当然离不开外在环境的基础。比如:国人可支配收入不高;我们的娱乐消费受到互联网和电影的影响非常大;以及剧场行业在中国发展起步晚,基础并不稳固;还有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音乐剧的接受程度;等等。外因的影响之大、之深远,其实超出行业内普遍的认知。对于音乐剧,我们起步也晚,我们在学习西方,参照亚洲的日本和韩国,努力复制他们走过的道路,行吗?似乎还是个问号。对此我曾撰文《影响中国音乐剧行业发展的几大外因》,说明中国的独特环境和必定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在业界产生了一些共鸣。
今天提到原创音乐剧,当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离不开内因,也即我们自身的创作和制作能力,若这个方面不发展,我们就只能依靠引进海外的音乐剧作品,其结果都是预料之中的,那就是代价高昂、票价居高不下。自身创作能力的提高,无疑是长远发展的关键因素。最重要的是,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用满意的方式,来满意地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
对于创作,短期可以提高吗?完全可能。但取决于基础和视野。创作力的提高,有诸多教育、环境、意识等因素,我们的音乐剧创作,同近百年来的中华文化一样,是在与各种外来文化的冲击之下融合与变化发展的。目前的状态,更像是“东不成,西不就”,既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叙事语言,也没有在技法上有超越西方的创新。我是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的,就我所知,中国会作曲的人不少,但能驾驭音乐戏剧写作的人却不多,因为我们缺少这方面的学习、训练、了解。
中国原创音乐剧有三个技术层面的创作问题,我认为是比较突出的:
首先是音乐剧中的音乐应该如何讲故事。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叙事方法,形成一个中国的创作共识和基础。以致目前大量音乐剧在讲故事上,或者虎头蛇尾,或者轻描淡写,或者拖沓沉闷,不能做到有效、有料、有度。其实这一方面无关灵感,而在于一种常规方法的达成。
如果我们留意来自英、美、德、奥的音乐剧,就会发现这些西方的经典作品往往有相似的创作手法。比如几乎所有英美作品,都会运用大量的音乐主题,反复穿插、重复出现,这些主题像砖块一样,设计出来后,被精心垒成一座音乐剧大厦。砖头好不好看,倒在其次,但选择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建造,是根本的差异。
西方音乐剧的音乐素材,被精心配置的方法有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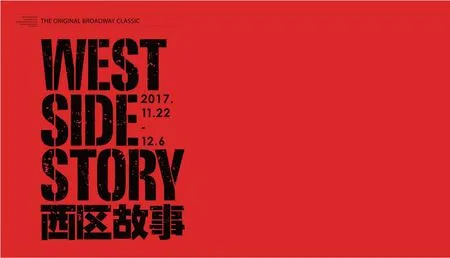
音乐剧《西区故事》演出海报(图片提供:上海文化广场)
比如《悲惨世界》中,有些音乐主题,会伴随孤独的情感出现,角色遇见孤独,便会借用相同的音乐旋律;也有些音乐主题,会伴随救赎的情感出现,每次表达救赎的情感,便有相同的旋律。德语音乐剧《伊丽莎白》中,死亡主题每次出现,必然是与死亡的气息有关。而有趣的是,同样的音乐主题,可以出现在完全不认识的角色身上,却分享着相同的情感。这些显然不是随意的,而是刻意安排的结果。
还有一类手法,是根据人物角色塑造音乐主题,这一手法被古典音乐前辈,特别是瓦格纳丰富地运用在了歌剧创作之中,一路走来,也影响着西方音乐剧的创作。比如《悲惨世界》中的沙威,他的音乐主题是节奏稳定而动机向下的,这个音乐主题就是根据沙威刻板而威严的形象创作的。每当沙威出现,主题就会出现。相反,冉阿让的音乐主题(WHO AM I),则是跳跃的,富有动感和力量的,这表现出人物的灵活和强悍,冉阿让当然必须强悍(不论生理上还是心理上),不然他无法在恶劣的环境中搏击并获得成功。歌曲《待天明》(ONE DAY MORE)中,更是全剧主要人物角色的音乐主题的大荟萃,将故事的悬念和人物的矛盾用音乐推至顶点。
此外,还有惯用的技术手法(它直接影响了音乐风格)。比如《西区故事》强调了增四度和小七度音程的使用,这些刻意的技术手法,使作品充满了独特的音乐质感。《悲惨世界》则特别强调四度音程关系的频繁使用,被大量用在宣叙调之中,形成统一的听觉感受。再比如节奏,《西区故事》中充满了“三拍对应二拍”的“西米奥拉”节奏,独特而不稳定,这颇符合纽约青少年帮派的躁动不安的状态。
其实,一部音乐剧里的各类旋律,也是相互关联的,一个旋律主题,一转型(比如大调变小调,或音程关系的调整),就可以转变成为另一个旋律的动机,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然后旋律不断衍生。此外,常用的音型、和声、配器,等等,都应该是作曲家精心设计的,而非随意为之。
以上这些,是西方音乐剧惯用的创作手法,用得好不好是其次,但管用。其最大功效,是让音乐成为一个整体,有系统,有关联,在情感上和听觉上产生回响与共鸣。
第二个方面,是原创音乐剧的整体戏剧节奏和结构普遍拖沓。
大多数原创音乐剧往往开局不错,因为需要介绍角色人物出场,自报家门,这与其他经典作品并无不同。但不知为何,每当角色开始发展,线索铺开时,中国原创音乐剧的叙事节奏就慢了下来,以至于常常不是故事带着观众走,而是观众对故事的节奏和变化感到厌倦。
故事的线索很重要,但如何将线索有机穿插在一起更重要。因为有了音乐的介入,让中国的编剧,特别是音乐思维比较弱的编剧,不容易编出“线索交织,角色也交织”的剧本。那种前几拍是一个角色唱,后几拍就换个角色唱,或者让音乐旋律暂时中断,去呈现另一件事,然后再回过头来继续讲述下去的能力——这是我们所缺乏的。有很多用几分钟讲一件事,再用几分钟讲另一件事,唯独不能用几分钟把两件事或者几件事一起讲了。这样叙事的速度和复杂度自然就弱了。这方面创作者显然需要综合思维,因为一部音乐剧历来不是一个人的安排,而是词曲、编剧及导演综合的结果。
好的作品是对观众智力和情感的挑战,而差的作品则让观众疲惫。这一点上,西方音乐剧给出了很好的解答,那便是注重故事的结构、节奏、线索,比如开场曲大致几分钟?第一个悬念大约出现在哪里?第二个矛盾大约出现在哪里?每个矛盾大约持续几分钟?以什么样式呈现?都会大致有个框架。这不应该被看作教条,而是推动故事前进的方法之一。
还比如全剧高潮点在哪里?在西方音乐剧里,有11点歌(11 o’clock SONG)的说法,也就是演出结束前的15分钟,一般是全剧高潮的共情点,因为之后故事就要准备收尾了。戏剧安排了几条线索?如何并置和推进?哪些线索一笔带过,哪些需要深挖?这其中都和节奏与结构有关。在整体安排上,第一幕多长?第二幕多长?以什么悬念来结束第一幕?这些都是有规划的,大的结构必然会影响小的结构,这样创作节奏就不会拖沓。创作者当然要有自己的感觉,但我要说的是,创作再尽兴,也要有规划,大的框架定好了,不能任由灵感发挥,让作品成为不受控的风筝。
第三个方面是人物塑造。
人物自己会说话。太多的小说,像沈从文的《边城》或是阿城的《棋王》,都是描写人的,当人物丰满了,你会感觉故事是次要的。而中国很多原创音乐剧的人物塑造,往往不自觉会带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刻意”,脸谱化。一个角色,你不知道她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性格是天生和固定的,还有令人生厌的套路感。很多中国演员的表演很容易拿腔拿调,煞有介事的样子(也许是从小就缺少真诚表达的机会吧),表达既不真实,也不流动。
在这一方面,法国音乐剧给了我们启示,比如《巴黎圣母院》,虽然法国音乐剧有崇尚写意而轻视叙事的传统,但它的每个人物是如此鲜活,格调极高,人物的对话非常不具体,却直指人心,反倒显得崇高。当人物立起来了,人物就自己会讲话,观众也能够自行弥补那些戏剧叙事留下的空白。
在西方音乐剧中,一般开场不久,便会有主角演出的“I AM SONG”(讲述角色身份)和“I WANT SONG”(表达角色的愿望),构成故事发展的基本动力,之后进入变化,让人物带着故事发展、变化、转折,增强戏剧的动力,随着各线索的进展,生出与观众共情的时刻。我们笔下的人物也需要动机,看他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让人物鲜活和流动起来。
以上是我认为中国原创音乐剧比较薄弱的地方。西方音乐剧很多方式值得我们借鉴,做得高级与否是一回事,但要做到有效,其实并没那么难,只是需要多学习和多练习。
音乐剧属于世界,当然不只属于百老汇,也不只属于伦敦西区,如何在自身环境中成长出一种音乐剧的新的形态,生出具有自身文化特点的创作手法,这是我们的课题。就像法语音乐剧和德奥音乐剧一样,虽受到百老汇和伦敦西区的影响,但更多是从自身的文化环境中长出一朵属于自己文化风格的花朵,一部部作品,都是在彰显自己的艺术价值和高度。
近六七十年来,伴随全球化和电力革命,西方流行音乐的体系以其现代感和“科学性”,成为了全球主流的音乐语汇,我们的听觉在接受这一套体系,是无需回避的。当然,我们有我们的审美,以及东方音乐的独特风格,但对于音乐剧,我们起步晚,对西方音乐剧的戏剧音乐创作技法的研究,是需要学习和借鉴的。我们需要在技术上学习,在创作中融合,也在听觉上认证。可惜大多数原创音乐剧的词曲作者并不了解这些,我们用了西方的作曲体系创作,用五线谱写下音符,沉浸在自己的灵感和判断之中,却不去了解一些行之有效的创作方法,这是很可惜的。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学习和了解不同创作的音乐手法,是创作的重要一步。
如今我们的文化自信,不是要独尊自己的文化,更不是要去取代别人的文化来体现优越感;而是知道只有自己的文化才最适合我们,也知道必须放心大胆地去学习和借鉴他国的文化,是为丰富我们自己的审美和语言。音乐剧正处于这样一个阶段,作为一个兼容并蓄的当代艺术门类,在我们寻找自己的创作语言和方法的过程中,狭隘的民族主义要不得,全盘的西化也不必要,不断地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不断融合、创新,必将赢来中国原创音乐剧的美好未来。
作者 上海文化广场副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