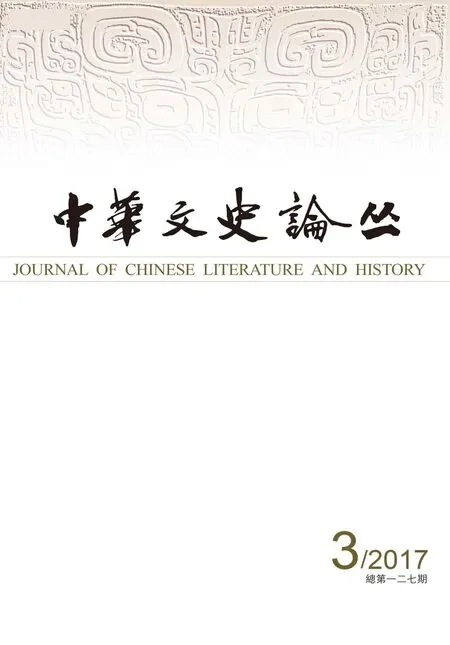劉廣之亂與晚唐昭義軍
——兼論唐代藩鎮變亂模式的演化❋
仇鹿鳴
提要: 新近刊佈的《李裔墓誌》爲研究晚唐昭義軍的劉廣之亂提供了重要的新史料。在會昌伐叛成功三十年後,劉廣仍能以劉稹之後的名義號召起事,證明唐廷此前的善後措施並不成功。出土的墓誌材料也表明,李德裕雖然誅殺了劉稹家族及其親信,但無法真正改變昭義軍的結構,正是劉氏統治昭義時期的厚加賞賜造成了昭義軍的“驕兵化”。中晚唐的藩鎮變亂可以畫分爲“政治性反叛”與“經濟性騷亂”兩種類型,前者以割據自立爲政治目標,劉稹之亂便是典型的案例;“經濟性騷亂”發生的頻度在晚唐日漸提高,反映“驕兵化”藩鎮將士自利性的訴求。會昌伐叛成功後,昭義呈現出“經濟性叛亂”頻繁發生的局面,與前期有了顯著的變化。
關鍵詞:《李裔墓誌》 昭義 變亂模式
昭義軍作爲唐王朝防遏河朔三鎮所設立的藩鎮,由於其横跨太行山兩麓的獨特政區規畫及重要的戰略地位,已引起不少學者的關注,但總體而言,研究的重點仍集中於辨析昭義軍控遏河朔三鎮的成效與武宗時平定劉稹之亂這兩個議題。*其中代表性的研究可以舉出森部豐《藩鎮昭義軍の成立過程について》,野口鐵郎編《中國史における教と國家》,東京,雄山閣,1994年,頁207—229;森部豐《唐沢潞昭義軍節度使考——中晚唐期における唐朝と河北藩鎮の關係をめぐって》,野口鐵郎先生古稀記念集刊行委員會編《中華世界の歷史的展開》,汲古書院,東京,2002年,頁97—131;張正田《“中原”邊緣——唐代昭義軍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2007年;陳翔《關於唐代澤潞鎮的幾個問題》,《陳翔唐史研究文存》,新北,花木蘭出版社,2013年,頁149—204;王國堯《李德裕與澤潞之役——兼論唐朝於9世紀中所處之政治困局》,《唐研究》(12),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487—521。對於會昌平叛成功之後,晚唐昭義軍的變遷,儘管已有學者指出在唐武宗平定劉稹後,昭義軍的節度使改由文官出任,而且多不久任,朝廷控制得到强化,但另一方面,鎮内動蕩不安,多次發生驕兵逐殺節帥事件,與前期的穩定形成鮮明對比。*森部豐《唐沢潞昭義軍節度使考——中晚唐期における唐朝と河北藩鎮の關係をめぐって》,《中華世界の歷史的展開》,頁103—104;張正田《“中原”邊緣——唐代昭義軍研究》,頁182—189。遺憾的是,由於武宗以後,實録修纂時斷時續,晚唐昭義軍的諸次兵亂不但記載寥落,而且舛亂不少,阻礙了學者進一步細化研究。以本文討論的劉廣之亂爲例,新舊《唐書》皆將其與中和元年(881)在昭義軍發生的成麟驅逐高鄩一事相混淆,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鑑》時爲辨明兩事特意撰寫了長篇考證:
《實録》:“澤潞牙將劉廣據潞州叛,天井關戍將孟方立帥戍卒攻廣,殺之,自稱留後,仍移軍額於邢州。初,高潯援京師,廣帥師至陽平,謀爲亂,不行,還據潞州,自稱留後,用法嚴酷,三軍畏之。方立乘虚襲殺焉。”又曰:“貶昭義節度使高潯爲端州刺史。”中和三年《實録》又曰:“初,孟方立殺高潯自立。”薛居正《五代史·方立傳》曰:“中和二年,爲澤州天井關戍將,時黄巢犯關輔,州郡易帥有同博弈。先是,沈詢、高湜相繼爲昭義節度,怠於軍政,及有歸秦、劉廣之亂,方立見潞帥交代之際,乘其無備,率戍兵徑入潞州,自稱留後。”《新紀》:“八月,昭義軍節度使高潯及黄巢戰於石橋,敗績,十將成麟殺潯,入於潞州。九月,己巳,昭義軍戍將孟方立殺成麟,自稱留後。”《方立傳》惟以成麟爲成鄰,餘如《新紀》。按乾符二年《實録》:“十月,昭義軍亂,逐節度使高湜,貶湜象州司户。”《柳玭傳》云“貶高要尉”。三年十一月,詔魏博韓簡云,“劉廣逐帥擅權”云云。是廣逐湜,擅據潞州也。《薛史·孟方立傳》亦云沈詢、高湜怠於軍政,致有歸秦、劉廣之亂,是廣亂在前也。《舊紀》:“九月,高潯牙將劉廣擅還據潞州。是月,潯天井關戍將孟方立攻廣,殺之,自稱留後,貶潯端州刺史。”此蓋《舊紀》誤,《實録》因之。《薛史·方立傳》曰:“見潞帥交代之際,帥兵入潞州。”不言何帥交代,若不逐帥,何能據州!事無所因,殊爲疏略。《舊紀》恐是誤以高湜事爲高潯事。《實録》此云殺廣,明年又云殺潯,自相違。《新紀》、《傳》皆云成麟殺潯,方立斬麟,月日事實頗詳,必有所出。今從之。*《資治通鑑》卷二五四唐僖宗中和元年(881),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頁8258—8259。
據《通鑑考異》引文可知,兩事在史源上已發生混淆,《實録》記載本身便自相牴牾,新舊《唐書》皆承《實録》之誤。儘管經司馬光的考訂,初步釐清了兩事的不同,但對劉廣之亂的始末,温公亦未能檢獲更多的史料。僅於《通鑑》乾符二年(875)十月條下記:“昭義軍亂,大將劉廣逐節度使高湜,自爲留後。以左金吾大將軍曹翔爲昭義節度使。”*《通鑑》卷二五二,頁8181。其所據者,便是《通鑑考異》所引及的乾符二年《實録》。在此背景下,新出碑誌對於研究晚唐昭義軍的價值,便不再僅僅停留在作爲傳世文獻附庸的補史、證史層面,而是成爲重建史實的基本依據。近年,西安市長安博物館刊佈《李裔墓誌》便爲廓清劉廣之亂的前後因果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李裔墓誌》,拓本刊西安市長安博物館編《長安新出墓誌》,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頁316。以此爲中心,結合其他相關碑誌,有助於廓清晚唐昭義軍的不少疑問。墓誌長、寬各60釐米,39行,滿行36字,兹先據拓本迻録誌文如下:
唐故隨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贈尚書考功郎中賜緋魚袋隴西李府君墓誌銘并序」
再從兄將仕郎前守尚書倉部員外郎鉅撰」

玉葉茂族,樞衡貴門。龍章鳳姿,□□王孫。有是俊造,瑩若璵璠。行馥枝葉」,學洞根源。貳過無兆,九思而言。□□□美,未伸逸翰。再遇紛擾,竟因戕殘。」福仁莫保,與善寧論。于郊半舍,□□□原。卜兹封樹,永閟幽寃。」
朝請郎守監察御史黯書」
一
誌主李裔雖不見於載籍,但家世顯赫,出身宗室大鄭王房,其父李福大和中進士及第,累歷方鎮,位至使相。李福兄李石更爲當時名相,兄弟兩人並位極人臣,子孫榮顯,門第清貴,爲時人所稱羡:
唐盛唐令李鵬遇桑道茂,曰: 長官只此一邑而已,賢郎二人,大者位極人臣,次者殆於數鎮,子孫百世,後如其言。長子石出入將相,子孫二世及第。至次子福,歷七鎮,終於使相。凡八男,三人及第,至尚書、給諫、郡牧,諸孫皆朱紫。*《太平廣記》卷七六引《劇談録》,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頁480。按此事傳佈甚廣,又載《北夢瑣言》卷一,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209。宋人纂修《新唐書·桑道茂傳》時,亦援據此類小説,將此事增益其中,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5813。
時又有三枝槐之説:
相國李福,河中永樂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過堂前屋脊,一枝不及。相國同堂兄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第宰執,惟福一人,歷七鎮使相而已。*《酉陽雜俎續集》卷一《支植下》,許逸民《酉陽雜俎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頁2125。除《酉陽雜俎》所載之外,《北夢瑣言》卷三亦引録,可知流傳頗廣。
這一系列傳説的演繹流播,正反映出李石兄弟在當時的顯貴。《劇談録》云李福八子,及第者三人。《新唐書·宗室世系表上》記其中六人: 就、扶、玩、黯、航、涪,*《新唐書》卷七上,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2020—2021。墓誌云李裔爲第三子,恰爲失載者之一。其及第三人中,可考者僅李涪。《北夢瑣言》卷九:“唐李涪尚書,福相之子,以《開元禮》及第。”*《北夢瑣言》卷九,頁198。誌文雖云李裔:“自《何論》、《毛氏詩》、《左氏春秋》,莫不貫穿義理,窮討旨奧。以至班馬二史,開卷閲視,如素習者”,但其所擅長者大抵是明經、三史之科,而非考取進士所講求的詩賦文章,故發現仲兄李扶屈於名場,久不售後,轉而選擇以門蔭入仕,釋褐河南府鞏縣尉。誌文云:“時相國在洛”,考李福事迹,其於咸通五年(864),自刑部尚書、鹽鐵轉運使任上出爲西川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但至咸通七年四月便因處置與南詔關係失當,爲蠻所敗,遭貶爲蘄王傅、分司東都。李裔在鞏縣尉任上因勤政而受到盧攜的賞識,並以從祖兄女妻之。盧攜,《舊唐書》本傳載其歷官:“咸通中,入朝爲右拾遺、殿中侍御史,累轉員外郎中、長安縣令、鄭州刺史。”*《舊唐書》卷一七八《盧攜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4638。未記曾宰洛陽,據《太平廣記》引《聞奇録》“後攜官除洛陽縣令,?兩改鄭州刺史”,*《太平廣記》卷一七七引《聞奇録》,頁1318—1319。則盧攜在遷鄭州刺史前,尚曾任洛陽縣令,恰與誌文所云“今分洛賓護相國盧公携時宰洛陽”相合。李裔墓誌撰於乾符六年(879)閏十月,此時盧攜身份爲“今分洛賓護相國”,蓋指其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乾符六年五月,“宰相鄭畋、盧攜爭論於中書,詞語不遜,俱罷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至是年十二月,復被招入長安爲相,*《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頁703,704。亦與史文相合。
由於鞏縣尉任滿之後需守選,中晚唐士人往往選擇轉任幕職,作爲仕進之階,身爲公卿子弟的李裔無疑不乏這方面的機遇,“白馬杜尚書慆奏署幕職,未之任,拜秘書郎”,杜慆因在龐勛之亂中堅守泗州有功,咸通十一年(870)正月“以檢校左散騎常侍、泗州刺史杜慆檢校工部尚書、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鄭滑觀察等使”,*《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頁674。李裔滑州幕之辟當在此時,但其並未之任。
爾後,高湜出鎮昭義時,再次辟舉李裔爲支使,並奏授檢校禮部員外郎的朝銜。高湜出身於中晚唐一個典型因科舉興起的詞臣家族,《新唐書》本傳云“史失其何所人”,*《新唐書》卷一七七,頁5276。但其父高釴、叔高銖、高鍇皆進士及第,高釴穆宗時曾任翰林學士,由此步入清流士大夫的行列。*因此目前所見幾方高釴家族的墓誌已皆云其出自渤海高氏,熟練地運用士族的語彙裝點其先世。另關於唐代因進士崛起的詞臣家族,參讀陸揚《論唐五代社會與政治中的詞臣與詞臣家族》,《清流文化與唐帝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283—304。至高湜時,不但已擺脱了其父“孤貞無黨”的形象,更被深深地捲入朝廷的黨爭之中。高湜本人亦進士及第,在朝中黨附於路巖,與厚於劉瞻的從弟高湘分屬兩派,兄弟鬩牆:
及咸通,韋保衡、路巖作相,除不附己者十司户: 崔沆循州、李瀆繡州、蕭遘播州、崔彦融雷州、高湘高州、張顔潘州、李貺勤州、杜裔休端州、鄭彦持義州、李藻費州,内繡州、潘州、雷州三人不廻。初高湜與弟湘少不相睦。咸通末,既出高州,湜雅與路巖相善,見巖,陽救湘。巖曰:“某與舍人皆是京兆府荷枷者。”先是劉瞻志欲除巖,温璋希旨,别製新枷數十待之。瞻以人情附己,不甚緘密,其計泄焉,故居巖之後。*《新輯玉泉子》,收入《奉天録(外三種)》,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123。另參《通鑑》卷二五二唐咸通十一年,頁8160。
路巖擊倒政敵劉瞻,放逐十司馬事在咸通十一年九月,次月便下詔“以中書舍人高湜權知禮部貢舉”,*《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頁676。而此次選舉恰爲路巖所操縱:
湜既知舉,問巖所欲言。時巖以去年停舉,已潜奏恐有遺滯,請加十人矣,即托湜以五人。湜喜其數寡,形於言色。不累日,十人敕下,湜未知之也。巖執詔,笑謂湜曰:“前者五人,侍郎所惠也;今之十人,某自致也。”湜竟依其數放焉。*《新輯玉泉子》,收入《奉天録(外三種)》,頁123。
咸通十年(869)科舉取士因受龐勛起兵的影響而暫停,故次年取進士四十人,較往年多出十人,但其中竟有十五人係路巖所托,高湜與路巖兩人實互爲狼狽,故其得典選舉與之前中樞時局的變化無疑有密切的關聯。
高湜出鎮昭義軍的背景雖缺乏直接史料佐證,但略考當時中樞格局的演變,不難窺見政治氣候的改易。咸通十二年四月,路巖因與原來的政治盟友韋保衡失和,被外放爲西川節度使,*《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頁677。但這似乎並没有影響到高湜的前途。前引《新唐書》本傳云其在以禮部侍郎典選之後,被擢爲兵部侍郎、判度支,*《新唐書》卷一七七《高釴傳附高湜》,頁5276。從一個可能入相的位置被外放爲藩鎮節帥,多少藴含了貶謫之意。另一方面,路巖在外放之初,亦未完全失寵,於咸通十四年五月加兼中書令。七月懿宗去世,僖宗繼位。九月,路巖仍循慣例與其他藩鎮節帥一起獲得加官,兼侍中,但至是年十一月,便被人檢舉有異圖,徙爲荆南節度使,十二月,再貶新州刺史,並於次年正月長流儋州,賜自盡。幾乎與此同時,咸通十四年九月,路巖曾經的盟友韋保衡被貶爲賀州刺史,十月再貶崖州澄邁令,進而賜死。*《通鑑》卷二五二,頁8165—8167。而昔日的政敵劉瞻及高湘則被自貶所召回。*《通鑑》卷二五二,頁8170;《新唐書》卷一七七《高釴傳附高湘》,頁5277。這一系列人事調整與高湜咸通十五年春出鎮昭義的時間非常接近。此外,從高湜子高彬的歷官中,亦能窺見些許蹊蹺,“未幾,相國秉鈞,遄加集賢殿大學士,遂奏授秘書郎、充修撰。咸通十五年春,尚書公出鎮潞州,堅欲棄官侍行”,*《高彬墓誌》,拓片刊《洛陽新出歷代墓誌輯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頁710;録文見吴鋼主編《全唐文補遺》(6),西安,三秦出版社,1999年,頁197上。此處相國指的是劉鄴,其初受知於李德裕,懿宗朝依附韋保衡、路巖而致高位,*《通鑑》卷二五二,頁8170。入相在咸通十三年正月。*《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頁679。高彬見知於劉鄴,蓋是朋黨援引之故。兩年後,高彬卻因其父外鎮,欲辭官侍親,雖未成行,但此舉在當時頗爲罕見。*一般僅有在父親老邁多病時,方有棄官侍養之舉,如“左拾遺王龜以父興元節度使起年高,乞休官侍養”,《舊唐書》卷一八上《武宗紀》,頁609。以上這些人事更迭都可以被視爲僖宗登基後政治更新的一部分,但這一變化無疑不利於在懿宗晚年得勢的高湜及其盟友。
另一方面,目前所見史料中對咸通中期以降昭義軍節度使人選的記載舛誤尤多,儘管吴廷燮《唐方鎮年表》據《通鑑》記咸通五年正月以李蠙取代被刺的沈詢爲昭義軍節度使條後,先後羅列了盧匡、高湜、張彦遠、高湜四任節帥,*吴廷燮《唐方鎮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490—492。其中高湜兩鎮昭義。但可靠的記載不過以下數條,且缺乏明確的繫年:
咸通末,(高湜)爲禮部侍郎。時士多繇權要干請,湜不能裁,既而抵帽於地曰∶“吾決以至公取之,得譴固吾分!”乃取公乘億、許棠、聶夷中等。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出爲昭義節度使,爲下所逐,貶連州司馬。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卒。*《新唐書》卷一七七《高釴傳附高湜》,頁5276。一般而言《舊唐書》本傳多依據實録國史改寫,記事較爲可靠,但《舊唐書·高湜傳》:“釴子湜,鍇子湘,偕登進士第。湜,咸通十二年爲禮部侍郎。湘自員外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咸通年,改諫議大夫。坐宰相劉瞻親厚,貶高州司馬。乾符初,復爲中書舍人。三年,遷禮部侍郎,選士得人。出爲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義節度、澤潞觀察等使,卒。”頁4388。將兩人事迹編入同傳,以致眉目不清。其中最後一句“出爲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義節度、澤潞觀察等使,卒”係指高湜,而非高湘。《新唐書》本傳則敍事較有條理,故取新傳。
湜出鎮澤潞,奏爲節度副使。入爲殿中侍御史。李蔚鎮襄陽,辟爲掌書記。湜再鎮澤潞,復爲副使。*《舊唐書》卷一一五《柳玭傳》,頁4308。《新唐書》卷一六三《柳玭傳》略同,但未記嘗歷李蔚幕府。
新舊《唐書》在《高釴傳》後附録其子高湜事迹,但未及高湜兩次出鎮昭義,此事僅見於《柳玭傳》,並云柳玭兩任昭義幕職間,曾歷李蔚幕府,故若能考知李蔚出鎮襄陽的年月,則大體能推定高湜先後兩度出鎮昭義的時間。此事見《舊唐書·李蔚傳》,“尋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與盧攜、鄭畋同輔政。罷相,出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舊唐書》卷一七八《李蔚傳》,頁4627。據上下文,約繫於咸通中。然而,這一記載相當可疑,首先是李蔚入相、罷相的時間,《新唐書》、《通鑑》皆繫於乾符二年(875)及五年,*《新唐書》卷九《僖宗紀》,頁265、268,卷六三《宰相表》下,頁1742;《通鑑》卷二五二,頁8301,卷二五三,頁8330。另《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記入相於乾符三年,頁695。本傳所云同時爲相者盧攜、鄭畋皆乾符間居相位,則罷相出鎮襄陽事當在乾符五年以後。《唐書合鈔》便已注意到這一牴牾,云“自太常卿以下至此,疑當在下文乾符四年上”。*《唐書合鈔》卷二二九,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年,頁1221。其次,李蔚罷相後,是否曾出鎮襄陽亦存在疑問,《舊唐書·僖宗紀》、《新唐書》本傳及《宰相表》、《通鑑》皆記其“罷爲東都留守”。*《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頁702;《新唐書》卷六三《宰相表下》,頁1742,卷一八一《李蔚傳》,頁5354;《通鑑》卷二五三,頁8209。乾符五年,王仙芝已縱横南方,時出鎮山南東道,參與鎮壓者正是李裔之父李福,故《唐方鎮年表》山南東道條下未列李蔚,*吴廷燮《唐方鎮年表》,頁645。李蔚罷相出鎮襄陽事很可能是出於誤記。另一方面,乾符六年二月,因爲前任節度使李鈞敗死,“辛巳,以陝虢觀察使高潯爲昭義節度使”,*《通鑑》卷二五三,頁8212。則於乾符五年後出鎮昭義者係高潯而非高湜,《柳玭傳》的記事很有可能與《通鑑考異》所引《實録》一樣混淆了高湜與高鄩兩人。事實上,高湜在咸通前期,名位尚輕,驟登昭義節帥高位而又爲本傳失記的可能性極小。如此則大致可以推定高湜僅在咸通末出鎮昭義一次。
至於盧匡、張彦遠兩人,並無確實依據,皆據《尚書故實》推定:
王内史《借船帖》,書之尤工者也。故山北盧尚書匡寶惜有年。公致書借之不得,云:“只可就看,未嘗借人也。”公除潞州,旌節在途,纔數程,忽有人將書帖就公求書。閲之,乃《借船帖》也。公驚異問之,云:“盧家郎君要錢,遣賣耳。”……盧公,韓太沖外孫也。*《尚書故實》,收入《唐五代筆記小説大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1167。字下點爲筆者所加。
山北係昭義代稱,此爲盧匡嘗歷澤潞的依據。由於《尚書故實》一書係李綽記賓護尚書河東張公談話而成,故四庫館臣認爲公乃張尚書自稱。《提要》云:“觀其言賓護移知廣陵,又言公除潞州旌節,則必嘗爲揚州刺史、昭義節度使者。”*《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65年,頁1034上。吴廷燮當受説影響,以爲張彦遠也曾歷澤潞。事實上,書中的賓護尚書河東張公究竟係何人,學界並無定論,余嘉錫以“賓護”爲尚書河東張公之名,考其爲張彦遠諸兄弟。*余嘉錫《四庫提要辯證》,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914。近年,陶敏指出“賓護”代指太子賓客,係官名,復考其爲張彦遠,*陶敏《尚書故實中“張賓護”考》,《唐代文學與文獻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660—668。但兩説都缺乏充分的書證。
另一方面,引文中的“公”是否確指河東張公其實也存在相當疑問,《尚書故實》中此則,通行文本即有三種,除了前引之外,《太平廣記》卷二九引録《尚書故實》云:
王羲之《借船帖》,書之尤工者也。故山北盧匡寶惜有年。盧公致書借之,不得,云:“只可就看,未嘗借人也。”盧除潞州,旌節在途,纔數程,忽有人將書帖就盧求售。閲之,乃《借船帖》也。驚異問之,云:“盧家郎君要錢,遣賣耳。”……盧公,韓太仲外孫也。*《太平廣記》卷二九引《尚書故實》,頁1600。字下點爲筆者所加。
前引《尚書故實》中三處“公”字,《太平廣記》引文中第一處作“盧公”、後兩處作“盧”,*檢《太平廣記會校》此三處皆無異文,張國風《太平廣記會校》,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年,頁3201—3202。即故事由兩位盧姓主人公演繹,並無張公出場。今本《劉賓客嘉話録》真僞摻雜,竄入多條《尚書故實》文字,其中亦有此則:
王内史《借船帖》,書之尤工者也。故盧公尚書寶惜有年矣。張賓獲致書借之不得,云:“只可就看,未嘗借人也。”盧公除潞州,旌節在途,纔數程,忽有人將書帖就公求售。閲之,乃《借船帖》也。公驚異問之,云:“盧家郎君要錢,遣賣耳。”*唐蘭《〈劉賓客嘉話録〉的校輯與辨僞》,《文史》第4輯(1965年),頁97。字下點爲筆者所加。
竄入《劉賓客嘉話録》這一則文字雖誤“護”爲“獲”,但來源甚早,宋人編録《紺珠集》、《類説》時皆引録,《説郛》本亦出於此。辨析這三種文本,以《劉賓客嘉話録》所引文意完足,雖自宋代便竄入《劉賓客嘉話録》,但仍保存了較爲原始的文本面貌。*前引唐蘭文云《太平廣記》“公”字均作“盧公”,誤也。陶敏主編《全唐五代筆記》中《尚書故實》即據《劉賓客嘉話録》訂正相關文字,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年,頁2292。據此嘗出鎮昭義者僅盧匡,與張賓護無干。盧匡其人,見於郎官石柱題名“司封郎中”、“吏部郎中”條下,*勞格、趙鉞《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頁273,574。《舊唐書·懿宗紀》咸通八年(867)有吏部侍郎盧匡,*《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頁663。咸通八年《盧公弼墓誌》云:“今吏部匡,皆府君之猶子”,亦可證。周紹良編《唐代墓誌彙編》咸通058,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2423。《桂林風土記》“拜表亭”下云:“前政山北盧尚書匡添建置”,*《桂林風土記》,明謝氏小草齋鈔本,亦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589册,頁68下。則其鎮昭義前嘗歷桂管。《寶刻類編》卷六會昌五年(845)盧匡書《修文宣王廟碑》、《修文宣王廟記》,*《寶刻類編》卷六,叢書集成本,1514册,頁185。知其本人亦善書法,其外祖父即著名的畫家韓滉。考其經歷,活躍於武宗、宣宗、懿宗各朝,不過《尚書故實》並未記載盧匡出鎮昭義的具體時間,吴廷燮繫於咸通中後期乃屬以己意推測。新見昭義軍將《李文益墓誌》云“大中五年,范陽尚書遷洺州防城使”,*《李文益墓誌》,拓片刊《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彙編》,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頁771。疑誌文中的范陽尚書即指盧匡,則盧匡出鎮昭義在宣宗朝。因此,咸通五年至乾符初,昭義軍確切可考的節帥實際上僅高湜一人。
幸而藉助出土墓誌,我們已可以確定高湜出鎮昭義的具體時間。前引《高彬墓誌》明確記載:“咸通十五年春,尚書公出鎮潞州。”至於高湜因劉廣之亂被貶離開昭義的時間,傳世文獻中有兩説,《通鑑》繫其事於乾符二年(875)十月,《新唐書》繫於乾符四年閏二月,*《通鑑》卷二五二,頁8181;《新唐書》卷九《僖宗紀》,頁266。學者以信從《通鑑》者居多。*吴廷燮《唐方鎮年表》,頁492;陳翔《關於唐代澤潞鎮的幾個問題》,《陳翔唐史研究文存》,頁180。但現據墓誌資料,可知當以《新唐書》爲正,高湜兄高瀚妻崔縝葬於乾符三年二月二十四日,誌文由高湜親撰,署“昭義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潞磁邢洺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上柱國蓨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高湜纂”,*丁永俊《唐高瀚及夫人崔縝墓誌考釋》,《河洛春秋》2002年第2期,頁10—18。可知高湜乾符三年初仍在潞州任上,其子高彬卒於乾符四年七月,時高湜已遭貶爲□崖郡司馬,其妻陳氏正是受此刺激病情加重,“殆至委頓”,高彬因服侍湯藥,操勞過度而染疾去世,則事當在此前不久。
《李裔墓誌》云“到職半歲,值劉廣亂”,則其至昭義赴任的時間約在乾符三年下半年。至於高湜爲何選辟李裔爲支使,而李裔在未赴杜慆義成軍僚佐之任後,爲何最終接受高湜的徵辟,前往潞州,目前我們尚無直接的史料可以證實兩家之間的政治聯繫。但若仔細觀察,我們可以注意到兩家在文化取向上有一些相近之處,高湜、李裔都是因進士科第得以在中晚唐政治中嶄露頭角,但有意思的是當這兩家因科舉而躋身於清流之列後,其第二、三代成員,卻與科舉保持了微妙的距離。上文已提及李裔“以仲兄屈於名場,年甫壯歲,方捨志業筮仕”,選擇以門蔭入仕,而《高彬墓誌》則云:“自長兄柷舉進士,府君以時風寢薄,□仲有同趨詞壤,求一第,或致紳間異論,遂堅請於尚書公,願以門蔭筮仕,俸錢爲婚娶之資,選授蘇州華亭縣尉”,*《全唐文補遺》(6),頁196下。同樣選擇了門蔭入仕。如果説高湜兄高瀚“二十從鄉賦,凡六就春官試,屬時宰有薄進士者,尤恚公卿子弟用是進,亟言於武宗皇帝,主司惴不敢第”,*《高瀚墓誌》,《唐代墓誌彙編》大中105,頁2332。因李德裕厭惡進士浮華而久不售,被迫另謀出路,那麽至高彬、李裔時,政治氣候早已發生變化,他們的選擇有更多的主動色彩。此外,高湜主持咸通十二年(871)科考時,所取四十人中儘管有十五人係路巖請托,但榜内孤貧有才名者有公乘億、許棠、聶夷中等三人,如公乘億已垂三十舉不第,*《唐摭言》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頁88。一時轟動海内。中晚唐進士取士過程中“子弟”與“孤寒”之爭,與當時政治中的黨派分野、人事安排有着密切的關聯,高湜、李裔兩家對於進士詞科似乎有着接近的立場。
二
儘管離開了政治舞臺的中心,高湜在昭義任上的前三年也算是過得風平浪靜,直至乾符四年二月不意發生了劉廣之亂,高湜遭亂兵驅逐,劉廣自立爲留後。對於此事的前後經過,《李裔墓誌》有較詳盡的記録,稍可彌補傳世文獻的不足,尤可貴者是保存了劉廣的出身及起兵的號召:
始,劉廣不知何人也,來自薊門,客於山北,常寓食將卒之家,有無良怙亂之徒,昌言於軍伍中,云是劉稹之族。
誌文提示我們劉廣是以劉稹之後的身份進行政治動員,煽動起事,進而成功驅逐高湜。會昌三年(843),武宗與李德裕君臣同心,力排衆議,斷然拒絶劉稹襲位的請求,協調各懷顧望的藩鎮軍隊,經過一年多的苦戰,平定昭義,改變劉悟、劉從諫、劉稹三代據有澤潞的局面,成功遏制了昭義軍“河朔化”的傾向。*傅璇琮《李德裕年譜》,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363—428;王國堯《李德裕與澤潞之役——兼論唐朝於9世紀中所處之政治困局》一文對唐廷平定昭義的過程論述甚詳,但除了割澤州隸河陽外,並未論及其他唐廷平定劉稹後的善後舉措,《唐研究》(12),頁487—521。此役一般被視爲憲宗中興之後,唐廷對藩鎮所取得的最重要勝利。乾符四年的劉廣之亂,上距會昌伐叛已有三十餘年,按照古人三十年爲一世的算法,已整整過去了一代人的時間,甚至也超過了劉悟祖孫三代統治昭義時間的總合。但直至此時劉稹依然是昭義軍中一個具有號召力的政治符號,這與之前慣常的對昭義軍“忠義”的印象不符,提示我們需要重新檢討唐廷平定昭義之後善後舉措的得失,同時也爲進一步認識晚唐昭義軍内部的構造提供了一個窗口。
會昌伐叛成功之後,在李德裕的主持下,圍繞着如何杜絶劉氏割據昭義局面的重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不但“稹族屬昆仲九人,皆誅”,*《舊唐書》卷一六一《劉稹傳》,頁4233。事實上,郭誼謀殺劉稹後,“悉取從諫子在襁褓者二十餘,并從子積、匡周等殺之。誅張谷、張沿、陳揚庭、李仲京、王渥、王羽、韓茂章、茂實、賈庠、郭台、甄戈十一族,夷之,軍中素不附者皆殺”,已進行過一輪屠戮,《新唐書》卷一三九《劉稹傳》,頁6017。對於劉稹餘黨,懲治苛嚴,株連廣泛。如劉稹的謀主郭誼雖殺劉稹,舉潞州歸降,朝廷非但未如其所期待的那樣授予旌節,反而盡誅其黨,*郭誼的誤判不得不説當歸因於李德裕的欺騙,李德裕曾通過其姻親降將李丕,誘其殺劉稹投降,許以重報。李德裕《賜李石詔意》云:“李丕是郭誼密親,尤合相信。卿宜暫追赴使,令與郭誼書,論以利害,遣其自圖劉稹,早務歸降。倘效誠款,必重酬賞”,另參李德裕《代李丕與郭誼書》,傅璇琮、周建國《李德裕文集校箋》,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頁110,156—157。李德裕之所以違背承諾,誅殺郭誼等,大約與其欲剷除昭義割據的社會基礎有關。“劉稹將郭誼、王協、劉公直、安全慶、李道德、李佐堯、劉武德、董可武等至京師,皆斬之”,“又令昭義降將李丕、高文端、王釗等疏昭義將士與劉稹同惡者,悉誅之,死者甚衆”。*《通鑑》卷二四八,頁8010,8011。按《通鑑》卷二四八考異引《獻替記》對此有更詳細的記載:“往劉稹平後,處置澤潞與劉稹同惡,僅五千餘人,皆是取得高文端、王釗狀,通姓名,勘李丕狀同,然後處分。其間有三兩人或王釗狀無名,並不更問”,頁8019。《考異》云“五千”係“五十”之訛。李德裕對於劉稹餘部的嚴厲處置,雖或有黨爭的背景,*李德裕以牛僧孺、李宗閔曾與劉從諫交通爲名,進一步將兩人遠謫,《通鑑》卷二四八,頁8134—8135。當然對於此事,也有不少爲李德裕辯誣者,認爲記載不可信,如岑仲勉《通鑑隋唐紀比事質疑》,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頁296—297;傅璇琮《李德裕年譜》,頁430—432。但總體上仍是爲了徹底剷除昭義割據的基礎。
唐廷在攻打昭義之初,便已注意到劉氏昭義内部存在着“主客之分”,力圖有針對性地加以分化:
其昭義軍舊將士及百姓等,如保初心,並赦而不問……劉悟下鄆州舊將校子孫及劉從諫近招致將士等,喻以善道,宜聽朕言……*李德裕《討劉稹制》,《李德裕文集校箋》,頁31。唐廷試圖激化主客兩個羣體之間的矛盾,以達成從内部瓦解劉氏昭義的目的,如李德裕《代彦佐與澤潞三軍書》云:“比聞從諫志在猖狂,招致亡命,逆人親黨,遊客布衣,皆在公宴之中,列於大將之上,一軍憤愧,固已積年。”《李德裕文集校箋》,頁150。
制書將劉氏主政下的昭義軍隊分爲昭義舊有將士與劉氏父子自鄆州任上攜來及新募親軍兩類,*張正田已注意了這一區分,將其分爲四類,但本質上仍爲主客兩分,特别是昭義舊將士、昭義軍舊大將等在詔書上下文中本視爲一類,不當强爲之别,《“中原”邊緣——唐代昭義軍研究》,頁178—182。後一類無疑是劉稹的腹心所寄。因此對於這兩類人,唐廷的招撫策略並不一致,對昭義舊軍將士或希望他們“以州郡兵衆歸降”,或誘之以利,“擒送劉稹者,别授土地”。對後一類人,一方面肯定其與劉氏家族有類於田横及其義附的關係,但强調:“豈嘗違拒漢使,留止田横;惟慕殉以成仁,不相挺而作亂”,勸誘他們:“如能感喻劉稹束身歸朝,必當待之如初,特與洗雪;爾等舊校,亦並甄酬”,可知這些親軍與劉氏家族關係緊密,甚至在某種意義上而言是基於“義”的結合,如“鄆州舊將校子孫”本是劉悟攜來昭義的親軍,世代效忠劉氏,這些都構成了劉氏割據的權力基礎,因此也是唐廷平定昭義後需要剷除的。
雖然唐廷誅殺了郭誼、王協等一批劉氏昭義的核心人物,並在《平潞州德音》宣佈:“用兵已來,劉稹所招收團練、官健,放歸營生”,*《唐大詔令集》卷一二五,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672。但遣散的範圍僅限於戰爭中劉稹新徵募的兵士,因此並不能徹底改變昭義的軍事結構。這批劉氏親軍之後的命運在傳世典籍幾無所載,但藉助於新刊佈的墓誌,已可窺見一斑,典型者可舉出李文益、高元郾兩人。李文益終官昭義軍洺州防城使,其爲上黨長子縣人,曾祖、祖、父三代皆未仕。
李文益雖是昭義本地人,但元和末曾於禁軍服役,大和初,爲劉從諫所招募,歷任鎮内中下級官吏,頗具吏幹,因此當劉稹覆滅後,李文益不但未受處分,反而被擢升,“以時會昌末年,范陽司空署洺州防城十將兼賊曹掾”,范陽司空即指唐廷所命負責昭義善後的節度使盧鈞。大中五年(851)進一步遷爲洺州防城使,至大中六年卒於任。如果説,李文益之前所任不過是傳舍、漕碾、鹽鐵等吏職,非劉氏昭義中的要角,爲唐廷所留用並不足爲奇,那麽高元郾的身份則顯赫得多。其女徐唐夫妻高氏因難産卒大中八年四月,不過二十出頭,其父高元郾時見任昭義軍親騎兵馬使兼押衙。高元郾出身顯赫,其曾伯祖便是元和初平定西川劉闢之亂的禁軍名將高崇文,伯祖高霞寓、堂伯祖高承簡、堂叔祖高承恭、親叔祖高霞寔,“一家兄弟叔侄子父五人,皆領雄藩”,是中唐著名的武將家族。高元郾“以累代節制之後,不墜弓裘,自弱冠即習武略,故昭義節度使、檢校太師、平章事沛國劉公好奇,聞侍御有韜鈐武略,遂命使貴金帛車馬就滑臺邀之”。*殷憲《〈徐氏夫人墓誌〉及其藩鎮家族》刊佈了墓誌拓本及録文,並作了簡要的考釋,《大同新出唐遼金元誌石新解》,太原,三晉出版社,2012年,頁269—276。據此高元郾本仕於滑州義成軍,*劉悟嘗鎮滑州,其子從諫能獲知高元郾的才能,不知是否與之有關,《舊唐書》卷一六一《劉悟傳》,頁4230。爲劉從諫重金禮聘而至,*誌文中所謂的“劉公”究竟是指劉悟還是劉從諫,尚難確定。劉悟、劉從諫生前皆帶使相銜,分别檢校司徒、司空,贈官分别爲太尉、太傅,似皆未嘗檢校太師,劉從諫嘗兼太子太師,暫繫於劉從諫時,參見《新唐書》卷二一四《劉悟傳》,頁6013—6015。深受信用,“遂署衙門之將,總帳下之兵”。高元郾移居昭義後,迅速融入了昭義鎮内的軍將網絡,其女高氏嫁給故昭義軍左廂都押衙徐克中之子徐唐夫。如高元郾這樣的流寓之士通過婚姻等手段完成在地化,並進入劉氏昭義的統治核心,並非孤例。如會昌之役中投降唐廷的牙將李丕,“頃歲寓遊上黨,與主公素未相知”,藉助劉從諫議親信郭誼的黨援,得以仕於昭義,並與郭家結成秦晉之好,“十三叔翦拂提攜,遂叨右職,尋蒙見哀羈旅,申以婚姻”。*李德裕《代李丕與郭誼書》,《李德裕文集校箋》,頁156。事實上,中晚唐各藩鎮中的外來者通過婚姻等手段迅速融入地方社會是極爲普遍的現象,如果將其與同時發生的士大夫遷居兩京的潮流相比照,則可注意到,士族儘管定居於兩京,漸次脱離鄉里,但依然大體維持了原有的通婚圈。可以説前者通過融入本土來構築認同,後者則藉助存異以保持門第不墜,看似相反的行動背後反映的是不同社會階層間的文化差異。而在墓誌撰文的大中八年,高元郾仍任昭義軍親騎兵馬使兼押衙,並未遭到清算,繼續在昭義軍中占據要津。
由此可見李德裕在會昌伐叛成功後,雖然較之以往采取了更爲淩厲的手段清洗劉稹餘黨,在此之後,晚唐歷任昭義節帥皆由朝廷派遣的文臣出任,消除了節帥跋扈自立的隱患。但從李文益、徐唐夫妻高氏墓誌透露的情況來看,*可以斷定這兩人在會昌伐叛中並没有棄暗投明,歸順唐廷,如有類似的舉動,在墓誌中肯定會着重表彰。李德裕的善後舉措也未能真正改變昭義軍隊的構造。因此,我們可以注意晚唐昭義軍雖未再出現如劉氏父子那樣割據自立的現象,但朝廷選任的文臣節帥往往難以彈壓鎮内的驕兵悍將,呈現出藩鎮内部頻繁發生兵變的新特徵。
這一特徵在會昌伐叛後首任昭義節度使盧鈞任上便已顯現。盧鈞素有能名,在嶺南、山南東道節度使任上清正廉潔、治績突出,故朝廷在決意討伐劉稹後,提前發表其爲新任昭義節度使,“鈞素寬厚愛人,劉稹未平,鈞已領昭義節度,襄州士卒在行營者,與潞人戰,常對陳揚鈞之美。及赴鎮,入天井關,昭義散卒歸之者,鈞皆厚撫之,人情大洽”。*《通鑑》卷二四八,頁8010。唐廷早早選定善於撫綏的盧鈞出鎮昭義,蓋“以昭義乘僭侈之餘,非廉簡無以革弊;當掊克之後,非惠和無以安人”,*李德裕《宰相與盧鈞書》,《李德裕文集校箋》,頁165—166。希望藉此穩定亂後人心,實現平穩的權力過渡。劉稹授首後,唐廷立刻下詔“昭義五州給復一年,軍行所過州縣免今年秋税。昭義自劉從諫以來,横增賦斂,悉從蠲免”,*《通鑑》卷二四八,頁8008—8009。蠲免租税,安撫民心。肩負重任的盧鈞入潞之後,處置不可謂不謹慎,特别是李德裕計畫進一步株連劉氏黨羽時,“盧鈞疑其枉濫,奏請寬之”,*《通鑑》卷二四八,頁8011。“盧鈞”原作“虞鈞”,當係誤排,檢胡克家翻刻元刊本不誤。雖未獲從,但表達出新任節帥寬厚的政治姿態,以安反側。孰料未滿一年,當朝廷計畫徵發昭義步騎二千戍振武時,“潞卒素驕,憚於遠戍,乘醉,回旗入城,閉門大譟,鈞奔潞城以避之”,*《通鑑》卷二四八,頁8017。甚至可以説盧鈞的被逐,與其寬厚的態度有關,武宗曾論及此事:“凡方鎮發兵,只合不出軍城,嚴兵自衛,於城門閲過部伍,更令軍將慰安。豈有自出送兵馬,又令家口縱觀!事同兒戲,實不足惜!”《通鑑》卷二四八考異引《獻替記》,頁8019。盧鈞這些疏於防範之舉,未必不是其爲安撫昭義人心故意所爲。揭開了之後昭義頻繁發生兵亂的序幕,盧鈞這位被寄予厚望的昭義節度使的生涯剛剛開始便宣告結束,召還朝廷,“拜户部侍郎、判度支”。*《舊唐書》卷一七七《盧鈞傳》,頁4592。高湜的被逐不過是這一系列反覆上演戲碼中的一幕。
李裔墓誌云:“劉廣不知何人也,來自薊門,客於山北。”則劉廣並非是昭義當地人,來自幽州,從時間推測當是在劉稹覆亡纔輾轉進入昭義軍,漸次獲得擢升,*墓誌中未記劉廣的官職,將其描述爲寄食昭義軍中的遊手好閑之徒,但傳世文獻中皆云劉廣爲昭義軍將領,或誌文對於劉廣的身份故意有所貶低。如之前高元郾的例子一樣,皆可證明藩鎮軍隊的來源並不是地域性、封閉式的,往往在唐廷與藩鎮、藩鎮與藩鎮之間存在着人員流動。*墓誌所見的另一個例子是李少榮,“府君本桑梓魏郊人也,於貞元十四年來到潞邑”,牒補綾坊押官、守武衛將軍、試太常卿,於大中元年去世,拓片刊《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續編》,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584。馮金忠《唐代河北藩鎮研究》對此現象已有所揭示,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年,頁47—53。昭義鎮特别是劉氏家族主政時期,估計有積極從北方招募出身胡族將士的傳統,如會昌伐叛後被殺的安全慶、平定劉廣之亂的安文祐,當是粟特後裔。又如“大和初,李聽敗館陶,走淺口,從諫引鐵騎黄頭郎救之”,*《新唐書》卷二一四《劉從諫傳》,頁6014。關於黄頭軍,陳寅恪最早注意到這條史料,《讀書札記一集》,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頁611;另參王永興《〈陳寅恪讀書札記——舊唐書新唐書之部〉疏證》,《陳寅恪先生史學述略稿》,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288—318。皆顯示出昭義軍隊多元的構成。儘管劉稹覆滅後,出掌昭義的文官節度使不再刻意羅致,但傳統不會驟然中斷,北方失意的軍人循着慣性南下昭義尋求出路,劉廣或許便是其中之一。當然外來的軍將要融入昭義軍已有的網絡,則要如高元郾一樣經過“在地化”的過程。劉廣“常寓食將卒之家”,可知與昭義軍中的將士往來頻繁,關係密切,這爲他以劉稹之族的名義煽動叛亂提供了條件。
那麽如何理解在劉氏昭義覆亡三十餘年後,劉廣依舊能以劉稹族裔的名義煽動起事?事實上,劉稹的親族在會昌伐叛過程中經過郭誼、李德裕的兩次屠戮,幾無孑遺,而上文所論“鄆州舊將校子孫及劉從諫近招致將士”這一支持劉氏昭義的核心力量,雖未能被李德裕徹底清洗,但經歷了時間的淘洗,至此時恐怕大都已漸次凋零。因此,劉廣之亂並不能被視爲昭義軍中劉稹餘部或者親劉稹勢力的一次起事,參與其事大都與劉廣本人一樣,與劉稹並無直接瓜葛。這只是證明劉稹這一政治符號在劉氏昭義覆亡三十餘年後仍頗具煽動性,足以引起將士的共鳴,激發變亂。這無疑暗示了在會昌伐叛取得勝利之後,唐廷對昭義的統治遠稱不上成功。
劉悟本係李師道部將,因殺李師道投唐而被授予義成軍節度使,其得據昭義本出偶然,是穆宗繼位後倉促調整一系列藩鎮節帥的結果。因此其鎮澤潞,所仰仗者僅是從鄆州帶來的軍隊,“劉悟之去鄆州也,以鄆兵二千自隨爲親兵”,*《通鑑》卷二四三,頁7844。直到劉從諫欲承襲昭義時,“惟鄆兵二千同謀”,*《新唐書》卷一九三《賈直言傳》,頁5559。當然我們不難注意到《新唐書·賈直言傳》新增的“惟鄆兵二千同謀”這一記載蓋本自杜牧《上李司徒相公論用兵書》中“從諫求繼,與扶同者只鄆州隨來中軍二千耳”,杜牧此書上於李德裕主持討伐澤潞時,或有貶低劉從諫的成分,參吴在慶《杜牧集繫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819。統治基礎并没有發生太大的變化。劉氏家族對於昭義而言,亦屬於外來的統治者。劉氏家族在昭義統治的穩固,大約要歸功於劉從諫的經營。“悟苛擾,從諫寬厚,故下益附”。*《新唐書》卷二一四《劉從諫傳》,頁6014。儘管劉悟時,已出現了“朝廷失意不逞之徒,多投寄潞州以求援”的局面,*《舊唐書》卷一六一《劉悟傳》,頁4231。但至劉從諫時,一方面改弦易轍,以寬厚的姿態團結昭義内部,另一方面則繼續招降納叛,“從諫志在猖狂,招致亡命,逆人親黨,遊客布衣,皆在公宴之中”,*李德裕《代彦佐與澤潞三軍書》,《李德裕文集校箋》,頁150。擴充自身的實力,昭義軍的將領多受其恩惠,整合形成了利益共同體,完成了劉氏政權的在地化。《舊唐書·劉悟傳》云:
從諫妻裴氏。初,稹拒命,裴氏召集大將妻同宴,以酒爲壽,泣下不能已。諸婦請命,裴曰:“新婦各與汝夫文字,勿忘先相公之拔擢,莫效李丕背恩,走投國家。子母爲托,故悲不能已也。”諸婦亦泣下,故潞將叛志益堅。*《舊唐書》卷一六一《劉從諫傳》,頁4233。
裴氏所言正反映劉氏父子與軍將之間膠固相結的關係。因此至會昌伐叛時,“劉從諫近招致將士”已足以和“鄆州舊將校子孫”並提,共同構成了劉氏昭義的支柱。
會昌伐叛後唐廷的善後處置成功清除了劉氏家族及其親信,與此同時,也斬斷了劉氏昭義時期節帥與軍將間親黨膠固的關係,在此之後確實再未出現昭義節度使擁兵自重的局面。從這一層面而言,李德裕的善後舉措達成自己的目標,扭轉了昭義“河朔化”的傾向。但正如上文所論,唐廷的清洗並無力真正改變昭義的軍隊構成,昭義鎮内的兵士失去了强悍有力的節帥約束後,反倒成爲新的不穩定因素。當然這些驕兵悍將實際上並無如劉氏那樣割據自立的野心,頻頻起事,驅逐節帥,所欲滿足者不過是自身經濟等方面的利益,這一類中晚唐在各藩鎮内部爆發的頻度越來越高、低烈度的動亂,不妨命名爲“經濟性騷亂”。*這種經濟性的騷亂本質上反映了藩鎮軍隊的自利取向,一般由兩類行爲構成,一類是以獲利爲目的的,比如謀取更豐厚給賜,另一類則是以維護既得利益爲目的,例如拒絶出境作戰、拒絶戍邊等,這兩類訴求皆會導致經濟性的騷亂。而與中唐時代,河朔藩鎮圍繞着自立地位這一明確政治目標與朝廷發生的連年戰爭,有着本質的不同,後者或許可稱爲“政治性反叛”。*對於藩鎮動亂的類型,之前的學者或多或少的都作過一些分類,代表性的可以舉出張國剛《唐代藩鎮研究(增訂本)》中分爲兵士嘩變、將校作亂、反叛中央、藩帥殺其部下四類,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60—63。但之前的學者分類的目的在於梳理史實,而筆者下文則嘗試利用這兩個概念闡釋唐代藩鎮變亂模式的演化。劉廣之亂雖以劉稹之族爲號召,但與劉氏昭義仿效河朔割據、試圖子孫相襲不同,其本質上仍是一場“經濟性騷亂”。誠如《李裔墓誌》所云“是時,潞土阻饑,賦入逋負者太半。高公雖無闕政,而士卒月儲、歲衣往往不足,以是乘其時而動”。昭義爲何從劉稹時“畜兵十萬,粟支十年”、“府中財貨尚山積”,*《新唐書》卷一八《李德裕傳》,頁5338;卷二一四《劉稹傳》,頁6017。轉而陷入“士卒月儲、歲衣往往不足”的困窘,這與志在割據的節帥往往采取聚斂境内以給賜軍士,進而獲取擁戴的贖買策略有關。《新唐書》本傳又云從諫:
性奢侈,飾居室輿馬。無遠略,善貿易之算。徙長子道入潞,歲榷馬征商人,又熬鹽,貨銅鐵,收緡十萬。賈人子獻口馬金幣,即署牙將,使行賈州縣,所在暴横沓貪,責子貸錢,吏不應命,即愬於從諫。*《新唐書》卷二一四《劉從諫傳》,頁6015。
前引《李文益墓誌》云其“改補鹽鐵,淬貮轉輸,不闕課利”,承擔的便是相關職任。劉從諫盤剝商人、聚斂財富所得,*科斂商人、開闢財源是劉氏昭義有效的聚斂手段,如王協税商人十分取二,裴問以富商子弟號夜飛軍,《通鑑》卷二四八,頁8005。這些賦斂的辦法在會昌伐叛後被廢止,這是昭義由富變窮的重要原因。除了滿足自己享樂所需外,主體當用於犒賞兵士,維繫軍將對其統治的向心力。比較一下劉廣逐出高湜後,立刻“横斂以給軍士”,邀買人心,所爲與劉從諫别無二致。由此可見,劉稹之族的身份之所以在昭義軍中仍具有號召力,恐非基於某種政治或道義上的權威,而是懷念劉氏昭義時期依賴豐厚給賜享受的滋潤生活。*因此儘管會昌伐叛一開始,唐廷就削奪劉從諫及子稹官爵,平定劉稹後,更命石雄將劉從諫剖棺戮尸,以叛臣目之,《通鑑》卷二四七,頁7984;卷二四八,頁8009。但前引《李文益墓誌》、《徐唐夫妻高氏墓誌》仍皆尊稱其爲劉公及官爵,反映了昭義鎮内對劉氏的態度。自劉氏割據時代舉全鎮之力供奉軍隊後,導致了昭義軍逐漸“驕兵化”,轉變爲依賴豐厚給賜維繫忠誠的自利羣體,*會昌伐叛中,王釗以洺州降唐,起因便是給賜不足,引起軍隊不滿,《通鑑》卷二四八,頁8006。與李抱玉、李抱真時代盡忠朝廷、抗衡河朔的面貌已迥然不同。因此,會昌伐叛後的一系列善後舉措,雖然遏制了節帥自立的傾向,但並不能改變昭義“驕兵化”的既成事實。*張正田已指出晚唐昭義驕兵化的現象,但並未述及原因,見《“中原”邊緣——唐代昭義軍研究》,頁182。上文所論盧鈞接任之後,軍士拒絶北戍振武,迫大將李文矩爲帥,也是一個驕兵自利的典型案例。此後,朝廷所命文官出身的節度使,不過將昭義視爲歷官遷轉中一站,與在地化的昭義軍將氣類不同,頗有文化隔閡,如在咸通四年(863)昭義軍亂中被殺的沈詢,素以風姿爲時人稱許:
沈詢侍郎,清粹端美,神仙中人也。制除山北節旄,京城誦曹唐《游仙詩》云:“玉詔新除沈侍郎,便分茅土領東方。不知今夜游何處,侍從皆騎白鳯凰。”即風姿可知也。*《北夢瑣言》卷五,頁103。
這位被目爲“玉筍班”的翩翩佳公子雖據聞“爲政簡易,性本恬和”,但恐怕不會如劉氏統治時期那樣注重保障軍士利益,刻意籠絡。儘管沈詢的死因有些特殊,其奴歸秦因與其侍婢私通,懼事暴露,陰結牙將作亂,殺詢全家。*《舊唐書》卷一四九《沈詢傳》,頁4038。歸秦這樣的微賤小人便能説動牙軍,沈詢與部下的關係恐怕本來便有嫌隙。除了節帥與將士之間的隔膜,劉氏昭義時期,文武僚佐皆劉悟、劉從諫父子一手羅致,親黨膠固,之後在朝廷派遣文臣節帥的治下,文職僚佐如李裔之輩皆爲節帥選辟,或出身世家,幕職之任不過是應付守選時的迴旋之地,而軍將則多是昭義本地人,世代從軍,文武之間氣類迥異,分途之勢已成。在此背景下,劉稹便成了將士懷念“美好時代”的象徵,進而成爲劉廣起事的機緣,但昭義軍將所懷念的不過是以滿足驕兵欲壑爲重心的統治方式。
在驅逐高湜,控制昭義之後,劉廣最初的期待是朝廷能接受這一既成事實,授予節鉞,而非割據自立。此時,唐廷采取了常用的拖延任命、靜觀其變的策略。在此背景下,出身當朝顯宦家族的李裔便成爲了亂兵眼中合適的溝通朝廷與昭義的中間人,“莫若縻一、二從事,以覬朝廷信恕”,“遂自擁衆請君,且以露刃脅之”。雖然墓誌中稱李裔的所作所爲皆是受亂軍脅迫,並一直伺機反正,但無疑其在劉廣盤踞昭義期間扮演了相當活躍的角色,“君常密畫覆廣之計,未有以發。會此强逼,既不可規免,且思用其寵而諧其志。乃若喜於邀辟,欣然從命。始以墜馬傷足爲辭,後乃乘輿趨府臨事,勤畏如初”。因此在亂後,李裔亦受到牽連,被貶爲隨州司馬。其父李福時領山南東道,隨州恰在其治下,可謂不幸中的大幸。但孰料半年多後,王仙芝攻破隨州,李裔死於任上。*隨州城破的時間,《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繫於八月,頁700;《通鑑》卷二五三繫於乙卯,按乙卯爲九月十七日,正與誌文合。《通鑑》另記:“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遣其子將兵救隨州,戰死。”蓋是李福另一子,頁8192。兩年多後,纔得以歸葬長安。
作爲高級官僚的子弟,李裔對長安朝廷的政治運作規則自然頗爲諳熟。如果墓誌所言不虚的話,那麽正是由於李裔的勸諫,使得劉廣放棄了出兵澤州,主動挑起戰爭的計畫,從而將驅逐高湜的行動限定在“經濟性騷亂”範圍之内。由於唐廷遲遲未授予節鉞,躁動不安的劉廣亂軍中曾有傳遞舊卒獻計挑起與河陽的戰爭,“澤本屬郡,可厚賂以招孟人出兵,掠其壁,據大□、劫河陰,以驚周鄭之郊,此乃疾雷不及掩耳,則節旄可翹足而待也”,即希望通過軍事行動施加壓力,迫使唐廷接受現實。澤州本屬昭義轄境,正是在平定劉稹後,轉隸河陽節度,“俟昭義平日,仍割澤州隸河陽節度。則太行之險不在昭義,而河陽遂爲重鎮,東都無復憂矣”!*《通鑑》卷二四七,頁7991。李德裕此舉無疑是爲了削弱昭義的實力,使其無法南下對洛陽構成威脅。*王國堯《李德裕與澤潞之役——兼論唐朝於9世紀中所處之政治困局》,《唐研究》(12),頁501—503;陳翔《關於唐代澤潞鎮的幾個問題》,《陳翔唐史研究文存》,頁176—177。傳遞舊卒所獻之計,便是南下進逼洛陽,以迫使朝廷承認,這一謀畫或許在軍事上頗具可行性,*《王宰墓誌》中描述了劉稹科斗寨之捷後,對於洛陽的震動,“天井下臨覃懷,勢逼河洛。衣冠士庶,莫不惶駭。姦謀訛言,亟生恟動”,拓片刊齊運通編《洛陽新獲七朝墓誌》,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363。澤州作爲昭義舊屬,兩地仍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但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此計達成的前提是“厚賂以招孟人出兵”,即在當時公認的政治默契中,劉廣若主動進攻河陽,勢必無法取得昭義鎮内將士的支持,只有先演一出苦肉計,纔能挾持昭義軍捲入戰事。這一政治默契的實質便是如何來確定“經濟性騷亂”與“政治性反叛”的界限,此處可以與劉稹之亂作一比較:
(劉稹)居喪求襲,阻命專權,數遣亂軍,侵軼鄰境。比者河陽、晉絳,未有重兵,侵犯顔行,屢焚廬舍。又疆埸之吏,收得彼管簿書,皆呼官軍爲賊,來即痛殺,可謂悖言肆口,逆節滔天。*李德裕《代李石與劉稹書》,《李德裕文集校箋》,頁152。
劉稹主動進攻鄰鎮,公開與官軍爲敵,是其被目爲叛臣的重要依據,其實這本非劉稹原意。按照王協的謀畫,“正當如寶曆年樣爲之,不出百日,旌節自至。但嚴奉監軍,厚遺敕使,四境勿出兵,城中暗爲備而已”,*《通鑑》卷二四七,頁7981;另參李德裕《賜何重順詔》,《李德裕文集校箋》,頁101。不出兵襲擾鄰鎮,便是其中的關節之一。正因如此,當戰爭之初,昭義將領薛茂卿擊敗河陽方面的唐軍,“破科斗寨,擒河陽大將馬繼等,焚掠小寨一十七”,兵臨懷州城下,但因“以無劉稹之命,故不敢入”。大捷之後,薛茂卿不但未獲封賞,反而因“太深入,多殺官軍,激怒朝廷,此節所以來益遲也”的讒言招致劉稹猜忌,*《通鑑》卷二四七,頁7989,7993。最終欲投降唐軍不果而被殺。此事典型地反映出劉稹叛亂時首鼠兩端的心態。在元和中興之後,唐廷與藩鎮達成的政治默契中,除允許河朔藩鎮自相承襲外,其他藩鎮再欲效仿河朔,追求自立而發動“政治性反叛”已不再有獲得赦宥的機會,這也是李德裕在會昌之役中獲得河朔藩鎮出兵協助平叛的依據所在。*即在承認河朔故事的基礎上,指出“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通鑑》卷二四七,頁8103。
由此可見,劉廣一旦出兵河陽,其性質就從“經濟性騷亂”轉變爲“政治性反叛”,前者尚能爲唐廷所含容,後者則被視爲叛逆。因此李裔所主張的“恭順以俟朝旨”,雖然使劉廣放棄在軍事上獲取主動的機會,但更符合當時普遍公認的政治邏輯。
最終,唐廷的拖延戰術起到了效果,在李係率軍兵臨城下的外部壓力之下,*李係爲中唐名將李晟曾孫,傳世文獻中僅有零星記載,集中在乾符六年(879)五月,“王鐸以其家世良將,奏爲行營副都統兼湖南觀察使,使將精兵五萬并土團屯潭州,以塞嶺北之路,拒黄巢”。十月,黄巢率軍北上,“李係嬰城不敢出戰,巢急攻一日,陷之,係奔朗州”,《通鑑》卷二五三,頁8214,8217。此役成爲黄巢坐大的關鍵之一,王鐸之所以會重用“有口才而實無勇略”的李係,除了將門之子的身份外,乾符四年率軍平定劉廣之亂的成功或許也起了不小的作用。昭義内部發生變亂,“安文祐時任軍候,紀綱心膂,咸惣統之。是夕,遂梟廣首擲城外”,牙將安文祐誅殺劉廣,歸順唐廷。但值得注意的是,唐廷雖犒賞安文祐之功,加官進爵,“召赴行在,授邛州刺史”,*《舊五代史》卷九《安崇阮傳》,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頁1379。實際上將其調離了昭義軍。誌文中所謂“護軍中貴人與軍吏咸請君知留事,始入治所,遽命擒前傳遞卒,仗煞之”,則是在劉廣被殺之後的權力真空期,監軍與昭義鎮内或曾有策動李裔爲留後的謀畫,但最終未獲唐廷允准,“以左金吾大將軍曹翔爲昭義節度使”,*《通鑑》卷二五二,頁8181。維持了以朝官出外爲昭義節度使的舊例,只是大約懲於高湜以文臣失馭的前車之鑑,改以禁軍將領曹翔出鎮。
三
儘管史書中批評“沈詢、高湜相繼爲昭義節度,怠於軍政。及有歸秦、劉廣之亂”,*《舊五代史》卷六二《孟方立傳》,頁961。將更多的責任歸咎於節帥的控馭失當,*與盧鈞不同,高湜在昭義亂後遭遠貶,可見朝廷明確地將劉廣之亂的責任歸咎於他,但是我們需要注意到此時正是高湜的政敵控制朝政,很難説這一處分背後没有政治報復的因素。但我們不難注意到晚唐這種“經濟性騷亂”發生的頻率日益增加,範圍不但涵括唐廷控制的藩鎮,即使在原本節帥自相承襲已成故事的河朔三鎮中,亦頗爲常見。*如果説在唐廷控制的藩鎮,多由文臣出任節度使,任期不長,文武隔膜,加之中央權威的衰退,難以駕馭鎮内的軍隊,導致了此類騷亂的發生。但河朔藩鎮世代相襲,節帥出身武夫,在傳統上對於本鎮控制嚴密,同樣發現此類現象,這只能説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甚至爲了防止軍士暗地串通,“河北之法,軍中偶語者斬”。*《通鑑》卷二四八,頁8014。胡注:“河北諸帥防其下相與聚謀以圖己,故嚴軍中偶語之法,以剛制之。盧弘宣至中山,乃除其法”。作爲晚唐藩鎮中普遍存在的一種結構性現象,將其僅僅歸因於節帥本人的失策或無能,恐未達一間。如上文所述的盧鈞便是唐廷精心選擇的人選,舉措謹慎穩妥,但亦難逃狼狽離任的命運。
昭義作爲唐廷防遏河朔三鎮設立的藩鎮,“肘京洛而履河津,倚太原而跨河朔”,*杜牧《賀中書門下平澤潞啓》,《杜牧集繫年校注》,頁976。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李抱玉、李抱真兄弟盡節王事,在歷次討伐藩鎮的戰爭中屢建功勳,昭義軍因此享有忠義的美名。自劉悟、劉從諫父子自相承襲以來,昭義轉向割據自立,會昌伐叛的勝利並未能改變昭義軍動蕩多事的格局,直至唐末因孟方立之亂最終分裂爲澤潞、邢洺二鎮,可以説昭義軍的面貌從中唐到晚唐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對於這一轉變,唐人與現代學者的觀察其實相當接近,都認爲昭義受到了河朔割據傳統的影響,*唐人對於昭義忠義形象的認知詳見下文,現代學者中較有代表性的論述可參讀張正田《“中原”邊緣——唐代昭義軍研究》中的討論,頁227—252。“比者河朔諸鎮,惟淄青變詐最。劉悟隨來舊將,皆習見此事”,*李德裕《賜李石詔意》,《李德裕文集校箋》,頁112。“豈謂移淄青舊染之俗,汙上黨爲善之人”,*李德裕《代盧鈞與昭義大將書》,《李德裕文集校箋》,頁154。將昭義的轉變歸咎於劉氏主政。因此,李德裕主持的善後工作,其根本目的便是要肅清劉氏家族的影響,“蓋以汙染之俗,終須蕩滌”。*李德裕《宰相與盧鈞書》,《李德裕文集校箋》,頁166。但在清洗劉氏及其親信之後,並未如唐廷所期待的那樣,恢復昭義軍“忠義”的傳統。正如上文所論晚唐昭義雖不曾再出現節帥割據自立,但“經濟性騷亂”頻繁發生,鎮内愈加動蕩。因此,我們對於前期昭義軍“忠義”的本質究竟爲何,實有重新思考的必要。傳世文獻中對於昭義軍“忠義”歷史與形象的記述所在多有,杜牧著名的《上李司徒相公論用兵書》論述頗詳:
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郳公抱真,能窘田悦,走朱滔,常以孤窮寒苦之軍,横折河朔彊梁之衆。貞元中,節度使李長榮卒,中使提詔授與本軍大將,但軍士附者即授之。其時大將來希皓爲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盧)從史爾後漸畜姦謀,養義兒三千人,日夕喣沬。及父?兌2死,軍士留之,表請起復,亦只義兒與之唱和,其餘大將王翼元、烏重胤、第五釗等及長行兵士,並不同心。及至被擒,烏重胤坐於軍門,喻以禍福,義兒三千,一取約束。及河陽取孟元陽爲之統師,一軍無主,僅一月日,曾無犬吠,況於他謀。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及元和十五年授與劉悟,時當幽鎮入覲,天下無事,柄廟算者議必銷兵。雄健敢勇之士,百戰千攻之勞,坐食租賦,其來已久,一旦黜去,使同編户,紛紛諸鎮,停解至多,是以天下兵士聞之,無不忿恨。至長慶元年七月,幽鎮乘此首唱爲亂。昭義一軍,初亦鬱咈,及詔下誅叛,使温起居造宣慰澤潞,便令發兵。其時九月,天已寒,四方全師,未頒冬衣服,聚之授詔,或伍或離,垂手强項,往往誶語。及温起居立於重榻,大布恩旨,并疏昭義一軍自七十餘年忠義戰伐之功勞,安、史已還叛逆滅亡之明效。辭語既畢,無不懽呼。人衣短褐,爭出效命。*《杜牧集繫年校注》,頁818—819。按引文中“李長榮”,本誤作“李長策”,據《舊唐書》卷一三二《盧從史傳》改,頁3652。
杜牧所論大體上可以代表時人對於昭義忠義形象的認知,會昌伐叛過程中,李德裕替唐廷及諸路將領草擬的詔敕文告,對於昭義軍忠義歷史的描述大體與之類似。在杜牧眼中,此前昭義軍中節帥、大將、軍士三個階層皆盡忠於朝廷,所謂“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即使有盧從史等個别豢養義兒謀求自立的節帥,亦無法獲得軍中大多數將領的支持,甚至銷兵等損害軍士切身利益的舉措,雖會招致不滿,但並不影響昭義軍戮力王事、爲朝廷作戰的熱情。因此,最初看來劉稹不過是盧從史第二,只要朝廷決心討伐,並不難底定。事實上,澤潞之役,迭經一年多的苦戰方告成功,若非李德裕的堅持,恐怕早就半途而廢了。由此可知劉稹時代的昭義較之以往已發生了相當的變化,這一變化的核心便是上文所論昭義的“驕兵化”,經過劉氏父子的統治,昭義軍已從一支“孤窮寒苦之軍”轉變爲依賴賞賜維繫忠誠的自利性軍隊。若放寬視野,不難注意到這類“驕兵化”的進程可以説在中晚唐各個藩鎮中普遍發生着,節帥只有給予將士更豐厚的給賜,纔能換取部下支持其對抗朝廷,謀取不受代甚至自相承襲的地位。但重複賞賜最終導致邊際效應遞減,將士的欲壑更加難以填滿,更容易受到煽動,進而鎮内騷亂愈發頻繁,節帥謀求自立與鎮内軍隊的驕兵化兩者可以説是互爲因果。*事實上,在驕兵主導藩鎮之後,節度使遑論謀求自立,僅維持自身地位便需要不斷地厚加賞賜,以換取擁戴,最終演化爲晚唐驕兵變易主帥,如同兒戲的局面。到了晚唐,大多數藩鎮都已完成了“驕兵化”的過程,這大約是當時各藩鎮“經濟性騷亂”頻繁發生的根本原因。
但須注意的是,除了“驕兵化”的轉變,劉氏統治下的昭義亦有不變的一面,即延續了由軍將階層構成昭義核心的傳統,*張正田《“中原”邊緣——唐代昭義軍研究》,頁159—161。在這一傳統下節帥與將士建立起密切而又相對平等的私人關係。回顧昭義前期的歷史上不難注意到,如李抱玉、李抱真等都是能與將士同甘苦的名將,因此自節帥、軍將乃至兵士的密切結合塑造了昭義軍的性格,同時鎮内將領也有較大的上升空間,建立功勳者有機會被擢升爲節帥。因此,一旦出現盧從史這樣試圖自立的人物時,並不容易獲得軍將羣體的支持,一個自相承襲的節帥家族反而會阻礙整個軍將羣體上升的空間。因此昭義前期的“忠義”表現與其説是一種文化傳統,不如説是這種軍將主導的結構及節帥個人取向所決定的。劉氏昭義時期,雖然轉變爲割據自立,但其本質上節帥與軍將間仍具有密切的私人紐帶關係,儘管這種紐帶關係可能更依賴婚姻、賞賜等手段來加以維繫。如上文引述的劉從諫妻裴氏與諸大將妻共宴,便是典型的例子,裴問也是因裴氏之弟的身份得以領邢州的。*《新唐書》卷二一四《劉從諫傳》,頁6017。按《舊唐書》卷一七七《劉鄴傳》云裴問係裴氏之兄,頁4617。由節帥與軍將主導昭義這一傳統並未改變,這在劉稹覆亡的過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只是軍將羣體更多的是由劉氏拔擢的私人構成。會昌伐叛後,李德裕主導的善後處置雖未能改變昭義軍的構造,但有力地削弱了昭義的軍將階層,更重要的是之後的昭義節帥由朝廷派出的文臣擔任,流動的節帥與本地化的軍人之間的隔膜顯而易見,改變了節帥與軍將間具有密切私人紐帶的傳統。同時鎮内軍將再無可能出任本鎮節帥,上升空間遭到封閉,而劉氏昭義時代的“驕兵化”,則使得軍隊本身變得難以駕馭,軍將階層的衰微與驕兵的活躍,使得昭義軍發生了從軍將主導向驕兵主導的轉變,這也是會昌伐叛成功後昭義經濟性騷亂頻繁發生的重要原因。
如果將中晚唐的藩鎮變亂初步畫分爲“政治性反叛”與“經濟性騷亂”兩種類型的話,那麽不難注意到兩者在時間與空間上各自具有不同的特徵。“政治性反叛”追求藩鎮割據自立、節帥之位的不受代乃至自相承襲,擁有明確的政治目標,强藩間合縱連横,甚至不惜主動挑起與唐廷的戰爭,具有外向型的特徵,以唐德宗時“四王二帝”連兵最爲典型。這一類叛亂,基本上發生在代宗、德宗、憲宗三朝。至長慶初,以唐廷承認“河朔故事”爲前提,朝廷與河朔藩鎮建立新的政治默契後,雙方關係長期保持穩定,甚至隨着河朔藩鎮的驕兵化,新任節帥往往需要唐廷的承認以强化其統治的合法性,對於唐廷的態度較之以往反而愈加恭順。*仇鹿鳴《從〈羅讓碑〉看唐末魏博的政治與社會》,《歷史研究》2012年第2期,頁27—44。另一方面,唐廷雖然默許了“河朔故事”,但對於河朔之外藩鎮如有“政治性反叛”的異動,往往傾向於武力討伐,以維護中央權威。“經濟性騷亂”則是分散而偶發的事件,發生的頻度在晚唐日漸提高,反映藩鎮將士自利性的訴求,一般没有明確的政治目標,範圍則集中於本鎮之内,基本的騷亂形式是驅逐原節度使,擁立新帥,並不直接挑戰唐廷的權威。即使在既往研究中被認爲驕兵跋扈典型的徐州銀刀軍亦不例外:
初,王智興既得徐州,募勇悍之士二千人,號銀刀、彫旗、門槍、挾馬等七軍……其後節度使多儒臣,其兵浸驕,小不如意,一夫大呼,其衆皆和之,節度使輒自後門逃去。前節度使田牟至與之雜坐飲酒,把臂拊背,或爲之執板唱歌;犒賜之費,日以萬計,風雨寒暑,復加勞來,猶時喧譁,邀求不已。牟薨,(温)璋代之。驕兵素聞璋性嚴,憚之。璋開懷慰撫,而驕兵終懷猜忌,賜酒食皆不歷口,一旦,竟聚譟而逐之……以浙東觀察使王式爲武寧節度使……驕兵聞之,甚懼。八月,式至大彭館,始出迎謁。式視事三日,饗兩鎮將士,遣還鎮,擐甲執兵。命圍驕兵,盡殺之,銀刀都將邵澤等數千人皆死。*《通鑑》卷二五,頁8099。
王智興驅逐唐廷任命的節度使崔羣而得徐州,因此組建銀刀軍以鞏固其地位,謀求長任,開啓武寧軍“驕兵化”的過程。之後歷任文臣節帥皆無法有效地加以抑制,至晚唐早已形成尾大不掉之勢。但值得注意的是,銀刀軍雖然經常變逐節帥,劣迹斑斑,但所謀求者不過是優給賞賜而已,並無進一步的政治目標,這在温璋被逐一事中表現得非常清楚。銀刀軍本因温璋性嚴而驅逐之,孰料朝廷不但未滿足預期,反而改派王式出鎮徐州。較之於温璋,剛剛平定浙東裘甫之亂的王式無疑更加難以對付,銀刀軍雖然對此强烈不滿,卻只能接受成命,無力再生事端,最終遭到屠戮。
在唐廷與藩鎮互相制衡的中晚唐時代,藩鎮普遍的驕兵化所削弱的更多的是藩鎮本身,而非唐廷。對於唐廷而言,因驕兵引發的經濟性騷動,由於缺乏政治目標,不過是疥癬之疾。另一方面,由於節帥不得不更多地將精力花在安撫或彈壓鎮内驕兵,無力外向,中唐之後,藩鎮對於唐廷的挑戰與威脅反而呈下降趨勢。在此情況下,唐廷得以根據對藩鎮内部形勢的判斷,從容地處置經濟性騷亂,手段較爲靈活,有時亦含容從之,承認亂軍擁立的新帥,以換取節帥對於朝廷更爲恭順的態度。*這在幽州張仲武身上體現得最爲明顯,《舊唐書》卷一八《張仲武傳》,頁4677。
如果作進一步觀察,“政治性反叛”藩鎮基本的權力構造一般是節帥與軍將的密切結合,由此形成穩固高效的統治模式,塑造出一支驍勇善戰的軍隊,從而具有謀求自立地位、挑戰唐廷的軍事力量。因此,前期的昭義軍雖然是作爲河朔的“敵人”而爲時人所認知,*會昌伐叛時李德裕嘗諭成德王元逵:“況卿當道,頃爲盧從史、劉從諫所敗,與澤潞素是深讐。”李德裕《賜王元逵何弘敬詔意》,《李德裕文集校箋》,頁121。但在結構上其實與河朔藩鎮更爲近似。而至晚唐,各藩鎮包括河朔三鎮在内或多或少都發生了“驕兵化”的過程,節帥受困於驕兵跋扈,自顧無暇,根本無力挑戰唐廷的權威,唐廷與藩鎮的關係反而變得穩定。而失去了“敵人”的昭義軍,不再具有“故欲變山東之俗,先在擇昭義之帥”的關鍵地位,*權德輿《昭義軍事宜狀》,《權德輿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751—752。可以由不知兵的文臣來出任。與中唐不同,經歷普遍的“驕兵化”後,晚唐藩鎮變亂轉而以“經濟性騷亂”爲特徵,以驕兵變易主帥爲主要形式,與前期呈現出不同的面貌,*渡邊孝曾比較成德與魏博不同的特點,認爲魏博是由牙軍所主導的,而成德的傳統是軍將層所主導,《魏博と成德——河朔三鎮の權力構造についての再檢討》,《東洋史研究》54卷2號,頁96—139。此文重要的貢獻是打破既往將河朔三鎮等而視之的成見,但其對於魏博的牙軍主導的歸納並非完全準確,李碧妍已指出田氏家族時代的魏博與成德一樣都是由軍將階層所主導的,直到史憲誠以後纔逐漸變成受牙軍支配。《危機與重構: 唐帝國及其地方諸侯》,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317—325。而從筆者一個籠統的觀察來看,軍將主導的藩鎮多與“政治性反叛”相聯繫,而驕兵跋扈則導致“經濟性騷亂”,因此軍將主導與牙軍主導的分野更多的是體現了唐代藩鎮前後期的變化。而昭義軍前後期的轉變,恰好爲此提供了一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