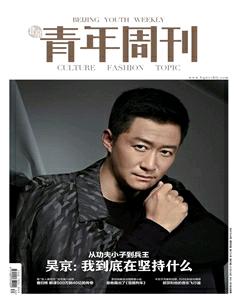跟随特立斯穿越纽约
小提

有这样一种写作,自诞生之初就带有某种程度的混血。比如美国记者盖伊·特立斯的“新新闻主义”写作。既不是完完全全的小说,也不是照单写下的实录;没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又脱不了虚构的底色。说到底,特立斯还是尽职尽责的记者。因此,就算调动小说的春秋笔法写身边诸事,行文之间也保留着原汁原味的现实味儿,不至于在追求虚构的路上越走越远,忘了他的本分。
普鲁斯特告诉我们“隐居有助于把生活转化为艺术”,特立斯写的是艺术,可隐居不是他的信条。都知道,有什么样的作者就有什么样的作品;反过来,有什么样的作品就有什么样的作者。《被仰望与被遗忘的》写纽约世情,不可谓不深。透过文字,我们看到细碎到骨子里的纽约,也看到涉世颇深的特立斯。他提到出没于纽约西城七十几街的巫师,身具“超凡洞察力、超凡听觉和超凡感觉”。事实上,特立斯才是那个具有“超凡洞察力、超凡听觉和超凡感觉”的巫师。一直以来,他看到我们看不到的,听到我们听不到的,感觉到我们感觉不到的。
的确,在特立斯之前,没有人像他那样描写纽约。《被仰望与被遗忘的》开篇即不同凡响,特立斯列举一连串数字,提醒我们纽约的非比寻常。“在这座城里,每天有250人死去,460人出生,15万人戴着玻璃或塑料假眼行走;这里还有500个巫师、600尊雕塑或纪念碑、3万只鸽子。”紧接着,他笔锋一转,轻轻撩开蒙在纽约头上的面纱:野猫睡在曼哈顿的街车底下;石犰狳爬上了高高的大教堂;蚂蚁穿行于帝国大厦犹如置身草丛;秃鹰在哈德孙河边捕食,忽喇喇飞起,留下一地鸽子头;建筑工人、水管工、接线员、清洁工、看门人活动其间,他们从未踏足云端,只是在云层下日复一日用力生活。
特立斯来自美国南方意大利移民家庭,父亲是一名裁缝。身为异乡客,他与上层阶级隔膜甚深,终不能毫无芥蒂地描述他们令人艳羡的生活。因而,他的写作注定是日常的,琐屑的,永远扎根在他熟悉的城市一角。他太希望从庸常中寻找“不寻常”,于是游历街头,采访身边人、身边事,不因其微小而有一丝松懈。读《被仰望与被遗忘的》好比跟随特立斯一起穿越城市,只见他手执摄像机,由远及近、由小到大、由粗而细,引领读者朝着城市的纵深处进发,去探寻与众不同的新世界。
是的,新世界。确切地说,是被霓虹灯覆盖的纽约,也是被媒体刻意屏蔽的纽约。1953年,刚过20岁的特立斯自信满满离开家乡,来到纽约闯天下。从送稿生到特稿记者,他在《纽约时报》一呆就是10年。10年间,他从一个对媒体所知不多的门外汉,逐步成长为熟谙新闻内幕的高手。他很清楚,记者不是理想主义者,而是现实主义者。逼人的现实要求他们动用一切资源去追逐热门题材,所思所想皆是为了制造吸人眼球的头条文章。至于微小、琐碎的城市日常,则可以尽力回避、忽略不计了。

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一个怪圈:新闻是阅过即弃的速生品。人们阅读新闻,如同吞咽速食面,不求品尝美味,但求填饱空空的肚肠。数十年后,再伟大的记者也难逃被人遗忘的宿命,连同他的问题、他的稿件和他的采访对象一起被遗忘。还好,我们还有特立斯,至少他从来没有落入新闻写作的圈套。这样的他野心十足,誓要“将非虚构写作提升到人所未知之境,一探虚构作家之禁臠,与同侪菲利普·罗斯、厄普代克一较短长”。
意思是说,靠作品说话,用故事发声,不必顾忌题材是不是够分量,内容是不是有说服力。今天我们还在谈论他50年前的旧作,应该归功于他独创的“新新闻主义”写作。阅读《被仰望与被遗忘的》是一个缓慢、有趣的过程。你永远不知道特立斯会如何抛出问题,更不知道他会从受访者那儿读到什么潜台词。比如采访,常规的问答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融合场景描写、人物素描的故事。如此一来,林林总总的故事齐聚一堂,几乎要把《被仰望与被遗忘的》变成特立斯的《纽约故事集》。我们读之,常常心生疑惑:不知道到底是新闻借用了小说的形式,曲里拐弯地再现真实世界的一切;还是小说拓宽了新闻的定义,把活生生的事实转化成天马行空的头脑风暴。
好比细针密缕、重工织就的纽约浮世绘,特立斯笔下众生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姿态。比如他谈到写字楼的女秘书,言谈之间像是在议论某个擅于玩弄权术的女王:她不分白天黑夜释放控制欲,仿佛要将城市整个搬来,捏在手里反复揉搓。“她们将占据证交所的位子,主宰空无一人的董事会会议室,向那些看不见的广告人挥舞拳头;她们无须通告就闯进那些商界大亨舒适的办公室,站在听写机前体验发号施令的感觉;她们能让摩天大楼的灯光彻夜不熄。从窗外看去,她们的身影和扫帚来回飞舞,就像一群女巫在施展魔法。”
毫无疑问,这是特立斯的纽约,细碎、草根,拥有无尽活力。在阅读《被仰望与被遗忘的》之前,我们常常自以为是地将纽约想象为流淌着奶与蜜的应许之地。事实并非如此。特立斯奉菲茨杰拉德为偶像,当然知道菲氏穷尽一生只是为了让我们记住盖茨比那张幻灭的脸。那么,特立斯呢?他64年如一日守护他的城市,看过无数张面孔,经历过太多希望与失望,却没有糟糕地陷入绝望。他应该记得身高8.2英尺(约为2.49米)的龙套演员爱德华·卡莫尔。这位羞涩的巨人梦想像彼得·奥图尔一样独立撑起一部大戏。尽管生活并不顺遂,他仍然相信,希望终会来临。只要肯努力,一切皆有可能。
当然,没有人能够预知未来,哪怕敏锐如特立斯。这个城市从来不缺少奇迹,它以招牌式的迅捷、兼容并蓄的胸怀吸引世界各地的人前来掘金。同时,纽约又是阴暗、危险、诡异的代名词,比如9·11。我们不知道特立斯会怎样描述发生在2001年9月的这场恐怖袭击。不可否认,他一直在那里,见证纽约的欢喜与忧伤、危机或劫难。多年之后,纽约巨人卡莫尔步入老年,回望自己的青春,应该不会有太多遗憾━━正是特立斯用手中之笔不断书写、记录,才有了眼前这个丰满多样的纽约。从此,卡莫尔的青春与他的城市牢牢地捆绑在一起,以铅字的形式完整地保存下来,成为经典,成为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