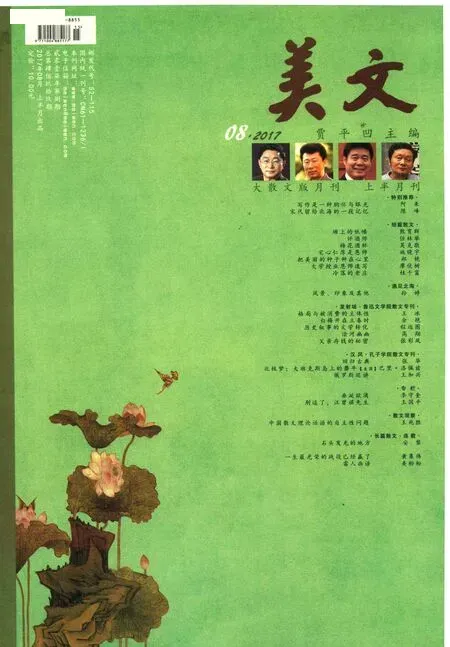把美丽的种子种在心里
◎郑艳
把美丽的种子种在心里
◎郑艳

郑 艳 笔名“与点”,生于七十年代,毕业于湖南师大中文系。曾任长沙电视台制片人,湖南卫视《新青年》栏目编导,《大学时代》杂志采编中心主任。现为《新课程评论》杂志执行主编。已出版《两个人的人生论语》《黄培云院士口述自传》《与点:我的时光之书》等作品。曾获湖南电视奖一等奖、中宣部“百本优秀人文图书”提名奖、“湖湘优秀出版物”一等奖等。
一
我第一次见到戴海老师,是在1992年6月。
那时,我已经接到湖南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并被告知保送生要提前报到。去长沙之前妈妈领着我去乡下外婆家,向亲戚们辞行。同族里有个老人听说我去的是湖南师大,就说,戴家里出去的有个戴海,在那当副校长。然后长辈们纷纷建议,说你们应该去走动走动,将来也有个照应。
爸爸妈妈记下了联系的方式,在送我到学校时,找到了戴海老师的家。
我的父亲母亲是那种很老实的工人,一辈子自给自足,基本不求人。第一次去戴家,当时的心态是为了孩子的前途,有点攀远亲的意思。
没想到,这样的见面,没给我带来世俗眼光中希望得到的实在“照应”,却奇迹般地影响了我今后的人生。
我清楚记得第一次见到戴老师和刘阿姨时的情景。
我们拎着些土特产,敲开戴老师家的门。进门后,妈妈自我介绍说,我是戴家某某的女儿,最近才知道您在这里,特地来问好。
见到这样三个自称是来自老家的陌生人,还带了些东西,在我们见面的最初几分钟,我觉得屋子里的主人除了礼貌的客气之外,有着警惕。
后来,听说这家孩子已经被保送到师大的中文系,特别是看到我带去的材料,知道这个孩子确实成绩不错时,戴老师和刘阿姨都笑了。
“我们以前一直在新疆,和老家没有多少联系。回长沙后,有这样那样的人上门来,希望解决各种问题。我们确实不愿意那么做。刚才看到你们,以为……”
然后几个大人聊起家常。我第一次知道戴老师的老家和外公家是紧邻,两家共一间堂屋。戴老师把外公称作他童年的启蒙老师。
“你的外公其实非常好学,可惜生不逢时。”
戴老师的母亲去世很早,后来,少年的他随父亲到长沙,慢慢和老家失去了联系。现在,我们的突然出现让他打开了记忆的闸门,许多童年往事都蹦了出来。
这样,我认识了一位生动的长者还有他善良的妻子。
他们对我说,大学四年对人生而言是非常宝贵的,一定要坚持不断地学习。
二
我记住了他们的话。现在回首,觉得我的大学过得还算充实与丰富。这一切,都与戴老师密切相关。
戴老师当时是主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那些年每一届新生入校,他都会到每个系去给学生做演讲。可以这么说,数以万计的青年,进入大学的第一课,是戴老师上的。那时的师大,戴海老师是大家心目中的“学生头”,他的演讲很有感染力,而且又总是和学生在一块。当时不流行用“名人效应”这样的词汇,那些年在师大,戴老师是颇具“名人效应”的。他的举动常常引起大家的关注,同学也热衷于谈论他,说是北有李燕杰南有戴海呢——常能听到诸如此类的议论。
我从来不参与这些议论。
自从第一次到戴老师家见到他们后,18岁的我就感觉到,我认识了一对正直的师长,在他们眼皮底下学习和生活,我只有不断努力才是。
接下来的大学生活,我真的很努力,而且,我没有告诉别人我认识戴海老师,甚至,在公共场合,有些刻意地对他敬而远之。
只是到了周末,我没有回家时,会跑到他们家去“打牙祭”。饱饱地吃上一顿,还得进行“思想汇报”。回到寝室时,不仅肚子饱饱,脑子更是饱饱。然后,那段时间更努力些。
现在想来,人在18岁到20来岁求学的时候,虽说已经成年,其实还是处在不自知的阶段,这时候遇到好的老师,实在是人生大幸。
在当时,我真是想得比较简单,戴老师是个正直的人,是个注重全面发展的人。他不会因为谁是他的亲戚而另眼相看,他注重的是实实在在的努力和实实在在的成绩。我知道我的情况他都会了解,所以我只能老老实实地去努力。
我大一下学期就参加学代会,参与校学生会委员的竞选,在那样大的礼堂里,我以最小的年龄去发表竞选演讲,虽然“镇定自若”;我不断练习写作,在各种报刊上发表文章,但基本不在同学中间张扬;业余时间和假期,我到报社和杂志社去见习。寒冬腊月,好多同学都不愿意出门,我却每天来回转公共汽车,有段时间奇冷,依然坚持住了。大三,当师大学生会副主席,参与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也不忘提醒自己:多读书,多读书……
所有这些,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我觉得戴海老师在关注我的成长,我不能丢脸。
三
大学临近毕业某天,我去戴老师家吃饭。晚饭后,他把我叫到阳台上,指着对面山上的松树枫树对我说,你就要参加工作步入社会,在喧嚣的人事中要学会保持好的心态,要努力保持单纯美好的心情,多多感知自然的变化,树儿发芽花儿开放,你要用心去感受。
我点头。
从小在钢筋水泥丛林里长大的我,对于自然,缺乏真正的接近。直到在岳麓山下读大学,才开始与自然多些亲近。戴老师特别强调与自然的接触,他说,要保持天性和灵气,要多读好书多多融入自然。
说到“融入”他加重了语气。
多年的职业生涯,我发现记者这个行当,真让人眼界大开。你可以接触各色人等,可以感知最新的变化。但是,这也是一个让人特别容易迷失的行业。太容易见到流光溢彩的生活,你会比较难的以爱心以沉静待人处事。
这些年里,我开始深刻地体会戴老师和刘阿姨带给我的影响。
多读好书多多融入自然。
日积月累的,读好书和与自然亲近已成为我日常的需要。我按照他们说的,带着发现的眼睛和善感的心灵去迎接每天升起的太阳。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反而越来越真切地懂得,戴老师他们在我的心里撒下了一把种子,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长出各种各样的花来。这些花儿需要不断地浇灌,文学、艺术、大自然、爱心、善良……是这些花儿最好的养料。
心灵里面有了花儿的种子,面对再炫目的状况,也不会那么容易发晕。心灵里面有了花儿的种子,让我无论在多么忙多么热闹的时候,会调节自己,让自己躲起来,哪怕是一小段时间,静下来,听听内心世界的声音。
我会听见一些小家伙在里面哼哼唧唧,这个说:“你得听点新的歌了,这段时间你老是听怀旧的,我都没办法发芽了。”那个叫:“你这两天像祥林嫂,老是说重复的话,得停下来想想了。我已经要枯萎了。”吓得我赶紧去照镜子,看看是否真像祥林嫂了。
心灵里面有了花儿的种子,就像养了可爱的小宠物,会很小心地珍惜。我何其有幸,得到这样美丽的花儿的种子。
四
有件事情,我一直没有告诉戴老师和刘阿姨。
我大学毕业时,通过考试,进入长沙电视台。但是当时师范类职业生改行,手续比较复杂。工作几个月了,手续还没有办齐全。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戴老师。
戴老师写了封信给当时广电局的局长,他熟悉的师大校友,要我交给他。
那封信一页纸,主要内容三段话。第一段介绍我在大学的成绩,第二段说明我通过考试,已经在其领导下的电视台上班,但市教委的手续还没完全办好,请他过问一下。第三段是这样一句话:“该生的品德、才干和将来的工作态度,我可以向局座担保。”
这封信我没有交上去,至今珍藏在我的抽屉里。
甚至,在我参加工作的第一年,我没有和局领导打过任何交道。
我把戴老师的信交到了自己的心里。然后,把心态归零,我不再是一个师大还不错的毕业生,而是一个陌生行业的实习生。我每天早早上班,拖地、打开水,把办公室每个人的杯子洗好,倒上水。然后就去问去学去跑。
一年以后,长沙电视台进行改革,把原有的栏目停掉,推五个新栏目,公开招聘新栏目制片人。部门领导推荐我报名,同事们也纷纷鼓励我,帮着我一块做策划书。
这样,我报了名,通过第一轮第二轮,进入最后的答辩。在会议室里,我坐在圆桌的下方,周围是十几位领导。他们开始提出各种问题。
我记得最后一个问题是主管栏目的副局长提的,他是一位满头银发的长者。
他问我:“你年纪这么小,而我们所处的是文化单位,有一个现状是人们彼此之间不容易服气,如果你当制片人,在这样的氛围中你怎样确立自己的威信?”
我回答:“首先,我认为威信不等于威慑,威信应该是内心的接近与认同,我会用真诚的心和踏实的工作去感染大家。虽然毕业才一年多,但是我已经感到辛勤的努力会有回报。这次我做的方案,同事们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我相信今后他们会一如既往地支持我。另外,我想强调的是,我非常清楚负责一个栏目,将面临复杂的情况,如果我成为制片人,我希望在座的领导给予我充分支持。因为我年龄比较小,我不想在做实际的事情之前,就陷入人事纠葛中,我希望领导们允许我组阁我的栏目,这样,我会更有信心把好的方案变成现实。”
没多久,招聘结果公布出来,24岁的我成为生活类栏目《百姓》的制片人。当时,被同事们笑称为“台史上最年轻的制片人”。
戴海老师写的那封信,就这样装在了我的心里。给我带来很大的压力,也给我带来很大的动力。
我会常常想起那封信,想起那最后一段。有时候,会不知不觉间掉下泪来。
那封信对外而言真是太重了,我觉得自己承担不起。我真不知该怎样努力,才对得起这样一位长者,用他的名誉,为我做担保。
五
那天,读《曾国藩家书》。曾国藩认为,“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
才明白,戴老师对我就是“有所激有所逼”。不光对我,对所有的孩子,他都是这样。
古语云“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这些年来,学生们在长大,戴老师也在不断成长。
他一直调整自己,不断吸收新的知识,结合自己的经验和阅历进行综合分析与思考,然后把加工过的更精华的东西,又传递给学生们。多少年来,他一直在言传身教。只是他的“言传”形式多样,用演讲用上课用聊天用深谈。至于“身教”,我觉得他在用点滴的行为融汇成一把把美丽的种子,然后抛撒开去。而且是尽可能广泛地抛撒开去。
我接住了几颗美丽的种子,种在了心里。同时我坚信有更多的年轻人,也接住了他抛洒过来的美丽的种子。
退休之后,戴老师才开始有了一点属于自己的空间。他把自己多年所想所说的陆续整理出来,他的书稿被中国青年出版社看中,先是《人生箴言录》,后又《秋林拾叶》,然后出版教育随笔《坛边话语》,接着又是日记选集《逝者如斯》。
他还是那么忙。每天上山,读书,给报纸写专栏,准备书稿,还经常被请去做演讲……
他有严重的白内障,医生有条重要的处方是:少看书多休息。他笑着说他注定是要“明知不能为而为之了”。面对他的生命状态,人们可以用很多的形容词,自强不息、诲人不倦、德高望重……但是他身边的亲人,真是会很为他着急。
这几天,我在读戴老师的《秋林拾叶》,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写,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读。面对这样用人生用心血结集而成的作品,我根本没有办法加快我阅读的速度。我想,每一个喜爱读书并且把读好书作为生命需要的人,对书都会有比较强的鉴别力。面对好的书,你读的时候,态度必定庄严。
这本书记下的,是他关于自然和人生的感悟,道德和学识的思考。读的时候,我觉得我不是在“读”书,而是被带入作者日常的丰富生活。在这个过程中我常常惭愧:自己在岳麓山下待了四年,怎么就这么忽略了身边的风景?同时也相信,自己会把这课补上。在这个过程中我还发现,戴老师是多么注重日常的学习和积累。
六
晚上,戴老师领着我重游师大校园。
在校办公楼前他停住,“你闻到香味吗?”
“闻到了,是桂花的香味。都冬天了,怎么还会开桂花呢?”
“噢,这是四季桂,冬天也开的。”
一边走,他一边说。他又问我在学校读书时,是否注意到这几棵樱花树。
“注意过,开花时像一片粉红的云,很漂亮。”
“那你知不知道它们是长沙市最大的几棵樱花树呢?”
“这我就不知道了。”
走着走着,我们听到蟋蟀的叫声。
“我们来晚了,他们的音乐会已经结束了。只剩下这只勤奋的蟋蟀,还在练习呢。”
我们走在学生宿舍旁的木兰路上。
有学生听到他的话语停下来,用小小的声音对同伴说,戴海老师,戴海老师。
也有人拉住他,向他问好。
在中文系前的路上,一个男教师拉住了他,“戴书记,您最近忙什么呢?”
“我每天在家写作业。”
“你可要注意身体,你是个好人,我们都记着你感谢你。”
…………
我站在戴老师身边,隔着半米的距离。
我听着他们的谈话,教学楼有灯光,我可以看见那个男老师真诚的表情。
我站在那里,心里,真的满是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