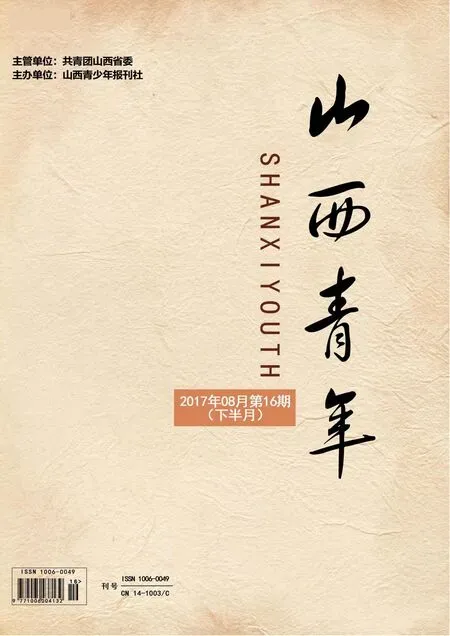浅析贾谊“三表”、“五饵”的民族思想
王 硕
浅析贾谊“三表”、“五饵”的民族思想
王 硕*
渤海大学政治与历史学院,辽宁 锦州 121000
“三表”、“五饵”是贾谊民族思想的核心内容,其战略本质是通过“德战”和物质上的诱降来争取匈奴归附。所谓的“三表”指的是“信、爱、好”,即“爱人之状,好人之技,仁道也。信为大操,常义也。爱好有实,已诺可期,十死一生,彼将必至;此三表也”。所谓的“五饵”是用盛服车乘、盛食珍味、高堂邃宇、音乐妇人和召幸娱乐来招降匈奴,达到“牵其耳、牵其目、牵其口、牵其腹”最终“引其心”的目的。这种通过先进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来改造和同化其他文明的斗争方式,虽然不能像贾谊设想的那样立即奏效,但却比通过武力征伐更容易被接受。
民族思想;匈奴;汉化
一、“三表、五饵”民族思想溯源
中华文明自诞生之初,就一直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处理与周边少数民族关系的问题。而在古代的汉民族观念中一直将周边民族视为不开化的野蛮落后民族。如《国语·郑语》中提到“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非亲则顽,不可入也。”由此可见,华夷之辨的概念最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初具雏形。西周后期,犬戎攻入镐京,周王室被迫东迁,中原政治动荡,周边少数民族也趁机屡屡入侵。
面对来自周边少数民族的侵犯,先秦时期主要形成了两种应对思想。其一是以强大的武力去防御、抵抗或者反击来自周边民族的掠夺,保卫自己的领土和人民。如《竹书纪年》中记载:“周王季伐西落鬼戎”,“周人伐余无之戎”,“周人伐始呼之戎”。《史记·匈奴列传》中也有记载:“武王伐封而营洛邑,复居丰、镐,放逐戎夷于径、洛之北”。到春秋时期,在管仲的辅佐下,齐桓公竖起“尊王攘夷”的旗帜,帮助燕国打败北戎,营救邢、卫两国,制止了戎狄对中原的进攻。战国时期,匈奴常常骚扰中原各国,由于他们善于骑射,长于野战,而秦、赵、燕在战国中期以前的作战部队主要是步兵和战车,行动迟缓,很难抵御袭击和掳掠。所以三国在北边开始大规模修筑长城以抵御匈奴和东胡人的进攻。《史记》记载:“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距胡。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距胡。当是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这种方法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少数民族带来的军事压力,但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从长时间来看民族关系始终紧张。其原因在于,相较于农耕民族,游牧民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较落后,但军事力量较强,对中原诸国的掠夺可以得到大量的物质资源和劳动力。
另一种方法就是用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去诱降同化周边民族,与其进行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文化战”。用“有教无类”的方式“用夏变夷”,所谓“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
在西周建立之初,它的统治者就很注重用怀柔的手段去安抚和招徕周边的民族。《墨子·兼爱中》记载:“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淮南子·要略》中也有记载:“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贿来贡,辽远未能至,故治三年之丧,殡文王于两楹之间,以俟远方。”《尚书·周书旅獒》记载:“明王慎德,四夷咸宾。”这些记载说明了“德战”的思想已经逐渐形成,统治者和思想家们都在思考除了战争以外对付周边民族的方法。
春秋战国时期,一些思想家也提出了用物质文明和思想文明去改变、同化周边民族的办法。如孔子的“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就是用“诚信”和“道德”来感化周边民族。墨家的“兼爱”思想也把当时被视作蛮夷的楚越之人包括在内,主张爱天下之人,《墨子·天志》记载:“譬之若楚、越之君,今是楚王食于楚之四境之内,故爱楚之人;越王食于越,故爱越之人。今天兼天下而食焉,我以此知其兼爱天下之人也。”《吕氏春秋》中记载:“蛮夷反舌殊俗异习之国,其衣服冠带,宫室居处,舟车器械,声色滋味皆异,其为欲使一也。”“圣王”只有“审顺其天而以行欲”,如此“执一”才可“四夷皆至”。这些方法的本质就是利用中原丰富的物质资源去迎合周边民族的欲望,从而进一步的吸引他们向中原文化靠拢,最终可以兵不血刃的完成对他们的同化。
二、“三表五饵”民族思想的提出和西汉的践行
周秦以来,社会逐步从列国林立,到局部地区的统一,再到大一统。贾谊所处的时期是一个民族形势空前严峻的时期,他以儒家和法家的思想为主体,融合先秦时期其他各派的对外思想,分析了以往与周边民族接触的具体事件,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加上自己的思考,凭借远超自身时代的眼光总结出来了一套对付匈奴的方法。其“三表、五饵”思想的实质,便是在大一统的前提下,用中原先进的物质文明去诱降、同化周边的少数民族,使其最终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在民族政策上的概念和方法的集大成者,他在对汉文帝的上书中首先陈述了当时汉匈双方的地位。他认为:
天下之势方倒县,窃愿陛下省之也。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蛮夷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是倒悬之势也。
窃料匈奴控弦大率六万骑,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五六三十,此即户口三十万耳,未及汉千石大县也。而敢岁言侵盗,屡欲亢礼,妨害帝义,甚非道也。
匈奴侵甚侮甚,遇天子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无已也。①
原本应该处于天子之下的蛮夷,居然屡次侵扰边境,侮辱汉朝,反而是处于天子之上,形成了倒悬之势。由于信息的局限性,贾谊对匈奴实力的估计并不准确,但对双方所处形势的判断还是准确的。据史书记载,文帝时期匈奴仅大规模入侵就有三次,分别为
其三年夏,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为寇。
孝文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骑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
军臣单于立岁余,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略甚众。②
至于小规模的侵扰,更是屡有发生。虽然汉朝也进行了不同规模的反击,甚至汉文帝本人也有“欲自击匈奴”的冲动,但总体形势还是匈奴占据优势,汉朝基本采取守势。
军臣单于攻汉时贾谊已经去世十年,但他生前曾提出过以“战德”为核心战略思想,即:
强国战智,王者战义,帝者战德。故汤祝网而汉陰降,舜舞干羽而南蛮服。今汉帝中国也,宜以厚德怀服四夷,举明义博示远方,则舟车之所至,人力之所及,莫不为畜,又孰敢纷然不承帝意?③
认为只要皇帝广施仁德,能做到“德被蛮貊四夷”,那么“子孙数十世”都可受益。将与匈奴的斗争方式,从国家政权层面的军事战争方式,转变为以争取匈奴民众脱离单于统治而归附汉朝的和平演变方式。
虽然西汉前期,通过和亲的方式,以及对于匈奴的诸多“馈赠”,已经在客观上发挥着“和平演变”的作用。但是贾谊“三表”、“五饵”策略的本质是争取匈奴民众的归附,由于匈奴普通民众地位较低,直接对匈奴进行“馈赠”的物品基本上都被匈奴贵族和少数上层人士所占有,并没有对基层人民产生诱惑,所以单纯的“馈赠”物品,只是使得“单于好汉缯絮食物”,并不能很好的与单于“争其民”。而汉朝在文帝时期开始与匈奴“通关市”,才正式使匈奴的普通民众感受到了来自中原文明的物质诱惑。甚至到了汉武帝时期,在与匈奴进入实际上的战争状态下,“关市”依然发挥着经济联系的作用,《史记》中记载:“自是之後,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於汉边,不可胜数。然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贾谊在论述“关市”的作用时说:

可以看出贾谊也肯定了“关市”对匈奴民众的所发挥的诱惑作用。到了汉景帝时期,史书中未见匈奴大举入寇的记载。或许,在风调雨顺的背景下,通过与汉人进行和平的物资交换,匈奴人的社会生活,可以基本得到物质方面的满足,因此不必借助对外寇掠的方式。
到武帝即位之初,匈奴已出现了“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的情况。但之后汉朝对匈奴的方针转变为以武力攻伐为主,数次发动大规模对匈奴的军事打击,使匈奴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严重下降,加上西域诸国亲附汉王朝脱离匈奴控制,使得匈奴的生存环境日益困窘。这样的情况下,虽然有大量的匈奴人投降汉朝,例如,在军臣单于死后,“军臣单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为单于,攻破军臣单于太子於单。於单亡降汉,汉封於单为涉安侯,数月而死。”之后又有“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降汉,凡四万余人,号十万。”但却不是贾谊所设想的被汉朝的物质诱惑和精神文明所征服,而是迫于军事压力而投降。
三、汉武帝之后“三表”、“五饵”民族思想的践行
武帝之后,匈奴外部受到汉朝强力的打击,失去了部分赖以生存的土地和大量的人口,内部在宣帝时期发生了“五单于争立”事件,导致统治阶级内部大乱,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呼韩邪单于归附汉朝。此后,直至新莽时期,中原政权对于匈奴的物质赏赐和援助,甚至超过了西汉前期。《汉书》中记载宣帝时赐给呼韩邪单于“冠带衣裳、黄金玺戾绶、玉具剑、佩刀、弓一张、矢四发、棨戟十、安车一乘、鞍勒一县、马十五匹、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被七十七袭、锦绣绮縠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到了元帝时期“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
东汉时期,由于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汉王朝灵活运用并不断调整对匈奴的诱降政策,采取扶南抑北的方针,使得整个南匈奴基本处于汉王朝的控制之下。甚至使匈奴到了“生长汉地,开口仰食,岁时赏赐,动辄亿万,虽垂拱安枕,惭无报效之地”的地步。
在这一时期的匈奴墓葬的随葬品之中,也发现了大量的汉族物品。如宁夏同心县倒墩子墓地出土了大量的汉式陶罐和五铢钱,李家套子墓地除了出土了同样的陶罐和五铢钱外,还有大量的铜器和铁器。远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中央省色楞格河畔诺彦乌拉山的诺彦乌拉墓,除了出土了来自中原地区的铜灯、铜壶、铜镜外,甚至还有带有“仙境”、“皇”等汉字的丝织品。经考证这些墓地的时间是在西汉晚期至东汉中晚期之间。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中原物品已经大量进入匈奴普通民众和贵族的生活中,受到中原物质引诱的匈奴已经有了主动变革,主动汉化的趋势。
周边少数民族在体会到“三表、五饵”的长远利益后,已经不仅仅只是倾心于中原的物质文明,而是在整个的国家制度和思想文化方面都开始积极向中原文明靠拢。在东汉之后的魏晋十六国时期,后赵建立者石勒,推行中原的封建赋税制度,停止“收掠野谷”的掠夺方式。夺取幽冀后,又“始下州郡阅实人户,户资二匹,租三斛”。前燕建立者慕容皝重视农业生产,曾下令“苑囿悉可罢之,以给百姓无田地者。贫者全无资产,不能自存,各赐牧牛一头”。前赵刘曜尊重儒教,在攻克长安后“立太学,选民之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择儒臣以教之”。这种从制度到文化都逐步汉化的过程基本上贯穿了整个十六国。
贾谊的“三表”、“五饵”之策,实质就是运用经济文化之长,化彼同此,达到民族融合的目的。应当承认,先进的经济文化,乃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基础。贾谊深知汉文明较高,匈奴文明较低,故所论是合理的,他的真知灼见在后世也一次次被践行,例如北魏的孝文帝改革,就促成了鲜卑族与汉民族的融合。
四、结语
宋代的程颐曾经评价贾谊的“五饵”:“贾谊有五饵之说,当时笑其迂疏,今日朝廷正使著,故得着许多时宁息。”同一时代的朱熹也说:“伊川尝言,本朝正用此术。契丹分明是被金帛买住了。今日金虏亦是如此。”可见,在程朱看来,贾谊“三表”、“五饵”之说作为一种对付匈奴的怀柔手段,在宋朝也被统治者用来对付拥有强大武力的辽朝和金朝。反观当时的金朝,在受到汉族先进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吸引的情况下,也积极开始自己的汉化进程。
不仅仅是中国,整个世界史也是如此,马克思曾经说过:“相继征服过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尔人,不久就被当地居民同化了。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化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⑤贾谊的“三表”、“五饵”论也是符合历史规律的民族观。
[ 注 释 ]
①贾谊.新书(卷四).卢文弨,校.中华书局,1985.
②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73.
③贾谊.新书(卷四).卢文弨,校.中华书局,1985.
④贾谊.新书.卢文弨,校.中华书局,1985.
⑤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6.
王硕(1990-),男,汉族,河北沧州人,渤海大学政治与历史学院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生。
K
A
1006-0049-(2017)16-007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