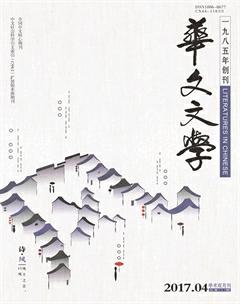高行健作品中的女性与道
刘剑梅
摘要:海外汉学对高行健作品的研究已经发展到一定的规模,最大的争议点是关于他对女性的描写和塑造。本文探讨高行健小说和戏剧中的哲学维度和性别维度,通过研究其作品中的道与女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来展示其深刻的关于女性个体命运的禅悟。在禅的场域里,欲望和两性关系是个体通往禅悟的必经之路,而女性的角色不可避免地与个体的自省和自觉紧紧相连。萨特的“他人是地狱”的命题,着重的是人与社会、人与他者的关系;而高行健的“自我是地狱”的命题,则把对自我的认知看成是当代文学的重要主题。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必须面对自我,反观自我,直面现代社会中自我的空虚和妄念,孤独与绝望,躁动与不安,唯有对自我“幽暗意识”的充分认知,才能够最终走出自我的地狱。高行健对女性的描写往往有意识地挑战传统文化对女性的定义,他非常重视女性不同于男性的生理和心理构造和特质,并由此来探寻个体生存的真实困境。
关键词:老子;庄子;禅宗;女性主义;道;有待;无待;性别维度;哲学维度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7)4-0014-09
海外汉学对高行健先生作品的研究已经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不过关于其小说和戏剧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则争议不断。有的学者给高行健贴上了“厌女症”的标签,比如Kam Louie(雷金庆)评论《灵山》时,认为“其厌女症的幻想与中国传统观念中对年轻女性的定义不谋而合,这些年轻女性似乎只有一步之遥就会被性欲望的洪水卷走。”①美国学者罗鹏(Carlos Rojas)评论《一个人的圣经》时,认为小说中描述的“女人性”(femininity)与高行健对官方政治话语的拒绝最终混为一谈,而“小说叙述者在某种程度上无视他自己的社会政治姿态里包含的有系统的厌女症。”②Belinda Kong分析《逃亡》的时候,把剧中女孩的被强奸阐释成“一种惩罚的逻辑——针对她对男权真相政治的大胆逾越,以及她勇敢要求的性解放,归根结底,针对她所扮演的女权主义者的角色。”③类似这样的批评声音,也可以在其他学者的论述中找到,即使这些学者的批评态度相对温和一些,他们还是认为高行健对女性的塑造有问题,认为他对女性的描写只是他自己文化身份认同和心理焦虑的折射,并非真正关心女性问题和女性命运。④
然而,跟以上的这些批评声音相反,以Mabel Lee(陈顺妍)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则认为高行健在其小说和戏剧中对女性形象的描写,正好体现了他独特的美学与哲学的辩证模式,而这一模式使他能够细腻地表现独特的女性思想和女性的内心世界。比如,通过探讨高行健在多层次的戏剧中对女性心理的表现,Mabel Lee挑战了以往那些给高行健的女性观贴上“厌女症”标签的研究,充分肯定了他对女性的同情态度,以及对女性情感、心理、无意识和复杂的内心世界的探索。⑤另外一位汉学家Mary Mazzili也同样指出“厌女症”的标签太过简单武断,完全忽视了高行健戏剧中关于性别问题所呈现的极其复杂和流动性的再现,“最好的例子之一就是《生死界》,在这个剧里,高行健运用复杂的表现方式来探寻性别问题,通过一个女人的故事来揭示女性的生存状况。”⑥
笔者将延续Mabel Lee, Gilbert Fong(方梓勋),Terry Siu-han Yip(叶少娴),Kwok-kan Tam(谭国根),and Mary Mazzilli等学者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探讨高行健小说和戏剧中的哲学维度和性别维度,通过研究其作品中的道与女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来展示其深刻的关于女性个体命运的禅悟。在禅的场域里,欲望和两性关系是个体通往禅悟的必经之路,而女性的角色不可避免地与个体的自省和自觉紧紧相连。如高行健所说的:“我眼中的女性无非是我自己制造的幻像,再用以迷惑我自己,这就是我的悲哀。因此,我同女人的关系最终总是失败。反之,这个我如果是女人,同男人相处,也同样烦恼。问题就出在内心里这个自我的醒觉,这个折磨得我不安宁的怪物。人自恋、自残、矜持、傲慢、得意和忧愁,嫉妒和憎恨都来源于他,自我其实是人类不幸的根源。那么,这种不幸的解决又是否得扼杀这个醒觉了的他?”⑦也就是说,在两性关系中,男性眼里的众多女性形象,无法排除男性自我对她者的幻想和塑造;而反之亦然,女性眼里的众多男性形象,一样无法排除女性自我对他者的幻想和塑造。何为真实?何为幻相?正如“佛告须菩提:万相皆虚妄,无相也虚妄”⑧。对于高行健来说,两性之间纠缠不清的争斗,虽然并不排除其来源于社会、历史及文化原因——男女关系的不平等,但是归根到底,更是来源于“自我”。也就是说,“自我是自我的地狱”——这应该是高行健最独特的文学理念之一。
萨特的“他人是地狱”的命题,着重的是人与社会、人与他者的关系;而高行健的“自我是地狱”的命题,则把对自我的认知看成是当代文学的重要主题。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必须面对自我,反观自我,直面现代社会中自我的空虚和妄念,孤独与绝望,躁动与不安,唯有对自我“幽暗意识”的充分认知,才能够最终走出自我的地狱,所以个体的自省与自觉往往被高行健看成是至关重要的走向个体啟蒙和个体自由的通道。在高行健的小说和戏剧中,一方面我们看到,在他眼里,女性是由社会和文化所塑造的,所以他对女性的描写往往有意识地挑战传统文化对女性的定义,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他非常重视女性不同于男性的生理和心理构造和特质,重视这一构造所形成的女性独特的无意识、内心世界和女性思想,并由此来探寻个体生存的真实困境。
女性和柔的力量
高行健的《灵山》充满了禅悟,给予文学评论家大量阐释的空间。“灵山”并不是地理意义上的一个具体的存在,而是每一人都需要自己去寻找的精神家园,这个精神家园可以是如同庄子哲学倡导的个体精神的绝对大自由,也可以是隐隐约约支撑着人们在生存困境中继续前行的内心的微光,不管怎样,在小说中高行健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答案,而是让仿佛是上帝的青蛙,眨巴一只眼睛,另一只眼圆睁着,一动不动地望着叙述者,也望着我们每一位读者。虽然“什么是灵山?”“什么是自我?”在小说中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叙述者的心灵之旅已经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意义就在这不断寻找、叩问和领悟的过程中。
高行健对欲望和两性关系的描写,一样属于他禅悟的一部分,属于他对生命终极意义叩问的一部分,包含着多层次的意义,有时甚至如《八月雪》中慧能的禅悟,只可意会,只可“以心传心”,而不可言传。六祖慧能曾说:“一切万法不离自性。”五祖弘忍大师曾说:“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⑨高行健的许多作品都围绕着对“自性”的认知,即使写到女性,也无一例外。女性既是他禅悟过程中关于“道”的载体,也可以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在彷徨和焦虑中,在男女关系的一次次挫折里,更加真切地了解和认知多层次和复杂的自我。《灵山》中出现的一些寓言式的故事,尤其俱有这种多义的功能,引发读者无穷无尽的阐释。
《灵山》第48章中,高行健重新讲了一则晋代笔记小说中的故事。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位非常有野心有权势的大司马,家中突然来了一位化缘的比丘尼,自愿从远方前来替他的老母亡灵做斋戒,并为他祈福消灾。这位女尼每日午后更香之前,必先沐浴一番,长达一个时辰,日日如此。有一次大司马偷窥到,这位女尼在沐浴时,竟然剖腹,把肝脏和盘掏出,细细清洗,洗完之后,再把肝脏塞入腹内,身体竟然完好如初。大司马惊愕困惑之余,请教女尼,她说“君若问鼎,便形同这般”⑩。后来这位野心勃勃图谋篡位的将军再也不敢越轨,守住了为臣的本分。这个神秘女尼剖腹洗肠的故事,在高行健的《生死场》做为一场剧的“伴演”(sideshow)再次出现,衬托出女主人公的内心纠结。对于这则寓言故事的多义性,高行健在《灵山》中写道:
……原先这故事自然是一则政治训诫。
你说这故事换个结尾,也可以变成道德说教,警戒世人勿贪淫好色。
这故事也还可以变成一则宗教教义,规劝世人,依佛门。
这故事又还可以当作处世哲学,用以宣讲君子每日必三省其身,抑或人生即是痛苦,抑或生之痛皆出乎于己,抑或再演绎出许许多多精微而深奥的学说,全在于说故事的人最后如何诠释。(273页)
不错,这故事可以从政治、宗教、道德伦理、处世哲学等角度进行阐释,一种阐释或一个角度根本无法完全涵盖其丰富的寓意。既然这故事中的女主角是比丘尼,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想到性别问题,当然还可以从女性自我与男性的关系,或是女性自我与世界的关系的角度去阐释。学者叶少娴和谭国根(Terry Siu-han Yip and Kwok-kan Tam)曾经提出应该从“无性别/本我”的角度来阐释高行健的作品,也就是说,高行健早已超越了男女性别的对立,所以女尼剖腹洗肠的故事实际上传递了一种哲学的寓意:“象征着女尼有意识地脱离与尘世之间的道德联系。”{11}这样的解读,超越了男女性别对立,确实提供了一个非常可信的阐释,因为符合高行健超越两极对立的思想,就像高行健曾经说过的:“一分为二、非此即彼、二律背反和辩证法这种二元论都把事物和问题简单化和模式化了。”{12}不过,我还是想尝试从性别和主体的哲学维度来重新阐释这则寓言故事。
在《灵山》的第48章中,叙述者“你”想讲述这个故事,并非因为他是一位历史学家,或是他有政治野心,或是想做道学先生,他想讲述的原因很简单:一是因为这个故事“纯而又纯”,二是因为他想对“她”讲述。这个“她”,也许是天底下所有的女性,也许是他臆想出来的女性,不管怎样,“她”也同时折射出叙述者自身的欲望和焦虑。在此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这个故事特地要对着一位女性讲述?这样一个有性别取向的故事隐藏着什么样的“道”?类似加缪的《西西弗神话》,每日把大石头推上山然后再无奈地看着它重新掉回谷底,女尼每日充满仪式化的剖腹洗肠的举动,不也指涉着个体存在状态的荒诞感?
这故事中的大将军本来野心勃勃,想要篡权,但是自从看了令他惊恐的女尼的剖腹洗肠,他马上放弃了对更高权力的渴望和追求。女尼让将军对自我有了反省,那天天需要清洗的血肠,就是对外界的权力、名誉、金钱等的无休无止的渴求,只有放下野心和欲望,才能获得个体的自由。女尼所扮演的“启蒙者”的角色,优于强悍的代表男性英雄主义的将军,这其中又有另一层深刻的含义,其实也表达了高行健相当独特的关于性别的命题,跟老子的柔弱胜刚强的哲学相通。老子在《道德经》第二十八章说过,“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13}根据刘笑敢的阐释,“‘知其雄,守其雌虽然不是直接指涉男女问题,但是毕竟隐含了在两性之间更推崇雌性特点的价值取向。”{14}老子哲学总是把雌性和“柔”联系在一起,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15}这一联系揭示了女性特点优于男性特点,也同时表现了老子的自然、容纳、柔弱、无为等概念和价值观。在高行健重新叙述的这则故事里,我们也同样看到了他接近老子哲学的推崇雌性特征的倾向。
高行健的舞蹈诗剧《夜间行歌》不仅探索了女性独特的内心世界,而且提供了一个从哲学、诗歌、舞蹈的角度来表现女性意识、女性认知和性别问题的方式,更重要的是,他也表達了推崇女性特征的倾向。跟《生死场》一样,这个舞蹈诗剧把女性无意识和内心世界展示在舞台上,通过艺术的表现方式来传达形而上的关于生命普遍意义的思考,是他关注女性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在《灵山》中,当高行健描写到女性时,只是统一用“她”指称,从而“构成一个复合的女性形象,或是女性的多重变奏。”{16}可以说,这样的设计,还是从男主人公的观点出发,让多重身份的她融合了男性虚虚实实的想象。但是在《夜间行歌》中,高行健则把重心完全放在女性身上,赋予女主人公“你”、“我”、“她”人称,就像《灵山》中的男主人公所拥有的“你”、“我”、“她”人称,都是自我的三种不同立场的体现。
当谈到对“你”、“我”、“他”三种人称的运用时,高行健曾经这样解释:
“你”一旦从自我中抽身出来,主观和客观都成了观审的对象,艺术家盲目的自恋导致的难以节制的宣泄与表现,不得不让位于凝神观察、寻视、捕捉或追踪。“你”同“我”面面相觑,那幽暗而混沌的自我,便开始由‘他那第三只眼睛的目光照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