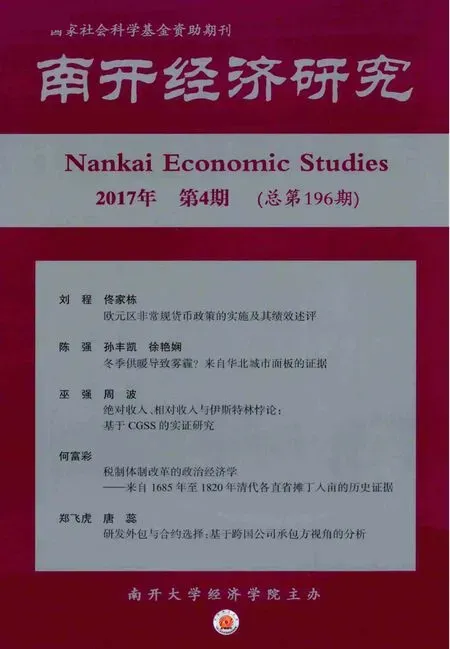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伊斯特林悖论:基于CGSS的实证研究
巫 强 周 波
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伊斯特林悖论:基于CGSS的实证研究
巫 强 周 波∗

利用CGSS数据,本文检验了中国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在考察了四种相对收入度量指标的特点之后,本文首选相对收入指标,并发现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均对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于低收入者而言,绝对收入对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相对收入无显著影响;对于高收入者而言,相对收入对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绝对收入无显著影响。究其原因,低收入者绝对收入的增加能改善其对家庭关系、人际关系和自身健康状况等方面的满意度,而高收入者则不能如此,但高收入者能通过相对收入的提高来改善其对自身居住社区的满意度。因此,在制定收入分配政策时,对于低收入者,我们需要提高其绝对收入水平;对于高收入者,我们在调节其收入时需要关注其相对收入水平的变化。
收入;相对收入;幸福感;伊斯特林悖论
一、引 言
自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需要转变,经济结构也需要调整,这些工作的着眼点在于使得经济发展为人民群众增加幸福感和获得感。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与此同时,收入分配问题一直是人们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与伊斯特林悖论相关,该悖论描述的是幸福感①无特别说明,本文的幸福感均指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与经济增长不同步的现象。迄今为止,已有不少关于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但是人们对于高速的经济增长是否带来了更高的幸福感并未达成共识。Brockman等(2009)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发现,1990年至200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较快而人们的幸福感均值却下降了0.9。尽管从世界幸福感数据库的数据来看,2001年至2012年,中国公民的幸福感在1—4分序列中增加了0.13,在1—10分序列中增加了0.39(Veenhoven,2014),但是,盖洛普的追踪调查发现,从1999年到2010年,中国居民生活满意度整体上是一条奇怪的“水平线”,城镇居民的生活分值上升了0.43,而农村人口则下降了0.13(Crabtree和Wu,2011)。
经济增长往往表现为人们绝对收入的增加,而已有研究关于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存在不同认识。绝对收入影响幸福感的理论基础来源于需要实现理论:一方面,收入增加有利于生理和安全需要的满足,所以绝对收入越高幸福感越强;另一方面,收入增加不一定会让爱、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得到满足,所以绝对收入提高不一定会提升幸福感。此外,适应理论(Diener等,1999)也认为绝对收入增加不是总能提高幸福感。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不同影响在大量的经验研究中得到检验:(1)收入对幸福有正向影响,例如Veenhoven(1991)、Frijters等(2003)、Stevenson和Wolfers(2007)、亓寿伟和周少甫(2010)、邢占军(2011)、刘军强等(2012);(2)收入对幸福有负向影响,例如Haring 等(1984)、Ng和Wang(1993)、Ng和Ng(2001)、Ng(2003);(3)收入对幸福无影响,例如Ravallion和Lokshin(2001)、闰丙金(2012);(4)收入对幸福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例如Seligman等(2006)、田国强和杨立岩(2006)、张学志和才国伟(2011);(5)幸福与收入的因果关系,例如Diener和Tov(2007)、Pischke(2011)。
与此同时,部分学者更为关注相对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联系。其理论基础来源于社会比较理论(Wood,1996)、欲望理论(Rojas,2007),认为个人与社会中其他人相关情形的比较结果、个人欲望中已满足的部分占总欲望的比例等相对值会影响幸福感。关于相对收入对幸福感影响的经验研究一般认为其影响是正向的(Clark 和Oswald,1996;McBride,2001;Ferrer-i-Carbonell,2005;Luttmer,2005;Fischer和Torgler,2008;裴志军,2010),也就是与别人相比收入越高或是比自己预期的收入高都会有较高的幸福感。当然,相对收入与幸福感的正向关系也有例外,朱建芳和杨晓兰(2009)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发现中国人在1995年、2001年及2006年的相对收入与幸福呈正向关系,而之前的1990年则显示相对收入与幸福呈负向关系。其认为该负向关系与当时的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相关,高收入者并未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
Easterlin等(2010)进一步阐述相对收入是理解伊斯特林悖论的一把钥匙,将“悖论”描述为当一个国家的主观幸福感受经济发展影响而上升到一定程度时,它可能出现停滞或下降状态,因为社会平均收入的增加会抵消一部分幸福感的增加。换句话说,相对收入的下降会抵消绝对收入上升带来的幸福感。
目前的相关研究已从诸多方面增加了我们对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认识,但仍存在如下问题:(1)在相对收入的概念下存在诸多度量指标,导致研究结论的可信程度需要再讨论;(2)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不确定,尤其是国内最近的研究成果在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上仍未达成一致;(3)相对收入与绝对收入对幸福感存在差异化影响的原因仍不明晰。本文确认了不同相对收入指标的有效性,并在此基础上利用CGSS数据考察不同收入群体的收入对其幸福感的影响。
二、相对收入度量指标的有效性及其选择
至少有四种指标可用于度量个人的相对收入水平,包括:自我评价的相对收入(Graham和Pettinato,2001;朱建芳和杨晓兰,2009;官皓,2010;张学志和才国伟,2011;闰丙金,2012)、与主观贫困线比的相对收入(Rainwater,1994;罗楚亮,2009)、与自身以往比的相对收入(Graham和Pettinato,2001;罗楚亮,2009;任海燕和傅红春,2011;闰丙金,2012)、与参照组比的相对收入(Van de Stadt等,1985;Clark和Oswald,1996;Ferrer-i-Carbonell,2005;Fischer和Torgler,2008;罗楚亮,2009;裴志军,2010;何立新和潘春阳,2011;任海燕和傅红春,2011)。这些指标的特性可以从客观性和精确性两个维度来评价(如图1),客观性用来衡量此指标是由客观数据计算得出还是由个人主观判断得到,精确性用来衡量此指标能在多大程度上精确度量出相对收入水平的差异。

图1 相对收入度量指标的特性
自我评价的相对收入主观性最强、精确性最低,其典型的提问方式如:“您的收入在当地处于什么水平?”(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2008)、“考虑一下您家在税收和其他扣除前所有的工资、薪水、保险金及其他收入,请选择您家属于哪个收入组?”(世界价值观调查,1990、1995、2001)。这种衡量方式极大地依赖于个人的主观判断,评价的结果常与实际上的收入水平产生差异,Graham和Pettinato(2001)对拉美17国的数据分析发现,在10级的经济地位评价中将自己评为最低等级的个体的平均收入实际上比将自己评价为次低等级的个体平均收入要高,而将自己评价为最高两个等级的个体的平均收入却比六到八级的平均收入要低。但正由于主观性强,自我评价的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也高,因为个体对刺激的知觉比实际的刺激在预测幸福感上更重要(Diener和Lucas,2000)。从认知的角度而言两者都是对自身生活状态的判断,只是前者强调生活的某一方面,后者则强调整体状态。需要注意的是,二者的关系取决于个人的预设,如果个人事先认为收入越高越幸福,那么利用数据分析的结果就是二者正相关,反之则相反。例如朱建芳和杨晓兰(2009)发现中国人自我评价的相对收入在1995年、2001年和2006年对幸福感有正向影响,而1990年则是负向影响,可以理解为1995年之后中国人认为收入越高越幸福,而在1990年前后则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价值观的改变带来了相对收入与幸福感间不同的相关关系。
与主观贫困线比的相对收入主观性强,但较为精确,其典型的询问方式为:“根据您家的实际情况,您认为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每月/年需要多少钱”(中国城乡住户调查数据CHIPS)。以这一指标来度量欲望高低,即如果家庭的主观贫困线越高,则认为其欲望也越强,反之则越弱。之后再将其实际收入与主观贫困线相比较,可得出个人收入相对于贫困线的水平。此指标在个人收入与主观贫困线差距不大时能较为有效地预测幸福感,差距较大时则预测效度降低。
与自身以往比的相对收入同样是一种主观评价,但由于有客观的比较对象,其精确性比与主观贫困线比的相对收入更高,其典型的提问方式为:“与三年前相比,您认为您的社会经济地位是:上升了、差不多、下降了?”(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但这种方式的问题在于其度量的更多是自身绝对收入的变化,而与我们一般意义上的相对于他人的“相对收入”概念差异较大。
与参照组比的相对收入客观性强,但精确性差,因为参照组的选取对度量结果的影响大,而对于如何选取却并无定式。Van de Stadt等(1985)按照教育水平、年龄和就业状况来定义参照组,Ferrer-i-Carbonell(2005)使用教育水平、年龄和地理区域选择参照组,裴志军(2010)以乡镇人均收入为参照群体的收入。Clark 与Oswald(1996)则设计了一个包含地区、年龄、性别、健康等因素的收入方程,然后用估计出来的收入方程预测某类人的收入,以此作为这一类人的参照收入。选择不同的参照组得到的研究结果事实上需要不同的细致的解释。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没有既客观又精确的指标可以衡量相对收入,任何研究都需要根据研究目标选取合适指标。本研究主要讨论相对收入和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一方面需要指标的客观性较强,另一方面需要指标衡量的是不同个体间的收入差异。鉴于此,本文首选与参照组比的相对收入指标,并将与其余几个指标度量后得出的收入与幸福感关系进行比较。
三、数据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数据来自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将2003年、2005年、2006年、2008年、2010年五年的数据合并之后进行统计分析,其中剔除了收入或其他人口统计学特征变量缺失的样本。CGSS中的幸福感是用单一指标度量的,关于单一指标的主观幸福感的有效性问题,刘军强等(2012)曾对此进行综述。一般认为主观幸福感至少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多维性,二是易变性。由于主观幸福感是多维的,要通过问卷调查准确衡量就需要设计多个问题,通过综合各个问题的情况来衡量(Lucas等,1996)。同时,由于主观幸福感作为一种感觉并不是长期稳定的,要精确衡量就需要在不同时点采集幸福感数据并最终拟合出一个幸福感(Kahneman和Krueger,2006;Collins等,2009)。这些衡量主观幸福感的方法尽管有较高的精确度,但实施的成本较高,获取大样本数据存在困难。由单一问题获得的主观幸福感数据成本相对较低,其可靠性与有效性也在可接受的范围内。Diener等(1999)的研究认为这样的数据是可靠的;Wilson(1967)通过比较自我评估和专家评估的幸福感水平,证明这样的衡量方式是有效的;Easterlin (2003)的综述性文章中也认为这种数据的可靠性、有效性和可比性都达到了用于科学研究的水准。
就幸福感变量的具体定义而言,2010年和2008年对五个等级的定义与其他年份略有差异,2010年为“很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居于幸福与不幸福之间、比较幸福、完全幸福”,2008年为“很不快乐、不太快乐、普通、还算快乐、很快乐”,而2003年、2005年、2006年三年相应的定义则为“非常不幸福、不幸福、一般、幸福、非常幸福”。其他主要变量及其描述如表1。

表1 主要变量及其描述

续表1
从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平均而言幸福感在一般和幸福之间,均值为3.53。所有样本中男性占48%,,平均年龄约44岁,城镇户口样本占57%,,汉族样本占93%,。经CPI调整到2009年的水平的样本人均年收入为1.35万元,大部分样本认为自己的收入没有发生变化(均值为2.18)、自己处于中下阶层(均值为1.98),82%,的样本有自有产权的住房。就教育程度而言,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样本占9.46%,,小学和私塾的样本占20.25%,,初中学历的样本占26.64%,,高中、中专或技校学历的样本占29.42%,,大专学历样本占8.36%,,大学本科样本占5.42%,,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样本占0.44%,。从就业状况看,约64%,的样本处于就业状态。就婚姻状况而言,未婚占10.63%,,同居占0.35%,,已婚占81.71%,,分居占0.45%,,离婚占0.24%,,丧偶占1.82%,,其他占4.8%,。
四、计量模型与结果
本部分首先以参照组相对收入作为相对收入的衡量指标,检验绝对收入、相对收入等变量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然后将其与其他相对收入衡量指标得出的结果进行比较,接下来讨论收入对幸福感产生影响的机制,最后总结此结论对于理解伊斯特林悖论的意义。
本部分主要应用序数Probit模型进行计量分析,模型如下:
因变量Happinessi为幸福感,自变量为绝对收入Incomei和相对收入Compincomei,绝对收入变量为对数化收入,相对收入变量在不同回归模型中包括参照组相对收入、收入变化、社会经济地位等。其中,参照组相对收入根据Clark与Oswald(1996)得出,具体如下:首先以收入为因变量,性别、年龄、年龄平方、户口、民族、学历、婚姻状态、就业状况、省份为自变量,用多元线性回归估计出各自变量的系数,然后根据系数估计出各样本的收入预测值,最后将收入的实际值与预测值取对数差后得到参照组相对收入。Xi为根据罗楚亮(2009)、官皓(2010)、刘军强等(2012)等文献选择的其他影响幸福感的个体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年龄平方、户口、民族、学历、住房、婚姻状态、就业状况、省份、年份。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引入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哑变量,应该能部分控制包括高生活成本在内的超大城市的特性对幸福感的影响,从而缓解我们未能直接控制生活成本所引起的担忧。1β、2β、3β分别为各变量的回归系数,iε为随机扰动项。

在基本模型的基础上,本文随后还区分五个样本、建立五个模型进行分析。从表2到表5的回归结果中,模型1均包含所有样本,模型2包含收入在25分位值及以下的样本,模型3包含收入在25分位值以上50分位以下的样本,模型4包含收入在50分位以上75分位以下的样本,模型5包含收入在75分位以上的样本。稍有不同的是,表6为了和引用文献的结果相对照,模型1包含所有样本,模型2包含收入在50分位值及以下的样本,模型3包含收入在50分位以上的样本。
(一)不同群体的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幸福感
以表2来看,总体上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都对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从模型1可以看出,对数化收入的回归系数(第1行第1列)和参照组相对收入的回归系数(第1列第3行)均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与罗楚亮(2009)得出的即使在控制相对收入后绝对收入对幸福感仍然有显著正向影响的结论相吻合,与官皓(2010)得出的在控制相对收入后绝对收入对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的结论相矛盾。
低收入者幸福感受绝对收入影响显著,高收入者幸福感受相对收入的影响显著。在表2的模型2和模型3中,对数化收入的系数为正且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上显著(第1行第2列、第3列),但参考组相对收入的系数则不显著(第3行第2列、第3列)。在模型4和模型5中,对数化收入的系数不显著(第1行第4列、第5列),而参考组相对收入的系数为正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第3行第4列、第5列)。这与McBride (2001)、Ferrer-i-Carbonell(2005)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表2 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幸福感
不同收入群体对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的看重程度是不一样的,使得绝对收入与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不一样。如前文的文献综述所言,绝对收入是通过对个体需要的直接满足程度来影响幸福感的,相对收入是通过改变社会比较的感受来影响幸福感的,不同个体对两种途径的偏重程度的差别可能是导致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产生差异的原因。低收入者更看重绝对收入,因为收入水平的提高更有助于满足自身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要。高收入者更看重相对收入,因为在基本生活需要满足之后,个人会更关注自己在社会中的相对地位,关注自己是否得到了尊重和是否有成就感等等。
其他变量的回归结果基本与其他研究的结论一致。男性不如女性幸福,城里人不如农村人幸福。年龄对幸福感的影响呈“U”型关系,即幸福感先随年龄的增大而减小,继而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增加。除了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不如本科学历者幸福之外,总体上学历越高幸福感越强。拥有自有产权住房者更幸福。已婚者的幸福感较高,离婚或丧偶者的幸福感较低①囿于篇幅,这里没有汇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如果需要可直接向作者索取。。
(二)不同相对收入指标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利用不同的相对收入指标也可能估计出收入与幸福间不同的关系,表3和表4分别为以自评相对收入和收入变化作为相对收入衡量指标对幸福感变量进行序数Probit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全样本还是以收入分组的样本,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几乎都对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且相对收入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

表3 自评相对收入与幸福感

表4 收入变化与幸福感
此处的相对收入之所以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可能源于这两个度量指标的主观性较强。自评相对收入可以理解为个人的相对收入感,收入变化可以理解为相对自身以往收入的变化感,两种感觉都是在绝对收入差异的基础上产生的,但与相对收入已有本质上的差别,而与幸福感更为接近。相对收入感和收入变化感类似于吴丽民和陈惠雄(2010)、张学志和才国伟(2011)的幸福感模型中的中介变量,换句话说,这里的相对收入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中介作用。所以,自评相对收入和收入变化在各个收入组均对幸福感有正向影响,这与以参照组相对收入分组回归得到的结论不一致,我们在看到相对收入对幸福感产生影响时需要特别留意其具体指标的选择。
(三)以CHIP、CFPS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
本部分利用其它数据库进行同样的分析能得到基本相同的结论,说明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前文提到有关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结论与罗楚亮(2009)一致而与官皓(2010)矛盾,所以这里主要将本文结果与二者的结果相比较。罗楚亮(2009)使用的是2002年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官皓(2010)使用的是2008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同样以参照组相对收入作为相对收入变量,分别使用CHIP2002数据和CFPS2008数据,经序数Probit回归得到的结果如表5和表6。观察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总体而言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对幸福感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5和表6的模型1),高收入群体的幸福感受相对收入影响而与绝对收入无关(表5模型5和表6模型3),低收入群体的幸福感受绝对收入的显著影响而与相对收入无关(表5模型3、4)。

表5 以CHIP 2002年数据得到的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幸福感
其它有关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文献得出不同于本文的结论,可能源于其不同的相对收入度量指标。罗楚亮(2009)在研究中使用与主观贫困线比的相对收入和与自身以往收入比的相对收入两个指标,官皓(2010)则使用自我评价的相对收入,这些指标的主观性较强,在回归中容易表现与幸福感的显著正相关关系。这类基于主观评价的指标,与一般意义上相对于别人的“相对收入”在含义上有一定差异,在理解其结论时需要注意。

表6 以CFPS2008年数据得到的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幸福感
(四)收入对幸福感各子维度的影响存在差异
幸福感是一个包含多个子维度的变量,至少包含了工作、家庭、休闲、健康、财务、自我意识、群体关系等方面的感受(Diener 等,1999)。CGSS2006年的调查结果包含了个体对家庭经济状况、家庭关系、人际关系、个人健康状况、住房状况、所居住的社区、工作等方面的满意度数据,这正好可用于分析绝对收入与相对收入对幸福感产生影响的路径。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低收入组包含收入在25分位值及以下的样本,中低收入组包含收入在25分位值以上50分位以下的样本,中高收入组包含收入在50分位以上75分位以下的样本,高收入组包含收入在75分位以上的样本。
总体而言,绝对收入与相对收入都对家庭经济状况的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绝对收入还对人际关系、个人健康状况、所居住社区状况和工作的满意度有显著影响,这从表7第1行和第3行的回归系数可以看出来。对于中低收入者而言,绝对收入对家庭关系、人际关系、个人健康状况、所居住的社区、工作等绝大多数满意度的子维度有不同显著程度的正向影响(表7第9行),而相对收入只在低收入组中对家庭关系和个人健康状况有显著正向影响(表7第7行)。对于高收入者或较高收入者而言,绝对收入除了对家庭经济状况或工作的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外,对其他子维度的影响均不显著(表7第13行和第17行),但相对收入对所居住社区的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表7第15行)。
不同收入者的幸福感各子维度受绝对收入或相对收入的影响存在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能解释为什么低收入者的幸福感与绝对收入相关而高收入者幸福感则与相对收入相关。此外,绝对收入的增加并不能带来高收入者对家庭关系、人际关系或个人健康状况满意度的增加,而这种影响对于低收入者则是显著的,这说明高收入者绝对收入的增加可能是以家庭关系、人际关系和个人健康方面的牺牲为代价而取得的。

表7 绝对收入与相对收入对幸福感各子维度的影响
(五)相对收入对不同程度的幸福感影响存在差别
序数Probit回归模型需要满足平行线假设,即在不同等级的有序多分类结果中,解释变量的效应保持一致,不会随等级的不同而变化。这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假设,绝大部分数据都是不满足这个假设的(Long and Freese,2001)。由Brant(1990)提出的Wald检验是一个常用的检验平行线假设的工具,它可以对每一个变量进行独立的检验并给出结论。通过Stata的brant命令进行Wald检验的结果显示,除了性别和年龄的平方两个变量满足平行线假设外,其余变量均不满足此假设。既然不满足平行线假设,序数模型中解释变量的系数所衡量的就并不是该变量对序数变量概率的边际影响,而是其对隐性变量“幸福感”的边际效应。好在我们所关心的只是该系数的符号而不是具体数值,它只能直接反映该变量对幸福感的影响方向。
由于数据不满足平行线假设,我们用广义序数回归的方法重新处理数据,结果显示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对不同程度幸福感的边际影响存在差异。广义序数回归并不需要数据服从平行线假设(Long and Freese,2001),表8是用Stata命令gologit2得到的结果,第一列标题为“1,vs(2-5)”,实际上是将所有样本分为幸福感等于“非常不幸福”和幸福感大于等于“不幸福”两组进行logit回归的结果,第二列“(1-2)vs(3-5)”则是将样本分为幸福感小于等于“不幸福”和幸福感大于等于“一般”进行回归的结果,“(1-3)vs(4-5)”和“(1-4)vs5”两列以此类推。对数化收入在不同分组中回归的系数分别为0.492、0.469、0.231和0.197(表8第1行),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各个层次上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程度有差别,幸福感较低时绝对收入的影响更大一些。相对收入则不同,系数分别为0.032、0.081、0.124和0.07(表8第3行),但幸福感在较低或较高时其影响都是不显著的。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非常不幸福或已经比较幸福的话,相对收入的增加对其幸福感是没有显著影响的。
此外,性别、年龄、户口、民族、学历、住房、婚姻状态等变量,在广义序数回归中的结果与之前序数Probit模型的结果在方向上都是一致的,说明如果只看各变量的影响方向,序数Probit的结果是稳健的。

表8 广义序数回归模型下的幸福感影响因素
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在幸福感的不同层次上有不同程度影响的这种特点,可能是导致相对收入与绝对收入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幸福感影响存在差异的原因。从表9的情况来看(子样本分组方式同前),收入越低则越依赖于绝对收入的增加来摆脱非常不幸福的状态,收入越高则越有可能通过相对收入的增加来达到幸福或非常幸福的状态。对于中低收入者而言,绝对收入在幸福感的各个程度上都有正向影响,且绝对值差别不大,分别为0.768、0.741、0.512和0.816(表9第5行)。对于低收入者而言,绝对收入仅在其从“非常不幸福”过渡到“不幸福”或从“不幸福”过渡到“一般”时有显著影响,系数分别为0.479和0.337(表9第1行),这说明低收入者更依赖于绝对收入的提高来摆脱不幸福的状态。对于中高收入者而言,相对收入对其幸福感从“不幸福”到“一般”以及再到“幸福”都有显著正向影响,系数分别为0.574和0.441(表9第11行)。对于高收入者而言,相对收入对其幸福感从“不幸福”到“一般”以及再到“幸福”或“非常幸福”都有显著正向影响,系数分别为0.533、0.346和0.446(表9第15行)。这说明高收入者依赖于相对收入的增加来达到较高的幸福水平。表9还有两个地方值得注意:一是对于中低收入组而言,相对收入在对其从“幸福”过渡到“非常幸福”时有显著负向影响(表9第7行第4列),这可能意味着这部分人相对收入的增加是以幸福感的降低为代价的;二是对于高收入组而言,绝对收入在其从“非常不幸福”过渡到“不幸福”时有显著负向影响(表9第13行第1列),这可能意味着对于本就不幸福的那部分高收入者而言,绝对收入的增加如果没有伴随着相对收入的上升,会降低他们的幸福感。

表9 广义序数回归模型下的不同收入人群幸福感受收入水平影响的差异
(六)从相对收入角度理解伊斯特林悖论
伊斯特林悖论往往能从纵向数据中得到支持,而难以在截面数据中得到验证,但本文利用截面数据得到的结果仍然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悖论。在收入较低的时候,幸福感主要受绝对收入的影响,所以由GDP增长带来的平均收入增加有助于提高主观幸福感。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幸福感主要由相对收入决定,而相对收入并不会随着平均收入的增加而提高。从本文的截面数据看,低收入者绝对收入的增加能显著提高其对家庭关系、人际关系和个人健康状况的满意度,而高收入者绝对收入的提高则可能是以这些方面的牺牲为代价的,高收入者需要不断提高相对收入来摆脱不幸福感,比如提高自己对所居住社区的满意度。由此,从纵向数据来看,收入的增长并不必然伴随着幸福感的提升,所以出现伊斯特林悖论,这与Easterlin(1995)的阐释相一致。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探讨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首先讨论相对收入不同度量指标的特点及收入对不同人群幸福感的不同影响。将四个相对收入的度量指标在客观性与精确性两个维度进行比较后,发现自我评价的相对收入主观性最强、精确性最低,与主观贫困线比的相对收入主观性强但较为精确,与自身以往比的相对收入同样是一种主观评价,但其精确性比与主观贫困线比的相对收入更高,与参照组比的相对收入客观性强但精确性差。对相对收入的衡量并不存在既客观又精确的指标,不同的研究需要根据不同的目标选择合适的衡量指标。
随后以参照组相对收入计量其对幸福感的影响,发现总体而言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均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但这种影响在不同收入的人群中存在差异。对于中低收入者而言,绝对收入对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相对收入无显著影响;对于中高收入者而言,相对收入对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绝对收入无显著影响。如果不同收入人群的幸福感在受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的影响上有差异,那么收入分配政策对不同人群的着力点就可以有所偏重。对于中低收入群体,以提高绝对收入为重点;对于中高收入群体,关注其相对收入的变化。从这个角度看,“提低”、“调高”的收入分配政策从提高个体幸福感的角度来看是值得坚持的。
当用同一数据比较了以自我评价、与自身以往比两种不同相对收入度量指标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后,发现绝对收入和以这两个指标度量的相对收入在不同人群中对幸福感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原因可能在于以自我评价或与自身以往比的相对收入更多是一种相对收入感,与幸福感一样是一种主观感受。由此,讨论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时,选择什么样的度量指标很重要,在对研究结果进行解释时也需要结合相应的指标,而不能笼统地讲“相对收入”的影响。此外,用CHIP数据和CFPS数据进行同样的分析后可以发现,低收入者幸福感受绝对收入影响而高收入者幸福感受相对收入影响的结论是稳健的。
从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路径来看,其对幸福感各子维度的影响存在差异。总体上绝对收入与相对收入都对家庭经济状况的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低收入者绝对收入的提高能改善其对家庭关系、人际关系和个人健康状况的满意度,高收入者的绝对收入则对此没有显著影响。此外,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对不同层次幸福感的边际影响都存在差异。从分不同收入组、不同程度幸福感的广义序数回归结果来看,可能是更多的低收入者需要绝对收入的增加来摆脱非常不幸福的状态,更多的高收入者则需要相对收入的增加来让自己进入比较幸福的状态。
结合收入增长与幸福感变化的所谓伊斯特林悖论来看,这个现象之所以出现,很可能是由于在总体收入较低时绝对收入的增加会带来幸福感的提高,但随着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只有相对收入的增加才会带来幸福感的提高,从而收入增长与幸福感提高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弱,甚至出现背离。
[1]弗 雷B.,斯塔特勒 A.幸福与经济学——经济和制度对人类福祉的影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官 皓.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绝对水平和相对地位[J].南开经济研究,2010(5):56-70.
[3]何立新,潘春阳.破解中国的“Easterlin”悖论——收入差距、机会不均与居民幸福感[J].管理世界,2011(8):11-22.
[4]李 静,郭永玉.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理论[J].心理研究,2008(1):28-34.
[5]刘军强,熊谋林,苏 阳.经济增长时期的国民幸福感——基于CGSS数据的追踪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12(12):82-102.
[6]罗楚亮.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城乡住户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J].财经研究,2009(11):79-91.
[7]裴志军.家庭社会资本、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一个浙西农村的实证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0(7):22-29.
[8]彭代彦,吴宝新.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与农民的生活满意度[J].世界经济,2008(4):79-85.
[9]亓寿伟,周少甫.收入、健康与医疗保险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J].公共管理学报,2010(1):100-107.
[10]任海燕,傅红春.收入与居民幸福感关系的中国验证——基于绝对收入与相对收入的分析[J].南京社会科学,2011(12):15-22.
[11]闰丙金.收入、社会阶层认同与主观幸福感[J].统计研究,2012(10):64-72.
[12]田国强,杨立岩.对“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答[J].经济研究,2006(11):4-15.
[13]王 鹏.收入差距对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1(3):93-101.
[14]吴丽民,陈惠雄.收入与幸福指数结构方程模型构建——以浙江省小城镇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2010(11):63-74.
[15]邢占军.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1(1):196-219.
[16]张学志,才国伟.收入、价值观与居民幸福感——来自广东成人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11(9):63-73.
[17]赵奉军.收入与幸福关系的经济学考察[J].财经研究,2004(5):75-84.
[18]朱建芳,杨晓兰.中国转型期收入与幸福的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2009(4):7-12.
[19]Brant R.Assessing Proportionality in the Proportional Odds Model for 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J].Biometrics,1990,46:1171-78.
[20]Brockman H.,Delhey J.,Welzel C.,Yuan H.The China Puzzle:Falling Happiness in a Rising Economy[J].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2009,10(4):387-405.
[21]Clark A.E.,Oswald A.J.Satisfaction and Comparison Income[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96,61:359-81.
[22]Collins A.L.,Sarkisian N.,Winner E.Flow and Happiness in Later Life: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Role of Daily and Weekly Flow Experiences[J].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2009,10(6):703-19.
[23]Crabtree S.,Wu T.China′s Puzzling Flat Line[J/OL].Gallup Business Journal,2011,http://www.gallup.com/businessjournal/148853/China-Puzzling-Flat-Line.aspx.
[24]Diener E.,Suh E.M.,Lucas R.E.,Smith H.L.Subjective Well-being:Three Decades of Progress[J].Psychological Bulletin,1999,125(2):276-302.
[25]Diener E.,Lucas R.E.Explaining Differences in Societal Levels of Happiness:Relative Standards,Need Fulfillment,Culture,and Evaluation Theory[J].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2000,1:41-78.
[26]Diener E.,Tov W.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Peace[J].Journal of Social Issues,2007,63(2):421-40.
[27]Easterlin R.A.Will Raising the Income of All Increase the Happiness of All? [J].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1995,27(1):35-47.
[28]Easterlin R.A.Explaining Happiness[J].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03,100(19):11176-83.
[29]Easterlin R.A.,Mc Vey L.A.,Switek M.,Sawangfa O.,Zweig J.S.The Happiness-Income Paradox Revisited[J].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10,107(52):22463-468.
[30]Easterlin R.A.,Morgan R.,Switek M.,Wang F.China′s Life Satisfaction,1990-2010[J].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Sciences,2012,109(25):9775-80.
[31]Ferrer-i-Carbonell A.Income and Well-being: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Comparison Income Effect[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5,89:997-1019.
[32]Fischer J.,Torgler B.Social Capital and Relative Income Concerns:Evidence from 26 Countries[R].NCER Working Paper Series 19,2008.
[33]Frijters P.,Haisken-DeNew J.P.,Shields M.A.Investigating the Patterns and Determinants of Life Satisfaction in Germany Following Reunification [J].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2003,39(3):649-74.
[34]Graham C.,Pettinato S.Happiness,Markets,and Democracy:Latin Americ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J].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2001,2:237-68.
[35]Haring M.J.,Morris A.O.W.A.Quantitative Synthesis of Literature on Work Statu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J].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1984,25(3):316-24.
[36]Kahneman D.,Krueger A.B.Developments in the Measurement of Subjective Well-Being[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6,20(1):3-24.
[37]Long S.,Freese J.Regress Model with Categorical Dependent Variables Using Stata[R].Stata Press,2001.
[38]Lucas R.E.,Diener E.,Suh E.M.Discriminant Validity of Well-Being Measures[J].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1996,71(3):616-28.
[39]Luttmer E.Neighbors as Negatives:Relative Earnings and Well-being[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5,112(3):963-1002.
[40]McBride M.Relative-income Effects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the Cross-section[J].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2001,45:251-78.
[41]Ng S.,Ng Y.Welfare-reducing Growth Despite Individual and Government Optimization[J].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2001,18(3):497-506.
[42]Ng Y.,Wang J.Relative Income,Aspiration,Environmental Quality,Individual and Political Myopia:Why May the Rat-race for Material Growth Be Welfare-reducing? [J].Mathematical Social Sciences,1993,26(1):3-23.
[43]Ng Y.From Preference to Happiness:Towards a More Complete Welfare Economics[J].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2003,20(2):307-50.
[44]Pischke J.Money and Happiness:Evidence from the Industry Wage Structure[R].NBER Working Paper,No.17056,2011.
[45]Rainwater L.Family Equivalence as a Social Construction[G]// O.Ekert-Jaffe,ed.Standards of Living and Families:Observation and Analysis,Montrouge.France:John Libbey Eurotext,1994.
[46]Ravallion M.,Lokshin M.Identifying Welfare Effects from Subjective Questions[J].Economica,2001,68:335-57.
[47]Rojas M.Heterogeneit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Happiness:A Conceptual-Referent-Theory Explanation[J].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2007,28:1-14.
[48]Seligman M.E.P.,Parks A.C.,Steen T.A Balanced Psychology and a Full Life[J].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2004,359:1379-81.
[49]Van de Stadt H.,Kapteyn A.,Van de Geer S.The Relativity of Utility: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85,67(2):179-87.
[50]Veenhoven R.Distributional Findings on Happiness in China(CN)[R].World Database of Happi-ness,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The Netherlands,http://www.worlddatabaseofhappiness.eur.nl/hap_nat/nat_fp.php?cntry=36&name=China&mode=3&subjects=227&publics=28,2014.
[51]Veenhoven R.Is Happiness Relative ?[J].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1991,24(1):1-34.
[52]Wood J.V.What Is Social Comparison and How Should We Study It [J].Personality and Social Bulletin,1996,22:520-37.
Absolute Income,Relative Income and Easterlin Paradox:Evidence from CGSS
Wu Qiang and Zhou Bo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Beijing 100029,China)
Using CGSS data,this study revisite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incom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China.After discuss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our relative income measures,we use the relative income compared to reference group as the main indicator.Based on CGSS data,we find that not merely relative income but also absolute one has significant effect on subjective well-being.As for the lower-income group,the absolute income has positive,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while relative income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As for the higher-income group,the statuses of absolute income and relative income are reversed.The increased absolute income of lower-income earners can improve their satisfaction of family relationship,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or health condition,while higher earners can enhance their relative income to improve the living satisfaction of their community.As for the income redistribution policy,we should enhance the absolute income of lower-income earner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relative income status of higher-income earner.
Income;Relative Income;Subjective Well-being;Easterlin Paradox
10.14116/j.nkes.2017.04.003
∗ 巫 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经济学院(邮编:100029),E-mail:yuyi3860@163.com;周 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邮编:100029),E-mail:bozhou98@126.com。本研究受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14YB02)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BJY134)资助,感谢第48批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中国税负归宿实证分析)支持,文责自负。
JEL Classification:D31 D63 I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