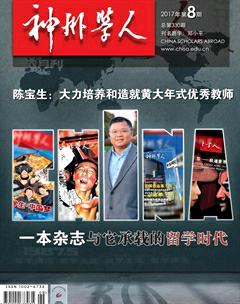给地球做透视的“科研疯子”
刘博智



2017年6月的一天,吉林大學,地质宫。
实验室里,2016级博士生高秀鹤不自觉地直起身子,往常,导师黄大年常常提醒她,要注意坐姿。
黄大年带的第一批博士生、“大弟子”马国庆比以前更忙了,晚睡早起,整天泡在实验室里,他要把导师未完成的工作做下去。
吉林大学人才办副主任徐昊一直在忙着为新兴交叉学部招贤纳才,这是黄大年始终的牵挂。
……
黄大年走了,又似乎未曾离开大家。
2017年1月8日,海归战略科学家黄大年猝然离世,终年58岁。
他是给地球做CT的人,是享誉世界的地球物理学家。他的科研可以上天、入地、潜海。他让中国地球物理勘探正式进入了“深地时代”。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黄大年生前最喜欢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他挥手作别,留下一襟晚照,和那短暂又璀璨的一生。
少年天问
“娃出去见了世面,吃了好东西,
总惦记着给母亲捎回来。”
地下千尺,黑褐色的煤层下埋藏着什么?这是黄大年少年时代的“天问”。
“为国家找矿”,于黄大年是一种使命。他总是比其他人更刻苦、更努力,无形的鞭子在鞭策他。
黄大年的焦虑感并非无来由,他太知道地质勘探对于一个国家有多重要。
回国后,有一次新华社记者问黄大年,中国的深地探测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多大的差距。
“我们是‘小米加步枪,人家是‘导弹部队。”黄大年语气中带着忧虑,就这些“步枪”,还是进口来的。
博士毕业后,他来到英国剑桥ARKeX地球物理公司领衔的海洋和航空快速移动平台高精度地球重力和磁力场探测技术团队,这是一支囊括外国院士等人才的高配团队。这项高效探测技术可以应用于海陆大面积油气和矿产资源勘探民用领域,多数产品已应用于中西方多家石油公司。他被誉为世界航空地球物理顶级科学家,成为这个领域的探路者和引领者。
科学家深奥繁复的工作和民众之间天然矗着一堵墙,只有一些简化的比喻才能代为转译。
“黄大年的工作就是给地球做CT,透视地球,军用、民用都有大用场。”黄大年的助手、吉林大学移动平台探测技术研发中心教授于平说,比如地震、海啸等地质灾害的发生,都有深层次机理,必须向地球深部进军,了解地球深部地质构造。
实际上,这种技术在军事领域的意义更加重大。正因如此,这项技术涉及的重要装备在国际贸易中被列为“非卖品”。而彼时航空地球物理科学研究在中国还几乎是一张白纸,直到黄大年归来。
2009年底,黄大年终于达成心愿,与吉林大学正式签下全职教授合同,担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当时国内的媒体习惯用“毅然回国”来形容他的回国。黄大年反对这样的说法:“我是这片土地哺育出来的炎黄之子,能够越洋求学获得他山之石仅是偶然,回归故里才是必然,而非毅然。”
“娃出去见了世面,吃了好东西,总惦记着给母亲捎回来。”在如今已是吉林大学仪器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院长的林君看来,黄大年的回国只是一次朴素又久违的回家。
“5年前我们是跟跑,经过我们的努力,到了今年,进入并跑阶段,部分达到领跑。”2016年,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黄大年给自己回国6年的答卷打了一个分数。
不过,在很多了解他的同行看来,这个分数有点“过于谦逊”。
短短几年,黄大年带领400多名科学家创造了多项“中国第一”,为我国“巡天探地潜海”填补了多项技术空白。以他所负责的第九项目“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的结题为标志,中国“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项目5年的成绩超过了过去50年,深部探测能力已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局部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赤子其心
“中国需要黄大年们,黄大年们更需要中国。”
一天中,有那么一会儿,黄大年什么话都没有。
他双手惬意地撑在三角形的吧台上,手中马克杯里有四分之一的红酒,傍晚暖煦的夕阳穿过满是公式的背板,洒在这间名为“茶思屋”的房间里。旁边低鸣的处理器不舍昼夜地处理着电磁重震的数据。
这里原是一间茶水室,后来被黄大年专门改造成学生的“造梦空间”。“茶思屋”的名字,是黄大年起的。提醒大家“慢下来,想一想”,所思之物,是他们所有研究的起点和归宿。
每当科研进入困境,黄大年在办公室和“茶思屋”间来回踱步时,他会想起这座地质宫的诞生:当年在筹备长春地质学院建校工作时,时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矿产地质勘探局副局长喻德渊向北京的李四光致函,询问他的意见。李四光立即回信,勉励喻德渊“今天人民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人民的需要,国家的需要,就是黄大年研究的起点和归宿。谈到这些,林君在空中比画出一个点,然后一圈一圈画出一个靶子,“国家需要什么,黄大年就研究什么,从这个原点出发去确定课题,然后再去组织团队,分派任务……”
有趣的是,现实生活中,黄大年却不爱用“大词”。“下午喜欢小酌一杯”“爱侍花弄草”“KTV里的麦霸”,学生口中拼凑出的黄大年可爱、直率,甚至有点儿“孩子气”。这跟人们想象中荣誉等身的学术大家相去甚远。
在科学的迷雾旷野,谁都是摸黑前行,赤子般的纯真就显得尤为可贵,孩童般大开的脑洞,有时却成了仄巷中的转机。黄大年举着这柄“火把”,点亮了地质宫,照亮了黑黢黢的“深地”。
杨振宁的好友库兰特夫妇在回忆杨振宁时说,在他们认识的科学家中,杨振宁是极少能与孩子平等交往、“有孩子般天真个性”的人。
这仿佛是存在于大科学家身上的特质。黄大年也不例外,即使日程排得再紧,他也会抽出时间给中学生作科普讲座,“用孩子们听得懂的话,把自己的工作讲给孩子们听。”黄大年的讲座似乎有一种魔力,“一场报告下来,很多孩子听得血脉偾张,抱定了大学要念地球物理的决心。”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党委书记黄忠民回忆说。endprint
黄大年要把少年时的“天问”传递给这些稚嫩的大脑,开蒙启智。更重要的是,他知道这些人就是未来中国科学崛起的脊梁。
同样被“蛊惑”的,还有吉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国家“千人计划”特聘教授崔军红。
“中国水下国门洞开”,黄大年语气中的忧虑让她难忘,跟黄大年从事的深地探测一样,当时还是美国康涅狄格大学教授的崔军红从事的水下通讯在国内也面临着高端设备依赖进口的处境。
“回来吧,吉林大学要上天入海,母校需要你,祖国更需要你。”黄大年的语气中有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魔力。闭门5小时的深谈后,崔军红走出地质宫,天擦黑,却心绪澄明,她打定主意回国。
后来她才知道,黄大年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他要打造一个学术特区。”2016年,黄大年统筹各方力量,打造了一个辐射地学部、医学部、物理学院、汽车学院、机械学院、计算机学院、国际政治系等非行政化科研特区。更有望带动上千亿元的产业项目。
而支撑起这个特区的,是一批像黄大年一样的归国专家,王献昌、马芳武、崔军红……
“试问有谁不爱国!”崔军红说。黄大年那没有任何杂质和计算的拳拳赤子心点燃了他们内心的冲动。“没有‘海漂经历的人,很难理解我们这些‘海归内心的急迫。”
“中国需要黄大年们,黄大年们更需要中国。”
在吉林大学移动平台探测技术研发中心,“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殷长春,腰上缠着治疗腰肌劳损的护腰,那是长年劳累的后遗症;当记者推开林君办公室的门,发现他在座位上握着笔睡着了……
在之后的采访中,不断涌现的细节一遍又一遍验证着,黄大年并非“孤勇”,这里有一群跟他一样的“疯子”。
“有一帮人在拼命,不是我一个人,一帮人全是这种心态,一帮‘疯子,我们在一块儿可热闹了。”黄大年曾这样说。
归去来兮
“那个赶时间的人怎么突然闲下来了?”
那盏盈盈的灯光还亮着。
时针拢向24点,又是深夜。司机刘国秋焦躁地按着喇叭催促。灯光终于熄灭,咚咚咚,沉重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再过几秒钟,一个壮硕的身躯,拖着皮箱从楼里走出来,一脸抱歉:“劉师傅,辛苦啦!”
在最初的几次碰面里,刘师傅烦透了这个黄老师。
“这客人我不拉了,您另请高明吧!”他跟黄大年的秘书王郁涵抱怨着。因为经常出差,学校想给黄大年找一个专车司机,但拉了两次,刘师傅就准备撂挑子,“哪有这样的,每次都是最晚的航班,回到家都两三点了。”
是啊,黄大年这般追星逐日,到底是跟谁赛跑?
7年间,他每年平均出差130多天,最多的一年出差160多天,几乎每次出差的日程都被安排得满满的。“最晚的班机”已经成了惯例,他总是在最后一刻合上电脑,下楼上车,等飞机平稳,再次打开电脑……
科学竞争只有第一,没有第二。不管你付出多少努力,都有可能在这场争分夺秒的竞赛中被其他人领先一个身位,顶尖科学家都有这种不安全感,黄大年也不例外,他对时间的支配简直是“吝啬小气”。
“真的没时间。”每次让黄大年填写荣誉材料,黄忠民都会被这句话堵回来,“大年参加学术会议或讲座,能准备十几页材料,但要让他填报荣誉材料,半页纸都找不到。”
黄大年办公室最右侧的柜子里,挂衣服的横栏上挂满了花花绿绿各种会议的胸牌,下面就是被褥,遇上科研攻关,累了他就在沙发上眯一会儿。
没人知道,黄大年把24小时掰成多少块。
一拨拨记者进入黄大年生前的办公室、实验室,跟他并肩战斗的同事和学生谈话,试图拼凑出一张黄大年回国7年的年谱,可这张年谱始终没能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它总是被分岔的线头引向千头万绪。当我们凝视着黄大年办公室里足以覆盖整个墙面的2016年日程表时才发现,在许多时间点,他同时做着好几件事。
时间长了,刘国秋的厌烦逐渐变成了自豪——“隐约感觉他是个干大事的人。”他们成了朋友,就算是午夜在高速路上驰奔,他也觉得与有荣焉。有一天,黄大年问他:“能不能帮我开一辆卡车?”刘国秋的这种荣誉感达到顶峰。
“不许用手机捏照片(照相)。”开卡车前,黄大年告诫刘国秋。直到很久之后刘国秋才知道,那台卡车装载的是固定翼无人机航磁探测系统工程样机和“国家使命”。他所不知道的是,无数次晚上开车赶飞机、接飞机,那个“干大事的人”正在创造历史,正在填补国内无人机大面积探测的技术空白。
这样一个争分夺秒的人,有时对时间却是“挥金如土”:看到别的高校申报的课题是国家未来发展战略急需的,黄大年会放下工作,帮助人家策划项目、申请资金。
黄大年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疲倦和伤痛包裹起来,不让学生、同事知道,更不让国家知道。
不过,细心人还是瞧出端倪。
刚回国时,羽毛球场上的黄大年很生猛,“连打两三个小时,我们这边换了两三拨人,他都不休息。”单位组织爬山,黄大年总是走在最前面。2016年开始,马国庆发现,球场上黄大年的身影消失了,他暂停了一切体育活动,“他仿佛预感到什么即将到来。”
如果将这场采访提前两年,学生和同事对黄大年的印象或许完全不同。“他浑厚有力的嗓音给人一种安全感,他像超人,似乎永远有用不完的精力,把所有的事都包揽下来。”他像一棵大树,学生同事都在这里遮风避雨,跟他相处久了,他们会偶尔偷懒,“一个项目申请书改到没有头绪时,放到大年老师的办公桌上,反正第二天早晨醒来就改好了。”
对于黄大年的学生周文月来说,这个“谎言”被拆穿是在1月4日傍晚,ICU那道重重的门开了,黄大年带着呼吸机、眼睛半闭着被推了出来,他衰弱地喘息着。周文月从没有见过这样的黄老师,他如此衰弱,又如此真实。那个“超人”不见了。
刘国秋也发现,黄大年好久没来坐自己的车了。“那个赶时间的人怎么突然闲下来了?”刘国秋心想。他想看看这个坐了他几年车的人到底做了些什么。他用手机翻看黄大年的百度百科,一句一句读下来,眼眶热乎乎的,手机拉到最后一句,“享年58岁。”
“黄老师正在用这种方式跟我告别呢!”刘国秋眼泪决堤。那天是1月8日,黄大年永远离开了地质宫。(摄影/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endprint
——黄大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