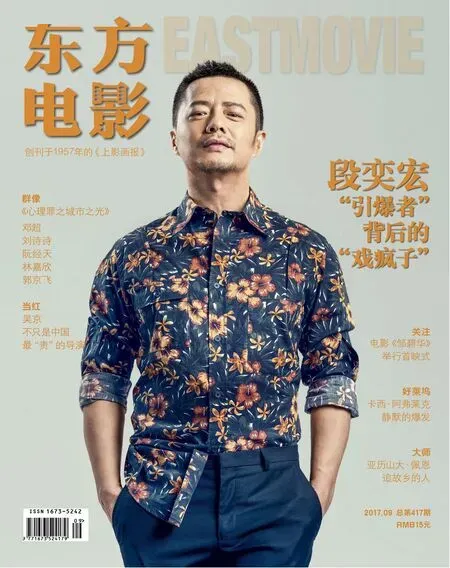亚历山大·佩恩追故乡的人
文/甘 琳
亚历山大·佩恩追故乡的人
文/甘 琳
2017年9月,亚历山大·佩恩带着自己导演的新作《缩身》亮相第74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缩身》的全球首映带有着双重身份,既是今年威尼斯电影节的开幕影片,也是主竞赛单元的参赛影片。一向倾心于欧洲班底的意大利水城如此款待一部来自美国的作品,足以看出亚历山大·佩恩对欧洲电影人的重要性。在好莱坞市场中突围而出的亚历山大·佩恩到底用什么吸引了欧洲人的目光,一切的源头都得回到他的故乡—内布拉斯加。

醉翁之意不在酒
2005年,凭借《杯酒人生》首次获得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的佩恩逐渐被公众熟知。此番成名,让佩恩印象深刻的回忆不是功成名就的荣耀,反而是一封“投诉信”。由保罗·吉亚玛提饰演的葡萄酒爱好者迈尔斯曾在《杯酒人生》中“批评”过梅洛葡萄酒。他抵触梅洛葡萄早熟、多产、生命力顽强的特征,反而对皮诺葡萄酒情有独钟,这个需要葡萄种植者和酿酒师精心照顾的葡萄品种,拥有着性情不定的发育特性,一场寒霜、一次虫患,就能对其造成巨大打击。但是,脆弱敏感的皮诺一旦成熟,其柔和、细腻的口感即会让人无限回味。因为此番好恶明显的葡萄酒品评,使美国同年度梅洛酒的销量下降了2%。一名梅洛葡萄酒酿酒师甚至特意写信给佩恩说:“亲爱的亚历山大·佩恩,我敢打赌,迈尔斯和杰克从来没有试过我的梅洛酒。”
其实,被观众扩大化的“梅洛和皮诺之争”并不是《杯酒人生》的重点,以刻画人物见长的佩恩真正想强调的是“人之底色”而非“物之特性”,以物喻人、移情人物,最后再感同深受,皮诺酒不过是迈尔斯对自我认知的假想:人到中年却庸庸碌碌,面对困境妄自菲薄,被生活的荒诞重重包围,他需要他人的助力和自我的救赎才能让脆弱敏感的自我趋向积极。
对于自己电影中的人物,佩恩总是徘徊在同情和讽刺他们之间,他善于用情感而不是恶意捕捉人性的荒谬。《内布拉斯加》里伍迪丢失在火车轨道上的假牙;《校园风云》里被蜜蜂叮出一个大包的麦考利斯特;《关于施密特》里因为吃了止痛药而精神恍惚的施密特;《杯酒人生》中为了要回钱包而被裸体男一路狂追的迈尔斯和杰克……所有这些洋相百出的窘境都是人物性格背景下水到渠成的荒谬,“如果你要达到人物的情感效果,你必须将他们放在冷峻的背景下,这样他们才能脱颖而出。”佩恩用契诃夫写给青年作家的信来形容自己电影中的人物设计,醉翁之意不在酒,人才是佩恩电影里最关键而根本的钥匙。
电影的精度
佩恩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完拉美文学学士学位后便立即开始了自己规划的迷影道路,他向美国多个著名电影院校提出了硕士申请,最后他同时被纽约大学、德克萨斯大学、南加州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录取。其中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鼓励学生写作的传统吸引了佩恩,他最终选择在此深造。
当佩恩还是一名电影学生的时候,他几乎每天都会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档案馆度过12个小时。他在档案馆看完了几乎所有黑泽明和布努埃尔的电影,认真为每一个他认为优秀的电影片段做笔记。1990年,佩恩将一部阿根廷中篇小说改编的黑色喜剧《马丁的激情》作为自己的毕业作品。处女短片中流露出的对剧本的严谨把控能力以及深厚的文字功底立刻吸引了好莱坞环球电影公司的注意,环球公司允诺投资佩恩在一年之内完成的剧本。这个机会对于一个刚毕业的电影专业的大学生来说实属难得,但是佩恩似乎并没有准备好在环球做出一鸣惊人的成绩。他在一年内大致完成了剧本的创作,关于一个退休老人如何重新开始自己生活的故事,却不知如何在细节上补充人物真实的生动。他最终放弃了和环球的合作。


没有接受环球橄榄枝的佩恩也并没有火急火燎地到处碰壁,闲着的他当过服务员也当过无业游民,甚至还给《花花公子》杂志拍摄过宣传短片。对佩恩抱着巨大期望的父母责备过他为什么不先放下对电影的追求,凭借自己的写作能力找一份编辑助理的工作。他们觉得读了斯坦福大学的儿子最终变成一个不务正业的服务员,都是因为电影的“诱惑”。本来好脾气的佩恩听到父母对自己热爱的电影误解,也会忍不住与他们争吵,因为从选择电影道路起,佩恩就知道自己要承担可能的损失。
与父母产生分歧后,佩恩需要一个室友一起支付他在洛杉矶的公寓租金。吉姆·泰勒的出现不仅挽救了佩恩的财政危机,也让佩恩真正开始了梦想中的电影之路。成为合租室友之后,吉姆在《纽约时报》上读到了一则关于女性堕胎的新闻报道,佩恩看过之后与吉姆心领神会,两人便一同创造出了长片处女作《公民露丝》。由此之后,吉姆成了佩恩常年的剧本合作伙伴,他们一同编写了多部电影作品,俨然是一对双胞胎兄弟。吉姆曾描述,两人在一起编写剧本经常用两个键盘控制一个电脑屏幕,方便两人可以直接对对方的文字进行修改和删除。佩恩和吉姆的合作编剧一直贯穿着故乡、父亲和过去时光的母题,面对这些在文学作品里就被连片累赘的故事,佩恩和吉姆并不怕自己会旧调重弹。在他们看来,老套路不一定不好或者没有建设性, 对待它们的蔑视态度才是更大的陈规旧套。重要的是懂得如何掌控它们。他俩懂得如何将这些老套路锻造抛光,雕塑成全新的状态。
找到合适的剧本伙伴只是佩恩电影成功的一半,还有一大半的原因在于佩恩对电影演员的善用。《内布拉斯加》实际的拍摄时间只有一个月左右,但挑选演员的时间却花费了一年多。本片中起用的许多群众演员都是内布拉斯加的本地居民,有退休的内布拉斯加农户、街头的路人、卡拉OK歌手等各色人等,威尔·福特和布鲁斯·德恩在霍桑酒吧里喝酒的时候,为他们服务的酒吧女服务员就在那间酒吧工作。“如果你试图在银幕上创造一个真实的世界,最好从现实世界中挑选出来。”在佩恩看来,关于过去和故乡的执念也是趋近真实的渐近线,也必须用真实来挑选。
佩恩的电影大都属于好莱坞独立电影的范畴,从新好莱坞电影运动开始,美国独立电影已经慢慢细化成了一套成熟的文化模式。即使是独立电影,也需要在资本的染指下做出让步,如今,独立电影中的日常人物需要大明星的出演才能吸引观众的关注。虽然电影明星的加入能够盘活小成本电影寂寂无声的局面,但即使明星们演技卓越,也很容易因为明星身份而抹杀掉角色本身的魅力。《杯酒人生》的剧本刚刚递交给制片公司,大明星乔治·克鲁尼就想饰演花花公子杰克的角色,佩恩却拒绝了乔治·克鲁尼的加盟,“我愿意用更少的钱来拍这部电影,以便有更合适的演员”。
独立电影因为成本的原因,很容易在表演环节顾此失彼,要不就是选择的演员过于业余而丧失了该有的艺术气质,要不就是帮衬的大明星过于耀眼而掩盖了角色应有的气质。佩恩很好地拿捏到了表演的精度,让表演不成为拖累反而变成了亮点。不像希区柯克将演员比做牲口,佩恩很重视演员表演的意义,将演员看得和自己一样重要:“根据我长久以来的观察,我发现演员与导演是相互妒忌的。我认为,导演妒忌演员的是演员可以随时表露情感,这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啊!演员妒忌导演的是导演可以冷静客观地处理感情,不动感情地指挥演员们。”在圣莫尼卡,忙完工作的每周五晚上,佩恩总是会穿着褪色的牛仔裤,配上白色的衬衫和领带,邀请演员到他住的房子里来看电影,和开派对,他希望能够在工作之余鼓舞人心和演员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关系。


乔治·克鲁尼在后来好不容易和佩恩合作了他期待已久的《后裔》。在这部电影里,乔治饰演的疲惫的父亲、愤懑的丈夫忙碌于家庭生活的累赘,昔日的英武荡然无存。“好莱坞惯常的现象是你挑选一位明星出演某个角色,然后你开始剪裁剧本,使剧本适应这位明星,为大家所预期的或者具有商业价值的惯常形象。我从来不那么做。我想要明星成为演员,并且成为剧本中描绘的那个人物。而且一旦他们这样做了,他们就不再是他们自己,也不再是他们的公众形象,他们成了一位演员,成了那个人物。之后,就要由观众来判断,他们的表演是否成功。”
永远的内布拉斯加
亚历山大·佩恩出生在内布拉斯加州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奥马哈,在美国地图里,内布拉斯加州几乎就在正中间,下面是堪萨斯,右边是爱荷华。放浪不羁的爱荷华少年(《我自己的爱荷华》)、误入绿野仙镜的少女(《绿野仙踪》),堪萨斯和爱荷华都属于美国电影的常客。被名声在外的堪萨斯和爱荷华包围着,内布拉斯加就像一位一言不发的老人,默默伫立在美国中部的平原上。
内布拉斯加的名字源自美国原住民的奇维雷语,是“平顺之水”的意思,在这个农业大州发生的事似乎都不够格成为好莱坞电影的传奇故事。然而,佩恩从第一部电影开始,就一直把内布拉斯加当作自己挥之不去的故乡印刻,他几乎所有的电影都发生在内布拉斯加。早期《公民露丝》和《校园风云》关于年轻人的嬉笑怒骂是诞生在内布拉斯加,中后期透露着中老年怨气和忿气的《关于施密特》《内布拉斯加》依旧扎根在那片土地。不是对故乡的歌功颂德,也没有什么近乡情怯的谨慎,佩恩只是把自己现实生活中真实的故乡展现出来,重要的不是电影里会发生什么,而是现实生活里会发生什么。《关于施密特》大获好评之后,有观众半开玩笑地说佩恩关于内布拉斯加和奥马哈的描述都是负面的,当时的佩恩立刻回应:“我又不是为旅游商会服务,但我就是喜欢内布拉斯加,没有人会去那拍电影,我来自内布拉斯加最大的城市奥马哈,我也许不了解内布拉斯加的乡村地区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我能感受到底怎样才是应有的真实。”
艺术家们终生探索的是自己的根源,威廉·福克纳于194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随后又回到了密西西比州的小城镇,续写着作品中那个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世系”。成名之后,佩恩在洛杉矶托潘加峡谷买了一套房子,但他依旧每年有大半时间在奥马哈度过,他在奥马哈市中心的装饰艺术大厦里拥有一个阁楼,离婚后,他和一只名叫露露的猫独自生活在两地。奥马哈在佩恩眼里就是个大宝库,他知道奥马哈哪一个中餐厅最古老,也了解每一个标志性建筑的前世今生,《关于施密特》里施密特退休前的伍迪保险公司就借用了奥马哈的标志性的建筑来拍摄。
佩恩对故乡的迷恋,就像是一种对神秘古老根源的探寻。《内布拉斯加》拍摄的内布拉斯加州的地点包括诺福克、奥斯蒙德、斯坦顿、里昂、克莱顿、普莱恩维尤和林肯。《内布拉斯加》里男主人公伍迪为了兑换自己想象中的彩票,从蒙大拿州和自己的儿子一路驱车来到故乡内布拉斯加,除了乡音无改鬓毛衰的感叹,故乡带给伍迪的复杂情感成了佩恩真正着力刻画的要素。伍迪在内布拉斯加的大家庭是个彻头彻尾的工薪底层家庭:兄弟多年后的重逢不是拥抱祝福,而是齐刷刷坐在电视机前观看无聊的运动和汽车节目;一旦自己“发财”,亲戚们便开始蠢蠢欲动觊觎自己幻想出来的财富。看起来就像家庭伦理剧里的亲戚往事,被移植到佩恩的故事里却并没有半点不妥,很大原因是因为《内布拉斯加》故意设置的黑白摄影。摄影师芬顿·帕帕迈可用黑白影像捕捉到了中西部的牧场上的空旷之美:寂静的长夜、巨大的农具、牧场的边界、空荡的广场、遗弃的木屋、不规则的墓地……它们如此之静,就像住在记忆中一样,每当父亲的眼睛眨动一下,生命就停顿了一秒。在灰色的氛围中,黑色和白色变得更加能够凸显纹理感,田地里的玉米茬、光秃秃的树骨架,甚至是萧萧落木中的人的背影,都达到了一种返璞归真的落寞感,而这种仅归属于故乡的落寞又不容得每一个故乡的过客随意去评价。这里毕竟是多年生长的地方,那些至今全是老人坐镇的酒吧、那些依然破败颓废的故居、那位年轻时和自己心意相通的恋人,即使伍迪向儿子木讷地说“我不记得了”,那也是关于故乡的斑驳记忆。
《内布拉斯加州》不是一部关于享受生命晚期顿悟的老人电影,也不是一部关于乡愁何处的抒情片,它更像是对自我的一次冷静围观,借由故乡这个场域,年迈的人褪去了虚伪狡黠回到了原点,年轻的人回溯源头反倒流变出了新的势头。故乡在伍迪、儿子,甚至佩恩的心理,已经超越空间,变成了一个时间阀门,站在现在的视点里,故乡是过去的堆叠,是关于时间延展的客观。关于故乡的回忆和依恋即对于过去意识的再造,认同了故乡的意义,也即认同了过去时间流逝的意义。伍迪年轻时候在内布拉斯加霍桑小镇上的酗酒、交友和日常塑造了现在的老伍迪,儿子慢慢拨开时间的云雾窥见了父亲过去的真实,父子二人终于在故乡的牵线下,在时间的拉扯中,达成了和解。在结尾,父亲开着儿子为他买的二手汽车,以趾高气昂的气势出现在故乡故人的面前,在回去的路上,父子俩不谈未来,偶尔谈及过去,却同样可以承载希望。未来也不过是时间流逝的一个模式,而过去的流逝才真正成了无常生命的一个普遍模式。“唯一让我不想活在过去的东西是我们的医疗—癌症药物和关节手术”,曾经被给予的东西漂浮在他眼前,佩恩对过去的执念被溶解在故乡这一有形的场域中。

亚历山大·佩恩的祖父是希腊裔的美国移民后代,经过多年的奋斗在奥马哈开了自己的弗吉尼亚咖啡厅,这个24小时营业的咖啡厅从开办起就从未关闭过,直到1969年被一场大火烧毁。在佩恩童年的回忆里,每周四晚上他都和母亲、哥哥一起在弗吉尼亚咖啡厅吃饭。弗吉尼亚咖啡厅也开启了佩恩的迷影生命,卡夫食品公司为了答谢弗吉尼亚咖啡厅的业务合作,给佩恩父亲送来了8毫米的电影放映机,《弗兰肯斯坦》《歌剧幽灵》都在这台小小的放映机上运行过,从这台咖啡厅的8毫米放映机,佩恩第一次感受到了电影的魅力。2013年,佩恩在意大利博洛尼亚的重逢电影节上购买了一部卓别林的默片,回到奥马哈之后,佩恩在奥马哈的大街上为孩子们放映了这部小短片,他的妈妈在厨房里为孩子们做爆米花,彷佛又回到了童年的观影时光。
父亲与奔跑
“他们慈祥而和蔼,不过不知怎么,他们像是在另一个星球。你终其一生都想知道我父亲所处的那个星球到底是什么样子。也许孩子和父亲之间存在某些动态的东西,这些东西使得孩子们感觉到,他们的父亲不可捉摸。”除了故乡的铭刻,父亲也是佩恩电影中必不可少的元素,在这些充斥着泪水和笑声的中年危机电影里,这些担任着父亲身份的男人,都在佩恩的电影里试图弄清自己的生活是如何出错的。
《关于施密特》里的施密特在妻子去世后才知道妻子曾经偷偷地爱上了另一个男人,他的女儿也恨他,并且正在嫁给一个失败者;在《杯酒人生》中,迈尔斯在离婚后饱受环境的压迫而不知道如何公然反抗,对前妻的念念不忘让他无法接受新的恋情;在《后裔》中,马特·金被女儿告知意外身亡的妻子在生前就已出轨,他不得不面对自己不是一个好丈夫和一个好父亲的事实。细数下来,佩恩电影中的男人无一例外都是因身边女性而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失败,男主角愚钝而容易博得同情的第一人称视角叙述能够精准地把人物抛在观众面前,让人忍不住去感受和反省。臃肿驼背的身型、沉重的步伐,这些在事业上虽然有所成就的男人,回到家庭反而走向边缘,但这种边缘又不是中心的对位或对立,而是中心的一部分,是家庭中心的直接延续。只要剖析得够深,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影片中的父亲形象其实只是佩恩电影世界中的社会人格缩影,除了父亲,其他人无端走向困境的行径同样令人无奈,父亲犯的错,你也可能会重复。


亚历山大·佩恩的早期作品《校园风云》不像其后期作品总是把镜头对准一家之主的琐事和颓靡。故事新奇地发生在校园这个充满活力的地方,一场校园学生会主席的选举激发出了所有的矛盾,第一人称视角的叙述不是一个人而是四个人,教师麦考利斯特和三位学生各自诉说着自己的欲望,每个人都在危险的最大限度之内趋向焦虑和自我的渴求。亚历山大·佩恩曾在采访中多次强调《校园风云》是他最喜欢的一部作品,不是后期频频获得奥斯卡和戛纳奖项的关于中年和父辈的作品,而是这部张扬着各种力量的校园青春作品。佩恩曾描摹了《校园风云》里自己最喜欢的一个片段:男主角高中教师麦考利斯特利用教学的间隙时间匆忙跑到便宜的汽车旅馆布置自己和女邻居的偷情秘事。一位在电影开头还在谴责同事不伦恋情的高中教师摇身一变自己也成了被欲望驱使的动物。最重要的是,完成这些可笑阴谋的过程,麦考利斯特都是用奔跑来完成的。与麦考利斯特敌对的学生翠西在撕毁竞争对手的海报后,同样也是用奔跑来逃脱自己的罪行。这些举止滑稽的奔跑行动类似于无声喜剧中卓别林和基顿的笑料设定,但是又带有亚历山大·佩恩所特有的人道主义的音调,拥有深厚文字功底的佩恩喜欢让对话驱动人物的发展,但却依旧保留了奔跑的动能。
每个人都有奔跑的目的和意义,就像每个人都拥有欲望的权利,佩恩对每一个人物的奔跑都没有流露出过多的好恶,他只是在传统的叙事参数下冷静记录,客观输出。不论是父亲还是年轻人,都逃不过奔跑的诱惑,也需要面对奔跑后的担当。奔跑到再远的地方,恍惚间却还是会回头凝望,在亚历山大·佩恩这个追故乡的人看来,回头的“故乡”里有我们丢失的,同时也有我们苦苦寻找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