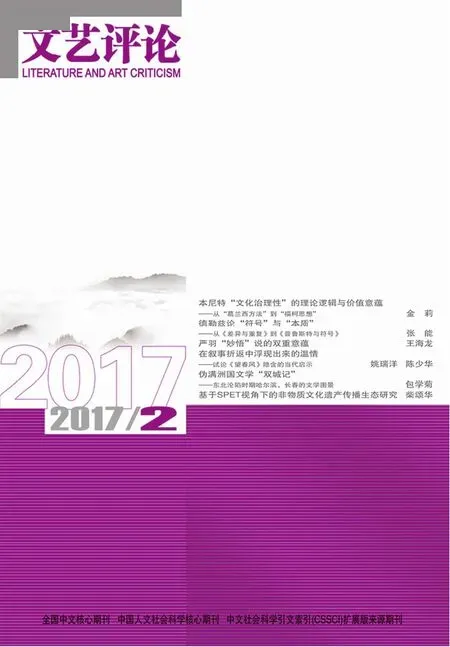“第三代诗歌”女性诗人群的影响探析
○朱国芳
“第三代诗歌”女性诗人群的影响探析
○朱国芳
女性诗人群是“第三代诗歌”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在西方女性主义影响之下诞生的具有鲜明性别色彩和女性意识的诗人群体。“第三代”女性主义诗歌与“朦胧诗”精神上的关联体现在主体意识、平等意识、人道主义启蒙等方面。就像“第三代”男性诗人在北岛等诗人的启蒙之下走向多元的个人风格一样,女性诗人也在“朦胧诗人”男女平等的原则之下,发现了女性生存的真实生活境况。
不过在其性别意识的觉醒下,女性诗人们很快意识到自己的双重“边缘”身份。也就是说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朦胧诗人”的整体意识而言,她们的个人意识已经觉醒,相对“第三代”男性诗人而言,她们的性别意识宛然。总之,“第三代”诗人中的女性诗人经历了个人意识与性别意识的双重觉醒。
一、书写母亲,寻找女性的传统
在父权文化主宰的男性文化价值观下,女性自身的历史就是一部语焉不详,充满中断、阻隔、反复的断简残篇。而女性的精神成长过程,显然也不能脱离父母家庭以及社会文化所造成的身体和灵魂的多重焦虑和不安。是安心于做“父亲的女儿”“家庭中的天使”,抒发女子气的感伤,还是在“抽象的人”面前不自觉地认同男性价值观成为男性文学风格的翻版,抑或是直面生存真相创造自己的“黑夜”?这是女性诗人面对的多重困境。
这是“身份”困境。如果说存在“影响的焦虑”的话,“第三代”女性诗人与男性诗人的“弑父”情结不同,她们最直接的身份确立来自于参照文学上的“母亲”。女性文学的特殊性,使得她们更为迫切地寻找自身的传统,并在这种传统下延续自我的存在价值。
在“第三代”女性写作者中,翟永明是一位有着女性意识的自觉的诗人。在她的写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明晰自觉地寻找女性传统的路径。她视野开阔,写出了磅礴大气、厚重深邃的女性诗歌文本。古今中外的女性艺术家以及她们的诗歌文本一再进入她的写作之中,如鱼玄机、普拉斯、弗里达·卡洛、路易斯·布尔乔亚等等女性艺术家就像是天空中的星星散落在翟永明的诗歌文本中。这种“身份”对话,在解构与重构的双重过程中增加了写作的深度。也正是这种自觉的源头意识让翟永明保持着对“身份”敏感,这让她一度对历史偏爱,除了寻找文学中的“母亲”,个人家庭中的母亲也是她写作中的重要因素,可以说偏爱家族史,一再书写“母亲”构成了翟永明诗歌写作的一条显明线索。
1984年的《女人》组诗中专门有一首“母亲”写给“母亲”的诗。这首诗淋漓尽致地表达了母与女之间的深刻关系。一方面是对母亲的爱,自身来自“母亲”并通过“母亲”领悟自身的命运。因此诗歌赞颂母女之间的命运关联,歌唱母性神圣的创造力量,“为那些原始的岩层种下黑色梦想的根。它们/靠我的血液生长/我目睹了世界/因此,我创造黑夜使人类幸免于难”。
但在长期的父权规训之下,“母亲”也往往意味着是男性的妻子,是被男性选择的人,并在不自觉中充当了父权的代言人。因此诗作在另一方面则对母亲的规训进行了抵抗,对母亲给予自己的生命来源表示了怀疑。“那使你受孕的光芒,来得多么遥远,多么可疑,站在生与死/之间,你的眼睛拥有黑暗而进入脚底的阴影何等沉重”。于是,在这首诗中作者反复抒发了“被遗弃”与“对抗”的情感症结,并将“母性”的神圣与压抑的双重性淋漓尽致地揭示出来。
《静安庄》里“母性生殖”主题构成了萧红《生死场》一般的精神氛围。在这里生的挣扎与死的无意义闭锁成一个古老、蒙昧、荒凉的生活世界。诗歌中出现了大量荒芜废弃的空间意象,翟永明仿佛倾向于将女性意象化为“场所”。她的诗歌中出现的“荒屋”与“荒村”等意象,很显然是诗人自我主体的意向性投射,也是对“子宫”的隐喻。对于这一蛮荒之地,诗歌主人公借着“到来—离去”的诗歌叙事完成了自我精神的独立。
在《女人》《静安庄》这类大型组诗里,翟永明的丰富性在独白的语言里绽放出来。因为需要将矛盾与舒展、光明与黑暗、温柔与残暴、坚信与毁灭纠结一体的女性生存经验统统在诗歌里表达出来,强大的语言驾驭能力是必不可少的。看似随着汹涌的情绪脱口而出的独白诗句,其中却充满了意象的腾挪、隐喻的深刻、象征的晦涩、潜意识里的疯狂与怯懦、不可思议的中断与突然的沉默,翟永明的语言架构坚实有力。
到《十四首素歌——献给母亲的组诗》里,翟永明的诗歌变得感性丰满且清晰,闪耀着智性的光辉。她举重若轻地处理了女性的个人家族史。这是完成文化、历史宏大叙事之后的一次贴近地面的飞行,是剔除了神话、巫术之后的更加个人化、平民化的个人家族叙事。翟永明经过沥胆析心的“独白”阶段,终于抵达了安全的开阔地带,明净的激情中处处透漏出敏感睿智。
审视母亲的女性视角直接开启了年轻的“70后”女诗人,比如尹丽川对母亲角色的虚妄进行了消解,进一步从日常生活的微妙之处入手拆解了无私奉献的母性神话。为他人活着的母亲在衰老之后,陷入无用、卑微的可怜境地,这是对身为母亲的女人丧失自我的警示。
二、身体写作的出场
寻找母亲的传统,说到底是为了建构自我、寻找自我。当女诗人寻找自我传统的时候,“母性”的传统又给予了她们对自身处境的“彻悟”。当诗歌由母女关系转到书写两性关系时,女性被贬抑和遮蔽的疼痛布满了女性写作。
在传统二元思维的框架结构内,男与女是典型的二元,身为女性意味着是男性的参照物。而传统的二元对立结构中,女性并不具有对等的平等性,往往是男性的反面。首先,在传统意义上成为女性意味着成为男人欲望的对象,她被赋予弱小、乖巧、温柔体贴等等所谓的女性气质。如果说成为女性意味着在文化中处于弱小的地位这恐怕没有多少异议。这种二元秩序导致“厌女症”。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一书中指出“在性别二元制的性别秩序里,深植于核心位置的,便是厌女症。在这个秩序之下,无论男人女人,无人能逃离厌女症的笼罩……在男人身上表现为‘女性蔑视’,在女人身上表现为‘自我厌恶’”①。因此,女性的成长经验可以说是由一系列的否定性经验构成的,而最能说明这些否定性体验的莫若身体经验。
翟永明在《女人》组诗痛苦地道出了真相,“我,一个狂想,充满深渊的魅力/偶然被你诞生。泥土和天空/二者合一,你把我叫作女人/并强化了我的身体”。在男女性别的二元制性别秩序里,显然男性是占有话语权的主动者,所谓女性气质被看成是男性的对立面并被男性话语所建构和强化。于是,成为一个女人就意味着符合父权话语的要求,并丧失掉女性自己的自我主体,“我是最温柔最懂事的女人/看穿一切却愿分担一切/渴望一个冬天,一个巨大的黑夜/以心为界,我想握住你的手/但在你的面前我的姿态就是一种惨败”。
与翟永明痛苦的揭示过程不同,伊蕾采用了另一种策略,那就是对被贬抑而不可宣泄的女性欲望的直接表达,在《独身女人卧室》肆无忌惮地大声喊出女性自身赤裸裸的身体欲望。
提到女性的身体写作,不能不提到“非非”女诗人小安,她有《为什么会美妙》这样清新透明的作品,“一起做爱能有多少年/你突然靠得如此之近/我看见了所有的一切/言辞和手势/多么美妙/请你说说/为什么会美妙”,温柔美好至极。
可见,在“第三代”女诗人的身体写作经验中,存在着翟永明、伊蕾、小安三种不同的写作倾向。身体写作直面女性的生存经验和真实的生命状态,在当时起到了令人震惊的艺术效果。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女性身体话语由于消费主义的增长渐渐失去了先锋力量,女性身体写作也呈现出迎合与挑战的两难局面。
“第三代”女性身体写作的策略在“70后”女诗人那里变得更加复杂化。身体经验变成了一种拆解:既挑战读者的阅读心理又嘲讽“崇高”、一本正经事物的策略。比如尹丽川《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喔再深一点再浅一点再轻一点再重一点/这不是做爱这是按摩、写诗、洗头或洗脚/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呢嗯再舒服一些嘛/再温柔一点再泼辣一点再知识分子一点再民间一点/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尹丽川书写的身体经验不再是解放话语下的自由主体性概念,而是一地鸡毛的凡俗生活的表征。她的这首诗写得聪明机智又调侃,超出了性别视角下的性别二元论机制。也就是说,身体经验在尹丽川这里不再是沉重悲切的容器,而是凡俗的日常体验。
但尹丽川也从另一个层面写出了身体经验的悲凉,具有某种存在论的味道。比如《情人》,“这时候,你过来/摸我、抱我、咬我的乳房/吃我、打我的耳光/都没用了/这时候,我们再怎样/都是在模仿,从前的我们/屋里很热,你都出汗了/我们很用劲儿。比从前更用劲儿。/除了老,谁也不能/把我们分开。这么快/我们就成了这个样子”。这样的身体经验哪有什么快乐可言,不禁让人想与小安的《为什么会美妙》那样诗歌相比较。与小安相比,尹丽川是冷酷与狠毒的,将性爱日常性、机械性的一面毫无保留地描写出来,拆解了男性给予、女性包容承受的性爱快感之类的神话。
三、黑夜意识与女性主体
“第三代”女性诗人有较强的理论自觉,西方女权主义思想和女性作家的呼吁,在这些女诗人内心得到了回应。翟永明、陆忆敏、伊蕾、虹影、海男、张真……“第三代”女性诗人是具有先锋色彩的女性,她们真诚地探索了身为女性的处境、使命和价值。她们中的翟永明大概是女性意识较为自觉且系统的一位。特别是在写作组诗《女人》之时,她提出了“黑夜意识”来表征女性意识,并成为笼罩1986到1988年间女性诗歌高峰时期的诗歌话语。翟永明的“黑夜意识”到底指哪些内容呢?《在黑夜的意识》《女性诗歌与诗歌中的女性意识》和《再谈‘黑夜意识’和‘女性诗歌’》这三篇文章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一)无法命名的女性现实。翟永明作为女性思想、信念和情感的承担者,“黑夜意识”来自社会现实处境中女性的痛楚经验,她个人内心不断纠结挣扎的体验以及形而上的追问与抗争。所以,“黑夜意识”首先是指孕育了白昼又被白昼遮蔽、无法命名的女性现实,是女性具有毁灭感、深渊感的命运。在父权的二元两性机制中,女性成为男性的阴影,就像鲁迅所言的“白昼将会使我消失,而黑夜又会将我吞没于无地”的境地。女性艺术家的性别认同与艺术认同一直是导致她们身心分裂的原因。因此,“黑夜”包含了女性在历史上的“空白之页”,在两新秩序中的被支配命运。
在男性诗人浪漫化女性的心理需要下,女性在“第三代”诗人的作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柏桦与杨黎的叙述中,因为美少女帅青促成的万夏、胡冬和廖希在西南师大的偶然会面,使“第三代人”和“第三代诗歌”浮出水面。美酒与美女大致可以称得上是“第三代”诗人的缪斯。但女性诗人在男性诗人中的地位真相是怎样的呢?对于很多女性艺术家来说,艺术只是她的生活或者仅仅是爱情的副产品。翟永明在《‘非非女诗人’秘事》中指出小安、刘涛被“非非”男诗人的强大的男性话语场遮蔽的事实,小安曾说过要写评论女诗人的诗评。她说“我们女诗人自己来写诗评,男诗人从来就没有真正理解过女诗人的作品,我来写,我一定会写得很好”②。因此,尽管“第三代诗歌”创作中涌现出了众多女性诗人,但与男性诗人相比仍然处于边缘化地位。女性诗人在20世纪80年代无法与想尽办法占有话语权的男性诗人相提并论,迟至20世纪90年代她们的创作才正式进入批评家的视野。
将翟永明在男性诗人眼中的形象作一番梳理也许是非常有意思的。翟永明是美丽的,是很多男性诗人口中的翟姐。韩东与翟永明相识于《诗刊》举办的第六届“青春诗会”,韩东这样介绍翟永明,“翟永明的风采令我叹为观止,我不免跟前跟后。为了和我保持距离,翟姐说我是个小孩,并自称姑姑”③。马松则更为巧妙地说:“伟大的翟姐,女诗人里面我没有见过比她更美的,只有在她身上,你才知道时间再无情也干不过诗。”④在杨黎眼里,翟永明是能满足他心理上的姐姐情结的人,她给他一种内心深处带来“很大的人”的感受。这大概是翟永明被男性诗人信赖的一面。
而在翟永明对自己的叙述中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一位敏感、羞涩、甚至有些木讷,悲观、坚强但又一心想要成为自己,不惜脱离各种安全的束缚,坚持“好诗主义”的女性艺术家。因此,翟永明的遭际与敏感独立的身份意识都将使她成为一位不可替代的诗人,不是靠理论靠学识,而是靠自身的生命体验说出真相,翟永明诚实勇敢且宽阔。
女性诗人几乎没有像男性诗人那样的诗歌团体,她们要么跟随有亲密关系的男性诗人加入某个诗歌派别,要么就是自己一个人单打独斗。所谓“女性诗人群体”也是一个文学批评或者文学史的概念。或如翟永明所言,女诗人算是一派的原因,是“因为天性中的恬淡、随意,及对诗歌本身的热爱和虔诚,使女性不会真正为诗歌之外的东西而争斗吵闹”⑤。女性气质和女性意识使得她们在写作中获得相互理解和认同。但这些女诗人并不是拥有坚实组织基础的有宣言、有团队的流派,只是松散地汇聚在性别意识觉醒这个关键词之下的一群女性诗人而已。
(二)创造和孕育的黑夜。但“黑夜”也具有包容和孕育的品质,这正是神话和传说中的“母性”精神。翟永明的“黑夜意识”也包含了这种精神层面,她将之称为“女性气质”。这种女性气质包容对立冲突,丰富且成熟。它蕴含着勇敢地直面自身毁灭性的命运,摧毁自我身体内的怯懦,最终自我支撑,自我成就的强大力量。
翟永明无疑具有伟大的“黑夜”精神。正是靠创作黑夜的自觉,翟永明写出了一批源头性的光芒四射的诗作。她才高气盛的诗歌气势、张力、动感带着白热状态和漩涡的冲击力,一如音乐中的斯特拉文斯基扫荡一切。或者说诗歌是翟永明的安全之筏逐渐带着她冲过生活的滔天巨浪和日常的各种震荡。可以说,翟永明“创造”了黑夜,投入“黑夜”,在语言的秘密炼金术中写下冲突、震动、质问与和解。
其实“黑夜意识”并不仅仅是作为女性诗人的翟永明才有的意识,诗人海子也在诗歌和札记里写下了“黑夜”,海子也是一个具有“黑夜意识”的人。“黑夜”意味着创造的时间,海子在《传说》中写道:“月亮还需要在夜里积累/月亮还需要在东方积累”。并在《传说》的原序言《民间主题》中将“黑夜”看成积极的创造力量,创造的时间。黑夜意味着民间主题灵性的复活,他写道:“这风也许是从夜里来的,就像血液是从夜里来的一样。这是一个胚胎中秘密的过程。”⑥就像海子一样,“黑夜意识”在翟永明那里也意味着创造的时间,是生与死的勾连转化之时,女性需要直面自己的“黑夜”的生存时间、生命直觉,用合适的语言和形式将之塑造成均衡的秩序,以抵达宁静的光明时刻。
陆忆敏的女性意识相当鲜明,她曾推崇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所提出的建立女性文学传统与女性文学标准的主张。“黑夜意识”在陆忆敏那里大概可以用“我们不时地倒向尘埃或奔来奔去/夹着词典,翻到死亡这一页”这样的诗句来表述。“倒向尘埃或奔来奔去”的无名、徒劳,毁灭不就是女性的“黑夜”吗?因此,陆忆敏在连续追问“谁曾是我”“谁?曾是我”之后,断然宣布,“你认认那群人/谁曾经是我/我站在你跟前/已洗手不干”。诗风干脆、利落、迅捷、轻盈。陆忆敏在女性诗歌上的风格与翟永明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一上来她就是节制、内向与精炼的,是女性诗人的另一种风格。
陆忆敏大概是那种边界意识很强的诗人,如果说翟永明在左突右撞中重建秩序,陆忆敏从一开始就有清晰的秩序感。这大概就是崔卫平所说的,“拥有许多小小的规则,并尽量遵守它们,不去存心触碰它们”⑦。因此,同样是面对“生与死”的界限的“黑夜”,“死亡”在陆忆敏那里缺少翟永明的“神话”色彩与形而上尺度,更多的是一种机敏和直接。比如《可以死去就死去》《温柔地死在本城》《死亡是一种球形糖果》三首写“死亡”的诗作,语言轻快利落,平淡从容,并有一种突然转入的决绝与沉着。比如宣称“可以死去就死去,一如/可以成功就成功”(《可以死去就死去》)、“死亡肯定是一种食品/球形糖果圆满而幸福”(《死亡是一种球形糖果》),陆忆敏这位都市之女,简直就像布尔加科夫的玛格丽特,尽管“气息纤细文弱”但有着绝不怯懦的天性。
结语
在诗歌不断边缘化,女性诗歌更加边缘化的时代,回望“第三代诗歌”的女性主义诗人群体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她们不是隐藏在新世纪背后日渐消逝的雾中的风景而是生生不息的力量。她们的声音会通过尹丽川、宇向、安琪、浅予等后来的女诗人的作品向我们说话,让人坚信由她们形成的女性诗歌将成为一个传统,她们的诗歌是后来的人们可以超越却不能不面对的山岭。
(作者单位:山东青年政治学院设计艺术学院)
①[日]上野千鹤子《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②⑤翟永明《白夜往事·非非女诗人秘事》[A],柏桦《与神语》[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4年版,第168页,第169页。
③韩东《他们或“他们”》[A],柏桦《与神语》[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4年版,第29页。
④马松《灿烂》[A],柏桦《与神语》[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4年版,第173页。
⑥海子《海子诗全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1022页。
⑦崔卫平《生活在真实中》[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78页。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博士科研启动基金资助;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课题项目“‘第三代诗歌’现代性诉求的反思”(14-zc-wh-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