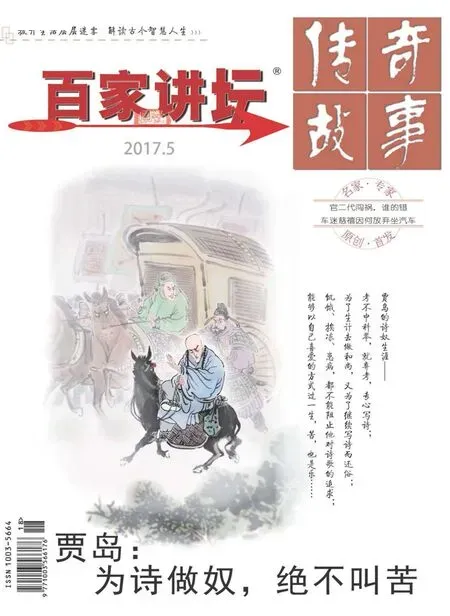南宋大儒:湖畔辩学为家国,药山炼丹寄后生
◎ 箜篌引
南宋大儒:湖畔辩学为家国,药山炼丹寄后生
◎ 箜篌引

鹅湖之会
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六月,信州(今属江西上饶)鹅湖寺。炎炎夏日,寺中却很清凉。森森古柏,幽幽钟声,丁丁清泉,几乎让人错认了季节。大儒吕祖谦缓缓走进树影,回望了一眼禅房,轻轻地吁了口气。
刚才,禅房里,条几,清茶,折扇……看似氛围清雅,实则剑拔弩张。朱熹和陆九渊兄弟面对面正襟危坐,神情专注,目不斜视。在他们身后,侍立着各自的弟子,弟子们神色紧张,彼此警惕地注视着对方,偶有风吹草动,心里便一片风声鹤唳。
这场高规格的学术辩论会已经持续两天了,却依然分不出胜负。其实,也没有胜负可分。学术辩论会是由吕祖谦发起的,从公来说,他想和稀泥,调停朱熹(他的故事请参阅本刊2016年12期)的理学派和二陆的心学派,让南宋理学蓬勃发展;从私来说,他想让朱熹和二陆消除芥蒂,成为好朋友。
吕祖谦是朱熹的世交和挚友,同时也是二陆的好友,对陆九渊则有知遇之恩—礼部考试时,他从众多考生中挑出陆九渊,并帮其宦海扬帆。可惜,他的好友们却因学术观点而形同水火,这是性情谦和宽厚的吕祖谦所不能允许的。因此,他选了这个机会,让好友们切磋技艺,以冰释前嫌。
这个时间刚刚好,是吕祖谦和朱熹携手共游后期、将要分手时;地点也刚刚好,鹅湖寺是朱熹曾经的寓所;人物更是刚刚好,二陆、朱熹和自己,三派四人,那两派各带门生,自己的弟子也来捧场,虽站在朱熹的地盘上,有自己一方在,二陆也不会有威压感。吕祖谦这样苦心孤诣搞平衡,好友们自然感激,但感激归感激,学术问题却马虎不得。
此次高峰论坛的中心议题是认识论。刚开始,朱熹和二陆还捏着端着,虽说以道会友,儒生还是礼为先,没过多久,三人便长驱直入,刀兵相见。朱熹批陆学空疏,二陆批朱学支离,朱熹一人力战二陆,体力明显不支。关键时刻,吕祖谦站了出来,叫了个暂停。
六月的蝉鸣中,天气明显燥热起来,三人住了口,把目光转向吕祖谦。吕祖谦笑了笑,招呼弟子们奉上清茶,趁大家品茗的工夫,他走出禅房透透气。
说实话,吕祖谦本人也是一代宗师,他创立的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学派,主张学以致用,反对空谈心性。因此,他虽然也心仪二陆的心学,但更倾向于朱熹学术的厚重绵密。不过此刻,他不能表态—他要调停双方,这场辩论赛必须是双赢,才能对朝局产生正面的影响力。因此,他只是打太极,说朱熹的“工夫就实入细,殊未可量”,而陆九渊的学术“欠开阔”。
这评论太春秋笔法,双方都不太满意:二陆嫌他偏袒朱熹,朱熹嫌他太取巧。结果,为期三天的辩论会结束后,四人各怀心思,不欢而散。
鹅湖之会成果乏善可陈,吕祖谦很怅然。余生里,鹅湖之会的挫败感一直伴随着他,如一粒沙子,进入他的身体,让他耿耿于怀。他不知道,这粒沙子得经过多长时间磨砺,才会变成珍珠,让他的理想玉润珠圆。
征程
吕祖谦出身名门,家族中屡出宰相、诗人和大儒。受祖先荫蔽,吕祖谦15岁即补为将仕郎,后又升为迪功郎,授严州桐庐县尉。这是朝廷对他的眷顾,但吕祖谦只谢恩,不赴任:在他心中,父荫之职不足挂齿,他家学渊源,一手读经,一手读史,誓要凭才学考中进士,然后像祖先们那样撑起宋朝大局。
隆兴元年(1163年),26岁的吕祖谦考中进士,被授为南外宗(衙门设在泉州)学教授。办公、侍母之余,他还做枪手,为好友代写奏表,以此来锻炼自己的政治敏感力。
可惜不久,母亲病逝,吕祖谦不得不回金华(今浙江金华)为母守孝。他名声在外,守孝期间,求学问道者也络绎不绝,他都悉心传道解惑。日子忙碌而充实,他却时时感到一种莫名的心悸。
冬日的深夜,吕祖谦倚窗而立,长时间望着临安方向:即位不久的孝宗对理学毫无兴趣,而自己人低言微,守孝期间又没有话语权,竟不能有所作为……月光如水,照在他的麻衣上,他低下头,回看自己长长的影子,不由得打了个寒噤。
吕祖谦思忖片刻,提起笔给一个朋友写信。这朋友要回京面圣,或者他能劝谏孝宗接受理学……理学虽有个“理”字,并不意味着空谈,唯有实践,学以致用,才能圆满自身,修齐进而治平……写完最后一个字,吕祖谦掷笔,长叹一声,瘫坐在床上。此时,天边已微露曙色,可不知朝廷何时能振作起来?
他在满腹愁绪中度过了三年,等母丧服满、复出时,朝廷还记得他,记得这个家世和才学并重的儒生,任其为大学博士。
这个任命出乎吕祖谦的预料。他本以为自己还要在地方晃荡几年,做做县簿之类的小官,但现在皇恩浩荡,在他离职三年后直接将他提拔到朝廷,让他有了接近皇帝的机会,这份知遇之恩不可谓不重。吕祖谦的眼睛湿湿的,愈发精神抖擞。他知道,新的征程就要开始了。
按照惯例,大学博士正式赴任前,还需赴外地就职,吕祖谦被补到了严州,以添差官的身份任严州教授。当初,他没有赴严州任桐庐县尉,时隔八年,这个宿命的地方仍迢迢向他招手。
这次,他欣然去了,因为严州有一个令他心仪的人。
二人转
这个人是张栻(他的故事请参阅本刊2017年3期)。
张栻是故相之子,湖湘学派宗师,与朱熹、吕祖谦共称“东南三贤”,此时正是严州太守。对吕祖谦来说,张栻不仅是上司,还是同门—二人的老师是堂兄弟,学术旨趣相仿,学术审美接近。严州有张栻,吕祖谦焉能不喜?他自然是欣然赴任。
到了严州,二人惺惺相惜,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他们尽力于公务,张栻搭台,吕祖谦大刀阔斧地唱戏,即精心整顿严州书院:制订常规,严肃纪律,加强修养,奖勤惩懒……东南二贤的二人转水起风生,要把严州打造成文化大府。
除了教育,两人的合作还涉及政治经济领域。因为政见一致,吕祖谦甚至甘愿做枪手,以张栻的名义写过一篇论文,陈述丁钱税的演变及危害。
朝政渐稳,虽然隆兴北伐不了了之,内政方面却有所改观,所以在公务之余,吕祖谦也有了心情和张栻喝茶论道。名义上二人是上下级,但他们都是谦谦君子,更是同道中人,对坐深谈,如春风沐雨,怡然自得,以至于多年后,吕祖谦还频频回望严州,留恋于他们的流金岁月。
在严州历练一年后,吕祖谦回京任大学博士,并兼任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不久,张栻也回京任郎兼讲官。在京城,两人又相见了,他们不仅是同事,更毗邻而居。狭小的小巷里,或张栻到吕府,或吕祖谦到张府,一条几、一壶茶、一卷书、一轮月……他们谈理学、谈史学、谈人生,不知不觉中,茶凉了又热,月圆了又缺。
偶尔,两人共同的好友老夫子朱熹也会加入铿锵三人行—以书信的形式。某日,吕祖谦喜滋滋地摊开朱熹的来信,张栻就贴过来。温暖的风中,信纸瑟瑟作响,好像是老夫子的絮语。两人读到某处,忽然相视一笑,眼里尽是醉意。朱熹,那个大他七岁的老夫子,虽然一向不苟言笑,有时却也憨态可掬,而他们为国的心都是一样的。
使命
吕祖谦和朱熹相知很早,吕父和朱父更是情投意合的好友,吕祖谦20岁时随父宦游福建时,遇到时为同安县主簿、到福建公干的青年才俊朱熹,二人一见如故,自此相识相知几十年,成为儒林佳话。
之后,朱熹的家乡婺源(今属江西上饶),朱熹为母守孝的寒泉精舍(在今福建南平),朱熹寓居的鹅湖寺……处处都有吕祖谦的身影。这给人一种错觉,好像和朱熹的交往中,一直都是吕祖谦主动,连《宋史》都说,吕祖谦沾了朋友的光,跟张栻、朱熹交好后便在儒学上精益求精。
事实并非如此。吕祖谦和张栻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他请教张栻修养问题,张栻向他请教史学问题,没有什么不妥。而对朱熹,吕祖谦服膺老友的学问,对其人品更是高山仰止,他们不仅结伴游学,还书信往来频繁,两人虽说学术观点有差异,却是莫逆之交。
朱熹不仅把儿子送到吕祖谦处学习,其大部分作品问世之前,都要经吕祖谦过目。吕祖谦也认真审阅,有需要商榷处,就搜集资料,写信直言求证。吕祖谦和朱熹的学术其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清代学人说:“观先生(吕祖谦)诸书,而朱文公(朱熹)之学可知。”
吕祖谦敦厚,朱熹峻急。朱熹曾说,“学如伯恭(吕祖谦),方是能变化气质”,对吕祖谦甚为佩服。其实吕祖谦也曾毛手毛脚,只是某日读孔子语录“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时,才忽然醍醐灌顶,急躁之意顿消,始觉宁静致远。
某种程度上,吕祖谦和朱熹是一种互补型的好友。因此,朱熹欲光大理学,力战其他学派,锻百炼钢时,心有灵犀的吕祖谦便游说、结交各派,练习绕指柔。在二人的巧妙配合中,不少学派纷纷转向朱学。
不过,两人也并非总是其乐融融。朱熹推崇《大学》,很看不惯动辄便劝人读《左传》《史记》的吕祖谦,批评其太重史学;又批评吕祖谦给好友张栻写的祭文太婆婆妈妈了。大多时候,吕祖谦会一笑置之,有时急了,他也会反批朱熹浮躁、需加强修养,过后则又安然处之。
正是基于对老友朱熹才学、使命和性格的了解,在淳熙二年,吕祖谦才义无反顾地组织了鹅湖之会。既然朱熹的使命是一统理学江湖、为南宋续命,那么吕祖谦的使命就是帮朋友圆梦、为家国出力。为此,他会前尽心组织,会中竭力调停,会后想法善后,尽力把事情做圆满。
他曾提携过陆九渊,此时也顾不得挟恩逼人,直劝二陆皈依朱学,不要因人废理,二陆却微笑不语。朱熹则合眼端坐,世界于他仿佛毫无关系。见此情此景,吕祖谦知道枉费心力,只剩下叹息了。
第四天清晨,通往鹅湖寺的路口,四人就此揖别。看着朋友们越走越远,吕祖谦的心忽然空落落的。他回望一眼鹅湖寺,红砖绿瓦的寺前,一群白鹅如老夫子般摇头晃脑地走过,他呆了一下,也无奈地转身快步离去。
炼丹
鹅湖之会一年后,淳熙三年,吕祖谦被任命为秘书郎、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奉命重新修订《徽宗实录》。这正合吕祖谦之意。他喜欢读史,甚至将儒家经典也看作史书。老友朱熹不推荐自己的学生读史,也对吕祖谦酷爱读史、积极著史的行为颇有微词。但在吕祖谦看来,历史是药山,入深山采药炼丹、根治南宋王朝之病,才是大事。
为此,他夙兴夜寐,废寝忘食地细心甄别该书谬误,花费一年才完成任务。之后,他借献书的机会进谏,希望孝宗认真读史,汲取教训,励精图治,广开言路,虚心纳士,以找出救国的方子。
正值艰难时世,这些话,孝宗听进与否不重要,但吕祖谦这种关心朝廷、勇于进谏的主人翁意识感动了孝宗。于是不久,吕祖谦就升为著作郎兼编修官。可惜官职虽多,却都是虚职,无一有实权。想想吕家的祖先们左手治学、右手治国,饶是吕祖谦淡泊,心里也不免泛起一丝酸意。
但他不会知难而退。不久,他又编成《皇朝文鉴》。这是宋朝的诸子百家,收录了宋代两百多人的一千四百多篇诗文,朱熹晚年誉为“篇篇有意……系一代政治之大节”。吕祖谦对朝廷重文轻武的现象十分忧心,可惜南宋国力疲弱,增强武备无法一蹴而就,武不够,文来凑,孝宗要彰显大宋实力,便要重磅推出此书。这部书,吕祖谦编得很谨慎,黜浮崇雅,取舍有道,分门别类编为150卷。
书成后,吕祖谦升任两浙路安抚司参议官。关于这次升职,据说还有大臣反对,理由是有功之臣才能升任。孝宗不置一词,将《皇朝文鉴》重重地摔在反对者面前,该大臣才噤声。
然而,孝宗有心,吕祖谦却已无力。他任著作郎时就已生病,编《皇朝文鉴》更是个体力活,若非有学术重任撑着,恐怕早就垮了,面对这次升职,他便以生病婉辞了。
淳熙六年,陆九渊之兄专程来金华拜访吕祖谦—他早觉今是而昨非,已经完全皈依朱学。时隔四年,原以为鹅湖之会是个烂尾工程,谁知终于达到了预期目的,吕祖谦很高兴,写信与远在福建的朱熹分享。遗憾的是,一年后,陆九渊之兄即作古。
又一年后,陆九渊专程拜访朱熹,请朱熹为自己兄长写墓志铭,并到朱熹主持的白鹿洞书院讲学。其时,吕祖谦已病入膏肓,听到消息后,挣扎着写信给朱熹,叮嘱他们切磋技艺,搞好关系。而此时,距他病逝只有短短几个月时间了。
所幸,吕祖谦看到了:经过时间的沉淀,经过自己和当事人不懈的努力,鹅湖之会上的书生意气,终于消解为智者间的一团和气,至此,鹅湖之会终于成了双赢。
淳熙八年,吕祖谦病逝,年仅44岁,而好友张栻已于一年前先他而去。只剩下比他们年长的朱熹,像他们的墓志铭,孤独而痛苦地活着。
吕祖谦一生搞学术、搞教育,平顺而平淡,几乎都是在朝廷核心之外徘徊。其实他也想像祖先一样干一番大事业,但最终成为宗师而非能吏的原因,正像他自己说的:成年后,“堙废于隐忧,竟失全功”,只剩下早年的壮志在风中飘零。
这隐忧自然有国忧:南宋“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内忧外患,着实让人心焦。但更多的是家忧:从他中进士的前一年开始,他的发妻、长子、母亲、继任妻子、女儿、父亲和第三任妻子在17年间相继去世,他眼睁睁地看着,想挽留,却无能为力,接连而至的沉重打击让他甚至有些怀疑自己—任重而道远,他自己却缠绵病榻多年,这是否预示着人生目标的最终沉没呢…?
这些隐忧让他沉痛,让他窒息,却也无意中让他的人品和才学益发生辉,使其身后哀荣无限。他去世半个多世纪后,宋理宗先追封其为开封伯,后令其配享孔庙,这个徘徊于朝廷核心之外的病弱儒生在身后却达到了吕家祖先都难以企及的高度。可惜,吕祖谦生前的最高目标—以理学+史学的双保险令悬崖上的南宋起死回生,最终也未曾实现。
宋理宗一方面纪念他的才华,一方面无视他在史学方面整理出的宝贵资鉴,竟重蹈了北宋末年联金灭辽、招致靖康之耻的覆辙,主导了联蒙灭金的战争,埋下了蒙古灭宋的祸根。耗尽平生力气炼的“金丹”,却被束之高阁,未能发挥奇效,吕祖谦生前若能得知,大概也只能像鹅湖之会结束后,报之以无力的长叹吧。
编辑/葡萄
2017年5期《百家讲坛》(蓝版)精彩看点
茶香绕室、青衫洁净,是我们对儒雅君子的基本设定。然而到了章太炎这里,屋子脏脏、头发臭臭、衣服没洗、虱子乱蹦……哎,内心世界的秩序都被他破坏了。虽然儒而不雅,人设崩塌,可是仍然有那么多人崇拜他,敬爱他,而他也是值得敬爱的。(详见P46《章太炎:这是课本之外的我》)
“作秀”这个词现在很火,你可知道,慈禧原是作秀者的前辈。想当年,慈禧为了让臣民对自己敬而生畏,自导自演了一场猎熊真人秀:只见她全身披挂,骑着骏马,手持长枪,英姿飒爽地出场了,正当所有人为她屏气凝神,捏一把冷汗的时候,黑熊被慈禧一枪毙命。这场真人秀看似很成功,不想却成了坊间的笑柄。(详见P17《慈禧立威,殃及异类》)
俗话说“人红是非多”,如果哪个明星不被扒扒黑历史,就说明他不够红。今天,小编也来扒扒某人的黑历史,但扒的不是娱乐明星,而是二战明星——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蒙巴顿。你以为战功赫赫的蒙巴顿生下来就是作战天才吗?No!在成为天才前,他曾把驱逐舰当车飙,自作主张把军舰的颜色涂成嫩嫩的粉红色,还打算用冰做航空母舰,甚至还想把属下的战功据为己有……(详见P50《蒙巴顿:赫赫战功难掩荒诞本色》)
“大师”扰乱社会秩序,怎么办?当然是抓起来问罪啊!谁知人家运气好,竟碰上皇帝大赦天下,非但没有坐牢,反而在京城混得风生水起,捞钱捞到手软。说实话,这只是因为他没有触碰到皇帝的底线,不然皇帝能给他好果子吃吗?(详见P8《大师有术,皇帝有道》)
成吉思汗让他的姓氏充满光辉,元朝灭亡后,草原上还流传着“只有成吉思汗正统的继承者才有资格称‘汗’”的观念。几百年后,爱新觉罗家族却成了成吉思汗的继承者。这是为什么呢?(详见P53《清帝:我是成吉思汗的继承者》)
2017年《百家讲坛》杂志更精彩!只需拨打邮购热线0371-56782056即可订阅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