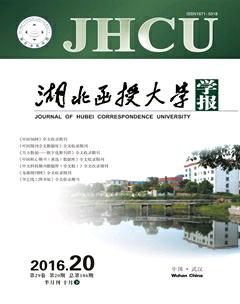性别之困与“革命”之厄:女性如何穿越“文革”
张闽敏
[摘要]严歌苓是旅关作家,她也是“文革”的亲历者,她穿越三十多年的时空隧道,携带着中西文化语境的特色,以其独有的视角对文革进行反思。她通过《白蛇》中孙丽坤、徐群珊这两个女性形象的塑造,展现了“极致环境”中人性的幽僻,更是对其背后的政治、生活、情感等因素进行了深入探究,深刻揭示出文革时代的女性生存困境。
[关键词]文革;女性;穿越;生存困境
[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6)20-0188-03
孙丽坤和徐群珊,是严歌苓在《白蛇》中塑造的两个女性形象,一个是曾经红极一时的舞蹈家,一个是叛逆而追求美的文艺青年,在文革这个“极致环境”中她们相遇、相恋、相离,敷演出一段让人唏嘘不已的故事的同时,更多的是展现了女性在那个非正常年代下人性的压抑、扭曲甚至是异化,她们的生存困境着力揭示出一个时代的隐痛。
一、“文革”对女性的践踏
(一)被压迫的政治困境
“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灾难,这场全民参与的政治运动长达十年之久,它以狂风暴雨之势席卷整个国家,每个人都无可避免地挣扎在这一场风暴中。
文化界也在劫难逃,满目疮痍。无数知名人士都遭受到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其中很多人不堪受辱而走上绝路。《白蛇》中的孙丽坤就生活这种“极致环境”中。她曾是省歌舞剧院主要演员,得过国际大奖,其自编自导的舞剧《白蛇传》在社会上引起极大轰动,所创“蛇步”更是风靡一时。可文革伊始,孙丽坤便成为“革命群众”锁定的目标,“于一九六九年被定案为资产阶级腐朽分子、国际特务嫌疑、反革命美女蛇,同时被正式关押审查”。孙丽坤在文革中身陷被压迫的政治困境,在强大的政治背景下,她是渺小的、失语的。这些在“官方版本”中可见一斑。“官方版本”是由省革委会宣教部、省歌舞剧院革命领导小组、市公安局等国家单位的几份公函组成。公式化的语言,权威性的文字,无不在昭示主人公的处境。在“革命”的名义下,法律是失效的,孙丽坤被关押、审查、定罪的主要依据是她本人长达四百余页的反省书,反省书的内容是她和捷克舞蹈家浪漫的三天恋爱经过,而这正是人们认为很有必要追究的腐化堕落,一次艳遇使孙丽坤成为“革命”的囚徒,在“革命”的强制权利话语下她的个人话语是被遮蔽的,所以,她被无休止地批斗,被一遍一遍地要求细节化反省书,甚至被暴力挟持进行妇科检查。“文化都莫得,我有什么反动思想?写反省书认罪书翻烂了一本字典。”孙丽坤的自嘲无疑是对所谓“调查”的讽刺,但是,何人可曾听见抑或何人可曾愿听,因为她已经完全丧失了话语权。“文革”结束后,孙丽坤获得平反,恢复了社会地位。《成都晚报》的特稿大张旗鼓地对这个“已人到中年,却坚持苦练舞蹈基本功”的“前著名舞蹈家”予以热情洋溢地歌颂,但是只字未提其在“文革”中所受的迫害,而且抹煞事实,把舞剧团成员粉饰成给予她莫大帮助的有功之臣。在特稿中的孙丽坤对新生活有着幸福的憧憬,内心宁静而温和。抽丝剥茧之下我们发现,从艺术家沦为反革命,又被平反,孙丽坤只能随着历史的洪流浮浮沉沉。她的悲剧命运,不过是那个“极致环境”中的一个小小缩影,突显出女性在政治困境中的无助,更影射出一个时代的荒诞。
在政治话语和男权社会的双重夹击下,即使得到总理关心的孙丽坤也只能接受命运的摆布,更何况是其他女性呢?徐群珊是在文革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少女,她叛逆,把《红旗》杂志、《毛选》的封皮套在电影杂志、《悲惨世界》的外面,但最终也不得不响应毛主席发出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去“修地球”。作为最弱势群体存在的女知青是失语的,她们往往在被逼迫的情况下用身体去换取相对舒适的生活,或者是回城的一纸批文。徐群珊虽然没有让这种厄运降临到自己身上,但是女知青的生活却是她情感命运的转折点,她开始轻蔑女孩子的肤浅,鄙夷男孩子的粗俗,寻找超然于雌雄性之恋上的生命。
(二)被扭曲的生活困境
孙丽坤的美因了《白蛇传》而愈显神秘、优雅、不食人间烟火。男人爱慕她,却觊觎有朝一日能被她的水蛇腰缠上床;女人艳羡她,却心生嫉妒和猜测。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炮制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展现自我、张扬个性的孙丽坤立即遭受到革命群众的冲击,她不再是画中人,高雅的“白蛇”立马化身风骚的“美女蛇”,成了国际大破鞋。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经典之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指出,“群体”最重要的心理特征是几乎像被催眠那样易于接受暗示,并具有极强的传染性。“但是从感情及其激起的行动这个角度看,群体可以比个人表现得更好或更差,这全看环境如何。一切取决于群体所接受的暗示具有什么性质。”“文革”前夕,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革命群众”凭敏感的“政治嗅觉”主动“发现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强,更何况是组织批判的。在这种畸形心理的支配下,群众才在会在一声令下之后随即便疯狂地响应、投入“革命”,做出种种超越理智的行为。“大会小会斗争她,她也不放下那个下巴颏”的孙丽坤的人生终被扭曲,甚至走向毁灭。
“给关进歌舞剧院的布景仓库不到半年,孙丽坤就跟马路上所有的中年妇女一模一样了。”一群女娃一手促成了孙丽坤的惊人改变,她们是歌舞剧院学员班的学员,过去对孙丽坤毕恭毕敬,把她当“祖师爷”。然而“文革”中这些女娃摇身一变成为专政队员,挥舞着大棒看押着孙丽坤。连女人的长辫都是革命对象的时代,雌性被压抑被扭曲,女娃们几年造反舞跳得宽肩粗腿大嗓门,过度的渴望导致她们对美变本加厉的仇视。于是,打著“革命”的旗号,她们肆无忌惮地发泄着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权利欲和破坏欲,摧毁自己曾膜拜的偶像,满足自己备受克制的欲望。
孙丽坤一发胖就成了个普通女人,优雅与美丽被磨灭了,自尊与廉耻也随之消失。她习惯了若无其事地跟女娃们脸对脸蹲茅坑,对加诸在自己身上的一大串不好听的罪名也满不在乎。臃肿、粗俗、泼辣的孙丽坤在建筑工们的挑逗与戏弄下越发沉沦,自甘堕落。为了一包烟锅巴,“她抓起脚后跟朝天上举起,两腿撕成个‘一字”,孙丽坤在笼子内般的铁栅栏内,成了一只马戏团的猴子,建筑工们也未曾料到,两年牢监关下来,如仙如梦的孙丽坤早已抛却了自尊与廉耻,变得粗鄙不堪。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提到:“如果说最严厉的惩罚不再施加于肉体,那么它施加到什么上了呢?……那就必然是灵魂。曾经降临在肉体的死亡应该被代之以深入灵魂、思想、意志和欲求的惩罚。”在文革中,身体惩罚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受迫害者遭受到从肉体到灵魂的多重折磨,孙丽坤已经彻底沉沦在被扭曲的生活困境中,等待救赎。
二、拯救的力量
当“那个青年背着手站在她面前。他背后是层层叠叠的败了色的舞台背景,孙丽坤突然意识到他就站在《白蛇传》的断桥下,青灰色的桥石已负着厚厚的黯淡历史”。徐群珊(化名为徐群山)的出现,如同一道闪电划过黑暗的天际,震撼了浑浑噩噩的孙丽坤。她猝然转身走进另一块布景搁置的小角落,“不是为了更衣修发,而是要彻底换一番精神容貌。她知道自己的精神容貌是丑陋不堪的,如同一具裸露的丑陋不堪的肉体”。这个意外的“下台动作”,暗示了孙丽坤内心深处对人格和尊严的维护。之前,孙丽坤的世界就是那群女娃和建筑工,做人的底线已经被他们践踏,于是她索性撕裂价值,毁灭美,满足众人变态、龌龊的私欲。可是,当她重新登场,面对这个人时,蛇一般的冷艳孤傲在她的容颜与心中复活了。
清俊而带有儒雅的猖狂的徐群珊,其对美的渴望与尊重,让孙丽坤重拾舞蹈,恢复美丽,更让她舒展出新鲜和生命。活到三十四岁,孙丽坤“第一次感到和一个男子在一起,最舒适的不是肉体,是内心”。她感觉他是来搭救她的,如同青蛇搭救盗仙草的白蛇。长期被监禁、被压抑的她,紧紧抓住这唯一的希望和救赎,即使被作弄、被迷恋、被折磨、被毁灭,也不管不顾,因为她已经不能没有他。内心深处的极度渴求让孙丽坤在潜意识里回避对方是同性别的可能,当真相慢慢揭开面纱,任她去否认去拒绝,却怎样也避开不了。在孙丽坤看来,同性恋是令人恶心的,但她已深深沉溺,再也顾不上这种让人作呕的感觉。荒诞岁月里催生的这个爱情故事,一度使孙丽坤精神失常,但她最终还是认同了性别错位的徐群珊,对这段被异化的感情选择了妥协。
小说中,徐群珊的性别角色是毋庸置疑的。她从小迷恋“白蛇”。《白蛇传》里青蛇本是男儿身,倾心于白蛇,于是两人约定比武,青蛇胜了,白蛇就嫁他为妻;白蛇胜了,青蛇就幻化成女的,一辈子服侍白蛇。结果青蛇败了,便化作女儿身,做了白蛇的贴身丫鬟,并以姐妹相称。青蛇和白蛇的情感是整个小说的底色,和情节的发展遥相呼应,也预示了青蛇和白蛇无法摆脱的宿命。徐群珊对青蛇的忠诚勇敢、体贴入微是认同的,对许仙是厌恶之极,青少年时期暗自滋长的异样情愫促使她给予落魄时的孙丽坤强烈的爱,这种爱是一种由生活的扭曲造成的性别认知倒置的爱。
少时的徐群珊面对自己的性别偏离是恐惧的,她常常告诫自己必须做一个正常健康的共产主义接班人。然而,在那个“极致环境”中,徐群珊越走越远。文革时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指导下,女性终于踏上历史舞台,不再是隐性的角色,“这个时期的女性是矛盾的混合体,是改造者,也是被改造者,或以准男性的战士的身份异化自己而获得改造他人的权力,在挣脱了历史枷锁的同时,失去了自己的性别和精神,拥有一种被异化的面貌。”事实证明,虽然当时的女性成为人们的关注对象,但是她们社会地位根本没有得到提升,甚至比以前还要低。她们看似获得自由,然而在这个历史特殊时期女性依然遭受到极大的伤害。所以,当徐群珊发现男性化的打扮在“修地球”的日子里避免了许多骚扰和欺辱后,她开始有意识地对性别进行思索与选择。她愈发抵制女性特征,自觉向男性化的特征靠拢,徐群珊的部分女性特质渐渐丧失,最终导致了她性别意识的迷乱和错位。因此她扮演的“徐群山”才能瞒天过海,并使“白蛇”为其倾倒,因缘际会下拯救了她。
三、吊诡的记忆
直到荒诞的时代结束了它的疯狂,离奇的故事也走向了尽头。在社会伦理和道德规范的强大制约之下,孙丽坤和徐群珊恢复了正常人的生活,各自找到异性伴侣,那段狂热年代的夹缝中进发出的情感成为了一段吊诡的记忆。
当孙丽坤接到徐群珊的结婚通知时,被狠狠弄痛了。但“她告诉自己,该为珊珊高兴,从此不会再有太大差错了。她们俩那低人一等的关系中,一切牵念、恋想都可以止息了”。表象上,孙丽坤抵触这段“低人一等”的感情,内心深处,她又泥足深陷。徐群珊曾是她生活的唯一一束阳光,充满尘埃,但却有真切的温暖。所以,孙丽坤潜意识里为徐群珊挑选的结婚礼物是白蛇和青蛇怒斥许仙的玉雕,这个充满暗示性的玉雕暴露了她对徐群珊扭曲纠缠而又难以言说的情感。当离别如期而至,孙丽坤回首告别已为人妻的徐群珊时,心里却在深深地呼唤另一个“徐群山”。一段秘而不宣的恋情随风飘逝,但于孙丽坤而言,何曾风过了无痕呢?
值得玩味的是,少时痴迷“白蛇”、文革中拯救了“白蛇”的徐群珊率先放弃了孙丽坤,她选择了与一个绝不标新立异的本分男人结婚。“珊珊在他身上可以收敛起她天性中的别出心裁。珊珊天性中的对于美的深沉爱好和执著追求,天性中的钟情都可以被这种教科书一样正确的男人纠正。珊珊明白她自己有被矫正的致命需要。”曾经叛逆而勇敢的徐群珊在社会秩序逐步恢复正常后,面对现实生活选择了妥协,她没有坚守这段感情,因为在社会规范和道德伦理之下,这种“拯救”已经丧失了力量,“畸恋”最终被中国式的家庭伦理收罗。
作為文革中的弱者与边缘人,孙丽坤和徐群珊遭受到中国父权社会的凌越歧视。严歌苓站在中西文化语境的交接地带,仍固守着在中国形成的关于两性的传统观念,最后让她们各自轮回到世俗的归宿中去,尘封记忆,眼睁睁地承认当下的残酷,透露出作者冷静的忧伤。
《白蛇》让我们看到在政治漩涡中思想被异化的幽僻人性,特别是女性在政治强权下命运无法主宰的无奈与悲凉,她们步履维艰、伤痕累累地穿越“文革”,促使我们对这样一段历史进行回望与反思,因为,一个忘记历史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
(责任编辑:封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