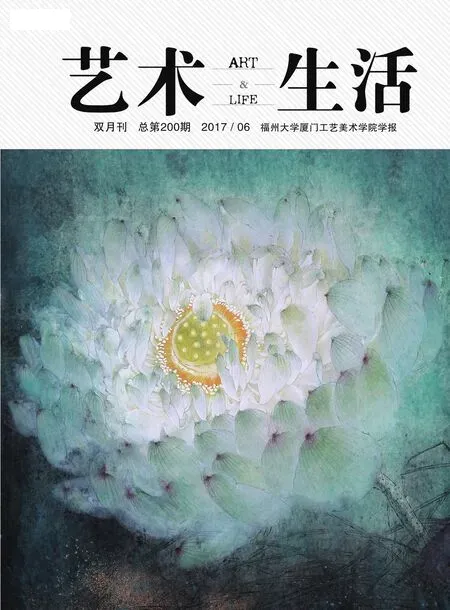包容万象与天人合一
——论隶书与汉代建筑设计思想的美学关联
连超
(四川大学 艺术学院, 四川 成都 610207)
北魏文臣江式在其《论书表》中言:“隶书者,始皇时使下杜人程邈所作附于小篆所作也。”[1](P64)隶书传为秦人程邈在云阳狱中所创,但据考古资料显示早至战国时期已有隶书的萌芽,即所谓由篆到隶的过渡时期——“隶变”。关于隶书的定义,西晋书论家卫恒在其《四体书势》中云:“秦既用篆,奏事繁多,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汉因用之,独符玺、幡信、题署用篆。隶书者,篆之捷也。”[2](P15)经过战国、秦代两个时期的演进,隶书至汉代尤其到东汉已臻于完备与鼎盛。此时书家迭出,刻石书法丰盛,许多名碑诸如《石门颂碑》《乙瑛碑》《礼器碑》《曹全碑》《张迁碑》等书法碑刻以其“蚕头燕尾”“一波三折”的独特造型魅力而流芳百世、名垂青史!
汉代的建筑与隶书同为汉代文明宝库中的璀璨明珠。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代建筑以其精湛巧妙的设计思想与宽博舒展的艺术造型,无疑在汉代艺术中占据了至关重要的地位,对后世建筑以及汉代其他艺术门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将结合汉代建筑的设计思想来分析同时期隶书的形式美感,进而总结两者的内在美学关联。
一、汉代隶书波磔的形式之美
“波磔”作为书法史中一个专有名词,用来形容隶书横向线条的飞扬律动,以及末端笔势扬起出锋的美学意味,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翻飞波动”“蚕头燕尾”之势。著名书法理论家金学智教授在其《中国书法美学》中指出:“分别向背,是八分的意法,也可说是隶书的意法,它集中体现在波磔之笔上,而这又促成了隶书左右开张的艺术风格”。[3](P472)东汉时期,随着国力强盛以及儒家奉行忠孝礼仪的制度影响,厚葬风气极为盛行,由此树碑列传之风盛行。作为该时期书法主导地位的隶书碑刻可谓瑰丽多姿,异彩纷呈。而每件碑刻中的波磔之美又不尽相同,各具特色。接下来就以部分碑刻为例来探讨隶书的波磔之美。
(一)《石门颂》:纵横开阖
《石门颂》(图1),全称《汉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亦称《杨孟文颂》。东汉建和二年(148年)十一月立,著名摩崖石刻,现藏陕西汉中博物馆。碑文详细记述了东汉顺帝时期司隶校尉杨孟文上书请修褒斜道及修通褒斜道的经过。《石门颂》为纵逸奔放书风的代表作品。该碑首先具有汉隶的典型风格,字形扁方,转折、波磔较为明显,反映出中国书法由篆而隶的演变过程;其次表现为符号化与抽象化,其造型极具浪漫性和装饰意味。采用抒情与夸张的用笔以增强书法的节奏感和运动感。该碑以圆笔为主,并将方笔与圆笔巧妙地融合而富于变化。起笔逆锋,含蓄蕴藉;行笔中锋,敦厚稳健;收笔回锋,少有雁尾而具掠雁之势。笔画圆润畅达、含蓄古厚而富有弹性,毫无做作之态。其结字舒展放纵,体势瘦劲开张,意态生动自然。通篇看来纵横开阖,意趣横生。
(二)《乙瑛碑》:俯仰有致
《乙瑛碑》(图2),全称《汉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史碑》。东汉永兴元年(153年)立,现藏山东曲阜孔庙。此碑记载司徒吴雄、司空赵戒以前鲁相乙瑛之言,上书请于孔庙置百石卒史一人,执掌庙祀之事。《乙瑛碑》是汉隶中有名的逸品,字势开张,浑厚古朴,俯仰有致,向背分明。特别是碑刻波磔后半段,采用笔杆左侧倾倒的逆向行笔,使每一点画力透纸背、入木三分。清人杨守敬曾言:“是碑隶法实佳。”翁方纲亦云:“骨肉匀适,情文流畅。诚非溢美,但其波磔已开唐人庸俗一路。”这正讲出了该碑的微妙处。临写此碑要特别注意波画的“逆入平出”,尤其是起笔逆势不能形迹外露。该碑书法看似规正,实则巧丽,字势左右拓展。书风谨严素朴,实为学汉隶的重要范本之一。

图1 《石门颂》局部

图2 《乙瑛碑》局部

图3 《礼器碑》局部

图4 《曹全碑》局部

图5 《张迁碑》局部

图6 汉代未央宫复原图
(三)《礼器碑》:清新劲健
《礼器碑》(图3),全称《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又称《修孔子庙器碑》《韩明府孔子庙碑》等。东汉永寿二年(156年)立。现存山东曲阜孔庙。碑文记述了鲁相韩敕修饰孔庙、增置各种礼器、吏民共同捐资立石以颂其德一事。《礼器碑》的笔画瘦硬刚健,收笔转折处多方折,笔画较细而捺画粗壮,形成强烈的视觉冲突,且与居延汉简书法多有相似之处。它虽瘦而不露骨,虽细而不靡弱,总体力度非凡。其碑阳书法更是精美绝伦。而碑侧与碑阴,因载捐资者姓名及钱数,字体大小疏密皆不经意,但反而有一种变化之美。其波磔则较其它笔画稍粗,至收笔前略有停顿,借笔毫弹性迅速挑起,使笔意飞动,清新劲健。“燕尾”即捺画大多呈方形,且比重较大给人一种气沉势雄之感。
(四)《曹全碑》:飘逸灵动
《曹全碑》(图4)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此碑立于东汉中平二年(185年)十月,出土于明万历初年陕西郃阳县旧城,1956年入藏西安碑林,碑文记述了郃阳县令曹全的家世及生平事迹。此碑是汉碑代表作品之一,是秀美一派的典型。其结体、笔法都已达到十分完美的境地。其点画刚柔相济,圆劲秀润,飘逸而不媚俗,丰实而不臃肿。此碑主要笔画多以飞扬波挑、蚕头燕尾形式呈现。其波磔弧度定有直线相对,使其飞扬流走处不至轻滑草率。字体纵向中稳健含蓄,从而使其结构广博而雍容,秀逸而多姿。
(五)《张迁碑》:质朴古拙
《张迁碑》(图5),全称《汉故榖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亦称《张迁表》。刻于东汉中平三年(186年)于明代初年出土,现存于山东泰安岱庙。碑主张迁,曾任谷城(今河南洛阳)长,改荡阴(今河南汤阴)令。碑文记述故吏韦萌等为追念其功德而立。运笔以方笔为主,棱角分明,总体具有方、直、齐、平的特点。其笔画粗细介于二分与三分笔之间。横势波画的提按顿挫不甚明显,与孔庙三碑的大撇重捺有所区别。其字形偏于古拙方正,字迹虽多斑驳,然端雅整练,剥蚀之痕亦显天然而又苍茫,结字运笔已开魏晋风气。碑阳之字朴拙厚重,碑阴之字雄逸纵肆,皆大气磅礴,酣畅淋漓。其整体结构揖让错综,灵活多变,生机盎然而又方劲沉着。
二、汉代建筑艺术的设计思想
(一)重威思想与壮丽之美的追求
汉代治国以儒家思想为宗,其建筑设计思想自然会受到儒家政教功能的影响。通过建筑形式来彰显至高无上的皇权与并吞天下的气度,成为汉代设计与营造建筑的主流思想。《高祖本纪》中曾记载,公元前199年,丞相萧何主持建造未央宫(图6)。因高祖刘邦信奉黄老、崇尚节俭,建国之初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见宫阙如此奢华浩大,十分震怒,故质问萧何:“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对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高祖刘邦听后觉言之有理,甚是高兴。萧何这种非壮丽无以重威的思想,在传承孔荀思想的基础上,极为巧妙地将汉代儒家思想运用在建筑设计之中了。孔子在《论语》中曾言:“君子不重则不威。”暗含形式对本质,外在对内在的重要性。 与此相应,荀子亦将此思想进一步升华到兴邦立国的层面,论及君权与王权之上。他在《荀子·富国》中谈到:“为人主上者,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强不足以禁暴胜悍也。”如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与了解汉代建筑追求壮丽之美的原因所在:一方面是出于艺术审美的需求,而另一方面则更是源于江山社稷的需要。
按照儒家的思想,建筑壮丽的概貌可达到重威的效果。相反,若想臻于重威的效果就应在建筑营造中追求壮丽之美,而质变的前提在于量变的累积。同理,建筑壮丽之美的生成的首要条件便是量。即建筑的大小、数量以及空间的占有量。故而,为了体现壮丽而重威的效果,汉代宫殿、陵墓和庙宇建筑均以奢华宏大、冠绝古今而著称。西汉初年始建诸如未央宫、长乐宫等大型宫殿。汉武帝刘彻时扩建上林苑,占地面积达3500km2,其规模之大可谓前所未有。与此同时。作为高大建筑负空间的营造也在地表留下成系列的纪念性建筑物。帝王陵墓便是典型代表。汉武帝的茂陵富丽堂皇、巨大无比。陵墓封土高达46.5m,边长230m。帝王陵寝如此,将相之墓亦然。西汉名将霍去病的陵墓如同祁连山一般气势壮阔,无疑带有非壮丽无以重威的寓意。除此之外,在大量体积较小的建筑装饰物件上也不难看出其深含此意。如汉代瓦当,其线条挺拔,造型奇特,形体奔放而气势雄强。鲁迅先生曾以“深沉雄大”来评价汉代的建筑,可谓凝练而中肯的评价。[4](P873)“非壮丽无以重威”的儒家思想为汉代宏伟壮丽的宫殿、庙宇、陵墓等建筑奠定了强有力的根基。
(二)阴阳五行与建筑的精神寄托
如果说儒家思想为汉代建筑提供了宏观的设计理念,那么阴阳五行则为汉代建筑设计确立了客观的建构方式,即一切建筑应遵循“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的准则。汉代建筑设计所采用的这种模式,蕴含了汉代人一种“容纳万有,并吞八荒”的气质。关于汉代建筑的设计理念,《礼含文嘉》中有言:“上圆象天,下方法地,八窗法八风,四达法四时,九室法九州,十二座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气,七十二牖法七十二候也。”《汉说》中以“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王者制宫阙殿阁取法焉”来描述未央宫。汉代著名学者张衡在其《西京赋》中曾提及:“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仿太紫之圆方。”此外,他在《东京赋》中也谈到:“复庙重屋,八达九房,规天矩地,授时顺乡。”
如此看来,汉代建筑将设计思想与天象地貌紧密结合,不仅将地上建筑的格局效法天象,而且在建筑内在的建构法则方面也做到了相互通感、彼此对应,这种天地相通、天人互感的表征,充分显露出一种大气魄与大智慧。建筑总体上体现了汉代人的时代精神和民族自信,建筑的设计已经超越了单纯物质空间的整合而已升华为一种精神气度的寄托!
三、隶书与汉代建筑的内在美学关联
(一)均以儒家思想为宗
先秦时期学术异常繁荣可谓异彩纷呈、百家争鸣,其中,儒家是创立较早、影响较大的一个学派。汉武帝时期接受董仲舒的建议,文化上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家思想随即登上汉代学术正统的宝座。先秦儒家的真精神以及思想最具创意的部分便是人本主义与心性之学,这是儒学的本源也是最具特色的部分。孔、孟学说在客观表现方面最重教化,政治、社会的功能皆系于此,孟子的性善论主要就是要在人心中建立起教化的依据。在此基础上,教化的方式是扩充四端,教化的工具是六艺,教化的目的是激发人的自信,且反求诸己以自行其善。“儒家思想与学术的基本取向是在对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探讨,儒家思想考虑的往往不在物质利益,而是首先从社会安定、以及人的思想意识着眼,对造物成器的形式和内容进行规范和渗透。”[5](P317)
关于美学与设计艺术学,儒家思想虽未作出更为详细而直接的总结,但是它所倡导的仁义思想、礼乐精神、道德规范以及以义制利的价值观念,则为隶书与汉代建筑提供了十分丰富的理论基础。同时,由于汉代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社会阶级矛盾又十分剧烈,这些都极大地刺激了隶书与建筑艺术的高度发展。儒家的六艺本非一人的家学,其中有多种思想之萌芽,后被人引申附会为对于不同的思想具有兼容并包的特征。因此,在汉代独尊儒术以后,与儒家本来不同的学说,仍可在六艺的大帽子下改头换面保持其存在。可见,汉武帝时期所独尊的儒家思想可谓兼收并蓄,开放包容,进而成为汉代雄强敦厚的艺术之风稳固的思想源泉。
(二)均以阴阳五行为本
从古至今,阴阳五行思想可谓涉及广泛,影响深远。古代关于解释宇宙的起源与结构有两条途径,其一见于阴阳家的著作,其二见于儒家的经典《易传》。前者有《洪范》和《月令》两部经典,都强调五行而不提阴阳,相反,《易传》则只强调阴阳而不谈五行。随着时代的进步以及人们思想意识的提升,发展至西汉,这两种思想已渐趋融合,因此,司马迁在《史记》中将两者合称之为“阴阳家”。阴阳五行遂成为汉代普遍流行的思想观念。在汉代人眼中,宇宙可总体上视为一,又可从基质上分为二,还可细化为四,进而扩展为八,最后衍生为六十四,最终生成万事万物。整个宇宙构成了一个条理清晰、秩序分明又可增减伸缩、互通互动的整体。不同事物之间既横向互通,又纵向相连,进而形成了新的境界——生理与心理互参,情感与道德互渗,自然与社会互动,时间与空间互转,抽象与具体互融,色声趋同,人神同质,总而言之为“天人感应”。
在汉代人看来,宇宙是一个浩瀚无比的体系,其中包含自然、社会和文艺等在内的互动系统,这其中当然也包括隶书与建筑艺术在内。汉代著名书法家蔡邕在其《九势》中曾言:“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此外,他在《笔赋》中又讲到:“书乾坤之阴阳,赞三皇之洪勋”。蔡邕所言意在说明书法的构成体现了乾坤之阴阳矛盾统一之理:有自然的存在,就有阴阳的矛盾存在。有阴阳统一的矛盾运动,就有了世事万殊,也就有了书法的形与势。汉代的这种相互通感的宇宙模式, 既为隶书与建筑艺术包罗万象的特点提供了哲学思辨,同时,又为其艺术特色确立了内在的逻辑构架。
(三)均以线性流动为美
汉代建筑不以单一独立的建筑为目标,而是十分巧妙地利用木质结构的特点,采取空间平面展开、彼此连接的群体建筑为宗旨。而建筑在平面上延展,实际上已把建筑的空间概念转化为时间进程。此外,在个体建筑的空间布局上也同样体现出了这种时间进程的流动美。由于建筑的流动之美是通过线条达到的,所以,汉代建筑总体又显示出“线”的艺术特征。汉代建筑屋顶的曲线与向上扬起的飞檐,使得原本沉重厚实往下压的屋顶,反而随着线条的弯曲上扬,而彰显向上挺举的灵动飘逸,加上宽广的屋身和敦厚的台基,使整个建筑文中安定而无头重脚轻之感,体现出一种超凡的力量感与运动感。
与汉代建筑所表现的线性特质相应,隶书亦然。众所周知,中国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以笔墨为媒介,以书家情怀为纽带而表达的造型艺术。书法的最终展现形式即以线条的自由舞动为根本。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先生曾言:“这种净化了的线条——书法美,就不是一般的图案花纹的形式美、装饰美,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有意味的形式’。它是活生生的、流动的、富有生命暗示和表现力量的美。”[6](P40)隶书那波磔开张的“蚕头燕尾”正是这种多样流动的自由美。
隶书波磔运动时必须转笔使笔锋聚焦,运行至水平线中段时再缓慢拱起,如同汉代建筑飞檐中央的拱起部分。继而笔锋顺势铺毫下压,力足势强之后再提锋转笔慢慢向右挑起,形成一个逐渐上扬的“燕尾”,也就是汉代建筑飞檐末端檐牙高啄的“出锋”形式。隶书的美建立在“波磔”线条的悠扬流动,如同汉代建筑以飞檐建构最主要的视觉美感印象。两者充分体现了强烈的动感与神秘的美感。[7](P72)
结语
建筑设计由于人为地艺术创造,因此,特定时代的思想意识和审美观念必定会映射其中,其风格特征也必然受到那个时代历史背景、主流文化、宗教信仰以及民族性格的影响。汉代建筑为了彰显皇权至高无上、独一无二的威严与神圣,为了体现汉人包罗天下、并吞八方的胸怀与气度,遂以儒家思想和阴阳五行作为宗旨。因而,汉代建筑采取宏伟的构架,并将建筑仿效天地,使得天地遥感、人神互通,最终使汉代建筑形成了壮丽宏大的艺术风格,这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同时期隶书的艺术特色。
与汉代建筑遥相呼应,汉代以降,隶书发展达到了繁荣兴盛的局面。此时期的隶书典型美韵便是横向张开的蚕头燕尾,这壮丽雄强的蚕头燕尾可谓“一划开天地”,成为连接汉代建筑与隶书的津梁,使两者跨越时空而紧密相连。正是由于横划的波磔而使得隶书极具动态美感,同时也深刻体现了汉代人们气度恢弘的民族自信和灵动飞扬的审美追求。隶书以“蚕头燕尾、左右开张”的态势而彰显独特的艺术魅力,而这份特有的艺术魅力与同时代的建筑设计思想有着必然的历史渊源,两者尽管艺术形式不同,功用不同,而那种厚重雄放、恣肆挺劲的艺术风格却具有时代的共同点。汉代建筑设计思想为隶书的发展乃至兴盛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作用。而隶书的美学内涵也同样为雄伟的汉代建筑艺术添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