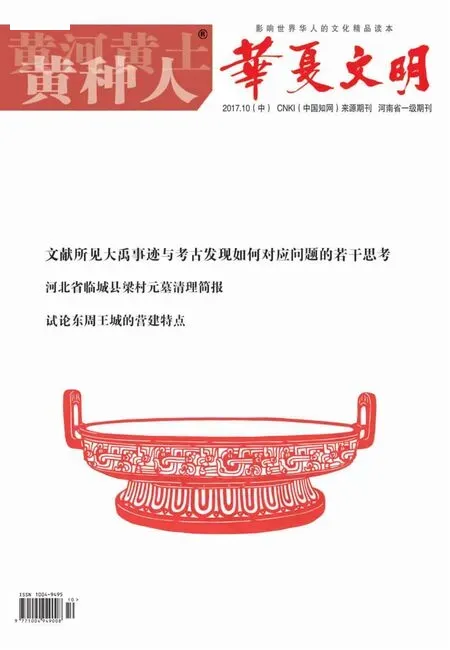宁夏明代“边防西关门”考
□周赟
宁夏明代“边防西关门”考
□周赟
明朝初期,蒙元势力退居漠北,宁夏成为明王朝与蒙古贵族对峙的边防前沿。明王朝先后设立“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绵延万里,分地守”[1]的防北要线——“九边重镇”,宁夏镇便是“九边重镇”之一的西北重镇。为戍守此道防线,明朝政府陆续沿“峰峦苍翠,崖壁险削,延亘五百余里,边防倚以为固”[2]的贺兰山山体建造了诸道长城墙体、关堡、壕堑、挡马墙、敌台、烽火台等防御设施,逐步建立起了一套依托贺兰山山体,攻防兼备的立体式防御屏障。在这个防御体系中,长城墙体是其主体,其他设施则为其重要的辅助和补充。
贺兰山沿线的长城墙体(即宁夏西长城)基本以赤木关(今永宁三关口)为界,其北山体高耸、足以峙守,故修筑长城时仅在一些宽敞、能通步骑的山口内修筑短墙——当路塞,其余部分则直接利用山险;赤木关以南则因山体低矮,难以直接依山戍守,故在贺兰山东麓台地历经多年建造了一道北迄赤木关,南到中卫黑林的长城。此段长城见诸文献的有 “城西南墙”、“边防西关门”等,前者因文献记载较为明确,学界对其认识较为一致;后者则因文献资料较为匮乏等原因,对其认识不一。笔者不揣浅陋,拟对此问题略作探究,以求教于方家。
一
“边防西关门”一词,最早见于《嘉靖宁夏新志》“边防”条目下的“西关门”条:“西关门者,北自赤木口,南抵大坝堡,八十余里。嘉靖十年,佥事齐之鸾建议于总制、尚书王琼,奏役屯丁万人,费内帑万金而为之堑者。初闻是议,父老以为不可,将士以为不可,制府亦以为不可。之鸾力主己议,坚不可回,踰六月而成之。成未月余,风扬沙塞,数日悉平。仍责令杨显、平羌、邵刚、玉泉四堡,时加调浚。然随挑随淤,人不堪其困苦。巡抚、都御史杨志学奏弃之,四堡始绥。”[3]该书明确记载了此道长城的起止、修筑年代、建造经历及废止原因等,是对此道长城最详尽的记录。但是除了这本史料外,在后来的史料中,无论《明史》《明通鉴》《明实录》等明代正史、通史,还是稍晚的宁夏地方史志《万历朔方新志》,以及清代《乾隆宁夏府志》《银川小志》等对此均无记载。
这道长城的具体位置在哪里?或者说哪道长城才是文献中所记载的“边防西关门”?这个问题尚未有人专门撰文探讨,仅在一些文章中偶有提及,对其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不确认说。此看法提出较早,如钟侃在《宁夏古代文物》一书中,未明确记载此道长城的位置[4],但首次将其称为“西关门墙”。
第二种:贺兰山山前说。此种说法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最早为许成等在《宁夏境内明代长城遗迹》一文中,将此道长城与南侧修筑于明成化年间的“城西南墙”一道,作为宁夏西长城“胜金关——赤木隘口”(又名三关口)段,认为其“应为嘉靖至万历年间,重新修葺、添筑而连成一线的”[5]。这种将“城西南墙”与“边防西关门”连成一道,认为其均分布在贺兰山东麓的观点后来逐渐成为主流。后来出版的《宁夏古长城》亦持此观点,且称其“今日保留下来的遗址断续可见,立于贺兰山东侧的半山坡上”[6];而稍晚出版的《贺兰山文物古迹考察与研究》一书中,虽然也是将此道长城归于西长城“胜金关——三关口”段,但并未笼统将其归于沿山长城中,只是在本段结尾列举了此道长城的文献资料[7];2003年出版的《青铜峡市军事志》中,则将青铜峡市境内的长城分为两段,其中北岔口以南属“城西南墙”,以北属“边防西关门墙”[8];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景爱先生则将此道长城全部归于“城西南墙”,其中将“青铜峡市向北,经永宁县进入银川郊区,止于赤木隘口”当作其延伸段,而西关门当是嘉靖年间对此道长城若干次修补之一处。同时,他又注意到了文献记录中的“堑”字,并将其释为“这是在边墙以外又增挖壕堑,以加强军事防御能力”,但是未指明此道壕堑的具体位置[9]。
第三种:赤木关说。此种说法以鲁人勇等为代表。其在“西长城”条目下,先是将此道长城归入西长城第三段(胜金关至赤木关),“其中大坝堡边关至赤木关,亦称 ‘边防西关墙’”,“由佥事督储官齐之鸾倡办修筑的西关门,即北自赤木口,南至大坝堡边关八十余里,当年即被风沙、山洪湮没而废。”但在后文辑录两次修葺赤木关后,又前后矛盾地增加一句“(赤木关)此为贺兰山诸口中最大之关墙,称之为‘边防西关门墙’”[10]。
以上几种观点,第三种直接将赤木关当作“边防西关门”,因缺乏直接证据,只存一家之说,本文暂不讨论。重点是第二种,持此观点的人较多,亦基本达成共识。现结合基础文献等对此观点进行分析探讨。
其一,从史料来看,《嘉靖宁夏新志》对此道长城记载较为详尽。按说该地方史志成书于嘉靖庚子年间(1540年),距离此道长城修建不足百年,其记录应该是真实可信的。本书将此道长城的防御意义提升到保障宁夏镇城西面安全的“西关门”之高度,足见对其褒嘉之高。(《嘉靖宁夏新志》还载齐之鸾亦曾为之撰 《朔方天堑西关门记》一文,惜此文已不存)。但是后来的诸多史籍文献均未对其记录,显然不合常理。如果真是如今三关口以南这道连续的、个别地段甚至原貌保存的长城的话,后来文献又为何空缺不载呢?
其二,《嘉靖宁夏新志》明确记载其“北自赤木口,南抵大坝堡,八十余里”。明确记载此道长城起点是“赤木口”,即今三关口,此处位置当无异议;问题在这道长城的止点 “大坝堡”。大坝堡位于今青铜峡市青铜峡镇韦桥村一组,在今唐徕灌溉水渠的西岸边,地势上属银川平原区。这里远离贺兰山与长城,距离最近的长城(大致在贺兰山大沙沟附近)亦有10多公里,若从山前分布的长城来看,三关口至此已有不下60公里。大坝堡属宁夏右屯卫所辖的十八屯堡之一,虽然文献中记载嘉靖年间(1522—1566年)曾设有官军仓场、驻扎有官军等,万历年间(1573—1620年),这里成为宁夏南路守备官厅驻扎之地。万历年间守备,属南路玉泉营管辖[11],但其性质和职能主要还是属于管理屯丁、屯田,为众多戍边兵士、马匹等提供饮食粮草等后勤保障的屯堡,其防御戍边职能相对较弱[12]。这就造成一个疑惑:为何此段文献中所记载的长城,其起点明确,在长城所在的山口处,但止点却不用位置清晰的贺兰山山口名称,而取一个与长城距离遥远且与长城防御关系不甚大的屯堡?
其三,从长城长度来看,《嘉靖宁夏新志》记载边防西关门全长“八十余里”,按明代一里约合今480米,“八十余里”即相当于今约38.5千米。按这个长度来推算,其南边当在今青铜峡市邵刚镇大沟村以西、贺兰山大柳木皋附近。但这里应为玉泉营戍守的范围,距离其最近的屯堡亦有邵刚堡等,而大坝堡在其东南约30千米处。如果这里作为“边防西关门”的止点,显然有悖常理。
其四,文献并未记载修筑长城墙体,而是壕堑。据我们现场调查,从三关口向南一直到北岔口这段夯土长城,因其多是沿贺兰山东麓的山前台地分布,其周围地表均属戈壁,多石少土,地势高低起伏,且多紧靠高山,故在其重点戍守的西侧均未发现有辅助长城墙体的壕堑遗迹 (北岔口以南长城西侧有一段壕堑,长10千米。其所在位置、长度等均与文献记载不符,显然非此道壕堑)。
其五,文献中所载的“边防西关门”,并未载其为“西关门墙”。墙即边墙,是明代对长城的一种变通称谓。直接将其称呼为“墙”乃是后来学者加上去的。西关门是宁夏西长城的一处防御设施应该没错,但它是不是就是长城墙体、是不是特指三关口以南、沿贺兰山修建的这道夯土长城,其证据尚不足。
据此,笔者认为,三关口以南的这道沿贺兰山东麓修建的夯土长城,可能不是见诸文献记载的“边防西关门”,而是历经多年修葺、增筑的“城西南墙”[13]的延伸部分。
二
那么“边防西关门”在何处?笔者认为,它可能是前几年长城调查中首次发现的暂定名为“黄羊滩壕堑”之长城。2007年开始的全国长城资源调查工作对宁夏明代长城进行了全面详细的调查,贺兰山山前沿线的长城是调查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在长达数年的田野调查中,文物工作者实地勘查了贺兰山沿线的明代长城设施,对存留的长城墙体、敌台、烽火台、关堡、壕堑等进行了性质认定、数据采集与登记、保存状况分类统计等工作,取得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尤其是三关口以南的这道长城,历时数年、不下四次的调查,对此段长城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三关口以南的长城,从三关口位于沟口处的头道关止点处开始,沿贺兰山东麓的山前台地(一些地段还在山间)辗转向南,途经磨石沟、北岔口、井沟、大佛寺沟、胜金关等沿山众多山口、关隘,最后出宁夏境与甘肃靖远卢沟界相接,全长约200千米。其中三关口以南直至北岔口两道长城交会处 (北岔口以南的长城可能为文献记载的“城西南墙”主体)的这道长城,虽然有诸如磨石沟等处几道长城交会、柳渠沟南侧长城错开等,但整体还是可以连成一线的,全长计22.3千米。在长城墙体之外未发现有壕堑痕迹,但在三关口东南侧的台地上新发现一道壕堑[14]。
此道壕堑的起点在三关口沟口东南约4.5千米、一道凸起的“丁”字形山梁上,是从山梁上的小井泉墩处开始,沿此处广袤平坦的山前冲积台地向东南,沿途经过诸条山峦、冲沟,烂营盘堡等堡寨,以及小井泉墩、福宁村烽火台等,横跨山前冲积台地,最后到平原地带(今永宁县闽宁镇福宁村)。全长16.9千米,方向基本呈西北—东南向。因其地处今永宁县黄羊滩农场场区内,故暂命名为“黄羊滩壕堑”(图一)。

图一 黄羊滩壕堑起点以南全貌
此道壕堑的修筑方式基本是在连绵起伏的台地上直接下挖一道壕沟,断面呈U形,两侧壁面较陡直,表面未经修整、加固处理。壕沟因受沙土淤塞等破坏影响,残存较深者可达9.6米,浅者不足1米,底宽约5米;壕沟内挖出的沙土等直接堆积在壕沟的西南侧边缘形成高垄。从断面看,垄属多次逐层堆积而成,质地疏松,未经加固处理。因长期坍塌破坏,今已成条状;残存底宽约5米,残高约1米(图二)。

图二 黄羊滩壕堑断面
首先,从长度来看,这道壕堑今存16.9千米。其向南已属现代村落,因农业开发、修路等原因,已损毁严重。据早年的调查及走访当地村民,均证实此道壕堑确实继续向东南延伸,按其走向向南延伸约23千米便可至大坝堡。如果将现存的16.9千米壕堑再加上这段距离,合计长度为39.6千米,与文献记载边防西关门的“长约八十里”基本相当。
其次,文献中明确记载有“堑”,但贺兰山三关口以南至北岔口以北段均未发现壕堑痕迹,反倒是在这道山前台地及平原处发现有壕堑。这一问题如何解释?此前学者有的避而不谈,有的只引用文献,只有景爱先生将西关门与壕堑分开,此观点较早明确地提出此道长城有壕堑遗迹,但其位置等并未明确指出。
通过梳理“边防西关门”这条文献记录,在“西关门”词条下,第一句是对其线路起止、长度的介绍,第二句以后则记录有关壕堑的情况。将新发现的黄羊滩壕堑与文献记载的“边防西关门”对比,可发现两者有以下相符之处:
1.此段壕堑西北自赤木关口处起,东南一直到大坝堡,与文献记载的起止点名称相符。
2.长度上,此段壕堑全长39.6千米,与文献记载的长“八十余里”基本吻合。
3.此段长城为壕堑,与文献中记载的壕堑性质相符。
4.现存壕堑周围以戈壁为主,易受风沙淤埋影响,与文献记载这段壕堑建成一月左右即被风沙淤埋的情况相符。
5.新发现的壕堑未修筑墙体,建造较为简单。文献记载此段全长八十里的长城,“役屯丁万人,费内帑万金”“踰六月而成之”。而对比其稍后9年建成的赤木关,城墙合计不及5千米(关隘、敌台、烽火台等不计),还得“督军夫四千”,历时三月,“共费金四万两”,尽管其有地势险要,水、土等资源不便等方面的因素,但两者对比还是可以看出西关门修建得简易、省工、省钱。
综上所述,长城调查中新发现的黄羊滩壕堑可能是《嘉靖宁夏新志》中记载的“边防西关门”。另外,《嘉靖宁夏新志》中将这道长城的地位抬高到宁夏镇城之西面关门的位置,但不见于以后文献。主要是因为此道壕堑建成月余便被风沙淤埋,失去防御功能;其次,此道防线途经山前平羌、杨显、邵刚、大坝等屯堡的屯田区,在明政府将西侧防线移至山前之后,沿线已无须营造防御工事;最后,此道长城属典型的当权阶层不遵从客观规律而劳民修建的失败案例。
[1](清)张廷玉等撰,郑天挺等点校:《明史·兵志三》,卷九十一,中华书局,1997年。
[2][3](明)胡汝砺编,(明)管律重修:《嘉靖宁夏新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
[4]钟侃:《宁夏古代文物》,宁夏人民出版社,1980年。
[5]许成、牛达生:《宁夏境内明代长城遗迹》,《宁夏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
[6]许成:《宁夏古长城》,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7]许成、牛达生:《贺兰山文物古迹考察与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
[8]青铜峡军事志编纂委员会:《青铜峡军事志》,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
[9]景爱:《中国长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10]鲁人勇、吴忠礼、徐庄:《宁夏历史地理考》,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11](明)崔景荣、杨应聘主修,(明)杨寿编纂:《万历朔方新志》,影印本。
[12]当然大坝堡亦非没有戍边义务,《万历朔方新志》载南路游击分守边城中“又分山隘八十三里,自西长城哨马营墩起,至打硙里口止,内大坝堡守备分边三十五里”。
[13]城西南墙明代史籍记载较多,较早如《弘治宁夏新志》所载“自双山南起,至广武界止,长一百余里”,其修筑于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由巡抚都御史贾俊奏请修筑,只是到嘉靖年间已“圮坏不堪”了。其址可能在今北起青铜峡邵刚镇以西的大柳木皋山脚下两道长城交会处,南端可能至中宁县渠口农场西北的南湖子沟口,合计长度约46千米。
[14]壕堑也是一种重要的长城类型,一般是独立于墙体之外,自成一体,是当时建造者根据具体地势所修筑的、长城墙体之外的另一道补充防线。它一般是在平坦低洼、便于凿挖之处直接下挖出一道连续的深壕,然后将壕内掏挖出的沙土等堆积于戍守的一侧而成堑。堑不经夯打加固等,整体成土垄状。
(作者单位 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责任编辑 赵建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