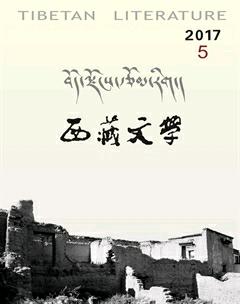“西藏文学”的坚守与突围
王本朝
感谢《西藏文学》的盛情,感谢刊物主编次仁罗布和四川大学《阿来研究》主编陈思广教授,给我近距离接触西藏文化和体验文学生活的机会。我主要想谈两点看法,一是西藏文学的坚守,主要是谈《西藏文学》及“西藏文学”对新时期文学特别是先锋文学的贡献;二是西藏文学的突围,谈文学体验和文学思想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
无论作为杂志的《西藏文学》还是当代的西藏文学都有自己的特色和贡献,就拿1980年代的先锋文学来说,它参与甚至可说是引领了先锋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大家熟悉的扎西达娃、马原、色波等相继推出了系列作品,如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西藏,隐秘岁月》《风马之耀》《世纪之邀》等,马原以先锋姿态在小说的叙事探索方面独领风骚,发表了《拉萨河女神》《冈底斯的诱惑》等小说;色波的《竹笛、啜泣和梦》《从这里上船》《圆形日子》等也有自己的特色;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还获得过1985-1986年度优秀短篇小说奖。西藏作家群体开始被全国所关注和推崇。可以说,《西藏文学》对西藏乃至全国先锋文学的发生、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西藏文学》1984年第4期发表马原中篇小说《叠纸鹤的三种方法》,第8期发表了马原的《拉萨河女神》,第9期刊发了色波的《竹笛、啜泣和梦》,1985年第1期头条刊发了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1985年第6期还设置了魔幻小说特輯,推出扎西达娃的《西藏,隐秘岁月》,色波的《幻鸣》,刘伟的《没有油彩的画布》,金志国的《水绿色衣袖》和李启达的《巴戈的传说》共5篇魔幻小说。编辑在“编者按”——《换个角度看看,换个写法试试——本期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编后》中认为“从拉丁美洲的‘爆炸文学——魔幻现实主义中悟出了一点点什么”,但强调他们的本土性追求,“所谓魔幻,看来光怪陆离不可思议,实则非魔非幻合情合理”,它“不是故弄玄虚,不是对拉美亦步亦趋。魔幻只是西藏的魔幻。有时代感,更有滞重的永恒感”。他们借鉴写作方法,但“魔幻”本身来自西藏自己的日常生活。可以说,1984—1987年的《西藏文学》是新时期先锋文学的重镇,已进入了文学史,并成为文学史事件,值得认真总结和研究。我也在搜集资料,阅读作品,准备撰写“《西藏文学》与新时期先锋文学的发生”,到时请大家多批评指正。
今年是《西藏文学》创刊40年,现在回过头来盘存、打望《西藏文学》和西藏文学的贡献和影响,有几点是值得重视和思考的。一是西藏文学不仅仅是西藏的地域或区域文学,它与世界文学和全国文学都有紧密联系,曾经还是潮流的引导者或参与者。二是西藏文学有自己的特色和身份,这个身份是什么呢?在我看来,也与它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有关,或者说是它们参与创造的产物,如它的宗教性、神秘感、人性情怀和故事性等等,都拥有区别于其他区域文学的精神特质和审美品格。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坚守传统,突破传统以及继续创新发展。
那么,我接着就谈第二个问题,也就是如何突破的问题。刚刚听次仁罗布介绍西藏文学特别是小说创作的一个特点就是故事讲得好,也就是会讲故事,善于讲故事。但又存在一个不足或者是弱点,那就是故事背后没有思想。文学要有思想的支撑,一般讲文学创作有三个问题,即写什么,如何写和写得怎么样?文学思想并非以理论观念存在于文学世界,而是渗透在文学体验里面。写什么要有思想,如何写也要有思想,写得怎么样更要有思想。怎样去获得思想呢?在我看来,需要体验和思考,或者说是“生活”和“阅读”。这也算是老生常谈。先说体验吧。“体验”即将主体生命沉入当下现实生活去感受、体会和琢磨。作为有生命的个体生活着,但不一定有生命体验,正如活了80、90岁的老人,他的生命很长但不一定就有很深切的生命意识。有的作家生命虽短暂,但对生命的体验和感受却非常深刻而独特,如现代作家中的萧红,当代作家中王小波。萧红只活了32岁,但她对孤独与荒凉的感受和体验超出了许多作家,形成了她自己的人生哲学,也成就了她的经典名作《呼兰河传》。王小波也一样,他们那一代人都有过知青生活,梁晓声以写知青题材见长,但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也写知青,他就是不一样。不同体验就会有不同的思想,会有不同的创作力度和思想深度。梁晓声写出来的知青生活是崇高的,王小波却是荒诞的。哪一个更有人生体验,更有文学的思想呢?这应该是一个不用讨论就能知道答案的问题。体验是反观念,反概念的,特别反预设逻辑。在逻辑上讲得通的问题并不一定就是生活本身,更不能等同于生命体验。文学体验要以独特、丰富和深切为目标。
再就是,文学思想的获得还需要阅读作支撑,要将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和文学经典都纳入阅读范围。人的经验是有限的,再丰富的人生经验也有耗费殆尽的时候。怎么办呢?只有通过阅读开阔人的视野,丰富人生经验,提升思维境界。搞创作的人,不读书不行,读少了也不行,要知道你身边的事,更要知道前人的思想、他人的想法。别人说了什么,写了什么,你还有什么可写的?这些只有在阅读中才能完成。一个想当作家的人,只关在家里不行,他和社会现实脱节了,如果只在现实里泡着,没有思考和思想,没有阅读,也不行,他就只能写看得见的那点东西,没法写出心里感受到又经脑子思考过的东西。写作是一场对话,作者要与写作对象发生对话,也要与同类题材、同样写法的其他作家对话,参与对话的人数越多,写出来的作品才经得住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考验。如果一个人想写就写,有了创作冲动和兴趣,是可以写的,到了一定时候,就要停下来琢磨这样一路写下来,写得怎么样呢?就需要有思想的支撑,需要通过大量阅读和思考去建立写作的参照系。不然,会自我重复,或在一条低水平线运动,没有大的造化和出路。
思考和思想是文学的力量。有故事的作品可以吸引人,有了思想的作品才能长期吸引人。这次《西藏文学》“特刊”编辑出版40年来刊物发表的代表作,其中次仁罗布的短篇小说《杀手》,我以前没有看,这次利用机会认真拜读,很有意思。它是一篇有故事能吸引人,也有思想深度的小说。它讲述了一个想复仇后又放弃的故事。康巴男子将仇恨藏在心里,想尽办法寻找杀父凶手,后来找到凶手。当看到凶手年幼的儿子和善良的妻子,还了解到了凶手为自己的犯罪已感受到了内心的煎熬和折磨,并且,他已变得身体弯曲、头发花白、满脸皱纹。于是凶手哭着悄悄地离开了。复仇成了心灵的救赎,显示了人性的仁慈与温暖。这里有次仁罗布的宗教情怀,也有他的思想和认知。有了思想的作者就会走上一条有文学深度广度的路,并且会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当然,思想和体验是相互统一的。体验是思想的足迹,思想是体验的眼睛。它们可以相互发现,相互促进,相互激活。体验是个人化的,复杂的,也是逐渐深入的。我曾经经历过一件事,在此聊可一说。我从小生活在乡下,后考上大学留在城市工作,深感父母的辛苦劳累,将她接到城里来生活,后来发现她并不适应城市生活,在与周边环境交流的时候,也有语言和经验上的障碍,于是,只好呆在家里,等年青人下班回来,或是一个人守着电视,久而久之,人就有些犯傻,变得寡言少语,对事物的反应也大不如从前。我想,人如一棵树,他应有他的生存土壤,有他所熟悉的生活环境,如人为地去迁移它,也是会出问题的。当然人虽没有植物那般娇嫩和稳固,不能随意处置和离开故土。人如一条鱼要在水里生活,人也要与土地在一起,特别是几十年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人,需要与炊烟、水井、方言在一起。我想还是应该把父母送回到她的乡下去。于是在征得她同意后,将她送回乡下去,谁知乡村已不是记忆中的乡村,年青人全都外出打工,留下的全是老弱病残,万一生个什么病,或遇见什么意外,邻里根本没有人,全是荒芜的土地,尽是比庄稼还要茂盛的杂草,成了野兔、野猪出没的世界。听说即将还要被开发,原住民需全部迁移到城镇上去。故乡成了异乡,熟悉变为陌生,人还是那个人,环境呢?没有了,还不跟城里一样!有的条件还没有大城市好。我问父母该怎么办呢?回城里去,还是留下来慢慢熟悉曾经非常熟悉的地方。她们茫然,没有回答。这件事对我冲击特别大,它不仅仅是经验上的,还是思想上,契合了我对现代化和后现代的体认和思考,特别是对“人与故乡”关系的感受。现代化就是将熟悉转变为陌生的过程,后现代再将陌生的变成碎片的事物。经社会这么一折腾、翻滚,人就生活在一个陌生而碎片化的世界里。
我的文学经验严重缺乏,不值一提,更多的还是阅读经验。在此,我再次附和次仁罗布的说法。文学写作只会讲故事,它成功了一半,还要能讲出有意味,有深度的故事。我的发言就此打住,耽误了大家时间。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邵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