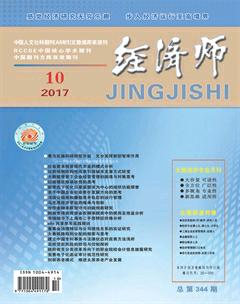哲学与传统的联姻
李文生
摘 要:中国古代的先哲和文人们早在几千年前便对语言表意的局限性和不完整性有了系统的认识,因而先提出了以“言不尽意”、“意在言外”为核心的“言意观”,文章对此进行了分析探讨。
关键词:哲学 传统 联姻 “言意观” 原因
中图分类号:F270;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7)10-237-02
一、“天人合一”的哲学背景
“言意观”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决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它有着深层的哲学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的民族精神。钱冠连先生认为:“为什么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以全息论的解释就是,一个民族怎么说话,怎么使用语言就是那个民族的精神生成的一种方式,这里,物质的语言与人的精神是同质同构的”。{1}因此,中国的文学独特的“言意观”也必然与我们的民族精神水乳交融的。那么我们与此相关的民族精神到底是什么呢?
冯友兰认为:“圣人的最高成就就是个人与宇宙的同一”,“他要做的事就是修养自已,连续地、一贯地保持无私无我的纯粹经验,使他与宇宙合一。”{2}这种与宇宙同一的“圣人”追求,便是引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哲学至高精神:天人合一。
中华民族发源于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黄河流域,人们始终在与大自然带来的各种灾难相抗争。在与自然博弈的过程中,人们终于认识到个人力量的薄弱渺小,自然的伟大而神奇。因此,自然是不可战胜的,唯一的选择便是学会顺应自然,遵循自然规律,最终与自然和谐共处。所以,认识到这一点之后,人们便习惯于了解自然,感知其变化规律。倾听感受大自然的脉搏,努力地去感受神圣的“天意”,虔诚地希望能与“天意”最直接地沟通。
老庄哲学正是以“自然”作为最高的哲学追求,而自然中无处不在的“道”便成了至尊主宰,宇宙间万物的自然状态便是不可逾越的“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与此同时,“道之为物,惟恍惟惚”(《老子·二十一章》)。“道”又似乎是无形的,难以捉摸的,是万事万物的存在状态,是自然生成的。因而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道家的这种对“道”的绝对敬畏就顺理成章地派生出他们的“自然无为”“顺其自然”等等哲学主张。
在“道”面前,最好的选择便是少说话,多感悟,多去体会。
道是万物自然发生的源头,道并不是某种实体,而是关于万物总体或者整体的实在性的那种状态。道是超越时空的,因而也就不能为我们的感觉器官所感知和为我们的理性所认识。具有超越理性的思维性质,只能被体悟。因此,道是不可言说的。换句话说,用语言来描述的道不是自然的道,自然的道是不要用语言来把握的。真要用语言表达,也只能勉强为之。作为中国哲学思想的两大主流體系的道家和儒家,尽管在很多领域“政见不和”,但对语言局限性的认识上却似乎有一种神秘的默契。
《周易·系辞》中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可不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意。”这段描述与道家的“得意忘言”,“得象忘意”之说真的是不谋而合;孔子心目中的圣人也便是道家的“天道”。无论是道家还是儒家,都不约而同地认识到语言的局限性。“道”和“圣人之意”都是自然存在而难以名状的,在语言之外还存在很多未知的世界。有限的语言在无限的真理面前是渺小而无助的。因而,庄子主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庄子·天道》)。世界的本真,是不要言说的,真知是无言的,天地万物与我是不可分的整体,正所谓“天人合一”。
同样地,作为中国主流哲学的另一个重要分支——佛教,也参与到“言意观”的讨论,并给予道家、儒家的极大的支持。
佛教进入中国之后,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一方面将佛教的“真如”直接诉诸于当下的“人心”、“人性”,并与儒家的“心性”的主张相融合;另一方面是在“言不尽意”论和“得意忘言”论的影响下,采取了拒斥一切语言文字的直觉修行方法。主张“言语道断”“以不二之悟,符不分之理“;宣称“反本成性”,“得本自然”,认为“本”是无形之象,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因而提倡“言外之意”,力求自身的“顿悟”。
佛教的“直觉顿悟”说从另一方面有力地策应了在“天人合一”的大背景下中国古代哲学所倡导的“言意观”。
葛兆光认为:“宇宙是相互关联的一个整体,“天”、“地”与“人”之间有一种深刻而神秘的互动关系,不仅天文学意义上的“天”与地理学意义上的“地”及生理学意义上的“人”,乃至政治学意义上也互相贯通,在现象上互相彰显,在事实上彼此感应”。{3}
“天作为命定、主宰义和作为自然义的双层含义始终存在。在古代,两者更是混在一起没有区分。从而在中国,“天”与“人”的关系实际上具有某种不确定的模糊性质,既不像人格神的绝对主宰,也不像对自然的征服改造。所以,“天”既不必是“人”匍匐顶礼的神圣上帝,也不会是“人”征伐改造的并峙对象。从而“天人合一”,便包含着人对自然的能动、适应、遵循;也意味着人对主宰、命定的被动地顺从崇拜。{4}
因此,“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和宇宙观对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也从根本上塑造了中国人“稀言自然”、“与道为一”的“言不尽意”、“意在言外”的语言观。
二、“诗言志”的创作传统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在中国文学史最早而最有代表性的文体,毫无疑问,也是诗歌。
在中国古代,无论是皇亲贵族、文人墨客,还是戍守边疆的将士,屯耕桑田的农夫,都会有即兴赋诗的冲动和愿望,就连那些流落于青楼的女子,也以能够赋诗作对而引以自豪。可以说,对诗歌的热爱和推崇充斥着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和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孔子更是把诗歌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他自己亲手编选了引领中国诗歌风气之先的《诗三百》,认为“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在儒家看来,诗是实现“仁”的最终途径,也是社会和谐的根本保障。endprint
对于诗的文学和社会功能,《尚书》里有着更为清晰的阐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在这里就诞生了我国古代文论一个悠久而深远的命题:诗言志。
“诗言志”就是通过“诗”来表达个人的“志”也即某种思想、欲望、社会形态、政治理念等。可见,这里的“志”所包含的内容是极为丰富的。用现代语言学的符号学来解释的话,“诗”即为符号(言),而“志”则为符号(意)。所有“诗言志”的命题实际上也是“言意关系”的问题。
“志”是一个意义复杂的范畴,是人对人与世界关系的全面认知以及对理想社会和人生的建构和塑造。“志”既浓缩了诗人的哲学思想也包含了个人的社会抱负,它的内涵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
这个“志”,也即儒家极力弘扬的“仁”,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自身修养和社会理想,也是“以天下为己任”继而“匡时救世”的“匹夫之责”;也是除恶扬善“救民于水火”的博爱之心;是懂礼守法,的终极伦理标准。
然而,理想是美好的,现实却又是残酷的。很多人在实行“志”的过程中,经常屡遭挫折,四处碰壁,郁郁而不得志。
因此,此时的“志”又返朴归真为自然无为之“道”。
在社会艰险、危机四伏之时,何不退隐闲居、以求自我解脱?在屡试不第,前途渺茫的关口,为何不能一笑而过,留连于青山绿水之间,物我两忘呢……
当然,这种“志”也可以是在经过人生的颠沛流离,酸甜苦辣之后,因而看破红尘的一种“四大皆空”的“顿悟”。
由此可看,“志”是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所指”,它“见仁见智”,随着时代的更迭、个人境况的变动而发生变化。是流动的、飘忽的、无限的。
与“志”相反的是,“诗”是一种言,是一个表达的工具,它的服务功能受很多因素(语言、语法、格律)的制约,因而是有很多的限定性。
要用这有限的“诗”(言)去表达无限的“志”(意),何其难也?
因而,此时的“言不尽意”便是一种必然的结局,是一种“无言”的尴尬。
另外,我们回头再来重读一下那段话“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孔子一方面倡导要“诗言志”,用词语表达心志,但另一方面却又要用“歌”、“声”、“律”的音乐元素来加强诗的效果,以此来达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的至臻化境。可见孔子似乎很早便意识到语言自身表达的局限性和不完整性,所以他和其他文人一样把音乐看作是诗歌语言表达个人情感的不可或缺的帮助。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他老人家“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感叹。《毛诗序》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因而,光有“诗”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把它放在“诗—舞—乐”三者合一的艺术形式统一体中,才能比较充分地实现“言志”的目的。
可见,“诗言志”的文学传统不仅使人们认识到语言的局限性,也迫使他們在现实生活中寻求其他手段来弥补“言不尽意”所造成的缺憾。
注释:
{1}钱冠连.语言全息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53
{2}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6.9
{3}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154
{4}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记[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332
(作者单位:广州番禹职业技术学院外语外贸学院 广东广州 510000)
(责编:若佳)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