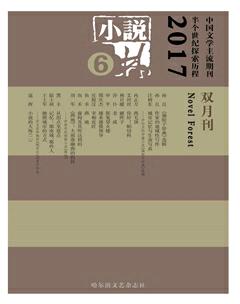老成
秋天了,村口那棵老榆树病了似的,被风吸干汁液的叶子瑟瑟地响着。树影淡淡地落在地面上。树下聚集了许多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大帮。鱼子站在人群里,手里拿着一根很粗的棕绳。他矮矮的个,干瘦的小脸上眨着月牙儿形的小眼睛。那双眼睛很阴沉,即使乐的时候,也只是嘴角一咧,眼睛不漏一丝笑纹。村民老成穿着白色夹衫,汗涔涔地走到他跟前说:“鱼子,八百五行吧?”
“八百五?没有这个价!就说牛肉卖八元五一斤,去了盘缠路费,满打满算我能剩几个钱?真是,还有这样的买卖!”鱼子的腮帮很瘦,皮贴着骨。他说话时嘴一张,整个脸的下部都在动。
老成的脸被太阳嗮得黝黑,张着嘴,嗫嚅着说:“这还不如让它死到手里,到集上去卖肉。”
“卖肉?死牛肉拿到集上,三元五一斤都烧高香,叫你白赔三百。”鱼子叼着烟,不愿理老成的样子。
老成的心很郁闷。眼下庄稼已割倒了,正急着用牲口呢,偏偏节骨眼上,牛病得不行了。前天傍晚日落的时候,他赶着牛车载着高粱从山坡上回来。中午牛就就没吃草,拉起车来十分吃力。当走到村东高岗时,无论怎样挥动鞭子,牛使尽力气,也拉不上去了。他不得不回村借了一头牲口,将高粱拉了回来。晚上牛只喝了一点水就倒下了。昨晌,他从镇上的兽医院将牛牵回来,兽医告诉他这牛已治不好了。昨晚他没吃饭,终夜吸烟。早上起来,他的两眼已如两只熟了的山桃。不光因牛死了糟钱而伤心,他宁肯让它死到手里也不愿将它送给那些牛贩子。可说归说,一头牛死了卖肉至多出五百块。人家鱼子常年跑城里,把牲口杀了拉到省城,新鲜牛肉少说八块一斤。
将牛卖给鱼子,他们就可多得三百块。三百块钱,秋后需卖两袋子包米才能换来呵。几袋子包米要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流多少汗珠子?他不忍心将牛卖给牛贩子,可那是三百块钱呢!
儿子小成二十六七了,在农村,是大龄青年了。秋后好孬也得给老实巴交的孩子成个家。牲口一死,得雇别人家的牛去拉庄稼;牛死了,再买新牛,还花钱。自己老了,重活干不得,全靠儿子小成,这孩子脑子笨,只会苦做。
“八百块,多一个子儿不要!”鱼子的小眼睛眯着,眉梢向上挑。老成低着头不吭声。五十块,就差这五十块吗?念它辛辛苦苦为家里卖的力,也不该再从它身上多刮这几个钱了。“那就给你吧!”老成咬着牙,眼睛里渗着泪。
村里一有热闹,村民便聚堆。哪怕两口子打仗,也会聚来一帮人。何况今天都来看鱼子在这里杀牛呢!
天气并不热,鱼子却脱下小褂,露出肋骨上的条条青筋。他得意洋洋地说:“黑娃,叫你妈做饭,今晚上烀牛头儿,喝酒。”黑娃七岁,是村头寡妇金玲子的小儿子。金玲子二十八,男人前年翻车砸死在田里,守着寡。鱼子这几年跑外,钱来得冲,出得阔气。虽有妻儿,却经常晚上带领一帮男人到金玲子的小屋去喝酒、打牌。喝得晕晕乎乎时,便醉卧在那热乎乎的炕头上。
黑娃跑去不一会儿,就见金玲子系着个花围裙从人群后走出来。她也斜着鱼子娇嗔地说:“呵,你小子不要命了,啥钱都挣,这么大牲口是你杀得的吗?”
“娘们见识,挣钱哪有容易事?邻村张屠户杀一头牛,开口就要一百元!他娘的,一头病牛,好杀,这一百元,自己赚!”鱼子对着金玲子笑,嘴角却木木的。
鱼子是村里的大能人,金玲子并不掩饰自己与鱼子的暧昧关系。她用余光扫视周围的人,嘴一咧,笑嘻嘻地三步并成二步走到鱼子身边说:“你小子想喝酒,快掏钱!”鱼子从口袋里拽出几张票子递给拎着酒瓶子站在旁边的黑娃。
鱼子冲着光棍王大嘴子说:“大嘴子,你弄张桌子来,杀完牛,牛皮归你。”王大嘴子的嘴都合不拢了,跑跑腿儿,就白落一张牛皮,立刻大步流星地离开了。
老成回到家里,从水缸里舀些水,又放些豆饼末进去。然后把桶送到那头趴在槽边的黄牛嘴边。它似乎睡着,却睁着两眼。老成用木棍碰了一下牛的脊梁,牛抬一抬头,仍没有动。老成拽了拽它的尾巴,它才费了好大力气站起来,用嘴拱拱桶内的干草末,没有吃。
它慢慢地随着老成向院外走,不时地低下头,嗅着院墙根的枯草。走到车子旁,习惯地停下了步子。以为还要拉车。老成拉过它,慢慢地向院外走去。
老成左腋夹着把镰刀,走在牛的后面。他的脸刻着深深的皱纹,满头的银发被秋风吹着,心格外的凉。他家祖祖辈辈种田,自己赶了一辈子牲口。小时候给地主放牛,成年时给队里赶牛车。后来田分给各家种,种地不养牲口,得雇人家的牛具,到秋后得还人家牛具钱。他走了三天,到一百多里地的畜牧场买回了这头老黄牛。虽是母牛,但劲大出奇。别的牛两头拉一辆车很费力,它自己拉一辆。它下了好多犊,长大卖了钱,老成给老伴治好了老寒腿,又重新修了房子。为了这个家它几乎流尽了最后的一滴血和汗。
老榆树下放了一张长桌,桌上堆着包米秸子一样粗的棕绳。一把闪亮的刀在秋阳下反着光。桌子旁边的地上放着一把镐和几根铁棍。秋风瑟瑟,鱼子的脸被风吹得更加阴沉,像那没有表情的天空。“怎么才牵来?”鱼子对着慢慢走在牛后面的老成,颇有几分不满。
“闪开,闪开!”王大嘴子忙得周身是汗了。人群自然闪开一条道,老成把黄牛牵到树荫下。
牛抬起头,望了望周围那一双双注视的眼睛,又低下了头,嗅嗅路边的草,舌头伸一下,仍没有吃。
魚子忙勒过缰绳说:“不能叫它吃草,一会儿不好洗肠子!”鱼子将它拉到树根下,牛以为要把它拴在那里,顺从地把头向树根靠了靠。“给我捆!”王大嘴子拿过棕绳,向旁边几个帮忙的人喊。
“慢着,娘的,懂个蛋!这样能捆住吗?”鱼子叫喊着。王大嘴子明白了鱼子的意思,忙到桌旁操起那根胳膊粗的铁棍,向牛的头部打去。牛正低着头,猛遭一击抬起头。一个满脸横肉的汉子又操起那把刨粪用的大镐,向牛的头部猛抡。
牛似乎明白了什么,向后退,发出“嗷嗷……嗷嗷……”祈求的哀叫。叫声在秋风中飘散,使人感到风格外的凄清。当它再抬起头,眼眶内已淌下了两行液体。“都是废物,像个娘们似的,看我的!”鱼子火了,抢过大镐,向牛的头部猛击。一镐正打在牛的眼部,血立即涌出来,眼珠冒在外面。它终于被绳索绊倒了。几个人忙拿棕绳捆它的腿。忽然它猛力一踢,又站起来,带着那个眼珠小血球绕着树根转圈跑。围观的人顿时吓出老远。
鱼子又操起闪亮的刀,向牛的颈部猛扎。刀扎得很深,再用尽全身的力向外一挑,牛的喉管便发出被刀割断的声响,像夏日吃西瓜,用刀开西瓜皮儿。
当鱼子的刀抽出来时,它的颈部喷出一股血,喷得很远,染红了鱼子的裤脚和鞋帮。它的喉管里微弱地响几声,便听不见动静了,只有风从耳边凉丝丝地刮过。
气喘吁吁的鱼子看牛不动了,把刀扔在长桌上,用袖子揩着满头的汗。几个人还在按着牛,鱼子喊:“废物,还他妈按着干吗!”他坐在树下的石头上,用血乎乎的手从口袋里掏出烟,点上后吧嗒吧嗒地抽着。
老成没有在现场。他不忍看着牛被人宰杀。
可是,当他看到儿子小成眼泪汪汪地回到家里,讲了鱼子杀牛的经过后,没等儿子讲完,他像雄狮一样暴怒地跳了起来,扬起胳膊怒吼道:“别说啦!”
张开的巴掌没有落到儿子小成脸上,而是怔了一下后,狠狠地打在了自己脸上。
当晚,金玲子家的屋内笑语喧哗。鱼子嗓门最大,几个帮忙的也都在猜拳行令。
“咳!鱼子,你小子这次又赚了一大笔,肉拿到城里卖了,少说五元五一斤,你至少剩三百。”“嘿!大嘴子,你别抱屈。一张牛皮拿到县城还不得卖个百八十块!这钱不能全落你腰包,得给我买两瓶好酒!”鱼子的笑声在静夜里很豁亮。
突然,门被人一脚踹开,老成闯了进来。
老成两眼红红的,浑身散发着酒气,怒视着鱼子。
“你,你,你要干什么?”看到一向老实巴交滴酒不沾的老成杀气腾腾的双眼,杀牛不眨眼的鱼子未免陡生几分恐惧。
“有你这么杀牛的么?你不是人!”老成上前一步,一把将饭桌掀了个底朝上。
作者简介:莎仆,原名刘凤国,男,1965年出生,现供职于哈尔滨铁路公安局。全国公安文学艺术联合会会员,《中国诗歌网》认证诗人。1989年开始在刊物发表小说、诗歌、随笔、文学评论。著有文学随笔集《凤言锋语》。有诗歌和散文分别入选《中国当代优秀诗人诗选》和《中国当代作家优秀散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