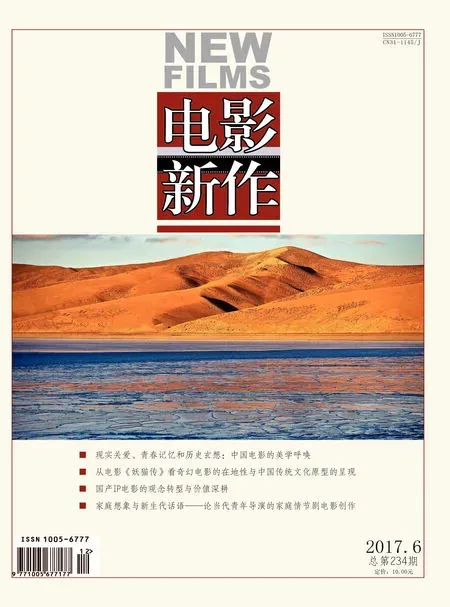无法模仿的绘画:戈达尔《受难记》中的艺术史观
韩晓强
让·吕克·戈达尔是迄今为止争议最多的导演之一,作为一个不断颠覆电影语言的反叛者,他的电影可以被看做一系列“哲学实验”。①而这些实验的目的,就在于寻找“电影的极限”,它可以是表达的极限,也可以是经验的极限,可以是词与物的极限,也可以是视力和听力的极限,还可以是历史的极限。②探测电影的极限,意味着我们需要从两个维度敞开,如果把电影看做一种媒介,那么这个问题就要放在技术史/媒介史中考察;如果把电影看做一种艺术,那么这个问题就要从艺术史中去寻找。③
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考察电影和其他艺术之间的差异与联系,也就是电影与绘画、音乐、雕塑、舞蹈、戏剧、电子游戏之间的一种不可化约性。在这些艺术门类之中,绘画(尤其是中世纪开始的油画)无疑占据了西方再现艺术历史中的核心地位,这令绘画/电影之间的关系成为研究古典/现代、人工/机械这些辩证话题的重点所在。戈达尔在索邦大学曾修习人类学、艺术史、音乐史等专业,这令他在探索电影和其他艺术时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④他拍摄于1982年的《受难记》,正是在探讨绘画之于电影的不可化约性这个层面上表达了自己的艺术史观。
一、理想的光线
《受难记》使用元电影(Meta-cinema)的结构,讲述了波兰电影导演Jerzi在一个工厂改造的摄影棚内拍摄一部名为《激情》⑤的作品,他希望能捕捉到一种“前所未见的真实”,并将其转化为极富吸引力的影像。在此吸引他的是如何将过往的那些绘画杰作——来自德拉克洛瓦、戈雅、伦勃朗的名画⑥进行电影化重构。也就是把这些美术作品转化成“活体绘画”(tableaux vivants)⑦,并一一置入他的电影中。他以一种绝对奉献的精神,不断试图对那些伟大作品进行重建,试图去还原每一个无穷小的细节。在这个过程中,各种琐碎的事情不断干扰他的创作,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来自周边设备——现实中的灯光以及演员的身体状态:他期待的那种灯光效果始终无法实现;与此同时演员们的身体无法完全适应他的要求——他们的姿态和手势总会有一些小缺陷。所有这一切让他的狂热努力成为徒劳,这种困难显而易见,这部电影也最终被遗弃了。
这就是戈达尔《受难记》所讲述的故事,它映射了当代艺术尤其是电影艺术的一种状态:一种美学探索中的冥顽不灵,一种对濒危遗产的缅怀之情,一种对精确表达无法企及的沮丧。⑧
这里至少有三个原因决定了电影对绘画模仿之不可能:第一个原因是现实的不可约束性,物质世界处于不停的变动之中,即使它能在某一刻被悬置,也终将复归运动。影片中的画外音揭示了这一点:“这不是一个谎言,那些想象的东西永远无法成真,也不会成为绝对的虚假……它无论如何都被外部的现实所隔离,被一种近似的计算所隔离。”即使导演舍弃一切投入到艺术创作的巨大激情之中,他仍然无法掌控他周围的一切,无法决定这部电影将会拍成什么样子。第二个原因是影像的机制问题,如果这部《激情》的任务在于通过关联和参比古典再现艺术而寻找电影专属的根本要素,他必须重新去理解那些传统艺术的物料和灵感。这导致了一个结果:电影无法重塑那些事物。电影是一种二级再现,这意味着导演需要按照画家的原始倾向对拍摄对象以及演员的身体、姿态进行调整,它提供的是一个“副本的副本”。在这里演员的身体并不是一个可以合规则的排列组合,而是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导演即使进行一万次重复,也不可能达到完美的复制。第三个原因则是更重要的,也就是现实的“光”,它构成了一种跨艺术的基础秩序。“摄影机始终仅仅是光的见证者,这也是我羡慕绘画的地方,因为画家可以自己创造光线。”影片中的导演Jerzi在此成为戈达尔的代言人,这也是他为何要致力于重构那些伟大的绘画杰作:因为他羡慕画家们总能得到他们理想的光。
“光”在这里同时具备了现实性和隐喻性的一面,对于电影来说,种类繁多的设备并不能带来理想的灯光。无论电影作者如何去复制绘画,总会有一些元素——明暗对比构图、背景的颜色、身体的反射光会偏离预设。对电影创作者来说,没有所谓“正确的光”,他们所拥有的只是一种真实而具体的光——这是一种无法被驯服的光线,因为它始终是一种现实因素,电影在此遭遇了自身的极限。
17世纪由伦勃朗开启的布光法把点光源、明暗对比和透视确立为绘画的规则,电影在发明后学习并继承了这种规则,然而在《受难记》中,摄影机无法复制伦勃朗的《夜巡》证明了这种规则的不可逆性。然而绘画则完全可以复制绘画,在古典时期的欧洲画室,一个画家通常会将一幅画绘制多幅,部分甚至由学徒或助手临摹完成,这些画作均可被视为原作。在画室之外,私人临摹出的赝品,也常常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⑨
画家拥有“创造光线”的权利,也就等于拥有了艺术创作中的上帝权威(“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圣经·创世纪》1-3),这里指向的是作为“万物之源”的太阳。但在绝大对数作品中,画家都不愿意让太阳出现在画面上,而是通过高光、暗影和投影的处理达到某种可靠的“真实感”。⑩同样作为再现艺术的电影则受制于光线,只能捕捉和利用现实的(包括人造的)光线。这种差别,就是电影和绘画中最本质的差异,也就是意大利美学家马里奥·佩尼欧拉所提出的不同门类艺术间的“不可化约性”。这种不可化约之物成为一种“余项”(remainder),被存放在该类艺术历史的“墓冢”(crypt)之中,它代表着这种艺术独一无二的特征。佩尼欧拉将这种“余项”比拟为“影子”(ombra),这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表述,意味着它是艺术可以召唤的“幽灵”,正是在这种解读上,佩尼欧拉将之等同于本雅明的“光晕”(aura)。
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所区分的“展览价值”和“膜拜价值”分别对照着复制品和原作,但在佩尼欧拉看来,后者存在的基础正是那种不可化约的“余项”。在此,绘画对于电影的最鲜明的“余项”,也许就是可以由画家自由操纵的光——这不仅是电影艺术难以具备的,也是其他类型的艺术难以具备的,或许文学可以某种形式实现,但文学作为一种非具象、非再现、非造型的艺术,于此并没有严格意义的可参比性。
二、图像V S影像
关于电影和绘画的理论,安德烈·巴赞在早年已经作出了诸多贡献,他聚焦于影片的景框如何突破传统的画框并获得一种开放意义。在巴赞之后,人们普遍将运动视为电影和绘画的一种本质区分,然而电影运动是每秒24格的画幅造就的,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将电影的截图视为一幅幅单独的图像呢?在巴赞去世后的1970年,罗兰·巴特在《电影手册》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第三意义》(Le Troisième sens)的文章,依靠对爱森斯坦电影的几幅截图的研究,罗兰·巴特区分了三个意义层面:信息层面、象征层面以及意指层面(即“第三意义”),在这个基础上他又把后两个意义层定义为“显义”和“钝义”。这篇文章一经发表,立刻招来苏联电影理论家科兹洛夫的批评,科兹洛夫认为罗兰·巴特的结论是建立在未经检验的、从电影理论角度看是完全臆造的基础上的,也就是“以具有不同本源和本质的各种涵义效应随意拼凑的结合体”。
科兹洛夫和罗兰·巴特的不同见解来自于电影可否采用“截图分析”这一事实。就这个问题而言,大多数电影史学家和理论学家都站在科兹洛夫的立场,毕竟去讨论一个电影镜头就好像它是一个孤立的图像(可与油画、素描和版画相比较),不是一种能被普遍接受的研究方法。电影本身的机制决定了它怎样“显现”和“遮蔽”事物,我们在观影活动中不可能像凝视一张图像那样解读出诸多“潜在”意义(就像罗兰·巴特所做的那样),因为影像总是转瞬即逝。倘若电影要展示某些特定的细节,它可以提供一种自主的“放大效果”(amplification),如慢放、停格、推焦、大特写等等。阿兰·马松(Alain Masson)指出,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习惯将注意力集中到不同的叙述单位,如人物、车辆、人群、时间、地点……而不是一个矩形图像。这也意味着帮助我们解读潜在意义的是基于电影机制的一种“显现”,而非人为地“截图分析”,这就是电影的“游戏规则”。罗兰·巴特对电影截图分析的武断认识,来自于他在电影机制研究方面的匮乏,这也成为哲学家谈电影的一种普遍局限。
截图/剧照是从电影中截取的图片,它是流动影像中的一个截面,但是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个画面并非是静止的,它可以向前或向后绵延。正如对一条河流抽刀断水,不能阻止它的流动,这属于我们看待电影的一种特有的知觉和经验,即“电影经验”。电影的图像需要放在整部影片中去认知,就在于我们拥有一种“电影经验”的知觉模式,它使我们把剧照结合为流动的影像,举个例子来说,我们日常使用的iPhone手机所拍摄的照片看似是一张单幅的照片,但如果我们用手指按住这个“照片”,就会发现它实际上是一个包含前后1.5秒的流动影像。换句话说,它是一段video,而非photograph。它类似于我们看到的“电影截图”,它看上去是一张单幅照片,但实际上是一个视频。
前文提及的tableaux vivants既可以指那些静态的场景复制,也可以指那些戏剧性、叙述性的场景复制。它复制的对象可以是绘画,也可以是电影,关于后者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辛迪·舍曼(Cindy Cherman)创作于1977-1980年间的《无题电影剧照》(Untitled Film Stills)。在这个系列的照片中,辛迪·舍曼把自己装扮成电影演员的样子,并让摄影照片看起来如一张张剧照。德国艺术史家汉斯·贝尔廷指出,“我们会情不自禁地用‘电影的目光’来观看这些照片,甚至感觉每一张照片都不是孤立的瞬间,而是从连续叙事体中切下的片段。”按照汉斯·贝尔廷的看法,电影作为一个媒介只存在于它放映的那一段时间,这意味着把图像时间化了,并要求观众采用一种不同的知觉。这也就是梅洛·庞蒂曾经指出的“体验的绽出使一切知觉都是关于特定某物的知觉”,在他探讨电影的唯一一篇文章《电影与一种新型心理学》中,梅洛·庞蒂认为所谓运动和静止并不是取决于“环境服从理性”的假设,而是取决于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我们身体预设的情境。正如iPhone手机“照片”的例子,一旦我们知道它实际上是一个“视频”,我们就不会再把它视为单独的静态照片。因此电影造就的那种“身体经验”不可经由图像式的“身体经验”来阐释。
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让我们回归戈达尔的《受难记》,影片所展示的“活体绘画”(tableaux vivants)是否是某种图像呢?我们在开篇伦勃朗《夜巡》的复制中可以看到,影片景框不仅再现伦勃朗同画框的全景,也揭示了画面的每个局部。在更复杂的拍摄戈雅一组画作中,则使用了更复杂的场面调度技巧:镜头中使用了《1808年5月3日夜枪杀起义者》(Third of May 1808 in Madrid:Executions on Principe Pio Hill' 1814)的场景设置,从士兵的枪支横摇至左侧躺在床榻上的《裸体的玛哈》(The Nude Maja),随后是牵着狗走过的《阿尔巴公爵夫人》(Duchess of Alba),狗跨过死者的尸体,呈现出整个《1808年5月3日夜枪杀起义者》的悲壮场景。后者是这一段的重心,戈达尔来回两次摇拍正在施暴的士兵,并捕捉投降者惶恐的表情,最后则以《查理四世一家》(King Charles IV and his family)以及导演和工作人员的对话作为这一场的结束。
上述细节足以证明这里的tableaux vivants就是电影本身,它是一个运动集合体,而不是摄影复制的图集。在这种电影范畴的复制中,它自身的表达取决于摄影机的机械性质、操作者的执行以及现实环境的制约,它们共同构建了拍摄对象。在这里,tableaux vivants不是巴赞所声称的“摄影机像纪录片一样漫游,将画家的全部作品处理成一幅幅长卷”,因为它不仅是一种“运动的复制”,还是一种“活体的复制”,它所拍摄的对象是被置换的鲜活的生命体。这种复制是一种第三方的复制,也就是借由对他者的复制来指向原作——戈达尔制造了一种断裂并在断裂中重新发现了联系,也就是一种域内和域外的重新沟通。它呈现了德勒兹意义上的“解串联”后重新生成的一种关联,它也必然会呈现某种痕迹,我们可以在《受难记》的片头找到证据:固定镜头呈现的碧蓝天空犹如画板的背景,飞机划过天空的白线成为一种运动的痕迹,成为一种对画板上笔迹的运动性置换,也成就了一种域内和域外的关联。在此,tableaux vivants不再满足于单纯意义上的复制,而是指向了整个环境的空间——摄影棚的空间设置及其带来的一种心理框架。
三、流动的美术馆
影片《受难记》中构建了一个豪华摄影棚,布满了华丽的布景和模型建筑,以便呈现那些绘画杰作的场景,摄影机则在不同的置景和人物之间穿梭,它构造了一种美术馆式的展览空间,并凸显了一种引领观众的电影视点。
参观美术馆的经验不同于电影的经验,我们可以在一幅画作前久久地伫立、凝视,可以按照个人的喜好选择展厅,可以不遵循箭头所指向的线路,这意味着在美术馆中我们都是“闲荡的人”(flneur)。然而摄影机的介入则会改变这种经验,将美术馆变为“流动的影像馆”。观众被迫开启了一种“凝视”,他们无从选择,只能遵守艺术家(导演)设定的规则。电影令美术馆(或具备同等功能的摄影棚)成为所谓的“非空间”,观众必须面对创作者奉为“神圣”的痕迹,跟随他们的线路,并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与他们一种悄无声息的对话。
最典型的案例是亚历山大·索洛科夫的《俄罗斯方舟》,这部电影可以视为tableaux vivants的一个历史典范,它取景于俄罗斯国立美术馆并将其虚构为历史上的著名宫殿。这项浩大而复杂的工程涉及35个展厅,使用850名演员,时间上横跨四个世纪,扫视了俄罗斯历史的动荡风云。而这部电影最大的挑战,是索洛科夫选择用一个镜头完成,这意味着摄影机在国立美术馆中不间断运行90分钟。摄影机的介入解构了一种观看经验,却也建造了另一种观看经验,这也是戈达尔《受难记》中的一个意图:影片中那位将自己关在豪华摄影棚拍电影的导演,和亚历山大·索洛科夫一样制造了一种空间,令包围他们的环境成为不二的主角——那些负载着历史过往的艺术品的存在成为关键元素,它们迅速被记录并将自己的痕迹留在了电影中。于是《受难记》中Jerzi的电影和索洛科夫的《俄罗斯方舟》一样,是一部关于踪迹的电影。然而这种踪迹同时呈现为异质性——和戈达尔那些扮演名画中角色的演员一样,索洛科夫对俄罗斯历史的复制也是建立在一种复制他者(即tableaux vivants)的基础上。而一种替代物的展示,则是美术馆/博物馆中“装置性艺术”的典型思维。
电影介入美术馆的情境,消解了那种“闲荡的人”的栖息地,剥夺了观者的归属感。摄影机迫使观众的目光按照它的路线移动,也就是从一种主动的观看变成了一种被动的参与,它除了把美术馆的藏品作为一个个礼物呈递给观众,也展现了整个空间。在美术馆/博物馆中,不单是艺术品本身,那些周边的设施以及观赏中的游客都成了“展览”的一部分,这类似与我们看到索洛科夫和戈达尔电影中演员和道具参与置景的功能。
我们还可以找到一种逆向的案例,也就是绘画模仿电影效果的情况。1979年安迪·沃霍尔在纽约海默·弗雷德里希画廊(Heimer Friedrich Gallery)展出了他一年前绘制的66件系列组画《影子》(Shadow)。这些作品挂在白色的墙上,安置的基线不同于观众视线的基线,一幅幅绘画的放置产生一种稳定不变的节奏感,沿着一个方向走向终点,但终点同时又是起点。这条连续而循环的饰带是由一个个独立的单元构成的,将其纳入传统绘画展览的行列也是非常困难的。艺术评论家卡丽·里奇(Carrie Richey)在为《艺术论坛》(Artforum)撰写的一篇评论中声称,“作品的摆放暗示出这些图像要按前后顺序来观看,就像是在看电影画面,简直就是电影制作。”她认为按顺时针方向来观看,前面60幅绘画中过分刺激的感官的色彩,在后面的6幅中被银色、黑色和白色所取代,这是一种电影画面逐渐淡出的感觉。
安迪·沃霍尔的组画衍生的电影感/运动感,来自于现代媒介经验的一种交互性,也来自于他本人也是一位电影导演的身份。从时间上来看,创作于1979年的《影子》和创作于1982年的《受难记》可以看做是同时代的作品。电影和绘画双向的模拟和靠拢,证明了不同艺术在泛媒体时代的一种融合迹象,而这两种激进尝试都发生在美术馆或者类似美术馆(华丽的摄影棚)的空间中,2001年的《俄罗斯方舟》等于把这种激进行动推向一个极端。
汉斯·贝尔廷把1800年视为古典和现代艺术的分界线,其标志就是公共美术馆/艺术博物馆的出现,它作为一种栖息地,是旧时欧洲拱廊街和林荫大道的替代品。作为一种艺术集合地,它在呈现复制、拼贴、对比的同时,也提供了一种彼此吸收、借鉴并相互化约的空间。20世纪30年代艾里斯·巴里就任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电影馆馆长是一个历史性时刻,它标志着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在美术馆/博物馆占据了一席之地。电影、绘画和其他艺术共处一室,为“装置艺术”这一现代艺术形式敞开了大门,最终造就了这种彼此融合、化约后的产物——装置影像(Installation Image)。从今天的分类来看,它很难被归类于电影,也无法归类为绘画/雕塑,而是介于它们之间的一种双重“余项”。
美术馆/艺术博物馆改变了艺术生产的逻辑,“前卫”正是在艺术博物馆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意味着对博物馆秩序的“反叛”,它反叛的前提就是博物馆建立的线性扩展和无限创新的逻辑,因为没有博物馆及其确立的艺术规范,所有的否定和造反都没有意义。这种艺术规范的确立便是立足于“分类”。德勒兹曾经提到,戈达尔的电影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不断创造分类范畴,譬如1980年的《各自逃生》就分为“想象”(l'Imaginaire)、“恐惧”(la Peur)、“商业”(le Commerce)、“音乐”(la Musique)四个元素,而影片《受难记》正是诞生于这种分类指向的新问题,也就是“何谓激情?”(Qu'est-ce que la passion?)德勒兹认为这种分类范畴绝非一劳永逸,而是在每一部电影里都必须重新结构、创造和再发明,它不是任意的,而是被完善地建立着。这种思维和现代博物馆的逻辑之间存在着一种潜在的联系,在电影被美术馆/博物馆收纳为其中一员后,戈达尔的电影实验,亦可以被视作对一种博物馆规则或体系的反叛活动。
四、绘画与电影2.0
我们可以把这种电影对绘画的模仿视作德勒兹意义上的“造假的力量”(les puissances du faux),也可以视作李格尔意义上的“艺术意志”(kunstwollen)——即一种让人看到新的艺术形态的强烈意愿,这在《受难记》的主角——导演Jerzi身上充分凸显出来。虽然这种对绘画的模拟宣告失败,但这种行为和追求本身同样可被看做一种先锋主义的尝试。《受难记》中对跨艺术探索的追求以及类似美术馆的艺术空间的使用让影片凸显出一种装置性的特色(至少有一种装置行为的观念)。
与安迪·沃霍尔电影化的陈设类似,戈达尔的电影凸显了某种绘画特性,也就是以画家的方式来思考镜头。《受难记》印证着戈达尔电影思维的一种转型,也就是从文学转向绘画,戈达尔的两部电影可以被视为其电影生涯的节点:第一部是拍摄于1963年的《蔑视》,它通过移植荷马史诗《奥德赛》,将古希腊文学植入现代人的感情危机;第二部是《受难记》,它通过呈现古典浪漫时代的历史名画,对艺术史和现代社会做了一次忏悔式地辩证。值得一提的是,这两部电影都是通过“元电影”的模式来完成的。德勒兹在《时间-影像》中谈到了两部电影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受难记》中将图式影像和音乐影像进行的自由剪辑让一种联系性感官机能得以肢解,而《蔑视》中也同样呈现了这样一种肢解,生命的绘画、尤利西斯的故事的双双解体以及两部影片中共同凝视的蓝天勾勒出一种幻象式的创造性演化。
未来的电影是否可以复制一种“活体绘画”?毫无疑问,数码影像的发展似乎已经开始克服“理想光源”这个难题,然而是否解决这个问题就回答了戈达尔的疑惑?在《受难记》创作的1982年,戈达尔尚未预料到技术变革的问题,但在之后创作的《电影史》系列中,他开始反思电影的存在和终结问题。我们不禁要问,当电影成为纯技术制作的图像而令摄影机、投影、电影院全部消失的时候,它还是否仍是电影本身?弗朗西斯科·卡塞蒂将这种状态称为“电影2.0”,用以和传统电影相区别。然而,无论电影1.0还是电影2.0,都是一种所谓的“技术图像”,按照维兰·傅拉瑟的看法,“技术图像来自文本,也依赖文本,但它们不是平面,而是粒子拼成的马赛克,是后历史的,没有维度的。”这也暗合了本雅明几十年前的论断,电影挑战着人的日常经验,但它始终只是一种技术渗透的图像,“眼前的现实景象,变成了技术大地上的一株蓝花”。以维兰·傅拉瑟的观点来看,电影复制带有先天的局限,倘若电影最终只能靠数码手段来完成,是否意味着它退化为技术维度本身?即使电影最终可以如此复制绘画,它也不再是一种“活体绘画”,而是“伪装的活体绘画”,这是否意味着电影离艺术的特征、离作者的初衷越来越远呢?影片《受难记》中的一段对白可以视为对这种宿命的解释,导演Jerzi询问剧组工作人员:“你觉得电影有规则么?”剧组人员回答:“我认为有两条:最低限度的工作,以及随时毁灭它们的绝对的烦恼。”这也可以看做是戈达尔对电影艺术之极限不断探索后的深切反思。
【注释】
①德勒兹认为戈达尔电影中的反思不仅针对影像内容,还有影像的形式、方法及功能,譬如造假和创造性,以及电影的光学和声学之间的联系。见Gilles Deleuze,Cinema 2:Image-temps,Les ditions de Minuit,1985:18.
②戈达尔曾表示,有声片诞生以来我们对电影语言的开发只达到了电影全部潜力的10%-15%,电影还有极大潜力等待我们去发掘。见大卫·斯特里特主编,《戈达尔访谈录》[M].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0:60.
③在德勒兹看来,自身反思与反思其他艺术类型是电影的职责,见Gilles Deleuze,Cinema 2:Image-temps,Les ditions de Minuit,1985:242.
④戈达尔在很多电影中都使用了丰富的艺术元素,如《疯狂的皮埃罗》中就使用了维拉斯盖斯、梵高、雷诺阿、毕加索、马蒂斯等人的绘画。
⑤这里片中片和影片本身的名字都是Passion,意思是激情、爱欲和苦难。影片中也向这三个维度展开,Jerzi拍摄电影的偏执行为可视为“激情”;他和两个女人之间的情感纠葛代表了“爱欲”,前两个方面彼此交织并升华至第三个方面,也就是“受难”。戈达尔电影的中译名《受难记》以象征的方式指向第三个维度,而片中Jerzi拍摄的电影则是指向第一个维度,因此这里可以译为《激情》,以和戈达尔的电影相区分。
⑥影片中出现的著名绘画包括伦勃朗的《夜巡》、安格尔的《瓦平松的浴女》、德拉克洛瓦的《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拉图尔的《忏悔的抹大拉的玛利亚》、高更的《雅各与天使搏斗》。戈雅的四幅画,分别为《阿尔巴公爵夫人》《裸体的马哈》《1808年5月3日枪杀起义者》和《查理四世一家》。埃尔·格列柯的三幅画,分别为《圣母升天》《剥去基督的外衣》《托莱多风景》。
⑦Tableaux vivants是一个源自法语的术语,指一种人们模仿绘画、雕塑和其他形态艺术的消遣形式,在19-20世纪曾流行于欧美。英文中有时候会译为“living picture”,但仍然无法表达这个术语的原意,“活体绘画”则是在《受难记》这部影片情境内的一种所指。
⑧Francesco Casettti,Eye of the Century:Film,Experienc e,Modernity.Trans by Erin Larkin with Jennifer Pranolo,(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8:104.
⑨在奥逊·威尔斯的《赝品》(1972)中,同样提供了由画家、作家和电影导演组成的造假群落,其中那位画家临摹的画作能轻易骗过美术馆等权威机构的鉴定人员。
⑩维克托·I·斯托伊奇塔,《影子简史》[M].邢莉、傅丽莉、常宁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