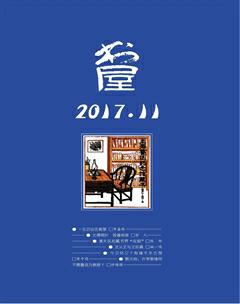牛郎织女:牛皮是怎样吹起来的
艾华
在诗中的星空,牛郎最初叫“牵牛”,与“织女”一起现身《诗经》,是在地上“牵”和“织”的人怨尤的对象。至《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两者始有隔河相望的爱情。此后文人遥看牵牛、织女星,看出的是两情久长,一夕暗渡。近世的民间传说,爱情主题一仍其旧,但“牵牛”俗化为牛郎,不再是天上拟人的星,而是地上的一名孤儿了。
民间传说牛郎从小放牛,骑在牛背上当放牛娃;在文人眼里他是自在的牧童,偶尔还放放风筝。一定是风筝最早引发了他上天的愿望——某只断线风筝在某阵风里变成了一只飞上天的鸟,牛郎望酸脖子,也没有看到这只鸟再飞下来。
长大以后,牛郎仍旧与牛为伴,不过位置从牛背上面移到了牛屁股后面。从小到大,牛郎本来是与哥哥相依为命的,后来哥哥娶了媳妇,他们便三人一起过活。但牛郎老娶不到媳妇,而且据嫂子的说法,牛郎还偷看她洗澡。“我没看!”哥哥听不进牛郎的话,提出分家。
牛郎分得了那头他从小就养的牛,还有一块半生不熟的地。某个寂静的午后,牛郎正在树荫里打盹,突然听到有人叫他:“牛郎。”
牛郎睁开眼,眨巴几下,把刚才的梦眨掉了。日头底下,他的犁歪在地中间,等着他和他的牛。他的牛已凑到他跟前,嘴里有青草和阳光的气息,一副吃好了也歇好了的样子。而他自己,屁股坐在暴出的树根上,背靠荫翳的大树,还想回到梦中去乘会儿凉:弯月,萤火虫,瓜果飘香,喜子(蜘蛛)从天而降……
“牛郎!”这一下牛郎听清了,叫他的不是人,是他的牛。牛郎睁大眼睛,看见牛的嘴巴在嚼动,不是在反刍,是像人一样在说话,结结巴巴的:
“牛郎,仙仙仙女们到河里洗澡来啦。你把谁的衣裳藏起来,谁谁谁就就就是你老婆啦。”
在三个或者七个仙女中间,牛郎很有眼光地选中了织女,因为男耕女织正是中国古代两性的传统分工。不必关心其他仙女是干什么的,在牛郎織女的故事中,她们只是些配角,男主角牛郎不会被她们白花花的身体晃花了眼。
没错,牛郎的目光几乎省略了河中那些白花花的身体,他急于寻觅的恰恰是遮裹那些身体的衣裳。在河边的草丛中他找到了那些衣裳,以衣取人,他和最美的一套衣裳一起躲入了树丛。等他再次出现时,河岸边只剩下了水淋淋的织女。
“恭喜!”那头牛这时也就出现了。
织女哭笑不得。她以在天上织云彩的手艺为自己织成的云衣霓裳,最终却成了贞节的经纬,自己的嫁衣。
这就是牛郎、织女在地上相遇的故事。如天下人所知,这个故事结束于天上,或者说永不结束——在银河两岸;而织女的霓裳云衣轻飘飘的,可以随风飞翔,既是她下凡的媒介,也是她再次上天的媒介。
那么,凡人牛郎上天的媒介呢?
虚与实,词与物,最后都归结为“牛皮”。
“牛皮”一词,如果指实物,无疑就是牛的皮。这样一个实在的词怎样变虚,有了“大话”的意思呢?一种解释是:在桥和船之外,单个的牛皮袋或者多个牛皮袋扎成的牛皮筏,都是一种渡河和水运工具。在有打气筒之前,牛皮袋是要靠人的嘴去吹的。把牛皮袋吹得鼓起来,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所以很多吹牛皮袋的人就成了说大话的人——腮帮子和牛皮袋子一起鼓一鼓,就都瘪了。“吹牛皮!”“吹牛皮!”旁观者于是瘪着嘴说。有的人气更短,干脆说:“吹牛!”当然,也有人本事过头,把牛皮袋吹破或者吹炸,于是旁观的人就说:“牛皮吹破喽!”“牛皮吹炸啦!”
不过另有一说:“吹牛”之“牛”乃是蜗牛,“牛皮”则是蜗牛的硬皮——蜗牛壳。古时候,人们常用蜗牛壳制成吹器,因其发声响亮,本是作为某种信号用的,比如报警,后来也许是有人谎报信号,导致信号无信,这小小的吹器就变成了刺激耳朵的玩具。“吹牛!”“吹牛!”听到响声的人都这么说,并不当真,后来就引申为夸口说大话的意思了。
夸口之大,莫如夸海口。有“吹大法螺”一词佐证。《辞海》这样解释“吹大法螺”:“法螺即螺贝,吹之声能及远。比喻佛之说法广被大众。后用来比喻说大话。”瞧,吹的是海螺,夸的就是海口了。
在中国民间,那些喜欢说大话、夸海口的人往往被称为“牛皮客”;如果牛皮客的牛皮吹得太神奇了,听者便称之为“天方夜谭”。“天方”是中国古人对阿拉伯的称呼,“夜谭”中则有神奇的飞毯。阿拉伯飞毯是可以托人托物悬空飞翔的,可是中国人为之惊叹的时候,偏偏忘了中国有比飞毯更神奇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牛皮,真正的牛的皮。这张真正的牛皮只在牛郎、织女的传说中飞翔,从未见诸别处,以至被阿拉伯飞毯盖住了风头。
民间传说,地上的牛郎娶了天上下凡的织女,从此男耕女织,衣食无忧,还生育了一儿一女。可惜好日子总是不长——天上没有一丝云彩的日子当然不会长,因为天上没了织女,就没有纤纤素手织云彩了,云彩越来越少,神仙们便发觉自己没了隐私。低头看人间,神仙们议论: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的头,他们不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脚了?这——成何体统?讲透明度,也得讲隐私权啊;而且,没有了云就没有了雨,岂不天下大旱,天下大乱?玉皇大帝一查,是织女下嫁了人间!于是派遣王母娘娘押解织女回天庭,牛郎、织女就被活活拆散了。
牛郎仰望苍天,苍天无眼。
牛郎低下头,身边一儿一女,还有他的老牛。
“牛郎啊,”老牛说话了:“我要死了。我死了,你就剥下我的皮,披披披在身上……”
老牛果然死了。它的皮被牛郎剥下,成了牛郎上天的披风。
披风是会兜风的,有翅膀的影子,但牛皮实在不适合做披风,而且是用于上天的披风。牛皮并不像羽毛那样能给人飞上天的联想,哪怕忽略了剥皮的血淋淋,把牛皮鞣制得再好,它终究也不会轻飘飘。相比同一传说中供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鹊桥,牛皮披风显然太沉重了。鹊桥是天下喜鹊飞上天,在银河上用翅膀搭成的桥,牛郎织女相会其上,比现代人睡在羽绒被上飘飘然,怕要欲仙欲死得多——毕竟一在天上,一在地下。
一个美丽的传说,只因牛皮披风的沉重,便显得不真实起来,难怪这张中国牛皮没有像阿拉伯飞毯那样闻名于世。中国人聊以自慰的是,至少曾经有一张牛皮比飞毯飞得更高,把牛郎及其子女送上了天,哪怕它是唯一的,并不像飞毯那样普遍。endprint
牛皮作为上天的媒介,没人能够再次利用,这种不可重复性说明,老牛的遗言对后来者而言实际上是“牛皮”(大话),牛郎借牛皮上天的传说实际上也是“牛皮”(大话),这是不是“牛皮”一词从实物虚化为“大话”的起源之一呢?
如果虚实结合,词与物对应,传说中那头会说话的老牛的“牛皮”,就应是天底下最大的“牛皮”。这“牛皮”是牛的嘴说出来的,也是从牛身上剥下来的,更是天地间的风吹起来的。没人考证那头牛是公是母。不过,“牛皮”一词后来又引出了一个新词,一音之转而成“牛屄”,字形上往往或原始或现代,写成“牛×”和“牛B”,词义则变成了“了不起”或者“自以为了不起”,“有本事、具威风”乃至“显本事、耍威风”。牛郎的那头老牛不管是公是母,其实都只有“牛皮”,不够“牛×”;它能自我牺牲,这固然可敬,但本事就这点本事,威风则一点没有。
老牛的自我牺牲是它的老实和本分,但也跟它的“牛皮”(大话)有关,它会说人话,无疑是跟人学的,牛郎也一定向它吐露过心愿——像风筝一样上天。为了兑现它的“话”,它只有献出它的“皮”。
老牛的自我牺牲感天动地?反正在传说中,牛皮是吹起来了。
“传说”辗转于口耳,依赖于语言。语言是人类发明的一种媒介。如果“大话”指向天堂,指向未来,指向乌托邦,那便是语言的“所指”对人的蛊惑。然而,哪里有“牛皮”(大话),哪里就有牺牲——不只是牛郎的老牛那样的自我牺牲。为了兑现,一头牛,很多人,都可以成为“大话”的祭品。
与“大话”相对的是“小话”:悄悄话,私房话,有人味的话。“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古诗十九首》中有关织女的“小话”,让地上的人抬头望见了她的身影。
这是美丽的倒影?反正在诗中,她就朦胧了。
在诗中的星空,织女不会清晰起来。即使有一点清晰的地方,也是纤纤素手,札札机杼。为什么不让天下人看清织女的脸?有一则笔记辗转于书本——明冯应京《月令广义·七月令》引六朝梁殷云《小说》,最终泄露了天机:织女“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容貌不暇整”。织女的脸,是一张无暇妆饰的脸。这样的一张脸,中国人是不会在诗中看清的。何况“容貌”這样的“小话”,对抗不了天大的“大话”,因为织女的身份已经注定:《小说》中的织女是“天帝之子”,《史记》中的织女乃“天女孙也”。
在牛郎织女的民间传说中,“牛×”的是玉皇和王母,他们有大帝和娘娘的身份,有拆散牛郎织女的权力。好在玉皇大帝后来准许牛郎、织女一年一会,于是佳期如梦,七夕也成了人间节日:瓜果飘香,喜子(蜘蛛)从天而降……而王母娘娘当初不仅把织女从人间带走,把一个女人从丈夫和子女身边带走,而且在牛郎将要追上织女的时候,拔下头上的金(!)簪一划,就划出了一条银(!)河。这样的本事和威风,只能用粗俗的话回敬,就是:
“小公马追小母牛——牛×急(极)了。”
急了怎样?
“小母牛翻跟斗——一个牛×接着一个牛×!”
在科学的天空,“银河”只是一“系”,“牛×”的也不会是天帝、玉皇、王母之类;而飞机、飞船之类则是阿拉伯飞毯和中国牛皮的现代科技版,是人类“牛×”的发明。在不一定科学的天空,飞碟、外星人之类也“牛×”,至少是人类的“牛×”想象;如果科学家、工程师自外于想象的世界,自闭于各自的领域,自得于所谓的“专家”称号,那么同样有粗俗的话等着:
一群小母牛由一头老母牛带着玩耍,突然老母牛喊:“快跑啊,专家来了!”小母牛们不解:“专家?专家是干什么的?”
“专家专门吹牛屄!”
这里的“牛屄”既然怕“吹”,就仍是“牛皮”(大话)的意思,只不过是专家专门吹的,便到底在专门这道窄门内。
不吹牛屄,只做实事,天文学家早已探测出来:牵牛星距离地球十六光年,织女星距离地球二十六光年,牵牛、织女二星之间的距离是十六光年。这就是说,牵牛、织女的星光要花八年才会相遇;如果这相遇的光就是爱情的光,地球人是否看得到?假设看得到,看到的又是多少年前的光?一道天文题,一道数学题。
如果诗意地说,牵牛、织女各自发出的星光是在地球人仰望星空的时候,刹那间相遇于有情人的眼中,那么,映在有情人眼中的星光才是真正的爱情之光——十年的错过算什么?十六年和二十六年的等待算什么?瞬间就是永恒。
如果要说爱情的永恒,作为恒星的牵牛、织女的爱情应在永恒之列。他们的爱情之光相对于赋予他们爱情的地球人来说是滞后的,这与地球人的永恒爱情在话语中滞后是一样的。因滞后而永恒,无论是光,还是传说;永恒的爱情要永恒下去,无疑需要能一直“后”下去的媒介。最好的媒介当然是人类发明的语言了,而最美的语言是诗,可以比喻为语言之光。
不学诗(三百),无以言;以诗为媒;有诗为证——这些说法和做法都凝聚了诗的光芒。如果没有《诗》三百,没有《古诗十九首》,没有有关“七夕”和“鹊桥”的文人诗歌,牵牛、织女的爱情恐怕不会传成永恒的经典。
不过永恒的爱情有时候也是一种大话,正如“有诗为证”有时候是一种虚饰。即便是牵牛、织女的爱情,在走向永恒的过程中,也有过“牛皮”被戳破的时候。
这个尖锐的故事是一篇小说,出自唐张荐《灵怪集》,亦录入宋《太平广记》“卷第六十八”之“女仙十三”。在牵牛、织女天上地下的版本演变中,这篇小说同于先前的诗而异于后来的民间传说;也就是说,俗称的牛郎此时还是天上的牵牛,虽然故事中他并不在场;而看完故事就明白,他不能在场。
故事说的是一个清高的文人郭翰,某个夏夜乘月卧庭中,时有凉风,香气渐浓;他觉得奇怪,仰视空中,有人冉冉而下——
“吾天上织女也,久无主对,而佳期阻旷,幽态盈怀。上帝赐命游人间,仰慕清风,愿托神契。”
织女这番话之后,作者啰嗦了一夜,其实不必啰嗦,只需“一夜无话”,然后“夜夜皆来”——郭翰戏之曰:“牛郎何在?哪敢独行?”对曰:“阴阳变化,关渠何事?且河汉隔绝,无可复知;纵复知之,不足为虑。”
后将至七夕,忽不复来,经数夕方至。翰问曰:“相见乐乎?”笑而对曰:“天上哪比人间……君无相忌。”
经一年,忽于一夕颜色凄恻,涕流交下,执翰手曰:“帝命有程,便可永诀。”遂呜咽不自胜。翰惊惋曰:“尚余几日在?”对曰:“只今夕耳。”
对话实在精彩,精彩到话犹在耳,话犹在口,现代人还是在这样听和说。
小说另有精彩处:一是有关织女的容颜:“欲晓辞去,面粉如故。为试拭之,乃本质也。”一是有关织女的衣服:“徐视其衣,并无缝。翰问之,谓翰曰:‘天衣本非针线为也。每去,辄以衣服自随。”一是有关语言,有关星光:两人别后,次年如约往来书函,是由织女的侍女在天地间传递的,然而仅有一次,从此断了音讯,“是年,太史奏织女星无光”。
小说中不精彩的,不幸得很,恰恰是两人书末的赠酬诗,“情人终已矣,良会更何时”,“人世将天上,由来不可期”云云。也许正是因为赠酬之诗并不精彩,精彩的对话又不能让牵牛听见,这个故事便淹没在了永恒爱情的“牛皮”(大话)中。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