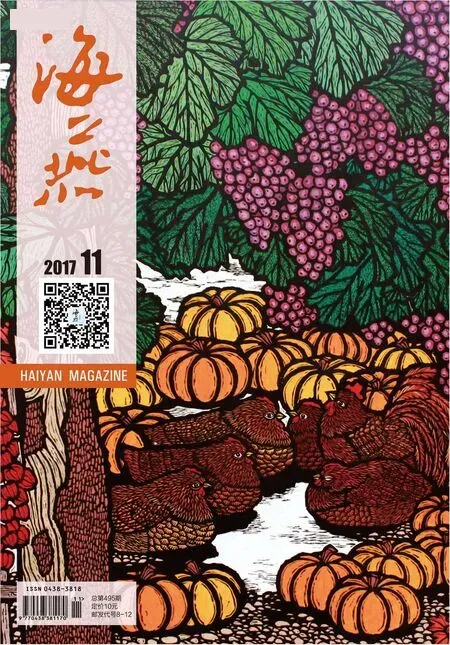塔山风琴引
□高海涛
塔山风琴引
□高海涛
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我在一架破旧的风琴前驻足很久。事实上它是整个纪念馆的第一件展品,破旧得像一件木质的黑色棉袄。讲解员说,在辽沈战役打响之前,苏联红军在东北收缴了日军大批武器装备,但移交给谁是个问题。当年我军服装混杂,也几乎没人会说俄语,与苏军交流很困难。事情发生在冬天,辽东半岛,海风猎猎,苏联人都穿着军大衣,长及脚踵,衣袖平整而简单,与伏尔加乌云同源的款式,前胸和后背都透出冷漠。当此之际,我军有个指挥员急中生智,叫人从小学校里搬出这架风琴,弹奏起著名的《国际歌》,那低沉、激昂、雄浑、辽阔的旋律立即引起了苏军共鸣,他们认出了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他们的同志和兄弟,于是高喊着哈拉少哈拉少,一车车的武器棉服移交给了衣着单薄的我军这支部队。
这件事的象征性可能更大于实际意义。记得列宁说过这样的话:革命者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凭借《国际歌》的曲调找到自己的同志。而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也说过: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确实,一架普普通通的脚踏式风琴,就其象征性而言,简直就是为即将席卷东北大地的辽沈战役奏响了胜利的序曲。
有个研究世界战史的美国女教授叫苏珊·维勒(Susan Wheeler),她于2005年到中国东北考察,在锦州的辽沈战役纪念馆,她和我一样,也被那架破旧的风琴深深吸引了,她觉得不可思议,一架旧琴,一首老歌,怎么会具有那么大的感召力、震撼力?至少在军事外交史上,这几乎是没有先例的。那次她拍了很多照片,稍感遗憾的是,没有人能说清那位风琴师(organ-grinder)的家世和姓名。最后她在纪念馆的留言簿上用英文这样写道:The organ-grinder has gone away, with the instrument left alone,to make the whole campaign full of music.(风琴师走了,只留下这架风琴,让整个战役充满了音乐性。)
离开锦州,南行约三十公里,就到了塔山。我们到达时,天空正下起蒙蒙细雨。塔山,其实只是个村名,当年这个地方,是既没有塔也没有山的,但就是在这个荒草迎风的小漫坡上,六十九年前,我军连续六天六夜,绝地扼守,成功地阻击了国民党驰援锦州的“东进兵团”,创造了震惊中外的“战争奇迹”。也许塔山之名,就是为了这一决胜之役及其英烈们准备的,因为塔山后来有了塔,高高的纪念塔,如今雪松环绕,知了声声,人们至此肃立,两只海鸥停在塔尖回忆往事。
塔山阻击战纪念馆的规模并不大,但我们参观了很久,因为这里的每件展品都太珍贵了——炮火穿过的战旗,那破洞似正可容下远山的落日;当年发烫的枪管好像仍未冷却,上面还留着战士们的手印和汗渍;纪念馆的留言簿上,写满了从将军到作家和诗人,从普通百姓到外籍参观者的留言与签名,包括国防大学2002年外籍班学员用英文写下的一段话:This is a great battle. It will keep on inspiring us.(这是一次伟大的战斗,它将不断赋予我们灵感。)……我翻到2005年的留言,没发现那位美国女士的名字,或许她当时只到了锦州,与塔山失之交臂。
所以诗人般的苏珊·维勒女士并不知道,塔山也有风琴。我的身边,走着一位农民模样的老人。顺着他的手指,我一眼就看见,一台手风琴放在展室的角落里,不知是展品还是非展品,附近没有任何解说词。
老人说:这风琴是我家捐献的!他用手指着手风琴,颤巍巍的,声音不高,但那种不容置疑的自豪感立即传给了所有的人。
老人其实已跟了我们很久了,也许说“跟”是不准确的,从我们走进纪念馆开始,他几乎就一直在引领着我们。纪念馆是免费开放的,据说每天都有当地群众自发参观,我们去的那天也不例外,多是老人带着孩子,时而也有几对年轻的恋人,不过他们都各行其路,走走停停,指指点点,并不跟随我们,但这个老人不一样,自始至终,他都和我们一起走,而且走在最前面,非常认真地听讲解员说话,还不时点头微笑,表示赞许。年轻的讲解员也微笑着,也许从她的角度看,这个老人很像我们这群人的领导,而这未免太特殊、太别致了,我们看样子都是文化人,还打着一面旗子,写着“三大战役采访团”,而这个老人的年纪,没有八十也差不多吧,一看就是质朴的辽西农民,面色黑红,衣着简单,腿脚利落,精神矍铄,总之,他走在我们中间的样子显得很不寻常。也许是觉得太不寻常了,几个当地的摄像记者对老人进行了几次劝阻,但收效甚微,老人到后面转了一圈,很快又跟了上来,直到他发现了手风琴。
可我没来得及和老人交流,就被喊出去上车,我们还要奔赴下一个参观点。
我们这个采访团共二十多人,一路从天津到沈阳,再从沈阳到辽西的黑山、锦州、塔山,然后还要从辽西去苏北和皖北。但行程不论多紧张,我们都不愿放弃任何一个与战事有关的地方,包括战壕和工事,以及临时指挥所旧址。
大巴车继续前行,有人传来刚拍的照片,大家看了都不仅莞尔。因为几乎每一张,都是那个老人和我们一起听讲解的场景,看上去就像是罗立中笔下的“父亲”和我们站在一起,似乎不和谐,却又有一种让人感动的美。塔山现属葫芦岛市,市文联负责人也在车上陪同我们,见我们在笑,也过来一起看照片,然后说:是他呀!那可是我们的“老馆员”了。看我们不解,他说这个老人叫程海,是当地的村民,也是当年亲眼见证过塔山阻击战的为数不多的老人之一,他曾多次到老人家里采访过,程海家老房子的房盖曾被国民党“东进兵团”的炮火掀翻过,至今前檐的木梁上还留着炸弹擦过的痕迹,那还是美式的飞机炸弹呢。
程海之所以被称为“老馆员”,是因为自从纪念馆免费开放以来,他三天两头就过来一次。特别是当听说有上级领导或外地专家来参观的时候,老人更是非来不可,无论下雨天还是下雪天。老人不仅跟参观者一路听讲,跑前跑后,有时还插话,执拗地发出邀请,让参观者都到他家去看看:去我家吧,去我家吧,离这不远,我家的老房子可是个见证啊!
那手风琴,的确是程海家捐献的,但拉手风琴的人却说不准,因此解说词一直没法写,程海只记得那是个年轻人,土改工作队的,喜欢拉着手风琴教妇女和孩子唱歌。那时候程海只有六七岁,他最喜欢唱的歌是“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他觉得那朴素明快的音色像是秋天地里的庄稼都熟了,人们在阳光下刷刷地磨着镰刀。
而秋天很快就到了,炊烟迈着踉跄的步伐,从屋顶上走过。这其实是个渔村,离打渔岛不远。阴历九月,村子里开始过兵,共产党林彪的兵穿土黄色,国民党廖耀湘的兵穿墨绿色。小程海不喜欢墨绿色,墨绿色的兵站在院子里发饷,每人两块大洋,几个乡亲也被叫过去充数,可发饷的刚走,当官的就把乡亲们的大洋收去,揣到自己怀里。塔山战斗发生的时候已经是深秋时节了,庄稼都已上场,田野布满寒霜。这时人们听到了激烈的枪声和炮声,辽西的男孩子都是傻大胆儿,就纷纷站到自家的房顶上去看。小程海家靠近火车站,隔一条小河,就是铁路桥头堡,而那正是塔山阻击战的主战场,在他后来大半生的经历中,他曾无数次的向人们讲述他当时所见到的风景:一块土黄色在强有力地坚守着,一堆墨绿色正疯狂而绝望地在向土黄色反复冲击,后来这两种颜色甚至搅在一起,迸发出鲜红的线条和斑点,构成了难以言说的印象派画面。当然,程海是不懂得印象派的,他只觉得像一个梦,或者他就是刚刚中枪死去的某个战士,用一种亡灵般的角度在看那场激战,如同在看野花盛开的山坡,天上的云影在飞,又似乎静立不动。他还看到一群海鸥,连续三天三夜,扑闪着硕大的翅膀,沿着铁路线,朝着天边的某颗星星飞翔,三天三夜,那些鸟就悬在空中,翅膀不曾触及海面。
塔山之战一共持续了六天六夜,小程海在房顶上看了三天三夜。第四天清晨,小程海刚刚爬上房顶站好,一颗飞机炸弹呼啸而来,将他家的房盖像掀被单一样掀起来,然后稳稳地平移到他家的猪圈上,小程海一愣神,才发现自己站的地方已是猪圈,而猪正在下面狼一样奔窜。那天晚上,拉手风琴的年轻人来了,说塔山那边吃紧,战士们伤亡很重,他要随工作队连夜顶上去。年轻人把手风琴放在他家露天的土炕上,说你们替我保管着,等我回来,估计锦州也解放了,我还得用它去参加庆祝呢。
其实锦州第二天或第三天就解放了,但年轻人却一直没有回来。如今,年近八十的程海还记得那天晚上,在只剩下一角房盖的家中,他怀抱手风琴,冻得无法入眠。他怀恋年轻人教他们唱歌的样子,想到碧蓝的大海和辽阔、苍翠的山峦,他思念被国军抓走当兵的二叔,想到二婶只身去葫芦岛,顺着码头朝大海喊叔叔名字的传闻,他想起房顶上的星光与白云,房顶对于像他这样的孩子是多么重要,他哭了,但不知为什么,他觉得那是一种土黄色的、强有力的哭泣,他哭得不像个七八岁的孩子,而像个成年的男人。
这就是程海老人的故事,市文联同志的讲述是如此生动,让我们都听得非常入神。我突然想到,虽然老人没来得及邀请我们,但他的家也许真值得去看一看。可是我们的大巴车已经到了另一个参观点,按行程,还有几个地方需要参观,返回去肯定没时间了。市文联的同志说,留个机会也好,以后还能见到。他说那房子还基本是当年的样子,半个多世纪了,老人一直住在那里,中间虽翻修过两次,但那个留下过飞机弹痕的小叶杨木梁却保存完好,一进院就能看到,在屋檐下很显眼。老人喜欢种瓜果蔬菜,他家的樱桃特别好吃,红透时连海鸥都会前来啄食。老人虽然年纪大了,但却保持了上房顶的习惯,他站在房顶上,等待可能的参观者,也巡视着他的家园——村外的庄稼,村口的孩子,菜园里樱桃,以及天竺葵、土豆藤和胡姬花。他说只要站在房顶,他就能听到一种来自远方的声音,那声音既不是战歌也不是什么别的歌,而是像流传了几百年的辽西小调,其中提到了许多城市的名字,村庄的名字,战士的名字,也包括那个拉手风琴的年轻人的名字,他想极力记住那个名字,叫张什么、李什么或王什么,但最后那名字还是如风飘逝。
音乐性,我觉得苏珊·维勒女士说的很对,战争也有音乐性。锦州纪念馆的脚踏风琴,塔山纪念馆的手风琴,你可以说它们没有关联,但那种内在的关联、精神的关联是无可否认的。所以当你一看到它们,它们就会遥相呼应,轰然奏响,从国际歌到辽西小调,从战斗的信念、革命的理想到老百姓沧桑无倦的家园,交汇成某种初始的、朴素的、潮水般的旋律。在采访团从北到南的整个行程中,我心中始终有这种浩荡而别样的旋律感。不仅是“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也不仅是“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还有风的旋律,从大海深处、草原深处、历史深处、人心深处刮来的风,仿佛隔着十万八千里那样悠悠吹来。是啊,许多牺牲者都是无名无姓的,就连风琴师、风琴手,也同样无名无姓,但他们确实创造了奇迹,战争的、军事的、历史的、风的奇迹。
责任编辑 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