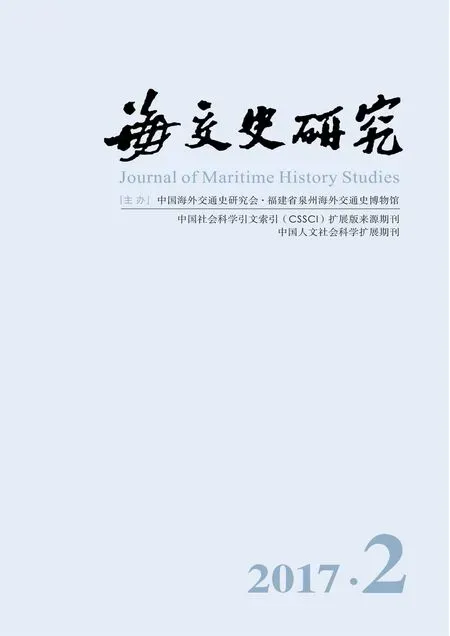试析广东十三行的企业制度特征*
张忠民
试析广东十三行的企业制度特征*
张忠民
广东十三行并不是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体制下,由民间资本、民间贸易自发产生的自主企业组织;而是在清前期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以实现清王朝管制中国与西方商人之间的对外贸易为目的,由清廷及其地方衙门主导、实施的一种特殊的企业制度。在此制度中,传统的家族势力虽然发挥极大的作用,但对于整个广州商界以及朝廷和官府来说,十三行却不仅仅只是意味着一个商人、一个商号,而是一个商业团体、一个商业家族。因此,从企业产权、企业治理结构以及企业剩余分配方面,对企业制度特征进行进一步的考察,也是广东十三行研究的重要内容。
十三行 企业产权 企业治理结构 企业剩余分配
引 言
广东十三行是中国海外交通史以及中国经济史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关于十三行的研究由来已久,成果累累。然而,在过去的研究中,学界的关注焦点多集中在对十三行起源及流变的考证、十三行与前清贸易体制的研究、十三行在一口通商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即使是对于十三行制度的研究,也只是侧重于其贸易制度。
关于十三行的研究成果,前人如根岸佶《广东十三洋行》、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等等,可参见冷东《20世纪以来十三行研究评析》。近年来的研究著述亦可参见李国荣等主编《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广州大学十三行研究中心、中共广州市荔湾区委宣传部编《广州十三行研究回顾与展望》,陈国栋《清代前期的粤海关与十三行》等。对于十三行的企业性质,有研究认为“广州十三行是清代封建外贸制度下形成的商业资本集团。”*李金明:《广州十三行:清代封建外贸制度的牺牲品》,载《广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但对于什么是商业资本集团,其内在的制度特征是什么,似乎还尚无具体论述。近年来,随着形势的变化,对于十三行研究有了新的认识,有著述提出,“十三行行商,不仅为中国的外贸,更为引进先进的经济思想文化,并成为中国最早的跨国公司或财团,乃至西方工业革命的‘影子银行’。”*谭元亨:《广州十三行——明清300年艰难曲折的外贸之路》,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15年。但是对于十三行作为前近代中国社会一种重要的企业组织或资本组织的形式以及其企业制度特征,实际上还较少有直接的研究。
广东十三行作为清前期重要的商业贸易组织,可以从其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内在管理等,来了解它的企业制度特征。这一企业制度特征大致上可以从企业产权特征、企业治理结构特征、企业剩余分配特征等方面来加以考察。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研究基础的薄弱以及相关文献史料记载的匮乏,本文主要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现有的文献资料为据,以合乎逻辑的分析框架,来提出、思考并讨论一些问题。
一、十三行的产权制度特征
在讨论十三行的产权制度特征之前,首先要明确两个前提:一是十三行的企业类别;二是十三行成立的依据。
十三行的企业类别从根本上讲,主要是居间性质的牙行,这在有关的史料记载中还是比较明确的。据雍正三年(1725)两广总督的一份奏折称:该年广州“六、七两月共到外国洋船十支,俱湾泊黄埔地方,委官弹压稽查,不许内地闲杂人等擅入彝船生事,并严饬牙行、通事人等贸易货物,公平交易。”*《两广总督孔毓珣为报洋船到粤情形及饬牙人等公平交易事奏折》,雍正三年九月初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广州“十三行”档案选编》,载《历史档案》2002年第2期。在商业贸易口岸设立居间买卖的牙行,以及长途贩运商人在买卖中的“投行”,是中国长途贸易的商业习惯,外来的商人更是如此。外商来到广州,依照商事惯例寻找相应的牙行及牙行商人接洽买卖。即使是一般的商业牙行,由于需要得到官府的颁照许可,因此多少都带有行业垄断的性质,而十三行由于贸易地点、对象、内容的特殊,更成为一种带有特许权的对外贸易牙行。
十三行成立的依据,由于其牙行的性质,成立自然必须得到官府的批准,这一批准也就是贸易特许,即经官府核准有条件的充任。这在康熙年间清政府关于设立洋货行的文告中有明文规定。康熙二十五年(1686),两广总督、广东巡抚与粤海关监督共同发布《分别住行货税》文告,决定设立金丝行、洋货行两项货店,“如来广省本地兴贩一切落地货物分为住税,报单皆投金丝行,赴税课司纳税;其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分为行税,报单皆投洋货行,候出海时洋商自赴关部纳税”。同时亦明确规定“如有身家殷实之人愿克洋货行者,或呈明地方官承充,或改换招牌,各具呈认明给帖”,但是两行不能混杂,“即有一人愿克二行者,亦必分别二店,各立招牌,不许混乱一处,影射朦混,商课俱有违碍。”*李士桢:《抚粤政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丛刊三编》(第39辑),北京:文海出版社,1988年,第729-732页。故有文章认为:“洋货行是专制国家运用行政命令强制建立起来的。为了建立洋货行必须招商承充。当时招商的条件并不苛刻,手续也较为简便,只要是‘身家殷实’‘愿充洋货行的’‘商民行人’‘或呈明地方官承充’‘或改换招牌,各具呈认明给帖’就行了。”*萧国亮:《清代广州行商制度研究》,载《清史研究》2007年第1期。在官府核准、特许制下,十三行还实行了一种官方认定的行东登记制度。行东由于去世或者其他原因需要更换行东,不仅需要官方批准,还得支付大额的贿金。行东有些类似现代企业制度中的“法人代表”,行号一旦有事,官府唯行东是问。有史料记载,石梦鲸在1778年开办而益行时,“为了避免一旦故世,移转行东登记时,让广州官场得到索贿的机会,石梦鲸一开始就把而益行登记在(次子)石中和名下。因此,面对官府时,而益行的行商就是石中和。”“不过,石梦鲸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往来贸易已久,因此在公司记录上始终称呼而益行的代表人为Kinqua(鲸官),而他其实也正是实际的经营者。”*陈国栋:《清代前期的粤海关与十三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83页。
关于十三行的产权制度特征,值得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三:一是十三行的资本组织形式,即十三行的资本究竟采用的是独资形式还是合伙形式,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二是十三行的资本规模或者说资产规模究竟有多大;三是与前者有关的十三行特殊的无限连带责任。
首先是资本组织形式。在前近代中国社会,资本组织形式大致上就是独资与合伙两种。从现有的资料看,十三行的商行似乎多为典型的家族独资企业。但是这种独资性质的商行一旦传至第二代、第三代时,就会出现一种因为各房子孙各自继承家业而使商行在事实上成为家族内各房子孙共有企业的情况。其产权归家族共同享有,但是经营权仍由指定的家族某一成员充任。
以潘氏同文行为例,到第二代潘启官时,商行虽然由其长子经营,但产权却归第一代潘启官的七房子孙共同所有。从理论上而言,原来由一个家长创办和经营的独资商行就成了由七个儿子,或者说是七房子孙共同合伙所有的商行。“同文行是家族的生意,产业归潘正炜的父亲潘有度及其六个兄弟共享。1807年,同文行获准歇业。潘氏兄弟原以为从此可脱离商界,于是将同文行财产分割,潘有度分得的份额占七分之一或多一点。”*参见潘刚儿等编著:《广州十三行之一:潘同文(孚)行》,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91页。可见,当潘文岩过世之后,同文行实际上就已经转变为潘有度以及其他六房嫡兄弟共同所有,商行的资本至少也就应该分成7股,实际的股东至少也有7名,而商行也就由原来潘文岩的独资商行转变成由潘有度七兄弟共同所有的合伙企业。
类似的例子还有在雍正年间由颜亮洲创办的泰和行,在其死后由长子时瑞接手经营,乾隆二十八年(1763)时瑞去世,商行由其弟时瑛经营。而时瑛一代,有兄弟12人,按照当时家产子孙共享的惯例,泰和行应该已经是颜氏家族各房子孙合伙共有的产业。故而才有“时瑛自己负责行务及对外交酬联络,其三弟时球负责家业及家族内部事务,四弟时珣负责建造宗祠及纂修家谱,九弟时理主要在福建采购茶叶,当是负责泰和行出口物资的采办工作。”*参见黄国声:《十三行行商颜时瑛家世事迹考》,载《中山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在这里,颜氏兄弟不仅共同拥有商行的产权,而且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商行的实际经营,这与当时一般的合伙企业已经没有什么不同。
在为数不多论及十三行资本组织形式的文章中,也有认为行商是合伙组织的。“行商的来源,包括盐商、洋行司事、通事、买办和鸦片经纪等,其资本来源主要得自中西贸易的利益。每家行号通常有几个合伙人,一般是兄弟或亲戚,带有浓厚的封建宗族色彩。”*章文钦:《清代前期广州中西贸易中的商欠问题(续)》,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遗憾的是,论者对此并未提供直接的佐证史料,亦未展开具体的论述。
如果十三行的合伙仅仅是如前引史料所见兄弟间因分家析产而导致的合伙,那么这种兄弟间的合伙与当时中国社会一般的异姓合伙人的合伙企业还是存在一定区别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这样的合伙企业中,商行股东的产权权益可能并不一致。作为行东的资本所有者似乎并不取决于拥有股权的比重,而仍然可以实现对洋行产权的控制。作为行号股东的其他各房子孙很可能并不参与商行的决策,或者过问洋行的事务,前述颜氏兄弟的事例可能只是一个特例。
其次是十三行的资本及资产规模。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资本规模与资产规模并不是等同的概念。一般来说,对于一个企业或者是一个资本组织来说,资本指的是该企业成立及成立之后的登记或者说注册资本,而资产则是企业在运营过程中所拥有货币及物质形式的财产,按其资产负债的原则,又可以分为总资产和净资产。因此,一个企业的资产规模总要大于资本规模。
关于十三行的资本规模,在现存的史料中我们似乎很难看到官府在核准洋行设立时对洋行资本数额的规定,而一般只有对洋行开办者包括其全部资产能力的要求。而在新充十三行商号的任职条件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的是要求充任者“身家殷实”。嘉庆年间,“如遇选新商,责令通关总散各商公同慎选殷实公正之人,联名保结,专案咨部备查。”之后,“总商等以新招之商,身家殷实与否,不能洞悉底里,未免意存推诿。倘有一行不保,即不能承充”。道光年间又改为“嗣后如有身家殷实呈请充商者,改监督察访得实,准其暂行试办一二年,果能贸易公平,夷商信服,交纳饷项不致亏短,即照旧例,联名保结,方准承充。”*(清)梁廷枏总纂:《粤海关志》卷25,《行商》,袁钟仁校:《粤海关志(校注本)》,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98、500页。明明是开办一个企业,为什么要求的不是“资本殷实”,而是“身家殷实”,这大致上可以说明两个问题:其一,对于十三行商人来说,其商行的资本多寡并不是官方注重的主要方面,而包括生活资料在内的全部身家财产的多寡才是考虑的主要方面;其二,官府之所以看重身家殷实而不是资本殷实,完全可以说明当时的十三行商人所负的无限连带赔偿责任。商行之负债是以商人的所有身家财产为无限责任赔偿的,故而“身家殷实”就显得尤为重要。
此外,在现有的资料里,我们也很难找到直接记载十三行资本及资产规模的史料。同时,在记载十三行商人财产的史料以及不少研究著述中,一方面说行商集中了大量的财富,另一方面往往又说十三行商人经营中的亏欠、夷债,以及借用钱款等等。出现这种矛盾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洋行的设立并不具有注册资本的要求,由此造成十三行最大的产权特点之一,就是无限责任下的“行、家资产不分”,即商行资本与家产混为一谈。在留存下来我们能够看到的史料中,记载的往往是某某十三行商人有白银二千万元财产等等。但是这些财产有多少是洋行的资本或资产,有多少是行商私人的宅院、地产等等,不得而知。
以著名的伍氏洋行为例,“伍氏家族富甲天下,嘉庆年间,已经‘每遇岁除家库核存常达千万有奇’。据亨特说,道光年间:‘伍浩官究竟有多少钱’,成为外商经常谈论的话题。1834年,伍秉鉴宣称,他的资产‘约值二千六百万元’。马士说:‘在当时这是一笔很大财产,或许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资财’。而亨特的另一著作又说,潘启官(正炜)‘有伍浩官三分之一的财产,约超过二千多万元’。故当时伍家的资产实际上还不止这个数目。”*参见章文钦:《从封建官商到买办商人——清代广东行商伍怡和家族剖析(下)》,载《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4期。但是在这些财产中,有多少是属于洋行的资本或资产,又有多少是属于行商的其他个人私产,完全没有作任何的区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几千万元的财产,一定是包括了伍氏行商、潘氏行商所有洋行资本和其他个人私产的全部数额。
十三行商人企业资产与家庭财产“家、产不分”的现象,在陈国栋《清代前期的粤海关与十三行》一书所列的而益行破产时,由行东石中和自己开列的一份资产负债表中表现尤为明显:

而益行资产负债表 单位:两
资料来源陈国栋:《清代前期的粤海关与十三行》,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91页。
因此,尽管有不少的资料称十三行商人家产殷实,但是亦有不少的研究著述认为十三行商人的经营资本并不雄厚或充实。“研究发现清代中叶广东洋行商人普遍经营不善的现象,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资金不足。”*潘刚儿等编著:《广州十三行之一:潘同文(孚)行》,第113页。“行商深受专制国家和官吏的各种压榨,行商资本常常处于短缺状态,而广州的对外贸易却在不断的发展。因此,行商越来越显得捉襟见肘,他们‘并没有经营广州全部对外贸易的足够的资本’。”*《广州纪事报》1828年8月2日。
“由于行商的资本不是近代意义的合股制资本,同当时其他中国商人一样,一般资本额不大。……乾隆年间的行商黎光华、倪宏文,因商欠十余万两至万余两而破产;嘉庆年间承商不久的潘长耀,因被罚饷银五万两而经济陷于困难,道光年间严启昌、王大同在交纳四万余两的手续费和买进栈房家具之后,已身无分文;多数破产行商家产被查抄变抵时仅值数万两,排除变抵中的压价因素,亦很少超过十万两。因此,估计当时行商的资本额一般是十万两至数十万两。”*章文钦:《清代前期广州中西贸易中的商欠问题(续)》,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
“行商普遍存在资金不足,如兴泰行在1837年4月19日写信给他的主要债权人查顿说:‘1830年,我以有限的资本开始营业,在开销了挂出招牌开张营业的费用和买进栈房和家具之后,我身上一文钱都没有了’。”*[英]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61页。
根据陈国栋的研究,“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以及当时其他外国商人的记载大多证实行商在开业时资本十分有限。一般而言,行商在准备领取执照的时候,手上的资金往往只有四五万两之多,至多的情形也不过是一二十万两。”*陈国栋:《清代前期的粤海关与十三行》,第248页。清前期十三行商人中最负盛名的当推怡和行及同孚行。“就怡和行而言,在1792年由伍秉钧开业时,资产甚微。”*陈国栋:《清代前期的粤海关与十三行》,第236页。
由于行商资本的不足,因此在许多行商的经营资产中,对外负债,尤其是对外商的负债占有极大的比重,这不仅导致洋行资本具有极高的资产负债率,而且还会进一步导致因经营不善而出现的资不抵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停业乃至破产。
十三行的经营资产中有相当部分是来自贸易中的往来账款,甚至是向外商借贷的钱款。在往来账款中,最主要的是出口货物的预付款。外商在预订来年的丝、茶等货时,预付货款的比重是较大的,一般可以占到全部货款的80%-90%。而且由于生产周期以及运输路途的遥远,订货的周期也是较长的,一般多在4至6个月甚至300天。1780年间,“茶丝和南京布预付货款,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惯例,这是保证到期(九个月或更早些)能够全部交货的唯一办法……在那些合约中,预付给潘启官的为601 500两,其中562 500两是2 250担(3 000包)生丝的预付款,每担定价265两,预付250两。”*[美]马士著、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二卷)》,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76页。这说明在洋行的经营资产中,外商的预付货款往往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不仅会大大加重洋行的资产负债率,而且如果洋行一旦将此预付货款挪用于代外商购买丝、茶之外的其他用途,并且在挪用过程中出现问题时,必然就会产生程度不等的“夷欠”。
对外商的借贷负债与前述贸易中的往来账款有所不同,它们是洋行纯粹的负债。为学者引用甚多的乾隆年间一份奏折表明,行商向外商借贷已是常事,而官府曾有例禁。“近年狡黠夷商,多有将所余赀本盈千累万,雇倩内地熟谙经营之人,立约承领,出省贩货,冀获重利。即本地开张行店之人,亦有向夷商借领本银纳息生理者。……嗣后,内地民人概不许与夷商领本经营,往来借贷,倘敢故违,将借领之人照交接外国借贷诓骗财物例问拟”。*《两广总督李侍尧为陈粤东防范洋人规条事奏折》,乾隆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广州“十三行”档案选编》,载《历史档案》2002年第2期。
无论是贸易中的信用交易还是出于各种原因的纯粹的资金借贷,其主要原因都是由于行商资本的匮乏以及资金的不足,此外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也由于广州本地传统金融机构以及资金供应的不足。一旦这种由于自身资本及资产不足而形成的高资产负债率达到临界点,行商就可能因为挪用或拖欠外商款项,造成自身无法清偿的巨额债务而陷入破产的境地。如乾隆年间泰和行行商颜时瑛、裕源行行商张天球,“明知借欠奉有例禁,乃不将每年所得行用余利,撙节归还,任听夷人加利滚算,显存诓骗之心……拟军从重革去职衔,发往伊犁当差……所有泰和、裕源行两商资财、房屋,交地方官悉行查明估变,除扣缴应完饷钞外,俱付夷人收领。”*(清)梁廷枏总纂:《粤海关志》卷25,《行商》,袁钟仁校:《粤海关志(校注本)》,第492页。
据章文钦《清代前期广州中西贸易中的商欠问题(续)》附录,《破产行商欠外商债务表(1758-1843)》统计,在此80余年间,行商所欠外商债务总额高达1 658余万元;而据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估计,在实行公行制度的82年间,无力偿付的行商债款总数为1 650万元以上。*章文钦:《清代前期广州中西贸易中的商欠问题(续)》,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由此也间接反映了洋行由于自身资本的不足而导致的极高的资产负债率。可以进一步观察的问题是,当时的洋行其资本的盈利能力以及资本的积累能力应该是较为有限的。如果洋行的经营利润可观,就应该很容易积累起资本;而如果洋行的资本积累充实,也就不应该会长期发生这么多的“行欠”“饷欠”“夷债”甚至是“破产”等等。
最后是关于十三行的无限连带责任问题。如前所述,十三行的重要产权特征之一是企业资产与家庭财产混为一谈,这一产权特征为十三行特殊的无限连带责任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础。在十三行的产权制度特征中,行商所负有的无限连带责任是极为显著和严重的。可以说,这种无限连带责任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企业制度中简直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
首先,这种无限连带责任表现为商行对本身经营的无限连带赔偿责任,商行如果倒闭或破产,包括家庭、家族其他成员在内的所有关联人员必须以自身的全部身家资产进行清偿。如前述“资财、房屋,交地方官悉行查明估变,除扣缴应完饷钞外,俱付夷人收领。”乾隆十二年(1747),行商倪宏文因赊欠英国商人11 000余两货银,“监追无着。经伊胞兄倪宏业、外甥蔡文观代还银六千两”,皆为事例。*(清)梁廷枏总纂:《粤海关志》卷25,《行商》,袁钟仁校:《粤海关志(校注本)》,第492页。
其次,这种无限连带责任还体现在一家商行破产,如果其本人或本家族的资产不够清偿时,其他的所有商行必须共同承担无限连带赔偿责任,为破产的商行进行“买单”,这就是所谓的各行商之间的“联名具保”。如前述乾隆年间行商颜时英、张天球欠英商债务无法清偿,本人被革衔充军,所有家产清偿债务,其不足部分“着落联名具保商人潘文岩等分作十年清还。”*(清)梁廷枏总纂:《粤海关志》卷25,《行商》,袁钟仁校:《粤海关志(校注本)》,第492页。乾隆五十六年(1791)行商吴昭平积欠外商货价,“所欠银两,估变家产,余银先给夷商收领,不敷之数,各商分限代还。”*(清)梁廷枏总纂:《粤海关志》卷25,《行商》,袁钟仁校:《粤海关志(校注本)》,第495页。
再次,所有的商行还必须对行业内所有必须承担和支付的“税负”“贡纳”“捐输”等等负无限连带责任。一个商行支付不起,其他商行必须负连带责任,共同支付所有的税负和捐输。据道光十四年(1834)两广总督的一份奏折所称,“统计前后倒闭五行,饷欠、夷欠共二百六十余万两,均归现开各行摊赔清楚。”*《两广总督卢坤为查办洋行各商积欠粤海关饷银事奏折》,道光十四年十一月初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广州“十三行”档案选编》,载《历史档案》2002年第2期。由此可见洋行对政府的税饷实际上也是由所有的行商负无限连带赔偿责任。
而上述所有这一切的无限连带责任,又都是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由朝廷和官府的法令、法规、谕旨的形式所规限的,在当时的社会中具有强制性的效应,这在前近代中国社会中的其他地方、其他资本组织中是极为罕见的。
二、十三行的企业治理结构特征
一个企业组织起来之后,一定有与其产权制度相适应的企业治理结构。十三行的企业治理结构究竟如何?具体的管理制度又是如何?这些都是研究十三行企业制度特征所需要认真考察的问题。然而由于史料记载的严重不足,考察十三行的企业治理结构似乎比考察其产权制度更为不易。*梁廷枏《粤海关志》虽有《行商》专卷,但是对于行商之组织构成,并无任何交代。从中我们无法得知行商的资本组织以及治理、分配的具体情况。
从理论上而言,十三行的企业治理结构与其产权制度特征是紧密相关的。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存不存在资本所有权与资本使用权的分离,存不存在职业化的经理人员及经理阶层,以及存在什么样的企业科层结构等等。
如前所述,十三行基本上是以家族经营为主体的产权结构,尽管这种家族经营在经历了一定的周期后可能会出现独资向兄弟合伙的转变,但是以家长为核心的独资经营可能还是十三行产权制度最基本的特征。如果十三行的产权构成基本上都是家族独资组织,那么其企业治理也一定就是以家长为核心的家族企业治理。企业的管理阶层,特别是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理应由家族成员出任。然而,我们在《广州十三行之一:潘同文(孚)行》一书引民国九年(1914)潘氏族谱关于潘启的从商经历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公家贫好义,由闽到粤,往吕宋国贸易,往返三次,夷语深通,遂寄居广东省,在陈姓洋行中经理事务。陈商喜公诚实,委任全权。迨至数年,陈氏获利荣归,公乃请旨开张同文洋行”。*潘刚儿等编著:《广州十三行之一:潘同文(孚)行》,第1页。
从上述记载中我们至少可以推断出两点:第一,潘氏洋行的创始人潘启在其独立创办同文行之前,已经在洋行中从业,而且担任的职务还不低,早期的洋行经历及经验,一定对其日后自身创办洋行具有直接的关联;第二,从上述引文中的“陈商喜公诚实,委任全权”可以看出,作为行东的陈氏本身似乎并没有直接经营管理洋行,而是将洋行的经营管理权委托给了异姓的潘启。在这里,作为行东的陈氏自然是洋行的所有者,其在企业治理结构中的地位有些等同于企业中的“董事长”;而被“委任全权”的潘启,其在企业中的地位有些类似于“总经理”。在企业的委托代理结构中,陈氏是产权的委托者,其将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委托给了作为企业雇员的潘启;而潘启则是被委托者,是企业经营管理权的代理者,也就是现代企业理论中所说的企业管理的“内部人”。
从上述这一事例中,我们似乎可以进一步推论,在清前期广东的一些洋行中,洋行的负责经理不仅完全可以聘用外姓人士出任,而且如果真有才干并且得到东家的信任,甚至可以出任最高经理人。如果此述切实,那么在当时的某些洋行中,洋行的产权所有者可以不直接经营洋行,而洋行的实际经营者则是行东的委托代理人。资本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实际上已经分离。
上述的记载似乎还不是个别现象,在其他一些史料记载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例如:怡和行的创始人伍国莹在承充行商之前,曾经是潘氏同文行的账房。*章文钦:《从封建官商到买办商人——清代广东行商伍怡和家族剖析(上)》,载《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3期。1792年开设达成行的倪秉发,在承充行商之前曾经是行商陈源泉开设的源泉行中的掌柜。陈源泉1789年故世后,因为其子难以胜任行务管理,源泉行一度还要依靠倪秉发经营管理。*周湘:《清代广州行商倪秉发事迹》,载《中山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1793年,当源泉行的继承人陈文扩的儿子因为被粤海关剥夺了一位得力的助手(倪秉发,他被任命为独立的洋商,因而无法继续在源泉行服务),而在经营上出现严重困难,无能力履行契约义务。”*潘刚儿等编著:《广州十三行之一:潘同文(孚)行》,第103页。此文称倪秉发开设达成行的时间是1793年,与前引周湘文章中所说的1792年稍有出入。潘氏洋行第二代潘有度过世后,其四子潘正炜“被安排担任名义上的洋商,而由一名名叫亭官的堂兄弟经理实际的业务”,“当1821-1822年潘正炜继任同孚行洋商后,由于他不通外文,所有涉外的事件全由亭官处理。”*潘刚儿等编著:《广州十三行之一:潘同文(孚)行》,第94、95页。
由此可见,在当时的十三行中,由行东聘用经理、甚至总经理似乎并不鲜见。在十三行的企业治理结构中,资本的所有权与使用权是可以分离的,洋行的产权所有者并不一定就是洋行的实际经营管理者。在当时的洋行中,可能实际上已经存在一个职业化的经理阶层,这些专门的经理人员在具备了一定的条件之后,往往又成为洋行的独立开办者。
考察十三行内部的科层结构似乎较之于前述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更为困难。然而,前文所引颜氏泰和行的一段史料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启示。根据该史料,泰和行在其创办人颜亮洲故世后,由其长子时瑞接替出任行东。时瑞去世后由其弟时瑛接替经营。时瑛兄弟12人,除了时瑛本人之外,至少还有1人参与了洋行的经营事务。其具体的分工就是前述资料所引的“时瑛自己负责行务及对外交酬联络,其三弟时球负责家业及家族内部事务,四弟时珣负责建造宗祠及纂修家谱,九弟时理主要在福建采购茶叶,当是负责泰和行出口物资的采办工作。”*参见黄国声:《十三行行商颜时瑛家世事迹考》,载《中山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泰和行在其内部组织上至少已经分有行务、对外交酬、采购三大部分,如果加上洋行经营必不可少的财务、仓栈,我们似乎可以大致上描述出洋行的基本组织结构。一家较具规模的洋行,其基本经营既有对进口商品,诸如毛呢、棉花以及其他西洋商品的销售,又有对丝、茶等出口商品的订购贸易;既有与外商的贸易,又有与内地销售商、供货商的联络等等。由此,其内部的经营部门至少应该分成外贸和内贸两大部分,加上其他的辅助组织,以及洋行的总机构,其基本的组织结构大致上可以推测示意如下:

广东十三行组织结构示意图
在上述示意图中,行务指的是洋行的总管理机构,或者说是总管理部门,外贸部门则是在行务领导下对外商进行贸易生意的机构和部门,内贸部门应该是洋行对内地商人进行洋货销售以及出口丝、茶采购等等的机构和部门。如果洋行的业务规模够大,很可能在外贸部门下还会分设负责进口洋货的部门以及负责出口土货的部门;而在内贸部门下还会分设负责销售洋货的部门和负责采购出口土货的部门。至于财务以及仓栈运输应该是任何一个洋行必不可少的机构和部门,只是在不同规模的洋行中,它们应该会有不同的设置。
在大致推测出洋行内部组织结构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大致推测出洋行的科层结构。在上述示意图中,所谓的出资人指的是洋行资本的所有者,也就是洋行的拥有者,即行东。当洋行是独资组织时,出资人就只有一个,当洋行是合伙组织时,出资人可能就是合伙的若干人。行东是指依照当时的法令、法规登记在册的洋行的代表人,即有些类似今日的企业法人,不论洋行是独资还是合伙,作为洋行的行东在一个时间内,一定是只有一个。大掌柜则是洋行的实际经营者和管理者,是洋行日常经营事务的最高管理者。无论是在独资还是合伙的情况下,这一职务或者说岗位,可以是行东本人出任,也可以是由行东聘任某人出任。只是在很多情况下,或者可以说在大部分情况下,出资人、行东、大掌柜往往是三位一体的,这种三位一体正是前近代中国社会中,独资企业在治理结构上最重要,也是最明显的特征。而在某些情况下,行东与大掌柜也是可以分离的,这种分离的理论意义就是资本的所有权与资本的使用权的分离,以及企业治理结构中委托代理的形成,职业经理人和职业经理阶层的形成。
从以上示意图我们还可以看出,清代前期的十三行,至少在一些较具规模的大洋行中,很可能已经形成了股东——行东——大掌柜——掌柜——业务人员的科层结构。这一科层结构正是洋行运营的基本保证。
三、十三行的剩余分配特征
剩余分配是资本所有权之一的剩余索取权的实现。在前近代中国社会的独资或者合伙资本组织中,企业在扣除经营成本以及税收等项后,在扣除一定的公积金等积累后,余下的剩余就是资本的剩余“利得”。一般来说,这种剩余总是按照资本的份额,在资本所有者内部进行分配。分配的形式一般是股息和红利。
十三行的剩余分配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分配的内容;二是分配的形式;三是分配的数量问题。
与一般的传统商业组织相比,十三行的剩余分配似乎显得更为复杂一些。这就是在一般资本组织的按资分配之外,十三行的剩余分配中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与向朝廷以及地方政府或官员的“报效”“捐纳”等相关联。官府以及官员的各项索取,到底属于不属于或者说算不算是剩余分配的范畴,这涉及到十三行的营业成本以及剩余使用的问题。
首先,剩余分配是资本的私权利,只有资本所有者或者说产权所有者才具有剩余索取权。而官府以及官员的索取实际上只是一种凭借公权力的索取实现。从这一点说,这种索取并不属于企业制度中所说的剩余索取的范畴。官府索取中的“饷银”,不论其合理程度如何,本质上都是一种国家税收,属于企业剩余分配前的扣除,属于企业的经营成本。况且这种税收很大的一部分还是属于为外商的代缴。
洋行的税饷最终究竟由谁负担?是外国商人还是十三行商人?十三行商人是税饷的代理者还是最终承担者,这在以往的一些著述中往往是含混不清的。十三行商人代理的税项应该是来自贸易商人的预付。只有在贸易商人不按约支付税项,而十三行又必须向官府缴纳时,才会发生亏欠或者是破产的情况。再有一种就是十三行商人挪用或者是亏欠了贸易商人的预付税项。
乾隆四十七年(1782)的一份奏折表明,“所有出口货税,应听行商先行完交。至进口货税,夷等不能即时措办,照依从前各船回帆之时,夷等将货物按照应交税数交明,行商上紧代卖输纳。”*《粤海关监督李质颖为督催洋行交纳洋船进口货税事奏折》,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初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广州“十三行”档案选编》,载《历史档案》2002年第2期。可见,无论是货物的进口税还是出口税,最终的负担者应该都是外商。
周湘《清代广州行商倪秉发事迹》有这样一段论述:“毕晓普和倪秉发开始了讨价还价。结果,倪秉发只愿意给这批原来估价16 000元的皮货出价11 000元,毕晓普对此感到失望。不管怎样,双方在7月6日达成了贸易,倪秉发给了13 000元,其中他取回5 000元以缴纳皮货的货税及船料等费用。据说,倪秉发在这桩贸易中毫无赚头,只不过这5 000元的应缴税款他可以拖延到来年农历春节前才上缴,他因而有了一些资金可供周转而已。”*周湘:《清代广州行商倪秉发事迹》,载《中山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如果这段记载属实的话,可以看出,行商向粤海关缴纳的货税及船料费都是由外商支付,并且在买卖货款中已经予以扣除的。而行商之所以会拖欠税款,是因为他们挪用并且无法还账。
事实上,不仅是税饷,即使是在实行“行用(行佣)”制度后,行用似乎也是向外商征收的,而不是由行商自行从其经营利润中提取的。1803年贸易季,当倪秉发就债务问题向东印度公司大班提出申诉时,大班们决定给予他优惠。因为“他们不会任其破产而不给他加以援助,因为他的债务将会落到他的同行身上,而其他行商则藉口增加行佣的征收额。”*[美]马士著、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二卷)》,第710页。
至于官府的索取以及官员的索取,或者是企业的成本开支,或者是对企业主已分配剩余的侵占,从其性质上以及法理依据上而言,并不属于企业的剩余分配本身,但是却构成对企业剩余分配的严重侵蚀,严重时甚至导致企业的倒闭和破产。
在十三行时代,洋行以及洋行商人承受的各种需索到底有多少名目?归纳起来大致上有这么几类:一是船钞、货税类的海关税饷,但这按理只是代外商缴纳,而不是由行商承担;二是海关附加税或称之为陋规性质的缴送、规礼、行用等项;三是多被称之为“常贡”的定时贡纳,或称贡银;四是各种名目的自愿不自愿的捐输;五是官府或官员在前述过程中的各种名目需索;六是不可预料的连带责任摊赔。
实际上,无论是何名目,总体上无非是两大类:一是各种正式、非正式的税、费;二是税费之外的其他需索。在第一类中,不管如何,大体上还是与贸易量、贸易额有关,而且从理论上讲,还多只是“保商”代外商缴纳。真正复杂的是第二类,因为从理论上讲,它们究竟是属于洋行的经营成本,属于洋行资本剩余分配前对洋行收入的扣除,还是剩余分配之后对行商剩余分配额的扣除,或者是对洋行商人个人财产的扣除,实在是难以分辨。但是,它们在理论上却是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
我们现在可以分析的是:
第一,无论是何种名目的常贡、报效、捐纳、摊赔,只要它们不是由洋行商人以个人名义、个人财产支付的,其来源只能是十三行商人的营业收入。
第二,从剩余分配的顺序来看,各种常贡、报效、捐纳、摊赔只要不是行商以洋行资产之外的个人财产支付,那它们就只能是在洋行资本的股息和红利剩余分配之前。这样,如果上述的各项需索加上正常的营业成本已经超过了营业总收入,那么洋行资本的剩余分配就将无法进行,因为企业已经没有了营业盈余。
第三,上述各项需索的制度依据就在于官府给予十三行的经营特许权,或者说是作为特许权的支付对价,只不过是这一对价的金额并不是事先约定或者是固定的,而是完全可以依照特许权给予方的意愿,不定时、不定数的索取。其结果不仅影响十三行资本本身正常的剩余分配,而且甚至会影响十三行的正常经营,其极端的事例就是商行为此而告破产。乾隆四十二年(1777),潘启官在给英商的信中所说的:“为了摆脱贪婪的权贵的掌握,而保存自己和家族,近年来他的支付,远非他的力量所能负担。”*[美]马士著、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二卷)》,第345页。
最后是关于十三行剩余分配的数量问题。从理论上看,一个企业的剩余分配与这个企业的获利能力直接相关。洋行的获利水平,以陈国栋的研究,每担茶叶(100市斤)约可获利白银4-5两。以10万担计年可获利50万两,20万担计,可获利100万两。行商与东印度公司的单纯茶叶贸易大致平均可获16%的利润,但是如果扣除相应从公司购入毛料买卖中的亏损,合计的平均获利率大致上在13%左右。1824-1825年,十三行行商与东印度公司总共成交了总价超过750万银元的21万担茶叶,以13%利润率相计,全体行商大致可获得97.5万元左右的利润。以最获利的茶叶买卖计算,如怡和行这样,要在二三十年间积累起2 600万银元的资产也是匪夷所思的。即每年盈余100万元(各项开销之后),也要26年。而据陈国栋的计算,1824-1825年,怡和行从东印度公司分配到的茶叶贸易额,大致可获利11万两左右。*陈国栋:《清代前期的粤海关与十三行》,第238、241页。而实际上,前述最负盛名的茶叶经营中13%的利润率,也只是扣除直接营业成本后的毛利率。如果扣除员工薪水、店铺开支等等开支,利润率可能还要更低些。如果进一步考虑进洋行在盈利最高的茶叶贸易之外的其他各种贸易,其实际的年营业利润率究竟处在怎么样的一个水平,还是值得认真考虑的。由此而进一步推论,即使是在垄断经营的十三行中,所谓的经营暴利究竟“暴利”到什么程度?这种暴利事实上究竟存在还是不存在?真的还是一个十分值得重新考量的问题。
与剩余分配有关的还有企业的成本开支问题。陈国栋对十三行的开支曾经有过一个比较具体的研究。他认为,行商的营业开支加上家族的生活费,“一个大行商每年大约要支出50 000-60 000元,小行商20 000元,平均约40 000元或30 000两。就这个行商团体而言,一年的支出约为300 000两。”*陈国栋:《清代前期的粤海关与十三行》,第242页。但问题在于,营业开支与生活开支属于完全不同的范畴。而且,如果没有一定财务年度内的总营业额,即使是有开支的估算,我们也很难知道洋行的营业成本以及经营盈余。由此可见,在现有的史料下,要对十三行的剩余分配数额作出哪怕是十分粗浅的估计,都是甚为困难的。
结 论
考察清前期广东十三行的企业制度特征,除了依据史料的发掘、考证,对事件、人物、问题的研究分析之外,基于某些基本理论框架的分析和研究也是可以尝试,并且是十分值得去做的一个方面。从中我们可以大致得出这样几个基本的结论:
一是十三行并不是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体制下,由民间资本、民间贸易自发产生的自主企业组织;而是在清前期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以实现清王朝管制中国与西方商人之间的对外贸易为目的,由清廷及其地方衙门主导、实施的一种特殊的企业制度。在这种企业制度下,与西方商人进行直接贸易的十三行商人及其商人资本,名义上虽然属于民间资本,但实质上却完全处于朝廷、官府以及各级官员的管控之下。从表面上看,是十三行垄断了中国与西方商人的对外贸易;但是在它的背后,却是朝廷与官府垄断着十三行。
二是在清前期广东十三行的企业制度中,传统的家族势力发挥着极大的作用。清前期的广东十三行商人,从其出身和来源上看,有相当部分并不是土著的广东人,而是外来的福建人。这些外来的福建人在到了广东之后,往往要经过相当一段时期的努力和经营,在自身和家族的生意及其商业声望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才有可能充任十三行商人。在这里,把这些福建商人推上广东十三行商人宝座的,不仅有直接充任十三行商人本人自身的努力和经营,而且还有其背后支撑和支持的家族团队的力量和努力。前述十三行开办之时,官府看中的首先不是“资本殷实”而是“身家殷实”;行商经营中企业资产与家庭财产的“家、产不分”;陈国栋关于十三行开支研究中,将行商的营业开支加上家族生活费的例证;而益行行东登记于石中和名下,而真正的经营者却是被外商称之为“鲸官”的石梦鲸;以及所谓“同文行是家族的生意”等等。这些印证的都是十三行形成以及经营过程中鲜明的家族色彩。对于整个广州商界以及朝廷和官府来说,十三行都不仅仅只是意味着一个商人、一个商号,而更是一个商业团体、一个商业家族。由此可以进一步启示我们的是,即使到了近代社会,当西方企业制度传入中国之后,在近代中国的民营企业中,发展最早、最快的,往往也是诸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这样的家族型企业。
三是在十三行的企业制度演变以及企业的盛衰存废中,基于传统社会不完全私有产权基础上的无限连带责任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传统社会的企业制度中,无限责任以及基于无限责任的连带赔偿是企业制度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内容。但是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十三行把传统社会的这一无限连带赔偿责任推到了极致。在完全的私有产权制度下,无限连带责任的主体最多也只能是与企业的产权、债权,以及经营事宜有关的民事主体。但是在十三行的无限连带责任中,凡是与行商有血缘、亲属关系的主体似乎都可以成为最终的无限连带责任者,这实际上已经完全超出了通常的一般民商责任,而是传统中国社会自秦汉以来就有的、地地道道的由血缘、亲属关系派生的财产“连坐”制度。从朝廷以及官府的层面看,这种基于血缘、亲属的财产“连坐”,可以保证行商债务的无限追索,以及官府垫付债务的有效收回;但是从根本上看,它们意味的却是传统社会中国家凭借公有权力对私有产权以及私有财产的一种强权性质的侵蚀。
作者张忠民: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上海:200020)
The system of the Thirteen Hongs of Guangdong was not an independent business organization developed from non-governmental capital and trade under market economy and free trade system. It was a special entrepreneurial system dominated by the Qing Court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that managed the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Although traditional family business played a great part in such a system, the Thirteen Hongs was a trade group or business family for the business sector and the government of Guangdong, rather than merely representing a merchant or a firm. This article provides an intensive study of the entrepreneurial system by analyzing property right, management structure and residual dividend, which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research on the Thirteen Hongs of Guangdong.
the Thirteen Hongs of Guangdong; Entrepreneurial Property Right; Corporate Management Structure; Residual Dividend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企业制度的生成与演变研究”(项目批准号:14ZDB046)中间成果。2016年10月“粤海关与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