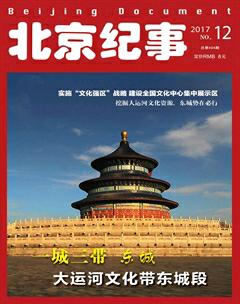上苑村:探寻北京原生态艺术村落
於俊杰
“注”在上苑
上苑村,地理上出了北京北六环,地图上高高地挂在市区“外面”,并不起眼。但是那里居住着一群艺术家,就变成了艺术村。我与好友约定一游,于是便真的去了。
此行的初衷,是参加一个叫作“注”的互动行为艺术项目,也就是自己带上一瓶水,倒进一个干涸的水库里。
我们早早地出发。地铁坐到天通苑北,出来又坐了约莫19站公交,穿过汽车搅动起的滚滚黄尘,经过熙熙攘攘的草莓采摘园,在上苑村外的桥头下了车。有一个身穿极长的花毛衣和极度宽松大裤子、留着小平头的小伙子在那里等着,这就是活动的发起人高大蔷。我与他的认识是在单位组织的一次活动里,我们去他们那里调研,了解情况,他们讲述自己作为“体制外”艺术家的生活状况。在那次活动里我知道这个“注水”项目,我对自己说:有点意思!于是暗暗下决心要自己来“注”一次。有点什么“意思”呢?其实我那时也不能确知。
他只比我们大几岁,算是同龄人,背着个灰色发旧的小单肩包,甩开大裤子,领我们慢慢往一个坡上走。坡的尽头是一排铁栏杆,栏杆的下面是一个广阔辽远的深坑,这就是那水库。现在里面一滴水也没有,长满了杂草,是个“草库”。我—下子想起了北大鸣鹤园北边一直到荷花池的一带,做学生的时候常去溜达,分明是“池”“湖”之类的名字,却也只是一片荒草地而已。近来听说已经有水把它们注满了,金鱼池有了金鱼,荷花池有了荷花,于是一定有更多的生命得以存活。水是一切生命的维系,有水的地方总是美好的。
朋友与我把拿着瓶子的手伸进铁栏杆,倾倒下两瓶不远“万里”带去的水,完成了一个小小心愿。他的水来自安徽,我的水来自广东。注水活动到此结束。我们三个“访客”要离开吗?要登上周围的山头眺望吗?要搜索周围的其他风景么?不,不,我们要下去,到艺术村里去走一遭。
走入艺术村
“艺术村”的意思就是:村还是那个村,只是比较艺术。走进村里,平庸的北方乡村格局之中,散布着一些院落,被作为艺术家的居所;在黄土和灰尘之中,隔三岔五出现一些别样的小房子,里面放着别致的创作。不少空间都被用来作为展览,有的展览很小,三五幅画往墙上一挂;有的展览很大,占据了整个高大的屋子。艺术家的家基本上也就是他们的工作室,艺术家基本上睡在自己的画旁边。总而言之,在这里,生活和艺术并不分离,总是一起从被观察到被欣赏。
高大薔领我们到了他的住处。推开大铁门,里面是一个长方形20平米左右的露天小院子,当中搁了张桌子,桌下堆着些砖头瓦片,桌上倒扣着一个大簸箕,往里横放着辆大摩托车,最里头是一藤茂盛的葡萄,还有厕所。院里随意地斜着个金色的画框,有只黑白两色的猫在房顶的角落里探头探脑。
院子的左右两侧,分别住着两位画家。一位是高大蔷,一位是郑大哥。
听见有外人的声音,郑大哥从屋门探出半个身子。他身穿的不知是什么年代哪个流派的土黄色军服,级别资历的条纹章赫然贴在胸前。他戏称其为“工作服”。屋里靠墙全部摆放着油画,写实的油画。他喜欢用革命年代的物件作为意象,不同的物件并置,往往取得诙谐幽默又让人思考的效果。就像博物馆所做的一样,这些画力求挖掘“物”的意义。比如一本“毛选”、一个搪瓷盆,放在展柜里,画在画布上,就不光是一个用来使用的物件。有一幅画,大红色的背景中,是一个生锈掉漆的老式暖水壶;我后来在网上查到,那幅画叫《火热的心》,既是那个年代也是那群人,名副其实。他使用革命年代的意象,并不是要讽刺或者反对什么。
我心里清楚,对于要时常出去“走动”的人,有个明媚的下午能自由作画,实在不容易。我们没有继续打扰,走出了他的工作室。
对门高大蔷的房间,一个角落里,全是之前参加注水活动留下的瓶子。五颜六色的瓶盖立在一起,像一片郁金香。我们的两个瓶子有幸加入其中。在我自己的瓶子上,我挑了句海子的诗写了_上去:“水……水/我有了养育的愿望。”在另一首长诗中,海子写道:“水,水……/我就是一潭高大的水,立在这里,立在这里。”倒是与这活动很贴切。有人问我,大老远跑去倒一瓶水有何意义?而且水库早已经干了。其实,天南海北的人带来了天南海北的水和对于水的希望,还有友谊,以及付出的时间,这个活动已经获得了意义。如果套用海子的一句诗来说,就是正因为已经没有水,我们才更加渴望,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说起“春暖花开”,不得不朝这个房间的另一头望去。在墙壁上赫然写着几句话,说明了此前进行的另一个行为艺术项目。这几句话是:“从2015年入冬到2016年春天,在空间内不采取供暖措施,通过本人和朋友们聊天、喝茶、吃饭、居住等等日常生活方式取暖,使室内温度保持在0摄氏度以上,即让一碗水不结冰(在实施过程中,如水结冰,即行为失败)。”落款是“2015年冬-2016年春”。这个活动的题目叫作:让这个冬天不再寒冷。我所知道的是,这里的艺术家在冬天大多靠往炉子里添蜂窝煤取暖,就像我们小时候那样。从前我自己租下的小房间,到了冬天便有室外的寒风从门缝中挤进来,苍白的手上,紫红色的血管非常清晰,如果洗过几件衣服,则整只手是红色的。这里艺术家的工作室往往很宽敞,但是在冬天,我猜也容易成为北风的跑马场吧。我想起在什么书上,写到莫扎特一家冬天没有煤的时候靠跳舞取暖。没有优越的条件,只有安宁的创作,这是属于他们的寒冷。
此刻已是阳春四月,我们四个人坐在软沙发上喝茶,喝椰子汁,并不会感到寒意。屋里还有几幅大油画,鲜明的色彩,表现的意味,内容有些是幽默的。另有一些小画,充满了形式美,虽然我不知道表达的观念是什么。还有几块涂黑的木板,有些已经被刻成了小幅的版画。坐了挺久,我们走出来,继续往村子深处探寻。 endprint
endprint
有个挺大的房子,里面摆满了作品,这个展览叫作《伤口》。在我看来是叫作“孕育”(我是多么喜爱这个词),其中的创作全部是关于孕育一个小生命的,那个小生命就是作者和他妻子的孩子。我们谁都知道孕育的过程有伤与痛,但是这一次的孕育带来的是独特的“这一个”的个人体验,而这些作品则是这种体验的准确凝结。作者本人在一个展览介绍里说:“此次妻子怀孕,从最初的温馨渴望到临盆时与医护间的激烈交锋,无疑是这些伤口中最痛和最新鲜的。”他把这种体验用这个词归纳了:伤口。他画在粗粝砖石上的孕妇,仿佛若有所思的圣贤;那些描绘出的孩子的脸,展示的是爱和生命力;墙上挂着的医院文件“现成品”,讲述着这个孕育故事里最为艰辛不易的部分。这使得整个空间里有了种宗教感。孕育和成长总是不易的
从生命的伤口里走出来,从哇哇哭泣中走出来,终归是要走向慈悲和爱,这是神圣天父给我们每个凡庸生灵早已指明的道路。只不过有的人安然地这样走着,有的人迷失在荒野之中。
这个展览的场地,是画家黑子建的一所房子,用来给一些画家免费使用。出了这个“伤口”的门,黑子的工作室就在那个院里,我们顺便溜达进去。黑子是个健硕的男人,浓须光头,悠然坐在舒服的沙发里,一旁有只油亮的黑狗,转动着友善的小眼睛。墙上多是小幅的油画,某院某落、大树花草、节日秧歌等等,满满的本地乡村风土。笔触鲜明、干净利落、生气勃勃。黑子指着那些画说:这是谁家,是哪里,这儿的人一看都知道。热爱生活的画家们总不会对眼前的事物无动于衷的。他的门外,落满了玉兰的花瓣,许多年轻艺术家聚在一起,正聊得海阔天空。
在另一处,我们刚巧遇见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妇,是当地的“素人”艺术家。他们多年前只是本地的村民,受到来此的艺术家熏染,也变成了艺术家,但未经那“科班”的训练,作品里仍保留着质朴独特的乡土风格。挪开竹编的篱笆门,我们进到他们屋里,四周都是画,中间有些泥塑。男主人的油画里经常出现拖拉机和毛驴,女主人的油画主题则常是花草。她告诉我们,上世纪80年代,他们经常开拖拉机跑业务。说及此事,她红润的脸上流露出喜悦自豪的神情,给我们感到那个年代一定是十分浪漫的。在一个架子上,有他们的小型泥塑,基本全是松鼠、鸭子、毛驴之类的动物。对于农民出身的他们,绘画是另一种形式的养育和耕种,收获的却是同样的快乐。
一个“疯子”的热情与执着
我们在出村的路上,经过了一栋灰色的建筑。建筑大约三四层,远看像一个装修未成的宾馆。门前几个工人在修两堵弯弯曲曲的红砖墙,几堆沙子摊在外面,一条狗在里面朗声吠叫,到处都是细细的尘土。高大蔷告诉我们,建筑的主人是个从文化部退休的老先生,画油画。
说谁到谁就到。我们一抬头,房子主人就在不远处。瞧吧!一个瘦长的男子,上衣和裤脚上尽是灰土,脑前的头发被风刮得高高地竖起,像一顶半圆形的冠冕,手拎一袋刚去壳的红皮花生,轻快地向这边走来。他是60多岁的人,却迈着40多岁的步子,印象中“画油画的老先生”并不应该是这样。我们称呼他“万老师”,虽然我终究不知道他的准确名字。我惊讶地看到这个人怀着不知哪里来的自信和豪迈、敏捷和力量,一把拉开大门,伸直手臂朝内一指,对我们这群访客大声说道:“你们看看这个吧!”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看到一个空荡荡的大厅,当中有一幅大油画。不,应该说是巨大的油画,40多米长,7米多高,巍然矗立在无比宽敞的厅堂之中。画的整体调子是蓝灰色,上面密密麻麻“挤”满了人。那些人物,不是帝王将相,不是英雄豪杰,而是朴实的农民兄弟。农民在干什么?在买卖牛。改革开放了,买卖自由了,农民出来赶集,这幅画表现的就是那个时代的那个特殊的历史瞬间。
长卷一样的画幅上,正中间许多青黑色的水牛稀疏地排成一个近乎三角的形状,承担了画面大部分的重量感,几头黄牛点缀其间,像春天草地上的黄花。两边,几百个牵牛挑担的赶集者挤在一起,各人有各人的动态,各自有各自的心事
疏朗处三五成群做着南国水乡的农活,密集处几十个人头聚在一起,好像田间开着大会。远处,古旧的、灰色的、朦胧的,静静地往地平线退去的,是一些典型的乡村景观,仿佛是过去的年岁,既富于莫名的诗意,也含着衰败的惆怅。我震惊了,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种不以灿烂辉煌得来的盛大,不以战争或英雄主题得来的壮阔。或许因为我眼前的并不是一幅画,而是一张老照片,是一首交响曲,是一个个体对一个年代以及在那之前的所有年代的记忆和情感,是一个关于南方农村和农民的博物馆。
这幅画远远没有完成,我们看到的只是它生成过程的一个片断。在这个三层高的灰色建筑里,到处摆着万老师精彩的创作。这儿是属于他自己的世界。我不禁心里问道:是怎样的创作热情和精力付出,让铺展这些画面成为可能?答案很简单:这些画都是他在文化部工作期间“抽空儿”画出来的。“别人在玩的时候我在画画,别人在睡觉的时候我也在画画”这就是他所谓的“抽空儿”。他把时间从日常生活手中抢下来,铸造在一幅幅的画面上。我能想象,多少个周末、假日他是在画中度过的,多少次在这个大都市尚未苏醒的清晨,他执笔继续着未完的创作。在这份努力之外,最可宝贵的,是做了“领导”以后,在别人不想画画的时候他还心心念念想着画画,而且非要倾其所有,画出精品来。他说:“我是个画家,如果不画画了,我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作为一个同样寄存在“体制内”的人,我感到十分惭愧。万老师坦言,将来的事情不可知,我只要好好完成这幅画,并把这画留下来。
谈话中,万老师屡屡自称为“疯子”。是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样看来,他确乎有点“疯”,不是么?
“外”与“内”
显然,比起我在这里看到的,我没有看到的还有更多。我去过798,去过宋庄,去过大芬村,但只有在这里,我才感到远离尘嚣和世俗庸碌的清净安宁,才看到这样一群安分守己、默默耕耘的艺术家,体会到他们为了艺术突破而辛苦劳作的耐心和勇气。所有的耕耘活动都像是一场赌博,因为你不能知道确切的结果。他们是真正的“农人”,他们耕种和收获的,是比草莓更加深沉的东西。而对于我们这群外人来说,到此收获的,也是比草莓更加滋润人心的营养。
但当我们深入察看“农人”的生存环境时,不得不承认这里的生活并不是阿尔卡迪亚式的诗意栖居。且莫说“栖居”,日渐上涨的房价、郊区农村的开发,尤其是艺术家“外来者”的身份,使得“定居”一词都有点成了一厢情愿。是的,他們就是一群外来者。对于中心、主流、体制,还有这个城市来说,都是外来者。好像只有对于“艺术”这块土地,他们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外来者聚拢在北京这个“里面”之中。对朝向“中心”聚拢的外来者而言,他们在“里面”选择的方式,是不断逃避咄咄发展着的大城市而在郊野形成“边缘文化”,不断突破人与自然、人与人的隔膜,寻求与自然万物和自我心灵的亲近。这不完全是为了逃避,只是一粒饱含深情的种子不能落在没有湿润泥土的地方,它总要寻找一个既能“格物”也能“修心”的处所。
同时,经历几次的“走马观花”,我不得不思索,自命为城市居民的我们,这些“里面”的人们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去体察和触碰一个艺术聚居地和一群自由的艺术家
是像一群置身事外参观风景的游客?像一群购买纪念品的逛街者?像一群到郊区采摘乡村风味的城里人?还是像一群参观动物园的猎奇家?我们总是沉默地选择着一种“里边”人的姿态,来消费都市边缘的这场“风景”,并且随后在忙碌琐碎的日常里把它遗忘。
除了具象的艺术作品,我们还应该看到一种新的生存方式一并非出于某个潮流鼓吹的生存方式。它的终极目的就是不受打扰、自在生长,它要张扬生命中自带的伟大创造力。正是这样的原因,不管对于“外边”还是“里面”的人,这里都像一个“精神驿站”
住在里面的“外来者”背负了艺术在流浪中间歇,从外边走入的“里边”的人暂时搁下“社会人”的负担而得以喘息。因此,再“边缘”的艺术聚居都不应该走得太远,它是我们生命行旅中必经的部分。它教会我们时不常地侧耳倾听内心轻快的马蹄声,丢弃透析外物的固有眼光;同时,把对“诗意地栖居”的心理渴望,化作“诗艺地栖居”的行动力。
(编辑·韩旭)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