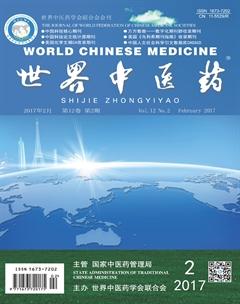不同时期脏腑辨证理论内涵差异初探
任北大 张保春
摘要 目的:明晰不同时期医家对脏腑辨证理论的发挥,完善脏腑辨证理论,并对临床诊治提供新的思路。方法:通过文献分析和差异比较法,对脏腑辨证理论在历史源流与内涵传承及创新两方面,分别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总结、分析。结果:自《黄帝内经》始,脏腑辨证经《中藏经》《备急千金要方》《小儿药证直诀》发挥,尤其是张元素《医学启源》对脏腑辨证理论进行了更为系统和全面的总结后,形成理法方药完备的脏腑辨证论治体系。结论:脏腑辨证理论体系的建立对后世易水学派、温补学派及扶阳学派各医家关于脏腑辨证理论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关键词 脏腑辨证理论; @ 张元素;医学启源;易水学派
Abstract Objective:This paper is to summarize understandings o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in terms of zang-fu pathological changes theory from physicians in different periods,so as to improve the theory and provide new prospects for clinical practice.Methods:By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difference comparison,this paper is to summarize and explore historical source,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Zang-fu orga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theory horizontally and vertically.Results:Dating from Huangdi′s Canon of Medicine,the theory of Zang-fu orga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developed in Treasured Classic,Invaluable Formulas for Emergencies,and Key to the Therapeutics of Children′s Diseases,especially Zhang Yuansu summed up the theory systematically and comprehensively based on his acquisition from Medicine Origin,forming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theory according to zang-fu pathological changes in principles,strategies,formulas and medicinals.Conclusion: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Zang-fu orga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makes great influence to the formation of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theory according to zang-fu pathological changes in later Yishui shcool,warm-recuperation school,strengthening-yang school and other physicians and schools.
Key Words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ccording to zang-fu pathological changes theory; @ Zhang Yuansu; Medicine Origin; Yishui school
中图分类号:R223.1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3-7202.2017.02.010
张元素,字洁古,金代易州(今河北易县)人,生卒年不详,据今人考证,张元素出生于金太宗七年(公元1129年)[1],易水学派创始人,温补学派奠基者。其学术思想主要源于《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中藏经》《小儿药证直诀》等经典古籍,张元素撷取前人精华,又通过自身临床实践经验,选择对中医学术理论有重大贡献的脏腑辨证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并系统总结,最终形成理法方药完备的脏腑辨证体系,为易水学派学术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脏腑辨证作为中医辨证理论的核心,金元之前,不乏医家、学者的研究,然或杂乱无序;或缺乏临证评判;或受当时医学知识所限,对脏腑辨证理论认識皆有不足之处,及至张元素,在前人启发和影响下,结合自身大胆创新,将其所首创的遣方制药理论与脏腑辨证联系起来,弥补了金元以前诸家对脏腑辨证论述所存在的缺陷,不仅在当时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对后世医家也有较高的临床参考价值。本文从深度和广度上对脏腑辨证理论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挖掘,力求揭示脏腑辨证内在规律和特征,以及其对临床诊治所产生的影响。
1 理论源流
脏腑辨证起源于《内经》,在《金匮要略》有所发展,此时脏腑辨证尚处于萌芽状态;《中藏经》标志脏腑辨证体系形成,为第一次系统总结,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备急千金要方》对脏腑辨证向脏腑证治转变、形成起到重大推动作用,为脏腑辨证第2次系统总结;《小儿药证直诀》在脏腑辨证理论上侧重儿科五脏辨证,并立五脏补泻方,完善了脏腑辨证体系;及至张元素·《医学启源》,形成理法方药完备的脏腑辨证体系,更加全面、系统,为脏腑辨证第3次系统总结,同时成为宋金之后脏腑病机制论的先导;至此,脏腑辨证体系基本完善,对当时乃至后世医家都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2 内涵差异
唯物辨证法认为:世界是永恒发展的,要把事物看成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明确其在发展过程中所处的阶段和地位,才能深刻理解事物本质并加以创新;同时,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也是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脏腑辨证理论形成、发展及成熟,符合人们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故从以下几方面对脏腑辨证理论内在规律及特征进行系统和全面的挖掘。
2.1 理论孕育形成阶段
2.1.1 《内经》 《内经》是秦汉以前医学成就的全面总结,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渊薮,包括藏象学说、病机学说、诊法学说和治则学说四大部分,藏象作为学说即导源于此。全书从内容分布上来看:脏腑论述见于金匮真言论篇第四、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六节藏象论第九、五脏生成篇第十、五脏别论第十一;五脏病机论述见于脏气法时论篇第二十二、至真要大论篇第七十四、本神第八;六腑病机论述见于邪气脏腑病形第四、师传第二十九;奇恒之腑论述见于平热病论篇第三十三、水胀第五十七。从内容来看,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脏腑论述以“天人相应”和“阴阳五行”理论为基础,形成以五脏为中心,内连六腑、五体、五华、五声、五窍、五志等,外应五方、五时、五味、五畜、五谷、五星、五音、五臭的五个功能活动系统并在生理、病理上紧密联系。2)脏腑病机尤重气:《内经》中提到气有3 000余处,其中气的种类接近300种。3)在诊治上强调脉色合参及利用五味和五脏制化关系。综上,脏腑学说在《内经》内容丰富、分布广泛,起到了基础理论的作用;但同时也说明其零散、不成系统,对临床辨证施治指导作用有限。
2.1.2 《中藏经》 相比《内经》《中藏经》创新之处在于:首创脏腑辨证之八纲,即虚实寒热生死逆顺,将《内经》零散、不成系统的脏腑学说内容首次进行系统归纳总结,如关于心之论述,《灵枢·本神第八》:“心怵惕思虑则伤神,神伤则恐惧自失,破腘脱肉,毛悴色夭,死于冬”;“心藏脉,脉舍神,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2]《灵枢·淫邪发梦第四十三》:“心气盛则梦善笑恐畏”;“厥气客于心,则梦见丘山烟火;”[2]85两处从心气之虚、实、梦及脉等病理方面进行了简单阐述,《内经》中关于心之论述不胜枚举,仅从这两处亦可看出内容分布杂乱不成体系;而在《中藏经》关于心之论述则集中体现在《论心脏虚实寒热生死逆顺脉证之法第二十四》一节当中,其所论述不仅包含《内经》中关于心的论述内容,而且更加深入全面,如关于心之脉的论述,就有太过、不及、浮大而散、沉而滑、弦而长、缓而大、左手寸口脉大甚与肿甚、沉小而紧、其缓甚、微缓、大甚、微大、小甚、微小、滑甚、微滑、涩甚、微涩、搏坚而长、软而散、急甚、沉濡而滑等二十多种脉象,并均有相应生理病理表现;关于心气虚实的论述,有“心气实则小便不利,腹满,身热而重,温温欲吐……”,“心虚则恐惧多惊,忧思不乐,胸腹中苦痛……”[3];其中详简一目了然。此外《中藏经》还对心之病理症状进行了具体的论述。这标志着中医脏腑辨证体系的初步形成。
2.2 理论完善发展阶段
2.2.1 《备急千金要方》 自《中藏经》之后,脏腑辨证经过《脉经》《诸病源候论》等著作的发挥,于《备急千金要方》实现了第二次全面系统总结。较之《中藏经》,《备急千金要方》发挥之处有以下几点:1)内容不局限于理、法,补充了方证内容:脏证腑证皆以虚实为纲,并列有对治的方剂;脏腑证皆有相对应的特异性脉象,是判断脏腑证病位与病性的依据;此外,扩展了脏腑病理内容,增加了脏腑经络循行内容,对判断脏腑病变部位与性质开拓了新的思路。2)对脏腑生理、病理及诊治认识更加深刻,且论述更加系统:《备急千金要方》在内容上基本包含了《中藏经》关于脏腑生理、病理的全部论述,并在论述上更加详细;在论述上脏与腑皆从生理至病理至脏证腑证论治,且腑从属于脏,表里对应之脏腑证列于脏卷之中。综上,每一脏、腑自成体系,内容上全面、详细,论述上调理、系统。如《备急千金要方》关于心脏论述,开头生理“论曰:心主神。神者,五脏专精之本也……”[4],篇幅长于《中藏经》,且内容详实;其次病理“凡心脏象火……”四十五种病理现象,较《中藏经》十七种更为全面;此外,增加了五脏经络循行内容“其筋起于小指之上…手少阴之脉起于心中…”[4];最后在辨证论治方面以虚实为纲,分为心实热、心小肠俱实、心虚寒、心小肠俱虚四类,每类又分以不同证候,不同证候下又列以对应方剂。
2.2.2 《小儿药证直诀》 《小儿药证直诀》是脏腑辨证在儿科领域的首次重大突破,对小儿生理、病理、五脏证治及适用范围做了简明扼要的概括。钱乙认为:小儿在生理上“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病理上“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成为其临证指导思想,并系统提出儿科领域的五脏虚实辨证理论,即辨证以“五脏为纲”,分列心、肝、脾、肺、肾五脏虚实的主要证候、治疗原则及处方用药,同时又认为五脏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五脏与自然界关系密切。以心为例:其主要证候为“心主惊。实则叫哭发热,饮水而搐,虚则卧而悸动不安”。“心病,多叫哭惊悸,手足动摇,发热饮水”[5];具体而言“心热,视其睡,口中气温,或合面睡,及上窜咬牙,皆心热也,导赤散主之”。“心实,心气实则气上下行涩,合卧则气不得通,故喜仰卧,则气得上下通也。泻心汤主之”[5]。通过统计涉及心之病种有目内证、心疳、惊啼、羊痫等13种,肝12种,脾胃28种,肺14种,肾13种,此外书中单列“五脏相胜轻重”一节,首次将五行生克运用于临床实际辨证当中,亦是此书一大发挥。
2.3 理论完备成熟阶段 《医学启源》以虚实寒热为辨证的基本纲要,以补虚、泻实、温寒、清热为基本治则。在具体内容上,张元素关于“五脏六腑,除心包络十一经脉证法”论述基本与《中藏经》一致,部分细节上仍略有出入,如同样关于心的论述,《中藏经》认为“心气实则小便不利”“诊其脉,左右寸口两虚而微者是也”“心脉沉小而紧,浮主气喘……微大则心痛引背、善泪出……”[3];《医学启源》则认为“心气实则大便不利”“其脉左寸口虚而微者是也”“心脉沉小而紧,浮之不喘……缓甚则痛引背,善泪……”[6];正所谓于细微处见真知,内容上张元素确有其发挥之处,脏腑辨证不同论述之间应引起重视,多加以比较。张元素依据《内经》《脉诀》补充以《主治备要》,增加了脏腑病机:五脏是动病、所生病;五脏治疗:五脏苦欲补泻及用药、虚实寒热之治则和处方用药。这就较《中藏经》《備急千金要方》之论述更为全面和精细,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脏腑辨证理论,而其中药物归经和引经报使之用药理论又是张元素对脏腑辨证理论的最大创新,为药物与脏腑、经络之间的对应关系指明了方向,使具体药物与脏腑证、经络之间的对治关系愈发明晰[7]。如其在《医学启源·去脏腑之火》中对泻火药所论述“黄连泻心火,黄芩泻肺火,白芍药泻肝火,知母泻肾火,木通泻小肠火,黄芩泻大肠火,石膏泻胃火。柴胡泻三焦火,须用黄芩佐之;柴胡泻肝火,须用黄连佐之,胆经亦然。黄柏泻膀胱火……”[6]在《医学启源·各经引用》中对引经药论述“太阳经,羌活;在下者黄柏,小肠、膀胱也。少阳经,柴胡;在下者青皮,胆、三焦也……以上十二经之的药也”[6]。临床上治疗过敏性鼻炎,除以阳虚为基本病机辨治,若以脏腑辨证定位病变脏腑,加之引经报使药,治疗效果极佳[8]。此外,张元素在《医学启源》中提出特色制方遣药理论:首创气味厚薄寒热阴阳升降之图,明确药物气味阴阳升降与功效关系;脏气法时补泻法,在《内经》五脏苦欲补泻理论基础上结合五脏苦欲药物,很好的补充了五脏证治缺少经验药物的弊端;三感之病与三才治法及制方法度等理论,这些都为临证指导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元素脏腑辨证之各部分内容较为平衡,未有偏颇,利于为后来者在此基础上继续发挥[9]。近人曾评价“元素在脏腑辨证方面的发挥较孙思邈的脏腑虚实辨证、钱乙的五脏虚实辨证都要系统和精细得多”[10]。
3 讨论
脏腑辨证是中医辨证理论的核心,其形成与发展符合中医理论自我完善的规律,在临床诊治中居于基础地位。张家锡认为:“脏腑是临床病证定位的主要依据,是其他辨证方法的基础。同时,因其概念确切、内容具体、纲目清楚、系统完整等特点,更易切合临床特点,因而为中医的内外妇儿等科普遍采用”[11]。如以五脏为框架论治慢性荨麻疹,切合临床辨证,指导意义较大。金元时期张元素为脏腑辨证体系之集大成者,并发前人未有之论述,将脏腑辨证理论提高到新的高度。在脏腑辨证具体差异比较中,本文以心为例,其在《内经》分布多零散、不成系统;在《中藏经》中理法皆备,形成体系;《备急千金要方》增加方证、经络等内容,更加详实、系统;而《小儿药证直诀》则是对脏腑辨证在儿科的一大发挥,且选方精确,疗效显著;及至张元素《医学启源》,理法方药皆备,理论系统完善,可言此为第一次真正之脏腑辨证理论体系,后世之发展亦在此基础之上而论。至此,脏腑辨证由系统研究阶段转入专题研究阶段,代表学说有易水学派之脾胃学说、温补学派及扶阳学派之肾命学说,理论研究与临证更加紧密,而且针对性更强。本文从纵、横2个方面论述脏腑辨证之源流,初探不同时期、不同医家关于脏腑辨证论述之差异,从而明晰脏腑辨证发展的时代背景及理论内涵,以期对现代中医发展起到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吴昊天,张保春.易水学派医家张元素生平补正[J].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14,38(3):263-265.
[2]居敬堂.灵枢经[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6:24,85.
[3](汉)华佗著,谭春雨整理.中藏经[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23,21-23.
[4]孙思邈,高文柱,沈澍农校注.中医必读百部名著备急千金要方[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245,248.
[5]钱乙,阎孝忠,编缉.郭君双整理.小儿药证直诀[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2-3,5.
[6]张元素.医学启源[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7-8,90,91.
[7]谷建军,庄乾竹.中医脏腑辨证的形成与发展源流[J].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2011,6(5):372-374.
[8]张静,张亚男,张纾难.张纾难教授治疗过敏性鼻炎经验[J].世界中医药,2014,9(3):345-346.
[9]刘瑞鑫.浅表易水学派脏腑辨证学说的发展传承[J].现代养生,2016(4):66-67.
[10]张元素,任应秋点校.医学启源[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8:3.
[11]张家锡.脏腑辨证的地位和规律探讨[J].四川中醫,2002,20(1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