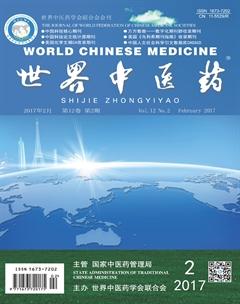探求经方体系药量原貌,建立经方药量国际标准
摘要 经方被历代医家所推崇,是治疗急症、重症及疑难杂症的有效方法。然而,目前国内中医医院能用中医治疗急症、重症的很少,多为中西医结合,不能突出中医治疗急症、重症的特色。虽原因多种,但其最主要的原因是:经方的药物用量问题。有鉴于此,笔者结合自己学习中医药及临证40余年体会,提出要发挥中医药治疗急症、重症及疑难杂症的特色,探求经方体系药量的原貌,建立经方药物用量的国际标准。结论:适宜的剂量是中医经方临床疗效尤其治疗一些危急重症获得可靠疗效的保证。现今中国中医药药典对于中医饮片临床使用剂量的限定严重限制了中医经方的合理有效使用,应当予以研究进行切合临床实际的调整,才能有助于促进中医经方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 经方药量;国际标准
Abstract Classical formulae are regarded as the effective method to treat the acute,severe and complex diseases.But nowadays,Chinese medicine practioners seldom use Chinese medicine classical formulae to treat the acute and severe diseases.Most of the cases were treated with integrated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which covers Chinese medicine′s advantages in treating acute and severe diseases.Among the many reasons,the most prominent one is the dosage.Therefore,the author put up the issue of utili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medicine to treat acute,severe and complex diseases,to explore the original dosages of the “classical formulae” system and thus establish an international standard for classical formula dosages,based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medicine with over 40 years of clinical experience.Conclusion:Appropriate dosage is the way to get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of Chinese medicine especially for severe and acute diseases.Nowadays,in China′s Chinese medicine pharmacopoeia,the limitation on dose used in clinical practice has greatly restricted the reasonable and effective use of Chinese medicine.Therefore,adjusting dose according to clinical circumstances can make way for Chinese medicine′s healthy development.
Key Words Classical formula dosag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中圖分类号:R289.5文献标识码:Bdoi:10.3969/j.issn.1673-7202.2017.02.034
近年来网络平台发展迅速,笔者亦经常通过信箱或微信为国内的亲朋好友开方。常遇到“量太大,药房不给抓药”“需要红处方”等情况,反复思之而执己一得,遂成下文。是否得当,望同道赐教。
1 古今经方药量的换算及当今应用状况
1.1 古今经方药量的换算 目前我国对古今度量单位换算说法不一,比较权威的有以下几种:高等医学院校中医教材《方剂学》在“古今药量考证”一节中说:汉代“一两约合现代的9 g(三钱),一尺约合六寸九分,一斗约合二升,一升水约合二合(200 mL)”。又说:“古方一剂等于现在的三剂药,如直接折算,可按一两约合3 g(一钱)计算”[1]。中医研究院编《伤寒论语译》《金匮要略语译》云:秦汉一两为今之6.69 g。江苏新医学院编经方药量附篇《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以下简称《药典》)据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3]记载谓东汉一两折为今13.92 g。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国家计量总局编《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均记载汉代一两为今之15.6 g。1981年我国考古发现汉代度量衡器“权”,并以此推出古方剂量,汉代一两为今之15.625 g,一斤为250 g。
1.2 当今应用经方药量的状况 近年研究经方药量的学者不少,仅举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研究生论文,就有不同的研究结果。首先该校博士郭明章的《仲景方用药剂量古今折算及配伍比例的研究》,属于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医药项目课题的一部分。研究方法及操作技术:1)应用问卷调查法以完善研究方案;2)应用文献研究对历代医家的观点和东汉度量衡[4]进行考证,并对相关药物的古今差异进行了全面考证,为实物测量药物的选取提供依据;3)通过实物测量对仲景方中非重量计量单位的药物剂量进行研究;4)在以上各研究方法中结合统计学方法进行综合研究;5)建立仲景方基础数据库和设计相应统计软件以方便对仲景方用药剂量折算和配伍比例做进一步分析研究[5]。研究考证的结果:支持李时珍的“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的折算观点。再就是该校硕士仇菲的《以中医经验文献挖掘分析为基础的经方临床用量策略研究》方法及结果:通过近10年中医经验文献研究、验案的分析以及导师仝小林教授在临床应用经方时个性化的验案总结,得出临床用之有效的用量策略。对经方本源剂量1两约等于15 g加以肯定。笔者同意后者的研究结论。
诚然,药量是影响临床疗效的关键所在,如何用量成为众多医者关心的话题。现实情况是,能采用经方药量者只是少数医家。擅用经方的老前辈年事已高,多在80岁以上,且逐年减少,中医经方应用现状令人担忧。有学者认为:“不少中医大学生走出校门后就对中医丧失信心而改从西医。青年中医不敢用经方,用西医的观点套用中药,见急症、重症避之唯恐不及。大部分中医院放弃了急症阵地,连中医研究院的病床上也吊滿了输液瓶”[6]。凡此种种,令人触目惊心。笔者认为:上诉状况非青年中医之过也。正如《思考中医》[7]的作者刘力红所说:“你按东汉的剂量治好一千个人没你的事,但只要有一个人出了问题,那你吃不了兜着走,你就要变胡万林。为什么呢?因为药典不支持你,你没有法律依据”。所以笔者认为,只有从完善和修订药典入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建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世界中联等单位组织中医药专家、学者,根据经典理论和临证经验立项研究,修改教材和《药典》之药量标准。此乃当务之急,也是我们继承、发扬经典学说的最重要环节。
以麻黄汤为例:《伤寒论》麻黄去节3两、桂枝2两、杏仁去皮尖70个、甘草炙1两。按照全国统编教材把《伤寒论》中药物的一两规定为现今度量衡的3 g。这样麻黄汤中几味的量为:9 g、6 g、6 g、3 g。《中国2010版药典中药规定用量》中麻黄2~10 g。用这样的教材教出来的医生,再加上《药典》的束缚,怎么能运用中医汤液(除了针灸)治疗急症、重症呢?只能把急症、重症患者推给西医了。所以当今经方大家黄煌教授也提出了问题:“我用经方,常有很多困惑。经方的用量是第一惑。先说说绝对剂量。《伤寒论》原方一两等于当今几克?一升等于现在多少毫升?如果按一两等于3 g换算,则桂枝汤中桂枝仅9 g,似乎量过小,如何能够分3次服用的?但如果按一两等于15.625 g换算,又与习惯用量相差极大,比如,黄连阿胶汤黄连四两,60 g黄连的药液患者能否下咽?大青龙汤麻黄达六两,近百克的麻黄煎汤下肚,患者将是何种反应?就是患者肯服,但由于用量远远大于《药典》的规定,其法律风险如何规避?”[8]。
笔者亦有同感,最大的困惑是开出了药方,在国内的药房抓不出药来。在中国中医药法案出台前的关键时候,我们呼吁修改《药典》中药的用量。
2 探求经方体系药量的原貌
2.1 从经典入手 《伤寒论》自序云:“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载,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伤寒的特点,发病急,传变速,故仲景立方剂量大,药简、力专、效宏,方能阻断病势传变,挽救危亡。然而,明代迄今,医家根据“古之一两今之一钱”的臆断,使用经方的十分之一,且袭至今,悬殊太大,计量过轻,不堪大任。大违仲景立方本义与用药原貌,严重影响了经方临证效用的发挥,阻碍了仲景学说的继承与发展[9]。
2.1.1 君臣佐使 层次分明 恢复经方体系药量的原貌,要从经典入手。仲景组方充分体现了君臣佐使的含义。君臣佐使的概念最早由《素问·至真要大论》提出:“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二臣三,奇之制也;君二臣六,偶之制也”属于医经的《黄帝内经》对君臣佐使如此详细的描述,被定为经方组方之理论根据。仲景经方君臣佐使层次分明,充分体现了药简、量大、力专、效宏的临证特色。
方剂能否治病,除了辨证准确,恰中病机,掌握君臣佐使,配伍精当,之后便是特定的剂量。以四逆汤应用为例:四逆汤是回阳救逆,起死回生的代表方剂。原方为生附子一枚,(去皮破八片),干姜一两半,炙甘草二两;按古今折算(一两等于15.625 g),则四逆汤剂量是制附子60 g(生附子一枚20~30 g,生附子效力是制附子两倍),干姜23 g,炙甘草31 g;而教材四逆汤剂量为:附子5~10 g,干姜6~9 g,炙甘草6 g。以这样的轻量之剂,要救生死于顷刻,诚然难矣!无怪乎国内中医院治疗心力衰竭等急重症需要中西医结合。用这样的轻量之剂必然会丢掉中医治疗急重症的阵地,也失去了仲景的学术特色[10]。
观今人之用方,以药量轻、药味数量多为普遍,有的方子多达20~30味。很难突出君臣佐使,君药多了则无君药,所以临证疗效就会大打折扣。
2.1.2 随机应变 经方活用 仲景经方除了君臣佐使的层次分明、药量大、药力专等特色外,根据病机转化,在煎药方法及服药时间等方面亦非常灵活。如仲景在桂枝汤后注强调:“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后服,不必尽剂。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后服小促其间,半日许,令三服尽。…若不汗出,乃服至二三剂。”可见仲景用方随机应变,并非象当今之医者给患者处方:3剂、5剂、7剂,回家服完再来!
在煎药方面,仲景亦精心备至,如葛根汤服法强调:“上七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葛根,减二升,去白沫,内诸药,煮取三升。覆取微似汗。余如桂枝法将息及禁忌。诸汤皆仿此。”现代人生活节奏快,多以机器代煎中药,其先煎、后下常被忽视。更鲜有处方上标有如葛根汤方后注“先煮麻黄、葛根,去白沫”者。因此,在继承仲景经方用量的同时,不可忽视在服药时间、药量的增减及煮药方法等细节。应当随着病机的转变,灵活变通,才能发挥经方的疗效。
2.2 从临证中求之
中医不传之秘,在于剂量。经方推广之关键,也在剂量。对于经方剂量问题,我们必须要重视经典原文,这些古代的经验和规范,是我们开展研究的原始凭据,这是基础,同时更要通过广大经方实践者从临证中求之。
2.2.1 前辈的经验 对于经方药量,上海柯雪帆教授考证:《伤寒论》一两等于当今15.625 g,并在临证应用中得到验证。如柯老用四逆汤加味救治心力衰竭危症,重症,一剂用附子达200 g,一昼夜按时服药3剂,附子达500 g以上,收到了满意效果[4]。笔者的导师御医传人马骥教授和国医大师张琪教授,他们都擅用经方辨治急症、重症和疑难杂症。还有长春已故国医大师任继学教授等,这些老中医对仲景经方运用灵活,艺高胆大,得心应手,疗效卓著。遗憾的是这些老前辈健在的很少了。已故李可老先生是当代中医临床大家,有胆有识,擅长用经方治疗危重病和疑难病。李老一语道破后世药物用量轻的原因,他说:“自秦汉以降中医就逐渐没落,后世腐儒庸医心虚胆怯,根本不敢用麻黄、附子、细辛,称之为虎狼药。而急重症非虎狼药不可”[11]。
2.2.2 笔者误打误撞之启发 1985年3月,病房一床的钱某是外县财政局的领导,患肾病,他的老伴(53岁)护理他。有一天我值夜班,钱夫人说:“看到病房的患者包括我丈夫治疗的效果都很好,您能给我也开个方吗?”遂为其四诊。患喘疾5年,靠服用氨茶碱及哮喘喷雾剂维持。到楼下打开水,上3层楼至少要歇息4~5次。刻诊:时至冬春交界之季,喘证加重,形体胖,面虚浮,口唇暗,动则气喘,额头汗出,咳嗽痰白清稀,胸胁胀痛,二便正常,舌质暗,苔白滑,脉滑数。辨证为素有痰饮外感寒邪而至喘疾加重。方用小青龙汤加减:麻黄15 g,白芍15 g、干姜15 g、桂枝15 g、生半夏20 g、五味子10 g、细辛5 g、炒枳壳10 g、炙甘草15 g,3剂水煎服,1剂/d,分2次温服。记得是周五早晨护士就把方子送到中药局了,加急处方煎药室当天晚上就会把煎好的汤药送到病房。待我周一到病房见到钱夫人,她兴高采烈,面浮已消,谓:“上下楼轻松多了,不用歇气了,昨日还走路去了动力区菜市场(来回约3~4 km),买了黄瓜和水萝卜。遗憾的是煎药室只送来一剂药!”于是我打电话给煎药室,曰:“3剂药煎好后装在1个输液瓶(500 mL)”。即询问患者,曰:“一瓶量多,我就分3次喝了,因为第2天还会送药。哪知道等也没来!”我恍然大悟!这次误服,正好符合仲景小青龙汤药物的用量(接近汉代一两为今之15,625 g);麻黄45 g、生半夏60 g、细辛15 g(打破细辛不过钱的禁忌)。而且也符合仲景“煮取三升、去渣、温服一升”的服药时间与一日的有效量,无怪乎其效果之奇!从那以后,对于哮喘证、外感发热、水肿病及过敏症等病证,只要辨证准确,放胆应用麻黄25~75 g,从未出现不良反應,且疗效满意。尤其是对于外感高热等急症,往往是“一剂知,二剂愈”。需要强调的是:随机活法,中病即止。正如《伤寒论》38条谓:“一服汗者,停后服”(剩下的药弃之)。
3 验案举隅
3.1 外感伤寒高热案 2006年2月曾治布达佩斯卫生局某领导,男,57岁。本来他答应参加我们中医药学会举办的春节联谊会,前一天下午来电话,说他发高烧,不能参加次日的活动了。我告诉他有厉害的汤药快愈的方法,他表示愿意一试,还诙谐地说:“要看看到底是他厉害还是汤药厉害?”。于是我带上饮片(单包)驱车至其舍。见其卧床厚被,面色晦滞。谓:感冒2 d,发热恶寒,热达39.5 ℃。无汗烦躁,头痛剧烈,全身关节痛,小便量少,2 d未大便。査所见:额扪之灼热,腹平软,舌暗红苔白,脉浮滑紧。其平素体健,出门送客,穿衣太少,感寒为病。辨证为外感风寒,入里化热。遂配大青龙汤加葛根1剂:麻黄50 g、桂枝25 g、杏仁15 g、生石膏50 g、葛根20 g、生姜30 g、大枣12枚。我亲自为其如法煎药,嘱分3次服。看着他喝了第一遍药,并嘱:如不汗出,4 h后可再服。次日,他西服革履来参加我们举办的活动,并竖起大拇指说:“中药真好,比抗生素还厉害!服第二遍药后,汗出象马一样(匈俗语),然后就痊愈了!”
3.2 湿浊中阻呕吐案 某男,71岁。病史:患慢性肾炎2年余。2014年4月21日,由于病情突然加重,恶心呕吐,而住进哈尔滨市某医院。患者连续10余天不能进食,靠输液维持。用止吐西药无效。4月27日,其亲属来微信索方,传来临床资料:面色萎黄无华,形体消廋,乏力至极,气短懒言,呕吐不止,下肢轻度水肿,大便稀少,小便清少,舌淡苔白滑而厚,脉象沉滑少力。实验室检查:血肌酐572.5 μmol/L,尿素氮32.94 mmol/L,血红蛋白74 g/L,尿蛋白+++,血压165/100 mmHg。西医诊断:慢性肾小球肾炎,慢性肾衰竭。本人辨证为脾肾虚损,湿毒内蕴,中焦受阻,升降失常,本虚标实。当宜急治其标,以燥湿降逆、和胃止呕为法。方用小半夏汤合半夏泻心汤加减:生半夏50 g、生姜45 g、茯苓35 g、黄连15 g、黄芩25 g、党参25 g、干姜30 g、炙甘草25 g、大枣12枚(擘)。1剂,水煎分3次温服。来微信告知:生半夏量太大,跑了几个药店,无奈只能以制半夏代之。患者服了3剂,呕吐止。后以培补脾肾兼以化湿降浊法,方用黎明肾气汤加减[12],调理半年余,症状明显减轻,体力增强,饮食尚可,腿肿已消,时有腰酸乏力,尿化验:尿蛋白+~++,血生化:血肌酐352.61 μmol/L,尿素氮19.06 mmol/L,血红蛋白92 g/L。随访至今,症情稳定,生活已能自理。
按:案例一患者平素平身体健康,外出送客,不慎感寒,不汗出而烦躁,头痛关节痛。为偶感风寒,阳气内郁,经气不畅,郁而发热。故用大青龙汤加葛根发汗之骏剂,重用麻黄、石膏各50 g。龙行雨施,汗出郁解,服三分之二剂而愈。案例二患者为慢性肾功衰竭,当下病机之要为湿浊中阻,升降失常,胃气上逆,呕吐不食。本虚标实,急则治标,以调和脾胃,恢复升降为法。方用小半夏汤合半夏泻心汤加减。小半夏汤是治呕之良方,半夏辛温涤痰燥湿,降逆止呕。生姜辛散,温中降逆。二药配伍,温中化饮,降逆止呕。合半夏泻心汤辛开苦降,故药后湿浊得化,胃气得降,脾气复升而呕吐止。继以调理脾肾而使肾功恢复。
4 结论
适宜的剂量是中医经方临床疗效尤其治疗一些危急重症获得可靠疗效的保证。现今中国中医药药典对于中医饮片临床使用剂量的限定严重限制了中医经方的合理有效使用,应当予以研究进行切合临床实际的调整,才能有助于促进中医经方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邢玉瑞.现代中医经典研究述评[J].陕西中医学院学报,2011,34(2):1-4.
[2]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5年版有关事宜的公告(2015年第105号)[J].中国药品标准,2015(5):370-371.
[3]王丹.评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J].青春岁月,2015,21:1.
[4]傅延龄,宋佳,张林.论张仲景对方药的计量只能用东汉官制[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3,36(6):365-369.
[5]孙燕.仲景方用药剂量古今折算的方法学研究[J].河北中医,2010,32(5):759-760.
[6]张天军.论中医药发展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J].中医临床研究,2015,7(4):120-122.
[7]刘力红.思考中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13.
[8]黄煌.我用经方第一惑-黄煌教授医话[EB/OL].http://www.med126.com/tcm/2015/20150126120003_8489/2015-1-26.
[9]中华中医药学会.奇医李可的学术经验[A].2012成都·第二届国际扶阳论坛暨第五届全国扶阳论坛[C].成都,2012.
[10]马荣.李可破格救心汤经验传薪[J].山西中医,2013,29(12):7-8.
[11]李可.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406.
[12]于福年,马龙侪.御医传人马骥学术经验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257-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