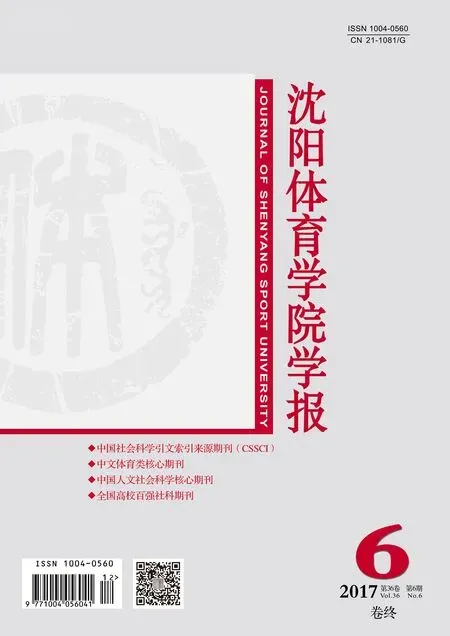公元7—8世纪的龟兹体育研究:内容、特征及启示
赵 犇,武晓敏
公元7—8世纪的龟兹体育研究:内容、特征及启示
赵 犇1,武晓敏2
(1.新疆警察学院 警体教研部,新疆 乌鲁木齐830013;2.昌吉州第二中学,新疆 昌吉831100)
体育娱乐活动是公元7—8世纪龟兹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历史文献和文物古迹的考证,对7—8世纪龟兹体育的内容及特征进行研究,并结合“一带一路”的建设背景提出历史启示。结果表明:1)7—8世纪的龟兹大致有依附于苏莫遮、行像、幻术和以乐舞为载体的4类体育活动。2)7—8世纪的龟兹体育,具有反映绿洲经济和农耕文明的特征、深受佛教文化影响、体现多元文明兼容并蓄的特点。3)7—8世纪龟兹体育对今天的启示:新疆民族传统体育可以作为多元文明交流的突破口;部分激进糟粕的伊斯兰体育观需要规训和扬弃;新疆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安全问题需要高度重视;古西域体育文化应当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体育史;公元7—8世纪;龟兹体育;一带一路
龟兹,西域古国之一(音 qiu ci,梵语 Kucina),又称屈支、鸠兹、丘兹。它既是一个历史概念,也是一个地理概念。从时间来看,龟兹在我国史籍中最早的记录见于《史记·匈奴列传》。史学界推测认为其政权的建立至少在公元前2世纪[1]。从空间来看,龟兹的势力范围大致在今天新疆的库车、阿克苏和沙雅、新和、轮台一带,其疆域与玄奘记载的“东西千余里,南北六百余里”[2]基本吻合。
公元7—8世纪是龟兹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受益于大唐王朝的庇护、“丝绸之路”带来的贸易往来和古印度佛教的弘扬,龟兹成为了当时西域的政治、经济和宗教中心,龟兹文化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为后世遗留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文物古迹。基于此展开的研究,今天统称为“龟兹学”。然而,在龟兹学的体系中,体育娱乐活动并未受到基本的关注,相关的研究成果更为鲜见。那么,作为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彼时的龟兹体育究竟扮演着何种角色?其基本内容和形态是什么?又能为今天“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体育发展提供何种借鉴?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入地研究。
1 7—8世纪龟兹体育的基本内容
1.1 苏莫遮中的体育
苏莫遮也称“飒磨达”“婆罗遮”。据《旧唐书》《一切经音义》和《酉阳杂俎》等文献记载,龟兹苏莫遮在每年的11月举行。在此期间,男女通常“并服狗头猴面”,举行“无昼夜的歌舞”仪式,期间还穿插“交互泼水”“搭钩捉人”“泥土沾洒”等活动,目的是为了祈求天气转凉和雨水充沛,以达到“穰灾”及“驱逐罗刹”的效果[3]。“苏莫遮”的盛大场景,今日虽已不能复现,但通过苏巴什佛寺遗址(今库车北)出土舍利盒上的细节(图1、图2),能够窥之一二。在这尊舍利盒上,由21人组成的“苏莫遮”队伍,有奏乐者,有舞蹈者,有持棍者,有喝彩者,尤其是头戴面具的几名舞者,衣着华丽,动作夸张,且均佩戴着长尾饰物,似乎正在模仿动物的形象,而一旁观看的孩童兴高采烈、拍掌叫好。如此富于特色的活动,在中原地区也得到了一定的传播。据《旧唐书》记载,公元704年,苏莫遮因“蕃夷入朝”传入唐廷(中原意译为“乞寒胡戏”或“泼寒胡戏”),唐中宗李显对其颇感兴趣,甚至“御楼以观之”,百姓则更是喜闻乐见。苏莫遮表演时,偌大的长安城内居然“阗城溢陌”。然而,因为“法殊鲁礼,亵比齐优”“妨于政要”等原因,公元713年苏莫遮被敕令“禁断”,从此退出中原的历史舞台,史载“此戏乃绝”[4]。但作为一种广泛流传于民间的文化形态,苏莫遮不可能因为政令的禁止而即刻消逝,一方面其表演乐曲经改编后演变为著名的词牌名“苏幕遮”流传后世;另一方面其基本形态则由长安东渐至日本、韩国以及越南,并成为日本天王寺的秘传舞蹈。当然,在西域地区,苏莫遮并未受到中原政令的影响,在10世纪后半叶依然较为流行。《西州使程记》对此有较为明确的记载,其中的 “舞蹈”“奏乐”“泼水”等细节,与7—8世纪的苏莫遮高度相似,同时也为今天双向实证苏莫遮的内容和形态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

图1 苏巴什佛寺出土的舍利盒
1.2 行像中的体育
行像是源自古西域的一种礼佛仪式,是把佛像安置在装饰性的花车上,由人抬其像在城内巡行,以供信徒瞻仰和膜拜,其间伴有舞蹈和杂戏的演出。据《大唐西域记》《酉阳杂俎》以及《洛阳伽蓝记》记载,龟兹国在每月的15日,以“行像及透索为戏”。所谓的透索,学术界一般认为其所指为类似跳绳的活动。不过,既然在诸多文献中能够与行像并列出现,透索的内容应当并非单纯意义上的跳绳,而可能是高度依附于佛教的体育娱乐活动——“绳舞”。在佛教中,世俗所指的绳索称为“羂索”,有“佛菩萨”通过其“摄取众生”的象征。在行像中以透索为戏,则表达了“信众通过花绳隐喻愿将自身委系于佛的”[5]虔诚态度。龟兹石窟中,绳舞大量出现在天宫伎乐图(图3)、供养人图以及佛说法图之中就是明证。而在今天的新疆,主体宗教虽已演变为伊斯兰教,但绳舞在库车地区的麦西来甫(维吾尔族民间娱乐)中仍有显著遗存,其基本动作顶胯、扭腰、捻步、旋转等极具古代龟兹特色,并与碗舞、鼓舞、飘带舞等共同构成了维吾尔族的“执物舞”。

图2 苏巴什佛寺出土的舍利盒的局部复原
同苏莫遮一样,龟兹行像的目的并非只为单纯的礼佛,而具有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按玄奘的记载,应当是龟兹的“国王大臣谋议国事”,借“行像”来“访及高僧,然后宣布”[5]。对于世俗百姓而言,行像之时的体育娱乐“透索”“彩幢上索”“作倡伎乐”等可能更具有吸引力,其盛大场面大概类似于今天的庙会或者香会,《大唐西域记》将其形容为:士庶“渴日忘疲”“动以千数,云集会所”[5]。在龟兹,一方面行像为体育娱乐提供了绝佳的场所和平台,使其更具影响力;另一方面,体育娱乐也拓展了行像的外延,使其更加贴近世俗生活,从而利于传播。二者共同构成的“场域”,形成了一种相辅相成式的互补。
1.3 幻术中的体育
在唐朝诸多的历史文献中,对于龟兹幻术的直接记载,仅见于僧人圆照的《游方记抄》:“过屈支国……。敬重三宝。多幻术。”虽然其记录语焉不详,但我们从同期的相关史料《旧唐书》《法苑珠林》中大致可以推断出龟兹幻术的内涵、内容以及形态。首先,龟兹幻术是龟兹体育娱乐的重要组成内容。两汉时期,类似于幻术的技巧,与今天所谓的一些杂技项目是没有显著区分的,都被包含在“百戏”(角抵戏)的范畴之内。如《汉文帝篡要》记载:“百戏起于秦汉曼衍之戏,技后乃有高絙、吞刀、履火、寻幢等也。”(图4、图5)其次,龟兹幻术又并不只局限于今天所谓的魔术。唐朝大儒颜师古认为,所谓的“幻”同“眩”[6],即看不清楚或令人惊叹,一种可能是掩人耳目的魔术,另一种则可能是技艺高超或速度极快的技巧类项目。在古代西域(包括龟兹),流传较为广泛的,前者如植瓜种树、易牛马头、截人屠马,后者如吞刀、履刃、走绳、跳丸、跳剑以及安息五案等,其中吞刀、履刃属硬气功的范畴,走绳即为高空走索,跳丸、跳剑则以交替掷丸或掷剑为戏,而安息五案则需要在叠摞起的案几上表演节目。这些项目都极具难度,考验着“幻人”们的勇气、胆识和技艺。再次,龟兹幻术和宗教有密切的联系。按照王青、何志国等学者的观点,来自西域的幻术可能是传播宗教时的一种常用手段,目的是使人们“相信有超自然、超规律甚至是反自然、反规律的现象存在”,以此激发对神灵的信仰,最终“吸引教众”和“延揽信徒”[7]。据遗失海外的敦煌文献记载,龟兹高僧鸠摩罗什就曾经以幻术表演博得了后秦统治者的信任,从而发展弘扬了佛教[8]。综上所述,古代龟兹的幻术,大体上是依附于宗教的、以技巧和魔术为基本内容的体育娱乐活动。

图3 库车克孜尔千佛洞第38窟“天宫伎乐图”中的绳舞形象

图4 《信西古乐图》中的吞刀吐火

图5 北魏胡人杂技佣
1.4 乐舞中的体育
乐舞文化是龟兹文化体系中最富盛名的内容之一。在隋唐时期的“九部乐”和“十部乐”中,龟兹乐舞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大唐西域记》中也记载到:“屈支国,管弦伎乐,特善诸国”。尤其是来自龟兹的著名舞蹈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五方狮子舞等(图6~图8),在隋唐时期风靡中原。从表演风格来讲,龟兹舞蹈多以健舞为主。健舞风格刚健,节奏明快,充分体现了西域各族热烈、奔放的民风。如男子独舞胡腾舞,动作以大幅腾跃与踏步为主;女子舞蹈胡旋舞,以旋转踢踏为主要动作;而柘枝舞则节奏明快,且以打鼓、摇铃作为伴奏;五方狮子舞以龟兹王降服狮子的故事演化而来,因为要体现狮子的凶猛和龟兹王的勇武,动作也异常刚健有力。从历史文献的描写和文物古迹的形态来看,龟兹健舞中蕴含了大量的肢体动作,典型的有跳、腾、转、劈等,《通典》将其描写为:“举止轻飙,或踊、或跃、乍动、乍息、跷脚、弹指、撼头、弄目。”其中“踊、跃、乍动、乍息”与现代体操、艺术体操的一些动作颇为相似,而“弹指、撼头、弄目”则成为今天新疆民族舞蹈的标志性动作。在表现内容和风格上,今天的新疆舞蹈与7—8世纪的龟兹舞也是一脉相承,如南疆响铃舞、手鼓舞之于柘枝舞,刀郎麦西来甫之于胡腾舞,塔什库尔干县的鹰舞、吐鲁番地区的那孜库姆之于五方狮子舞等。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龟兹乐舞的内容虽有部分遗失,但其基本风貌却得到了较为完整的保留,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图6 唐胡腾舞佣

图7 唐兴福寺残碑柘枝舞

图8 莫高窟220窟胡旋舞
2 7—8世纪龟兹体育的特征
2.1 反映绿洲经济和农耕文明的特征
7—8世纪的龟兹体育,首先受地理特征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从人们一贯的逻辑认知出发,处于我国地形第一阶梯的西域地区,应当属于典型的游牧文明。但古龟兹因为地处塔里木盆地北端和天山南麓,地势较为平缓,其体育项目则高度具备绿洲经济以及农耕文明的特征。第一,据文献记载与学者研究,龟兹代表性体育项目苏莫遮,与象征春耕即将到来的波斯雨神节和中亚传入的“诺鲁孜节”颇有渊源[9],目的都是为了祈求天气转凉雨水充沛,从而得以“气序和”与“宜糜麦”。第二,在《旧唐书》《新唐书》《大唐西域记》等文献中,龟兹与其近邻乌孙、突厥、婼羌等,虽然都有与马、牛、驼等相关体育娱乐活动的记载,但目的却有明显的差异。如龟兹通过“斗羊马橐它七日,观胜负”,以“卜岁盈耗云”[10],显然是为了进一步的经济发展,而突厥以“畜牧为事”“随水草射猎”[11];乌孙“有天马”“行国,随畜,控弦者数万”[12],则更多出于自给自足或军事的需要。第三,龟兹的乐舞表演,无论服饰、道具,不仅种类繁多,且较为华贵,如龟兹乐器,仅文献记载的就有琵琶、箜篌、筚篥、胡鼓等15种;舞蹈服饰则有皂丝布头巾、绯丝布袍锦袖、绯布裤等,而幻术和行像也有固定举行的时间和场所,这都说明龟兹民众有能力、有精力、有场地、有规划地进行各种娱乐活动,显然是“逐水草而居、飘忽不定”[13]的游牧族群难以具备的。综上所述,从体育娱乐活动中便可以印证出龟兹虽地处西域但却具备农耕文明的生产生活方式,并且物质经济水平较为发达,应当是符合历史文献中“温和、田美、广饶水草”“耕田产牧为业”“帛纯宫室壮丽焕若神居”[14]等记载的。
2.2 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
宗教文化是龟兹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自西汉至隋唐时期,先后流行于龟兹的主要宗教有萨满教、祆教、摩尼教和佛教,尤以佛教的影响最为深远,对龟兹社会也产生了方方面面的影响。因而7—8世纪的龟兹体育也具有浓重的佛教色彩。比如苏莫遮,又称“婆罗遮”,目的是“驱逐罗刹”,其中的婆罗和罗刹均为佛教用语,前者意为到达彼岸,后者则为恶鬼的总称。从这一意义上讲,苏莫遮可视为是民间通过歌舞仪式来渡灾、渡劫,以超脱尘世烦恼的活动。因此,苏莫遮虽然具有体育娱乐的形态,但其内涵却由佛教所统摄。再如行像和幻术,在教育水平和自然科学较为落后的古代社会,是推行佛教的有效手段[15]。夹杂于其中的体育娱乐,则大多是佛教传播时的附属品或者衍生物。至于龟兹民间乐舞,佛教色彩也较为浓郁:其一,在表现内容上,有众多的菩萨、飞天、罗汉与世俗人物相结合的舞蹈场景;其二,在道具使用方面,出现大量的盘、绳、撒花、飘带等,“可能是受到佛教服饰以及相关仪式的启发而设计的。”[16]上述情形当然是有深层次社会根源的。一方面在宗教中融入体育娱乐,对于世俗百姓而言,显然强于单纯的讲经和说教,传播效果可能是立体式的,如苏莫遮“七日乃停”,行像则是“观者如堵”。另一方面,体育娱乐依附于宗教,在缺乏自然科学的时代,可能会寄托民众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这对于以佛教作为国教的龟兹,是非常利于上层阶级对普罗大众的思想控制的。因此,7—8世纪的龟兹,具有如此丰富多彩的与佛教相关的体育娱乐活动,与上层阶级的推行和支持是密不可分的,正如《大唐西域记》所载“屈支国,每岁秋分数十日间,举国僧徒皆来汇集,上自君王,下自士庶,损废俗务,奉持斋戒,受经听法渴日忘疲”。
2.3 体现多元文明的兼容并蓄
7—8世纪的龟兹,是古代丝绸之路北道上的耀眼明星,也是“古印度、希腊—罗马、波斯、汉唐文明在世界上唯一交汇的地方”[17],多种文明的交织和碰撞,造成了欧亚大陆文化的大融合和大发展。体育也深受影响。比如苏莫遮,史载受西方大秦文化的影响,并夹杂着古波斯“雨神节”的印记,经丝绸之路流入龟兹,后传至中原,虽然因政治原因被唐朝“禁断”,但因其在民间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最终东渐至日本,成为日本雅乐“蘇莫者”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据文献记载和学者考证,风行于龟兹的行像和幻术,也可能与古印度、古波斯、古罗马等国的信仰、民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其中的体育娱乐更是如此。如安息五案来源于古波斯,跳丸、跳剑发轫于古罗马,倒舞、走绳则出自于古印度。极富盛名的龟兹舞蹈,则最具兼容并蓄的特点,在内容上承袭了西域康国、米国的特色旋转、腾跃,在服饰、道具和造型上借鉴了“希腊式”的犍陀罗风格,而舞蹈时的配乐又具备典型印度北宗乐的特色。更难能可贵的,是龟兹舞蹈还经受了王朝更迭、信仰变化的历史考验,显示了比苏莫遮、幻术、行像更长久的生命力。尤其是在今天盛行伊斯兰教的新疆,依然能够在库车、喀什、和田、哈密一带的舞蹈中看到古代龟兹乐舞的身影。可以说7—8世纪的龟兹体育,就是印射多元文明兼容并蓄的一面明镜。所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如今“一带一路”在我国重焕生机,可能也预示着中西文化以及中西体育文化会迎来新的交流契机。
3 7—8世纪龟兹体育的启示
3.1 新疆民族传统体育可以作为多元文明交流的突破口
从宏大的历史进程看,古代龟兹既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枢纽地带,也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明的激烈对撞区,更是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祆教、景教、摩尼教、萨满教的交汇核心。龟兹体育作为肢体展演的活动,逾越了语言、民族、宗教以及政权的鸿沟,在跨文化兼容并蓄的过程中,发挥了难以替代的宣传和推动作用。今天“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不仅为中国,也为广义上的古西域国家,即今天的中亚、西亚甚至欧洲等国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契机和历史机遇。虽然各国之间的国体并不一致,政见也有所不同,但作为东西地缘枢纽的新疆和带有多元文明印记的新疆文化,是有可能成为各国求同存异的基础的。尤其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等这些“丝路经济带”上多个国家、地区的共有民族,拥有文化内涵相近的传统体育活动,如赛马、骑射、叼羊、达瓦孜、且力西、阿肯弹唱等,可以成为体育外交的突破口。因而从这一层面上讲,龟兹体育给我们的启示:今天的新疆民族传统体育,完全可能成为打开与中亚各国交流、创建和谐外交的钥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对“一带一路”建成“文明之路”的期许:“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推动文化、体育、卫生务实合作,用好历史文化遗产,密切各领域往来。”
3.2 部分伊斯兰体育观有待于商榷和转变
7—8世纪是龟兹历史上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段,这一时段正值中原唐朝的统治,其军事、经济以及文化也因此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然而,8世纪中后期的安史之乱,使得唐朝由盛转衰,也放松了对整个西域的掌控。龟兹先后为吐蕃、黠戛斯、回鹘所占据,并在9世纪中叶开始了回鹘化和伊斯兰化的进程,佛教和佛文化也因此受到严重的破坏。这一系列变化在龟兹的体育娱乐上也有所反应。在内容和特征上,原本依附于佛教的苏莫遮、行像、幻术等日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表现略显激进的走索、斗狗、马上运动等伊斯兰化体育。其次,在活动主体上,7—8世纪的龟兹体育几乎是全民参与且较为开放:行像、幻术举行时,民众“云集会所”“观者如堵”,乐舞则是“妇女衣髻,不重从容,俱仓宽缓”[17]。苏莫遮更是“男女无昼夜歌舞”。但是,伊斯兰化之后的龟兹乃至整个西域,虽然提倡民众参加射箭、驯马、摔跤、赛驼等体育活动,却对妇女却做出了明确的限制。《古兰经》指出,妇女参加运动“要遮盖羞体”(成年女性手和面孔以外的部分)、“要避免男女混合”[18],《布哈里圣训》则谕示:“妇女应在男子看不见的地方参与体育活动”[19]76。即便在日常的穿戴中,她们也需要“降低视线,隐蔽首饰”,使“身体的轮廓不让外人看到”[20]。在教义的压力下,穆斯林女性不得不远离体育运动,“在行动和舆论上逃避男性的注视,通过牺牲体育娱乐的权利来换取其他方面的相对自由”[19]178。遗憾的是,不仅在9世纪以后,即便到了文明高度发达并且崇尚男女平等的今天,新疆南部包括库车(古龟兹所在地)一代的体育活动中也很少能看到穆斯林女性的身影。因此,我们认为伊斯兰化后的龟兹体育,虽然是新疆民族传统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对女性体育权利的漠视是有待于商榷和转变的,尤其是在当前“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开放包容”成为时代主题,成为“丝路精神”的显著特征,穆斯林女性应当具有自主参加体育活动的权利。2017年4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工作条例》正式施行,“干预文化娱乐活动,排斥、拒绝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言论和行为,已经明确被认定为是极端化的表现。这一条例在政策上也保障了穆斯林女性的体育权利。总而言之,今天的新疆民族传统体育,在维持特色的基础上,还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使其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明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3.3 新疆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安全问题需要高度重视
文化安全是指“国家观念形态的文化,包括民族精神、政治理念、信仰追求等生存和发展不受威胁的客观状态”[21]。文化安全的核心内容是要维护本国、本民族的“多元文化”和“个性文化”。7—8世纪龟兹体育表现为多元文化的多边交流,如果以狭义上的西域(即今天的新疆)为中心,那么龟兹体育文化的交流,既包含幻术、行像的西来,也有苏莫遮、乐舞的东渐,还夹杂着佛教文化的南来北往。然而,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和资本力量的不断扩张,西方世界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消费文化和享乐主义正在成为一种“全球性文化”[22]。体育文化应有的多边交流也在资本力量的驱使下演变为西方竞技文化的一家独大。在今天的新疆,不仅龟兹体育文化难觅其踪,就是在此之后盛行的伊斯兰体育也日益面临严峻的传承危机,葫芦人绊跤、奥尔朵、萨哈尔地等项目甚至已经在消逝的边缘,其中蕴含的人文价值、风俗习惯以及反映的时代特征也正在逐步流失。古代西域和现代新疆的多元文化正在被资本推动的全球化齐刷刷地斩断。更为严重的是,西方文化在传入的过程中,还裹挟着强烈的政治意图,尤其是新疆,由于地缘、政治、经济、历史、宗教等问题的特殊性,极易成为敌对势力推行分裂主义的前沿。而民族传统体育这种极具代表的个性文化,在“泛伊斯兰化”“泛突厥化”以及“泛清真化”等激进思想的影响下,可能异变为民族主义,甚至在有些时候与国家安全问题纠结在一起。近年来,就曾出现过类似的案例,如在新疆和田某地和喀什某地,一些激进份子借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之机,声称某些项目是“维吾尔人的运动”“穆斯林的运动”,排斥“汉人”“汉文化”,并借此进行非法传教、挑唆民族情绪等违法犯罪活动,妄图借文化差异之名,达到鼓吹极端思想的目的。因此,面对上述情况,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可能出现大量文化输入和输出的背景下,一方面应当提高文化自觉的意识,大力保护和发掘新疆历史上优秀的体育文化,维护新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多样性;另一方面还需要对新疆民族传统体育进行正本清源,要摆脱宗教极端思想的渗透,最大限度地降低其沦为破坏文化安全工具的可能性,避免重蹈苏莫遮因为干预政治而被“禁断”的覆辙。
3.4 古西域体育文化应当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从古至今,我国就是一个民族多元化的国家,多民族的文化共同构成了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然而,长期以来“大汉族的历史被默认为主流,而55个少数民族特殊的文化风貌和历史变迁,只被只言片语地提及,并且没有真正走入大众的视野。”[23]因此,我们所说的中华文明,在少数民族这一环可能是有所缺失的。具体到体育学科,则是关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远远不及汉族传统体育项目武术、舞狮、赛龙舟等丰富多彩。事实上,仅仅通过对7—8世纪龟兹体育的研究,我们就可以判断出古西域体育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形式是极具时代风貌的,甚至苏莫遮、行像、乐舞等活动曾经对汉文化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如果没有对史料和古迹的追根溯源,我们可能不会得知龟兹的体育文化曾经如此绚烂,也可能无法认识到在汉唐文明以外我们的国家同时还存在着恢宏的西域文明,一如绝大多数民众对古代西域和今天新疆的认识尚且局限于戈壁、沙漠以及贫穷与落后。不过,令人欣喜的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党中央关于“新疆若干历史问题研究座谈会”的召开,不仅预示着新疆在未来将迎来快速的发展,同时还为我们提供了认识西域文明的绝好机会。乌孙、柔然、婼羌、高昌、于阗等古西域诸国的体育文化以及各民族及其前身塞种人、吐火罗人、回鹘人等的体质人类学变迁等内容,应当会引起,也必将会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这种关注既是对古西域厚重历史的尊重,也是“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我们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更重要的是,由此产生的示范作用,可能会带动其他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工作,从而进一步助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进程。
4 结束语
回溯历史,发现以苏莫遮、行像、幻术、乐舞等为代表的7—8世纪的龟兹体育,内涵丰富,形式多样,是古代西域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历史文献和文物古迹的考证,可以明确的是7—8世纪的龟兹体育,还反映出彼时的龟兹社会具有反映绿洲经济和农耕文明的特征、深受佛教文化影响、体现多元文明兼容并蓄等方面的特点。展望未来,我们也期望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下,学术界能够更多地关注西域体育文化,从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诸多层面推进当前新疆体育文化的研究和建设工作,让曾经灿烂的西域体育文化和西域文明重焕生机。
[1]刘锡淦,陈良伟.龟兹古国史[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2:41.
[2]玄奘.大唐西域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5:16-20.
[3]释慧琳.一切经音义(电子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79.
[4]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303.
[5]陈安琪.隋唐时期龟兹乐舞服饰研究[D].西安:西安工程大学,2016:35.
[6]何志国.东汉外来杂技幻术与佛像关系及影响[J].艺术考古,2016(1):76-82.
[7]王青.西域幻术的流播以及对中土小说的影响[C].第三届吐鲁番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8.
[8]郝春文.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26.
[9]库尔班·买吐尔迪.从苏幕遮到诺鲁孜——古代西域戏苏幕遮来源略考[J].中央戏剧学院学报(戏剧),2006(2):98-103.
[10]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424.
[11]魏徵.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8:57.
[1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2:335.
[13]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03.
[14]吴平凡,朱英荣.龟兹史料[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87:66.
[15]尚永琪.西域幻术与鸠摩罗什之传教[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30-40.
[16]余太山.西域通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242.
[17]季羡林.季羡林学术思想精粹[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119.
[18]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6:1125.
[19]马坚.古兰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76.
[20]穆斯塔发·本·默罕默德艾玛热.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219.
[21]阳煜华.穆斯林女性、体育参与和身体文化论衡[J].妇女研究论丛,2013(3):76-83.
[22]潘一禾.文化安全[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1.
[23]胡惠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29.
Qiuci Sports in 7-8 Centuries AD:Contents,Characteristics and Enlightenment
ZHAO Ben1,WU Xiaomin2
(1.Department of Police Training,Xinjiang Police College,Urumqi 830013,Xinjiang,China;2.Changji Second Middle School,Changji 831100,Xinjiang,China)
Sports entertainmen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social cultural life of the Qiuci sports in 7-8 centuries.Based on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cultural relics,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conten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Qiuci sports in 7-8 centuries,and puts forward its historical enlightenment combined with the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background.The results show that:1.Qiuci sports in 7-8 centuries can be divided into Sumuzhe,Xingxiang,magic and art.2.Qiuci sports in 7-8 centuries,ha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flecting the local production and life style,deeply influenced by religious culture,reflecting the exchange of diverse civilizations.3.Qiuci sports in 7-8 centuries inspire that Xinjiang traditional sports can be regarded as the breakthrough of multi civilization exchange;part of the radical Islamic sports need discipline and discard;cultural security of Xinjiang traditional sports should be highly focused on;the Western Regions sports culture should arouse extensive attention in academia.
sports history;7-8 centuries;Qiuci sports;the Belt and Road
G80-054
A
1004-0560(2017)06-0138-07
2017-09-21;
2017-10-2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研究项目(15YJC890047);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科研专项课题(16TY2613046ZB)。
赵犇(1985—),男,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文化和健身健美理论。
郭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