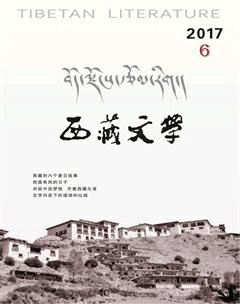纹身
边巴
此时,我最后悔的事情莫过于当年纹身时,胸口刻下的竟然不是“反清复明”“五讲四美”之类的字,哪怕是“发配沧州”也可以啊!
随着耳边传来的“嗞嗞”声,我胸口的表皮上流动着钻心的痛。我咬着牙紧闭着双眼,裸露着上半身,仰躺在褐色的医用床上。感觉到从发丝间渗出的汗珠子流过鬓角,淌入耳廓里。我的双手紧紧地抓着身下的床沿,手心里浸满了汗水。我想现在我的面目都拧成一团皱纸了吧?
俯身在我胸口上方的大夫,有张国字脸,留着寸头,浅蓝色医用口罩上方戴着黑色方框眼镜,鬢角似乎灰白。
“大夫,不是说洗纹身不痛吗?”我将眼睛睁成一条缝对着大夫有气无力地说,显然我弱弱的声音有些嘶哑和微颤,像是影视剧里临死前忍着剧痛交代遗嘱的喃喃低语。
“洗纹身嘛要刺破皮肤,粉碎植入皮层的色素,是会有些疼痛感的小伙子!忍忍啊!要不想象一些美好的东西来分散注意力!”
于是我闭上双眼开始想“一些美好的东西”,我的眼前浮现出我美丽的未婚妻卓玛:瓜子脸,长睫毛大眼睛,笑起来有一对酒窝,身材纤细高挑。一想起她,我忍痛的决心和毅力便强大了很多。我咬了咬牙,感觉到自己腮帮子上的肌肉在蠕动。如果我放弃洗纹身,我能想象得出入洞房那夜未婚妻看到胸口这个纹身时的表情,她一定先会用她纤细的食指轻轻抠着我的纹身刨根问底。当我坦白交代后,她就会放下搂住我的双手,翻过身,将头埋进被窝,泪水流得像燃烧殆尽的花烛那般。然后一两天将自己反锁在屋里,任你怎么解释、忏悔、求饶。即便和解,也可能将这种折磨反反复复复发于往后的生活,甚至有可能从此葬送了这段美好的爱情和婚姻,而我已经不小了。上次她帮我收拾房间时,无意中看到我影集里那几张与央金相拥而照的相片,她先是装淡定,然后旁敲侧击追根溯源,确认我和央金曾经相恋过后就用被子捂住头歇斯底里地大哭,像个孩子。过了几日和解了,但依旧时不时拿这事儿不依不饶地冷嘲热讽,这样的日子真是不好过啊!只好当着未婚妻的面将合影照片撕得粉碎,并以谎言狡辩:当时并没有投入感情,也没法对央金产生感情,不然怎么会草草分手?狡辩归狡辩,但我打心眼里喜欢未婚妻,她不仅美丽端庄,穿着得体不显臂露脐,而且内心似乎很传统,我们每次亲热逐渐升温时,或者说我的手像蛇那般乱窜到女孩的“禁区”时,她总会克制并喃喃地制止我:“尼次!我迟早是你的,但在婚前不想太草率!”但自从上个月,她的这句话改成了:“尼次!领完结婚证的洞房夜,我将自己完好无缺地交给你好吗?”
因为这句话,我把她当成我的未婚妻。
也因为这句话,她至今不知道我胸口的这个纹身。
我不想因为这个纹身而让她伤心欲绝,至少不想坏了洞房里的好事以及往后的很多好事。“我将自己完好无缺地交给你好吗?”这句柔柔麻麻的话,太甜,太酥,太诱惑我了!每次回忆起这句话,我的眼前总会浮现出卓玛那诱人、无瑕的玉体,紧接着又会联想到自己胸口这大煞风景、扰心败兴的纹身。于是我横下心照着广告地址去街边的这家美容医院彻底清除纹身。就像年少时横下心去纹这幅纹身那般。
“……领完结婚证的洞房夜,我将自己……”我闭着眼睛揣摩着她的这句话,我们之间是她先提出的“结婚证”这个词,这让我很舒服!她的这句话是上个月我带她去和我一个女同事吃饭后的第二天开始出现的。那天吃完饭回去后卓玛就跟我说,以女人敏锐的直觉她发现,吃饭时女同事的眼神有点拘谨不自然,但又自作矜持、故作自然结果适得其反,这些行为流露的情感复杂纠结:暧昧或者暗恋和吃醋的成分掺和在一起。最后她总结出的结论是——女同事肯定对我有好感!当时我也很佩服女人所谓的第六感,但我百般狡辩,说这简直是无理取闹!还强调说:“除了你!我谁都看不上!”当然,强调的这句是发自我肺腑的。
“你臂上的斧头不洗吗?”
“不!这个先留着。哎哟!好疼啊!大夫,你们广告上不是说无痛……”
“考警察的话,身上一处纹身都不该有吧?”
“我刚才跟您开玩笑的,大夫。”我依旧紧闭着双眼说道。
我觉得我刚才一进来就撒给大夫的谎言还是没有经得住他的推敲,只好跟他说是开玩笑的。再说了洗纹身原来还这么受罪,谁愿意再多洗一幅来增加痛苦?况且臂上的“斧头”又不会影响我现在生活的“和谐安宁”,洗它不是找疼吗?
我一直紧闭着双眼,我仿佛看见一束红红的火光沿着胸口那两个讨厌的字迹一路烧灼着肌肤,像一把锋利的破冰刀那般爆破着浸满色素的细胞。广告上明明写着“无痛洗纹身”,骗子!我提出质疑后大夫又吞吞吐吐地说个别体质会有轻微的疼痛感。扯淡!这撕心裂肺的疼搁你身上还会感觉轻微?难不成大夫玩文字游戏?他的话里是不是暗含“除了个别体质轻微疼痛,大多数人会感觉剧痛”的意思?胸口这两个该死的字也真是,笔划那么多!我强忍着痛,心里暗骂着。
“拉姆是谁啊?”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正在疼痛难忍的时刻,这个贫嘴的大夫又提起我胸口上那两个令人一辈子生厌的字。我已经记不清拉姆的脸了,记忆里她的脸已经被很多其他的脸给覆盖了,只记得她经常穿一件粉红色的毛衣,好像是粉红色吧?哦!也许是蓝色!管它呢!毕竟高中时期与现在时隔十年。我现在不想回忆她,我现在最恨的就是胸口这两个难以剔除的她的名字。干嘛非要纹上去啊?我当时的脑袋是被驴踢了还是被门给夹了?热恋就热恋,痴迷就痴迷吧,干嘛要把人家的名字纹自己的心口上去呢?为了讨好女孩?咳!好像有一半,还有一半就是当时觉得往后的一切都会永恒,包括拉姆和我。纹拉姆的名字时疼过没有?记不得了,只记得当时刻意选择了心口的位置表示刻骨铭心,而且纹完后很兴奋,在拉姆面前老有一种想光着膀子的冲动,也许当时是被爱情给麻醉了!如今,曾经以为会永恒不变的那段爱情已经被岁月侵蚀得拼不出一个完整的记忆片段。拉姆的脸在我的记忆中已经模糊得像打了马赛克一样!拉姆早在十年前已经从我心里走出去了,但我心口的肉上依旧清晰地留着她的名字!这个一直阻碍我辞旧迎新策马奔腾的名字!这个危害我未来家庭“安定团结”的名字!这个让我哭笑不得的名字!如果当时纹的是“精忠报国”或者“反清复明”四个字有多好!至少现在不用这么受罪,非要纹个女孩子的名字!咳!endprint
“哎哟!别给我提那两个讨厌的字!”我恼怒地回大夫的话,似乎是在表达我的懊悔,由衷的懊悔!
“讨厌?讨厌怎么会纹得这么深刻?前女友?”
“前前女友。”我纠正了一下,但话刚一出口,我就后悔得想抽自己一个大嘴巴!我责备自己跟一个陌生的、贫嘴的人说了实话。我的这张嘴怎么像个棉裤腰似的?只要不少他一分一厘,何必一五一十地讲清楚呢?真该“嗯”一声应付了事,省得他又以此为话柄接茬。
“那前女友的名字纹哪儿了?要不要一并洗掉?”
我说了吧!这个大夫果然是个能让妖怪抓狂的贫嘴唐僧!我才不会傻到每恋爱一次就将时任恋人的名字拿自己的肉身去刻一次,我的身体又不是封神榜!再说了因为我心口所纹的“拉姆”这个名字,前女友央金也没少折磨我!她心情好的时候笑话我的纹身:“拉姆?啊哈哈哈……这是你的商标?还是前任题的字,留下的墨宝?如果是那样,那我也留一行字在你屁股上吧?就刻‘时任女友央金到此一游!?”她心情不好的时候就用涂满血红指甲油的尖细指甲抠我的纹身,因此我还经常用贴膏药盖住纹身的方法、穿紧身汗衫遮住纹身的方法、熄灯亲热的方法,但经常是亲热到赤身裸体的阶段就会断片,甚至引发内战反目成仇!战役的结局往往是她鹊巢鸠占地把我赶出我的房子。我忍无可忍只好对央金吼叫:“我给你一把刀,你把我心口的这块肉给割下来好吧?”那时的我感觉自己就是一个无法赎清罪过的刺配犯人!
听到大夫让人抓狂的话,我猛地睁开了双眼,瞪着他,却从他口罩上方的眼神中看出他在笑,目光貌似很专注地盯着我的胸口,并没有瞥我一眼:“说说话可以分散注意力,减轻疼痛感地!小伙子!”
我只好重新闭上了眼睛,胸口流动的疼痛让我的脸又重新皱回了一团废纸。
“以前啊,也有一个小伙子,在高中热恋时,将他女友的名字‘婷婷纹在了他的胳膊上,后来与‘婷婷分手找到了新欢‘芳芳。他怕‘芳芳看到纹身会责怪哭闹,但又惧怕洗纹身时的疼痛,于是在‘婷婷两个字的后面又纹了三个字——‘是婊子。后来又与‘婷婷复合,无奈在‘是婊子三个字前又纹了一个‘不字,再后来又和‘婷婷分手,他只得在‘不字下面纹了一个‘辶。啊哈哈哈哈……”
哎哟妈呀!这个大夫一惊一乍的,自己讲笑话自己笑!他这突然的一笑,吓得我差点没滚到床下去。我并没有把他的这段话当笑话听,因为这个段子,更像是在讽刺我们这号人,而且“婷婷”、“芳芳”、“婷婷”的我也没听出个究竟来。我怔怔又有些怯怯地瞪着他。他随便瞥了我一眼,将手中的仪器放入我枕边的盘子中:“怎么?不好笑?不好笑也没事,完事了!注意回去后冷敷,不要吃辛辣的、不要酗酒抽烟……”
我起身坐了起來,我以为我的胸口会像一张用橡皮擦擦过的白纸一样干净!于是低头看了看胸口,墨绿色的“拉姆”两个字倒是不见了,但是沿着字的印迹是起泡泛红的皮肤,与周边的肌肤颜色迥然,像是被猫挠了那般。轻轻抚摸有明显的凹凸感,像一幅浮雕作品。一幅浮肿泛红的“拉姆”取代了墨绿色纹身的“拉姆”!这两个讨厌的字不仅没有像想象那般被剔除得干干净净反而变得血肉模糊更加恶心了!这使我有些失望和恼怒。我半张着嘴瞪着大夫:“这就完事了?字还在我胸口上的嘛!而且变得这么恶心!”
“小伙子,洗纹身不是洗玻璃,也不是变魔术!破皮伤肉的事情总会留些疤痕的,需要慢慢愈合!”大夫边收拾推车上的器具边慢慢悠悠地说,他并没有看到我恼怒的表情。
“那没有更快的方法?”
“有!就是增加次数!要每隔一个月洗一次!你这种情况可能至少要洗四次!墨绿色不好洗干净的。”
“四次?”我瞪大了眼睛惊呼,一下子想到那撕心裂肺的疼。无论如何我可不想再遭那种罪了,别说四次,一次都受不了!“那洗一次到底要多久才能彻底让纹身消失?”
“这个嘛!要看个人的体质!”大夫边说边弯着腰背对着我在墙角拔仪器的插头。又是该死的“个别体质论”,这简直成了他们的挡箭牌和遮羞布!大夫起身将插头放入推车上的托盘,又用镊子夹起一块棉花继续补充道:“人体皮肤自我修复能力很强,一般一年后会恢复原样,不过也说不准,因为个人的体质有差别。”又是一个文字游戏,一句带着歧义的模棱两可的话,“说不准”到底是指也有可能不用等一年还是指有可能一年之后都恢复不了?这不废话吗?
“躺下!”大夫用镊子夹着棉花走过来,将我胸口上的血渍擦洗干净后,将涂了一层药的纱布用膏药贴在我胸口的“浮雕”上。
我结账后回家,满怀希望地期待着揭开纱布的那天奇迹出现。
一声“口哨”从手机里传来,划开一看是我的未婚妻卓玛发送的微信:
“哇!今天在地区上见到了高中时候的死党耶!好激动啊!”
我回道:“男的女的?”
“是我闺蜜!当然是女的啦!”
“哦!那你们俩肯定有说不完的话了!”
“我从村里到地区办事,是跟着我们领导去的,没好意思和她长谈,再说了当时我那死党拖家带口的要去过林卡。”
“哦!”
“她的儿子好乖啊!他竟然管我叫姐姐!好高兴!”
“是吗?高兴就好!”
“我那闺蜜现在的生活好幸福啊!”
我本来很想回:“这样的幸福正向你走来了呢!”或者“别急!咱们拖家带口去过林卡的日子也即将到来了呢!”但想了想觉得这种回信在胸口的“拉姆”还没彻底销毁前是一种引火上身,自找麻烦的举动。
于是就回了“是吧?幸福就好!”
这种只言片语、不痛不痒、没法接茬的回信虽然略显冷漠,但在这个“非常时期”还是更保险一些,免得因为用语不当或者过于热情的废话让事情节外生枝。
五天后,我对着镜子开始拆胸口的纱布。我像是在打开裹着奇珍异宝的层层锦缎玉帛那般一片一片将外层的膏药小心翼翼地撕开。我期盼着奇迹的出现,又怕希望落空。endprint
揭开纱布,镜中我的胸口上分散地凝结着干巴巴的暗红色血块颗粒,我用手轻轻抠下时,一块块米粒大小的干血块便沿着胸脯滚落了下去,有的还抠不下,稍微一使劲就拖皮带肉的,强行抠下来后就在那个位置又重新渗出殷红的血丝来,很疼!于是只好就此打住,赶紧拿出一个新的纱布涂上美容医院配的药膏,重新盖住。
再过五天后,我又裸着上身在镜前拆纱布,拆到一半,牛仔裤兜里的手机传来短信的铃声,划开手机,显示发送人为“卓玛”:“怎么没看微信啊你!还是觉得太突然?或者不愿意?”我觉得莫名其妙于是赶紧打开微信,看到未婚妻卓玛发的一行字:“你不打算向我求婚?”这句话令我又激动又紧张,感觉口舌都燥热了起来。想了又想,我知道这虽然是让我向她求婚的信号,但我老有种被她求了婚的感觉!就像她的这种传达方式,用短信提醒看微信的内容,这让我想起了奶奶常挂嘴边的一句谚语:“绕着荆棘扇兔子的耳光”。
“如果不是这纹身,我早就向你求婚了。”我对着镜子自言自语道。镜中的自己,韩版蓬松大背头发型,略带莫西干风格的剃发鬓角,棱角分明的脸上蓄着浅浅一层络腮胡;古铜色皮肤,身板硬朗,虽然腹肌们已经沉没,但腹部平坦匀称,还没有赘肉,两块结实的胸肌还是有模有样的。我很满意地打量着自己,以我这个形象,我有信心向卓玛求婚。“我将自己完好无缺地交给你好吗?”这时我的耳畔更加频繁地回响起她这句带着魔咒的话,要不我这就求婚?对!对!免得夜长梦多!我正打算立即回复短信正式求婚时我胸前拆了一半的纱布掉落在手机上,我抬头看了看镜子,乍一看,胸口之前很显眼的墨绿色“拉姆”确实不见了,这令我很高兴,但走近一看,洗纹身后留下了浅肉色的斑痕,而周边的皮肤是古铜色的,新旧皮肤色泽的反差使我的胸口依旧映襯出两个浅色的字:拉姆!
此刻我的心分成两派,激烈地斗争着。迫不及待想与卓玛肌肤之亲和害怕与卓玛有肌肤之亲的矛盾思想在内心激烈地火拼着!突然想到人家问的是求婚,求婚是一种前期志愿申请仪式,距离结婚啊洞房啊之类的实质性东西还比较远,并不是说一求婚一答应就得马上将新娘抱入洞房,毕竟这里不是原始部族,我也不是拿着矛穿着草裙脸上涂着面粉的部落酋长的女婿。于是没再怎么想就发了一条短信给我的未婚妻。
“卓玛,你愿意嫁给我吗?”
卓玛很爽快地接受了我的求婚,但我并没有太大的兴奋,或者说有一团顾虑的乌云遮盖着那个本应该很炫目的兴奋。
“咱打算啥时候领证呢?”卓玛接受求婚后又立即发来一条短信。
“……一般一年后会恢复原样”想起那个大夫讲的这句话,我觉得自己绝对等不了这么久。我在较长的“皮肤自我修复期”与迫不及待想验收卓玛完美无缺身体的欲望之间折中选择了公历7月7日,也就是过一个月之后。
“为什么是7月7日?”卓玛回信反问?
“因为是七夕!”
“拉倒吧你!七夕算的是农历!如果这样选好日子的话,我倒也想过藏历10月15日,我们拉萨的白拉姆节,你一定知道这一天的意义吧?”
我当然知道,这个每一年让拉萨姑娘们最兴奋的日子。据传护法神班典拉姆的女儿白拉姆和大昭寺护法赤尊赞相爱后私定终身惹怒了班典拉姆,于是王母娘娘,哦不!班典拉姆将两个情侣隔于拉萨河南北两岸,每年藏历10月15日才允许隔河相望一次。现在有人将这一天称为藏族的情人节,不少情侣也会特意选择这一天领证。但我脑子里一不小心就会将这个故事与《牛郎织女》混作一团。
“当然知道!藏历10月好像对应的是公历12月了吧?”
“还是公历6月10日去领证吧!6月9日我刚好结束驻村返城。”
我只得说好。因为一开始就是我追求卓玛的,另外虎视眈眈的竞争对手确实也不少,我必须认清形势,抓住机遇。我只希望自己的体质超凡、皮肤细胞们很争气,希望皮肤自我修复组织兢兢业业加班加点,发扬“争分夺秒、连续作战”的精神,争取在与卓玛的肌肤亲密接触前,“洗心革面、痛改前非、还原如前!”
离领证的日子只剩下三天了,这三天的时间简直弥足珍贵,又度日如年!我在期待与惧怕之中度过了这三天。三天里,夜晚我加大药膏剂量,用纱布包好胸口纹身疤痕;白天阳光明媚时就袒胸露乳仰躺在院子里,期待着高原强烈的紫外线辐射将浅色纹身斑痕与周边皮肤颜色中和,等到了领证那天,纹身疤痕自然愈合匿迹,看不出丝毫来。
6月10日清晨。镜前半裸的我,右手耷拉着,指间捏着纱布,镜中的自己有些失望地眨巴着眼睛,看着那胸口,白斑构成的“拉姆”两个字,只要凑近看依旧清晰可辨。看来“拉姆”是铁了心要留下来看我闹洞房,然后看着我被闹出洞房。
此时,一首仓央嘉措的道歌从街面的音响里飘飘悠悠传来:
夜半去寻伊人
黎明却降大雪
隐瞒无济于事
脚印全在雪上
这真是专门给现在的我配的背景音乐啊!不过我想,即使越抹越黑,也要把“脚印”从雪地上抹掉!
于是我实行了下下策的权宜之计——plan B:贴膏药。我取出一片差不多巴掌大的肉色膏药,平平地盖着纹身贴了上去。
咦!什么也看不见了,我盖住了“拉姆”,似乎感觉盖住了卓玛的眼睛。这下潘多拉的盒子被膏药给合上了?能合住多久?盖得住初一能盖得住十五?这是掩耳盗铃还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我领证结婚的大喜日子,却被这样的担心充斥着。
9点左右,卓玛穿着一身黑底金丝绣花的丝绸藏装过来了,柔软亮丽的藏装上流着光。她将手里拿着的邦典(藏式围腰)放在一旁,帮我穿上我的藏装,我将藏装的领口提到头顶,双手置于后脑勺,看着镜中忙着帮我整理袍子后褶的卓玛将后面的头发绾髻于脑后,这显得她的脖子白皙细长,里面粉色藏式衬衣的袖口和领口挽在藏袍的袖口和领子之外,随着她帮我系腰带的动作,她的裙摆下面偶尔露出黑色高跟鞋,那个鞋跟碰触水泥地板的“哒、哒”的声音很美妙,扣人心弦!我浮想联翩,暂且忘了胸前那个用膏药合上的潘多拉盒子。endprint
10点,我和卓玛穿着藏装在民政局附近的照相馆里照结婚照和几张简单的“婚纱照”。在镜前整理袍褶梳理头发时,我再次亲眼目睹了女款藏装惊人的修身效果!镜中的卓玛穿上藏装变得更加修长苗条,亭亭玉立,几乎要亮瞎我的眼睛,加上高跟鞋,仿佛要高过我这1米78的身高。
“咦!你怎么不系上邦典呢?”我想她如果系上这宛如彩虹的邦典会更加迷人。可是她只是拿在手上,却没有往腰上围起来。
“还没有领证呢!一拿到结婚证我就围上。按我们拉萨的习俗,结婚之前女孩是不能围邦典的。”她的这句话却让我鬼使神差般地想起她的另外一句话——“在婚前不想太草率!领完结婚证的洞房夜,我将自己完好无缺地交给你好吗?”
想到这句话,我由衷地想讴歌夜的美。
下午5点,我和卓玛满面笑容地走出了民政局办证大厅,各自边走边端详着自己手里暗红色的结婚证。
“呀!尼次!你从男友升级为老公啦!我们去尼泊尔餐馆小小地庆祝一下!”卓玛将结婚证揣进怀里后边往腰上围邦典边对我说。
我“好好”地应着,眼前却浮现出我将一碗白净的生米倒入高压锅,然后迫不及待地打燃煤气灶的情景。我看了看天,太阳依旧当空,高高的。
我们在尼泊尔餐馆点了丰盛的异国风味食品和五光十色的朗姆酒,当作小小的婚礼,耗掉余下的白天光景。
入夜,繁星点点闪烁在夏夜。穿过华灯初上的布达拉宫广场,我和卓玛牵着手来到了她住的公寓楼。我借进入卫生间解手之机,赶紧脱掉藏袍的袖子,解开茧绸衬衣领襟右侧和腋下的藏式纽扣,扒开衬衣,检查了一遍胸口,那肉色的膏药与我的肌肤似乎浑然一体,只是有股很浓的药味扑鼻而来。我洒了一点香水后放心地呼出了一口气,走出了卫生间,这时卓玛已经脱掉了藏装,穿着黑色打底裤踩着高跟鞋“哒哒”地走进了卫生间。
我点了一根烟,坐在卓玛卧室的一张椅子上。她的闺房很整洁,一缕清风从阳台拂过卧室的窗纱,窗纱轻轻舞动在双人床边桔红色的台灯上。
静静的夜里,窗外传来大昭寺金顶风铃在风中摇曳的“叮叮”声,我下意识地稍稍挪动了身子面向着大昭寺,默默地祈祷今夜一切顺利,但紧接着脑中出现了两个问题——佛会搭理这种事情吗?佛会为一个夹着烟祈祷洞房平安的人加持保佑吗?
此时,卓玛穿着一件睡衣,拖着拖鞋走出了卫生间。
过了半小时后,我和卓玛在那张床上绸缪激吻,忘乎所以中已是宽衣解带、蹬鞋丢裤。
“咦!你的胸口怎么啦?”卓玛从我身下轻轻抚摸着我胸口上的膏药问道。
“哦!这个,我今天胸口有点疼……”
“是吗?”卓玛说着停了一会儿,想了想,伸出她细长白皙的左胳膊,说:“巧了!我这边的肌肉也有些酸痛,也贴了膏药”。
我看见卓玛的左上臂也贴着一片膏药,这使我提到嗓子眼儿的心,慢慢沉了下去。她胳膊上的这片膏药像是来陪伴和呼应我胸口这莫名其妙的膏药似的。于是我顺水推舟:“咱俩这是情侣装啊!”
其实,我此时真想抚摸着她的那片膏药并蠕动着喉结,深情地对膏药说,谢谢你!亲爱的膏药!
躲过了这一劫,我便肆无忌惮地继续狂抱软玉温香。
一对新婚燕尔干柴烈火,厮磨绸缪,水乳交融,少儿不宜。
云雨罩巫山之后已是大汗淋漓……
半夜,被清風抚弄的窗纱挠醒了我。床边的台灯依旧亮着,我的手又摸向了卓玛。当我们又一次开始厮磨绸缪时,卓玛突然停止了亲热,我看见她的目光直盯着我的胸口,像是在研究一幅地图。我低头也看了一下自己的胸口,呀!胸口的那片膏药已不翼而飞了!也许是在缠绵的“肉搏”和淋漓的大汗中膏药失去了粘性脱落了。我的心又跑到嗓子眼儿了,扑通扑通!卓玛微微转动着眼珠子,目光在我胸口轻轻扫了两下,然后挤了挤眼珠眯眼思考了几秒,突然她眨巴了几下眼睛,然后不太自然地对我微笑了一下说:“你的膏药掉了。”
“哦!哦!不碍事不碍事……”
卓玛闭着眼睛用双手从我身下抱上来,然后我们又继续着鱼水之欢。但第二回合的缠绵似乎更像是一场例行礼仪,卓玛一直闭着眼睛,不冷淡也不激烈。完事儿后,相互礼仪般地抚摸片刻后,她翻过身背对我睡着了。我也背对着她,眨巴着眼睛无意识地看着对面粉白色印花墙纸,心里却有些忐忑不安,我暗暗低头看了一下胸口,她到底看到了没有?如果看到了,怎么会是那种反应?我在试图读懂那几秒里她眼神的内涵的过程中也睡着了。
一缕灼热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射到我的脸上,我醒了。于是翻过身,看见卓玛依旧在甜甜的梦乡里。我端详着我娇美的新娘,她的酒窝很美,她的脖子细长,她的胳膊……等一下!!她的胳膊上怎么也有跟我胸口这个色泽一样的斑痕?这不是昨夜她贴膏药的地方吗?膏药已经脱落了,露出的印迹很像是纹身洗后留下的白斑。当我确认那是文字时,心扑通扑通直跳,是的,尤其第二个字很清楚是“次”,但第一个字模糊不清,又像“尼”又像“巴”,到底是“尼次”呢?还是“巴次”呢?如果是“尼次”,她为什么会遮起来呢?当我急切想看清,凑近去时卓玛翻了一个身,将胳膊埋入了被窝里……
责任编辑:邵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