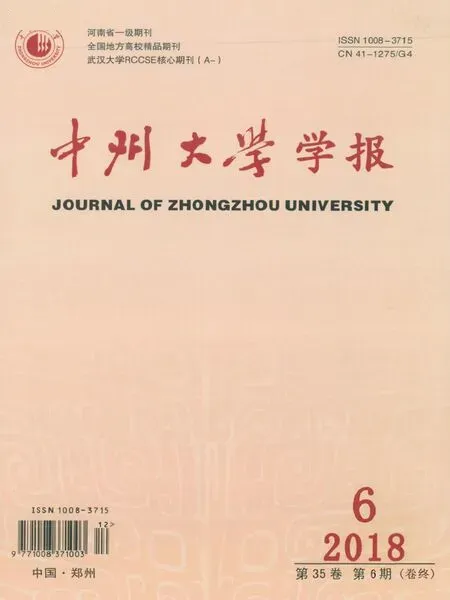从四个视角看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文学
谭旭东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从1978年至今,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环境,这40年中国文学走过了不同寻常的道路,经历了自身的变革,无论是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散文,还是诗歌,乃至儿童文学、科幻文学和文艺理论批评都取得了不小的进步,涌现出不少优秀的作家作品,形成了独特的时代文学景观。这40年间,中国文学经历了多重时代的变革,经受了来自内部与外部的双重蜕变,构成了带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的文学史知识谱系,形成了中国文化中堪与五四现代文学相媲美的最具有活力的部分。
一、从媒介与媒介环境变化看
观察和梳理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文学的历程,第一个需要考量的是其外部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其媒介文化环境的变化。从这一个视角可以发现,中国文学经历了由传统的印刷文化环境到电视文化环境,再到网络文化环境,直到当下的自媒体环境的多重场域,且这多重场域有时是单独用力、左右文学的发展;有时是同时存在、互相影响,形成了立体的文化空间,对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
(一)印刷文化环境
在这一文化环境下,图书出版和文学期刊引领文学风潮,报纸也搭建重要平台。1978年后,至80年代中期,几乎每一个重要作家与文学现象都与图书出版及文学报刊有关。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十月文艺出版社和各地文艺出版社,还有《人民文学》《当代》《十月》《收获》《青年文学》《萌芽》《青春》《作品》《上海文学》《花城》和《清明》等文学期刊,可以说,引领着年轻人的阅读;《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中国青年报》的文学副刊和《文艺报》这样的专业报纸也培养了一大批文学新人,参与了多个文学的论争。就是《辽宁青年》《青年博览》和《中国青年》这样的青年期刊,也成了文学的阵地。文艺出版社以纯文学出版为主业,文学阅读成为时代风尚。
(二)电视与电视文化环境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黑白电视普及,进入普通家庭;90年代初,彩色电视普及,城乡居民都生活在电视机陪伴的环境里,电影逐渐淡出了大众的日常生活。随着港台电视连续剧进入,台港流行文化与通俗文学风行一时,随后是家庭情景剧、肥皂剧和娱乐频道、选秀节目,成了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电视媒介比期刊报纸更有影响力和话语权,电视塑造名人,追星成为时尚。电视培养了大众对视觉文化的偏好,于是,深沉的文字阅读变成了“观看”,大众看小说,都要追求“好看”,是否有视觉冲击力成为文学写作的一个重要标志。电视为了博得更多的收视率,它取向一种中性文化,于是,年轻人扮酷,老年人装嫩,就成了一种文化消费心理。美国媒介文化研究专家阿瑟·阿萨·伯格把美国的电视比喻成“侵入一株大树的真菌”——“你在外面什么也看不出,但真菌却慢慢杀死了大树”。他还认为“电视正在破坏我们的文化,腐蚀我们的政治生活”[1]102。在电视文化环境下,与欧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似的娱乐为底色的青年亚文化出场了,电视文化改变了整整“80后”一代人,也改变了其他社会群体。
(三)网络与网络文化环境
网络媒介在90年代后期进入公众生活,但真正发生大的影响力是在2000年以后。随着个人电脑的普及,网站、个人主页、BBS论坛和QQ聊天给大众提供了无门槛的表达平台和空间。网络平台是一个很大的草根社区,网站也好,主页也好,还是QQ聊天空间也好,都像一个个不同的社区,让人人有话语权,让人人都可以展示自己。不过,草根社区让大众有了话语空间,也就消解了真正意义上的话语权。印刷文化建构起来的话语权威,在网络文化环境里不再具有绝对的权威,甚至还可能被网络平台祛魅。传统的图书和报刊编辑的权威也受到了挑战。文学写作自由化、民主化、大众化,网络文学形成了一种与民间文学类似的特征。
(四)自媒体文化环境
2010年以后,微博、微信和公众号出现,原来的网站和博客似乎成了信息孤岛,因为微博、微信和公众号与个人电脑、iPad、手机与新技术、人工智能快速随身联动,形成了一种新媒介互联网,它们更能激发人们的表达欲望,并能迅速实现信息互动,其影响力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种媒介形态。在自媒体时代,纯文学期刊和报纸读者很少,发行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有数据表明传统的文学期刊和报纸基本上处于亏损状态,纷纷倒闭停刊,但网络文学与新媒体写作热闹非凡,且成为重要的文学生活。“余秀华现象”就是一个自媒体时代出现的例证,《诗刊》杂志在微信公众号里就把她推到了成千上万个读者面前。余秀华这样的脑瘫患者的形象,在电视文化环境里是不可能变成诗歌明星的,因为她的形象不具备视觉文化的标准;而利用传统的纸媒,她的诗作也不可能赢得众多读者的青睐;但微信公众号的独特的传播方式,使其迅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于是,从自媒体到报纸媒体,“余秀华现象”逆向走到了公众的视野。
二、从政治经济环境看
政治与经济一直是规训和制约文学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当代,政治对文学不但具有引导作用,还有制约与规训,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一直是处在特殊的管理机制里运作的。众所周知的中国作家协会及各级作家协会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管理机构,它不但具有文学管理职能,也有规训和制约的属性。它表面上是一个公共文化机构,属于群团组织,但实质上,它是一个国家意识形态管理机构。经济也是文学发展的基础,是物质基础,经济环境本身也孕育着新的文学,并成为文学书写的内涵,如以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等为代表的“改革文学”就是改革进程的忠实记录者。改革开放40年,政治在上,经济在下,文学在政治和经济的中间运行,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现象。
(一)改革开放之初
改革开放之初,政治清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并存,个体户与民营经济能快速致富但没有社会地位。文学作为年轻人的梦想寄托,具有莫大的魅力。“人”的主题是新时期之初文学的基本主题,戴厚英的《人啊,人!》倡导人道主义,王晓明、陈思和等提出“人文精神大讨论”“重写文学史”等命题,等等,就是在改革之初宽松的包容的政治环境下文学界的五四精神回归与重聚。而“朦胧诗”“改革文学”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之所以能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学符号,也与启蒙的思想和改革的时代主题相一致。
(二)90年代市场经济时期
90年代市场经济时期,个体户、民营企业开始获得尊严,但商业化浪潮冲击了文学与文化,经济往高处走,但文化往低处走。纯文学开始走下坡路,诗歌被边缘化,文学期刊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小,纯文学开始小众化。以作家协会主导的主流文学圈也开始分化,一部分作家下海,一部分作家走流行文学的路子,还有一部分作家逐渐游走在主流与民间之间,寻找适合自己的路径。但由于强大的文学体制的维护,主题写作与纯文学依然有很大空间,顺应时代的写作被不同程度地强调和扶持。
(三)21世纪初
21世纪初,社会贫富悬殊,矛盾加剧,生态危机与经济危机并存,纯文学跌入低谷。这一时期,文化创意产业兴起,图书出版产业化,期刊报纸走向没落,而网络媒体、新媒介迅速崛起并取代纸质媒体。这一时期,图书出版品种越来越多,炒作热点及对畅销书的追求成为出版产业化的一个标志;网络文学和新媒体写作成为文学的新现象,网络文学和流行文化的IP开发,成为一种文学时尚和市场选择。但因其自主创新力不足,加上经济持续低迷,文学的大环境也受到影响,虽然2012年10月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振了大众对纯文学的信心,但文学图书出版码洋的急剧走低与文学期刊发行量急剧走低,是文学界心照不宣的疼痛。
三、从文学的评价机制看
改革开放40年,文学的发展除了受到媒介文化环境、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艺政策和经济环境的影响,还有几只无形的手在操控其发展和变化,那就是文学的机制,包括作家协会机制、市场机制、学院机制和民间机制。
(一)作协机制
作协机制包括官方专业作家制度、签约作家制度、鲁迅文学院作家班,还有各种形式的官方文学评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是官方最权威的文学评奖,筛选出了一批优秀作家作品,也试图以官方评奖方式把当代文学推向经典化。官方文学评奖,借助体制的优势,不但可以自成一个系统,还适时地与文学教育体系及官方媒介合力,促成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阿来的《尘埃落定》、王安忆的《长恨歌》和贾平凹的《秦腔》等体制内作家作品的经典化,但也把余华的《活着》和莫言的《丰乳肥臀》等佳作遗漏在茅盾文学奖之外。
(二)市场机制
市场机制,主要看市场的销量和码洋。自1992年实施市场经济体制后,文学的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诗歌分化成了众多的不成体系、不成规模,但自说自话、自我表演的小流派;小说分化成了纯文学写作和畅销小说的写作。这一变化,体现在作家富豪排行榜成为衡量作家的一个重要标准,还有汪国真、琼瑶、席慕容、席娟、海岩、郑渊洁、杨红樱等畅销书作家的涌现。市场是文学写作和出版的一个重要杠杆,余秋雨、易中天和于丹等大学教授也成为畅销书作家。
(三)学院机制
从专业评论和学院批评的审美标准来看,40年的文学又是不一样的样态和风貌。学院机制是与大学教育和学院批评紧密联系的,学院是一个话语自产自销的平台,大学教授可以把课堂和学生当作理论话语销售场所,文学在其中可以实现内循环;并且学院掌控着文学教育的权力,本身就有作品诠释的优势,文学教材的编写、作家作品的经典化和对文学现象的评点,甚至各种文学评奖等,都有学院的参与。学院是一个教育机构,却有着不低于作家协会这样的官方机构的文学话语霸权。
(四)民间机制
从草根文学角度来看,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文学,还存在一个不可忽视的民间机制,这种机制没有固定的机构来支撑,也没有所谓的领袖,却体现着大众趣味和民间立场,这是一种无形的机制,是文学与阅读的民意。民间机制没有官方机制那样的研讨会、新书发布会和官方评奖活动,但带着鲜明的叛逆性,甚至有时候会站在官方机制与学院机制的对立面,与其形成剑拔弩张的局面。在诗歌界,“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对立与争锋,就是典型的例子。当民间机制发生作用时,官方机制和学院机制往往会面临身份危机。
四、40年中国文学值得研究的现象
就文学本身来说,改革开放40年,涌现出很多作家作品,而且这些作家作品通过各种路径,尤其是大学文学教育,进入了文学史,形成了具有历史知识性质的现象。
(一)朦胧诗现象
相对于“伤痕文学”和“反思小说”,新时期之初的朦胧诗在精神气质和美学追求上既接续了五四文学,又联通了欧美现代文学,是当代文学里最成功的艺术尝试,也是改革开放中国文学最重要的成果。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之前,当代文学“苏俄化”,“朦胧诗”之后,诗歌和小说的形式探索摆脱了这一束缚,寻根文学和先锋小说在形式上模仿、借鉴魔幻现实主义、卡夫卡和博尔赫斯的潜意识心理剖析和客观叙述的技法。程光炜认为,新时期之初的这种形式探索,“它的意义,一点都不亚于1917年的‘文学革命’”[2]。如果说,“朦胧诗”是时代的先声,不如说,它是艺术的先声。它是新时期中国文学从语言艺术到思想境界最勇敢的表达,为后来的诗歌写作与文学的艺术化突围,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应该说,改革开放40年间,几乎所有的爱好文学的年轻人,都接受过“朦胧诗”的影响或洗礼。
(二)女性写作现象
女性写作现象,解构着男性霸权,重建男权世界看待女性的方式。女性写作,主要是女性诗歌写作和女性小说写作。女性诗歌的代表性诗人和作品是翟永明的《黑夜》《女人》、伊蕾的《独身女人的卧室》、唐亚平的《自白》和陆忆敏的《美国妇女杂志》等。舒婷是女性诗歌的先锋,她的《神女峰》《致橡树》《惠安女》等诗歌就像现代女性意识的宣言,告白了女性对独立人格的追求。女性小说的代表性作品是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和卫慧的《上海宝贝》等,女性小说从观念和主题上颠覆了男性霸权主义,她们用女性的视角来书写女性生命体验,包括女性的身体、性与成长等。女性小说写作因为在身体上过界,在传统观念具有强大惯性的环境下一时难以获得主流文学的位置,但女性小说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文学成果。
(三)金庸武侠小说与港台通俗文学现象
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他创作了《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等家喻户晓的武侠小说。先在香港《大公报》连载《书剑恩仇录》,《香港商报》连载武侠小说《碧血剑》;后他创办《明报》,为了吸引读者眼球,扩大报纸发行量,开始了长篇武侠小说《神雕侠侣》的连载写作,结果无声中应和了类型化文学写作的规律和方法,于是,他的武侠小说自然就成了畅销书。当然,金庸的武侠小说连载后受到欢迎,与香港的都市文化有关。金庸的武侠小说属于类型化文学,它的兴起,与电视文化趣味相通相适。金庸的武侠小说和港台通俗文学在大陆的广泛传播,和大陆改革开放与港台联通起来也有密切的关系。没有改革开放的政治宽容和文化包容,就很难有金庸武侠小说和港台通俗文学在大陆的流行。
(四)莫言现象
莫言初入文坛时,是军旅作家身份,但在新时期小说家中他几乎没有被归到“军旅文学”中去,而是被归到了“寻根文学”里去,也被划到“先锋小说”里去。他的小说创作似乎又带着强烈的批判意识,好像属于“现实主义小说”,甚至有人认为他是“新感觉派”的当代延续,如庞守英这样评价:“莫言是在不知不觉中,凭着本能,凭着潜意识,契合了新感觉小说的。他无意举旗帜,也没有发宣言,但是他的创作实践却告诉人们,他已经成为一名合格的指挥官,像指挥千军万马一样,指挥着那些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感觉。”[3]203
2012年10月,莫言以长篇小说《蛙》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振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信心,但也折射出中国文学的狭隘的文化思维,尤其是对莫言作品的魔幻现实主义的误读。另外,在历届茅盾文学奖中,莫言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也说明中国当代文学的阐释力及对世界一流作品的认识能力,还有待提高。莫言获奖后,中国主流文学界出现了两种态度,一种是欢呼,一种是贬损。欢呼者中部分属于狭隘民族主义思维,贬损者中更不乏失去理智的嫉恨。
(五)曹文轩现象
曹文轩是成长于改革开放中的儿童文学作家,尽管他最初以儿童文学成名,但他很长时间对“儿童文学作家”之名有所忌讳。不过,他的确是一位执着于儿童小说创作的作家,他的《草房子》《根鸟》《细米》《青铜葵花》被称为塑造了“忧郁的田园”,是诗意的写作,为广大儿童读者所熟悉。2016年4月4日,曹文轩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上获得“国际安徒生奖”,这个奖被童书界称为“小诺贝尔文学奖”,也有人认为它与诺贝尔文学奖有很大差距。因为,第一,它不是纯粹的文学奖,它的主办方是国际儿童读物联盟,因此“国际安徒生奖”是一个童书奖,或者说,就是一个国际儿童出版物评选,而且没有奖金,纯属荣誉性的国际图书奖。第二,诺贝尔奖是瑞典文学院主持的。不可否认,曹文轩的儿童小说创作是卓越的。由于曹文轩获奖是在儿童文学和童书处于市场黄金期的一个表现,使得很多人看不出:他的获奖与整个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水平并不完全契合与呼应,他超越了从五四以来的“儿童本位”。
(六)刘慈欣现象
2015年8月,刘慈欣的《三体》获得国际最权威的科幻文学奖“雨果奖”(73届);2016年8月,郝景芳的科幻小说《北京折叠》获得第74届“雨果奖”。连续两届拿下“雨果奖”,给中国文学提供了很好的阐释空间,因为科幻文学一直属于小文体,叶永烈、郑文光、童恩正、肖建亨、刘兴诗等的科幻小说虽然影响很大,广受儿童读者欢迎,但在当代文学里它几乎没有什么位置,也长期被人忽视。科幻文学一直被儿童文学所接受,并被儿童文学研究界和童书出版界归到儿童文学文类里,但科幻文学不甘于做“小儿科”,一直不愿意被当作“儿童文学”,可当代文学主流圈又没有它的位置,所以科幻文学一直处于边缘状态。刘慈欣和郝景芳的获奖,为科幻文学争得了荣誉,也使得许多科幻作家有了将科幻文学变成独立的文学文体的勇气。
(七)儿童文学现象
改革开放40年的前20年,儿童文学是紧跟着成人文学走的,或者说,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取向基本上保持着与整个文学一致的步伐。如新时期之初,成人文学中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的主题都在儿童文学里得以表现。但后20年,儿童文学完全与市场接轨,像一匹脱缰的野马,跑出了成人文学的藩属地,它变得相对独立,并恣意于市场的狂欢之中。儿童文学界普遍认为,进入21世纪后中国儿童文学经历了“黄金十年”,且预言2016年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后,又会迎来第二个“黄金十年”。其实,儿童文学市场需求量大与儿童文学创作的水平高是两回事,市场销量好,不等于儿童文学具有了经典水平。但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以前成人文学作家是不屑于儿童文学的,他们即使参与,也是被动地接受党和政府的号召。现在不少成人文学作家自觉进入到儿童文学创作行列中,如张炜、马原、赵丽宏、虹影等,都主动地加入到儿童文学创作队伍里,形成了一个儿童文学的“虹吸现象”。这是整个文学界没有意识到的,儿童文学自身也没意识到这一点。
(八)网络文学现象
网络文学是改革开放40年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80后”文学就是在电视文化向网络文学过渡时期涌现出来的一个文学现象,也是一个青春文化现象,它既适应了电视文化对“偶像”的追捧,也应和了网络文化的亚文化形态。进入新世纪,网络文学日益显示出强劲的势头,有三个原因:一是网络文学的兴起与个人电脑和网络的普及有关;二是网络文学因为凭借的网络就是最具有大众性的信息传播媒介,于是,网络文学一出现就带着媒体的优势,其影响力的扩大是很自然的事;三是网络文学的兴起与官方作家协会体制对众多写作的压抑有关。传统的机制把文学变成了某些人的特权或者一部分人的生存机会,而网络文学把文学的权利、写作的权利还给了所有人。值得深思的是,随着网络和新媒体的普及,网络写作、在线阅读或电子阅读成为大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此,网络文学能够成为一种文体已不值得争论,它会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以上这八种现象还缺乏很深入系统的研究,通行的几种文学史的写作还没有很好地分析它们背后的社会因素,也未阐释好它们的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特别是对于金庸、莫言、曹文轩和刘慈欣等都还缺乏准确的认识;文学史的书写还基本停留在排座次的地步,对当代文学与政治的纠葛还认识不足,当代文学研究者也未充分理清当代文学与媒介的互动关系,或者说,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文学还无法摆脱一些外在的场域的局限。
总之,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文学取得了很多可喜的成就,不但影响了当代人的日常生活、切入了语文教育,也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但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当然,这些问题的出现有的主要归结于内部原因,包括作家的修养和艺术追求,也有的则可以归因于外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种种迹象表明,1978年和2018年都是时代的一个重要节点,因此不难预言,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文学可能成为文学史书写的一个阶段,它甚至可以取代“新时期文学”这个命名。
2019年又将迎来五四的一百年,相信随着国内政治经济政策的调整,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的重组,中国作家的创造力既可能被激发,也可能被改造。无论如何,改革开放是大趋势、大潮流,中国文学会步入国际化的进程,融入多元的世界文化格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