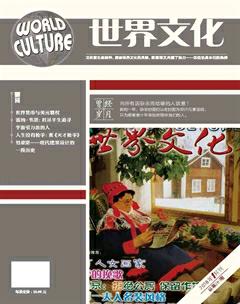包豪斯——现代建筑设计的一段历史
李珺

1926年12月4日, 一列蒸汽火车缓缓驶入德国东部的工业城市德绍(Dessau),火车上坐着1000多名宾客,来这里参加包豪斯学校的落成典礼。包豪斯校区位于德绍的城郊,宾客们首先要穿过这座古老的城市,当他们到达包豪斯校区,现代主义的建筑与城区形成了强烈对比。开幕典礼当晚,灯光照亮了包豪斯校区建筑的墙面,令这座建筑看起来像灯塔一样闪耀,带着活力照亮了战后八年的夜空。接下来的两天里,展览、音乐会不间断地上演着。一位学生这样写道:“当晚灯光照耀下的包豪斯建筑令人格外难忘,建筑外部的金属轮廓在光线的切割下,形成了一个无形的立方体。”艺术家和政治家们把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团团围住,43岁的他,是包豪斯的建筑设计师,也是这所学校的校长。
从魏玛到德绍:包豪斯的成立
国立包豪斯学校(德语:Staatliches Bauhaus),通常简称包豪斯。这座学校的起点是1919年的德国城市魏玛,瓦尔特· 格罗皮乌斯校长在一座没有任何建筑特色的公共大楼里成立了包豪斯学校。包豪斯的字面意思是“建筑的艺术”,格罗皮乌斯的目标是艺术与技术的统一,包豪斯采用工厂学徒制,进行双轨教学,并形成了一种新的工艺产业。现在,我们称这种理念和做法为“设计”。包豪斯希望学生设计的产品兼具艺术性和实用性。在这里,格罗皮乌斯设立了各种学科:金属、编织、美术、舞台设计和舞蹈。色彩这门课程由保罗·克利 (Paul Klee,1879年—1940年,德国画家, 1920年—1930年任教于包豪斯学院)、康定斯基( Wassily Kandinsky,1866年-1944年,俄裔画家,现代抽象艺术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奠基人,从1922年开始在包豪斯任教)来教授,他们在包豪斯开办了新的工作坊,我们今天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电器和家具即将在这里被逐一设计出来。

1925年,魏玛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艾伯特去世,右翼势力支持的兴登堡在新一轮的总统选举中获胜,魏玛的包豪斯学校被关闭。格罗皮乌斯开始在其他城市选址重建。社会民主党在德绍政党中占多数,他们同意给包豪斯学校的重建发放支持资金。德绍拥有7万人口,是德国重要的工业中心,对于前卫艺术和重工业的结合来说,可谓是一座理想的城市。校址被指定在了一处相对荒凉的地方,铁路把这片区域和城区分开。建筑师不必再受城市线条的限制,也不再需要遵循特定的规矩。当时,格罗皮乌斯相当于项目的客户兼设计师,这使得他可以从学校的真正需求出发来进行设计。他把学校各部门的建筑体交织在一起,组成了一个任意的不对称形状。学校特殊的要求决定了各建筑体之间的连接方式。包豪斯的建筑形式、意义和它所蕴含的情感,无法自一开始就为人们所理解。格罗皮乌斯认为如果从空中俯瞰的形式来看包豪斯,就很容易看清楚整体的布局。包豪斯不能只用一个角度来观察,一座大楼需要变换着角度去理解。艺术高等学院是整个学校的建筑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具标示性的一栋,这个工作坊坐落在建筑群的一侧,呈六面体,外立面的材料为玻璃,这使得工作坊内部与外部环境形成了高度延伸,内外一体,不管你是在楼内还是楼外,是演员还是观众,透过玻璃,你可以看到一切。格罗皮乌斯希望工作坊成为整座建筑的代表面、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那面。建筑群的中间部分是礼堂,其承担集会、表演等功能。整个建筑群中最高的楼群是宿舍楼,24个房间分布在4层空间里,每间宿舍都有一块伸出的阳台空间,黑白交错的外层颜色,与光影相呼应,这种手法后来被同时期的建筑师反复挪用。校长办公室位于建筑的中心,这一空中过道把技工学校、工作坊和艺术学校连接起来,在最初的草图阶段中,格罗皮乌斯已经有了这个空中过道的想法,讓他犹豫的是这座“桥”该建多大,如果太大,他就不得不与别人共享这一区域,如果太苗条,会显得缺少气势,最终他决定用钢铁作为这个空中过道的主要材料,这座桥贯穿两边的空间,突显立体主义的特点。完成建筑的主要外部设计和功能设计后,格罗皮乌斯需要决定朝向问题:建筑与自然环境相和谐,是创造学校美好环境的保障,他希望夏天的太阳能自然唤醒学生,提醒他们学习任务的开始,他把最主要的工作坊设计成东西向,使工作坊从早到晚都有光线摄入,技工楼则会得到太阳落山前的最后一道阳光。
从形式到情感:包豪斯的使用和影响
包豪斯建筑真正投入使用后,学生的感受却并非与格罗皮乌斯的设计和设想一致。他们最大的困扰是夏天阳光照射带来的燥热,很快,工作坊里都被挂上了窗帘,格罗皮乌斯追求的透明感不复存在。冬天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金属框架开始生锈,室内热量也很难保持,几年后金属框架就全部被换成了铝制材料。格罗皮乌斯原先的设想是让整个外立面和建筑本体分离,如今为了安全问题,这面玻璃墙又被装上了铁栏,玻璃外立面最终还是和建筑内体连接了起来。但格罗皮乌斯的优秀设想并没有被掩盖,外立面仍像是一面独立的玻璃墙,直接站立在地面上,不再承担承重的任务,而是由墙下的支柱来完成承重。工业建筑是测试新概念的最好方式,7年前与汉斯·迈耶 (Hans Meyer,1889年—1954年,瑞士建筑师,包豪斯第二任校长)合作设计法古斯工厂时,格罗皮乌斯就做过部分玻璃窗帘的实验,不同的是在德绍,他实现了整面墙的玻璃窗帘立面。当时日新月异的美国建筑是格罗皮乌斯的灵感来源,德国在建筑艺术上无疑占有领先地位,但在美国这样的现代工业社会,新建筑每天都在拔地而起,这些建筑普遍庄严宏伟,这是德国同类建筑所无法比拟的。北美拥有丰富的资源,大公司拥有现代的工作坊,而德国当时还处在战后的物资短缺阴影下。格罗皮乌斯还效仿采用了福特汽车的生产线理念,使得包豪斯在一年内就完成了建造工程。endprint

在歐洲,包豪斯很快成了最受欢迎的电影拍摄对象和谈资,清晰的视线让人们可以看到每一处,大家可以看到别人,同时也被别人看到。整座楼身主要使用金属板搭构,外立面是整体的玻璃,简洁而敞亮,却丝毫没有隐私可言。包豪斯究竟是一个提供创作自由的地方,还是一个受压抑的场所呢?它抛弃了个人隐私,将公共利益放在了个人利益之上。格罗皮乌斯则可以通过校长办公室的桥上,随时观察他的作品。建校以来,包豪斯提倡创造的自由,一些批评者称这里为疯狂的实验中心。但作为一栋外表线条如此严肃的建筑来说,包豪斯带来的活力令人震惊。格罗皮乌斯的建筑其实相当实际,他想要向工业家证明自己的设计理念是理性的。整个建筑有四个楼梯间,区分出各个区域,没有任何花哨的装饰元素。所有不同的区域也可以互相交流,传统建筑里狭小阴暗的楼梯间,在这里变成了光线充足的宽敞转折中心,成为人们的会面点。所有的设计都是以相遇、交流为出发点,让校园成为教师和学生移动会面交谈的场所。包豪斯的礼堂并非一个封闭的空间,打开其中的一扇小门,剧场就可以和餐厅连接起来。就连学生宿舍也是共享式的,没有任何一处空间是适合独处的。每间卧室的小阳台从外面看,整齐地处在同一平面上,代表着集体的欢乐。平平的屋顶也可以被用来作为聚会的场所。在包豪斯,你几乎不需要走出校园,这里成了自给自足的小镇,找朋友只需要站在阳台上吹吹口哨就可以。玻璃墙带来的自由感和通透感是包豪斯值得自豪的地方,同时也代表着隐私的牺牲。透过巨大的玻璃,你可以看到在休息、工作的人们,甚至看到别人的私人生活细节。建筑里的所有元素都毫无隐藏,所有金属物件都裸露在外,很容易就能看出哪些材料已经使用多年。传统设计里想要藏起来的东西,在包豪斯都被展露在外面。在传统中产阶级家庭的走廊里,通常会挂上一幅画,格罗皮乌斯却把一块暖气片挂在了走廊区的墙面上,使它看起来像现代艺术展览一样,展现对日常生活物品的崇敬。但当时的德国是贫穷的战败国,后勤供应时常跟不上需求,格罗皮乌斯不得不使用一些朴素的机械构建,这样的包豪斯看起来更像是对工业时代旧欧洲的怀念,而非对理想中美国现代工业社会的展现。
对格罗皮乌斯来说这是一个完整的建筑事业,大到建筑设计,小到门把手的设计,他坚信建筑的整体与细节有着密切的联系,包豪斯试图通过细节的设计来实现这种统一的理念。室内设计是由包豪斯的学生来完成的,金属工作坊设计并制作了这座新楼所需的所有照明设备。油漆的颜色代表了不同的楼层和不同的工作坊,不同区域的功能分区。色彩的使用是为了突出建筑目的。颜色随着不同的房间结构而产生变化,实现了平面空间立体化。
把工作坊和学校建好之后,格罗皮乌斯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要处理:教师的住宿问题。要如何用全局的建筑观点来调和个人与团体呢?他决定把这个区域放在包豪斯校区之外,在离学校几百码的地方建了一些独栋房子。克利和康定斯基等一些老师住进了这些有点与世隔绝的房子,这样也更强调了他们大师级的身份。从外形设计和细节处理来看,这些房子就像未来中间阶级郊区独栋的样板房。一个广告影片宣扬了包豪斯学校学生和老师设计的生活物品,以及这些物品展示的未来生活品质,尽管房间设计处处代表着生活的艺术,但这并不代表入住的老师对这种环境感到满意。康定斯基就难以接受路人可以在外面透过玻璃看到室内,于是把玻璃用白漆粉刷上了,同时,室内大片的白墙也让他感到不安,于是用170种颜色重新粉刷了整个空间。
从昨天到今天:包豪斯的废弃与重建
很快包豪斯成为选举中左翼议会和逐渐壮大的纳粹党之间争论的焦点,1933年,深知在纳粹党的统治下学校注定会被关闭,这座当代最著名的艺术院校不得不把全校学生一起迁到了柏林。格罗皮乌斯则离开了欧洲,去寻找他的美国梦。纳粹党怀疑这些与德国传统风格相悖的平板房能做些什么。有人建议给包豪斯楼顶加上传统德国式的屋顶,随后放弃了。也有人提议把包豪斯的建筑继续加建,最后形成纳粹的标志形状。最后他们什么也没有做,这里成了一所女子烹饪缝纫学校,“二战”前夕,部分包豪斯校舍曾被用来训练纳粹军官。

1945年由于德绍遭遇空袭,包豪斯的玻璃墙遭到了损坏,格罗皮乌斯的教师宿舍则完全被摧毁,“二战”后,德绍被划入了民主德国。进入20世纪50年代,民主德国也不欣赏包豪斯的建筑理念,在一份官方文件里,他们认为这个学校的存在是对建筑理念的践踏。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仍是没有销毁包豪斯建筑,而是决定继续保留它,并草草补上了空袭时炸出的洞。为了表示历史已经翻篇,在格罗皮乌斯的教师原址地,新建了一座带着德国传统斜面屋顶的私人住宅,其他老师的房子则继续被遗弃在树林里。
瓦尔特·格罗皮乌斯于1969年在美国去世,他在美国成名,并彻底改变了美国的建筑历史。又过了20年,官方对包豪斯的评价终于发生了变化,1976年包豪斯终于被重新修复。柏林墙倒塌后,原先的教师宿舍也被重新修建成了展览区。包豪斯学校的思想体系是现代设计的发源地,对世界艺术的发展有着建设性的推动作用,如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包豪斯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包豪斯校区被重新投入使用,一半作为校区,一半作为展览区重新对外开放。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