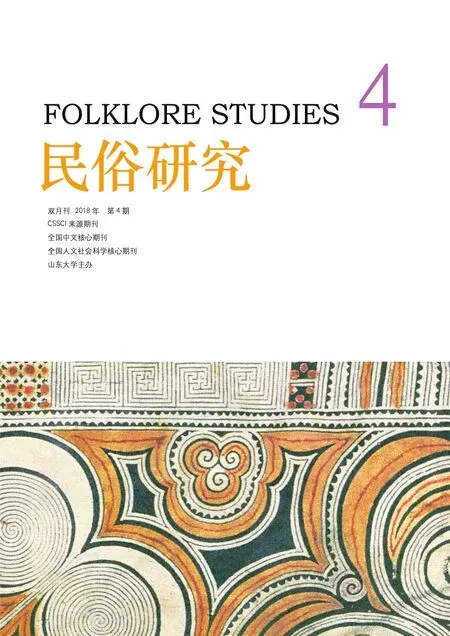物质文化研究的格局与民具学在中国的成长
周 星
“物质文化研究”是一个既古老又很有新意的学术领域。中国古代既有“博物志”记录的积累,也有“格物致知”的智慧传统,还有如赵明诚《金石录》那样的朴学路径,但近代以来,“博物”和“格致”逐渐向“科学”缓慢地实现着知识体系的转化*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331-344页。,随后,中国的“物质文化研究”便基本上是在西方现代学术的影响之下,形成了诸如考古学、博物馆学、人类学及民俗学的物质文化研究、技术与物质文化史、艺术史、工艺美术学等一些不同的“板块”。20世纪70-80年代以后,在西方学术界逐渐兴起了跨学科的“物质文化研究”(Material Culture Studies),试图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学术领域关于“物”的研究积累予以梳理和体系化。尽管这些努力始终面临着不同表述中研究视角、话语体系和不同用语以及关键词的交错、混淆和重叠,但它还是逐渐地在其当代“文化研究”中,发展出了所谓的“物质转向”。和较早时期以考古学和历史学(艺术史)的物质文化研究相比较,这一新的“转向”突出地强调“物”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它的社会生命史、符号性、语境性、文化关联性,以及它对于人的自我认同、社会身份建构等所具有的价值,甚至涉及“物性”对于人性的形塑等。近年来,这一“转向”也开始影响到中国,刺激中国学者也对物质文化研究相关的理论问题予以关注。*韩启群:《物质文化研究——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物质转向”》,《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孟悦、罗钢主编:《物质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韩启群教授引用了阿瑟·埃萨·伯格(Arthur Asa Berger)在《物的意义:物质文化导论》中的经典性说法,即正如“文化”的定义面临困扰,“物质文化”也有数百种之多的解说,且受到不同专业背景的影响*Arthur Asa Berger,What Objects Mean: An Introduction to Material Culture,Walnut Greek Left Coast Press,2009. p.17.,接着,他在自己的论文中整理了西方学者有关物质文化的多种定义,包括考古学家的说法(人类一切遗留物)、人类学家的说法(物质文化不是文化本身,而只是文化的“产物”),以及很多其他观点,例如,有的学者把物质文化局限于“人工制造”,但也有人主张,它还应该包括形成生活世界的所有自然物等等。*转引自韩启群:《物质文化研究——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物质转向”》,《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显然,对应于不同的定义或界说,物质文化研究也就非常自然地形成了许多不尽相同的研究路径:从具体的物到抽象的物、从实用功能的物到表达功能的物,从富于技术含量的物到富于象征意义的物,等等。
在学习和思考物质文化研究的相关问题时,笔者深感当前中国学术界亟需在积极借鉴西方物质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视角的同时,还应该对中国自身的物质文化研究领域的基本格局予以必要的梳理和总结。但每逢此时,也就难免会痛感中国的物质文化研究尚有一块巨大的“缺漏”,亦即民具研究的落伍。笔者相信,只有尽快地弥补这一“缺漏”,彻底纠正相关的认知偏见,促使民具学在中国有相当的成长,中国的物质文化研究才有可能逐渐和海外的物质文化研究真正实现接轨,并最终得以并驾齐驱。
一、民具学在中国的“缺漏”
“民具学”是一门通过“民具”研究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文化的学问。所谓“民具”,就是普通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所制造和使用的用具、工具、器具等所有实物、器物的总称。正如“民具”一词,能够和“民俗”“民谣”“民话”“民艺”“民居”“民宿”等一系列概念相并置一样,它主要就是指那些民众生活里寻常可见但又不起眼的器物。民具学可以说是广义的民俗学(如果把民间口头文学的研究视为狭义民俗学的话)的一部分,也不妨称之为民俗学的物质文化研究。*钟敬文主编的《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曾专列“物质生产民俗”和“物质生活民俗”两章,中国民俗学的物质文化研究也大多把器物分为生产用具和生活用品两大类。主张在物质民俗领域开展综合性研究的美国民俗学家迈克尔·欧文·琼斯,曾将物质文化研究归纳为若干种视角:视手工艺品为历史传承物的视角、基于器物实体样式进行类型学研究的视角、透过物质民俗揭示所属群体之文化(设计、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的视角、关注制作和使用器物之行为的视角等。*[美]迈克尔·欧文·琼斯(Michael Owen Jones):《手工艺·历史·文化·行为:我们应该怎样研究民间艺术和技术》,游自荧译,《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5期。所有这些视角虽然和人类学、考古学的物质文化研究纠葛不清,但美国民俗学的物质文化研究依然是形成了一定的传统*张丽君、李维屏访谈:《美国民俗学领域物质文化研究的兴起与现状——印第安纳大学民俗学与音乐人类学系杰森·拜尔德·杰克逊访谈录》,于倩、程安霞译,《民俗研究》2012年第4期。,也大都与我们在此讨论的民具研究可以通约。
当然,民具学同时也可以是文化人类学之物质文化研究的一部分,亦即探讨“人”与“物”的关系,通过实物、器物和广义的“物”去研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等,只是文化人类学的物质文化研究所视之为研究对象的,并不局限于成“器”(例如,农器、乐器、玉器、陶器、漆器、竹器之类)、成“具”(例如,家具、灶具、玩具、灯具、文具之类)之物,举凡食物(饮食人类学)、财物、药物(医药人类学)、嗜好品*高田公理ほか編:『嗜好品の文化人類学』、講談社、2004年。、货物、礼物、饰物、遗物(物化的遗产)、吉祥物*祁庆富编著:《中国少数民族吉祥物》,四川民族出版社,1999年。、纪念物、技术产物、以及人类的各种“造物”行为*床呂郁哉、河合香吏編:『ものの人類学』、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11年。、拜物教、商品化*本田洋:「商品としての南原木器-韓国のものつくりに関する一試論-」、伊藤亜人先生退職記念論文集編集委員会編:『東アジアからの人類学-国家·開発·市民-』、第3-18頁、風響社、2006年。、影响族群关系的商品交换体系*吕俊彪:《财富与他者—— 一个古镇的商品交换与族群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带来文化传播的物资流动*张应强:《木材的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肖坤冰:《茶叶的流动:闽北山区的物质空间与历史叙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河添房江:『唐物の文化史』、岩波書店、2014年。[美]高家龙:《中华药商:中国和东南亚的消费文化》,褚艳红、吕杰等译,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物的社会生命史(物的文化传记)*罗易扉:《松散的连接:物的社会生命史》,《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4年第5期。,甚至于野生动植物(例如,民族植物学或文化植物学的研究路径*关于文化植物学,可参阅街顺宝:《绿色象征——文化的植物志》,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13页。)等,皆可大做文章,故其视野要比民俗学、民具学来得更加宽阔。*关于文化人类学的物质文化研究,较方便的中文参考读物有:黄应贵主编:《物与物质文化》,(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2004年。[英]迈克尔·罗兰(Michael Rowlands):《历史、物质性与遗产》,汤芸、张原编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马佳:《人类学视域中的物质文化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13年第4期。尹庆红:《英国的物质文化研究》,《思想战线》2016年第4期。总之,文化人类学是通过“物”的存在和演变确认文化及文明的特点与进化,通过既定社会中“物”的交换与流动等现象分析社会的功能、结构与变迁。*彭兆荣:《物的民族志述评》,《世界民族》2010年第1期。
有不少学者认为,“物质文化研究”难以被文化人类学、考古学或民俗学等某一门学科所单独涵盖,它其实是在许多学科领域内部分别独立生成,并先后形成了各自的理论、路径和方法,只是到最近数十年才初步出现了跨学科趋向的一门颇为庞杂的学问。*孟悦、罗刚主编:《物质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潘玮琳:《海外中国研究的物质文化转向》,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编:《世界中国学理论前沿》,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第56-70页。以“人”与“物”的关系为主题的物质文化研究,既可以涉及历史,也可以涉及当今;既可以是局地的、族群的研究,也可以是全球化的研究;它构成了对现有诸多学科的越界和连接。例如,对于“技术”的人类学、民俗学与工业考古学研究*张柏春、李成智主编:《技术的人类学、民俗学与工业考古学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年。,对于“艺术、技艺与科学”之技艺物质文化的研究*罗子婷、罗易扉:《艺术、技艺与科学:今日欧美技艺物质文化研究读本述评》,《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5年第4期。,对于“民族与物质文化史”的相关研究*卢勋、李根蟠:《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民族出版社,1991年。等等,就是很难被现有的学科分类所固化,反倒是需要在“技术”“技艺”或“生活文化”之类的一些关键词的统领之下,能够将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建筑史、技术史、手工艺研究、产业考古学等很多领域对于“物”的研究成果整合起来。虽然诸多类型的旨在探讨“物”在社会及文化中的作用及其存在意义的研究,往往都是说要把日用物品,包括代代相传的、手工制作的俗凡之物也纳入视野之中,但从实际出版的成果来看,总体上还是以艺术品、工艺品或那些可以被用来讲“故事”的“物”为主,相比之下,那些真正草根性的、由庶民默默地使用着的“民具”,通常是很难真正引起学者们的关注。
在中国物质文化研究的基本格局里,大体上,考古学的物质文化研究,指向的当然是古代甚至远古,很多时候,它可以弥补史料的不足,不断地通过发掘、发现和复原的作业,使得后人对于古代乃至于远古的历史真相有所发现。如果和考古学相比较,民具学的指向则完全是当下,虽然它也关注一些传统的民具,例如,风车、水车、石磨、铁犁、卧具、灯具之类在古代中国是怎样的,但这种兴趣主要还是因为它们在当下的民众生活里仍然被使用着。归根到底,民具学主要还是对现在老百姓的物质文化生活感兴趣,只不过有时候它需要寻求对于某些器物的起源性解释。以在第三次文物普查中对蔚县夏源关帝庙壁画*戴建兵:《府县乡里百工:蔚县夏源关帝庙壁画》,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的“发现”为例,固然它是考古学或清代文物研究的对象,但壁画中“百工图”的意义,从民具学的立场看,却是在于它和后世现存的民间百工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连续性。
在中国的“文物研究”领域,将“文献”和“文物”结合起来进行物质文化史的研究,一直是最为基本的学术理路。由于绝大部分的文物存量和文献记载主要都是和帝王将相有关,因此,即便研究者,例如,沈从文先生在致力于“为物立传”的“抒情考古学”研究之际,非常重视和关照到一些日常琐物*季进:《论沈从文与物质文化研究》,《爱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纪要》第151号,2018年。,但要涉足更为寻常且“名不见经传”的民具的世界,则几乎是不可能的。和“民具”这一范畴存在着一定程度重合的,确实是有“民族文物”和“民俗文物”之类的概念。有时候,这两个概念还会被混用在一起。*例如,白劲松主编:《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俄罗斯民族民俗文物》,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4年。“民族文物”是以“民族”为单位来整理物质文化的资料,它的指向更多地是为了体现物质文化的民族特点,甚或论证民族文化的辉煌,所以,器物的族属或器物的民族特点往往被视为关键。*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编:《凉山彝族文物图鉴》,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美术出版社,2004年。德红英:《达斡尔族木轮车的民俗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此种思路的物质文化研究,主要就是“族别式”*关于“族别式”的文化研究,参阅周星:《中国民族学的文化研究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开放时代》2005年第5期。的物质文化研究;它经常把器物的历史上溯至远古,但同时又把它视为“民族史”或“民族”文化史的一部分,例如,对土家族“器物的创制及其演变”的研究*黄柏权:《土家族器物的创制及其演变》,《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便是如此。若要克服“族别式”物质文化研究的局限性,有时候,就需要有“族际式”或通文化、跨文化的物质文化研究*任国英:《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物质文化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1年。,亦即强调某些物质文化的族际共享或跨文化传播。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存在一个不成文的惯例,亦即往往是把汉族之外的才特意称作是“民族”的,于是,“民族文物”也就更多地或主要是指“少数民族文物”了。显然,这和本文讨论的“民具”及民具学的理念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若是以孟凡行分别在陕西关中和贵州苗寨所进行的民具研究为例,他首先需要确认它们分别作为汉族或苗族的“民族文物”的属性,然后,再去强调这些器物的民族文化特色,然而,正如他的研究所已经表明的那样,即便“理论”上可以将关中汉族民具和贵州苗族民具分别视为“民族文物”,但贵州苗寨的“民具组合”或“民具群”却难以叙说苗族文化的特色,因为它们和周边其他民族所使用的民具有很多共享的部分,而且,其不少民具还是通过集市从其他民族那里购置而来的。至于关中农村的民具,如果在不需要将它们和其他族群的民具进行比较时,说它们是“民族文物”,似乎也没有多大的意义。显然,“民族文物”的概念若被僵硬地理解,将会妨碍通过民具探讨普通民众之生活文化的尝试。其实,在具体的学术实践中,很多情形都会凸现出这一概念的局限性,例如,把中国西南甚至东南亚地区广泛存在的“铜鼓”说成是“民族文物”,似乎并不能由此确认它的民族属性或民族文化特色。
关于“民俗文物”,确实是和本文讨论的“民具”概念密切相关。按照徐艺乙等学者的提示,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曾经相继出现过“民俗物”或“民物”等用语*徐艺乙:《中国民俗文物概论》,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194-202页。,应该是较为接近“民具”的理念。但毋庸讳言,“民俗物”或“民物”这些表述,后来并没有在中国学术里发展出进一步的讨论,相关的学术研究几乎没有展开。尽管如此,截至目前中国民俗学对“民俗文物”的相关研究,还是能够成为民具学非常重要的学术资源,值得民具学家认真地汲取和借鉴。但在笔者看来,“民俗文物”的相关研究还需要朝着民俗学的物质文化研究,亦即民具学这一方向再做一些延展。为此,笔者甚至还曾经特别提出过“中国民俗学的物质文化研究应该向日本的民具学学习哪些方面的经验”*周星:「中国民俗学の物質文化研究は日本の民具学から何を学ぶべきか」(What Chinese Folklore Learn from the Study of Folk Implements in Japan?)、『非文字資料とはなにかー人類文化の記憶と記録ー』、第64-75頁、神奈川大学21世紀COEプログラム 第1回国際シンポジウム、2005年。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民俗文物”这一概念也存在一些难以绕开的困扰,首先,因为它是基于民俗学家对于民俗的“分类”得以成立的,故在相当程度上,很自然地就可能带有民俗分类本身的局限,这样的民俗分类,其实大都是出自民俗学家自身较为随意的主观判断。按照民俗学的观点,并不是所有的文物都是民俗的反映,而只是与民俗有关的文物才可能被作为民俗的实物证据。也就是说,那些被人为地排除在民俗分类之外的,自然也就无法成为“民俗文物”,例如,收音机和手电筒若被视为和“民俗”无关,那它们也就很难成为“民俗文物”。其次,“民俗文物”,主要是在“文物”研究的话语体系之内对其价值进行判断的,这就容易使之脱离它所由产生的社区生活背景而成为零散的孤件;文物价值判断的“稀缺”(物以稀为贵)原则,还有对它们的类似“老古董”之类的理解*[英]迈克尔·罗兰(Michael Rowlands):《历史、物质性与遗产》,汤芸、张原编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第184页。,自然都会影响到研究者对“民俗文物”的看法。也因此,现在我们看到的“民俗文物”,绝大多数都是一些精心特意挑选出来、被认为可以反映某些民俗事象的民间物件,至于更为大量、普通、不起眼和重复存在的民具,则是无法被“民俗文物”所涵盖和观照到的。除此之外,“民俗文物”之所以不能被完全等同于民俗学的物质文化研究,还因为即便它有时候能够成为非常重要的线索*[英]鹤路易:《中国招幌——西方学者解读中国商业文化》,王仁芳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但往往仍无法涵盖或反映某个传统行业或部门的技术体系的全貌。*朱霞:《云南诺邓井盐生产民俗研究》,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法]蓝克利(Christian Lamouroux)主编:《中国近现代行业文化研究——技艺和专业知识的传承与功能》,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
中国还有农业考古与农具史的学术研究领域,很值得我们关注,它们和民具中的(农业)“生产工具”有相当部分的重合。中国农业考古和农具史的研究,通过把民族志/民俗志的相关资料和古代文献资料(例如,唐陆龟蒙《耒耜经》等)、图像资料(例如,元王祯《农书》中的“农器图谱”、明宋应星《天工开物》的图录、明徐光启《农政全书》的灌溉图谱、历代耕织图、以及近代年画中的“女十忙”和“男十忙”等题材)以及考古发掘资料(例如,墓葬壁画所描绘的农具、各地历代遗址出土的农具实物等)予以相互参照、使之彼此结合的研究方法,产出了很多重要的学术成就,值得民具学家认真参考。但是,民具范畴中涉及“生活用具”“玩具”“祭具”等方面的内容,一般是无法在农业考古和农具史的框架里得到处理的。此外,农业考古和农具史的研究,归根到底是指向于古代,当属于“过去”之学,民具学则基本上应该是“现代”之学,正是那些当下仍在使用或虽然已不再使用、却仍为乡民们不忍抛弃的农具,才是民具学集中要去探讨的。
截至目前,除了考古学,中国物质文化研究的主流其实是已经蔚为大观的传统手工艺研究。传统手工艺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虽然程度不尽相同,其很多门类在现当代的中国社会里依然是生生不息,持续地得到国人的喜爱甚至追捧。对于传统手工艺的研究,大多是聚焦于名匠大师(例如,被认定的国家级或省级传承人)的手艺绝活及其产品,亦即那些被认为具有较高的技术和艺术价值的“工艺品”。这方面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徐艺乙《手工艺的文化与历史》*徐艺乙:《手工艺的文化与历史——与传统手工艺相关的思考与演讲及其他》,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上海文化出版社,2016年。大概就是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成就。但也毋庸讳言,传统的具有较高艺术水准的手工艺品(例如,牙雕、玉雕、景泰蓝、御用瓷器之类),在过往的王朝时代,主要是服务于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巨商富贾以及士大夫阶层的,其工艺绝活也主要是附丽于社会统治者集团才能够存续的。一般而言,它们可以代表中国传统工艺的最高水平,但其所产出的终究不是一般民众日常生活中寻常可见的普通器物。
若进一步追究,固然是不能够将两者截然地割裂开来,但手工艺研究在中国其实是有两个层面,一是上述对那些具有很高的技艺成就、专为上层社会提供服务的高级手工艺及其作品(大都是“国宝”)的研究,二是对那些广泛地见于民间的各种手工业及其产品的研究。*[美]鲁道夫·P·霍梅尔(Hommel,R.P.):《手艺中国:中国手工业调查图录(1921-1930)》,戴吾三等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例如,德国学者艾约博(Jacob Eyferth)对四川省夹江县传统的以毛竹为原料而形成的手工造纸业所进行的系统性研究*[德]艾约博(Jacob Eyferth):《以竹为生: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20世纪社会史》,韩巍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1月。,应该属于后者。于是,和凝聚着精湛技艺的高级工艺品相比较,就又有了“民艺品”这一概念,它主要是指民间工匠的手工制作的工艺品*[日]滨田琢司:《民艺与民俗——作为审美对象的民俗文化》,周星译,周星、王霄冰主编:《现代民俗学的视野与方向》,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68-278页。,或一些从手工业的普通产品中“发现”和挑选出具有美感的那些器物。相对而言,“民艺品”比起那些高级的手工艺品而言,的确是较为接近民俗学的物质文化研究的理念,它从很多普通的器物发现和发掘出“美”来,将它们视为是具有审美价值的,称之为“身边的艺术”。*徐艺乙:《身边的艺术》,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妨将与“民艺品”相关的“民艺学”,视为是“民俗艺术”研究的一部分,所不同的只是“民俗艺术”的范畴,除了那些成“器”之物(“民艺品”)的存在,还包括各种“无形”的艺术形式,例如,民间舞蹈、民间绘画以及刺绣、剪纸、年画等等。在中国,民艺学已有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倾向和趋势,例如,张道一、潘鲁生等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努力要建构的“民艺学”。*张道一:《张道一论民艺》,山东美术出版社,2008年。潘鲁生:《民艺学论纲》,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8年。潘鲁生、唐家路:《民艺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20页。“民艺”这一概念和“民艺学”的思路,其实也部分地来源于日本,和柳宗悦提倡的“民艺运动”的理念及其实践密切相关。简单地说,所谓“民艺”就是“民众的工艺”*[日]柳宗悦:《工艺文化》,徐艺乙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59页。,这意味着民艺学关注那些用具、器物,其视角主要是艺术性的,在承认民艺品之“功能”的基础之上,更加突出其“审美”的价值。*潘鲁生、唐家路:《民艺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21-164页。应该说,“民艺”的概念和“民艺运动”的思路,后来对东亚各国及地区的艺术人类学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陈景扬:《日本的民艺与都市消费:一个人类学艺术研究方法论与案例的考察》,周星主编:《中国艺术人类学基础读本》,学苑出版社,2011年,第311-333页。然而,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除了“民艺品”之外,还有大量被认为够不上“艺术”的器具或实物,因此,“民具”这一概念自然也就有了它自己的空间。正如日本国内的学术界往往是将“民艺”“民俗”和“民具”三者相并列一样,在“民艺学”之外,民具学也成为不可或缺的学术领域。在很多时候,民艺学家和民具学家往往需要面对同样的器具或实物,前者是从艺术家的目光,试图在普通百姓生活中的寻常器物中看到“美”,例如,犁具的造型和曲线之美,又比如扎西·刘通过对马桶的凝视,发现了它的“臭美”等等*扎西·刘:《臭美的马桶》,中国旅游出版社,2005年,第42-43页。;后者则是侧重于关注朴实的民具在生产和生活中被制造、使用、修缮乃至于二次利用和废弃等的过程及状况,重视民具的实际功能以及凝聚其中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智慧。
接下来,似乎还应该提到博物馆学的物质文化研究。博物馆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文化教育设施,致力于物态藏品的搜集、收藏、整理和展示,与此对应的博物馆学的物质文化研究基本上也就是围绕其“藏品”的相关研究。由于文化展示的逻辑,博物馆的藏品搜集难免带有猎奇色彩(殖民主义时代尤其如此)或过于追求独特性和艺术性,故对俗凡常见的民具也缺少兴趣。不仅如此,博物馆对于物品的处理,是要把它们从其原先的文化语境中抽离出来的*[英]迈克尔·罗兰(Michael Rowlands):《历史、物质性与遗产》,汤芸、张原编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第147页。,即便在一些民族学、民俗学或人类学的博物馆里,存在着以“民族志”的观点来搜集和展示某一族群之文化的尝试*王嵩山:《博物馆与文化》,(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5-8页。,其遗产化的趋好仍然经常会使其忽视当下那些俗凡的民具。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中,博物馆民族志通过“物象叙事”*安琪:《博物馆民族志:中国西南地区的物象叙事与族群历史》,民族出版社,2014年。,往往更多地是要展现国家或地区、族群的宏大历史,总是很难顾及社区日常生活中的那些琐碎细物。
通过以上对中国物质文化研究相关各个领域所做的初步扫描和概观,不难发现民具学在中国学术界“缺位”的这一基本事实。笔者对中国物质文化研究领域里各个主要“板块”的上述点评全无贬损之意,而只是为了突出地强调在中国物质文化研究领域中长期以来始终存在的这一巨大的空缺,亦即民具学没有发展起来。由于民具学构成了物质文化研究中最为基层和基础的部分,因此,它的缺位也就使得中国现有的物质文化研究难有更加雄厚的底气。民具学的缺位或它在中国难以发展起来的原因很多,但主要还是因为一些偏见屏蔽了我们的认知。中国被视为是“民具的宝库”*1998年9月,经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文化人类学家横山广子先生推荐,笔者以“中日民具的比较研究——日本民具学理论的应用”为题,申请了住友财团1998年度“亚洲诸国的日本相关研究”资助计划。1999年3月申请获准,当时的立项通知书上附有专家委员会的评论:“中国是民具的宝库。在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进程中,大量民具正在从日常生活中消失,通过此项研究从日本导入民具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非常有意义,也具有紧迫性。”,这是一笔巨量的文化财富,它不仅强力支撑着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其中还蕴藏着普通老百姓无数深邃的知识和智慧。因此,在中国发展民具学将是大有可为的。
二、民具学在中国的导入及成长
民具学是起源于日本的一门学问,以1975年日本民具学会的成立为标志,至今已有40年多年的历史了。当然,民具研究在日本的历史则是要更加悠久一些,大体上可以追溯至1925年涩泽敬三创立“阁楼博物馆”之时。*周星:《日本民具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周星主编:《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上册)》,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76-325页。伴随着改革开放和中日两国学术交流的日益深化,一些留学、访学日本的中国学者很快就注意到,在日本学术界,存在着“民俗学”“民艺学”和“民具学”三足鼎立的格局,通过对介于柳田国男的“民俗学”和柳宗悦的“民艺学”之间,由涩泽敬三、宫本馨太郎、宫本常一等人所提倡的“民具学”的了解,他们深知民具学在中国也将会有巨大的学术空间,于是,基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理念,就出现了把“民具”的概念和“民具学”的理论和方法翻译介绍到中国来的各种努力。*王汝澜:《略谈日本的民具研究》,《中国民间工艺》第6期,1988年;张紫晨主编:《中外民俗学词典》,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93-194页;天野武:《庶民生活的见证——民具》,王汝澜译,王汝澜等编译:《域外民俗学鉴要》,第119-138页,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日]佐野贤治:《地域社会与民俗学——“乡土研究”与综合性学习的接点》,何彬译,《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2期;周星:《日本民具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周星主编:《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上册)》,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76-325页;王建新:《神奈川大学日本常民文化研究所——独树一帜的物质文化研究中心》,周星主编:《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上册)》,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326-338页;周星:《垃圾还是“国宝”?这是一个问题——以日本福岛县只见町的民具保存与活用运动为例》,王文章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田野工作方法》,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第408-436页;孟和套格套:《日本民具学研究概说》,色音主编:《民俗文化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第140-145页。孟和套格套:《民具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内蒙古文物考古》2010年第1期。在这些努力中,也不乏日本学者的支持。*日本学者山口彻曾在与中国学者交流时,用日语发表过介绍民具学的讲演,具体记录参见:山口徹:「日本における民具研究の現状と課題」,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神奈川大学人文学研究所编:《中日文化论丛1993》,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68-82页。与此同时,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中国“以北京、南京等地区为中心”,也形成了在民艺研究的大框架内同时发展当代民具研究的某些动向,“民具研究”的概念开始出现。*许平:《〈中国民具研究〉导论》,《浙江工艺美术》2003年第1期。
对于日本民具学给予较高评价,认为其对中国学术具有建设性的中国学者,不仅有民俗学家,还有一些从事传统手工艺或民艺学研究的学者,以及从事考古学研究的学者。民俗学家柯杨认为,中国民俗学研究由于诸多历史原因,比较侧重于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而对“物化”了的民俗器物的关注和研究,显得比较薄弱和不足,可以说是一种“跛足”的民俗学。为此,他曾撰文指出,应当在参考日本学者的民具“功能分类法”的基础之上,结合中国的实际,制定出中国自己的民具分类体系,为开展民具研究打下坚实基础。*柯杨:《农具:农业民俗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民俗学博客-Folklore Blogs:观复草堂——柯杨的空间,2018年5月12日访问。通过这样的分类,可以使散乱无序、数量众多的民间器物体系化、秩序化、全景化,从而有助于揭示其产生、发展、演变和流传的规律性。在柯杨看来,农具乃是生产民具的一个子系统,可以将它与牧具、渔具、猎具、织具、蚕具以及建筑民具、冶炼民具、酿造民具、烧窑民具等相并列;在农具这一子系统的下面,还可以再细分为平田整地农具、播种农具、田间管理农具、灌溉农具、收割农具、打碾农具、簸扬农具、粮食贮存农具、粮食加工农具等。柯杨建议中国民俗学会农业民俗专业委员会的专家,应该编制出一份“中国传统农具调查研究分类细目”;也建议中国民俗学会组织力量,编制一份“中国传统民具调查研究分类纲目”,以便推动中国有形(物质)民俗文化的田野作业和研究工作的推进。在分类、普查的基础之上,再进一步去开展不同层次、不同专题的学术研究,例如,《中国传统民具大辞典》的编纂;以县为单位,编写和绘制《民具志》和《民具图录》;在广泛搜集传统民具的基础上,建立国家级和地方级的民具博物馆;展开各种专题性的研究(例如,民具的材质与形制演变、民具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汉族民具与各少数民族民具的相互影响、民具作为商品的流通、中国民具与周边各国民具的比较、某种民具的变迁史或传播史、传统民具与生活用品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民具的再生与振兴地方经济、民具博物馆展示的原则与方式、民具与人类智能的关系等)。柯杨指出,从日本民具研究的经验看,要想使中国民具研究跃上一个新台阶,就必须充分利用考古学、文献资料学、科技史、经济史、美术史等相关领域的知识和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的方法,进行多学科相互交叉与渗透式的研究,才有可能取得扎实的进展。
民艺学家许平致力于在“民艺学”中发展出“民具研究”的方向,为此,他曾在南京艺术学院开设过民具调研方面的课程。1997年9月,许平出席在大阪举行的日本道具学会首届年会暨首届理论研究会时,以“中国的‘造物文化’研究”为题发言*许平:《中国的“造物文化”研究——在日本道具学会首届年会暨首届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许平:《造物之门——艺术设计与文化研究文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第138-156页。,向日本同行介绍了张道一教授等人的“造物文化”研究,以及中国民具研究的一些特点:例如,文献资料丰富;民俗学的物质文化研究起步虽早,但遭遇挫折;当代民具研究在民艺学的框架内发展;中国民具研究出现了和现代设计、现代经济建设相结合的新动向等。1998年5月,许平在参加台湾“国立”艺术学院传统艺术研究中心“传统艺术研讨会”时,又以“《中国民具研究》导论”为题做了发言,提出中国的“民具研究”应当在吸收国际同行的研究经验与成果的基础之上,形成中国自己的特色。*许平:《〈中国民具研究〉导论》,《浙江工艺美术》2003年第1期。值得一提的还有,南京艺术学院在设计艺术系设立了“中国民具研究所”,明确地将民具研究作为主要的工作方向。
考古学家熊海堂1985-1992年间曾留学日本,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于1993-1994年在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开设过“民具学”课程,承担过教育部资助的民具学调研课题,并带领学生开展过民具学的调查和研究工作。熊海堂认为,民具学的调查研究成果将成为书写劳动人民创造之历史最为直接的实物证据,它不仅构成文化人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对研究考古学遗物有相当帮助。所以,考古学家应该重视民具学,对现存的传统民具在品种、类型、组合、制作、功用等方面多做科学的调查工作,以便研究人类物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他在“怎样写学年论文”一文中提到,“以民具学调查资料为主,论证某地区民具与自然、民具与文化、民具与传统、民具与技术的关系,在横向比较时可以划分出同类民具的地方特色,为文化区的划定提供有力证据;从纵向比较,可以用民具学调查所获得的知识复原古代同类民具的形态和使用方法,探明某种民具发展的渊源”*贺云翱:《熊海堂先生学术生涯述忆》,中国遗产网,2009年5月15日。。
如上所述,“民具”的概念和民具学逐渐被介绍到中国以后,引起了一部分中国学者的关注。与此同时,也开始有一些青年学者在各地进行了一些民具调查*例如,许平:《惠安女印象——闽东南沿海民具调研散记》,许平:《造物之门——艺术设计与文化研究文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第440-457页。,或从事有关民具的专题性学术研究,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民具学研究成果。*孟凡行:《民具·技艺与生活》,方李莉等著:《陇戛寨人的生活变迁——梭戛生态博物馆研究》,学苑出版社,2010年,第207-334页;王宁宇主编:《关中民间器具与农民生活》,学苑出版社,2010年;孟凡行:《民具的性质与文化结构——以贵州六枝梭戛长角苗民具为个案》,色音主编:《民俗文化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第107-133页;李国江:《传统农具保护中民众参与做法之我见——日本民具保护“只见”方式的启示》,色音主编:《民俗文化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第134-139页;刘昌翠:《侗族社区的民具类型——以贵州省黎平县三龙中寨为例》,色音主编:《民俗文化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第146-183页;吴琼:《生存与理想——鄂伦春族狩猎时代桦树皮民具纹饰分析》,《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当然,在此必须指出的是,在“民具”的概念和民具学的思路进入中国之前,中国的物质民俗研究*可参阅苑利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 物质民俗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民俗文物研究*可参阅宋兆麟、高可、张建新主编:《中国民族民俗文物辞典》,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农具研究、传统手工艺研究等,其实也都分别积累了颇为丰厚的学术成果。虽然如尹绍亭教授等人的云南物质文化研究*尹绍亭:《云南物质文化 农耕卷 上/下》,云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罗钰:《云南物质文化 采集渔猎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唐立:《云南物质文化 生活技术卷》,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罗钰、仲秋:《云南物质文化 纺织卷》,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周星:《物亦载道——简评《〈云南物质文化〉》,《中国图书评论》1999年第4期。,多少可被视为是在日本民具学的影响之下写作较早、相对较为完整的民具志*孟凡行:《器具:技艺与日常生活——贵州六枝梭戛苗族文化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第9页。,但其中还是有很多方面的研究,是在没有或很少受到民具学思路的影响之下完成的。毋庸讳言,“民具”概念和民具学思路的导入,确实是为中国物质文化研究的各相关领域带来了一定的刺激,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笔者也认为,在中国学者的物质文化研究成就和民具学的理念及思路之间,理应能够形成较高水准的学术对话。例如,由民俗学家金煦和民俗画家陆志明合作完成的《吴地农具》一书*金煦、陆志明编著:《吴地农具》,河海大学出版社,1999年。,对苏州蠡墅一带曾经兴盛一时的陆松祥、陆聚兴“椿木作”*旧时苏州一带将生产木制农具的作坊称为“椿木作”,把专卖木制农具的店铺叫做“椿作店”,把制作农具的匠人称作“椿木匠”。制作农具的情形进行了系统的著录和解说,他们对于江南稻作木制农具的详实和形象的记录*金煦、陆志明:《苏州稻作木制农具及俗事考》,《民俗研究》1993年第3期。,就曾引起日本民具学家的高度关注;再比如,中国江南地方有为稻作农具“号字”的风俗,亦即在农具上墨书或张贴涉及族房户主、制作年月日等方面的信息,以及一些吉祥祝语等,这些信息对于民具学家而言,乃是了解民具的历史、称谓以及制作和使用情况的重要线索。*杜晓波:《江南稻作农具的“号字”风俗》,《神州民俗(通俗版)》2012年第6期。这种被地方志(乾隆《吴江县志·卷五·风俗》)描述为“牛耕器具,各有名号”的风俗,其实是可以和日本的“纪年民具”等*周星:《日本民具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周星主编:《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上册)》,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76-325页。做一番比较的,它应该也是今后开展跨国民具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王宁宇主编的《关中民间器具与农民生活》一书*王宁宇主编:《关中民间器具与农民生活》,学苑出版社,2010年。,在中国近年来的物质文化研究成果中显得较为突出。和很多其他地域性的传统器物研究成果大多是“编纂”而成的有所不同,这本书主要是基于田野调查撰写的。作者们对于陕西关中地区十多个县几十个乡镇的上百个村落进行了实地踏勘,深入考察了木匠、铁匠、制秤世家、手工编制、豆腐制作等传统的手工艺行当,不仅对乡村的家常饮食、民居、仓储、老水车、农机具、手工纺织机等予以重视,甚至还对簸箕、笤帚、灯具、饴铬机等一些经常会被忽视的民具也予以专题调查,从而为我们理解当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提供了独特的角度和大量鲜活的第一手资料。由于坚持“忠实记录”的原则,该书除了文字记录,还通过测量、拍照、绘图、制表等多种形式,整理了大量的数据和资料,故具有可靠的学术价值。
如果套用中国民俗学研究中“事象本位”和“地域本位”的说法*周星:《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区域本位”和“事象本位”》,“中国民俗学会成立20周年纪念大会”会议论文,2003年11月。,关于“事象”亦即个别专题的物质文化研究,例如,叶涛的《泰山石敢当》*叶涛:《泰山石敢当》,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山曼等的民间玩具研究*山曼等编著:《山东民间玩具》,济南出版社,2003年。和“民间玩具”概念相近的,又有“乡土玩具”一词,具体可参阅[日]香川雅信:《乡土玩具的视野——爱好者们的“乡土”》,周星译,周星、王霄冰主编:《现代民俗学的视野与方向》,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79-287页。、胡泽学的《中国犁文化》*胡泽学:《中国犁文化》,学苑出版社,2006年。、朱尽晖的《陕西炕头石狮艺术研究》*朱尽晖:《陕西炕头石狮艺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等等;或者关于地域本位的物质文化研究,例如,近几年相继出版的《闽台传统器具》*林慰文:《闽台民间传统器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东阳传统器具》*东阳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东阳传统器具 上下册》,西冷印社,2016年。、《湖湘民间生产生活用具》*陈剑、焦成根:《湖湘民间生产生活用具》,湖南美术出版社,2012年。等等,确实都分别有不少重要的研究成果问世,但是,关于“社区本位”,亦即基层村落的物质文化研究仍然显得非常稀少。文化人类学家杨懋春教授早年曾经意识到农具改进的重要性,故在其大作《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一书中,有过一个简单的农具附录,他同时还注意到村民们通常并不自制工具,而是去集市购买*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张雄、沈炜、秦美珠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5-26、243-249页。;〗青年民俗学家詹娜的《农耕技术民俗的传承与变迁研究》一书*詹娜:《农耕技术民俗的传承与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9月。,也是以社区为背景,部分地经由农具探讨了乡土社会之农耕技术民俗的相关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另一位青年民俗学家蔡磊采用村落民俗志的研究方法,对北京市房山区一个荆条编织品生产的专业村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并由此探讨了乡村手工副业与村落共同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包括村落传统如何规定和制约手工副业的形式和规模,以及这种手工副业如何通过新的联结机制增进了村落的内聚等。*蔡磊:《劳作模式与村落共同体:一个华北荆编专业村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除过这少数几个例外,中国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的社区研究几乎全都不怎么关注民具。不久前,孟凡行的《器具:技艺与日常生活——贵州六枝梭戛苗族文化研究》*孟凡行:《器具:技艺与日常生活——贵州六枝梭戛苗族文化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得以问世,令人耳目一新。作为中国第一部系统地研究一个少数民族基层社区的民具学著作,它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突破,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三、民具的文化遗产化
晚明江南文人文震亨撰写的《长物志》,乃是一部着力于品评鉴赏文人雅士之闲居生活所涉及物品的笔记体著作,它共分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榻、器具、衣饰、舟车、香茗等十二个部类*(明)文震亨著、赵菁编:《长物志:中国古代物质文明史》,金城出版社,2010年。,突出地展现出了明代文人所刻意追求的被认为是清新典雅的生活方式及其审美趣好。从庭院的园囿林池到室内的陈设雅趣,从起居坐卧到焚香品茗,无处不在显示文人雅士通过器物或陈设来建构品位和张扬情调的追求。但这部得到颇高评价、在中国古代造物设计领域具有重要地位的著述却有一个特点,亦即文震亨在赏鉴一切物品尤其是器物时,无处不以标示其“雅”为准则,对于他认为“不雅”之物则极力贬损和摒弃。由于是将“雅”“俗”对举,从而鲜明地表达了尚“雅”卑“俗”的审美理念。英国学者柯律格(Craig Clunas)对文震亨《长物志》做了系统性的研究,并出版了《长物志——早期近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地位》一书,由于作者是出身于博物馆领域的研究者,故对于艺术品较为重视,换言之,他的这部被推崇为在中国物质文化研究领域开风气之作的著作,也是集中对艺术类器物的审美解读,不同的是,他在揭示明朝文人通过对于雅致器物和情调的追求以建构其社会地位这些方面,很是值得称道。*[英]柯律格(Craig Clunas):《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高昕丹、陈恒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正是在文震亨所建立的那个器物审美传统的延长线上,对于雅致器物的研究得以成为中国物质文化研究的主流,这并不令人意外,但令人沮丧的是,普通民众的物质文化生活,他们所使用或珍惜的那些被目为“俗物”的俗凡质朴的无数民具,则不仅被忽视,甚至还被不公正地遭到贬斥。这也许是真正的民具学研究原本就是无法在“民艺研究”和“传统手工艺”研究的框架之内获得实质性进展的缘由。
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的见解是“多数日常用品也应该认为是艺术品”,应该承认“它们的形状都具有艺术价值”*[美]博厄斯:《原始艺术》,金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22页。,但孟凡行在贵州的苗寨所实际观察到的,却主要是人们对民具之功能的重视,以及对于民具的外形及装饰有意无意的忽视,那里的人们对于民具并没有特别的审美要求。的确,民具形状的朴素之美,那些类似木犁的各种曲线,竹编器皿的均衡纹路,以及家具的各种合乎“人体工程学”原理、以便于令主人趁手使用的民具的诸多特点,并非完全没有,但是,对于外部视角的研究者而言,符合或内含所谓“美”的元素的民具,在当地非常稀少,除了因为嗜好,男人们不惜工本,选找曲度优美的“人面竹”制作的烟杆(烟具)之外,苗寨民具几乎都以质朴、实用、粗糙的面目示人。但即便如此,人们对于民具依然有着情感上的不舍,纵使不再使用的民具一般也绝少丢弃。
或许我们可以说,中国传统的物质文化其实也是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大传统”,是典雅、华丽、有品位和为皇室、贵族及文人士大夫们所享用及推崇的雅致器物的传统,另一个则是“小传统”,它是为最广大民众所使用和倚重的民具的传统。民艺学和民艺运动的贡献,在于从俗凡的民具中发现了“美”,或挑选出一些被认为“美”的器具,将其作为艺术品来欣赏,但它对于那些没有被挑选上的“俗物”却并不关心。显然,那些被目为“俗物”的民具,确实是急需民具学方面的学者去重视和研究它们。德国的东方学家、艺术史学家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曾致力于在中国的汉字和印刷活字、青铜器、陶俑、瓷器、丝绸、漆器、建筑、书法、绘画、玺印等众多不同门类的“艺术”当中,发现能够贯穿“万物”的诸如“模件化”之类共通的要素。*[德]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张总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这个学术理路启发我们,如果能够将中国物质文化的上述“大”“小”两个“传统”均同时纳入视野,相信也有可能发现能够贯穿两者的诸如中国式“造物”的那些最为根本的原理或理念。
中国在世纪之交,迈入了全面实现“生活革命”的新时代。城乡生活革命的发展,突出地表现为大面积的物质文化嬗变。一方面,回归传统和追求优雅生活方式的动向,促使中国传统器具尤其是逐渐衰落的古典家具等有了一些新的机遇,但另一方面,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以及全中国朝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迅猛转型,则促使大量的传统农具和俗凡的生活用具日渐被工业产品所取代。都市型生活方式的普及,推动了人们日常使用的生活用具的更新换代,于是,大量的传统民具便被废置甚或抛弃。换言之,在剧烈的社会及文化变迁过程当中,传统民具的去向和命运正日益成为令人担忧的问题。无数普通俗凡的民具不仅是特定时代、特定的地域或社区、特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亦即文化的物证,而且,它们还承载着中国亿万庶民的生活智慧和情感,因此,理所当然地,民具应该就是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民具的散失、废弃或零碎化,自然就会走上成为古董甚或垃圾的命运,但民具如果呈现出组合的形态,或是成为具有明确的社区群景的民具群,那它们就能够成为社区博物馆的收藏和社群历史记忆的载体以及地方文化的物证,也才能够成为毫无疑义的文化遗产。*丁晓蕾、孙建、王思明:《江南稻作农具民俗文化遗产的文化表现及其意义》,《中国农史》2015年第6期。这方面,日本民具学中的“只见模式”,亦即动员社区居民,认真地搜集和整理本社区那些已经不再使用的民具,使之以民具组合和民具群的形态,成为社区有价值的文化遗产,进而再将其登录为日本国家级的有形民俗文化遗产的经验*周星:《垃圾还是“国宝”?这是一个问题——以日本福岛县只见町的民具保存与活用运动为例》,王文章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田野工作方法》,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第408-436页。,很值得中国去借鉴。
眼下在中国社会,出现了若干全新而又醒目的文化现象:例如,像潘家园那样的旧货市场生意非常红火,其中展示的器物鱼龙混杂、真假难辨,但基本上都是在中国传统的古董行业的延长线上得到定位的,虽然其中也有小部分民具能够引起“收藏家”的青睐,但它们大多都是零散的单件,很少有构成完整组合的情形。近些年来,除了作为“收藏指南”而编撰的一些出版物*南文魁:《生活用品(上/下册)》,青海民族出版社,2014年。蓝先琳:《民间器具》,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年。之外,还有一些主要是为了满足读者“怀旧”记忆的出版物*沈玥瑛:《走进记忆——沈玥瑛江南旧时农家器具藏品图集》,古吴轩出版社,2007年。,再就是有一小部分知识分子,特别是具有艺术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前去各地的乡下搜集“老物件”或“民俗用品”*钱民权:《上海乡村民俗用品集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8-59页。,把它们带进城市,或出版画册,或举办博物馆,或用它们来点缀各自的画室或书房。一旦人们将这些器物带离了它们所在的社区,点缀于博物馆或画室、书房、画册、影集等之中,那也就意味着对它们的重置文脉,将它们视为怀旧和寄托乡愁的对象,也就是对这些器物采取了“民俗主义”式应用的姿态,因此,便构成为当代中国“民俗主义”现象的一部分。*周星:《民俗主义在当代中国》,张士闪、李松主编:《中国民俗文化发展报告2015》,第98-136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16年。所有这些努力固然都很值得赞赏,但他们所获得的器物的价值,与其说是学术的,不如说主要是艺术的。例如,有人试图以“复活平民的历史”为指向,采用摄影的理念和技法,使寻常百姓的劳动工具和生活用具之类的“老物件”,能够以“原生态”的形式彰显出来,但这归根到底乃是一种艺术的求索*沈继光、高萍:《老物件》,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1、56-60页。,虽然和国家文物图录不同的是,他们努力去记录平民的器物,但如果透过摄影镜头看到的是乡愁,那就很难说是科学的记录。无论摄影师把民具的纹路、疤痕等细部多么清晰、多么艺术地呈现出来,没有时代背景,缺乏社群出处,就依然不超出“民艺学”的思路。
相对于传统的手工艺研究的理念而言,对于老物件或民俗用品的关注,确实是有一定的进步,但要么是有“把玩”古物旧器的倾向(除了“把玩”,还有人为特意地通过“包浆”作旧而实现古董旧器之“再生产”的途径*赵旭东、孙笑非:《器物之灵:作为文化表达的包浆与意义的再生产》,《民族艺术》2017年第1期。),要么是把民具“艺术品化”,均和本文所追求的记录、分析和理解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有所不同。在现当代的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人民富足,能够消费得起较为昂贵的工艺品的民众日益增加,如此的“工艺品热”,其实也就是诸多艺术品消费热潮的一种,只是其指向的是传统文化,并促成了对于很多传统器物之价值的重新评价,它们被用来点缀人们的生活空间或满足持有者把玩的欲求。然而,那些更为俗凡和朴实无华的民具,却不断地沦为无用之物,或改做他用,或束之高阁,或被焚烧,或被抛弃。*王宇菲:《6架清代水车被村民当废品拆毁木头零件当柴烧》,宁夏新闻网,2013年3月22日。少数“运气”不错、或许可能成为“活化石”的,则有可能被“识货”之人(有时候,可能就是外国人)所收购*孟凡行:《民具·技艺与生活》,方李莉等著:《陇戛寨人的生活变迁——梭戛生态博物馆研究》,学苑出版社,2010年,第207-334页。,抑或孤零零地作为“民俗文物”被纳入某个民俗博物馆的收藏。近年来,“民俗文物”的海外流失亦曾一度成为重要的话题,有论者以为除了现行国家法律法规对于“民俗文物”缺乏明晰和严格的界定之外,国内收藏单位因为没有足够资金去征集和保护它,才使得大量的“民俗文物”不断流失。*柴海亮、刘晓莉、朱峰:《我国民俗文物大量外流令人十分担忧》,《经济参考报》,2006年5月17日。在笔者看来,中国现有的“文化遗产”概念和相关范畴,虽然是把“民俗文物”视为有形的文化遗产,但对一般的民具却并不视之为文化遗产,也因此,人们对于“民俗文物”的理解,或多或少就是把它当作“值钱”的旧货或“宝物”看待的。其实,若想要改变这种现状,也许将比“民俗文物”更为宽泛的“民具”也界定为文化遗产,就将有可能为“民俗文物”的遴选或征集,提供更为丰厚和源源不断的出处。
“民俗文物”和“民具”概念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是从后者挑选出来的,挑选的标准是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而且应该是典型器具,外形完整且有一定的美感。*徐艺乙:《征集民俗文物的几个技术问题》,王文章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田野工作方法》,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第57-75页。当然,有些则应当是能够反映某种特定民俗事象的。通常,它们一经被挑选出来,就不再属于它曾经所属的社群,而是需要肩负或承载起更为广泛的文化遗产的功能。虽然任何民具都是存在于具体的社区和家庭,它的制造者(部分被商业化)、所有者或使用者基本上是明确的,但它们很容易被宽泛化解释,例如,被用来说明人类或中国农业技术史的某个环节,或某省某区某民俗的某种特点等。由于“民俗文物”往往是零散的孤件,即便它被某博物馆收藏,往往也处于边缘性地位,并不是很受重视。正如徐艺乙指出的那样,中国的“民俗文物”研究,其实也因不大受重视而处于“缺失”状态。*徐艺乙:《关于民俗文物》,《民俗研究》2007年第3期。民具虽然相对而言更不被博物馆或很多学者、知识分子所重视,但对于民具学家而言,如果它们不仅具有社群背景,还往往能够以民具组合的面目存在,那么,就可以成为探讨其所在社群民众的生活文化,或探讨其传统农业生计之生产技术体系的珍贵且第一手的资料。2013年10月,第三届中国(山西)特色农产品交易博览会在太原举办,除了现代化的播种机、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土壤翻动机、喷洒机等农机设备之外,还特别设有一个“古旧农耕具”的展厅,展示了曾经被用于称量的斛、斗、合以及灌溉农田用过的水车等已经“退休”多年的农耕具,引起了广大观众的浓厚兴趣*赵静:《200余件古农耕具亮相山西农博会 市民忆苦思甜》,中国新闻网,2013年10月18日。,正是由于它们以组合配套的形式被展示出来,其在农业科技史上的价值就显得特别醒目。
截至20世纪50年代,中国各地基于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关于“经济文化类型”,可参考林耀华、[苏]切博克萨罗夫:《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林耀华:《民族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04-142页。而分别形成了各自独特而又成熟的农具和民具体系(例如,在江南吴地就形成了以“江东犁”和“龙骨车”等为代表的水乡稻作农具体系),它们同时也是不同生计技术和相关乡村生活模式的反映。但是,近代以来中国农业的机械化进程缓慢而持续的发展,促使很多传统农具的形态以及相关的农作业逐渐发生了变化。以江南地区的稻作生产而言,20世纪50年代以前,乡村主要使用传统的农具和以人力、畜力为动力,而60年代以后,传统农具不断改良,部分农具逐渐被农业机械所替代,动力也逐渐地过渡到以电力为主。尤其是灌溉排水作业,电动力极大地减缓了劳作强度;铁制或橡胶管线的广泛应用,甚至改变了田间沟渠的景观。在旧时的稻作农活中,“脱粒”是一件劳苦之事,与此配套的也有一些农具,后来伴随着“脱粒机”的普及,不仅劳动量极大地减轻,相关的传统农具也慢慢退隐。脱粒机在江南农村又叫做“轧稻机”,它曾经从全部木制发展到铁木结合,亦即零部件既有铁制的,也有木制的;作为一种典型的近代化农具,其动力源也从1960年代的人力(脚踏脱粒机)发展到1970代的电动式;随后,又很快地被“收割脱粒机”(康拜因)所取代。在中国,脱粒机的出现、改良和普及,以及它对传统脱粒农具(连枷、禾戽/禾桶等)的取代,它被“收割”和“脱粒”合一的更为现代化的“康拜因”所取代的全过程,可以说就是中国农业机械化进程的一个缩影。类似的情形,还见于现代农机具对耕耘、播种、插秧、收割、搬运以及粮食加工等几乎所有农业生产环节的程度不等但也颇为全面的介入,也因此,其和传统农具之间就形成了此消彼长的关系。
在日本,伴随着传统农具和家具分别被现代化的农业机械和家用电器等所替代,那些被淘汰下来的器物就作为“民具”被对象化和客体化了,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近代化”进程的一部分。1954年日本修订其《文化财保护法》,强化并充实了有关民具等民俗资料的调查、搜集和保护的制度,这个举措其实就是与其都市化、经济增长所伴生的大面积“消失”相关;到1975年日本民具学会的成立,则意味着把传统器物对象化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多积累。其中有关“器物和政治”的研究很值得中国学者借鉴。例如,日本各地农村曾经很具有地方性的犁,被大正时期(1912-1926)普及的“改良犁”所取代,这其实是和政府提高稻作产量的政策构想有密切的关系;但在一些山区,由于部分小农执著于旱田作业,他们也就继续使用传统的犁。*牛島史彦:「モノの近代-民具研究の現代性-」、『日本民俗学』第216号、1998年。类似的情形也见于中国,政府基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逻辑不断推进农业技术革新和农业机械化政策,持续地导致乡土社会里传统知识和传统农耕技术体系发生变迁,虽然在山地等机械化生产设备较难展开的地方,传统的农耕用具、耕种方式乃至于观念等仍多少得以保留,但机械化促使传统知识体系的衰落亦是不争的事实。詹娜在辽东沙河沟村的研究发现,以前农家最为繁忙和重要的春种、夏锄、造粪和秋收等几件大事,虽然重要性依旧,可它们已经不再是每个男性农民所必不可缺的技能了。市场经济原理深入乡村,很多“大事”往往可以通过雇佣方式解决,由于被雇者会带来专业装备并亲自操作,于是,旧时有关“扶犁”“招犁”等传统乡土社会评价男子劳动力的普遍性技术,就逐渐地被少数人士掌握的专业性技术所替代,当然,传统农具及其使用的方法和技术,也就不是这一代农村的年轻人所必须学习和掌握的了。*詹娜:《断裂与延续:现代化背景下的地方性知识——以辽东沙河沟农耕生产技术变迁为个案》,《文化遗产》2008年第2期。
1994年9月,中国民俗学会民俗博物馆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民俗博物馆事业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近些年来,遍布中国城乡各地的民俗博物馆在保护民俗文化遗产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通过“民俗文物”的遗产化,地域性的民俗文化也逐渐被视为重要的资源,它们不仅是各地独特的历史传统和民众生活文化的物证,往往也成为地方的“名片”和旅游观光产业的文化资本。确实是有一些民俗博物馆获得了成功,例如,河南省滑县民俗博物院,经过广泛搜集和认真筛选,它收藏了滑县及周边市、县的民俗物品1000余件(套),这些在当地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展品,大都是现已退出人们日常生活的传统器物,仅有小部分在当今中原地区的农村仍依稀可见。*汪俊枝:《民俗文物透视豫北地区农村生活的历史变迁》,安阳新闻网,2010年8月4日。该博物院分别设计了婚俗厅、纺织厅、生活厅和生产厅等,浓缩反映了截至20世纪80-90年代中原地区农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纺织厅展示了轧花、弹花、纺花、打线、浆线、络线、经线、灌杼、刷线、织布等从棉花到布匹的全过程;生活厅反映了居家过日子的习俗,例如,煤油灯、马灯等物品,很多都是老百姓曾经用过的,反映了不久前农村百姓的生活场景。但实际上,更多的民俗博物馆,则经常因为藏品的短缺而发愁*郭子升:《中国的民俗博物馆》,中国民俗学会编:《中国民俗学年刊(2000-2001和年合刊)》,学苑出版社,2002年。,这主要就是由于缺乏民具作为文化遗产的意识,导致征集和收藏工作的视野比较狭隘,没有将民俗文化的概念扩大解释到民具的层面,故其藏品就显得单薄,以至于很多民俗博物馆结果都成了“婚俗”博物馆。但其实,伴随着民俗博物馆的需求增加,就连农具或民俗器具的模型制作都可以吸引很多看客。*高道飞、彭宇:《74岁老汉“复原”500件古代农器具形态逼真》,《武汉晚报》2013年9月6日。民俗博物馆如将民俗文物的概念扩大解释到民具,就有可能极大地拓展自己的馆藏资源。这方面的创意很多,既有依托乡村旅游或农业旅游而创办博物馆的,例如,南京市雨花台区江心洲街道农民鲁维胜创办的“农趣馆”,陈列600多件既可参观、又可参与操作的旧时农具,该馆自2000年5月开馆以来,每年要接待数十万人次的游客;也有依托地方产业而发展出来的专题博物馆,例如,在“鞋都”温州的“中国鞋文化博物馆”等,中国各地依托民具和民俗文物,发展博物馆事业的前景,可以说是非常广阔的。
二十多年前,笔者在浙江省兰溪市的姚村进行民俗调查时,曾经提出过把即将或已经流失的民俗文物和民具,就地保存在村落社区的祠堂或文化中心,建立社区博物馆的构想。*周星:《姚村:物态象征的民俗世界》,《亚细亚民俗研究》(第五辑),学苑出版社,2005年。2016年4月,笔者时隔二十多年重返姚村,看到了在姚村新建的总祠堂里,确实摆放着一些不再使用的传统农具(木犁、风车)之类,但也是任其风化的状态。由此可知,乡村基层社区往往是确实存在类似的需求,至于它能否真的实现,除了意识观念的变革之外,主要还是在于人,亦即当地社区居民的具体实践。陕西省户县甘亭镇西坡村的农民刘养利,利用自己的农家院,于2005年办起了“泥腿子艺术馆”,其中特意设置了一个民俗馆。他跑村串户,收集了一批过去曾经使用过的老式农器和工具进行展示。这个民俗馆开办以来,参观者已有好几千人次*黄亚平、黄智卓:《村民办艺术馆展览老农具 望“留住农耕文化烙印”》,《西安晚报》2012年2月20日。,乡亲们看了都说感到亲切,这些老式农器和工具唤起了人们对于过往时代农耕生活的鲜活记忆。可以说,这就是将民具之类的文化遗产保存在基层社区,并为社区居民所珍视的范例,其价值在于它提示了本地人(在地)的视角,所以,有助于摆脱传统博物馆式的分类展示法,能够将物件置于当地的文化和情景之中予以展示。*[英]贝拉·迪克斯(Bella Dicks):《被展示的文化:当代“可参观性”的生产》,冯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56页。2016年9月,内蒙古师范大学设立在呼和浩特和林格尔县南山文化产业园的“来喜民具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免费开放,据说这是国内首家以“民具”命名的博物馆,它有两个展厅、18个展区、2000余件展品,基本包括了传统农具、民国器具、文革藏品、办公用品、教学用具、家用电器等在内的各种实用器具,集中反映了内蒙古地区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城市时代多种生活方式的历史。王来喜教授历经20余年,不辞辛劳地从内蒙古中、东、西部102个旗县(市、区)搜集了大量的物件*霍晓庆:《来喜民具博物馆唤起乡愁记忆》,内蒙古新闻网,2016年9月10日。,或许正是由于采用了“民具”的概念,其收藏品的范围确实是有较大的拓展。眼下,该馆已经被确定为内蒙古师范大学本科生、研究生的教学实践基地,“蒙古族文化保护发展研究会民具研究专业委员会”也设在这里。笔者相信,类似的民具博物馆的实践,今后在中国肯定也是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的“在地”民俗学家田传江,不仅撰写了《红山峪村民俗志》*田传江:《红山峪村民俗志》,辽宁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1999年。,还搜集和整理了250多件红山峪村以农具为主的“民俗器物”。2002年6月16-23日,枣庄市博物馆举办了“红山峪村民俗器物展”*鲁讯:《“红山峪村民俗器物展”在枣庄举办》,《民俗研究》2002年第4期。,由于这些器物不仅具有明确的村落社区背景,还有翔实可靠的《红山峪村民俗志》作为背景文脉的解说,因此,其学术价值应该是更为靠谱的。至于那些和农具有关的民俗,包括故事、情感和人情世故等,都会成为民具研究的珍贵资料,例如,乡亲们“夸农具”“借农具”“骂农具”“吆喝农具”*田传江:《锄——红山峪村农具民俗之一》,《民俗研究》2001年第4期。等行为,如果没有社区的背景知识,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它。王新艳对山东省的民间盛器——“箢”所做的研究,除了揭示这种普通民具的种类及其在乡民日常生活的各种场景被频繁使用的情形之外,还特意提到了“送箢子”“借箢子”“挎大箢子”等民俗事象。*王新艶:「山東省の盛り容器としての『箢』(ユウン)と民俗生活」、『民具マンスリー』第46巻第11号、2014年。旧时在华北农村,乡民之间彼此合用农具或频繁地借贷农具(“合具”“搭伙具”)*张思:《近代华北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农耕结合习惯的历史人类学考察》,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71-74、81-83页。,曾经形成了颇为严密的乡土社会规则。江南地区的农民在过年时,总是要在农具上“贴红”,有的人家在祭祖时往往也要摆上农具或用于制作农具的工具等(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日本的“道具供养”民俗*周菲菲:「『道具供養』についての宗教民俗学的考察」、『比較民俗研究』第32号、2018年。);在不少地方,女儿出嫁时,是要把一些农具和家具列为陪嫁品,甚至办喜事时就把“犁铧”之类的农具或马桶之类的民具摆在新房里。显然,如何理解这些涉及农具和民具的民俗事象,应该也是中国民俗学的课题。
四、物质文明的更新换代与物质文化研究的大视野
当代中国城乡的生活革命,导致普通民众的“衣食住用行”均发生了极大变化。*周星:《中国人的生活革命》,《社会科学报》,总第1557期第6版,2017年5月11日。塑料制品、不锈钢制品、电视、沙发、摩托车等等,都先后进入了山村边寨,它们引起的发展和变革远不止是传统民具的衰落,更是民众物质生活的升级换代。中国民众所能够享有的物质文明,在近数十年间是如此迅猛地得以提升,其速度和规模可谓前所未有。在全国各大、中、小城市,人们对于旧家具、老物件的淘汰颇为彻底。如果我们不把民具局限于乡村的生活用具和传统农具等,那么,城市里的民具流失更是令人触目惊心。无数乡民进城、无数市民乔迁新居,他们的家具器用总是追求焕然一新(犹如20世纪80-90年代,现代风格的大小立柜迅速地取代了传统的箱柜家具组合一样),故除了极少数看起来“值点钱”或有点艺术性的进入了旧货古董市场之外,绝大多数均被扫地出门、沦为了垃圾。慢慢地,旧物件损坏之后已不再需要修理,所以,修钢笔的、修手表的、弹棉花的和补锅的匠人们,也就从当今的社会中逐渐地销声匿迹了。*蒋蓝(文)、顾斯嘉(图):《正在消失的职业》,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年。伴随着消费主义的兴起,1990年代以降的“一次性消费”打破了长期以来民众“惜物”的价值观,这固然促使物质文明快速发展,却也导致一次性筷子、纸杯和塑料袋等垃圾的成倍增长。*鲁稚(文)、陈强(图):《正在消失的物品》,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年,第24页。
由于民具实在是过于俗凡,人们对于它的留恋远远达不到要去惋惜或珍藏的程度。诸如,自来水系统确立之前的水缸、水桶、水瓢;已经被铝蒸笼替代的竹蒸笼;城乡居民做饭和取暖时用过的风箱、火盆和火钳;爱美人士的假衣领和用来去除虱子、头皮屑的篦子;被电熨斗取代的火熨斗;被一次性纸巾取代的手绢;因电灯的普及而不再使用的油灯、马灯、手电筒;被计算器或手机替代的算盘;被电子游戏取代的陀螺、铁环、滑轮车、万花筒和跳皮筋;被室内卫生间取代的马桶、痰盂;被洗衣机取代的搓衣板;被“席梦思”替代的木板床及传统棕垫;被小推车取代的摇篮、站桶和母亲背孩子的竹背椅等等。*鲁稚(文)、陈强(图):《正在消失的物品》,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年。除了一些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器物用品,像油印机、红宝书、军挎包、石膏像、收音机等等之外,还有铝饭盒、回力鞋、油纸伞、蚊帐、暖壶、热水瓶、鸡毛掸、缝纫机等,不知何时就悄然退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只有当更为宽泛的民具概念的意义被更多的人们体味到,这些曾经的俗凡之物的价值,这些能够反映民众生活史细节的器物,才有可能被重新认识。有些看起来很不起眼,甚至人们有意无意地忽视和选择遗忘它们,但其在过往生活中的意义却非常重要,可以成为时代变迁和生活革命的指标性物件。例如,在1990年代前后纸尿布、纸尿裤和卫生纸传入之前,中国广大城乡曾经广泛使用过“尿布”和“月经带”(卫生巾),现如今,卫生纸已经取代了旧式的卫生巾,纸尿布也正在向乡下迅速普及,纸尿裤还越来越多地用于照护自理能力衰退的老年人。不言而喻,正是这些新的物质文明的产品,极大提升了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乃至于个人卫生的水准。
如果扩大视野,我们不难发现,当代中国物质文明的更新换代,其实是处于更为广阔的推动人类物质文明大规模和大面积提升的全球化物流事业的延长线上的,某种意义上,中国物质文明的更新换代既是它的一部分,当然也是中国人民孜孜以求、追求美好生活之持续不断努力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既有对中国古代传统器物的继承、创新和扬弃,更有对海外器物的接纳、利用和改造。19世纪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伴随而来的就有各种西洋器物,这其中既有日常用品,诸如肥皂(洋碱)、火柴(洋火)之类,也有各种近距离(马车、人力车、自行车之类)和远距离(摩托、汽船、汽车、火车、飞机之类)的交通工具,还有通讯设备(诸如电报、电话之类)、文化娱乐(照相机*葛涛、石冬旭:《具像的历史:照相与清末民初上海社会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魔术、电影之类)以及缝纫机*袁蓉:《缝纫机与近代上海社会变迁(1858-1949)》,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兵器、电器(电灯、电梯之类)等等。*隋元芬:《西洋器物传入中国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王敏:《近代洋货进口与中国社会变迁》,文化发展出版社,2016年。苏生文、赵爽:《西风东渐:衣食住行的近代变迁》,中华书局,2010年。这些西洋的“奇器淫巧”曾经令国人眩目,给当时的民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时间,人们趋之若鹜。*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第39-5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大批“日用洋货”长驱直入,从东南沿海各地,不断且迅速地向内地扩散。荷兰学者冯客(Frank Dikötter)曾经对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这一百多年间,中国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物质景观所发生的各方面变化进行过研究,他认为,所有这些变化早已经和全球化的进程发生了十分密切的关联。长期以来,“舶来品”成为中国各界精英人士展现其现代化价值观和自身社会地位的标志;同时,无数“日用洋货”也逐渐进入到寻常百姓的家庭。*孔祥宇:《“西化”影响下的北京家庭物质生活变迁(1912-1937)》,《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第1期。和对于西方某些价值观的拒斥形成鲜明对照的,便是对西方器用几乎是没有多少犹豫的接纳。工薪阶层的普通民众热衷于追求所有看起来更为现代化、更为摩登洋气、更为便利和具有更好品质的器用物品,巨大的需求甚至催生了大批生产廉价低端仿制品的企业,当然也有各种各样的模仿和再创造。此类“物质现代性”在民众的家庭日常生活中出现并不断地积累,从而日甚一日地改变了当代中国的物质文明,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出现了大量积蓄“生活‘非’必需品”*鏡味治也:「生活〈不〉必需品の効用」、『民博通信』第154号、第16-17頁、2016年。,亦即通过占有更多财物来彰显富足的情形。在冯客看来,这是一个“主动性借用、创造性拼装和适应性仿效”的过程。*潘玮琳:《海外中国研究的物质文化转向》,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编:《世界中国学理论前沿》,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第56-70页。显然,在对中国传统民具的体系予以总结的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近代以来中国民众的物质文化生活确实是深受海外“洋货”的渗透和影响。关于“西物东渐”所带来的社会变化,有学者曾以收音机为例,进行过专题研究*姜红:《西物东渐与近代中国的巨变——收音机在上海(1923-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其实,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沙发”之西物东渐,再从东南沿海的大中都市逐渐地朝向内地县城一级城镇的扩散,再到“沙发”和电视机在山村乡民家庭内部的配套,则是又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
在把民具研究的视野从乡村扩展到城市,把当代中国民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和更大范围及规模的全球化物流联系起来予以思考的同时,具体、实证的类似“考现学”那样的物质文化研究就显得尤其重要。“考现学”(modernology)这一概念,是由日本学者今和次郎于1927年提示的,和“考古学”相对应,它主要是指对于现代都市社会的风俗、世态和各种现象进行绵密的野外调查、记录和分析的学问。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社会进入剧烈变迁的时代,日本民众传统的生活结构也开始发生巨变,于是,就出现了对世态变迁予以调查和记录的动向。1930年,今和次郎和吉田谦吉合作出版了《考现学》一书*今和次郎、吉田謙吉:『モデルノロヂオ 考現学』、春陽堂、1930年。,引起了很大反响。今和次郎通过对传统民居和民具进行详尽的实测,非常细致地观察现代社会的风俗,诸如服装、饰品、室内家具器物的配置等变化,不仅留下很多珍贵的记录,同时也开发出风俗世态研究的一种全新的方法,亦即在既定的场所和时间带(例如,定期在东京银座的街头,实地观察行人的发型、服饰,并进行必要的统计等),组织对特定现象的系统性观察与调查,进而分析相关风俗世态的流变。采用这种方法,可以对社会生活所有领域的变迁均进行如实记录和研究,它因此也被认为是和日本民族学的原点相互可以通融的。*久保正敏:「考現学と民博」、『月刊 みんぱく』(特集 今和次郎の考現学とその遺伝子たち)、2012年4月号。1960年代以后,高速经济增长和工业化使得日本人传统的生活结构趋于彻底解体,于是,只是观察和琢磨现代生活变迁的“考现学”似乎也落伍了,随后就又发展出旨在帮助民众设计和选择生活方式的“生活学”。无论民具学,还是考现学,乃至于“生活学”,它们都是具体、实证的研究,其价值在于能够记录和揭示那些往往被宏大叙事性研究所遮蔽或湮没的历史与生活的细节。就此而论,不久前在日本和韩国文化人类学及民俗学领域得到实施的“生活资财生态学”研究,例如,“2002首尔生活样式”项目(亦即对某市民家庭的全部生活资财予以全数调查和彻底分析)的方法等*周星:《追问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东亚民俗学者的新探索》,周星、王霄冰主编:《现代民俗学的视野与方向》,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999-10138页。,也是很值得推荐给中国学术界的。近些年来,中国新兴的中产阶层的物质消费模式,亦即注重品位的物质欲望*朱迪:《品位与物质欲望:当代中产阶层的消费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及其对全社会的示范和引导作用,应该也是中国物质文化研究的新课题。徐赣丽将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纳入都市民俗学的研究领域*徐赣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都市民俗学新课题》,《民俗研究》2017年第4期。,认为现存的手工艺已经不再具备它曾经有过的那些传统的功能,眼下主要是面向城市里新的中产阶级而进行生产,它们只有提升技艺水准,增加产品的文化附加值,才可赢得城市文化精英们的青睐,进而作为收藏品或高档装饰品而重新获得全新的机遇。*徐赣丽:《手工技艺的生产性保护:回归生活还是走向艺术》,《民族艺术》2017年第3期。
中国当前正处于“生活革命”的进程之中,民众生活的变迁及物质文明发展的无数细节需要有翔实和准确的记录,也需要有基于翔实记录而展开的物质文化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日本民具学和考现学的思路、理念和方法都是具有参鉴价值的。当然,民具学或考现学并不是唯一有效的路径,事实上,中国物质文化研究的不少领域所取得的成绩及其特点,往往也是能够和民具学或考现学形成对话、交流,从而相得益彰的。例如,对于从汉字形义对器物文化的标记及命名相关问题的研究*朱英贵:《汉字形义与器物文化》,人民出版社,2009年。,对于中国古代农器记录之观念传统的研究*王琴:《显与隐:中国农事器物记录观念论》,《民俗研究》2015年第5期。,当然,还有中国农具的很多研究*金煦、陈志明:《苏州稻作木制农具及俗事考》,《民俗研究》1999年第3期。詹娜:《农具:肢体功能的延伸与象征意义的衍化——以辽东沙河沟人的农具制作与使用为例》,《民俗研究》2006年第3期。詹娜:《农耕技术民俗的传承与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都是完全可以充满自信地和日本的民具研究形成学术对话;至于对相同或类似民具进行中日比较研究,也无疑是有很多潜在的可能性。中国学者对于传统器物的分类,主要就是将其分为民间生产用具和民间生活用具,其下再有诸多小目,例如,《东阳传统器具》一书的上册为生活用具,分为坐置、寝卧、盛储、饮食、灯饰、文娱、防保等7类;下册为生产用具,分为农耕、渔猎、饲养、加工、腌酿、编造、泥作、木作、五金、贸易等10类,大体上也还是可以涵盖日本民具学所涉猎的范围。不仅如此,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往往还独辟蹊径,对物质文化的研究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例如,张柠对乡土器物所承载之乡土价值的研究,就非常富有想象力。*张柠:《土地的黄昏:中国乡村经验的微观权力分析》,东方出版社,2005年。他是把“乡土器物”视为理解乡村秩序和乡村生活的基本路径,以此为前提,深入讨论了器物对于人的支撑和限制,指出人和器物关系的变化亦即乡土价值的变化。张柠的研究事实上提示了从器物研究去接近行为、结构和社会文化逻辑的路径。通过“物”及其周边事象深入研究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变迁或文化结构,乃是当代物质文化研究的范式之一,但若要这样的研究获得可靠的成果,则有必要借鉴“新史学派”的研究方法,亦即着力考察普罗大众包括衣食住用行等在内的日常生活,经由那些似乎是微不足道的琐碎器具或物品,把它们视为重要的“文本”资料或基本素材。
中国民具研究的重要特点之一,还在于有相当一批研究往往是从设计学的角度出发,分析和研究各个地方和各个民族的传统民具,通过在田野现场的观察和实测,掌握构成传统民具之生产工具和生活器具的基本形态,并依据现代设计学的原理,分别从形制、功能、结构、材料、工艺、装饰等多方面,对传统民具的设计特征进行归纳,进而探讨影响其设计的各种因素,揭示传统民具所内含的“造物”理念和民众智慧。*张亚池:《皖南民俗家具研究》,北京林业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梁盛平:《赣南客家传统民具设计研究》,南京艺术学院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行焱:《陕西关中民俗家具研究文化》,北京林业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巩聪:《自然、人文环境视野下藏族民具设计研究》,江南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张重:《山西民间家具的研究》,北京林业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陶琨:《藏东南传统民具设计研究》,江南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巩淼淼、陈黎:《江南传统桶型木器的造型和工艺》,《设计艺术》2002年第2期。沈法、张福昌:《民问竹器物的形式特征及本原思想研究》,《竹子研究汇刊》2005年第4期。从设计学的角度探讨民具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设计之“原道”本在于日用*李立新:《日用作为设计的“原道”——兼论“小道致远论”》,《2016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长沙理工大学,2016年,第457-460页。,将日用之物的设计求诸于传统民具,堪称是一条正本清源的路径。这一路径将古拙鲜活的民具视为当今各类产品设计的基础或源头,由于传统民具被认为是蕴含着生活之美(包括造物之美和物用之美)的设计,因此,它能够为机器时代冰冷的高科技用品带来些许暖意。在这个思路的延长线上,很自然地就会探讨到传统民具对于现代工业设计所可能具有的借鉴性意义。*董洁晶、武瑞之、汪成哲、李梦:《论传统民具对现代工业设计的启示》,《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显然,对于这方面的中国民具研究应该认真地予以总结,而不应妄自菲薄。
总之,针对中国这个“民具的宝库”,民具学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中国尚有无数类似的村落社区蕴藏着巨量的民具,有待民具学家去发现、发掘和研究。不仅如此,全国各地民间还有无数的集贸市场,其中也有为数众多的农具交易活动,有的甚至还发展成为专门的农器市场。例如,苏州过去有“轧神仙”“游石湖”等许多民俗庙会,庙会的会期往往同时也是买卖农具较为集中的时期;每逢此时,制作农具的“椿木作坊”沿着蠡墅河滩搭满作业场,前来购买农具和农船的船只络绎不绝,甚至挤满了河道。*金煦、陆志明:《苏州稻作木制农具及俗事考》,《民俗研究》1993年第3期。福建省武夷山市(原崇安县)在每年农历的二月初六,有所谓“柴头会”,届时,全市各乡镇的民众汇集城中,进行耕牛、苗木、农具、竹木制品等各种农副产品的民间贸易集会。这天,除了本市基层乡村的民众会来赶会之外,邻近县市如邵武、建阳、浦城以及江西省的铅山、上饶、广丰等地,也有很多民众前来参加交易。*龚少峰:《武夷山市“柴头会”研究发轫》,福建省民俗学会1991年学术研讨会论文。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的灌阳县,有一个“二月八”农具文化节,一年一度每逢农历二月初八,灌阳及周边县市,甚至湖南江永、道县等地的数万名民众,就会聚集在灌阳县城,出售或购买各种农具、果苗及种子。*赵琳露、杨陈:《民间能人广西灌阳农具节上亮绝活 桂湘两地万人赶集》,中国新闻网,2013年3月19日。虽说是“农具节”,其实除了琳琅满目的农具,还有大量的竹木制品和各种家具器物,届时这些民具会把一条街挤得水泄不通。这些大都是在春耕农忙季节到来之前,集中进行农具和各种农副产品交易的好例。在农具节上,不仅民间手工艺人相互交流献艺,很多乡民前来参加,近些年还有不少城里人也来“淘宝”,他们对于箩筐、犁、蓑衣、撮箕等自制农具也充满兴趣,有的还把做工考究的农具作为手工艺品买回家去。再比如,云南保山市隆阳区河图镇大官庙村,也有一年一度举办的“哀牢犁耙会”,它也是一个依托庙会发展起来的农具交易市场。早先的“哀牢犁耙会”是民间自发的,现在逐渐发展到由政府参与筹办,所以,赶会的人数可达数万人。“哀牢犁耙会”的会期为正月十四、十五两天,届时四邻八乡甚至外县市的数万人聚集在大官庙下从事交易,很多前来赶会的农民将自制农具拿到这里出售,或以物易物,换取自己中意的农具。*廖珮帆:《犁的制作工艺与民俗》,北师大民俗学微信公众号【物质民俗|民具】,2016年5月1日。交易的器物大都是一些传统的生产工具,诸如犁耙、扁担、绳索、竹帽、蓑衣、镰刀、锄头、粪箕、筛子、簸箕、篮子、扫把等,既有木器,也有竹器和铁器等。
上述例子表明,虽然从全国范围看,物质文明的提升将导致传统民具日趋衰微,但到具体的社区和地域去做实地观察,则不难发现传统民具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笔者认为,这些也都应该成为中国民具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五、结 语
近些年在中国兴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极大地推动了国家的文化建设事业,纠正了过往只重视“文物”的较为狭窄的文化遗产观。但也无可讳言,有些媒体人士和少部分学者过于强调文化遗产的“非物质”属性,不仅把文化的“有形”和“无形”加以割裂,甚至还对“非物质”的表述产生了误解、误读,似乎只有“非物质”,才是真文化。其实这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原本只是作为国家文化遗产行政的“工作概念”做出了过度阐释,并且将其本质化了。这种理解当然既不利于中国物质文化研究的健康发展,也会妨碍对于文化的全面性认知。*参阅彭兆荣:《物·非物·物非·格物——作为文化遗产的物质研究》,《文化遗产》2013年第2期。实际上,文化既有物质的层面、物化的形态或载体,也有非物质的内涵和意义,而它们原本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也因此,各地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经常就是离不开采取物化的形态,例如,采取博物馆展示的方式,就必须依托各种包括传统民具在内的征集物;与此同时,对于传统的生产工具、生活器具的研究,当然也不会只停留在其物化的形态或材料、造型的层面,而是需要揭示它所承载的技艺、身体感觉乃至于情感。*梁景之、李利:《西藏跨越式发展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传统生产工具为中心》,《西藏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换言之,民具研究的本义原本就应该包括深入地探讨民具的物质性和非物质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包括民具与环境的关系、民具所体现的民众生活智慧、民具所承载的族群历史和身体技艺等等。*蒋萍:《过山瑶的民具——以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三江乡石口瑶寨为例》,中国民俗学会2011年年会论文。
目前国家大力推动的“新型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正在实质性地促进着城乡居民日常生活在物质层面的进一步变革,因此,传统民具之日益趋于衰微乃至于进一步流失的可能性也就不容忽视。所以,加紧民具的调查与研究,其实也就是对于文化遗产的抢救性作业。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反倒也有可能为民具研究和传统民具的保护带来新的机遇。因为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之“新”,就在于要“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于是,乡愁情感所得以寄托和依存的老房子、老物件、传统民具等,就都会成为“宝贝”,更加受到青睐。在笔者看来,只有把无数的传统民具,尽可能多地保存在基层的村落社区或地域社会之中,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或慰籍最大多数城乡居民的乡愁情感。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各个地方凡是有条件的村落或村镇社区,如果都能够对传统民具进行必要的“在地保护”,就将可以为当地居民提供乡愁可以依凭的实物根据,也可以为子孙后代保存最大宗的文化遗产,从而为社区的文化传承作出贡献。中国各地大量涌现的民俗博物馆,如果能够树立起超越“民俗文物”和“传统手工艺”之类的理念,真正对俗凡却又传统的民具也予以重视,则其可能收藏和展示的物质文化和乡土生活的幅度和深度,都将会更上一个台阶。显而易见,把传统的民具中那些具有艺术感的器物带离它们所属的社群或地域社会,将其在完全不同的其他文脉下用来点缀的民俗主义实践,虽然也有文化创意之类的意义,但相比起来,把它们保存在基层的社区博物馆或陈列室里,成为社区居民生活历史的见证,则要更加适得其所。
伴随着中国民众所享有的物质文明的全面提升,物质文化研究的界域当然不能为民具的概念和民具学的思路所局限。例如,当物质文化研究面对现代社会之家用电器已然普及的现状时,研究者也必须与时俱进,予以正面回应。汪民安基于个人生活中的使用经验,认真地思考被家用电器所形塑的家庭空间,他对于人与家用电器的关系的分析,以及对于家用电器之文化功能的追问,进而对于机器为人带来的解放、对人的控制和促使社会分层等多方面的探讨*汪民安:《论家用电器》,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笔者认为,其实都是有可能与来自民具研究的结论形成呼应和对话的。更进一步,还有手机导致的社会变迁,不只是信息的便捷化,更有促成社会的“个人化”。*藤本憲一:「ケータイ文化人類学の可能性」、『月刊 みんぱく(特集 ケータイ)』2006年第7号。费中正:《手机与西江苗民的生活:城乡转型发展中的文化传承》,人民出版社,2016年。周星:《信息机器(手机)与“贴身”的生活革命》,『日常と文化』第3号、第115-132頁、日常と文化研究会、2017年。那么,人拥有一件民具和拥有一部手机,究竟会有哪些不同呢?虽然民具学通常是把民具在与现代工业产品进行了区隔之后予以定义的,笔者依然相信,民具学不应该在现代社会止步不前,我们经由民具研究所获知的那些关于“人”与“物”之关系的智慧,多少还是能够且应该被延伸至对于人与手机之类关系的阐释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