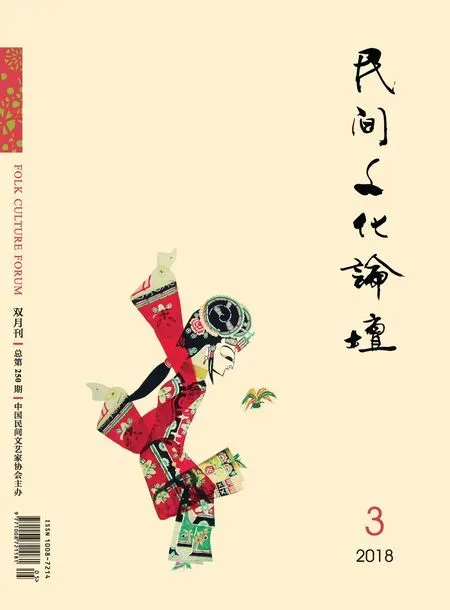民俗研究的历史:我们为什么需要它?
[美 ].丹 ·本 - 阿默思(Dan.Ben-Amos) 著 贾琛 译
借用威廉·詹姆斯( William James)的话说,一个新理论有三个发展阶段:首先,它被攻击为是荒谬无理的;然后,它获得认可,但被认为是显而易见、无足轻重的;最后,它被视为确乎重要的,但根本毫无新意。①我的引述不足以表现原文的智慧。最后这句话,原文是这样写的:“最终,它被认为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反对者们也宣称他们自己发现了这个理论。”William James, Pragmatism: A New Name for Some Old Ways of Thinking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07), p. 198.接下来,无论是反对者还是支持者都将其视为思想史不可或缺的部分,并孜孜不倦地追溯其学术渊源与哲学谱系。近来,学者对民俗研究史高涨的热情表明,民俗学至此已经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②参见Richard M. Dorson, The British Folklorists: A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Dag Stromback, ed., Leading Folklorists of the North: Biographical Studies (Oslo: Universitetsfolaget,1971). 另外《民俗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Volkskunde 65: 1 (1969)]致力于刊发与欧洲及美国的民俗学学术史相关的文章。更可说明学界对民俗研究史具有浓厚兴趣的是已完成或正在写作的针对这一话题的论文数量。最近发表的有:Richard A. Reuss, "American Folklore and Left-Wing Politics 1927-57"(Indiana University, 1971); Francis Anthony de Caro, "Folklore as an 'Historical Science': The Anglo-American View Point" (Indiana University, 1972); and Harry A. Senn, "Folklore Scholarship in Fra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2).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卡罗尔·亨德森和琳达·莫莉都参与了这组文章,她们关注加拿大民俗研究史,弗朗西丝·钱尔德的传记也关注了这方面。另外,苏珊·德怀尔·希克正在写作美国民俗学研究中的人类学派相关文章。印第安纳大学中,威廉姆·麦克尼尔也正在研究美国民俗学的历史,1888—1907。即使其他学者不这么做,至少民俗学专业的学生会宣称自己学科的知识与学术传统来标明它的科学性,证明其在学术研究中的地位。
但是,除了满足这一需求(它是学术需求,但心理需求同样重要),问题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为什么我们需要民俗研究的历史?”为什么我们要再次展露曾经的争辩、已被遗忘的失败,以及希望遗忘的错误,将它们再次公诸于众?尤其是当前民俗研究的任务愈加繁重,难道我们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承担它吗?
毫无疑问,最简单的方法是以登山运动员的回答作为回应:因为它就在眼前。民俗学的历史存在着,像山巅一样,它掩盖着历史的云霞,优美迷人,在日益遥远的时间长河中若隐若现。发现历史真实、审视历史存在对研究者来说是一个挑战,就像登山者想要登临绝顶、俯瞰群峦一样。但是这样的回答反映了历史研究可能潜藏的缺憾,而非对其价值意义的阐述。研究民俗学的历史可能只是为收藏癖提供了一个新的宣泄口,我们专业也被偏见或嘲笑地认为仅限于此。①参见 Alan Dundes, "On the Psychology of Collecting Folklore," Tennessee Folklore Society Bulletin 28(1962): 65-74.它将富有进取心的民俗学者的精力从收集故事、歌谣、谚语以及索引卡片转移到收集历史事实上。无论我们的先辈试图隐藏什么,我们都将吃力乏味地揭开其神秘面纱,窥探其信函抽屉,收集和分类过去关于收集和分类的历史。将早期民俗研究方法转移到新兴课题上,民俗学家会很容易陷入“习惯性的谬误”中,②参见David H. Fischer, Historians' Fallacies: Toward a Logic of Historical Thought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0), p. 152.列举那些只在时间演替中相互关联的现象,由此产生的叙事可能只是历史记录而非历史研究。③历史记录与历史研究的区别已经在历史学文献中被详细讨论过了。例如, Benedetto Croce, History-Its Theory and Practice, trans. Douglas Ainsli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1921), pp. 11-26; R.G.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London: The Clarendon Press, 1946), pp. 202-203; Morton White,Foundations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1965), pp. 222-270; Arthur C. Danto,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 (Cambridge: The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112-142.
毕竟,民俗研究在很多方面并没能成功规避与记录法类似的研究方法陷阱。文本的积累、索引的编制已经证明我们是称职的口头传统记录者而非研究者。我们根据随意的主题系统组织资料,而经常不考虑文本本身主题和母题之间的内在关系。汤普森(Stith Thompson)这段对索引目的的陈述是索引本质最有力的注脚:“作为民俗学的一种方法,母题-索引仅仅是未来研究的基础工作。它几乎不能称之为研究。我们并不研究任何一种罗列的母题。这项工作与未来民俗研究的关系就像字典与文学创作者,地图与需要辨正方位的探险家之间的关系一样。”④参见Stith Thompson, Narrative Motif-Analysisas a Folklore Method, FFC 161 (Helsinki: Suomalainen Tiedeakatemia, 1955), p. 9.
然而,尽管记录法已被谴责为不适合进行历史的陈述、解释和分析,民俗学中与之相应的方法却长期以来被视为学术研究的基石之一。民俗学草创时期曾致力于研究工具的构建,例如分类体系、索引、目录、注解集等。这些工作是为了使民俗学家具有专业性,同时防止其他学科学者因个人目的“窃取”这些素材。但是对技术和工具过分的关注导致了对最初引发民俗研究兴趣的理论和哲学问题的不可避免的忽视。因此,民俗学变成了一项技能,而非科学。
更有代表性的是,道尔逊(Richard M. Dorson)在一本新教科书中希望能限定一些特征将民俗学者与“人类学家、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以及政治科学家”区分开来,他讨论的是民俗学者的技能:田野调查、博物馆的利用、索引的使用。⑤参见 Richard M. Dorson, ed., Folklore and Folklife : An Introduc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2), pp. 5-7.当道尔逊更多地着手讨论学科理论而非技能时,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当代民俗学理论》⑥参见Current Folklore Theories. Current Anthropology 4 (1963): 93-112.是《民俗与民俗生活:概论》的早期版本,它的标题很清楚地表现了这种倾向。而且这一点很快清晰可见;尽管民俗学的理论是从其他学科借鉴过来的,但它所使用的技术工具都是自己的。事实上,在这篇文章的早期版本中,道尔逊通过其所派生的学科名称定义了一些理论,例如“人类学理论”“心理学理论”;其他诸如“比较民俗学理论”“国家民俗学理论”“结构民俗学理论”,他们和历史学、政治科学、语言学等学科也有密切的关系(尽管在标题中并没有直接反映)。后期版本包含了更多最近的民俗研究理论,道尔逊根据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来定义,例如“历史地理学”,他们认为这么做的目的是达到“历史的重构”,甚至是“意识形态的重构”。忽略之前的民俗学理论概念,而以更新的视角去看待它们,这一能力本身或许就反映了民俗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成熟过程。但是,民俗学家(很明显包括道尔逊在内)几乎没有认识到他们自己开创了民俗学发展的新阶段。他们仍然在疏忽地谴责自己的学科太关注技术层面,缺乏讨论显著而独特的思想和理论问题。在一次并非界定民俗学定义的场合,道尔逊指出:
我们应该更好地界定民俗学者,然后再假设他的研究对象是民俗。前提是民俗学者应掌握一套技能将他与文学、人类学、语言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近邻学科区分开来。这些技能可能都不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合在一起,它们代表了一类学者的格式塔(Gestalt)形态。①参见Richard M. Dorson, "The Techniques of the Folklorist," Louisiana Folklore Miscellany 11 (1968):2, reprinted in Folklore: Selected Essays, ed. Richard M. Dors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2), p. 12.
对技能,而非思想和理论的强调也成了教学活动的重点,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项目也是这样。有好几次,我都尝试在博士生资格考试中加入民俗研究的目的,民俗研究与通常意义上的人类本质、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的题目,但每次都遭受拒绝,或者是委员会主席认为它们太模糊而将之删除,或者是学生们就直接避开作答。
掌握研究工具而无用武之地的两难处境催生了沮丧、不满、学术自卑等情绪的交集。民俗学学生对其他学科的态度很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民俗学者总是比其他学科更多地倡导并实践跨学科工作。他们从人类学、语言学、文学、文学批评、文化地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中寻找观点、论题和理论框架。当然,尝试去打破学科间的边界和壁垒是值得称赞的,但是,如果只涉及单方面的借鉴和交流,它只能是学术地位低下的表现,而非学术自由的象征。根据乌列尔·福阿(Uriel G. Foa)的观点,通过归纳“某学科引用其他学科文章的频率,可以反映这一学科在被研究学科中的相对地位”②参见Lee Thayer, Communication: Concepts and Perspectives (Washington: Spartan Books, 1967), p. 149.。根据我的印象,民俗学者总是更倾向于引用其他学科的成果,却被这些学科的学者引用得最少。
意识到民俗学在学科中的低微地位,学界开始寻找“替罪羊”来责怪这种令人沮丧局面的形成。其中最受指责的是不可解释的,被断言不可定义的我们的学科名称:民俗学。关于这一点,一个朋友最近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表达了一种经常被讨论,却很少被用文字表述出来的感觉:
民俗学,不像当今的符号学(或者二十年前的语言学),它不是正在形成,而是已经形成;而且它不可能像符号学和语言学一样因为‘民俗学’这个有魔力的词语而得到资金支持。③1977年10月8日通信。
将民俗学的处境归咎于术语,就像新娘形象欠佳却责怪服装一样。语言学、符号学的术语是时髦的,但更重要的是,它们关注研究的是长期以来被人类思考的主题和问题。如果我们要将民俗学从技能发展为科学,名称的转变至多只能像是一场魔法秀。它并不足够。我们必须以思想充实学科,有能力概括性地提出问题并且在研究的基础上解决问题。在民俗学的后工具化时代(postinstrumentalization era),研究过程以及学科概念中的这种转变显得尤为迫切。为了促进民俗研究的重新发展,我们必须返回到这个学科的前工具化时代(pre-instrumentalization),研究最初激起对民俗研究兴趣的思想和观念。
民俗研究根源于17世纪及18世纪早期思想艺术的沃土,有些甚至可以追溯至更远时期。与民俗有所关联的浪漫主义、民族主义、文学和政治运动,是其起源,但已经是孕育民俗学的最后阶段了。俄国形式主义学者巴赫金正确地指出,“大众特色和民俗学的狭义概念在浪漫主义运动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只是最终完成于赫尔德和浪漫主义学家们。”①参见Mikhail Bakhtin, Rabelais and His World, trans. Helene Iswolsky (Cambridge, Mass.: M.I.T.Press,1968), p. 4.尽管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思想家们的思考方案在当代已无需复兴,但是他们提出的关于信仰与历史,语言与想象,人类、自然与社会的本质等基本问题仍然对当今研究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它们对民俗研究提出的挑战应该结合当代概念、方法和理论框架来讨论解决。对民俗研究史的研究因此也就可以回复到在拓展研究工具时被抛弃的学科思想维度上来。
当然,从格林兄弟记录口头故事开始,到汤普森为所有可用文本编制索引为止,这个历史时代展现的初衷和结果并非协调一致。这期间,部分民俗学学生分享着理论与思想,但学术研究的重点还是为学科发展创建技术工具。现在,既然工具已经存在,民俗学者又燃起探索思想理论、重审学科前提的希望与渴求。研究民俗学的历史可以将民俗学形成的理论问题扩展到前范式阶段,进而使其与在关注方法问题时被搁置的问题一并得到关注。它同样可以改变民俗学的边缘境地,赋予其学科合法性,使其在关乎人类本质的学术讨论中发挥主要核心作用。
一些民俗学者通过其他途径来实现这个最终目标。应用民俗学(applied folklore)②参见 Dick Sweterlitsch, ed., Papers on Applied Folklore, (Folklore Forum Bibliographic and Special Series, no.8), Bloomington,Ind.,1971.如今的兴趣完全在于贴近当代迫切的社会问题进行研究,为理论探讨寻找切实可行的研究出路。因此,如果应用民俗学将研究与社会需要结合起来,对民俗研究历史的探寻也就重新建立起了民俗学科与关于人类的主要观点之间的联系。
但是民俗研究史并不仅仅为了满足当前的需要。它是一个以自身为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的课题。民俗学学生与研究课题的互动、不同学科的交叉渗透,以及民俗学大众运动和政治运动体现出的复杂社会关系共同构成了科学史上一个几乎未曾涉及的研究章节。对于“谁研究谁”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在涉及到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社群等历史变量时也变成了一个复杂的叙述。格林兄弟传记以及英国民俗学史给大家留下一种印象,认为民俗学是“知识贫民化”的,它是中上层阶级对贩夫皂隶之人的研究。③参见Gunhild Ginschel, Der junge Jacob Grimm 1805-1819, Deut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 Veroffentlichungen der Sprachwissenschaftlichen Kommission 7 (Berlin: Akademie Verlag,1967); Ruth Michaelis-Jena, The Brothers Grimm (New York: Praeger, 1970); Murray B. Peppard, Paths Through the Forest: A Biography of the Brothers Grimm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1971);Richard M. Dorson, The British Folklorists: A Hist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这种研究关系的产生不一定与阶级意识或对研究对象的轻视态度有关。在很多时候,由于民俗研究得以建立的浪漫民族主义背景,学者们往往更崇拜敬仰那些出身低微、不加雕饰的叙述者或者歌手。不过总体来说,我们在这方面缺乏细节,至今也无法建立一种行为模型来测量民俗学者与调查对象之间的社会关系及所持态度。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传闻轶事,但是它们表现出的是例外而非常规,例如,一个来自布鲁克林的第二代犹太移民并不研究自己的文化,而转向研究苏格兰穷人的文化。因此,从社会学视角,我们学科有了历史的维度。这种探索直接关系到我们学科的思想和理论,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它们是科研过程和田野经历的直接成果。①人类学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可参见 Dennison Nash and Ronald Wintrob, "The Emergence of Self-Consciousness in Ethnography," Current Anthropology 13 (1972): 527-542,以及附于文后的参考文献。
学生与研究课题之间的社会互动只是复杂社会关系中的一个参量。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根据社会的阶级结构设想研究者的行为选择。学科规范和学术传统已经影响了我们研究民俗学的方法,它建构起一张同样值得研究的处于变动中的关系网络。相关论文直接反映了民俗研究史的这一特征,同时展示了美国民俗学领域的一些重大进展。当然,它们并不代表早期民俗研究中的所有重要趋势。例如,它缺少了对族群、区域和职业边界相关民俗记录与研究的讨论。“联邦作家计划”(Federal Writers’Project)参与记述口头传统而产生了大量的民俗出版物,它们影响了民俗学科的发展进程,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形塑了很多美国民俗学者的研究兴趣。②参见 Jerre Mangione, The Dream and the Deal: The Federal Writers' Project, 1935-1943 (Boston: Little,Brown and Company, 1972), pp. 265-285; Benjamin A. Botkin, "WPA and Folklore Research: 'Bread and Song'," Southern Folklore Quarterly 3 (1939): 7-14; and Benjamin A. Botkin," Living Lore on the New York City Writers' Project," New York Folklore Quarterly 2 (1946): 252-263.同时,“通俗化”在理解民俗学作为一门专业学科时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也应被全面分析。③对民俗学的一般印象直接影响了民俗学在大学中的发展,因为通过国防教育法案拨款的资金后来被撤回了。参见 Richard M. Dorson, "Folklore and the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75 (1962): 160-164.最近研究表明,与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相比,民俗学相关于思想和行为的更紧密非学术趋势。赫尔德的思想最初刺激了欧洲民俗学的诞生,而且影响了美国文学派对“民”的认知,现在它被转化成政治运动中或左或右的意识形态。④参见Richard A.Reuss, "American Folklore and Left-Wing Politics 1927-57";R.Serge Denisoff, Great Day Coming: Folk Music and the American Left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1); Sing a Song of Social Significance (Bowling Green:Bowling Green University Popular Press, 1972); Gene Bluestein,The Voice of the Folk: Folklore and American Literary Theory (Amherst, Mass.: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72); and Wolfgang Emmerich, Zur Kritik der Volkstümsideologi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71).这种社会宣传和方法论研究之间复杂的历史关系,应站在历史的维度去看待和分析。
亨德森(M. Carole Henderson)结合加拿大情况谈到了这个问题。她恰当地指出,民俗研究构建出一个很容易受到社会和政治事件影响的开放系统。民俗学范式⑤科学史上对于范式概念的讨论可参见 Thomas S.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2nd e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Margaret Masterman, "The Nature of a Paradigm,"in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ed. Imre Lakatos and Alan Musgrave (Cambridge: Th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59-89.应该在更大的社会承启关系中被研究和检验。
然而,这方面的大部分论文还是围绕着民俗学范式的形成过程来谈的,也就是说,他们叙述了为研究奠定基础的一些尝试,包括课题的确定和选择、理论框架的建构及研究方法的建议。他们也描述了社会和学术语境中民俗学的体制化过程。学术机构的重要性也被美国民俗学的创始人关注到了。他们十分清楚,建立机构可以帮助他们规范、系统、执行研究及出版相关事务,因此,贝尔(Michael Bell)和达内尔(Regna Darnell)在各自论文中表现出的强烈个性差异实际上反映了在研究路径上科学取向与思想取向的区别。他们的论文讲述了美国民俗学的创始故事,描述了学科前辈在有关神话界定方面的争论。但奇怪的是,与我们熟知的神话叙事不同,失败方幸存了下来,并且在接下来的很多年间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
像贝尔和达内尔陈述的那样,美国民俗学会在这场关于研究方向的讨论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博厄斯(Boas Franz)和纽厄尔(William Wells Newell)依据此权力基础展开了各自的学术斗争。他们在学会中都占据着既得权益。一方面,博厄斯抗议波士顿和华盛顿的人类学当权派,通过美国民俗学会推进自己的理论,推出生源。①参见 George W.Stocking. Jr., Race, Culture and Evolution: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8), pp. 195-233.另一方面,纽厄尔挑战由巴塞特(Bassett)领导的芝加哥民俗学会秉承的纯文学研究方向。这两股力量结合起来为美国民俗学会留下了人类学理论印迹。托雷森(Thoresen)在论文中指出,这种倾向助推了克罗伯(Kroeber)进行人类学-民俗学研究,这在当时可以说是社会科学理论的先驱了。
在美国,像很多其他学科一样,民俗学有两种制度化形式:学会和大学。博厄斯和纽厄尔是学会主席,但是他们,尤其是博厄斯的志向是在大学中建立科研与教学机构。实际上在合适的时机下,博厄斯在人类学领域实现了他的目标,民俗学则相对落后,它在很多年后才在大学中建立了自己的大本营。(实际上,这其中有超过50年的鸿沟,美国民俗学会在1888年创立,而印第安纳大学最初授予民俗学学位是在1949年。②“民俗新闻”(Folklore News)版块发布了这则消息,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62 (1949): 193.其他关于美国大学中民俗学科的信息可参见Ralph Steele Boggs, "Folklore in University Curricula in the United States," Southern Folklore Quarterly 4 (1940): 93-109,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olklore in a University," in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d. George R. Coffman,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Sesquincentennial Publications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45), pp. 106-111;Richard M. Dorson, "The Growth of Folklore Courses,"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63 (1950): 345-59, "Folklore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Folklore 62 (1951): 353-366, "The American Folklore Scene, 1963," Folklore 74 (1963): 433-449, and "The Academic Future of Folklore,"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Supplement, May 1972, pp. 104-25 (includes seven commentaries); and Ronald L. Baker,"Folklore Courses and Programs in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84(1971): 221-229.)
尽管如此,在这期间仍然有一些大学在进行不同强度和集中程度的零散教学。当然很多课程反映的是巴塞特和芝加哥民俗学会倡导的文学方向,而非纽厄尔和博厄斯致力的人类学方向。文学派的支持者来自于并未参与学会斗争的第三方,也就是因推崇民歌而知名的乔叟故事研究者查尔德(Francis J.Child)。大部分的大学课程都直接或间接地相关于他19世纪末在哈佛大学的讲学,以及追随其脚步的他的弟子基特里奇(George Lyman Kittredge)的课程内容。就像莫莉(Linda Morely)说的那样,查尔德是因为对中世纪英国文学的兴趣才开始民俗研究和歌谣研究的,而这种文学倾向持续影响了民俗学者的研究与教学。当汤普森和泰勒(Archer Taylor)在20世纪20年代在哈佛大学跟随基特里奇学习时,他们继续追随着这种文学传统。当他们将关注点转向芬兰民俗研究方法时,两者也毫无违和,因为历史地理法同样部分来源于对民俗传统的文学兴趣。这两位学者对美国大学中民俗学的教学方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建立了以文学而非人类学为基础的教学指导。因此,虽然人类学派很多年来在美国民俗学会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在大学中占据主要地位的却是由巴塞特和芝加哥民俗学会主导的文学派。这个传统的影响至今仍然存在,现在大部分的民俗学课程还是安排在文学学科下,而非人类学学科下的。①参见Baker, "Folklore Courses and Programs in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围绕学术活动中心展开的斗争不应掩盖个人在学科发展中的作用。它为我们提供了特定时期学术活动的部分境况,尤其是具有表演性的境况。通过筛选,阿尔维(Alvey)最终确定了这个研究角度:巴里(Phillips Barry)对民俗学的贡献。他展示了一个叛逆、不墨守成规的学者,也就是一个不对任何人负责,不对任何机构和科学规范负责的人的重要性。巴里因此可以探索新的理论与方法,可以挑战权威,可以尽情地推测想象,也就因此可以开创新的研究领域。
上述大部分论文的传记性特征不能也不应该掩盖探索民俗研究历史的目的,也就是,检验不同时期构成民俗研究基础的理论和思想。尽管传记类的记述很容易变成叙述个人轶事,但利用恰当的话,它也可以描述学科的发展,不仅作为一种观点,而是作为一种经验。②参见Jacob Gruber, "In Search of Experience: Biography as an Instrument for 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in Pioneers of American Anthropology: the Uses of Biography, ed. June Helm ( = The American Ethnological Society Monograph, 43)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6), pp. 5-27. 也可参见the "The Making of Modern Science: Biographical Studies," Daedalus 99, no. 4 (Fall, 1970).就像这些论文展示的那样,这种类型的研究强调了过去学术研究对人的关注,它是被复杂的人际互动、对失败的沮丧,以及对成功的喜悦所影响的。这些文章有助于我们理解比其自身更为广泛的承启关系,同时也建构了学科发展的模式,正是这些模式或独立或完整地塑造了民俗学的基本形式。
——学院派民俗学的世界史纵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