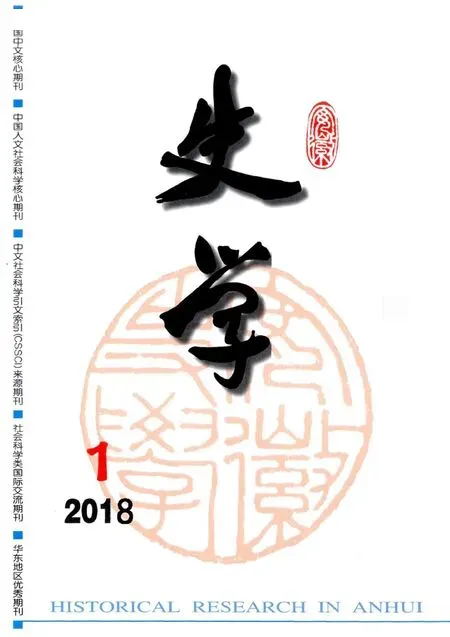潘光旦与胡适自由思想比较散论
杨宏雨 武良刚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潘光旦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学贯中西、通晓古今”的学者,其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探求实现个人和社会的自由发展之道,为提振中华民族的“位育力”而不断努力。潘氏对自由问题的论述在不少地方独树一帜,发人深省。胡适是五四以后中国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胡适的自由思想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影响很大,几乎任何有关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研究都绕不开他。本文拟对两人的自由思想作些比较,自知不全面、不系统,故称散论。
一、潘光旦:“自由是生命的最大目的”;胡适:“只有在自由独立的原则下,才能有高价值的创造”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古今中外,之所以无数的人热爱自由、追求自由,甘愿为自由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那是因为自由在个人和社会的发展中有着无尚的价值。潘光旦和胡适都属于自由知识分子*本文的自由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涵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带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两类人物。带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用潘光旦的话说就是“内外转不分明”的一类人。潘光旦说自己不喜欢任何主义,自然也就不喜欢被贴上自由主义的标签,从他的思想和行为看,比较适合带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这个标签。,他们都高度推崇自由的价值。潘光旦说:“自由是生命的最大目的,个人要自由,社会也要自由。”又说:“唯有自由的生命才能比较长久的保持它的活力,个人如此,社会也是如此。”*潘光旦:《自由、民主与教育》,《潘光旦文集》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7页。他阐释说,从个人的角度看,“人人有发展的欲望,才力比较优异的分子更有完成自我而为人群致用的要求。满足这种欲望与要求的场合当然不能由别人来规定安排,而必须由自己来规定安排,自己的要求,只有自己最明白,别人无论如何体贴,如何设身处地,总有几分隔靴搔痒,何况别人又未必能体贴,甚至于名为体贴我,而实际上则专为他自己或他所隶的小群谋权势地位的巩固与扩大呢?”*潘光旦:《民主政治与民族健康》,《潘光旦文集》第5卷,第474页。从社会的角度看,“一般的自由,包括很基本的信仰自由在内,确乎是文明进步的一大动力。”*潘光旦:《沉着与自由》,《潘光旦文集》第5卷,第276、277页。他检讨美国强盛的原因,指出:“美国民族的伟大,是由于他们是移民。”“他们对于自由的爱好,可以说是身心天性中的不可须臾离的要求。‘不自由,无宁死’是端为这一类的人说的。”自由在美国的社会发展、进步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信仰的自由与自由的信仰是美国民族所由强大的一个缘由”。美国的发展起初是爱好自由的人“发挥了自由的信仰与创立了自由的制度”,然后是这种信仰与制度“转而维持与培植爱好自由的人”。这样,美国社会“自由的人文环境,其程度远在其它民族的人文环境之上”。*潘光旦:《沉着与自由》,《潘光旦文集》第5卷,第276、277页。因此,可以说没有自由就没有美利坚,就没有美国民族持续的兴盛与进步。
胡适也非常强调自由的意义。他说:“只有在自由独立的原则下,才能有高价值的创造。”*胡适:《谈谈大学》,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41页。他认为专制制度最大的弊端就在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胡适:《易卜生主义》,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6、485、488页。一个社会限制了人的个性,也就从根本上妨碍了人“充分发达自己的天才性”。*胡适:《易卜生主义》,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6、485、488页。自由是个人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进步的动因。“盖人类进化,全赖个人之自荩。思想之进化,则有独立思想者之功也。政治之进化,则维新革命者之功也。若人人为他人之故而自遏其思想言行之独立自由,则人类万无进化之日矣。”*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16页。“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就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国家是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的。”*胡适:《易卜生主义》,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6、485、488页。正是因为个人自由与他人自由、社会自由具有统一性,所以胡适喊出了他那振聋发聩的口号:“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1—512页。
自由包含的内容很广泛,如表达自由、信仰自由、身体自由、通讯自由、迁徙自由等等。在各种自由中,胡适特别强调信仰自由与言论出版自由的重要性,“我深信思想信仰的自由与言论出版的自由是社会改革与文化进步的基本条件。……如果没有思想信仰言论出版的自由,天文物理化学生物进化的新理论当然都不会见天日,洛克、伏尔泰、卢骚、节浮生,以至马克斯、恩格尔的政治社会新思想也当然都不会流行传播,这是世界近代史的明显事实。”*胡适:《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10、609页。
胡适在美国留学多年,对美国的民主制度和文化“神往之至”。和潘光旦一样,胡适非常看重民主自由对于美国革新与进步的重大意义,“五十年来的美国,是以社会的制裁,政治的制裁,和社会的立法,建立了自由民主制度。以大量生产建立了工业化的自由平等的经济制度,提高了人民生活,无贫富之悬殊,作同等的享受,用不着革命(也不会有革命)而收到革新的效果。”*胡适:《五十年来的美国》,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2卷,第828页。不仅如此,胡适还认为,以英美为发祥地而兴起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大潮流”、“大方向”,“从历史上来看,世界文化的趋向,那民主自由的趋向是三四百年来的一个最大的目标,一个最明白的方向。”*胡适:《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10、609页。所以,“我们中国人在今日必须认清世界文化的大趋势,我们必须选定我们自己应该走的方向。只有自由可以解放我们民族的精神,只有民主政治可以团结全民族的力量来解决全民族的困难,只有自由民主可以给我们培养成一个有人味的文明社会。”*胡适:《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第613页。
提起美国,许多人都会想起纽约的自由女神像。的确,自由女神像是美国的象征,自由是美国的精神特质。1943年,费孝通访美,写下传诵一时的作品《初访美国》。在书中,费孝通不仅竭力称赞美国的繁荣与富裕,而且指出这繁盛背后的文化因素——美国“独来独往,不卑不亢,自负自骄,耐苦耐劳”的国民性,而这一国民性的养成应该“归结于它们崇尚平等,爱好自由的精神。美国的创造力并不是凭空获得的,而是从这种对生活的认真,对自由的爱好中长成的。”*费孝通:《初访美国》,《费孝通文集》第3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
自由精神以及自由制度的培植和发展对美国的兴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绝大多数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共同看法。
二、潘光旦:“个人的自由不是天赋的”;胡适:自由“是一些先进民族用长期的奋斗努力争出来的”
西方启蒙思想家洛克等人曾根据自然法以及社会契约论的精神提出“天赋人权”的学说,认为“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如果不得本人的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使之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力。”*[英]洛克著,叶启芳、瞿菊农译:《政府论》下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59页。“天赋人权”理念的提出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它不仅有效地满足了早期资产阶级反抗封建王权的斗争要求,而且还为此后广大人民要求实现和保护自己的自由、生命、财产、追求幸福的权利提供了重要依据。换言之,人权的实现程度成了民众判断政府的行为是否合法合理的重要依据,而这又为推动政治理念的现代转型开创了重要条件。众所周知,在人类近代政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标志性意义的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都是基于“天赋人权”这一神圣理念而草创的。
当然,我们在充分肯定“天赋人权”理念提出的重大历史功绩的同时,也要辩证地看待和分析这一概念。毕竟“天赋人权”思想的提出是基于自然法以及社会契约论这些“虚构”、“假设”理念之上的,“严格地说,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都只是理论上的虚构,它们没有也不可能得到严格的科学证明。”*唐士其:《西方政治思想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6页。潘光旦与胡适都很看重自由之于人类发展的价值和意义,但是他们都不相信有什么“天赋人权”、“人生而自由平等”之说。潘光旦说:“个人的自由不是天赋的,是人为的,不是现成的,是争取的。以前西方的政论家认为自由是天赋人权之一;究竟有没有所谓人权,此种人权是不是由于天赋,我们姑存而不论,我们只承认人既不同于普通的飞走之伦,便不会没有自由的企求。”他认为天赋人权说至多只是表明人类有要求自由的潜能,“要潜能变成动能,而发生实际的效用,却终须人工的培养,人工的培养就是教育。”*潘光旦:《自由、民主与教育》,《潘光旦文集》第5卷,第257—258页。胡适虽然终生服膺西方的自由主义,但他也对天赋人权说持否定态度。他说:“自由不是天生的,不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是一些先进民族用长期的奋斗努力争出来的”。*胡适:《自由主义》,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2卷,第806页。“从前讲天赋人权;我们知道这个话不正确。人权并不是天赋的,是人造出来的。所谓民主自由平等,都是一个理想,不是天赋的。……在某种社会上,人如果没有力量保护自由,专制的人可以把你的自由夺去。我们过去经过很多年的专制社会,那时我们的自由权利一点都没有,所以我们现在渐渐明白民主自由都不是天赋的人权,是人慢慢感觉到自己的尊严,人是有价值的,人格是宝贵的,慢慢的才自己感觉到某种权利与他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有了某种权利,才能使得他的教育完整,发展他的聪明才智人格道德。”*胡适:《三百年来世界文化的趋势与中国应采取的方向》,《胡适作品集》第26册,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109页。
由于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别,加上近代实证主义思维的影响,天赋人权说在中国并没有多少市场,严复、章士钊、孙中山、胡适、罗隆基、潘光旦等都对天赋人权论持否定态度。1912年,章士钊直言:“天赋人权乃十八世纪不可通之旧说。”*章士钊:《国权与民权》,《章士钊全集》第2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623页。1914年,严复曾专门撰写《民约平议》一文批驳卢梭的天赋人权说。*严复在1914年写信给熊纯如说:“自卢梭《民约》风行,社会被其影响不少,不惜喋血捐生以从其法,然实无济于治,盖其本源谬也。刻拟草《民约平议》一通,以药社会之迷信。”(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14页)1924年,孙中山在民权主义的演说中指出:“就历史上进化的道理说,民权不是天生出来的,是时势和潮流所造就出来的。”*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4页。1930年,罗隆基针对有人给他和《新月》月刊戴上宣扬天赋人权的帽子,发文声明:“我们不主张天赋人权”,“我们从来没有主张过天赋人权说”。*努生:《我们不主张天赋人权》,《新月》第3卷第8期。
当然,否认天赋人权说并不意味着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不要自由,不主张争自由。但在如何争自由这个问题上,潘光旦主张通过教育——自由教育来获得民主和自由,“从教育的立场看,惟有一个真正民主的政治环境,始能孕育真正自由或通达的教育,而从政治的立场看,惟有真正的自由或通达的教育才可以造成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二者实在是互为因果的。”*潘光旦:《自由、民主与教育》,《潘光旦文集》第5卷,第262页。胡适主张通过制定法律、实行法治来保障人权,“民权的唯一保障是法治”*胡适:《民权的保障》,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5页。;“只有站在法律的立场上来谋民权的保障,才可以把政治引上法治的路。只有法治是永久而普遍的民权保障。”*胡适:《民权的保障》,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5页。他呼吁南京国民政府“快快制定约法以确定法治基础!快快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胡适:《人权与约法》,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5卷,第529页。
近代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渐进的社会改良。造成这一特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在接受西方启蒙思想时,把自由、民主与天赋人权割裂开来”,导致了“近代生命理念的缺失”,“造成了近代启蒙思想的弱化和转向”*隋淑芬:《生命理念的缺失:近代天赋人权说的两难困境》,《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三、潘光旦:“我容忍人,人即自由,人容忍我,我即自由”;胡适:“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
说到自由,不少人都想到解放。的确,自由意味着从束缚自己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但自由决不是不要法律、不受约束的为所欲为。恰恰相反,自由是容忍和节制,是遵守法律和尊重他人权利的统一。古罗马的贺拉斯说:“谁是自由的呢?那就是能节制自己的贤者。”*转引自张秀枫主编:《大学生启示录》,南海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233页。黑格尔说:“当我们听说,自由就是指可以为所欲为,我们只能把这种看法认为完全缺乏思想教养,它对于什么是绝对自由的意志、法、伦理,等等,毫无所知。”*[德]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5—26页。
潘光旦和胡适都是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他们都认识到“容忍”——相互尊重,彼此包容、忍让对自由发展的意义。潘光旦主张以容忍代替自由一词:“‘自由’这个名词甚不妥当。自由的概念本来很捉摸不住,引用起来,每须注解,例如在法律范围以内的自由呀,以不侵犯别人的自由为自由呀……后面一说更是糊涂。实则‘自由’就等于‘要别人容忍’。如今只说自由,字面上看去,好像只为了自己着想,没有顾到别人;事实上也确有人如此看法,自由变成自肆,社会因而蒙其大害的。‘容忍’不明指人我都适用,而隐含人我都适用,我容忍人,人即自由,人容忍我,我即自由,不比较妥切么?”*潘光旦:《尚同与尚异》,《潘光旦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6页。换言之,自由是有边界的,这种边界不仅体现在法律的强制性规约上,更体现在人我之间“内在自觉”的约束上。如果说法律规定的每个人的权利界线是外界的、刚性的约束,那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信条就是内在的、柔性的约束。后一种约束是建立在个体道德修养和内在自觉上,其适用的范围不仅比前者要广,而且是前一种即法律所规定的刚性的约束得以推行的前提。没有每个个体自觉的自我约束,要完全通过法律来实现社会和谐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一是因为成本大、代价高;二是因为法律再多、法网再密,也会有漏洞、死角;三是因为立法者和执法者都是人,他们被法律赋予了很大的权力,如果他们缺乏道德,不能够自我约束,法律就会成为他们欺压人民、为非作歹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法网越密,人民身上的枷锁越多,权利被侵害得越多。
胡适不仅认同自由需要容忍,而且还更进一步提出了“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论断。他说:“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胡适:《容忍与自由》,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1卷,第827页。“法国哲人伏尔泰说的最好:‘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赞成,但是我会拼命力争你有说这话的权利’。这是多么有人情味的容忍态度!自己要争自由,同时还得承认别人也应该享受同等自由,这便是容忍。自己不信神,要争取自己不信神的自由,但同时也得承认别人真心信神,当然有他信神的自由。如果一个无神论者一旦当权就要禁止一切人信神,那就同中古宗教残杀‘异端’一样的不容忍了。宗教信仰如此,其他政治主张,经济理论,社会思想,也都应该如此。民主政治作用全靠这容忍反对党,尊重反对党的雅量。”*胡适:《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第611页。
胡适认为,无论是在宗教史、思想史上,还是在政治自由史上,“容忍的态度是最难得、最稀有的态度”。“人类的习惯总是喜同而恶异的,总不喜欢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为。这就是不容忍的根源。不容忍只是不能容忍和我自己不同的新思想和新信仰。一个宗教团体总相信自己的宗教信仰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所以它总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宗教信仰必定是错的,必定是异端、邪教。一个政治团体总相信自己的政治主张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所以它总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见解必定是错的,必定是敌人。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由于这一点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心理。因为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胡适:《容忍与自由》,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1卷,第825—826页。如果说“喜同恶异”是人类的天性,那么“迷信自我”就让这一天性走上了邪路。

基于对自由与容忍关系的认识,潘光旦和胡适都反对一党独裁,主张开放政权、公平竞争。胡适说:“自由主义在这两百年的演进史上,还有一个特殊的,空前的政治意义,就是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自由权利。向来政治斗争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被压的人是没有好日子过的,但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却渐渐养成了一种容忍异己的度量与风气,因为政权是人民授予的,在朝执政权的党一旦失去了多数人民的支持,就成了在野党了,所以执政权的人都得准备下台时坐冷板凳的生活,而个个少数党都有逐渐变成多数党的可能。”“在近代民主国家里,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权利,久已成了当然的政治作风,这是近代自由主义里最可爱慕而又最基本的一个方面。”*胡适:《自由主义》,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2卷 ,第808—809页。胡适认为,一党专政不仅不符合民主的原则,而且因为没有反对党的监督,极容易产生独裁和腐败。任何一个政党都应该确认“人民的福利高于一切,国家的生命高于一切”,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应该存有党权、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错误思想,妄想依靠武力垄断政权。*胡适:《政制改革的大路》,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1卷,第622、621—622页。他希望当时执政的国民党“抛弃党治,公开政权”,“颁布宪法,实行宪政”*胡适:《政制改革的大路》,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1卷,第622、621—622页。,引导中国政治早日“走上民主宪政的路”。*胡适:《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里求得一个共同政治信仰》,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1卷,第568页。
与胡适的上述主张很相似,潘光旦认为,“毋我”是民主的前提,是社会和谐发展的条件。“毋我”不是“无我”,它不是“不要我”,“硬把我取消”,而是“不要把主观的我抬出来,不要被主观的我所控制,受主观的我所蒙蔽”。*潘光旦:《毋我斯和平统一》,《潘光旦文集》第6卷,第215、216、215页。他认为,政党最容易受“主张、主义、理想之类”的东西蛊惑,“初则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终则派别森严,短兵相接”*潘光旦:《毋我斯和平统一》,《潘光旦文集》第6卷,第215、216、215页。,给社会的和谐发展带来极大的纷扰。面对抗战胜利以后国共冲突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他提出“毋我斯和平统一”的口号。他说:“和平要大家从毋我做起。”真正清明的政治与比较持久的和平,“必须以此为基础,才有把握”。*潘光旦:《毋我斯和平统一》,《潘光旦文集》第6卷,第215、216、215页。他希望中国的每个党派特别是当时实力最强的国共两党能做到“毋我”——抛弃“主义之争”,为中国的民主政治与和平发展奠基立业。“保守的人与进步的人,政治的主张虽有不同,虽不属于同一党派”,但“在朝的甲至少可以容许在野的乙一个合法的地位与活动的自由”*潘光旦:《类型与自由》,《潘光旦文集》第5卷,第227、225页。,这是政党政治的底线,有了这个底线,两党竞争或多党竞争才有可能。潘光旦特别欣赏英国的两党政治,他说近代英国政治“时而保守,时而进取,时而有所不为,时而大有作为,……在一切文明国家之中,是最稳健的,稳时不失诸静止,不妨碍进步,健而不失诸过激,不妨碍和谐。”*潘光旦:《类型与自由》,《潘光旦文集》第5卷,第227、225页。“英国人讲自由,是多少已经到了家的,已经有些炉火纯青的,就其民族分子中少数最能代表的例子说,仿佛已经接近那种‘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这种成熟的自由,表面看来就是沉着。时然后言,言必有中,时然后动,动必中矩,表面上看得见是真沉着,底子里看不见的是真自由。”*潘光旦:《沉着与自由》,《潘光旦文集》第5卷,第278页。
四、潘光旦:“只有真正人民自主的政治方能保障一般生活与特殊才智的自由发展”;胡适:“只有民主的政治方才能够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
在民主与自由的关系问题上,潘光旦与胡适有着比较一致的看法。

胡适对于自由和民主之间的辩证关系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和体悟,他说:“民主主义的生活方式,根本上是个人主义的。”*胡适:《民主与极权的冲突》,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哲学与文化》,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82页。“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胡适:《自由主义》,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2卷,第810、806、807—808、808、808页。东西方都有许多为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而奋斗的豪杰之士,都有悠久的争取自由、要求解放的历史,“我们中国历史上虽然没有抬出‘争自由’的大旗子来做宗教运动,思想运动,或政治运动,但中国思想史与社会政治史的每一个时代都可以说含有争取某种解放的意义。”*胡适:《自由主义》,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2卷,第810、806、807—808、808、808页。但为什么东方的自由运动始终步履蹒跚、成绩不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东方自由主义运动始终没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终没有走上建设民主政治的路子。西方的自由主义绝大贡献正在这一点,他们觉悟到只有民主的政治方才能够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所以自由主义的政治意义是强调的拥护民主”。*胡适:《自由主义》,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2卷,第810、806、807—808、808、808页。对比东西方,胡适指出,要保障人民的自由与幸福,只有建立民主制度,把一个国家的统治权“放在多数人民的手里”*胡适:《自由主义》,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2卷,第810、806、807—808、808、808页。,让人民自己掌控自己的事务。“我们也曾在二千年前就废除了封建制度,做到了大一统的国家,在这个大一统的帝国里,我们也曾建立一种全世界最久的文官考试制度,使全国才智之士有参加政府的平等制度,但我们始终没有法可以解决君主专制的问题,始终没有建立一个制度来限制君主的专制大权”*胡适:《自由主义》,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2卷,第810、806、807—808、808、808页。,所以,在中国,“民为邦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调子唱了几千年,但人民的自由和幸福始终没有落到实处,无法得到永久的保障。民本思想强调的是权力为民,即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这在古代社会,确实有了不起的进步意义,但因为权力掌握在统治者而不是民众手里,所以权力能不能为民或在多大程度上为民谋利,都只能依靠统治者的自觉程度,更不必提经常发生的那种主观为民客观扰民的蠢事了。民本思想也承认人民有推翻统治者暴政的权利,“为君臣易位、王朝兴替提供了合法依据”,但又对推翻暴君暴政的行为提出一系列的限制,比如“严格限定革命的主体,即惟有获‘天命’的人才能高举义旗,放伐暴君,另立新朝”;“严格限定革命的时机,即在一个王朝、一位君主的天命未绝之前不得革命”;*张分田:《民本思想与中国古代统治思想》下卷,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04—505页。因此,从总体上看,这一理论并不鼓励老百姓通过抗争来维护自己的权益。由于革命和反抗总是和流血、牺牲联系在一起,因此在中国古代社会,这种革命和反抗不是到了人民忍无可忍、无法生活的地步,一般不会出现。在中国古代,真正把王朝的前途和民众的利益结合在一起,能“以民为本”、“爱民如子”的明君圣主、廉吏贤臣屈指可数,人民安居乐业、其乐融融的太平盛世也是不多的。民主政治是主权在民的政治,“民主政治的意义,千言万语,只是政府统治须得人民的同意。”在民主政治下,人民可以通过选举自由自主地选择自己满意的统治者,统治者的任期是有限的,当统治者的行为违背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时,人民可以通过合法的程序以和平的方式换人。“民主政治制度是最有包含性,可以推行到社会的一切阶层,最可以代表全民利益的。”在民主制度中,“不须采用惨酷的斗争或屠杀,可以用和平的方式,做到代表最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政治。”*胡适:《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第610页。主权在民,任期有限,制度保证,可以换人,人民无须依靠统治者的仁德,就可以自主地实现和维护自己的利益,民主政治的这些优势是民本政治无法企及的。
五、潘光旦:“个人主义的自私自利主义和自由主义是分不开的”;胡适:“自由主义,最浅显的意思是强调的尊重自由”
潘光旦与胡适对自由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的看法,但也存在着不少分歧。
胡适是五四以后中国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他终身服膺实验主义,肯定、赞赏自由主义。胡适认为,人们虽然对自由有各种各样的界定,这些界定也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自由主义的某些特点,但“自由主义,最浅显的意思是强调的尊重自由,现在有些人否认自由的价值,同时又自称是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里没有自由,就好象长坂坡里没有赵子龙,空城计里没有诸葛亮,总有点叫不顺口罢!据我的拙见,自由主义就是人类历史上那个提倡自由,崇拜自由,争取自由,充实并推广自由的大运动。”*胡适:《自由主义》,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2卷,第805页。他积极肯定西方的自由主义运动,认为这一运动“自己要争自由,同时便想到别人的自由,所以不但自由须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界限,并且还进一步要求绝大多数人的自由。”“自己要享受幸福,同时便想到别人的幸福”,进而提出“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把这作为人类社会的目的。“自由、平等、博爱”是西方自由主义运动的三面大旗,“美国的革命,法国的革命,一八四八年全欧洲的革命运动,一八六二年的南北美战争,都是在这三大主义的旗帜之下的大革命。美国的宪法,法国的宪法,以至于南美洲诸国的宪法,都是受了这三大主义的绝大影响的。”“旧阶级的打倒,专制政体的推翻,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观念的普遍,‘信仰,思想,言论,出版’几大自由的保障的实行,普及教育的实施,妇女的解放,女权的运动,妇女参政的实现”*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都是欧洲18世纪以来自由主义运动的重要成绩。
与胡适对自由主义的颂扬与肯定不同,潘光旦对自由主义基本上持批判的态度,翻检潘光旦的作品,我们发现,除了1944年他在《外人之评论与我之自省》一文中比较正面肯定自由主义,认为“自由主义的真谛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其中最直接了当而发人深省的一个是:在人格或国格的发展中,我们一面要尊信自我,一面更要批评自我”*潘光旦:《外人之评论与我之自省》,《潘光旦文集》第5卷,第272页。,此外,几乎找不到其他对自由主义肯定的提法。潘光旦对自由主义的否定是他在1946—1949年的国共内战中政治上趋于左倾、靠近中共的思想基础。1949年8月,他在一份未完成的手稿中写道:“美其名曰个人主义的自私自利主义和自由主义是分不开的。两者不止是一丘之貉,并且事实上是一回事,自由是我们所蕲求而要努力充分实现的东西,但自由一成主义便变做放纵、散漫一类生活现象的冠冕名词;自个人生活言之,是放纵,自社会生活言之,是散漫。放纵的个人是不自由的,不但不自由,并且是一个奴隶,被物欲所支配以至于宰割的奴隶。外边有物的刺激,里边有欲的鼓荡,内外夹攻,腹背受敌,试问自由又在那里。资本主义发展后的西洋所谓中流以上的人,即一切自由主义者,就是这样主观的自以为自由而客观受了奴役的分子。尤其是在美国,人口少,资源多,物的刺激,欲的反应,交相勾引,层出不穷,终于造成一种幻觉,以为呼无不应,求无不得。”*潘光旦:《论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和服膺这种“主义”的人》,《潘光旦文集》第10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1页。潘光旦对自由主义的反感与不满,一是因为潘光旦厌恶一切主义,二是因为他把个人主义看作自私自利的代名词。
潘光旦在理论上反对一切主义,他说:“主义是成套数的,是多少先经过一番规定的,是有一定的解释,而发生疑义需要重新解释时又须诉诸一定的权威的,是具备了近乎教条的形式与精神、只须信仰而不容怀疑评论的。”*潘光旦:《派与汇》,《潘光旦文集》第6卷,第99页。一切主义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偏蔽”、“我执”、“武断”、“党偏”等毛病。学术上不同观点的分歧,本是一种正常现象,双方可以通过交流、辩论实现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不同的人或人群因为思想、经历、兴趣、气质、偏好等方面的不同,在不同的问题上价值取向不一致,行为选择有差异,只要不违反道德与法律的底线,都应该是允许的。“君子和而不同”,“君子周而不比”,“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些古老的名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但如果学派或政治见解上的不同上升到主义层面,就会把合理的矛盾分歧夸大,原本属于相反相成、多元共存的格局就会走向二元对立、分崩离析。潘光旦认为,崇尚主义,容易加剧思想间的排斥和倾轧,造成党同伐异的不良风气,更进一步,容易造成政治的宗教化、专制化,不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自由主义也是一种主义,自然也在他的排斥之列。
潘光旦认为,自由主义的基础是个人主义,“民主的立场始终承认个人的存在与每个人的需要充分健全的发展,是不成问题的。但这决不是个人主义。”潘光旦认为,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重视个人是对的,但这种重视应该是适度的,不能过分,社会和个人之间需要平衡,极端的重视或排斥个人利益都是错误的。自由主义极端推崇个人,“把个人推崇到一个成为主义的地位,那问题就来了。在这样一个崇高的地位之下,一个人所想到的第一个个人必然是他或她的自己。”由于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忽视公共利益,这样“在不健全的社会环境与制度之下,此种自我的觉察与关注必然会变成高度的自私与妄自尊大”。*潘光旦:《论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和服膺这种“主义”的人》,《潘光旦文集》第10卷,第370、371页。所以,“揭穿了看,个人主义就是赤裸裸的自私自利主义,一点折扣也没有。”他认为,从世界历史来看,“二百年来,个人主义国家的不夺不餍,对外恣意侵略,对内尽情剥削,外而招致战争,内而引起革命,穷兵黩武,自祸祸人,这便是一个主要的解释了。”*潘光旦:《论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和服膺这种“主义”的人》,《潘光旦文集》第10卷,第370、371页。
与潘光旦从个人与社会对立的角度来理解个人主义不同,胡适侧重从个人与社会统一的角度来看待个人主义。胡适指出,有两种个人主义,一种是假的个人主义,这种所谓的个人主义其实是一种自私自利,“只顾自己的利益,不管群众利益”的“为我主义(Egoism)”;一种是真的个人主义,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Individuality)”,“他的特点有两种: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胡适:《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卷,第564、567页。更进一步,胡适认为,这种“真正的个人主义”不仅不是自私自利的代名词,而且内含着反抗诸如家族、国家或是“社会”的束缚,为“人类”负责与奋斗的博大情怀,“试看古往今来主张个人主义的思想家,从希腊的‘狗派’(Cynic)以至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那一个不是一方面崇拜个人,一方面崇拜那广漠的‘人类’的?主张个人主义的人,只是否认那些切近的伦谊,——或是家族,或是‘社会’,或是国家,——但是因为要推翻这些比较狭小逼人的伦谊,不得不捧出那广漠不逼人的‘人类’。所以凡是个人主义思想家,没有一个不承认这个双重关系的。”*胡适:《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卷,第564、567页。胡适说:“民主主义的生活方式,根本上是个人主义的。”*胡适:《民主与极权的冲突》,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哲学与文化》,第682页。这种个人主义是健全的个人主义,它主张“个人须要充分发达自己的天才性;须要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胡适:《易卜生主义》,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卷,第485、487、488、486页。但须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胡适:《易卜生主义》,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卷,第485、487、488、486页。真正健全的个人主义决不只是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行所为都负责任”。*胡适:《易卜生主义》,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卷,第485、487、488、486页。有了后一条作保证,自由就不会变成放纵与自肆;有了后一条作保证,“‘为我主义’,其实是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胡适:《易卜生主义》,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卷,第485、487、488、486页。
从表面上看,潘光旦犯了不分青红皂白反对一切个人主义的错误,而胡适则能把个人主义分为为我主义和个性主义两种类型,但实际上,双方都有一定合理的内核。胡适认为,要变革社会,就要解放个人,社会的进步特别需要每个个体积极主动地争取自己合理的要求,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潘光旦则认为,即使是合理合法的个人利益,强调得太过分,也会对社会的和谐发展造成不良后果。
六、潘光旦:“自由就是中庸”,“真正的自由第一步是对内对己而言的”;胡适:自由“是不受外力拘束压迫的权利”,“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
如何处理个人与社会(抑或集体)之间的关系历来是思想家关注和讨论的热点。如果以个人与社会作为谱线上的两极的话,基本的类型有三种:其一,是偏向个人一极的所谓“个人主义”的自由传统;其二,是重视社会一端的“社会主义”自由路向;还有一种是走的类似于平衡两者的“中间自由路线”。潘光旦反对任何主义,自然也就比较认可第三种“中道平衡”的自由样式,反对过于偏向个人或社会。潘光旦说:“一种比较健全的社会思想,总不能不承认两个对象的存在,一是个人,二是社会。……这两个对象,要是发展得正当,是不冲突的,并不是不两立的。西洋社会思想界所有的群己权界的争论,以至于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森严壁垒,都不妨说是庸人自扰的表现。为什么?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是相辅相成的。社会生活需要个人生活的充实,个人生活需要社会生活的涵养。”*潘光旦:《论青年与社会思想》,《潘光旦文集》第5卷,第280、282页。从个性和通性的角度观察,潘光旦认为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各有所长,也各有其弊,“个人主义在人格一壁只着眼在个性一方面,在社会一壁当然只着眼在竞争,在进步,在效率,在速度,在变动不居,日新月异。以此为基础的英美社会生活虽占过许多的便宜,但也吃过不少的亏。”集体主义“在个人方面注重通性,在社会方面注重秩序、划一、与通盘的计划。”苏俄是当时世界上唯一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它已经收了不少的效果,但同时也已经发见不少的弊病和限制,而这种弊病与限制的一大根源,便是个性的抹杀”。*潘光旦:《论青年与社会思想》,《潘光旦文集》第5卷,第280、282页。“个人主义容易忽略通性,而集团主义容易忽略个性。”*潘光旦:《论品格教育》,《潘光旦文集》第5卷,第373页。无论是个性还是通性,都是一个社会安所遂生不可或缺的,因此,一个社会要和谐、进步,比较妥当的做法就是走中庸之道,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斟酌损益,中道平衡创自由。“自由就是中庸,就是通达,如果我们把不偏不易的旧解释撇开,而把中庸的概念和经权的概念联系了看,甚至于当做一回事看,我们就很容易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潘光旦:《自由、民主与教育》,《潘光旦文集》第5卷,第257页。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要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5卷,第511—512页。与潘光旦中庸的自由观不同,胡适的自由观明显偏向于个人主义的权利观。胡适可以说是当时中国比较彻底的个人主义者。为什么要热烈地呼唤和倡扬个人主义呢?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写到,“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胡适:《易卜生主义》,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卷,第481、486、488页。所以一个社会要进步,首先要靠个人来打破旧的习惯、腐朽的思想,“社会是个人组成的,多救出一个人便是多备下一个再造新社会的分子”。*胡适:《易卜生主义》,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卷,第481、486、488页。“自治的社会,共和的国家,(不)只是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自己所作所为都负责任。若不如此,决不能造出自己独立的人格。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胡适:《易卜生主义》,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卷,第481、486、488页。
1948年9月5日,胡适在《世界日报》发表《自由主义》一文,指出自由有两种不同的概念:一种是“看轻外面的拘束力量”,“回向自己内心去求安慰,求自由”;一种是“含有‘解放’之意,是从外力制裁之下解放出来”。*胡适:《自由主义》,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2卷,第805、806页。“我们现在讲的‘自由’,不是那种内心境界,我们现在说的‘自由’,是不受外力拘束压迫的权利,是在某一方面的生活不受外力限制束缚的权利。在宗教信仰方面不受外力限制,就是宗教信仰自由。在思想方面就是思想自由。在著作出版方面,就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胡适:《自由主义》,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2卷,第805、806页。从胡适的这段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所倡导和追求的自由比较接近于西方自由主义政治传统中的“外部自由”,而不是中国儒家哲学传统意义上的“内心自由”。
潘光旦虽然也时常倡导言论、学术研究以及教育自由等,但是其对于这种“外部自由”的追求却是基于其对“内心自由”的关注和提倡之上的。“内心自由”在潘光旦的自由思想中无疑占据着核心地位。他说:对自由的误解与误用有两种,“一种是根本不承认任何限制,其结果是不顾一切的自肆。这一种错误到今日是谁都承认了的,连同自由主义者自己在内。”“第二种是虽承认应有限制,却只知道此种限制是外铄的,而不是内发的。”*潘光旦:《梦魇的觉醒?》,《潘光旦文集》第10卷,第176—177页。西方政治学说中所说的“自由应以不妨碍别人的自由为原则”;“自由是法律范围以内的自由”等讲的都是外铄的限制。潘光旦认为,对自由而言,外铄的限制是必须的,但如果没有内心的自我控制,“外铄的限制是不发生效力的”。“自由的限制必须从每一个人的内心出发,方才有效。”*潘光旦:《梦魇的觉醒?》,《潘光旦文集》第10卷,第177—178、178页。他发挥中国儒家重视内心的导引和推己及人的思想,指出“真正自由的第一步是对内和对己而言的”。“一个对一己的欲望、情感、兴趣、思虑、理想、信仰随在能拿得起而亦能放得下、能抒展亦能收敛的人,才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自由的人是一己欲望、情感、兴趣、思虑、理想、信仰的主人,而不是它们的奴隶;有了这第一步,第二步对外对人的自由不求而自至。美国革命所标榜的幸福,以及社会主义者所称的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至少一半也必须从这种自由里产生,否则徒然是攘夺,是苦恼,不是幸福。”*潘光旦:《梦魇的觉醒?》,《潘光旦文集》第10卷,第177—178、178页。
伯克说:“既没有智慧又没有美德的自由又是什么呢?它是一切可能的罪恶中最大的罪恶,因为它是缺乏教养和节制的愚蠢、邪恶和疯狂。”*[英]埃德蒙·伯克:《法国大革命感想录》,伯克(Burke,E.)著,陈志瑞、石斌译:《埃德蒙·伯克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3页。自由需要节制,这是一个大家都明白的道理。但在规范自由的因素中,内在的约束与外界的压力哪一个更重要,则是一个难以说清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内省和德性的养成,潘光旦受其影响,认为个人内心的修养和内在品格的养成是第一位的,这自然有相当大的合理性。潘光旦提出,自由不是散漫与放纵,是“内发的节制”与“自动发生而有机的秩序”;自由就是“中庸”、“通达”、“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这些都是非常有见地的看法,在自由思想史上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参阅杨宏雨、武良刚:《潘光旦自由思想述论》,《福建论坛》2017年第6期。但过犹不及,譬如他说自我认识和自我控制是自由的两个先决条件,“一个人能先具备这两个条件,则不求自由而自由自至,别人在外表上不容许他自由,在实际上自由还是他的,剥夺不了;否则一切都是空谈。”*潘光旦:《散漫、放纵与“自由”》,《潘光旦文集》第5卷,第230页。这就完全否定了外在自由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失之偏颇的。
潘光旦和胡适在处理群与己、社会与个人关系立场上呈现出明显的分歧,这种分歧可以理解为书斋中的学者与社会活动中的思想家之间的差异。前者通常比较关注一般性的学理,后者则明显带有针砭时弊、为时代发声的热情。由于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特别是受中国集体主义文化传统的影响,自由在近代中国一直是比较稀缺的元素,近代中国在发展中遭遇的困境不是个人主义的自肆,而是个性的萎缩和个人权利的缺失,因此胡适的论断有的放矢,更符合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需求。
结 语
如上所述,潘光旦与胡适的自由思想既有高度一致的“共识性”表达,又有各具特色的“差异化”阐释。造成两人自由思想“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和而不同、并立相容”特点的原因何在?
潘光旦(1899—1967)和胡适(1891—1962)差不多属同时代的人,他们有着类似的求学经历和教育背景。胡适和潘光旦都曾留学美国,深受美国自由文化的熏陶,认同西方自由文化的基本内核及其进步性。这是两人在自由思想的主要方面或大原则上有较多共识的重要缘由。
胡适和潘光旦都接受过良好的国学教育,两人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都很深厚,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学贯中西、博晓古今”的思想大家。但潘光旦与胡适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是不完全一致的。潘光旦的态度是欣赏,他力图以中释西,比如他以中庸释自由,强调自知与自胜是一个人实现自由的前提,等等。通观潘光旦的文章,可以发现,他引述中国的古语、古籍很多,西洋的东西不能说没有,相比较而言,所占的成分比较少。刘绪贻说:“潘先生读经太多太久,中了儒学的毒。”*刘绪贻:《博学、济世、风趣的社会学家潘光旦教授》,《多情人不老——刘绪贻散文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2页。这是一针见血的看法。潘光旦想打通中西,实现中国儒学的新生和创造性转化,这个目的是好的,但他忽视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有许多根本性的缺陷,比如权利意识、法治意识、平等意识、民主意识等现代思想资源不足。他在其中浸润太久,渐渐走上以西学为儒学辩护的路子,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胡适在自己的文章中也喜欢征引中国文献,以求中西文化能相互印证。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还提出过“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文化建设主张。但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整体上持批判态度。他说自己整理国故的目的是为了捉妖、打鬼。“我披肝沥胆地奉告人们:只为了我十分相信‘烂纸堆’里有无数无数的老鬼,能吃人,能迷人,害人的厉害胜过柏斯德(Pasteur)发现的种种病菌。只为了我自己自信,虽然不能杀菌,却颇能‘捉妖打鬼’。”所谓整理国故,就是要“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相;用明白晓畅的文字报告出来,叫有眼的都可以看见,有脑筋的都可以明白。这是化黑暗为光明,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化神圣为凡庸:这才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他的功用可以解放人心,可以保护人们不受鬼怪迷惑。”*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4卷,第117页。胡适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潮非常推崇,是一个全盘西化的主张者。他积极引介、宣扬西方的自由思想,为自由主义辩护,成了五四以后中国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唐德刚说:“胡适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史上的贡献,与其说是他的学术‘理论’和政治‘行为’,倒不如说是他笃信自由主义的‘身教’和崇尚民主政治的‘形象’!国人一提到‘民主’、‘自由’,立刻就会想到‘胡适’。”*唐德刚:《胡适杂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这是非常准确、传神的话。
最后值得一说的是,潘光旦与胡适的人生志趣也是影响他们自由思想的重要因素。毫无疑问,潘、胡两人都是学者,但潘光旦可以算是一个喜欢沉迷于书斋的纯学者,胡适虽然也热爱书斋,但他总是忍不住跑出书斋来关心政治。从《努力周报》、《新月》、《独立评论》、《自由中国》等一系列胡适创办或参与创办的刊物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所以,相较于潘光旦,胡适的自由思想中更深切地凸显出“现实的政治关怀”色彩。
潘光旦与胡适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位思想大家,他们的自由思想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各具特色而又相互“补益”。深入比较研究他们的自由思想的异同,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20世纪上半叶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复杂性和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