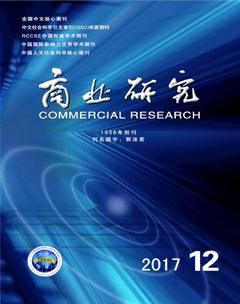服务业主导产业模式的服务交易民法调整研究
王福友
内容提要:服务业主导产业模式标志社会进入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民法应通过制度创新对此做出回应,以实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我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制度性解决。本文基于服务交易连通生产与消费环节的特点,提出了商事行为与民事行为并存同一交易下如何调整的新问题。服务接受者对服务业者存在严重的交易依赖,服务业者应坚持与商品交易不同的商业模式,即在坚持服务业内含的伦理约束下追逐营利。服务合同应在民法典编撰中实现有名化,重点通过规定服务业者义务的立法形式,维护服务接受者在服务交易中的信赖。
关键词:贯彻十九大精神;服务交易;商业模式;服务合同
中图分类号:D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8X(2017)12-0011-10
一、服务业主导产业模式对社会的影响
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已经形成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服务业内含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因子,若不能通过法治方式促进服务业独具的价值因素的有效释放,会导致服务业发展中经济逻辑与价值追求间的背离,单纯市场引导下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趋向难获价值性抑制,伴随产业结构变迁的或将是社会主要矛盾的不断深化。故研究服务业主导产业模式下服务交易的民法调整问题,虽直接体现为民法典对现代社会的积极回应,但深层意义则在于,其着力实现民众美好生活需要与发展间的关系改善,旨在通过民法努力推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制度性解决。
我国产业构成中,2013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467%,首次超过第二产业44%的占比。其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在由原来的工业主导型经济向服务主导型经济转变,这种趋势将对中国经济增长、就业以及各个方面带来深远而持久的影响。这一态势得到了持续且稳定的发展,到2015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已经超过GDP总量的50%以上,标志我国产业结构发生本质变化。服务业伴随着人们从满足于生存转向追求生活本身而蓬勃发展,对现代生活方式的追求成为推动服务业发展的驱动力,与其他产业驱动力相比,更具本源性。其突出表现在服务业支出占收入总额的比重持续放大,驱动消费与推动服务业健康发展成为一体两面。就我国居民生活消费情况观察,恩格尔系数呈现逐年走低趋势①,但“旅游恩格尔系数”②则呈逐年走高的趋势(张祖群,2011)。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自2009年以來,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交通和通信消费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始终保持在10%左右,人均文教娱乐服务消费支出的占比始终维持在85%以上。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把人类需求分成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五类,据此形成不同的消费者市场。上述数据表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居民已经摆脱以维持生存为目的的需要层次,向着以自我实现为追求的更高需求层次迈进。我国服务业的大发展是现代生活方式驱动的结果,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现代化的需要。现代网络技术对包括交易方式、生活方式等社会生活诸领域产生全方位影响,对这种影响的接受甚至超出实际收入水平增长的承受能力。网络、计算机与人的日常生活须臾不可分离,基于“留在现代社会”的客观要求推动人们对服务业的需求;尤其青年人在现代生活方式创新中发挥的引领性作用,在利用现代网络技术上发挥代际的逆向拉动,成为推动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动力。二是城镇化的需要。我国城镇化正处于高速发展的进程中,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4年的548%,年均增长达1个多百分比,每年有近1559万人成为城镇常住人口,而这一期间全球城镇化率年均增长只有约041个百分点(易信,2016)。我国城镇化发展需要从“重视非农化的城镇化”过渡到“重视市民化的城镇化”,促进进入城市的农民工逐步市民化和实现社会融合,推动生活方式变化和消费发展(尚虎平和高玲玲,2016)。三是老龄化的“需求效应”亦很明显,“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偏好服务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大,会使整个社会的服务需求增加,对服务业发展产生推动作用”(陈为民和施美程,2014)。
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并不是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之外新兴第三产业。“现代服务业既是工业结构调整和水平升级的产物,反过来,现代服务业发展又将反哺工业,促进产业内部结构调整和水平升级”(王可侠、彭玉婷,2017)。服务业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的发展领域:一是传统服务业的升级。以餐饮业等为代表的传统服务业,属实物或者劳务交易,法律上呈现出以买卖为主要形态的交易模式,服务只是交易的附带性成分。现代社会中传统服务业凸显服务之特质,通过服务环境、服务方式等方面的变革实现产业升级,服务在法律上具有区别于商品的独立调整价值。二是传统产业的服务业转向。服务作为一种经营形式和消费需求方式,是其他产业延长价值链的重要体现,该特点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均有体现。“在城市化、工业化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为解决农业产业化实践中的种种问题,应重视将服务业嵌入到农业产业化体系中,以服务业推动农业现代化模式重塑”(刘奕和夏杰长,2014)。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亦是现代制造业的主要发展方向(夏杰长、倪红福,2016)。但我国由于垄断行业改革不到位、专业化高水平人才不足、社会诚信体系有待完善等问题,金融服务、信息服务、商务服务、现代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难以与制造业融合互动发展,远未形成促进制造业升级的服务支撑体系,影响产业竞争力的有效提升(杨玉英和郭丽岩,2009)。三是现代服务业。主要是与现代经济发展形态相适应,且与信息、网络等现代手段相结合的新的服务业领域。
服务业主导产业模式引致社会发生深刻变化,促进以消费者增进权益目标的实现,既能够最大限度刺激需求,又实现人现代生活方式的转变。工业主导产业结构中,不利于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制度正面临巨大挑战,“到19世纪中期,法律制度以农民、工人、消费者以及其他相对无力的群体的利益为代价,以有利于商业界和工业界的方式重塑了。法律不仅确立并维护了经济与政治权力的再分配的规则,而且,在社会的其他任何一个领域中,只要可能,法律都积极促进不利于社会最弱势群体的财富再分配”(霍维茨,2005)。服务业以消费者为主要交易对象,内含满足消费者服务要求的本质,与工业主导产业结构的法律制度之间存在着法律价值上的冲突,若法律制度不做相应调整,伴随服务业发展的将是消费者弱势地位的加深。“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商人行为模式与普通市民的生活关系之间会明显不同”(近江幸治,2015)。服务业主要是社会分工深化后带来的专业化问题,相比于商品需求,接受服务属消费者享受型、个性化的高端需求,这种需求并不完全是消费者的主动性选择,甚至绝大多数是现代社会发展推动的结果。罗斯托提出,以公共和私人服务业(主要指生活服务业和城市、城郊建筑业等组成)为主的主导部门综合体系,表明经济成长阶段已经进入了“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董瑞华和傅尔基,2001)。在这个阶段中,现代技术不再被用来生产有形商品,而被用来改善生活质量的服务,不仅使人们生活得舒适、安逸,而且在精神上树立新的“价值标准”,为新的“理想”、“目标”而奋斗(董瑞华和傅尔基,2001)。产业结构高级化必然带来社会利益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变化,工业革命极大改变交易结构和市场秩序,社会阶层的分化呈现前所未有的特征,行政管理和国家控制的实现方式亦有变化(夏小雄,2012);加快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转型,亦有助于提高劳动者报酬、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形成利益结构和社会结构优化的新常态(迟福林,2015)。若不能辨别出服务业改善市民生活关系这一特质,就会使市民生活或者被淹没于交易关系的法律调整模式中,或者被异化为交易关系本身,社会结构调整也会丧失产业结构高级化带来的机会。endprint
二、服务交易民法调整的特殊性
(一)服务交易客体
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中,服务为市场交易的主要客体,但其是否具有法律调整的独立意义,使商品与服务二元交易客体体系的构建成为民法制度创新点不无疑问。商品交易以作为有体物的商品为交易客体,交易相对人旨在从中获得客体的某种权利;而服务则与之不同,但服务究竟为何不无疑问。有学者从商品思维出发,将服务交易客体界定为“商品服务”,“从服务业本质讲,其提供的是服务商品,本身具有非实物性、不可存储性及生产与消费同时性等特点,将其进行具体分类实为不易(刘伟和冯涛,2014)”。服务的上述特征显然与商品差异甚大,服务商品的说法虽并无不可,但这里的商品显然是能够涵盖服务与狭义商品的大概念③。欧洲民法典草案将建筑、加工、保管等均列入服务合同的范围,其认为,“服务结果可以是但不必然是有形的固定建筑物、有形动产或无体物”(克里斯蒂安和埃里克,2014)。其采取对服务业的宽泛理解,将建筑等纳入服务合同范围。有学者认为,服务的实质是让渡人力资本使用权。“商品交易的是商品所有权,服务是人力资本从事经济活动的过程,不存在所有权的交易,服务只是让渡人力资本使用权”(江小涓,2011)。该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将服务交易等同为劳务交易,但服务合同并非提供劳务的合同,“在提供劳务的合同中,标的只是完成一定的行为”(王利明,2002),有偿服务合同的履行是,“定作人获得由于执行人完成一定的行为或进行一定的活动而带来的利益的事实。定作人根据合同所获得的利益效果是非物质性质的,与承揽合同恰恰相反,承揽合同定做人所获得的一般是新的物或者已经存在的物的消费品质发生改变(变得更好)”(苏哈诺夫,2011)服务合同客体仍然没有超越债权客体的意义,但其却存在着特殊性。虽仍然是追求债务人对给付义务的履行,但服务合同旨在使服务接受者受益,债务人履行给付义务并不是服务合同追求的终极目标,其仅是服务于接受者受益这一目标的手段。非服务合同中,债务人给付义务与债权人追求目标是一體两面,给付行为本身应属中性。
笔者认为,服务本身乃无形物,服务业者通过商事营利行为或者职业行为针对服务接受者所期待的某种状态改变付出的努力;服务是接受者基于对提供者商事营利行为或职业行为信赖而对某种状态改变的交易期待。服务交易不以有体物的形式展开和结束,服务过程中涉及之有体物多属服务工具性质。某种状态的改变系服务接受者的主观追求,至于“状态”变好还是变坏均非所问。围绕期待性的权益,德国法区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取得权利的希望。它只是一种在将来取得权利的机会,能否在某个时刻取得该权利不确定,这种希望不被法律规范所保护。二是期待。只有在取得权利的部分前提条件已满足的情况下才存在(汉斯和沃尔夫,2012)。服务合同的标的介于希望与期待之间,由当事人约定受到债权保护的期待利益。服务业者不负有为服务接受者利益考虑之无限义务,具体合同中期待利益的确定与判别,要在满足特定服务类型一般服务目的的基础上,考虑服务接受者支付对价等因素。但在合同没有明确的相反约定,该期待利益不能低于该特定服务的行业标准,否则,该合同已经不再是服务合同。
(二)服务交易的主体
就主体与客体关系,商品交易中,商品置身于交易主体之外独立存在,交易过程主要是交付的问题而不是商品形成过程,交易结果为商品交易的主给付义务。服务之实现有赖于服务业者的商事行为或职业行为主导,亦需要服务接受者的参与或者配合,属主体嵌入式给付方式,服务交易中主体与客体须臾不可分离。提供者通过独有服务工具或者直接参与提供服务,其嵌入的形式及程度,甚至为消费者参与、享有服务创造的条件等均属服务的构成性要素。服务接受者通过直接参与到服务中得到服务满足,与商品交易中买受人仅接受商品不同。服务业者之义务履行对接受者权益影响甚巨,交易相对人的人身安全之保障义务并非如传统交易中居于附随义务之地位,在服务合同中则属基础性义务。就过程与结果相比,服务交易更加注重“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服务的过程就是“结果”,服务接受者在接受服务的过程中得到某种状态的改变,况且作为服务结果的“状态”,往往受制于服务业者投入程度及接受者的差异性,导致相同类型的“状态”对不同的服务接受者有程度不同的体现。
服务交易中双方主体的关系观察,服务业者以从事职业行为为表征,服务接受者呈现出对服务业者的更深依赖。服务领域职业化越高,服务接受者对服务业者的了解就会越困难,只能依赖于社会中形成的经验性评价,在专业化调查机构未能有效发育的情况下,服务业者会依靠行业、地域的业务支配力,甚至会操控市场评价,使服务接受者在选择服务交易对象上表现出极大的盲目性。对服务项目的选择更多依赖服务业者的描述,与商品交易中交易对象的实体展现不同,服务本身甚至不能基于重复性、体验性做出选择。即便在职业化水平不高的传统服务业中,服务业者亦会因长期深耕某一职业,或者对多元服务方式的不断创新,对其所从事服务行为的风险具有较强的预判力。服务接受者接受服务过程中,会在提供者参与的情况下对服务行为产生信赖,降低常态性的风险预判和防范能力,在享受服务过程中全部身心安全置于较日常生活更低的放松状态,甚至在接受医疗诊治等服务项目中,将自身生命安全等置于他决状态。服务交易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交易的基本逻辑,意思自治原则在交易关系缔结阶段能够得到贯彻,但因服务接受者参与接受服务过程,交易履行中其自我控制力会因对服务业者的依赖而降低。服务业者不断增进或者加深接受者对服务内容的依赖程度成为主要的营销策略,并推动服务业创新发展,“服务概念创新是企业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及环境的变化,对服务形成的新的理解,并根据这种新的理解形成的具体运作模式,是为解决企业生存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理念或方法”(姜铸、李宁,2015)。这一过程必然造成服务接受者依赖程度加深。若仍在传统交易模式下调整服务交易关系,会导致自然人接受服务这种生活状态只能在意思自治的框架内寻求合理性,契约自由可能成为限制自由和尊严的工具。“契约自由是自由和尊严的一部分,它是‘尊重每个人成为人这一最高道德律令的体现”(谢鸿飞,2014)。会导致服务业者与服务接受者之交易目的被等同视之,服务接受者因依赖服务业者导致的不利因未受到制度关怀而归由自己负责;服务业者则基于最大经济利益追求,对服务接受者的信赖采无视立场并不断加深服务接受者对其依赖程度。endprint
(三)法律调整机理的创新
商品交易的最大特点在于该交易模式下交易主体与客体间的关系状态,即客体脱离主体而存在,展现出“主体—客体—主体”的交易关系模式,主体间因对客体的不同需求样态而达成交易关系。“私人经济领域的需求满足主要通过以资产交换为目的的合同得以实现” (汉斯、沃尔夫,2012)。商品交易模式建立起法律居中立地位的调整机制,法律不会在主体间选择远近亲疏,交易利益交由当事人按照意思自治原则予以安排。但法律保持中立地位的原因不无疑问,通说认为,“民事主体具有平等性和互换性,因此国家可以采取放任的态度,让他们根据自己的自由意思,通过互相平等的协商,决定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他们所订立的契约被视为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梁慧星,1997)。平等性和互换性虽为有力解释,然平等性乃交易主体法律地位的形式假设,显无突破之可能;互换性则会因特定主体间的一次性交易,或者从事不同性质交易而无法保证交易得失上的无法抵消,仍然停留在假设层面。故平等性与互换性作为解释之根据并不足够,调整交易关系的合同法仍存在强制性条款,以矫正交易关系中的某种不平等因素,但深究其调整意图,亦并非针对平等性与互换性之维护展开。
笔者认为,商品交易模式内在地契合契约自由原则,其在法律上建构起交易双方主体与客体间的均衡状态,双方主体到达客体的距离在法律上相等,才促成法律在对待双方交易关系上持超然中立地位。主体到达客体的距离主要受制于双方行为的法律价值判断与双方掌控交易客体的能力两个变量,以平等主体间买卖关系为例,出卖行为与买受行为在价值判断上均属商行为;作为交易客体的有体物游离于主体之外独立存在,双方主体履行必要的交易注意,即可实现对交易客体的掌控,故商品交易模式下,双方行为的法律价值判断与双方掌控交易客体的能力两个变量对双方当事人无差异,法律建构起两段距离平等的理想且均衡状态。服务交易双方主体平等性假设并未发生变化,将接受服务者视为服务合同中的“弱者”,进而主张该类合同存在于不平等主体间,该认识有失妥当。服务交易的最大不同应在于,合同法基于商品交易而假设的交易均衡状态无法得到维持,影响主体到达客体距离的两个变量均呈现不同状态。(1)双方交易行为的法律价值判断不同。服务交易连通生产与消费环节的特点,提出了商事行为与民事行为并存同一交易下该如何调整的新问题。服务业者作为经营者其交易行为属商行为,旨在追求经济利益,其与商品交易并无差异;而接受服务体现为对高端生活质量的追求,相较于服务业者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显然具有更高的价值位阶。大村敦志认为,“民法是市场中交易的基本法,同时也是市民生活的基本法。……在生产和消费已经存在相当分离的现代,这两个方面虽然同样包含在民法之中,但是逐渐成为相对独立性很强的领域(至少有必要加以不同的考虑)”(大村敦志,2004)。若对此不予重视,服务业发展中消费环节的法律意义无异会被生产环节的法律逻辑所覆盖。服务业者的职业标准、职业道德、职业责任等,均构成服务接受者的交易信赖,尤其是职业行为中内涵职业伦理,形成对经济利益单向追求的有效抑制,使得服务交易具备更大的伦理性。(2)服务交易中双方掌控交易客体的能力差异甚大。服务属主体嵌入式给付方式,传统“主体——客体——主体”的交易关系模式对服务业难以适用,而呈现出“服务业者(服务)——服务接受者”的新模式。服务接受者对服务之接受呈现出对服务业者的依赖,应通过立法予以消解。综上,就两个变量情况的考察,必须基于服务业构建起新的法律调整机制,以在交易双方之间保持交易的均衡状态。服务业尤其是消费服务业形成了新的商业模式,即存在于主体间的具伦理性的逐利模式,而不是传统立足于主体针对客体即作用于自然资源的单纯逐利模式。应通过立法围绕服务目的之实现课以服务业者更多的义务,确保服务接受者对服务过程的有效享有,构建与服务业健康发展相适应的交易调整模式。
三、服务合同的有名化
(一)民法典编撰中服务合同应成为有名合同
就各国立法观察,没有将服务合同列为独立合同类型居多,但在民法典的债法修订中,服务合同问题被得到普遍重视。(1)以俄罗斯民法为代表,服务合同作为独立的合同类型,作為立法概念而不仅仅是学理概念存在。但其立法没有关于服务合同的一般条款,“转让财产所有权(物权)的债、转让使用权的债及完成工作的债有共同的一般条款,但提供服务的债没有与之共同的条款。不能认为《民法典》第39章就起到了一般条款的作用,因为它所明确的调整范围仅仅是事实上的,而不是以服务的法律特征为标准”(苏哈诺夫,2011)。(2)2009年日本研究团体“民法(债权法)改正检讨委员会”出版的债权法改正试案,建议新增融资性租赁及役务提供两个新契约类型。“日本改正试案增订役务提供契约之目的,并非增列与传统承揽雇佣委任截然不同之契约类型,而仅为形成所有服务契约均可资援用之原则,即建立服务契约之上位契约类型,具体服务契约如不属于法律有名契约类型,即可适用役务提供契约之规定”(陈自强,2013)。(3)《欧盟私法的原则、定义和示范规则:共同参照框架草案的暂行性版本》在第四编“有名合同及产生的权利义务”中,规定了服务合同。其前两章分别为一般条款和服务合同的一般规则;后六章规定了服务合同中的6种更具体的有名合同:建筑、加工承揽、仓储、设计、信息和咨询、医疗等(傅俊伟,2009)。(4)我国台湾地区“民法”未直接规定服务合同。学者认为,“劳务(服务)性契约,亦可分为有偿契约与无偿契约,惟均以委任为典型”(刘春堂,2010)。受任人乃忠实义务人,应负忠实义务,例如律师和医生(谢哲胜,2004)。但委任制度与服务合同又有不同。就未来服务合同的立法前景,有学者认为,“随着工业社会来临,经济发展之主轴,已不再是工业商品之制造与销售,而为专业拥有者之服务提供,以服务为交换对象之契约类型,不仅千变万化,更是与之俱增,令人目不暇接。欲事先掌握所有服务契约,类型化并妥为规制,事实上不可能,传统民法典对服务契约之规范方式,不外以承揽、雇佣及委任三种基本契约类型为核心,身边跟随若干特殊类型(如旅游、运送、居间、行纪等),并无法满足现代服务业者之服务提供之规范需求”(陈自强,2013)。endprint
我国《合同法》未将服务合同列为有名合同,对其如何适用应予研究。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易货交易,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根据该两条规定,服务合同为有偿合同但并非属“易货交易,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的”之交易,不能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基于此,服务合同之调整显无适用《合同法》分则之余地,只能按照合同法总则部分予以调整。然民法总则是以“物”为交易对象作为制度设计和安排的逻辑起点,日本学者认为,“因为设定全部客体的通则在技术上有困难,而‘物又是物权、债权中共通的重要事项。所以在民法中,仅设置了与‘物有关的规定。另外,即使是以‘人的行为为目的的债权,实现其利益的中心(构成要素),一般也是‘物(向某人要求某物)”(近江幸治,2015)。若不承认服务合同为独立的合同类型,会造成服务业的商业模式无法被固定下来,主要依靠合同约定配置权利义务,而服务接受者对服务业者的强烈依赖,必然导致接受者对提供者寄予的信赖与提供者试图通过合同约定逃避责任之间的紧张关系。围绕服务合同的立法模式,周江洪(2010)将其归纳为5种模式:超大服务主义、大服务主义、中服务主义、小服务主义、个别服务主义立法模式。有学者研究服务合同有名化的一般问题。有学者就服务合同类型中部分无名合同主张有名化的观点,如旅游服务合同、信用卡合同、寄递服务合同、医疗合同、机构养老服务合同、物业服务合同等等。合同法必须针对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做出快速反应,“作为一种契约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发展更为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提供保护。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当一国的契约维护制度质量越差时,交易双方潜在的机会主义行为就越可能发生;预期到这一点,涉及契约密集型服务产业的分工和交易越不可能发生,从而阻碍服务业发展”(汪德华等,2007)。服务合同有名化是促进服务业契约维护制度完善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服务合同的立法模式,可以有两个选择:一是在《合同法》分则部分增加“服务合同”这一有名合同;二是在《合同法》之外以特别法的形式单独规范服务合同。二者选择决定于对服务合同立法的内在机理问题该如何认识?《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据此,若认为服务合同单独立法的机理在于主体间的不平等,则服务合同应以特别法的形式存在;反之,若认为服务合同并没有突破主体间的平等性,则应选择在《合同法》分则中将其规定为一种新的有名合同。笔者认为,后者可资赞同。
(二)服务业者的主要义务
1忠实义务
服务合同中当事人间的结合程度要高于其他合同。百度给服务所下的定义是,“服务是指为他人做事,并使他人从中受益的一种有偿或无偿的活动。不以实物形式而以提供劳动的形式满足他人某种特殊需要”。服务交易中服务接受者对服务业者的信赖不以合同约定为要件,双方关系应属忠实关系、服务提供人应履行忠实义务④。忠实关系是指当一方信赖他方并将自己权利托付他方的情形,双方所产生的法律关系⑤。而忠实义务是指被信赖托付的一方对他方所应尽的忠诚且笃实的义务,是一种以他人利益优先于自己利益而行为的义务⑥。如英美法系中,如果金融服务业者处于利益冲突地位或者处于投资者信赖、依赖的地位,那么就负有更严格的法律义务,如美国法上的信义义务⑦。我国学者亦认为,“金融机构在管理运用资产时,其自身利益与投资者利益一旦存在冲突,必须以投资者的最佳利益为重,不得将自身利益置于投资者利益之上,不得在管理运用资产中为自己或第三人牟利”(叶林和董爱学,2010)。为服务业者设定忠实义务并非鼓励其从事纯粹的利己行为,而是为服务接受者服务目的达成尽心竭力。
2服务目的达成之促进义务
就合同当事人间的关系而言,即便是诚实信用与公平交易义务,仅为消极义务,而非积极义务,即仅要求当事人不得为损害他方之行为,而不要求积极增进他方利益(李宇,2016)。但服务合同并非以结果实现为终极目标,服务业者应基于對接受服务的合理期待,且因服务业者的职业能力,应尽力促成服务目的之达成,否则,难谓尽到忠实义务。其突出表现在对服务合同中不可抗力、免责事由的规定应对服务业者提出更高要求。按照职业标准能够被赋予合理期待的意外事件均不能免除服务业者的责任,如境外旅游合同中,旅行社发现游客存在可能被遣返之情势而未予提醒,主动向履行地签证机关举报,导致游客在入境环节被遣返,旅行社主张适用不可抗力要求免责,不应予以支持。
3服务信息披露义务
商品与服务交易在瑕疵担保的问题上存在着差异。出卖的物由生产者生产,出卖人获得之商品乃生产者生产之状态。围绕商品“应有性能”,出卖人只能立足于商品的现有状态,所负担者乃是商品合格证明和其他标识的验明义务、商品质量保持义务等⑧,而不是“应有性能”之促成义务。“我们不应当将‘应有性能理解为出卖人负有促成此种性能的义务,……‘应有在这里只是意味着,出卖人‘因偏离而负有责任或者‘应当对此负责人”(迪特尔,2007)。服务业者处于相当于商品生产者之地位,服务并非实体物,亦非特定物,不存在绝对相同的两次服务。“在服务交易过程中,需求方既无法在交易之前对服务商品质量进行检验,又很难在事后对其质量进行有效的评估”(汪德华等,2007)服务交易主体间存在较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代服务业领域更为突出,服务接受者无法从标准认知、他者经验等渠道获得关于服务的确定知识。服务业者的职业、专门化、团队特征,是服务接受者无法超越的优势。服务接受者无法通过其尽到足够的注意义务实现对服务的充分了解,必须有赖于服务业者的单方披露,不以服务接受者是否询问为前提。服务业者要针对其从事服务的内容、服务风险、服务准备等核心问题进行主动且充分的信息披露义务,该义务会对服务交易的效力、服务接受者权益维护、服务交易法律责任等产生影响。如医师之说明义务就是将合同拘束力回归至当事人真实意思过程的结果(刘勇,2009)。endprint
4服务过程尽到职业水平的义务
服务业自身通过资格准入制度、高度市场化等路径不断推进职业化进程,其中现代服务业更因技术特质而呈现出高度专门化水平,“由于现代服务业具有资本技术密集性、准入门槛高以及体验型经济等特征,决定了现代服务业对供给质量和供给有效性的要求并不弱于制造业”(邓智团,2016)。服务难以像商品能形成公认的社会客观标准,但在社会分工细化过程中应达成行业标准,服务业者能够按照职业标准完成服务成为服务接受者的合理期待。服务交易中其所属行业的职业标准、职业准则等理应构成判断服务业者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根据,具体包括服务接受者安全保障义务、注意事项提醒义务、服务目的实现的保障义务,超出合同约定但为专业人员应该采取的行为亦应纳入对服务业者的义务约束范围。服务业者应当达到的注意义务标准取决于相关行业或职业内一个相当称职的代表所具备的技能,并进一步取决于该行业普遍接受的(技术)标准和惯例(Christian von Bar and Eric Clive,2010)。职业标准在服务交易中至少应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对服务接受者的个性关注义务。“我国模仿型排浪式消费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生存型消费阶段‘一批一批消费者的时代开始成为历史,服务型消费阶段‘一个一个消费者的时代开始到来”(迟福林,2015)。服务接受者接受服务属个性化行为,如年长的游客应得到旅行社个别关注;医疗行为中要充分考虑患者的个性化差异等。专家服务中,“专家所提供的服务,以适应顾客的多样要求的‘非定型性为特征”(能见善久,1996)。金融服务中应遵循适合性原则,金融业者向客户销售或推介金融商品,应有合理基础相信该交易适合于投资人,对客户不为不适合的销售劝诱行为(熊进光,2013)。服务业者从事的相同类型的服务,应针对具体服务合同面临的情景,采取更有针对性而非基于经验的行为。二是服务相关资源的职业动员能力。消费服务中接受服务旨在满足身心需要,服务对接受者会产生波及性的影响,故服务业者是否很好履行义务并不能单纯在提供服务这一横断面上加以判别。服务业者必须对服务中可能对接受者产生的影响做职业性预判,并对必要的服务相关资源有合理的动员力,以避免因此给服务接受者造成损害。三是服务后续必要跟踪义务。应立足服务的特殊要求,基于对服务接受者更好享受服务考虑,对服务后续履行必要的跟踪义务,该义务并非是全部服务业均有的义务。
(三)服务合同解释的特殊性
《民法总则》第142条规定有相对人和无相对人意思表示的解释规则。因服务合同之特殊性,不加区分地适用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解释规则,在促进服务合同价值追求的实现上难谓有力。交易相对人,接受服务旨在寻求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状态改变,这种改变因人而异更具主观性,故交易目的会成为服务交易中法律的调整重点。该条第1款规定: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服务合同中双方当事人处于较高程度的信任状态,服务业者应为服务目的之实现尽力,法律的这一价值追求较多时候难以在合同所使用的词句上体现出来,故目的解释在其中应发挥主导性的作用。如实践中较为普遍存在的“穷人游”问题,应理解为在该特定旅游合同中服务业者并未追求盈利目的,暗含有赠予或者广告效应之目标,不能做出相反的判定。台湾地区民法亦作此解释,“旅游营业人提供旅游服务必须收受旅游费用,如提供旅游服务而不收受旅游费用者,除得解释为恩惠行为或无偿委任外,非民法本节之旅游契约”(林诚二,2007)。故旅行社若在旅游期间多次到购物点购物影响游客的旅游,应认定其存在违约行为。“卖方愿意与不特定的多数交易对方缔结这种亏本合同这种亏本是卖方自己自觉做出的商业决策。双方在缔结该合同时所能预见到的仅仅是已经亏损的履行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不应当多加干涉”(于韫珩,2016)。但在服务合同完全没有约定报酬的情况下,是否该做同一解释值得研究。律师所为他人实施代理行为,但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委托代理合同,在代理行为属有偿还是无偿问题发生争议时,我国二审法院判定为无偿代理(葛文,2005)。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在类似的示例中,则得出相反的结论,主张合同中没有约定价款的事实并不足以构成毋须支付价款的约定(克里斯蒂、埃里克,2014)。笔者赞同后一观点,服务业的商业模式乃具伦理约束的逐利模式,服务交易中期望服务业者作为商主体应无偿满足接受者服务需求的意见缺乏根据。
(四)违约责任中的精神损害赔偿
服务业者既是服务合同的当事人,又是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在服务业者与接受者之间形成違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倘仍受制于传统思维,必然导致若主张违约责任则无法获得精神损害赔偿之结果,解决这一问题的路径有二:一是重新审视民事责任竞合理论。对于医疗事故、旅游合同等要树立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模式,应承认当事人通过主张违约责任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张民、崔建远,2011)。鉴于服务合同所涉问题,有学者主张,坚持“请求权相互影响说”理解责任竞合较为妥当。其实质在于使两个请求权的构成要件、内容、效力形成一统,名为两个请求权,实为一个请求权(傅鼎生,2008;朱晓喆,2015)。二是突破民法传统理论上违约不能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以解决司法实践中制约服务接受者精神损害赔偿主张的关键因素。如在一运输合同中,法院认为,“本案是侵权与违约的竞合,原告选择违约之诉,而精神损害赔偿以侵权为前提,故对原告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请不予支持”(朱晓平,2017)。就各国(地区)立法及司法实践观察,服务合同领域承认精神损害赔偿已形成较为普遍的趋势。英国法中,在部分服务性合同中承认精神损害赔偿,即合同的标的是提供游乐、休闲以及精神安慰,如提供休闲度假服务、趣味旅游、婚照服务、新婚游乐、烦恼解除等。美国法中,“运送旅客合同、旅馆接待客人合同、运送遗体合同和传送噩耗合同。违反这些合同特别可能造成精神损害。在违反其他种类合同的情况下,如违约结果导致受害人一贫如洗或突然破产,也可能造成更为严重的精神损害,但是如果这种合同并未使精神损害成为一种特别可能的风险,这种精神损害不予支持”(姜作利,2001)。德国债法修订,承认基于合同之诉可以主张非财产损害赔偿。我国学者亦从不同角度阐述服务类合同违约应精神损害赔偿的合理性,有学者认为,“以增进精神利益为目的的合同,如婚庆合同、旅游合同等。……人身伤害时的精神损害是使受害人现存的精神利益减少,而这种精神损害则是未能使受害人的精神利益有所增加”(谢鸿飞,2014)。有学者认为,商业合同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非商业合同中适用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包括两类合同:一是与精神安宁紧密联系的合同,如运输合同、住宿合同、医疗合同、特殊保管合同等;二是关乎精神享受的合同,如旅游合同、观看演出合同、特殊服务合同等(尹志强,2014)。endprint
合同违约包括不履行和不完全履行两个主要形态,应注重从过程而不是结果的维度把握服务交易中违约的特殊性。“以医疗合同为典型的服务合同的期待利益具有典型的不确定性特征。鉴于医疗水平、手術风险、患者个人身体素质等诸多因素,几乎没有医生敢确保患者能够得到一定期待利益,更遑论医患双方对医疗结果的期待往往是不一致的”(于韫珩,2016)。单纯不履行的结果在服务交易中不能直接认定为服务业者违约,银行金融服务过程中发现储户可能被骗时的拒绝付款⑨;游客在登山游前突发病症,旅游公司应阻止其继续登山,并妥为照料;外科医生在开胸后发现癌细胞扩散而无手术必要等均属该情形。服务结果因服务接受者的个性化差异而有不同体现,故债务不适当履行的判断不能唯结果论,如医疗行为中病人个体差异会对相同医疗服务有不同的反映;教育服务会因受教育者的差异在服务结果上有明显不同。专家责任的非定型性使债务不履行的判断发生困难(朱晶,2006)。
注释:
① 20世纪80年以前我国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一直在55%以上;1982-1993年间恩格尔系数一直在50-55%间;1994年以来,恩格尔系数一直在50%以下,到2008年降低到37.9%。
② 旅游恩格尔系数=旅游支出金额÷消费中支付金额×100%。
③ 有学者主张:“必须抛弃传统的‘物必有体说,尽管有体物可能是民法之物的绝大部分,但不应再比照有体物的特性构建物的概念,即不能以有体物为主体建立物的定义,再将有体物之外的物依照明确列举或者视为物的方式勉强进入物的范畴。因此,在物的外延上,坚持‘有体物+无体物的体例,将两者都明确予以规定,且在物的概念之下处于彼此节分的状态。其次,必须明确物的内涵,即借助抽象物之共性的方式上,将其构成要素明确指出,使其成为判断是否为物的基本标准。在这一点上,必须坚持‘可支配性为物的本质属性,辅之以‘人体之外‘有用性的必要属性,构成物的内涵界定”。王毅纯.民法体系中“物”之概念的反思与重构[M]//梁慧星.民商法论丛(第59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182.
④ 如在托马斯诉考德威尔案中,埃利特法官认为,当一个鉴定人为了得到费用而就动产的价值向其主顾提出建议时,信托关系就建立起来了。王军.美国合同法判例选评[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171.
⑤ 参照Black?s Law Dictionary 626(1990);36A C.J.S.(1987).转引自谢哲胜.财产法专题研究(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81.
⑥ 参照Black?s Law Dictionary 625(1990).转引自谢哲胜.财产法专题研究(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81.
⑦ FISCHER J M.Understanding remedies.New York:Mattew Bender,2000,613.转引自黄爱学.论金融商品交易业者的说明义务[J].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73.
⑧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33条规定:销售者应当建立并执行进货验收制度,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其他标识。第34条规定:销售者应当采取措施,保持销售产品的质量。
⑨ 一个骗子在QQ上冒充胡女士在国外的儿子,称需10万元还债,心急母亲不辨真伪就要转账,银行工作人员不顾谩骂,反复劝说,提醒母亲与儿子确认,证实是一场骗局。黄女士收到短信,称自己被一知名电视栏目抽为幸运观众获得大奖,在银行转账缴费领奖时,被银行女职员善意提醒,最终骗局被戳穿。“银行人员劝阻受骗储户转账”, http://roll.sohu.com/20130523/n376831967.shtml。
参考文献:
[1] 张祖群. 从恩格尔系数到旅游恩格尔系数:述评与应用[J].中国软科学(增刊下),2011:110.
[2] 易信. 我国真实城镇化率的特征、成因及对策建议——国际比较视角[J].全球化,2016(11):87.
[3] 尚虎平,高玲玲.我国城镇化绩效评估:类型、方法与关键指标[J].行政论坛,2016(3):75-80.
[4] 陈卫民,施美程. 人口老龄化促进服务业发展的需求效应[J].人口研究,2014(5):4.
[5] 王可侠,彭玉婷. 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路径研究[J].江淮论坛,2017(5):43.
[6] 刘奕,夏杰长. 以服务业促进农业现代化:思路之辨与路径选择[J].宏观经济研究,2014(5):16.
[7] 夏杰长,倪红福. 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服务业还是工业[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6(3):46-47.
[8] 杨玉英,郭丽岩. 对我国服务业发展现状的再认识[J].宏观经济研究,2009(4):38.
[9] 莫顿·J·霍维茨. 美国法的变迁1780-1860[M].谢鸿飞,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383-384.
[10][日]近江幸治. 民法讲义Ⅰ 民法总则(第6版补订)[M].渠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4.
[11]董瑞华,傅尔基. 经济学说方法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278-283.
[12]夏小雄. 社会变迁和体系因应:合同法的理念更新和结构调整——以意大利合同法制为例[M]//梁慧星.民商法论丛(第50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486.
[13]迟福林.“十三五”推进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转型[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2):15-17.endprint
[14]刘伟,冯涛. 要素再配置效应对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研究[J].经济学家,2014(12):71.
[15]克里斯蒂安·冯·巴尔,埃里克·克莱夫. 欧洲私法的原则、定义与示范规则: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全译本)[M].于庆生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340-346.
[16]江小涓. 服務业增长:真实含义、多重影响和发展趋势[J].经济研究,2011(4):5.
[17]王利明. 合同法研究(第一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354.
[18][俄]E.A.苏哈诺夫. 俄罗斯民法(第四卷)[M].付荣,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1280-1281.
[19][德]汉斯·布洛克斯,沃尔夫·迪特里希·瓦尔克. 德国民法总论(第33版)[M].张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63,370-371.
[20]姜铸,李宁. 服务创新、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J].科研管理,2015(5):30.
[21]谢鸿飞. 合同法学的新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32.
[22]梁慧星. 从近代民法到现代民法——20世纪民法回顾[M]//民商法论丛(第7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234.
[23][日]大村敦志. 民法总论[M].江溯,张立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33.
[24]陈自强. 日本债权法改正新动向[M]//债权法之现代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15-216.
[25]傅俊伟. 欧盟民法典草案之述评[M]//民商法论丛(第43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475.
[26]刘春堂. 民法债编各论(上)[M].三民书局有限公司,2010:3.
[27]谢哲胜. 财产法专题研究(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94-95.
[28][日]近江幸治. 民法讲义Ⅰ民法总则(第6版补订)[M].渠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39.
[29]周江洪. 服务合同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8-21.
[30]汪德华,张再金,白重恩. 政府规模、法治水平与服务业发展[J].经济研究,2007(6):54.
[31]李宇. 国际合同法最新发展:比较法视野下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新修正[M]//民商法论丛(第60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439-440.
[32]叶林,黄爱学. 论商业银行理财业务中的信息披露义务[J].法治论坛,2010(3):114.
[33][德]迪特尔·梅迪库斯. 德国债法分论[M].杜景林,卢谌,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37.
[34]刘勇. 论医疗合同中的医师说明义务[J].南京社会科学,2009(7):128.
[35]邓智团. 网络权变、产业升级与城市转型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下上海传统产业的创新实践[J].城市经济,2016(23):5.
[36]Christian von Bar and Eric Clive. Principles, Definitions and Model Rules of European Private Law:Draft Common Frame of Reference[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1650.
[37][日]能见善久. 论专家的民事责任——其理论框架的建议[M]//民商法论丛(第5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506.
[38]熊进光. 论金融商品销售的适合性原则——美、日金融商品销售行为规范的经验与启示[J].甘肃社会科学,2013(3):164.
[39]林诚二. 民法债编各论(中)[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14.
[40]于韫珩. 信赖利益在违约损害赔偿中的适用:以亏本合同为例[M]//民商法论丛(第60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58-62.
[41]葛文. 授权书与律师代理费——对上诉人某银行与被上诉人某律师事务所诉讼代理合同纠纷的评析[M]//民商法论丛(第32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42]张民,崔建远. 责任竞合的“收”与“放”——我国《合同法》第122条规定的解释与适用[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1(5):150.
[43]傅鼎生. 赔偿责任竞合研究[J].政治与法律,2008(11):77.
[44]朱晓喆. 瑕疵担保、加害给付与请求权竞合[J].中外法学,2015(5):1144.
[45]朱晓平. 违约责任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研究[J].法律适用,2017(11):49-50.
[46]姜作利. 美国合同法中的精神损害赔偿探析[J].法学论坛,2001(6):39.
[47]谢鸿飞. 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理论的再构成[J].环球法律评论,2014(6):17.
[48]尹志强. 论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正当性及适用范围[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4(6):118-121.
[49]朱晶. 论专家责任的性质[J].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6(5):68.
Abstract:The service industry leading industry mode marks the entry of society into the pursuit of quality of life. Civil law should respond to it through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so as to realize the institutional solution of major contradictions of the new era put forward in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rvice trading connects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link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new problem of how to adjust the coexistence of business behavior and civil behavior. Service recipients have serious trading dependence on service providers, and the service industry should adhere to the business mode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commodity trading, that is to pursue the profit under the ethical constraints contained in the service industry. The service contract should be famous in the compilation of civil code. The key is to maintain service acceptors′trust in the service transaction by providing a legislative form of service providers′ obligation.
Key words:carry out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spirit; service trade; business model;service contract
(责任编辑:李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