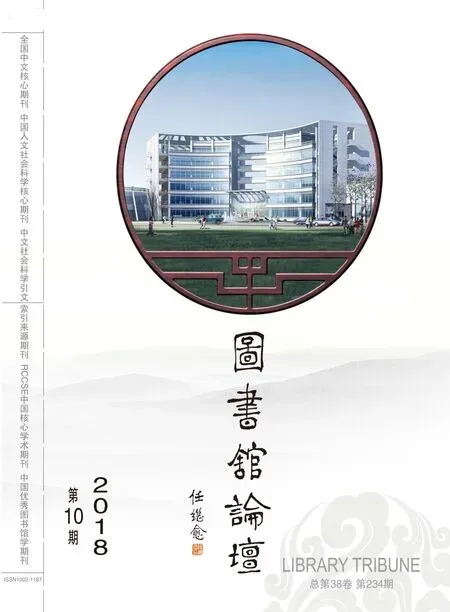阅读遴选视域的中外文学及相关问题思考
——对2017年大学图书借阅榜的解读
由《文摘报》微信公众号2018年4月18日汇聚的“北大、清华等17所名校图书借阅榜”广受关注,这份源自各高校图书馆发布的本校2017年阅读报告的借阅榜①,其关注视野极大限度地超越了图书馆界。比如,登上这份榜单的图书,其搜狗百科的内容介绍一夜间添加了一条信息:“2018年4月,XX(书名)排名XX大学借阅榜第X位。”[1]这说明图书馆的阅读数据蕴含极高的文化信息价值,有待挖掘和利用。从这份借阅榜可以读出不少引人兴味的信息。本文仅就其中文学阅读取向背后的信息略谈三点:网络文学已成主流;日本文学倍受青睐;大学教育的失败。
1 网络文学已成主流
1.1 网络文学明显占优
这份高校图书借阅榜涉及的学校并非都是名校,包括了湖南工业大学、广东财经大学等普通院校。其实,学校的多样性更能反映中国高校的阅读实况。就这17所高校的图书借阅榜来看,有14所高校排在榜首的借阅书目是文学作品。其中,浙江大学、天津科技大学、东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四所高校排名榜首的是传统纸本小说《平凡的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广东财经大学等三所高校排名榜首的是网络小说《盗墓笔记》;中山大学、山东大学等两所高校排名榜首的是网络小说《明朝那些事儿》;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两所高校排名榜首的是法国19世纪小说《基督山伯爵》;武汉大学、湖南工业大学、河南大学等三所学校排在榜首的分别是《神雕侠侣》和日本的《嫌疑人X的献身》《源氏物语》。如果在这些小说中剔除外国文学,那么,源自传统纸本的《平凡的世界》《神雕侠侣》,以及源自网络文学的《盗墓笔记》《明朝那些事儿》均五次荣登榜首,看起来传统纸本文学与网络文学打了个平手。但若加入时间维度,网络文学明显占了上风。传统纸本小说,无论是《平凡的世界》,还是《神雕侠侣》,均是20世纪的中国文学创作;新世纪的文学,在这个借阅榜中属于网络文学的天下。如果将这个榜单的视野再放开一些来看,北京大学排行前十的图书,只有一本是小说——网络小说《明朝那些事儿》。中山大学排行前三的《明朝那些事儿》《盗墓笔记》《藏地密码》都是网络小说。山东大学排名前三的《明朝那些事儿》《藏地密码》《你好,旧时光》也是网络小说。就17所高校借阅榜全部书目中文学作品的总频次来看,《平凡的世界》出现11次,排名第一;《明朝那些事儿》出现9次,排名第二;《盗墓笔记》出现8次,排名第三;《藏地密码》(也是源自网络小说)出现7次,排名第四……在总频次上,网络文学也是明显占优的。
虽然如今各类阅读排行榜可谓多矣,但大学图书馆的借阅排行榜不存在商业利益动机暗藏的猫腻,而且高校毕竟是文化高地,部分大学生毕竟更能代表中国文学的未来。所以,其信息对判断中国文学发展状况的意义不可低估。
行文至此,需要就网络文学的界定补说几句。关于网络文学,有一种十分宽泛的定义,泛指一切在网络上传播的文学。如此宽泛的理解,在媒介文体学上没有意义。本文认可北京大学中文系邵燕君的观点:网络文学“专指在网络上生产的文学”[2]。从网络上生产出来之后,经过网络阅读的汰选,优胜者再出纸本,是网络文学经典化的一种方式。故源自网络文学的纸本,应该属于网络文学范畴。
1.2 文学汰选机制的博弈
很难将21世纪传统纸本文学在大学图书馆借阅榜上败下阵来的原因归结为艺术质量的优胜劣汰。这其中关键的因素,可能还是在两种文学汰选机制的博弈中,网络文学成了赢家。
一般来说,随着信息量的剧增,信息汰选变得尤其重要。在如今这个信息空前大爆炸的时代,网络文学比之于传统纸本文学,拥有更具优势的汰选机制。就纸本长篇小说的产量而言,1919-1949年我国出版的原创长篇小说不过400余部,而今一年生产纸本原创长篇小说在4000部以上,生产网络原创长篇小说在15万部左右[3]。无论是传统纸本文学还是网络文学,其汰选机制都必须以阅读为基础。但是,传统纸本文学是一种“个人化”的从“密室写作”到“密室阅读”的方式,“密室阅读”的封闭性使其能见度主要体现在文学批评文本上。因而,传统纸本文学汰选机制主要依赖专业文学批评家的评论及这种评论对读者的影响。在纸本文学时代,常见的情形是一拨作家的出道常常伴随着一拨批评家的出场,比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经典化与刘再复、何西来等批评家的业绩关联;再如,莫言、马原、余华等先锋作家的经典化与季红真、吴亮、陈晓明等批评家的成就关联。但是,当一年产生4000余部纸本长篇小说的时候,批评家们有限的阅读能力必然使传统纸本文学的汰选机制陷入挂一漏万、盲人摸象的尴尬。而网络文学的汰选机制是建立在互动阅读的开放可见基础上的,并以量大、速高、累进式计量来显示人气指数,它可将每年15万部长篇小说进行以人海阅读为基础的年复一年的累进式人气指数排序。因此,网络文学汰选机制与传统纸本文学汰选机制的PK就演变成为大数据与专家眼光的PK。如果说,在数据偏小的情况下,专家眼光胜出是大概率,那么在数据如此庞大且日益庞大的情况下,大数据就显出它的优越性。虽然可以忧心忡忡地质疑这种“数字人文”之审美趣味,以及这种审美趣味对社会文学鉴赏力的平面化牵引,对文学生态多样性的破坏,但无以抗衡它对作品的巨大举荐能力。
1.3 媒介变革的文学迭代经验
谈及网络文学,通常会因其门槛过低而导致规模庞大、质量堪忧、品位低俗,让人低看一等。其实人类史上哪一次媒介革命,如果以习惯的旧媒介标尺度量,不都是一次内容的下坠与堕落?从龟甲楔刻神谕到纸代简帛之私人书信的涌现,其文字内容由神圣之言走向家长里短、儿女情长是下坠与堕落;机印术开启通俗小说大行其道当然也是下坠与堕落。
机印术发明之后,诞生了世界文学史上第一部伟大的长篇小说《堂吉诃德》。通常认为,塞万提斯的这部小说意在嘲讽当时风行的骑士小说,这当然是不错的。但这部小说并未就此止步,而是将当时骑士小说的风行与机械印刷兴起关联起来,认为正是欧洲机械印刷的兴起使得以赢利为目的的书籍生产成为可能,才导致胡编滥造的骑士小说的涌现。这一内容写于该书“第六十二章 通灵头像以及其他不可忽略的琐事”[4]。可惜的是,后来关于《堂吉诃德》的阐释虽然层出不穷,高见迭出,却恰恰忽略了塞万提斯特别提示的这一章所“不可忽略的琐事”(即机械印刷革命导致内容生产的下坠与堕落)。有意味的是,《堂吉诃德》不仅同样是当时机印术的产物,而且在它出版后近200年的时间内都被归属于情节随意且漏洞不少的地摊逗笑读物。对其评价越来越高是200年以后(即18世纪以后)的事。直到19世纪,评论家才认识到,“在欧洲所有一切著名文学作品中,把严肃和滑稽,悲剧性和喜剧性,生活中的琐屑和庸俗与伟大和美丽如此水乳交融……这样的范例仅见于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5]。因此,在对待网络文学的态度上,需要具有将今天的阅读观察放进历史视野的能力,否则,不能鉴往知来而超越流俗观念。
2 日本文学倍受青睐
2.1 日本文学占半壁江山
这份图书借阅榜显示的是各高校图书馆借阅排名前十的书目。在这些书目中,外国文学总计29种38频次,而日本文学就占据了14种17频次。其他国家的排序是:法国5种7频次(《基督山伯爵》《小王子》各出现2次,《悲惨世界》《偷影子的人》《羊脂球》各出现1次);英国5种5频次(《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案》《一九八四》《呼啸山庄》各出现1次);美国2种5频次(《冰与火之歌》出现4次,《银河帝国》1次);阿富汗1种2频次(《追风筝的人》);哥伦比亚的《百年孤独》、挪威的《苏菲的世界》各出现1次。
在14种17频次的日本文学书目中,出现最多的是东野圭吾的小说,计有《嫌疑人X的献身》《白夜行》《十一字杀人》《分身》《变身》《白马山杀人事件》等6种9频次;其次是连续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却未能获奖的感伤作家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且听风吟》3种各上榜1频次;其余上榜1频次的作品是安倍夜郎的《深夜食堂》、美嘉的《恋空》,以及《青山七惠小说集》《日本精彩推理小说选》。在当代作家之外,还有一部公元11世纪的古典名著《源氏物语》。
这份书单阅读总频次排名前三的国家中,进入中国大学生眼帘的作品,无论是排名第二的法国文学,还是排名第三的英国文学,主要都是过去时代的经典之作。当然,法国有一部当代畅销书《偷影子的人》进入了借阅榜。阅读总频次与英国并列排名第三的美国文学则几乎都是当代作品。之所以说“几乎”,是因为阿西莫夫的《银河帝国》属于1950年代的创作,而拥有4频次的乔治·马丁的系列长篇《冰与火之歌》的创作一直延续至今。日本文学14种17频次中,当代作品占据13种16频次。由此可读到这样的信息:外国当代文学对中国青年形成的影响,首当其冲是日本,其次是美国,法国再次,英国则属于辉煌往昔的余辉,而曾经在1950年代对中国构成绝对影响力的俄罗斯文学已经从中国青年的阅读偏好中远去。
2.2 东野圭吾的中国读者
东野圭吾是当代日本推理小说的头牌。世界推理小说重镇原在英美,自1960年代开始移向日本。东野圭吾作品于2008年引进中国之初,其版税是每部万元人民币,到2012年蹿升至每部百万元人民币。截至2017年,其作品在中国发行106部,发行量超过800万册。有报道说:“打开北京开卷统计的畅销书排行榜,没有哪位作家能够撼动东野圭吾的位置,比如从2017年以来,他的三部作品长时间连续霸占虚构类排行榜,没有什么值得怀疑东野圭吾在中国读者心目中的位置。”[6]从2017年高校图书借阅榜看,东野圭吾的阅读热潮还带来了国人对推理小说的热情。第一代推理小说头牌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第二代推理小说的头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案》也都上榜;东野圭吾是第三代。
为什么中国会迎来这么一波以东野圭吾为旗的推理小说热浪?有调查从微观层面显示,它可能与中国1999年引进日本动画《名侦探柯南》有关。在该动画引进的随后数年里,在中国排名前50的动漫作品中这部动画位列前二。当年浸润于该动画的少年儿童十年或十几年后成长为今天热捧推理小说的读者。所以,热衷东野圭吾的读者91%是18-30岁的青年人[7]。
从更宏观的层面看,中国工业化社会的进程日益偏向于工科理性思维,其对校园文化和社会文化的塑造与推理小说注重严谨理性和精湛的逻辑推理以揭示案情迷题的过程相契合。这或许是理工科出身的东野圭吾及其推理小说广受欢迎的社会文化基础,更何况中国民间一向崇尚孔明、吴用神机妙算的智慧之光,并拥有源远流长的公案小说传统。
2.3 浮物之下的流动
中国近代以来所遭遇的创痛,虽然并非全部来自日本,却以日本最多最巨,因此中国人对日本人积怨深厚。2012年钓鱼岛事件以来,无论是主流媒体中有关中日外交、军事的报道,还是网吧微信的民间八卦传播,都令历史积怨找到了火山口,以至于爱国与不爱国在许多国人眼里直接与是否反日甚至抵制日货简单地划上等号。在这样的情绪氛围之中,高校的阅读以及它所反映的当前中国的阅读文化却呈现出一角烂漫樱花,着实令人寻味。这是否意味着,相比于文化之潜沉,社会层面的恩怨以及由钓鱼岛事件激起的政治外交事件及民众情绪可能更像是浩浩汤汤历史长河之上飘荡聚散的浮物。在这浮物之下,一衣带水的邻居间千百年来最热烈的文化学习有其不受一时一事干扰的定力。日本民众曾经是中国文化最热烈的学习者,正是这种学习令日本最完整地保存了中华古代文化的某些精髓部分,比如服饰、建筑、书法、围棋和禅宗。近代以来,日本作为东亚现代史上的先发国家又成为中国学习欧美现代文化的中介,以至现代汉语中社会和人文学科方面的名词、术语,70%来自日本人对西方相应语词的翻译。最近20多年,从日本动漫到村上春树,再到东野圭吾,一定程度地伴随国人从少年到青年一代的文化成长。郭敬明们以《幻城》为代表的奇幻文学的风靡与日本动漫及受此动漫文化浸润成长的一代人有着内在的联系,而翻开中国80后的青春文学,村上春树小说那种以修辞的华丽支撑作品的感情、人物、逻辑,那种都市时尚色彩的意味,尤其是那种忧伤、孤独、无奈的情绪,俯拾即是。东野圭吾是动漫、村上春树之后又一波日本流行文化在中国的涌流。这涌动澎湃而起于2012年,竟然与钓鱼岛事件爆发的年份重合!钓鱼岛事件之后中日关系的持续紧张显然并未构成对东野圭吾在中国人气的打压。
而中国当代文学,如果在异国成为畅销书,也多半是在日本。比如,1960年代中国与日本的邦交尚未正常化,杨沫的《青春之歌》就曾是风靡日本的畅销书;新世纪莫言摘取诺贝尔文学奖桂冠之前,在日本早已成为“中国的马尔克斯”[8]。
3 学校教育的失败
3.1 令人沮丧的信息失控
这份图书借阅榜呈现的高校阅读遴选视域中的中外文学,从教育的立场看,则着实令人沮丧。如果说信息并非知识,知识是基于特定认知与理解目的而组织起来的信息,那么这种“组织化”首先体现为对信息的滤选。通过滤选而纳入一定的结构系统,才可能建构成知识。北美媒介生态学者尼尔·波斯曼将信息的知识化建构看成是对泛滥信息的限制和控制,学校则是对泛滥的信息实施有效限制和控制的最重要机构。一个有趣的故事是,印刷机的出现给聪明的学生通过自主阅读而超越老师掌握的知识提供了机会,以至于15世纪有一位历史纲要的作者发问:“既然年轻人可以依靠勤奋读书学到同样的知识,为什么还要老师呢?”[9]这个历史学者的发问包含这样的意思,即印刷机的发明使学校变成多余。但事实刚好相反,在1480年由印刷机引发信息爆炸之前,英格兰只有区区34所学校,至1660年学校总数达444所,平均每12平方英里就有一所学校。在尼尔·波斯曼看来,现代学校的大规模诞生与发展,实乃对印刷机所带来的信息泛滥的必要回应。“课程设置的发明就是逻辑的第一步,目的是对信息源头进行组织、限制和区分。……它们使一些信息流动合法化,另一些信息流动声誉扫地。”[10]就中国高校对中国文学信息进行的组织、限制和区分来说,网络文学就处于声誉不佳之列,它虽然来势浩荡,却基本上未能在大学的文学课程、教材以及推荐参考书目中占据合法性地位。它在高校图书馆的借阅书榜上获得如此亮眼的频次会令许多资深的人文学教授感到羞愧。同样,在我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体系中,亚洲文学是被边缘化的,印度文学与日本文学常常点到即止,其教学重点是欧美文学和俄罗斯文学。但在这份借阅榜单上,日本文学几乎占据外国文学的半壁江山,俄罗斯文学竟未露面。
这份图书借阅榜所呈现的文学河山与我国高校文学教学导向大相径庭,它意味着学校教育的信息失控,一定程度反映了我国学校教育的失败。
3.2 如何应对新的阅读文化
如上所述,现代学校教育诞生于对印刷机所造就的泛滥信息环境的回应。而声光影像、数字传媒、“互联网+”所造就的数字化文明已远非印刷文明的信息环境可望项背,它使信息生产与传播的形式、数量、速度、可获得性以及信息的偏好等都发生了深刻改变。这些深刻改变重塑了社会话语结构,重组了文化知识和其价值秩序——传统的金字塔形的结构和等级已经趋于扁平化、平等性。比如,在今天,荷马的《伊利亚特》、但丁的《神曲》、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曹雪芹的《红楼梦》、乔治·马丁的《冰与火之歌》、东野圭吾的《嫌疑人X的献身》、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当年明月的《明朝的那些事儿》都进入了“读秀学术搜索”之类的数据库。在这类数据库中,读者可从诸如题名、作者、主题、关键词、引文、文本片段、时间等多种路径直达自己所需要的文本及文本局部。尤其是在搜索凸显的文本局部面前,任何著作,无论是曾经显赫的经典抑或是地位卑微的消遣读物,它们之间的阅读价值鸿沟都接近消失。阅读价值只与读者特定的甚至是临时的需求相关,唯有读者个人化的需求才是至高无上的。数据库是这样,互联网的各种搜索引擎也是这样。信息技术与互联网就这样塑造了去文化等级化的、以个人化需求为价值标尺的阅读文化。
新的阅读文化必然包括阅读味蕾的改变。曾经“只是看不厌”[11]的《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如今赫然排入“死活读不下去的书”排行榜的前十位②。它意味着新的阅读文化已经将经典边缘化。老师劝说学子阅读经典的理由大多是:经典属于经过漫长时间过滤后剩下的精华,是经过了人类历史上最智慧的人所挑选,或者说它有千百年来最智慧头脑的背书,知识含金量高,因此阅读经典的投入产出比高。但是,既然已经“死活读不下去”,其投入产出比显然会走向反面。
其实,道理(观念)总是片面的。如果唯经典是瞻而厚古薄今,就意味着生在塞万提斯的时代你会错过《唐吉坷德》,因为它从地摊读物达到经典标准需要至少两百年的时间。同样,生在罗贯中时代的你会错过《三国》《水浒》,生在曹雪芹时代的你会错过《红楼梦》,生在鲁迅时代的你会错过《呐喊》《彷徨》,这难道不也是一种阅读的大不幸?从年龄代际的特征来说,年轻人更倾向在好奇的意义上阅读,易于厚今薄古;上年岁的人更倾向在回味的意义上阅读,易于厚古薄今。因此,信息的知识化与学校对信息的限制与等级化区分,实际上也是一种代际文化话语权的博弈。
传统社会的文化话语权掌控在长者手中,因其文化价值迭代的周期相对漫长。孔子时代以30年为一“世”③,唐代李世民做了皇帝,为避讳,“世”以“代”替,仍然是30年。民间俗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说的正是这样一个世代周期。但现代信息社会的“互联网(以及移动互联网)+”时代,世代周期明显缩短。其重要表征即人文书籍的文献半衰期缩短,因而厚今薄古的阅读取向压倒厚古薄今的阅读取向。
面对如此新时代和如此新阅读文化,学校基于印刷文明的一套信息组织、限制和区分之管控体制应该如何变革自身来回应这巨变的时代?学校教育的信息失控,将此问题凸显出来。
注释
①参见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科技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广东财经大学、湖南工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东南大学以及河南大学等图书馆发布的2017年阅读报告。《文摘报》微信公众号(2017-04-18)对这些阅读报告的图书借阅榜的汇聚,其链接地址为https://mp.weixin.qq.com/s/i69bhjv0JvcQ6wEAI OJWZA.
②“死活读不下去排行榜”是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3年6月通过对近3000名读者吐槽最多的“读不下去”的书进行统计后发布的排行榜。榜单前十名依序是《红楼梦》《百年孤独》《三国演义》《追忆似水年华》《瓦尔登湖》《水浒传》《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西游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尤利西斯》。
③《说文解字》卷三之卅部曰:“三十年为一世。从卅而曳长之。亦取其声也。”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孔子说:“如有一位王者兴起,也必三十年时间,才能使仁道行于天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