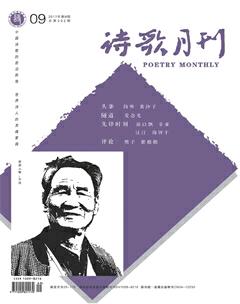黄沙子的诗
黄沙子

渡船
用作渡船的是一艘水泥做成的船
它的好处是不必担心腐烂
乘坐渡船的人其实可以绕远路
从河流的浅处涉水
但我们忙着赶往对岸
忘记了沉重的肉身可能会
加剧水泥的下降速度
如果一艘船提供的浮力
与它承受的压力不相称会怎样?
易于腐烂的事物可能飞得更高
正如跑调的嗓音唱出更人声的歌曲
我们旁若无人地谈起
过去很久的事并且赞美它们
直到憎恨的光深入骨髓
谁也不知道一艘船到底要
载走多少人过河才会坍塌
渡河的人中谁会成为受害者
成为那最后的一个
也许一群人走亲戚回来
会满足深水对于灾难的渴求
这样一艘水泥的渡船
波涛也只能让它轻微晃动
在我们到达对岸之前
它已经抵消了一部分向上的力
相遇
为什么快乐时孩子们走在前面
危险时他们又被藏在身后
有时候我们在路边等候
即使一大群人聚集在一起
也像是孤单一人在等
我们不知道开花的
到底是珙桐还是鸽子树
同一种植物拥有不同的名字
如同你站在这里
另一个你却已远行
回来的人才会被精确命名
但多半情况下是有人告诉你
回来只是一种可能
所以我们总在等,一个人在等
一会儿像个孩子跑到前面
一会儿躲在人群背后,像外表坚强
内心却无比敏感的病人
没有谁知道前后跑动的两个人
在什么时候相遇
对于“未知”的事物
“已知”其实是毫无所知的孩子
有用之物
从一片低洼地里
我们把腐烂的棺木拖出来
里面还有一些骨殖被泥土和水
侵蚀得几乎无法认清
但有人记得那是我们的
一个前辈,仔细论起来
其实相隔并不算太远
坚硬的头盖骨现在只需要
轻轻一捻就变成细末
因为潮湿它们发出沉闷的呲呲声
我们起出了所有看起来
是埋下而非本来就在这里的事物
一连几天田野上到处
都是做着同样事情的人
越来越多的雨水落在平原
让原本高昂的地势显得有些低沉
还算结实的棺木被挖出来后
有很多其他的用途
比如铺在水井边,河滩上
让打水的人不至于陷进淤泥中
祖父六十岁以后再也没有下田耕作
但他记得哪一块土地里
埋着哪一个人因而在他的指引下
我们准确地找到很多有用之物
断指重植
我的右手小指上
有一个长长的伤痕
绕着指骨几乎形成圆环
它让整根手指看起来像断后重植
这是很多年前一把锋利的镰刀
割开它之后留下的印迹
那时候二姑妈刚出嫁不久
看着满手鲜血的侄儿失声恸哭
但我丝毫没有感觉到疼痛
反而暗中庆幸不已
之前这把镰刀
刚刚将小学校操场上的
高大榆树环切掉一圈树皮
我想验证的说法是
如果有了一个圆满的伤痕
这棵树会不会因此死去
医生将我的伤口缝合起来
敷上药膏后用纱布紧紧捆扎
整个手变粗了像一只白色的棒槌
几天后那棵榆树的枝叶开始枯萎
在完全死去前人们锯断了它
成为一根与木柴为伍的树
传说平原之外的地区有很多山
十五岁以前我从来没有亲眼见到过
现在我已居住在群山之中
再也没有离开
鸵鸟
最近有个朋友给我留言
他得了结核病,好几个月来
反复洗肺,胸透
大把吃消炎药
越是凉夜越是咳嗽得厉害
所以他回乡下去了
辞职手续正在办理之中
他告诉我,那里空气很好
人也少
生活简单像一只鸵鸟
过了好些天我才有空去看他
我们什么也没有说
一起走在田埂上
透过薄雾眺望远处的灯光
头顶密集的星星散发出湿土的味道
而从他的呼吸中
我能感觉到寂静所带来的
蓬勃的力量
我见过最快的流水
大雨过后,武漢变得热起来
平日里用来锻炼的步道
被涨起来的江水淹没
有人开玩笑说那是上游漂过来的人
在代替我们走路,然而快多了
浑浊而永不回头并非那么容易做到
如果这些年,我不曾离开水上的生活
会不会有一天终究要收起木桨
放下船帆,听任流水将我
带到它所能到达的任何地方
在我还能睁开眼看这个世界时
会不会有熟悉的白鹳
或许到了大海之上,海鸥将代替它们飞翔
我见过最快的流水
不过是雨滴从天而降
我见过的最快的死亡
不过是一觉醒来,亲人不知去向
真的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
江水裹挟着一切,将岸越推越广
旧房子
很多次动念,要将花湖的房子卖掉
再到武汉找一个也同样有芦苇
有飞鸟的湖边重新购置一套别墅。
但是想想那么多的旧家具
别人不一定喜欢,我也舍不得丢弃。
栽在门前的合欢树和栾树
几年时间就长到三楼那么高,
它们一个在夏天开白花
一个在秋天挂起满树的红色果实。
我曾经绕着花湖走了很远
最终因无路可走而停下脚步。
没有人可以理解,为什么我要
蒲公英一般被风吹到哪里都可以生根。
我只在花湖住过短短两年
得到过细雨中的安静睡眠。
躲避
记得一个人穿的衣服但记不得那个人
记得一场人雨,但记不得雨停。
记得人雨一直下着,以至于湖水上升,村庄陷落
飞在空中的鸟变成水而划船的渔民。
什么时候我拥有了开始
但忘了结束,像一个老人看着电视
在故事进入高潮時入睡,在广告声中惊醒。
为了躲避烈日我紧跟一团乌云,这些年
为了活得长久些我不惜离开家到处旅行
有些事物是永恒的,但拥有它们的
是一些转瞬即逝的人。
红花继木
进入中年,开始变得容易忘事
刚栽下的树,浇了很多的水用来定根
长了多年的树,我也害怕它耐不得干旱
因而一并浇个透湿
栾树的细枝落满庭院
铺在地上像是拆散的鸟巢
可是鸟儿们去哪里了?电话一整天没响
老是担心信号中断,在这少有人来的
花马湖边只有远处的山
在水中留下倒影,多么宁静,我已经忘了
那些伴随着热血剧烈吹拂的风是怎样
将一个男孩变成父亲
在红花继木被剪断的枝叶上
一只蚂蚁正抱着另外一只蚂蚁
仿佛不这样就不足以抵挡
从高处降落地面时的震动
拉幕
今天的风好大,扎了好几天的竹篱笆
又被推倒在地,我是不是应该
准备几根粗一点的铁管
在铁管上写下几个大字,告诉
所有试图进入我的领地的人
你们不受欢迎,陌生人,你们
应该和我一直分开
舞台上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的箱子
它不可打开,从不言语,却永恒地
充当着道具,我本该像孩子一样
将探索这个箱子当做终生职业
因而在米粒上跑马,在露水中
游泳,我想做一个医生
只允许神经错乱、对世界有妄想的患者
进来,如同拉幕人正在合上
本该拉开的大幕
洪水
我反复向你描述过那一场洪水:
房子,稻谷,活着的人被带到别处。
只有一群鸟先是飞走,然后回到这里;
一些草,先是变老,然后又被暴晒,
枯得不成样子。看不见的都已
不存在,我躲在树上,只能是树的儿子。
脚下流水欢快而浑浊,积聚了
一个家所能拥有的全部器具。
一个神龛丢失了一扇门,里而也没有神,
一头牛和一只狗抱在一起,抱得很紧,
要是它们的主人看到,一定会大感惊奇。
雨还在下,收割还在继续,我看到
一个女人抱着木头从我身边过去,
尽管她知道割下的谷物还会发芽,
那么多的树叶,拖着蚂蚁在跑。
站着打盹
我想告诉你并不是只有苍耳随着你走了
有一只苍耳还留在枝头等着老去
我们围在餐桌旁但盘子是空的
爱你的人不知道还要多久才会来
也许她爱你饿着肚子抽烟的样子
像沙滩上搁浅的帆船等着月亮升起
越来越胆小的一生早已提前规划路径
夜深人静时提着灯笼穿过深深的草丛
你走后有人犹在寻找可能的生活
有人犹在谈论老虎隐身的山顶
最恬美的睡眠莫过于站着打盹
最赏心悦目的事莫过于活着但依然会死
下山的人忙着回去收集干草
下山的人走着走着就飞起来了
像是中年以后一切已被洞悉
我的黄雀儿啊并不在柞树林里繁殖
但迁徙途中也会短暂歇息
它们夜晚给沉睡的姑娘唱歌
白天在城市北面的草地上觅食
中年以后我总是被各种各样的歌声打动
大风吹得树叶沙沙作响也是其中一种
有时候我能看见牛群甩着尾巴
给越来越老的一生做上整齐的标记
下山的人忙着回去收集干草
有人说走到这里就行了
我的一生在一块大石边停下
我要的一切就在此地
上天允许人们展示分享的能力
除了麻雀和喜鹊
我能叫出名字的鸟儿不多
有一种鸟儿在田埂下筑巢
有人走过时就惊慌地叫着飞起
我总是看到它们偷食稻谷
但父亲对此不以为意
他相信上天赐予我们粮食
也允许我们展示分享的能力
有一种体形修长的褐色鸟
善于在大雨来临之前飞向高处
那时所有虫豸都在低空挣扎
我们也早已回到家中
醒着的人可以倒下即睡
十二点一过,新的一天就开始了
狗躺在翻过来的地毯上
睡得酣畅连磨牙也忘得一千二净
爪子还紧紧地按着骨头仿佛
食物的贫乏从未让它停下脚步
但最有效的搜寻是在梦中
四周安静得能够听见狗的鼻息
白天它在碎石上弄伤了自己
向前奔跑又遭遇其他生物的袭击
看起来从地底开出来的道路
尚未与地面的人接上头
秋天开放的花时刻准备着凋谢
醒着的人可以倒下即睡
无需计较一切是否已经结束
走失
没有人知道牛去哪里了
在河边可以看到它的足迹
河对岸是翻滚的稻浪
牛不会为了吃它们而游过去
人群分成两拨
一拨划船顺水而下
一拨沿着河道往上游的树林
所有人在清晨的阳光中默不作声
我们无法呼喊一个没有名字的生物
事实上平原一眼就可以看到很远
即使隔着树林也可以听见牛吃草的声音
那一天我们到了南垸湖
寻找走失的牛变得像是去探望亲戚
没有人担心它再也不回来
不管往哪个方向
安静的河水总会让我们相遇
现在它只负责提供寂静
栾树茂盛的树叶形成浓荫
整个田野只有这里是清凉的
一只伯劳全然没有在意闯入者
轻巧而熟稔地钻到我们头顶
漫长的旅行后,值得回忆的并不多
栾树俯视着新燕河
河水被青草包裹着消失在远处
所有能够被我们听到的声音中
蜜蜂的嗡嗡声是最令人愉快的一种
——让人联想到美好的事物
勤勉与预言,阳光与花朵
我们知道栾树一定见过很多次
但现在它只负责提供寂静
告别
终我一生可能都无法理解
为何有些事物越长越大,像树
有些人却越长越小,像我的祖母
她很瘦,很轻,分明是小鸟的骨肉
我慢慢地摸索她的脸
最后停在她的头发上,只有头发还是
那么坚硬,粗壮,带着灰白的颜色
我将她的手指一根一根分开
长久地抚摸指掌上的茧
几十年来她从未停止过耕作
房前屋后的菜地里还有成片的
菜蔬等着一个弯下腰的人
我不知道此刻是不是一天里
最寒冷的时刻,我拥抱她,因饥饿
而发抖的双腿跪在地上
总有一人我也会像她一样
仅仅为了安歇而永恒地躺在黑暗之中
地底的事物依然擁有催生一切的能力
要恢复一块菜地的生产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我提着
锄头走到菜地边时,我仿佛看见
祖母正蹲在那里给雨后的
辣椒苗绑上树枝,我知道她是要
给它们找一个支撑以免植物
贴着地而生长,最终烂在土里
她曾无数次经营这块菜地
在播种和收获中度过漫长的一生
我也曾无数次地设想该有多少
虫子在泥土中使劲,将那些种子
顶出芽和茎梗,又顶出绿色的叶子和
可食用的果实,我从不相信
仅仅靠阳光和雨水它们就可以长大
祖母去世后,我将荒废的菜地
清理干净,祈祷那深埋在
地底的事物依然拥有催生一切的能力
万籁俱寂
最明亮的不是星光而是
你躺下的地方的香火
此刻曾台村是寂静的
细雨将人事驱赶一空后又悄然离去
我独自漫步在看望你的路上
夜色中突然传来布谷鸟的叫声
——人世有多艰难
它的呼喊就有多孤单
我知道死去不过是一转眼的事情
活着却要经过一片又一片树林
我知道有人已先我而来
那先我而去的
分明是告别的红叶在落下树枝前
最后一次伸展腰肢
我也要向你做一次告别
在黑暗中接受光明的指引
从死去的人身上抽出线头
大雨整夜整夜地下,我却没有醒来
如果不是一个孩子在哭
我可能永远也不会醒
雨水和阳光落下来是同一个声音
无论白天或黑夜,我已学会不去分辨它们
死亡和出生混为一团
没有谁能够改变它们的顺序
从死去的人身上抽出线头吧
即便它正努力穿过针眼
我能看到的只是一个孩子哭着挥舞手臂
像是要从这浑浊的世界
划出一条清亮的河流
尽管母亲已给了他容忍的权利
席卷而去
如果有什么是我不能接受的
那只能是沉睡了一整天后
听见窗外柳树上的蝉鸣
我看不见它是如何死死地
抱着满是皱纹的树皮
在这毫不在乎黑暗降临的傍晚
一个人,再也没有谁来陪伴他了
隔壁是空的,所有活着的
都像是被做过的梦席卷而去
但愿我还能找到一朵开着的花
俯下身,狠命地嗅上几把
黑夜已降临了不止两次
黑夜已降临了不止两次
河的两岸都是亮着灯的房子
我们留宿的客栈山坡上
一座孤单的坟墓插满香火
像死去的人依然睁着眼睛
山坡下雨水将石板路冲洗干净
我们在窗前等着雨停
在陌生人到来之前
等着黑夜再一次降临
但仿佛是因为我们过于沉默
客栈老板关上了大门,他以为
今天不会有人投宿而我们已经离去
宁静是另外一回事
我在犹豫
在柯尔山居住的这些天
我们像是被遗忘了
柯尔山只是一个低矮、毫不险峻的圆形丘陵
但仍有一些事情是我们
从来未曾享受过的
山坡上的罗勒草和迷迭香并非本地植物
有人种下它们后不知去向,看起来
记忆除非形成文字,否则会消失
在柯尔山,快乐是一件大事
宁静是另外一回事
雨水把低洼的地方变成沼泽
树林又把薄雾变成白云
当探险的人试图在黑暗中辨别方向
每次我们都以失败告终
我在犹豫是否有这样一个结局
尽管多半时候只是沉默地坐在一起
我们也将为此付出努力
细小绿色的鳞羽
在柯尔山,我的房子最小
但三个人各有自己的天地
也许羊群并不喜欢这片牧场
因为看不到一点人世的痕迹
雉鸡在山坡上散步
白云中还有古老的珊瑚朴
令人瞩目的是那些灌木
它们生来矮小却活在高处
天空在月亮出来后变得遥远
星星多得让人感觉不到丝毫寒冷
但我们知道随时都有可能下雪
因此我不停地补着屋顶
生命不长也不短
所知不多也足够应付
在柯尔山的每一天都灿烂无比
我们看到了茁壮茂盛之美
也看到它们细小绿色的鳞羽
飞来飞去的黄蜂
在它飞走之后,说它的嗡嗡声
如何巨人显然有些夸张
营地附近最主要的树
是身材矮小的小叶榆杨
这些树外形匀称,有时候沙沙作响
但远不及一只黄蜂,它瞬间完成的
短途旅行让我们看到了柯尔山受到祝福的剖面
我们已在此度过两夜
面前的任何一些枯叶,一些甜风
都高过我们的希望与经验
我们甚至在黄蜂飞过的时候停止了赞叹
好长一段时间后我们才能从
黄蜂翅膀所造成的轻微震动和它不断的嗡嗡声中
转过身来,我看到妻子那疲惫
苍白、幸福的脸
樱桃
一小篮樱桃中,被放进去一根带着
叶子的茎
显然其中的一枚
曾经从上面出生,开花,结果,慢慢长大
現在,那枚樱桃被混进大约70枚
差不多红
差不多大小的樱桃中
有时候
它顺着风摇晃,有时候又
藏在母亲宽大的衣襟下
它抓着母亲的手臂以至于
母亲也不得不微笑着低下头
它还会唱歌,歌声柔美
但相当低沉
和我的想象相反,它有力的翅膀
噗噗地振动着,像一只穿过血管的鹌鹑
它一定就在附近,像一个
从没有离开过家的孩子
摘棉花
一个小人儿在棉花地里像个穷光蛋,除了棉花,那么白。
他慢慢走动,穿行于近似理想的缝隙。
要是偶尔发现一只燕子,向南飞,往低处靠近,
棉花会吞噬他的呼喊。
他不知道母亲在左边还是右边。淮也没见过这么温暖的风。
这么多的白都成熟了,唯一一个小人儿失散了家人。
沉默
阳光在二月
消除了世间事物的所有阴影。
我和张博九并排走着,望着远远离去的冬天和
湖边惊飞的白鹭若有所思。
张博九长大后,我们在一起散步的机会
变得越来越少。
偶尔他和我说起在实验室解剖兔子
分割开的肢体的每一个部分
都摆放得整整齐齐
只有心脏还会急促跳动一会儿。
有时候是兔子,有时候是鱼
和老鼠,这些都是
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家伙。
更多的时候
我们沉默着
我希望此刻他是在考虑
对于生活这个躲在幕后的老家伙
从哪里动手更为适宜。
仲夏夜
我们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
像一群松鼠紧紧抱着过冬的食物
此刻北方的云团离得还远
仲夏的风还没长大成人
只有明月提早升起
挂在离我们很近的天空
还有一个晚收工的农民
正在清扫禾场上散落的谷粒
我们等着他将我们叫醒
他可能是我们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