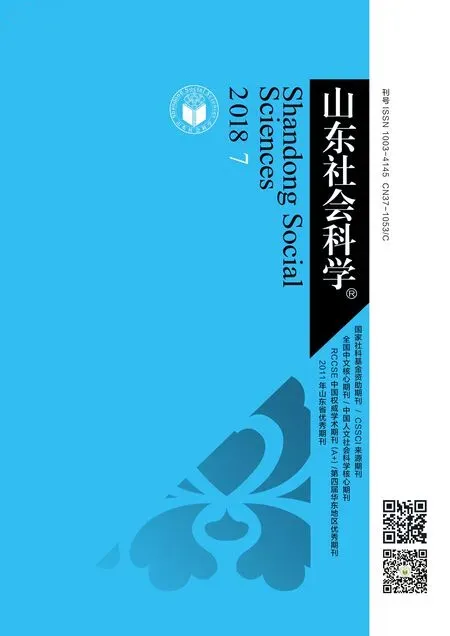工厂关系的计划化、社会化和世界化
——意大利自主论马克思主义“工厂社会”思想的三个发展环节
张早林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23)
当代意大利自主论马克思主义理论(Italian Autonomist Marxism)家奈格里(Antonio Negri)因与美国学者哈特(Michael Hardt)共著《帝国》一书而声名鹊起,其与哈特共同提出的帝国统治时代来临的思想与全球控制社会的概念引人注目。在追寻他的理论缘起时,我们不得不回溯到意大利自主论马克思主义的早期时代。在那个时代,一群意大利自主论马克思主义者(时称意大利工人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重读《资本论》及其手稿,提出很多独特的看法,其中“工厂社会”思想尤为重要。它不但从资本的直接生产的“工厂关系”出发,阐述资本统治具体的展开机制,还将资本主义的危机归结为工人主体的自主抵抗所致。前者暗含了当代规训社会与控制社会的理论萌芽,后者则潜在地指向了当代西方流行的生命政治理论话语。因而,揭示“工厂社会”理论逻辑的具体表现和历史演进就显得非常重要。当然,早期意大利自主论马克思主义学派除了奈格里外,潘齐尔里(Raniero Panzieri)和特龙蒂(Mario Tronti)是另外两个代表人物,他们三位相继从不同路径发展了“工厂社会”思想。面对“工厂社会”思想,潘齐尔里、特龙蒂和奈格里相继前进,先后提出“资本专制计划”、“工厂社会”和“社会工厂”等概念,从而在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图景中展现了意大利自主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通过对“工厂社会”思想的梳理,我们不仅能够认识到早期意大利自主论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资本统治的工厂机制这一侧重点,理解其指向“规训社会”、“控制社会”、“帝国统治”诸概念的逻辑必然性,而且,我们也能意识到《资本论》中所潜含着的“生命政治”思想。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在他们经验化马克思的生产关系后,他们只能提出激进的工人主体自主拒绝式的解放图景了。
一、潘齐尔里:计划专制的“工厂社会”
意大利自主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意大利工人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Italian Workerist Marxism)。意大利工人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派是由一群在意大利共产党之外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反对苏联模式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秉持工人自主抵抗资本剥削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原则,积极参与现实的工厂斗争和社会斗争,并为之提供理论指导。在这种现实的抗争和理论的探求中,逐渐形成了三个核心人物:60年代初期的潘齐尔里、60年代中后期的特龙蒂和70年代以后的奈格里。这批左翼知识分子在重读《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过程中,探讨了资本主义的专制扩张和工厂社会的形成,提出工人抵抗资本的优先性和资本主义新危机观,以此来指导意大利工人的抗争运动。
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意大利中左联合政府尝试以“凯恩斯主义计划(Keynesian planning)”解决国内问题。在这种形势下,以潘齐尔里为代表的意大利左翼知识分子把批判目标定在“作为计划者的国家(State-as-Planner)”身上,其分析的焦点是“群众工人(the mass worker)”抵抗性特征问题。当时,潘齐尔里面对的是意大利共产党和工会组织所信奉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在他看来这一理论具有两大局限性。首先,这一理论的核心是“生产本位主义”,即“深信‘生产力逐渐发展’和人类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动力,相信道路只是暂时受到‘市场无政府状态’的阻碍,并且因为资本主义的另一特征,即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正,而变得曲折”*[法]雅克·比岱、厄斯塔什·库维拉基斯主编:《当代马克思辞典》,许国艳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38页。。因此,这种“生产本位主义”不仅没有去强烈质疑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反而认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把生产力当做中立性的,而不是内含资本关系性质的,其必然结论是把生产力的发展当做当然的历史解放的前提,认为只要推动生产力发展,人类解放就能自动到来,从而陷入了“技术-田园式的观念”中。其二,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认定资本主义永远处于“市场无政府状态”之中,认为这种“市场无政府状态”必然造成与生产力发展不可解决的矛盾,进而发生革命,生成共产主义社会。潘齐尔里认为,恰恰是这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意大利共产党要求工人与资本家妥协而不是反抗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因为这种理论观点强调了历史发展的客观性而忽视了历史主体的反抗性,因而不能指导意大利工人运动。
为了从理论上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上述两种观点,为工人反抗斗争提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支持,潘齐尔里重新解读了《资本论》,重点从资本直接生产的工厂层面,去反驳生产本位主义,去拓展资本的专制计划性和工人的反抗性。
在潘齐尔里看来,正统马克思主义中缺乏工厂分析概念,这导致它对资本关系中的生产力非中立性质和计划性认识不足。潘齐尔里首先从《资本论》中引出资本直接生产领域——工厂,指出工厂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实现形式,是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为资本服务的最主要形式。他写到:“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通过它的不同历史阶段而展现为一种劳动分工( division of labour)的发展历程,这个过程的基本地点是工厂:‘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一个产物,就是物质生产过程的智力作为他人的财产和统治工人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这个分离过程在简单协作中开始,在工场手工业中得到发展,在大工业中完成。在简单协作中,资本家在单个工人面前代表社会劳动体的统一和意志,工场手工业使工人畸形发展,变成局部工人,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科学为资本服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18页。”*Raniero Panzieri,“The Capitalist Use of Machinery: Marx Versus the Objectivists”,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http://libcom.org/library/capalist-use-machinery-raniero-panzieri.在这里,潘齐尔里从马克思的论断出发,把工厂定位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空间组织形式,把大工业的生产力定位为资本的生产力。如此明显的生产力的资本属性,为何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眼中呈现为中立性呢?
潘齐尔里指出,因为他们坚持了一种技术—组织形式的客观主义视角,所以不幸信奉了资产阶级宣传的生产力中性论观点。在他看来,工厂生产组织技术的合理性发展表现出一种异常强大的技术“宿命论”作用,具有将人从有限性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人在强大的技术面前屈服了,认同技术自身的纯粹发展,并以一种技术—田园式的观念制造出人们所有的矛盾和问题都可随着技术的发展而得到解决的完美前景。不仅如此,正统马克思主义还由此产生了一种不同于马克思本质主义的矛盾观,即伴随着对直接生产组织过程对就业者的活劳动吮吸感知的消失,对新的生产组织形式所要求的技能水平的强调出现了。管理、功能、技术等从社会关系中被孤立出来,并集中为一种客观化的系统,就业者与这个系统之间的矛盾变成了个人素质与系统要求之间不匹配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新的工人范畴(如技术员、生产性的知识分子)的出现。而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将此看成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因此,“在这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the clash between productive forces and relations of production)表现为一种技术上的‘非-一致性(non-correspondence)’”*Raniero Panzieri,“The Capitalist Use of Machinery: Marx Versus the Objectivists”,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http://libcom.org/library/capalist-use-machinery-raniero-panzieri.这种技术矛盾观必然指向工人要适应生产组织的要求,而不是去反对生产组织处于其中的资本关系。这从反面强化了资本生产力的力量,而非工人的力量。由此,潘齐尔里批判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客观主义视角,批判他们的生产力中立论的错误。
在重构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潘齐尔里重点指出了资本主义工厂生产的专制计划性本质和这种专制计划性所具有的扩张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的趋势。他从《资本论》的“协作”章出发,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协作是根本的形式,而协作就是一种生产的计划,计划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然要求。于是,他下了一个结论,即资本与计划是天生融合的,并能从直接的生产工厂扩展到整个社会生产层面,具有总体社会的计划性,以此反驳市场无计划观点。他说:“协作对于劳动力的社会生产力发展而言是基础。因而,在资本主义形式中的协作是价值(剩余价值)规律的首要的和基础的表达。……从协作开始,资本就指挥控制了一个已计划好的劳动过程了。计划在直接生产的层面上并不直接地表现为与资本运行模式的矛盾,而是直接地表现为一种资本发展的必要性外观。因此,在计划和资本之间不存在任何不相容性,对于其在协作形式中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来说,资本同时表现为这个过程的根本而特有的性质,即计划性。”*Raniero Panzieri, “Surplus Value and Planning:Notes on the Reading of Capital”, translated by Julian Bees, The Labour Process and Class Strategies, No. 1, 1976.由此,潘齐尔里得出一个结论:计划是资本内在的性质。
既然如此,进一步而言,资本工厂中的计划是否具有向整个社会扩展的趋势呢?在他看来,计划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资本家应对无秩序和工人反抗的一种方法,具有从工厂扩展到整个社会范围的趋势。潘齐尔里在“凯恩斯计划国家”的政策中就指出了这种现实表现。他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指出了这一点:“实际上,马克思的分析是倾向于表明,在生产性过程日趋迈向更高水平的形势下——从简单协作到手工业到大规模工业——资本如何利用计划以强化与扩大它对劳动力的控制,并获取一种实现劳动力更高水平的通道的。进一步说,马克思分析的目的显示在工厂中,一种发展着的资本主义计划的使用是资本对个体资本的无秩序运动和冲突的消极效应的反应,而这种个体资本的无秩序和冲突是在流通领域和强制实行对劳动力的广泛剥削的法定界限中发生的。”*Raniero Panzieri, “Surplus Value and Planning:Notes on the Reading of Capital”, translated by Julian Bees, The Labour Process and Class Strategies, No. 1,1976.为解决这种消极效应,资本的计划功能就从直接工厂层次扩展到整个社会范围。因此,“资本主义越发展,生产组织就会越来越扩展成为整个社会组织”*[法]雅克·比岱、厄斯塔什·库维拉基斯主编:《当代马克思辞典》,许国艳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43页。。而这恰恰意味着工厂计划逻辑的社会扩展,表现为新的资本主义在经济发展方面的计划性增强上。于是,一种扩展性的“工厂计划性社会”观点就出现了。
资本主义生产计划性总是与专制合理性相连。在潘齐尔里看来,资本家在工厂中大肆采用机器生产,并进行有效的组织,因此这是一种计划,是一种“专制合理性(despotic rationality)”。他认为资本主义无限制地普遍性地使用大机器,造成对工人劳动力的最大程度的剥削,造成工人最大程度的屈服。资本因使用机器而使剩余价值的获取具有无限性。那么资本主义发展的界限在哪里?不可能在直接生产过程的连续运动中,而只能在这种生产过程的断裂处。这种断裂不可能来自资本家,必然来自于工人阶级的反抗,是工人阶级的反抗造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界限。潘齐尔里说:“在直接生产的层面上,马克思基于一种生产力的无限发展而把资本主义看成了计划:在这里,我们发现了那种资本主义生产的对抗性质的根本性的表达。那‘内在的矛盾’并不在于个体资本的运动,即它们不是内在于资本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唯一界限不是资本自身,而是工人阶级的抵抗。计划的原理——它对资本家来说意味着‘预测’、‘结果的确定性’,等等——只是作为一种强制工人的‘无法抵抗的自然规律’。在工厂体制中,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方面只是存在于工人阶级的不服从上,存在于工人阶级对‘专制合理性’的拒绝上。”*Raniero Panzieri, “Surplus Value and Planning:Notes on the Reading of Capital”, translated by Julian Bees, The Labour Process and Class Strategies, No. 1,1976.从而,工人阶级反抗资本生产关系的主体性危机理论出现,这揭开了意大利工人主义的“社会危机”理论的序幕。
潘齐尔里通过对工厂生产的一系列分析,论证了他关于资本生产力非中立性和资本生产具有计划性的观点,在西方战后普遍贯彻“凯恩斯主义”的资本主义阶段,他的“工厂计划性社会”思想得到了验证和支持。在此论断之上,他强调了工人阶级在工厂这个直接生产环节的反抗战略。
二、特龙蒂:工厂关系化的“工厂社会”
20世纪的60、70年代,法国左派理论家们聚焦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同样,意大利“工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关注这个领域。不过,这群意大利学者关注的不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宏观和细微统治机制问题,而是资本在实现增殖的再生产过程中的那种计划性和控制性问题。此一时期,西方国家社会服务业日益发展,“后工业化”进程开启,面对这一现象,特龙蒂提出了“工厂社会”概念。
如果说潘齐尔里已经指出了资本的计划从工厂扩张到整个社会的历史现实,只不过他的“计划”侧重于社会中的总资本生产的总体计划上。特龙蒂则发挥了马克思相对剩余价值理论与吸纳理论,结合“第三产业”的兴起,把潘齐尔里的“工厂计划性社会”思想通过变形推进到资本实现增殖过程中来,指出资本在增殖过程中具有把整个社会以至于国家都吸纳进来的趋势,从而正式提出“工厂社会”的概念。
特龙蒂从《资本论》出发,明确地指出资本统治确立后所具有的强大的把一切社会因素都卷入资本增殖过程中的客观趋势。特龙蒂在分析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后深刻指出:“千真万确,在劳动过程中资本因为控制了劳动、劳动力的劳动因而控制了工人并得到发展;恰恰在增殖过程中发展了一种强制的关系,这种强制关系迫使工人阶级去进行剩余劳动,并从剩余劳动中产生剩余价值。资本能够以它自己的方式占有内含增殖过程的统一的劳动过程,并且以越来越广泛的方式占有它们;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越能抓住所有其他社会方面,侵入整个社会关系网络。”*Mario Tronti, ”Factoty and Society”, translated by Guio Jacinto, Operai e Capitale, Roma: DeriveApprodi srl, 2006, p.35.这里,特龙蒂指出了资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强制工人生产出剩余价值,而这种直接生产过程越来越越出工厂的高墙而扩展到整个社会领域,同资本实现剩余价值的流通过程一道使整个社会领域都变成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
但这个趋势是如何发生的呢?特龙蒂认为,恰恰是资本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导致了工厂的社会化趋势,这种趋势表现为生产与流通的一体化,表现为工厂的社会化与社会的工厂化,在其最高阶段,社会和国家亦化为资本生产的一个环节。特龙蒂特别地指出这一点:“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有机地连在一起。相对剩余价值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所有内在变迁有机地连在一起,一方面,是在劳动过程与增殖过程,劳动条件的变革与对劳动力的剥削,技术和社会过程之间明确而日益复杂的统一;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专制。资本主义发展越进步,即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渗透和扩张得越厉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就必然性地越加闭合。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和资产阶级社会之间的关系,工厂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达到了一种程度越来越高的有机的联系。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水平上,社会关系被变革为生产关系的一个环节,整个社会被变成一个生产的关节,就是说整个社会作为一种工厂的职能而存在着,而工厂则把它的专制统治扩张到整个社会。”*Mario Tronti, ”Factoty and Society”, translated by Guio Jacinto, Operai e Capitale, Roma: Derive Approdi srl, 2006, pp.47-48.在这里,社会成为了工厂,资本工厂的专制扩展为社会工厂的专制,特龙蒂的“工厂社会”思想出现了。并且他还进一步指出工厂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当工厂抓住了整个社会——所有的社会生产变成了工业生产——那工厂的特性就在社会的一般性中消失了。当整个社会被简化为工厂时,工厂——就像这样——似乎消失了。”*Mario Tronti, ”Factoty and Society”, translated by Guio Jacinto, Operai e Capitale, Roma: DeriveApprodi srl, 2006, p.49.于是,“工厂体制表现为决定性的社会关系”*Mario Tronti, ”Factoty and Society”, translated by Guio Jacinto, Operai e Capitale, Roma: Derive Approdi srl, 2006, p.49.。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变成了一个总体上的“工厂社会”,在这种没有有形厂房的社会中,具体的工厂消失不见了,工厂的强制关系却遍布各处。也因此,所有处于这个社会中的劳动者,都必然被纳入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工厂的生产体系之中,成为一名雇佣工人,从而被控制和剥削。
面对着20世纪60年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的“后工业社会”进程,特龙蒂就以其工厂社会理论解释解释这种变化趋势,特龙蒂把这一发展趋势称为“第三产业化”,他说:“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最高水平暗示着全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最为深刻的神秘化。真实的无产阶级化过程的日益加深,把自身表现为第三产业的形式化过程(formal process of tertiarization)。”*Mario Tronti, ”Factoty and Society”, translated by Guio Jacinto, Operai e Capitale, Roma: Derive Approdi srl, 2006, p.49.以此证实了资本生产关系的现实扩张性和后来的奈格里的“社会工人”的出现。
但是,在特龙蒂看来,如果资本仅仅把社会关系变成资本生产关系的一个环节,把整个社会变成工厂社会时,它还没有达到资本生产统治的最彻底性,因为国家的政治领域仍然可以处在资本生产关系之外,从而对资本生产施加自己的强大影响。但这种国家的外在性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国家没有中立性的位置,它必然要为资本服务,并承担起维护资本生产顺利进行的职能。特龙蒂就指出了资本生产关系也一定会把国家变为资本自身的一个部分。他说:“正是立足于这个基础之上,政治国家的机器倾向于越来越与总体资本家的形象保持一致;它越来越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性并因此成为资本主义的功能。资本主义社会一体化的构成过程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定发展所强制实施的,它不再容忍存在这样一个政治领域,即这个政治领域形式上独立于社会关系网络。”*Mario Tronti, ”Factoty and Society”, translated by Guio Jacinto, Operai e Capitale, Roma: Derive Approdi srl, 2006, p.48.这样,资本生产关系也必然把国家纳入了自己的体系之中。
面对工厂、社会和国家的一体化现实,特龙蒂总结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的社会关系、政治关系都从属于资本的工厂生产关系,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为生产而生产的社会,生产是目的,其他都是它的中介工具。所以,“在此意义上,在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社会关系从来不与生产关系相分离;生产关系更加被等同于工厂的社会关系;工厂的社会关系每一时刻都要求一个更大的和直接的政治满足(内涵)。因此,资本主义发展自身倾向于把整个政治关系从属于社会关系,把整个社会关系从属于生产关系,把整个生产关系从属于工厂的关系。”*Mario Tronti, ”Factoty and Society”, translated by Guio Jacinto, Operai e Capitale, Roma: Derive Approdi srl, 2006, pp.50-51.在这里,我们看到特龙蒂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角度得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即资本的工厂关系统领了整个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不存在任何外在于资本工厂关系之外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一切权力都是工厂经济权力的变体,任何非资本权力都将消失。在这里,特龙蒂明确了资本工厂关系权力的绝对统治性,同时也明确地批判了所谓国家和市民社会是对立关系以及国家中立性的观点。
特龙蒂并没有就此止步,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后来福柯所探讨的微观权力关系对人的灵魂的奴役性问题,从而把资本的专制从外在机构性效应深入到了工人劳动者的内在意识观念领域,涉及到了劳动者生成自愿服从心理的权力关系机制。他写到:“只是把这些人约束在自愿地出卖他们的劳动力上也是不够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要前进到这个程度上,即在那里发展出一种工人阶级,通过教育、传统和习惯把那种生产方式的需要看作明显的自然规律。生产过程的组织克服了所有的抵抗……;这种经济关系的无声强制把工人密封在资本主义对他们的统治之中。确确实实的是额外的经济权力直接地并异常地持续地被使用。”*Mario Tronti, ”Factoty and Society”, translated by Guio Jacinto, Operai e Capitale, Roma: Derive Approdi srl, 2006, p.48.通过这些论述,特龙蒂揭示了外在权力的专制统治效应对工人心理的塑造问题,我们也看到了与福柯微观权力话语殊途同归式的结论。
在工厂社会中,工人阶级如何解放?秉承潘齐尔里主体反抗的危机话语,特龙蒂提出了“拒绝工作”的策略。在他看来,只有在工人主体的反抗中资本主义社会才能构成危机状态,产生出解放的可能性。同时,反抗只能发生在直接的生产领域才能有效,在分配的社会流通领域中反抗是无效的。因为直接的生产领域和分配的社会领域在资本循环运动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工厂是直接把工人活劳动并入剩余价值的领域,贯彻的是剥削原则,而社会作为实现剩余价值的流通领域,遵循的是平等交换的市场价值原则。相应地,工人在这两个领域中面对资本运动时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前一场合工人可以直接施加反对资本的行动,而后一场合工人则只能顺应这种市场原则。因此,工人对资本的反抗只能产生于工厂生产领域之中,只有“拒绝工作”,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危机,1960年代意大利出现了以“拒绝工作”为口号的工人造反运动。
至此,特龙蒂从资本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角度论述了工厂生产关系的扩张,论述了“拒绝工作”的战略。但是这种工厂社会关系的逻辑还不完整,还必须补充资本流通过程才能完整地阐明工厂社会的思想。特龙蒂的工厂社会还局限在民族国家范围之内,当它后来扩张到整个民族国家之间甚至地球空间的时候,就需要新的理论加以阐述了。这成为了奈格里的任务。
三、奈格里:流通扩张中的“社会工厂”
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来,随着世界资本主义“滞胀”危机的出现,凯恩斯经济学和“计划—国家”遭遇危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出现,危机—国家来临。同样,意大利经济也发生困难,其经济政策出现巨大转型,生产形式开始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转变,社会开始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第三产业发展起来。整个社会成为大工厂,社会群体身份变得繁杂,有分散化的社会化的工人、学生、妇女、移民、有色人种以及边缘群体等。各种社会运动也此起彼伏。由于工人斗争遭到意大利政府的镇压,工厂工人运动衰落了。相应地斗争主体从以工厂工人为主转向了以社会群体为主,斗争形式从工厂委员会的自主斗争转向社会群体的自主运动。在60年代中前期,意大利工厂斗争是基本形式,形成“工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形势的发展推动着理论的前进,原有的狭义工厂扩张到整个社会甚至整个世界,反抗主体变成了社会主体,斗争策略也需改变。“工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亟需向前发展。
奈格里担负起分析社会最新变迁的任务。他提出“危机—国家(crisis-state)”与“社会化工人(socialized worker)”的概念,以此分析资本主义新的统治策略与生产技术构成,分析此种统治策略和技术构成之上的新劳动阶级构成及其自主解放策略,一种新自主论马克思主义出现了。为此,奈格里深入阅读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按意大利自主论马克思主义学者习惯简称《大纲》),以期从中得出不同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自主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在对《大纲》的解读中,奈格里不仅建构出了劳动与资本对立同时优先于资本的本体论的政治历史观,还发现了在资本流通过程中资本的不断扩展趋势,从而把“工厂社会”概念推进到“社会工厂”概念的程度。
我们看到,在解读《大纲》的过程中,奈格里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与利润理论连在一起。他认为剩余价值规律直接的就是剥削规律。剥削就是对剩余劳动量的最大程度的无偿占有。而这种占有只能在流通中实现。于是,剩余价值规律社会化就表现为利润规律,利润是剩余价值平均化,这样利润范畴出现。如果说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生产领域的剥削理论,那么“利润理论应被看作流通中的剥削理论,被看作社会剥削的理论”*Antonio Negri,Marx Beyond Marx,Translated by Harry Cleaver ,Michael Ryan and Maurizio Viano,London:Pluto Press,1991,p.82.。这样,柰格里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就从生产领域转向社会流通领域。相应地,其寻求革命主体的意图也从生产领域前进到整个社会领域。这就意味着不仅生产工人是被剥削者,而且社会上诸群体也都是被剥削者,于是社会工人阶级概念在理论上的出现成为可能。
奈格里认为,资本在流通过程中不断将新的社会条件纳入资本之中,具有将整个社会、国家甚至世界变为资本社会的能力。他特别看重马克思关于资本流通过程中所产生的紧缩时间和空间趋势的精彩论述,“流通时间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限制=必要劳动时间的增加=剩余劳动时间的减少=剩余价值的减少=资本价值自行增殖过程的障碍或限制。因此,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8页。。在马克思眼中,资本生产过程是一个总体运行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从生产出发经过一系列资本的具体表现形态又复归生产,从而完成增殖。而流通过程是实现剩余价值的过程,这个过程时间越短,资本的周转越快,资本积累越多。因此,资本总是力图缩短时间。但是流通过程总是在空间中进行,它一方面是扩大空间,另一方面又是要缩小空间。其解决矛盾的方式是以时间消灭空间,以缩短时间,尽可能凭借最快的循环速度扩大资本的增殖的量和积累的量。但奈格里在这里却把重点放在了资本统治范围的扩张上了。在他看来,资本在生产领域中把社会条件设置为资本所要面对的一方,即还有没有被资本纳入的生产条件因素的存在,而在流通领域则消除了两者的对峙,资本统一了社会条件,把社会条件变成自身,出现了资本的社会。奈格里说:“这样一种双重性和分离(指剩余价值理论中资本与社会条件的对峙状态——笔者注)不再存在了。资本建构了社会,资本完完全全是社会资本。流通产生了资本的社会化。”*Antonio Negri, Marx Beyond Marx, translated by Harry Cleaver, Michael Ryan and Maurizio Viano, London:Pluto Press, 1991, p.114.社会资本范畴出现。这个范畴和社会劳动范畴一样具有质的飞跃性。奈格里强调指出了社会资本的作用,“它是资本范畴的质的飞跃,使社会向我们展现为资本的社会(capital’s society)。通过这一过渡,全部社会条件被资本所吸纳了,也就是说,它们成为资本的‘有机构成’。除了社会条件——它们在它们的直接性里表现自己——之外,资本还野心勃勃地吸纳其流通过程中所有的要素和物质,由此,所有涉及生产过程中的一切在这里就构成了那从手工业到大工业再到社会工厂的过渡的基础(the foundation for the passage from manufacture to big industry to social factory)”*Antonio Negri, Marx Beyond Marx, translated by Harry Cleaver, Michael Ryan and Maurizio Viano, London:Pluto Press, 1991, p.114.。流通使资本变成了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使整个社会被纳入到资本实现价值增殖的过程之中,资本由狭小的工厂渐渐扩张到整个社会范围的一切领域,资本的专制原则也一同统治了社会,社会成为了“社会工厂”。这是特龙蒂工厂社会概念在流通过程中的发展。
不仅如此,奈格里还认为资本扩张与国家之间具有强烈的对应关系,资本力图使国家成为资本的国家,资本每一最新发展的特殊要求都要使国家认可、赞同和维护,其根本途径就是把资本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法律的意志,并以法律条文规定下来,从而资本借助于国家的权力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资本权力、国家权力、法律权力和各种制度权力融为一体。市民社会在经济生产领域和政治国家领域之间的中介地位慢慢萎缩了,它融进了国家的统治权力之中。国家成为资本的国家。奈格里在总结马克思关于美国这个由最新型的资本家阶级所建立的国家的特征时就解读出上述论断。他认为,马克思运用的第一条原理涉及到一个资产阶级社会(如美国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趋势,即美国资产阶级社会自主地发展起来,超越了此前一个世纪的运动的各种界限。在这里,“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对立仅仅表现为隐约不明的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并且国家是市民社会的直接综合,因为资本直接就是社会资本,其他因素都被资本化了。奈格里认为马克思能够运用的第二条原理是建立在资本集中和国家集权之间的一种对应性上。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和集中化决定了——无论像美国这样一种开放社会,还是像欧洲大陆那样的一种封闭社会——国家权力的一种持续扩张和集权化的必要性。这一过程直接由生产与流通之间的对抗所导致,而这种对抗产生于资本主义的集中化。结果是“国家成了‘经济和谐’的最后避难所,而它最初被斥之为这些和谐的唯一的破坏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第三条原理是资本的深化原理,是必然性的,“是在世界市场的层面上的矛盾和对抗的原理,而这是随着那国家的形象变成了(中介的或直接的)资本集中化”*Antonio Negri, Marx Beyond Marx, translated by Harry Cleaver, Michael Ryan and Maurizio Viano, London:Pluto Press,1991,p.53.。从奈格里的总结中我们看到,资本对立扩张有三大原理:第一,资本从工厂扩张到社会;第二,资本从社会扩张到国家;第三,资本从国家扩张到世界。相应地,资本专制关系也一起扩张起来,扩张到社会、到国家、到世界。
这样,奈格里在解读《大纲》中,从资本流通过程出发,指出了资本不断吸纳社会条件而不断扩张的趋势,从而将社会、国家和世界变为资本关系中的社会、国家和世界。意大利工人主义的直接生产领域的工厂资本专制关系就这样扩展到整个社会领域了,国家也不能幸免,资本的世界市场也必将到来。社会工厂形成了。
如果进一步看,当资本主义扩张到整个世界的时候,世界市场形成时,资本的全球社会就会出现。此时,资本把整个世界社会控制在自己手中,全球社会工厂出现,全球控制社会出场,帝国到来。这是奈格里和哈特在21世纪初《帝国》一书中描述的资本统治现实。
四、结语
早期意大利自主论马克思主义者在面对现实工人斗争需要、在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背景中,从马克思的工厂理论出发,立足于直接生产中资本对劳动的具体控制关系,将其拓展到流通领域中,从而出现了工厂关系的专制性特征扩大到社会、国家和世界的发展趋势,展现了其独特的“工厂社会”的思路。这一思路不仅批判了正统马克思主义中片面的生产力中立论,批判了对科学技术去资本化的迷误,而且深入揭示了资产阶级政治上层建筑与资本经济关系密不可分的一体性,批判了政治国家中立化的观点,揭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关于国家与经济两分化的荒谬性,对认识资本同社会、国家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这在当代批判新自由主义的话语中展示出来。另一方面,这种思路对于资本统治权力的分析,指向了解析其具体化为各种生产机构、社会机构和政治机构的微观权力机制,这恰恰与福柯从机构层面探讨权力话语的来源具有同源性,也可以说是当代西方生命权力政治话语的来源之一。
但是,这种从工厂具体资本关系出发对本质性资本关系的理解,毫无疑问经验化了资本关系。这种经验化马克思本质性资本关系的思路必然会混淆资本剩余价值直接生产过程和剩余价值流通实现过程的区别,造成了生产流通化,流通生产化的认知,从而使他们不再关注变革资本私有制的基本意义,而偏向于在流通的社会层面探讨资本的矛盾表现,造成在主体力量优先的本体论基础上,走向当代单纯强调社会主体自由力量对抗资本权力以寻求解放的激进政治理论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