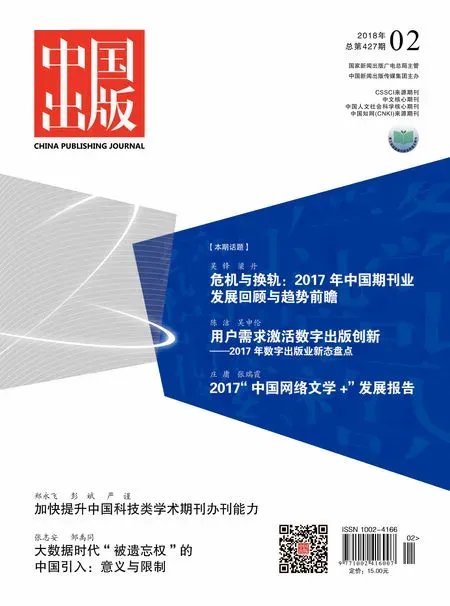大数据时代“被遗忘权”的中国引入:意义与限制*
□文│张志安 邹禹同
大数据时代在给我们带来各种生活便利的同时,其技术的两面性也暴露出种种问题,公众的网络表达和在线行为都可以被精准记录和分析,由此带来的隐私保护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圆形监狱”的隐忧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欧盟确立了可删除过去“不好的、无相关的、过时、无必要”信息数据的“被遗忘权”。
一、大数据时代下“圆形监狱”与“被遗忘权”
所谓“圆形监狱”(panopticon)最早由功利主义大师边沁提出,意指构建一所监视者位于圆心,被监视者房间呈环形分布的监狱,借用圆的几何特征以及一些相应建筑设计实现一个监视者就可以监视所有的犯人,而犯人却无法确定他们是否受到监视的目的。[1]米歇尔·福柯在其《规训与惩罚》中指出,这种监狱会使得人变成了一个个整齐划一、有用而听话的“肉体”。[2]长期以来,“圆形监狱”的概念被视为一种关于极权主义的构想,但在当下的大数据时代,却已成为现实生活中隐私被全方位窥探的形象表达。
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使海量数据的存储、分析和传输变得非常便利。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云存储和云计算技术进一步催生了大数据在各行各业的运用,而所谓大数据就是“通过高速采集、发现或分析,提取各种各样的大量数据的经济价值。”[3]从使用有实时路况反馈的GPS导航出行到入住可在线支付的快捷酒店,再到通过海量数据模型运算做出的经济发展政策,无一不依赖于大数据技术的支持。然而,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在享受便利的同时,地理位置、银行账户、个人照片等隐私信息又会被云存储在各大数据库中,网络数据追踪技术又可以联通各个数据库,通过对数据的挖掘形成相关的数据链,直至还原出一个可对应现实个人但同时又透明无隐私的数据化个体。可以说,网络数据库是其监控数据化个体的空间,而数据追踪技术则是对个体进行凝视的目光,数据空间中的每个个体实质上都无法逃离其凝视。[4]同时,作为个体,通常无从知晓自己是否被凝视,数字化的“圆形监狱”就这样悄然形成。由于数字记忆的永久性,使得这个“监狱”的监视者还拥有翻看每个个体表达和行为历史的能力,在这样的监视者面前,个体的现在和过去几乎都可以被记录和窥探。
在这种数字化“圆形监狱”的背景下,公众隐私的保护迫切需要新的手段,于是,“被遗忘权”作为新的隐私概念在以注重个人信息保护著称的欧盟得以率先提出。2012年,欧盟公布了《关于涉及个人数据处理的个人保护以及此类数据自由流动的第2012 /72、73 号草案》,首次提出数据主体应享有“被遗忘权(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所谓“被遗忘权”又可被称为“擦除权”,指相关个人有权要求数据控制者永久删除与其个人有关的信息数据,有权被互联网所遗忘,除非数据的保留有合法的理由。[5]2014年,欧盟法院通过了“谷歌诉冈萨雷斯被遗忘权案”的判决,判处谷歌公司败诉。法院认为谷歌作为数据控制者应按数据个体冈萨雷斯的要求,删除其“不好的、不相关的、过时的、无必要的”个人信息。自此,欧盟以判例的形式正式确立了“被遗忘权”。
“被遗忘权”一经提出,就引来众多争议,但不可否认,它提供了公众逃脱数字化“圆形监狱”的一条途径,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带来重大影响。通过行使“被遗忘权”,一方面,相关个体可以删除过去“不好的、无相关性、无必要、已经过时”的信息,降低和避免过去已发生的不良信息对当前产生的影响,保障当前安宁的生活,更好地融入主流社会。[6]另一方面,“被遗忘权”可视为数据主体作为被监视者对于监视者的一种权利宣言,宣示了个人对于自己个人信息的所有权以及自己隐私的不可侵犯。
“谷歌诉冈萨雷斯被遗忘权案”中就营造了谷歌公司作为数据控制者(监视者)与冈萨雷斯作为数据个体(被监视者)的冲突关系。而最后谷歌的败诉,使“被遗忘权”成了保护数据个体不受监视者监视的法律武器。通过删除信息数据可从源头上降低被监视的可能性,也可在主观上以违法风险促使那些数据控制者对监视行为有所约束。当然,被遗忘权的确立会对谷歌这类网络公司带来较重的运营负担。谷歌公司资料显示,仅在被遗忘权确立的2014年当年,公司就收到了大量公民为行使被遗忘权而进行的投诉,其中审核后删除的比例占到41.8%。[7]
继欧盟之后,多个国家也相继出台了“被遗忘权”的规定。例如美国加州出台的橡皮擦法案,该法案要求Facebook和推特等网络巨头应允许美国的未成年人擦除个人的网络痕迹。[8]俄罗斯则在民法典、信息法和民事诉讼法三个层面上出台了“被遗忘权”法规,三者分工明确、相互配合,保障“被遗忘权”的实施。[9]2016年2月,日本东京琦玉县地方法院要求谷歌删除一名男性3年前被捕的旧闻以及相关搜索结果,也以法院判例的形式承认了“被遗忘权”。[10]
二、我国引入“被遗忘权”的必要意义
发轫于欧盟的“被遗忘权”至今尚未正式引入我国,相关学者对于中国是否应引入“被遗忘权”仍存在不同看法。部分学者从隐私保护的需要出发,认为我国应引入被遗忘权,而且我国已有现行立法中也存留了确立被遗忘权的空间,例如《侵权责任法》中36条关于网络侵权“通知—取下”的规定。[11]也有部分学者则认为,我国的国情与欧盟差异较大,“被遗忘权”的基础在于“删除权”、而我国目前法律对“删除权”尚无规定,[12]加之“被遗忘权”的保护可能会对其他公共价值的张扬有过大的影响,因而对于引入“被遗忘权”的必要性持迟疑态度。我们认为,从我国引入“被遗忘权”的必要性看,至少有三方面的意义。
1.庞大的网民规模凸显隐私保护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尽管我国的网络普及率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但从网络产业、网民人数等总体规模看,从大数据技术在互联网领域的运用看,我国与欧美国家相比毫不逊色甚至还有超越之势。市值排名全球十大互联网企业中,我国就占据其中的4家(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CNNIC的2016年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披露,截至2016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31亿,普及率达到53.2%,超过全球平均水平3.1%,超过亚洲平均水平7.6%。中国网民规模已经相当于欧洲人口总量,而其中手机网民占比达95.1%。报告还指出,我国的手机支付的用户规模已达4.7亿,线下支付已成为习惯,网络社交产业更是非常发达。另据腾讯公司发布的《2016年微信数据报告》中披露,微信在2016年9月的平均日登录用户就达7.68亿,其中50%的用户使用时长在90分钟以上。
庞大的网民规模背后,是海量个人隐私数据存在着巨大的泄露风险。一方面,由于缺乏足够明晰的行业规则、充分普及的隐私保护意识和非常严格的监管机制,大量网络应用产品在争取用户注册、鼓励用户用其他平台账号进行登录的过程中,存在着隐私保护权限设置级别不高、隐私风险提醒不够的情况。另一方面,用户在网络平台上的隐私数据被泄露导致的网络诈骗、电信诈骗案件频发,直接给用户带来巨大伤害。某些犯罪分子甚至通过合法手段在网络上收集到的网民浏览痕迹、关联的社交账号或媒体历年来公开的信息,结合相关的数据比对技术就可推测出该网民的地址信息、真实姓名等资料,进而实施诈骗或者进行敲诈。此类案件中,犯罪分子其实已经在扮演“圆形监狱”中监视者的角色,网民作为被害人背负着类似被监视“囚犯”般的巨大风险。同时,又由于这类犯罪在获取初步信息时,采用的是公开收集互联网上信息的手段,要对此类犯罪行为进行治理的难度比较大。
2.把关人缺失的自媒体时代需要“被遗忘权”的约束
随着相关大数据、互联网、手机终端技术的进一步普及和融合,以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为主要传播平台,有着个体化、自主性、高速性、内容多样化、传播圈群化等特征的自媒体得到了蓬勃发展。[13]自媒体的出现,革新了传统的传播方式,开启了个人成为传播源、拥有话语权的自由信息时代,对社会管理能力的提高和公民社会的建设都有着积极推进作用。[14]而与此同时,与传统媒体采编、审核、发布等严格把关环节不同,自媒体的信息传播过程由于发布门槛低、审核不严格、标题党泛滥甚至受商业利益过度操纵,都会导致因把关人缺失而带来信息失真和伦理失范的问题。基于此,在自媒体上快速和广泛传播的海量信息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侵犯公民隐私及相关个人权益的信息。
针对这一自媒体传播过程中存在的固有缺陷,现有的解决模式是设置根据敏感词自动屏蔽的机器审核再配以相应的人工审核,这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信息把关的作用。然而,由于自媒体传播的信息数据量极为庞大,现有的管理模式往往只能对于那些造成社会影响较大的不实虚构信息做到适时甄别删除,对于侵犯公民隐私这类社会影响相对较小的信息则几乎起不到实质作用。以2017年7月发布的移动端iOS版本的某社交媒体APP为例,在该APP中,要通过移动端以侵犯人身权益的理由对于其他用户发布的微博进行投诉较之网页版进行操作要更加困难和不便。[15]此外,自媒体的传播模式具有圈层化扩散的特点,即通过在线社交圈实现多对多的传播,尽管初期传播以熟人圈为主,但只要被扩散进微信群或经广泛转发之后,就实质上从群体传播变成了大众传播,这样的传播方式和效应反而更容易产生公民隐私泄露以及其他人身权益侵犯的情况。针对这一现状,在我国引入“被遗忘权”会对相关自媒体的信息传播产生法律上的约束作用,赋予公民“被遗忘权”让他们更加充分意识到个人隐私保护的紧迫性和个人信息权的意义,促使自己成为个人信息传播的有效把关人,才能在更大程度上弥补自媒体传播的缺陷。
3.我国当前存在着引入“被遗忘权”的法律基础[16]
在法治意识传播方面,当前我国一部分公民对于“被遗忘权”已有一定的权利意识,“任甲玉诉百度一案”便是例证。该案中,原告任甲玉之前与一家名为陶氏教育机构有过合作,而原告在离职后,在百度公司提供的搜索网页中仍可大量搜索到原告在该机构的任职记录。而该机构声名不佳,使得原告离职后受之前的搜索记录所影响,无法顺利再就业。为此,原告起诉百度,认为百度侵犯了其一般人格权,要其停止侵权并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同时,任某要求行使“被遗忘权”,删除其与该教育机构相关的搜索结果。最后,受理该案的海淀区人民法院以百度公司未侵权且我国不存在“被遗忘权”等理由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此案中原告的诉求说明,我国当前现实社会中已经自发产生了对于“被遗忘权”的权利意识和权利保护的需要,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现实需求对立法进程有所推动的现象。
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由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2017年3月15日通过,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民法总则》也在法律逻辑上为“被遗忘权”的引入提供了相应的条文支持:第110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应当确保依法取得的个人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个人信息。”[17]在总则的高度上,此条法规明确了个人对于自己的数据信息使用具有自主权,即个人可自主决定个人信息被何种方式使用。而从立法目的来看,此项权利也应包括在合法前提下,个人有权出于被遗忘的目的对于自己的数据信息进行删除这一内容。由此,我们可以初步认为,我国后续如果要引入“被遗忘权”,是既有立法需求又有法条支持的。
三、我国引入“被遗忘权”的限制因素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我国引入“被遗忘权”有积极意义。然而,一种新生事物的出现必然会引起一连串积极或消极的反应,“被遗忘权”的引入也会带来可能的一些负面影响。
1.引入“被遗忘权”会对舆论场的开放和完整带来影响
人类语言的不精确性,使得人类口头表达与内心真实意思之间存在着鸿沟。可想而知,在行使“被遗忘权”去甄别审核删除相关数据信息时,也会产生部分模棱两可的情况,比如不能明确确定网络表达的内容是属于言论自由这类合法保留范畴,还是属于通过行使“被遗忘权”应删除的范畴。
“被遗忘权”一旦确立,为了保证其实施必然也将配套相关的法律制裁机制。例如俄罗斯的“被遗忘权”规定中,相关拒绝履行被遗忘权的法人将被处以8万到10万卢布(1美元约合72.88卢布)的罚款,而相关拒不履行的自然人将被处以3万到5万卢布的罚款。[18]因此,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相关数据控制者由于害怕面临巨额罚款或起诉,很可能会大量删除那些原本不该删除的信息,尤其是在面对判断模棱两可的情况时可能会倾向于先删除以避免风险。[19]此外,相较于由注重形式语法而表达时显得较为繁琐的英语书写数据而言,由注重表达简洁而意义深远的汉语写就的信息数据,其在判读时出现模棱两可的情况可能会更多,这给具体实施信息保留或删除时的判断带来更大困难。
另一方面,“被遗忘权”实施时需要数据控制者对于删除数据进行判读和审核,这需要数据控制者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同时如果其一旦因判读审核错误而拒绝“被遗忘权”行使又将面对相关的法律制裁。于是,在权衡利弊之后,信息控制者就会对删除信息的要求有求必应。[20]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本不该删除的信息数据被大量删除,或者网民在情绪化状态下表达的观点被大量删除,这势必将对整个网络舆论场的完整、开放和真实性带来影响。
2.引入“被遗忘权”会极大增加我国互联网公司的运营成本
“被遗忘权”在欧盟确立之后,单谷歌公司一家从2014年5月29日到2015年4月15日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已收到239948项行使“被遗忘权”的申请,需审核的网址总数高达870102,其中同意移除的达到41.5%。[21]毫无疑问,处理这些申请和满足用户需要会给谷歌公司增加巨大的运营成本。
一旦我国引入“被遗忘权”之后,各大互联网公司收到行使“被遗忘权”的申请数量及其需要审核的信息可能是惊人数字,而为处理这些“被遗忘权”申请,互联网公司势必也将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导致自身运营成本的大大增加。可以预见,“被遗忘权”引入我国之后带来管控成本上升的同时,也会导致相关互联网企业用于创新性的资源可能会有所减少。
3.引入“被遗忘权”带来的司法纠纷会占用较多的司法资源
“被遗忘权”引入之后其带来的司法纠纷也不可避免。当下,我国互联网产业发展迅猛,互联网协会与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于2016年3月18日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站发展状况及其安全报告(2016)》中指出,我国互联网网站总数达到426.7万余个,同比年度净增长62万余个,超过前五年中国网站净增量总和。[22]这样的繁荣发展态势,既会导致这类司法纠纷数量激增,也会导致在每一个涉及“被遗忘权”的司法纠纷中的证据案件材料的数量将会无比巨大,进而使得相关纠纷解决需要巨额司法资源的投入。
再以任甲玉案为例,其一审判决时间为2015年7月21日,二审判决时间为2015年12月9日。[23]而根据我国民诉法的规定,二审应在一审判决书送达之后的15日内提出,二审的期限一般为3个月。任甲玉案从一审判决之后到二审判决,中间相隔了4个月18天,已超于一般情况下的最长期限。从两审的时间间隔中,也可以看出任甲玉案的复杂程度及其背后较大的司法资源投入。而我国当前本就处于案多人少的司法环境之中,[24]如果“被遗忘权”带来的司法纠纷再占用大量司法资源,将会给整个司法治理带来更严峻的挑战。
上述三个方面,既是我国引入“被遗忘权”可能承担的成本,也是政策制定者在考量是否引入“被遗忘权”时需要直面的问题。一旦看清公民隐私权保障和未来司法改革的方向,充分考虑到各方利益的均衡点,下决心并有能力解决这些限制因素,那么,引入“被遗忘权”就是水到渠成的事。
四、结语与探讨
尽管我国引入“被遗忘权”会带来如前所述的各种限制因素,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理解和实践“被遗忘权”的价值。在互联网发展的早期,甚至都存在过排斥法律规则对网络世界调整的论调。[25]总体上,我们要根据我国现有的司法状况和实际情境去审视引入“被遗忘权”的问题。
当前,我国现有的法律中已有部分借鉴“被遗忘权”的内容。例如《侵权责任法》中36条关于网络侵权“通知—取下”的规定,以及2016年11月7日通过的《网络安全法》中43条的规定:个人发现网络运营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双方的约定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有权要求网络运营者删除其个人信息;发现网络运营者收集、存储的个人信息有错误的,有权要求网络运营者予以更正。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措施予以删除或者更正。然而,上述条款中对于有权要求网络运营者删除其个人信息的情形,是建立在网络运营者侵权违法在先或者存在信息错误的前提下实施的。而“被遗忘权”的定义中,只要信息是“不好,过时,不必要、无相关的”就可要求相关主体给予删除。从这方面来说,“被遗忘权”的权利外延比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要更宽。
令人欣慰的是,之前提及的《民法总则》中已明确规定了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到法律保护,这为我国进一步确立“被遗忘权”提供了法律基础。我们相信,在今后民法典分则的编撰中必然会有涉及“被遗忘权”的相关重要内容。不过,在这项权利被正式确认之前或确认之后,作为网民,都有必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网络素养,在享受社交媒体传播便利的同时增强个人隐私信息的保护意识,懂得对个人信息传播的后果做必要的预期分析,并掌握通过有选择性的传播信息或采取自我删除信息的方式来管理社交网络。
注释:
[1]孙运梁.福柯监狱思想研究——监狱的权力分析[J].刑事法评论,2009(1)
[2][法]米歇尔·福柯著.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3]Gantz J,Reinsel D.Extracting value from chaos.IDC iView,2011:1-12
[4]吴飞,傅正科.大数据与“被遗忘权”[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2)
[5]2012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Article 17
[6][11]杨立新,韩煦.被遗忘权的中国本土化及法律适用[J].法律适用,2015(2)
[7]Global Data Hub Google Spain and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http://unitedkingdom.taylorwessing.com/globaldatahub/article_2014_google_spain.html
[8]裴洪辉.美国推“橡皮擦”法案,抹掉未成年人的网络过失[J].法律与生活,2014(1)
[9]张建文.俄罗斯被遗忘权的意图、架构与特点[J].求是学刊,2016(5)
[10]保护“被遗忘权”日本法院要求谷歌删除旧新闻,信息时报,2016年2月29日. http://news.ifeng.com/a/20160229/47621921_0.shtml
[12]王融.“被遗忘权”很美?——评国内首例“被遗忘权”案[J].中国信息安全,2016(8)
[13]宋全成.论自媒体的特征、挑战及其综合管制问题[J].南京社会科学,2015(3)
[14]汪頔.探析自媒体时代对社会价值观的影响[J].中国报业,2013(2)
[15]笔者于2017年7月4日更新下载的ios移动端新浪微博app显示,举报理由包括垃圾营销、不实信息、有害信息、违法信息、淫秽色情、人身攻击、抄袭、违规有奖活动等8项,8项以外的人身权益纠纷投诉只可在网页版进行操作且操作流程相对复杂。
[16]此案例涉及内容均来自中国裁判文书网
[17]见全国人大网权威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2017年3月15日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7-03/15/content_2018907.htm
[18]俄新法赋予公民网上被遗忘权来源广州日报,网易科技,2016年1月2日http://tech.163.com/16/0102/07/BCAEGI8K000915BF.html
[19]伍艳.论网络信息时代的“被遗忘权”[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3(11)
[20]Emily Adams Shoor,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BRook. J. INT’L L. Vol. 39: 1
[21]http://www.google.com/transparencyreport/removals/europeprivacy/,2015-04-01
[22]《中国互联网站发展状况及其安全报告(2016)》在京发布,新华网,2016年3月18日 http://news.xinhuanet.com/info/2016-03/18/c_135200752.htm?1458396430450
[23]以上涉及的时间均来自于中国裁判文书网
[24]孙笑侠.“案多人少矛盾”与司法有限主义[N].北京日报,2016-11-07
[25]夏燕.“被遗忘权”之争——基于欧盟个人数据保护立法改革的考察[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