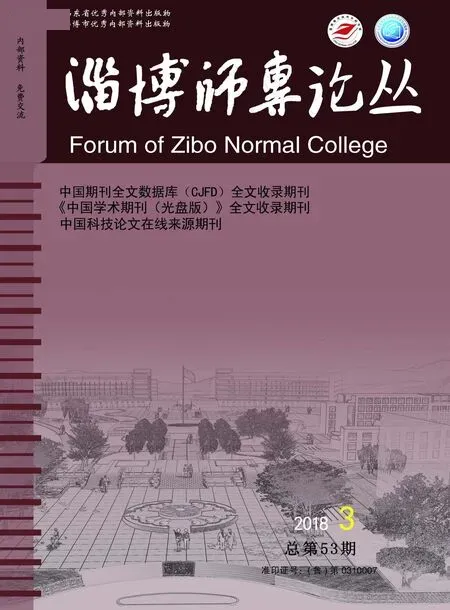中国古代未能形成政教合一体制问题探究
赵寒霄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院,北京100032)
宗教,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世界各地大行其道,也因其对民众强有力的控制力而广受各地统治者的推崇。然而相较于历史上其他大帝国,中国始终没有建立起一个政教合一的王朝,政教关系一直是“政主教辅”。诸如欧洲的罗马帝国、法兰克王国、神圣罗马帝国,中东的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等,这些帝国均是政教合一的宗教国家,宗教同时主导着世俗与精神世界。反观中国,为什么宗教始终不能占据国家的主导地位呢?
有学者认为我国一直都是一个宗教国家,“儒教”便是国教。笔者认为儒家思想不能算作宗教,甚至可以说与宗教格格不入。自孔子以降,便是“子不语怪力乱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从历代帝王呈献给孔子的尊号看,中国人心目中的孔子一直都是政治人伦的而不是宗教的,是至尊的“先师”而不是万能的上帝。[1]儒家不谈神明,不讲轮回,唯敬天地祖宗。“神”这一意向在儒家思想里没有一席之地,大儒不寄希望于死后,不求轮回享来世,唯以此身事国家。一个如此世俗化的思想如何能说其是宗教呢?若非要以西方的观点来看中国的儒学,无异以驴唇而对马嘴。
另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商朝便是政教合一的朝代,是神启王朝。其实不然,商朝的“帝”崇拜带有浓厚的巫术色彩,商人好卜筮,商王便是全国最大的巫师,巫术与宗教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宗教是以神御人,而巫术则是以人御神。巫术所有的动作只是达到目的手段;宗教则是包括一套行为本身便是目的行为,此外别无目的。[2](P69)
一、古代欧洲和中东政教合一的原因
古代欧洲与中东的政体,是典型的政教合一的体制,政教合一在这些地区的出现有其必然性,政教合一体制也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
(一)下层民众的需要是政教合一的社会基础
政教合一的政体,首先要有信教的社会基础。马克思指出宗教存在的根源,在于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异己力量,包括自然力量与社会力量,只要人们还受这种力量的支配,宗教就会存在。[3]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底层人民生活困苦,政府的基层组织一盘散沙,给了基督教良好的生存土壤与传播空间。伊斯兰教创建时,阿拉伯社会贫富悬殊、高利贷盘剥、部落氏族对立、血亲复仇盛行、战争频仍、经济衰落,[4]民众迫切地需要一种宗教来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乔达摩·悉达多创建佛教时,古印度各国之间互相讨伐、并吞,阶级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民众苦于种姓制度而不得反抗,社会沙门思潮涌动。因此,从根本上说是民众对宗教的需要催生了宗教。
(二)统治阶级的需要是政教合一的决定性因素
统治者的皈依与推动是建立政教合一体制的决定力量,政教合一的政体对巩固统治至关重要。
1.弱化自由意志,统一国民思想。欧洲的罗马帝国、中东的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均是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国内没有一个占据绝对多数的民族,向心力不强,易出现叛乱与分裂思想,传统的武力压制难以维持其统治的长久性。宗教的存在超越了民族界限,各族共尊一神,给国民洗脑,达到弱化其反抗意识的目的。以罗马帝国为例,三世纪以后,罗马国力下降并陷入全面的危机,经济衰退、城市萧条、官场腐败、内战频繁。[5]为了维护统治,罗马转变了其一直来对基督教的迫害,立其为国教,试图扭转混乱的国内形势。
2.神化王权,维持政权稳定。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说,最高统治者的合法地位很难获得各个民族的认可,统治根基不稳,宗教的存在能够将皇权“神化”,统治者作为神的代表实行统治,其统治便具备了合法性。教父德尔图良在呈献给罗马皇帝的《护教篇》中谈到:君主是神的代表,基督徒应像侍奉神那样去侍奉罗马的君主。基督徒们应为所有的皇帝祈求长寿。[6]
3.团结国内民族,一致对外扩张。这些大帝国均靠对外征服为生,以其强大的武力来保证其统治地位,一旦其扩张的脚步停止,国家很快就会失去生命力,走向衰弱。然而随着扩张的脚步越来越大,如何团结新征服的民族,使之参与到新帝国的扩张轨道上来,便是摆在所有统治者面前的问题。无论是阿拉伯帝国的对外征服,亦或中世纪欧洲的十字军东征,都是打着传教的旗号,将侵略美化为“圣战”。转移国内矛盾,把战争的矛头指向境外,既能团结新并入的民族,又能扩张国土,宗教的作用毋庸置疑。
二、古代中国没有产生政教合一的原因
宗教在中国占据不了主导地位的原因,简单讲就是三个字:不需要。中国人对宗教信仰的依存度不高,国家自然不需要政教合一。
(一)独特的地理环境
中国地处欧亚大陆东部,一枝独秀,得天独厚的条件对中国形成“政主教辅”的政教关系奠定了基础。
1.中国地处温带季风气候区,气候宜人、平原广阔、河流众多,临海多湖,山川丘陵广布,自然资源丰富,中国自古便有“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说法。优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安定的农耕文明,使得中原地区的人民能够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不受饥寒之苦,不必寄希望死后或来生。位于中国边远地区的游牧民族,自然条件恶劣,生产方式落后,一个冬天往往能冻死部落半数人口,这些民族无法靠自身获得安定与幸福,便只能求之于神明。
2.中国东临大洋,西抵葱岭,北有大漠,南隔横断,四面“天堑”,地理空间相对闭塞。远离其他文明古国,受到外界影响小,能够独立发展自己的文化。反观中东素有“五海三洲之地”之称,古埃及与古巴比伦均发祥于此,东有波斯,西有罗马,南有阿拉伯,各种文明相互碰撞,民族相互攻击,战争不断,是名副其实的四战之地,百姓长期处于流离失所的状态之中,对于宗教的需求极为强烈。
(二)强大的专制皇权
中国古代皇权至高无上,任何其他的权力都需要为皇权服务,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宗教只是皇帝可以利用的工具。回首中国历史,神权一直从属于皇权。南朝时梁武帝崇佛,曾让佛教昌盛一时,恰恰反映了皇权的至高无上,皇帝喜欢佛教,佛教兴;皇帝厌恶佛教,佛教衰。中国历史上四次出现大规模灭佛运动,佛教在皇权面前羸弱如幼童,皇帝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念兴教,一念灭教。古代中国“政主教辅”的政教关系从根本上弱化了宗教对于政治的干预力。
中国的皇位是皇帝自封的,而不是宗教的神封的。中国人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并不迷信皇族血统论。项羽少年时见到秦始皇东巡便敢言“彼可取而代之”。中国人信奉的平等,是人人可修仙,人人可成佛,人人可争皇位,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在西方就是“僭主”,但在中国“有枪便是草头王”,得到江山的都是真龙天子,中国皇帝不需要“神”来承认其统治的合法性。反观阿拉伯帝国,千百年来关于正统一直争论不休,什叶派至今仍然只承认阿里及其后裔为合法继承人,这在中国人看来是很难理解的。
(三)深厚的人文理性
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西方人眼中是“神秘而独特的”,我们的传统思想与西方正统价值观格格不入。独特的东方式思想使宗教在中国难以大行其道。
1.人本主义思想。中国的人本主义体现在“人本而神末”。唐代骆宾王《讨武曌檄》中有云:“人神之所共忌,天地之所不容。”《旧唐书·于柚传》有云:“肆行暴虐,人神共愤,法令不容。”人先“忌”而神后“忌”,人先“愤”而神后“愤”。 “民为神之主”“神依人而行”。[7]对比藏传佛教的活佛制,中原的大乘佛教讲究“人人皆可成佛”,“一念成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自己成不了“佛”的宗教对中国人来说是没有吸引力的。相比于上帝、安拉、佛祖的高高在上,毫无“绯闻”,中国的神,都是“人化”后的神,可以有玉帝娶妻生子,可以有七仙女下凡幽会,甚至可以有天蓬元帅堕落成猪。神话中的天庭,更是直接把人间的朝廷搬到了天上,神仙之间勾心斗角,毫无神性,有的只是人之常情。
2.实用主义思想。即使在古代不发达的科技条件下,中国人特别是上层社会的中国人也是“敬鬼神而远之”,骨子里并不相信 “神”能够救国救民。商代可以算是中国最尊崇神明的朝代了,却仍旧摆脱不了灭亡的命运,以商为鉴,周人对神的作用产生了质疑,周人说:“天不可信”,(《尚书·君奭》)表明了对天的怀疑。周人还认为神是否保佑一个朝代,根本的原因是看君主是否反映了百姓的意愿。[8]这种功利主义的直接产物便是“周公制礼”,《尚书》有云:“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人取得了凌驾于神的权力。人之所欲,神不得不予;人之所憎,神不得不弃。中国人从显贵到百姓,往往不问是哪种宗教的神与庙,见神就拜,见庙就烧香。[9]百姓抱有一种不管哪路神仙,能保佑我的就是好神,至于虔诚,不存在的。
3.人定胜天思想。今天的中国,敢开高峡平湖,敢铺万里天路。这些“敢叫天地变颜色”的壮举并非今人之所独有,中国人骨子里的血脉便是“人定胜天”。西方的神话中,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都被说成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9]人类是靠“神启”发展的,神一次又一次地拯救了人类文明。给世界各民族带来普遍灾难的“大洪水”,西方靠着“诺亚方舟”,靠神的怜悯得以延续生存,中国人则靠“大禹治水”,一路刀劈斧砍,遇山开山,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了天灾。从燧木取火、仓颉造字、精卫填海、神农尝百草、后羿射日等神话就可以看出我们的文化是崇拜自我,崇拜奋斗,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夏尊天,商尊鬼,周尊人,中国人一步步走上了无神化道路,“神”在中国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人之所至,再无神之位置。
(四)相对单一的人口组成
作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汉人占据人口的绝对多数。无论是务农、经商还是从政,对于绝大多数汉人来说,从其出生起面对的竞争者便都是汉人,即使有外族人,也是经过汉文化同化以后的“外族人”。单一的民族构成使得统治者仅仅依靠政府控制而不需要借助宗教的手段,便能够维持国内稳定。罗马帝国治下民族成分复杂,罗马人、凯尔特人、希腊人、犹太人、埃及人、日耳曼人都拥有相当大的人口基数,阿拉伯帝国治下同样有着阿拉伯人、波斯人、犹太人、西哥特人等诸多强大民族,占据国家统治地位的民族人口上没有绝对优势,以宗教的方式共尊一神,在思想上形成统一的信仰,对巩固统治至关重要。
单一而庞大的人口是古代中国国力长期强大的重要因素。冷兵器时代,人口的多少直接决定了国力的强弱,长期的强大造就了中华民族强烈的文化自信。汉人长期视外族为“蛮夷”,视外族宗教信仰为“鬼怪邪说”。纵观中国历史,少数民族于中原建国后,均要采用汉人的统治方式,改宗孔子,改奉儒学。而西欧5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没有一个能够占据绝对多数的民族,日耳曼人、凯尔特人、罗马人、希腊人等较为强大的民族人口差距不大,各大民族之下又有诸多小民族,各国间的相互制衡使得教权有了极大的腾挪空间,相对弱小的单一民族政权无法对抗跨国的教权,这才有了“卡诺莎之辱①”。
(五)本土化的信仰特质
西方人常说中国人没有信仰,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中国人有着一套与西方截然不同的信仰体系。
1.内涵丰富的祖先崇拜。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拜超过任何神明,这与西周实行的宗法制以及秦汉以后形成的封建家长制的家族特性息息相关,中国人逐渐由信仰公共神明转向家族式祖先崇拜。中国人无论贫富,都要供奉祖先,逢年过节烧香磕头,祈求保佑以荫庇子孙。人们通过这些仪式寄托其对于同出之祖的缅怀以及对祖考的敬仰,更重要的社会功能也许是以此教化子孙、强化家族内的宗法关系,也借此婉转地表达出他们对于血缘的崇拜以及对血缘传递的由衷关怀——那种视子孙为自我生命之延续的、一体的感觉。[10]
2.影响深远的儒家思想。儒家思想覆盖了国人一生的各个阶段,唯独不讲生前和死后,而是着重关注现世的人文关怀。读书人自幼便读《三字经》《弟子规》,稍大便学“四书五经”,一生所求乃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生以此身安天下,哪管死后地狱轮回。更重要的是儒家思想潜移默化到了下层百姓,伦理纲常就是无论贵贱都要遵从的道理。儒家学说还解决了多民族国家问题,其认为区别民族不在血统而在文统。凡承认君臣从属关系的族群就是华夏,不遵守君臣从属关系的就是夷狄。[7]这就为李世民这样有少数民族血统的皇帝统治的正统性做了背书。一套如此严密而完美的体系使得宗教在现世的存在不为大多数中国人所需要,而政权掌握在通过科举上位的儒家学子手中更是断绝了宗教干预政治的可能性。
历史是一个偶然中孕育必然,必然中充满了偶然的合力,中国没有成为政教合一的国家,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中国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政教合一的尝试,只是最终都走向失败。东汉末年,张鲁以“政教合一”统治方式割据巴汉三十余年。张鲁“不置长吏,以祭酒为理,民夷信向。”(《后汉书·刘焉列传》)。元代安西王阿难达在14世纪初于西北和四川曾建立起伊斯兰教团体,使依附于他的15万蒙古军队的大部分改信伊斯兰教,图谋帝位后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有资格争夺皇位的穆斯林。如果阿难达成功夺取帝位,中国有可能会伊斯兰化。
中国历史上不存在宗教问题。激烈的反神者和虔诚的信神者可以和平地并存共生,极少发生宗教歧视,没有宗教迫害,更没有宗教战争。[11]各大王朝的国策向来都是“宗教信仰自由”,政府的民族宗教政策上表现为“因俗而治”“兴教安边”的路向。[12]古代中国人可以信佛,可以做礼拜,可以诵圣经,可以炼丹打坐以求长生,一座长安汇聚天下各宗而相安共生,一朝皇都遍布道观寺庙而和谐与共,强大的文化自信使得中国人能够昂首挺胸自择诸神。中国有自己独特的政教关系,在宗教信仰上我们没必要仰人鼻息,不必因西方指责我们没有信仰而自惭形秽,我们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一套完整的东方信仰体系。无论是历史上的从未断代的文明进程,还是今天日益强大的综合国力,我们有理由相信自己的信仰基础,有理由对自己的文化自信。
注释:
①1077年1月,德皇亨利四世冒着风雪严寒,前往意大利北部的卡诺莎城堡向教皇“忏悔罪过”,三天三夜后,教皇才给予亨利四世一个额头吻表示原谅,而这位教皇出身于皮鞋手工制作之家,这就是“卡诺莎之辱”。此后,“卡诺莎之辱”在西方世界成为屈辱投降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