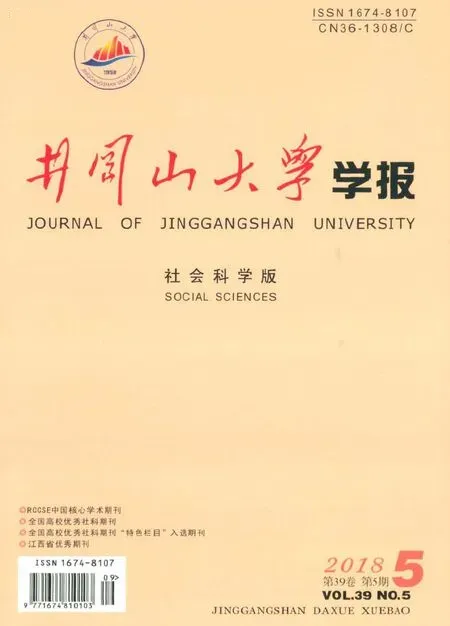也说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
王昌英
(武夷学院思政部,福建 武夷山 354300)
马克思,其名字与学说传入中国,是在中国的晚清时期。但最早传入的具体时间,既有研究成果给出了多种不同说法,概括起来,具有代表性的是1898年说、1899年说和1902年说。其中,1902年说已被可靠资料予以了否定;1898年说成为1987年以后的主流观点,但这一观点实际上证据不足。
一、1898年说
关于马克思学说传入中国的最早时间,1987年至今的主流说法是:1898年。
这一说法的始作俑者当推陈铨亚。他1987年9月16日在《光明日报》第3版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一文,指出:“目前,国内一般都认为1899年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节译基德的《社会进化》一书为马克思之名见诸国人之始,事实并不是这样。”[1]他说:美国人伯尔纳写了一本叫作《1907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的书,书的第28页上说,1898年夏,《万国公报》的编者在中国出版了第一部系统讲解多种社会主义学说的著作。他认为这一说法可信,但对伯尔纳没有提到书名和内容表示遗憾。他猜测,伯尔纳未看过此书,否则,伯尔纳不会同意把1899年的《万国公报》视为最早提到马克思的中文报刊。在这些叙述之后,他断言:“伯氏提到的这一部著作实际上就是英人克卡朴 (Kirkup)所著的 《The History ofSocialism》①原文如此。在of和 Socialism之间应该有个空格,这是微不足道的问题,容易识别,因此,为保持此文原貌,笔者引用时未作修改。(《社会主义史》)。此书因广学会的著名人物李提摩太委托,由胡贻谷(有作胡颐谷的)翻译,于1898年夏在上海以《泰西民法志》之名交付广学会出版。”[1]
接下来,陈铨亚就《泰西民法志》作了些叙述。他说:这本书已经很难见到,只是《唐庆增经济讲演集》中偶一提及。李季译《社会主义史》影响最大,此书译自克卡朴著、辟司(Prase)1913年增订的本子,“由于胡译自1892年布克莱(Black)②笔者暂未查到出版该书的书局。这里,陈铨亚提供的英文名和中译名之间是一种非对应的关系,想必有一个错误。若英文名拼写正确,则其相应的中译名应为“布莱克”,而非陈文中提供的“布克莱”;反之,若中译名正确,则其英文名非陈文中提供的Black。书局初版本,李译自1913年的辟司增订本,两书在内容、体例安排上已稍作更动,不能见其原貌。幸赖辟司在序中有说明,遂不致有很大困难。”[1]根据辟司关于第一至九章保持原书内容未作变动的说明,陈铨亚推断,“马克思”在第七章,相信辟司没作变动。他引用了一段未说明出处的提及马克思的话,说明《泰西民法志》已经提到了马克思,并断定说,《泰西民法志》虽未引起很大影响,甚至差点被人遗忘,但“马克思名字也好,马克思主义学说也好,说到他们在中国的传播都应把首功归之于它”。[1]
笔者最初了解到陈铨亚的1898年说并非通过上述陈文,而是通过《胜利论坛》1987年第2期上的摘录文章《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我国》[2](P76)。
虽然这篇摘录很简略,陈文中的“第28页”在摘录中为“第82页”,且只在末尾注明摘自《光明日报》,未注明原文作者及发表于《光明日报》的年月日,但它摘录自陈铨亚的上述文章无疑。
撇开书籍和报纸文章等不说,1987年以后,仅笔者查阅的学位论文和公开发表的期刊论文,就有数百篇采用陈铨亚的上述观点。虽然这些文章的作者们大多并未注明观点出处,而是将其当作确认无误的事实加以陈述,但追根溯源,此观点无疑来自上述陈文。
二、学界对1898年说的质疑与反对
也有极少数研究者对马克思学说最早传入中国的1898年说表示存疑或反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前者如汪家熔和唐宝林二位先生,后者如王也扬先生。
(一)汪家熔先生质疑1898年说
汪家熔在1993年第1期的《编辑学刊》上发表了《最早介绍马克思恐非胡贻谷》一文。文中,他列举了几点理由,证明陈铨亚的论据“极软弱无力”。他说,陈铨亚“是以证实伯尔纳为方法提出胡贻谷在1898年夏最早向国人介绍马克思的”[3](P95-96),但这一方法存在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陈铨亚所引伯尔纳的文字中,伯氏并未提到他所说的那本书的作者、书名、译者、中文书名、广学会的组织者,陈铨亚未提出任何根据,未对中译本作任何外表的、内容的描述,未说明某人的文字中提及该书的翻译情况,却断言该书是克卡朴的《社会主义史》及其中译名、译者、组织者。从文章看,陈铨亚也没有见过他所说的译自 《社会主义史》的《泰西民法志》。虽然“《唐庆增经济演讲集》中偶一提及”《泰西民法志》,恐怕并未说过此书译自《社会主义史》,也未提到其中有对马克思的介绍,否则陈铨亚会引用唐庆增的文字来证明。所以,伯尔纳和唐庆增似乎都没有提到,陈铨亚自己也没有看到,而说有这么一件事。
第二,1898年的广学会工作年报作于当年12月22日,其中有“今年出版的书刊”一节,罗列了广学会1898年所出书刊的目录及印数、页数,其中,宗教、科技、政治图书共48种,没有“泰西民法志”或接近于“社会主义史”的书名。“如果胡贻谷是1898年夏天交稿,或年底交稿,如果确有此译,后来广学会或其他单位出版了。那末也不一定能‘把首功归之于他’——进入1899年了。”[3](P95-96)
第三,陈铨亚根据辟司的序,知道辟司增订本第一至九章保持了克卡朴原书内容,“马克思”在第七章,他“相信辟司没有变动”。说明后,陈铨亚引用了未注明出处的译文介绍克卡朴如何介绍马克思。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19世纪除必要,如法律,政治书一般都是意译、节译。如果胡贻谷是节译,第七章“马克思”可以不译;如果是意译,文字肯定不是李季的译文。
第四,按照上世纪末确定译名的习惯,“社会主义史”大概应该译成“泰西大同学案”或“泰西学案”。
基于上述几点理由,汪家熔以标题中“恐非”和正文中“或”等不确定词的使用,表明自己对陈铨亚1898年说的态度:不断然否定,但甚为怀疑。
(二)唐宝林先生质疑1898年说
汪家熔发表此文几年以后,唐宝林在《光明日报》1998年4月3日第7版发表了 《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一文,对陈铨亚的1898年说表示“值得商榷”。他对陈文的困惑可概括如下:
第一,他见到的《泰西民法志》出版于1912年,胡贻谷的序写于1910年,二者皆不在1898年;
第二,《泰西民法志》的“篇七”是“马格司”,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名全书用的是“马格司”和“恩吉尔”,不是陈铨亚引文中的“马克思”和“昂格思”;
第三,他见到的《泰西民法志》,其原著作者为“甘格士”,而非“克卡朴”;
第四,从文章看,陈铨亚也没有看到1898年版的《泰西民法志》,文中关于“马克思”的一段话引自辟司(Prase)1913年增订、李季1920年翻译出版的《社会主义史》,而非《泰西民法志》。
第五,中国人民大学的高放教授也见过《泰西民法志》,与他持相同看法;并且,高放教授几年前访美时曾见到伯尔纳,“问起此事,伯尔纳回答说他写的那本书中没有提到《泰西民法志》”。
唐宝林的结论是:“《泰西民法志》不大可能是1898年初版,1898年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之说值得怀疑。”[4]唐宝林与汪家熔一样,对1898年说表示怀疑,却不断然否定。从文章看,唐宝林此时尚未读到过汪家熔的前述文章。
(三)王也扬先生反对1898年说
明确反对1898年说的论者主要是王也扬,他在2000年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的一个说法之误》一文中说,陈铨亚没见过1898年版《泰西民法志》,又拿不出其存在的确证,却说有这年出版的这本书。对于这一观点,“惟唐宝林先生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一书,在使用《泰西民法志》1898年出版说时,认为此说可能有误,表示存疑。”[5]从这句看,王也扬在写作此文时,与唐宝林一样,并未读到汪家熔的前述文章。他用两个比较有力的证据,否定了陈铨亚的1898年说:
第一,广学会1898年度的工作报告没有出版《泰西民法志》的记录,而其1912年度的工作报告中有当年该会新版和再版书籍的完整目录,《泰西民法志》(History of Socialism (Kirkup)by I.K.Hu)清楚地列于1912年新版书之中,并记有印数1000册。
第二,王也扬见到了《泰西民法志》的译者胡贻谷1917年为其老师谢洪赉(又名庐隐)撰写的《谢庐隐先生传》①王也扬提供的书名少了“略”之一字。笔者在图书馆查阅到的书名为《谢庐隐先生传略》。参见胡贻谷:《谢庐隐先生传略》,上海:青年协会书报部,1917年版。,书中写道:“著者获遇先生,在一八九八年之初,盖为余初入中西肄业之年也,时年仅十四。”[5](P85)一个初入中西书院学习的 14 岁少年不可能翻译《泰西民法志》这样的著作。
王也扬考证后的结论是:《泰西民法志》一书首次在中国问世不在1898年,而在1912年。
三、结论
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时间在几个学科和专业领域都必定要涉及,而证据不足的1898年说又已成为被广泛采纳的观点,并且继续着其以讹传讹的过程与结果,笔者便不得不在这里对其中几个小问题加以澄清,并对1898年说作一简要小结。
(一)几处笔误与小问题
前述几位学者及其他学人在论及或转述1898年说时,提到了几部著作、几位作者。在提到时,出现了几处小小的笔误与问题。这几处笔误与问题若只是个别人提及,本无关紧要,但事实上它们一再被提及。因此,有必要对其加以澄清和说明,以免学界继续以讹传讹。
第一,“伯尔纳”应为“伯纳尔”。
笔者循着陈铨亚在文中提供的线索,查阅了他所说的伯尔纳著《1907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6]一书。笔者看到这本书的第一眼即吃惊地发现,书名下方,作者名赫然写着“伯纳尔”,而非“伯尔纳”。之所以说“吃惊”,是因为论者们无论是支持、认同还是质疑、反对1898年说,在提及陈铨亚提到的这本书的作者时,无一例外,说的都是“伯尔纳”。尽管将Martin Bernal译为马丁·伯纳尔或马丁·伯尔纳皆可,但论者们无一例外将其称为“伯尔纳”,显然并未查阅这本书。
第二,“第 28 页”、“第 82 页”应为“第 26 页”。
引自《一九○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的话所在的页码,摘录说在第82页,原文说在第28页。既然是摘录和原文的关系,摘录中“第82页”显然系陈铨亚原文中“第28页”之误。
经查阅,书上的确有陈文征引的话,但它既不在第28页,也不在第82页,而在26至27页。笔者推测,陈铨亚将“26”错看或错写成了“28”,而非笔者与陈铨亚看到的书系不同版本。
第三,“Prase”应为“Pease”。
陈铨亚在文中提及辟司增订、李季翻译的《社会主义史》时,提供的辟司的英文名为“Prase”。从音译的角度说,Prase对应的中译名应该不是辟司,而是普瑞斯、普雷斯等。笔者怀疑,在辟司和Prase这二者之间,或许有一个是错误的。笔者见到的相关文章和著作,述及辟司时,提供的英文名几乎都与陈文相同,唯有汪家熔的文章提供的名字是E.R.Pease。经查阅,在1920年版《社会主义史》[7]正文开始之处,明确标示了“辟司 Edward R.Pease增订”。所以,辟司对应的英文名为Pease,非Prase。
第四,“克卡林”应为“克卡朴”。
克卡朴为Kirkup的中译名,译为柯卡朴、柯卡普、刻卡朴等皆可。然而,一些论文和著作中写的是克卡林。笔者推测,“克卡林”这个名字不是从英文翻译而来,而是某位或某几位作者将中文的“克卡朴”误认、误写作“克卡林”,其他研究者以讹传讹,而有此结果。
第五,“甘格士”即“克卡朴”。
前文述及,唐宝林质疑《泰西民法志》初版于1898年的说法时,曾说他见到的1912年版《泰西民法志》作者为甘格士,而非克卡朴。笔者发现,其它文章和著作中也有将作者写作甘格士的情况。比如,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在其1985年选编出版的《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资料选辑)第 1 辑》[8]中,将 1912 年版《泰西民法志》作者写作刻卡朴,而在其1987年选编出版的《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资料选辑)第 2 辑》[9]中,却将同一版本的此书的作者写作甘格士;在这两套书中,1920年版《社会主义史》的作者又被写作克卡朴。甘格士与克卡朴(或刻卡朴),这两者的发音差距较大,不能不令人怀疑是否系两个人的名字。笔者查阅 1912年版《泰西民法志》[10]发现,此书作者的中译名的确写的是甘格士。虽然如此,作者是甘格士还是克卡朴的问题实际上并不成其为问题,因为此书在版权页提供有作者的英文名。只要对照此书标着的作者英文名Thomas Kirkup和中文名甘格士便可知道,甘格士与克卡朴,是同一作者的不同中译名。这点若不加以说明,的确容易给研究者造成困扰。
第六,“《唐庆增经济讲演集》”应为“《唐庆增经济演讲集》”。
陈铨亚文中提及《唐庆增经济讲演集》。后来的诸多转述,笔者见到的,只有汪家熔的提法是《唐庆增经济演讲集》。汪家熔明确说过他未见过此书,但他对书名的提法却是正确的。其实,讲演和演讲,二者的意思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差别不大。但既然书名明明白白是《唐庆增经济演讲集》[11],它的名字如今又被广泛提及,还是纠正一下为好。
第七,“李懋庸”或应为“李懋猷”。
陈铨亚在文中说,“1920年李懋庸(季)的译本名《社会主义史》影响最大”[1]。而蔡元培在为李季译的《社会主义史》所作的序中,提到李季时说的是“我友李君懋猷”[12]。笔者粗略了解到,李季字懋猷,他还有其它名与号,但似乎并无李懋庸这个名字。未知李季的确用过“李懋庸”之名,还是“李懋庸”系陈铨亚笔误。
(二)1898年说证据不足
通过对陈铨亚的前述文章进行逻辑上的推论,对陈铨亚、汪家熔、唐宝林、王也扬提供的线索进行查证,同时参考汪家熔、唐宝林和王也扬的观点,笔者认为,1898年说证据不足。①前文提及的几处错误,从这里开始以纠正后的形式提及。
1.陈铨亚没有任何直接而有力的证据,却肯定性地给出1898年出版有《泰西民法志》的结论,存在逻辑上的漏洞
第一,陈铨亚提及,美国人伯纳尔在其《一九0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一书中说,《万国公报》的编者在1898年夏出版了第一部系统讲解多种社会主义学说的著作。陈铨亚自己也注意到,伯纳尔没有提书的名字和内容;他猜测,或许伯纳尔自己也没看过那本书,否则,伯纳尔就会把1898年的那本书而非1899年的《万国公报》视为最早提及马克思的中文报刊了。这里,问题出现了:陈铨亚分明注意到了伯纳尔之说的不确定性,也注意到伯纳尔本人也持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1899年说,却在文中以肯定语气说,伯纳尔关于中国1898年出版有第一部系统讲解社会主义学说的著作之言是“可信的”。未知何以见得其“可信”?进而,以这种事实上并不一定“可信”的线索为前提或依据,陈铨亚以肯定语气直接给出了结论:伯纳尔提到的1898年夏出版的书,实际上就是胡贻谷受李提摩太委托翻译的克卡朴著 《社会主义史》,此书以《泰西民法志》之名出版。这里的问题是:从一个线索是如何得出一个结论的?求证、说明、推论等中间环节都在这里缺失了。
第二,陈铨亚提及,《泰西民法志》如今已很难看到,只有《唐庆增经济演讲集》中偶一提及。唐庆增是怎么提的,陈文没有征引相关内容。笔者查阅《唐庆增经济演讲集》,其中是这样“偶一提及”《泰西民法志》的:
近人每谓社会主义在中国流行为五四运动以后之事实,此说殊不尽然,据不佞所知,清末胡君贻谷曾承西人李提摩太 (为宗教家极喜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之嘱,将英人克卡泼(T.Kirkup)所著之《社会主义史》(A History of Socialism)译出,以《泰西民法志》一名出版,该书在当时虽未见有何等重大之影响,然为国人研究社会主义之碻矢,可知此项主义之流入华土,非自今日始耳。[11](P124)
从这段文字看,唐庆增虽然提到胡贻谷、李提摩太、克卡泼、《社会主义史》、《泰西民法志》,却并未提到《泰西民法志》的具体出版年份;他虽然提了一个时间概念,即“清末”,但“清末”毕竟不等于1898年。
第三,陈铨亚提及,在李季译《社会主义史》中,增订者辟司在序言中说明,增订版第一至九章保持了克卡朴原书内容。《社会主义史》第七章为“马克思”,陈铨亚“相信辟司没作变动”。换言之,他推断,从原书译出的《泰西民法志》第七章也如此。于是,他引用了提到马克思的一段话,以表明1898年出版的《泰西民法志》已经提到了马克思,马克思学说因而是1898年传入的。他没有说引文源自哪里,但结合上下文判断与查阅 《社会主义史》可知源自《社会主义史》。不过,笔者查阅《社会主义史》后发现,陈铨亚的引文与原文有个别字句和标点的出入,不知他是从《社会主义史》征引而来,还是转引自别处。
在结合唐庆增的说法与《社会主义史》的序和内容的情况下,征引《社会主义史》的一段内容,表明《泰西民法志》上也有这段,这样做似乎并无不妥;而且,1912年版的《泰西民法志》上的确有这部分内容——尽管文字表述不同。但是,没有看到实物而从逻辑上进行推论,就必须考虑到一种可能性,即汪家熔提到的情况:“上世纪末除必要,如法律,政治书一般都是意译、节译”。那么,胡贻谷若是节译,“‘马克思’一节可以不译”。[3](P95-96)换言之,胡贻谷若是节译,《泰西民法志》中不存在“马克思”这一章也是有可能的。事实上,《泰西民法志凡例》中对书的翻译有这样的说明:“是书为英国甘格士先生原著,分上下二卷,都十六篇。译者就文敷陈,不参臆说,间有删汰,则以专论西事,与华人渺不相关也。”[10]这句话就明确提到,译本中删汰了一些原书内容。退一步说,从逻辑上推论,就算《泰西民法志》中译出了“马克思”这一章,它也只能说明此书提及了马克思,不能说明此书初版于1898年。
2.汪家熔和王也扬提供的材料有力地反驳了1898年说
第一,汪家熔指出,广学会1898年的年报作于当年的12月22日,其中罗列了广学会1898年所出书刊目录和各书印数、页数,包括2种期刊、3种重复版本以及48种宗教、科技、政治图书,共53种,并无“泰西民法志”或接近于“社会主义史”的书名。
第二,王也扬也指出,广学会1898年度的工作报告没有出版《泰西民法志》的记录。此外,他还指出,广学会1912年度的工作报告中有当年该会新版和再版书籍的完整目录,《泰西民法志》清楚地列于1912年新版书之中,并记有印数1000册。[5](P85)
第三,王也扬还提供了另一条重要信息:《泰西民法志》的译者胡贻谷在1917年为其老师谢洪赉(又名庐隐)撰写的《谢庐隐先生传略》一书中说过,他获遇谢庐隐先生,在1898年初,那年他十四岁,初入中西书院。一个初入中西书院学习的14岁少年不可能翻译 《泰西民法志》这样的著作。[5](P85)笔者查阅了《谢庐隐先生传略》,确认王也扬提供的这条信息无误,并认同王也扬的判断。
综上所述,陈铨亚提出1898年说,在逻辑上存在漏洞,在事实上缺乏实物支撑。汪家熔关于1898年广学会年报没有出版 《泰西民法志》或《社会主义史》的记录的考证,王也扬关于广学会1912年度工作报告将《泰西民法志》列为新版书,以及1898年的胡贻谷只是个初入中西书院的14岁少年的考证,有力地反驳了陈铨亚的1898年说。
这里特别说明一点:本文至此要说的是,到目前为止发现的材料表明,1899年是马克思的名字与学说传入中国之始。笔者所不支持的,是基于陈铨亚指认1898年出版有《泰西民法志》的1898年说。如果有其它相关确切材料被学界发掘、发现、整理出来,则马克思学说在1898年甚至更早传入中国,并非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