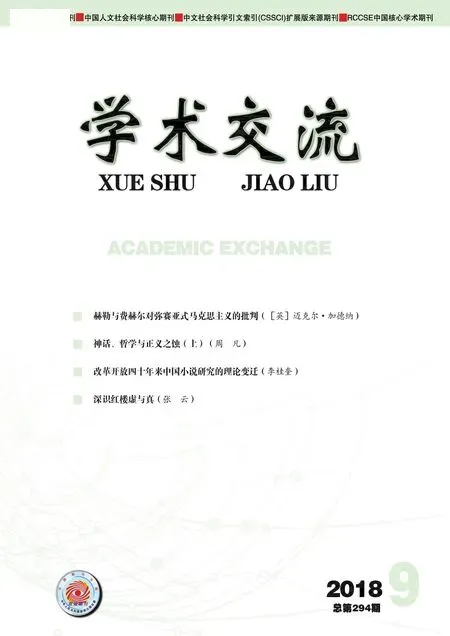西施形象与貂蝉形象比较谈
——以《浣纱记》和《三国演义》为中心
张 驰
(哈尔滨师范大学 文学院,哈尔滨 150025)
目前,学界对于西施和貂蝉的个人形象研究较多,而对两个形象的比较研究尚不多见。有的论者曾指出:“在以男权文化为基础的中国文学史上,西施与貂蝉两个美人的故事,构造了巨大的叙事张力,为美人计的讲述范式提供了丰富的创造和阐释空间。”[1]可见,对同样作为实施政治目的重要媒介的两个女性形象进行对比剖析,显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在文本选择上,《浣纱记》中西施形象刻画笔墨较多,相对较为丰满;《三国演义》中貂蝉连环计的内容较为集中,故选此两种文本为文字根据,同时以古代小说、戏曲中先进的女性文化观念的表达为主线,分析两者形象上的同中之异。
一、女性形象作为政治手段的同中之异
西施和貂蝉皆有着倾国倾城之貌,她们被当作政治手段为所谓的国家利益而牺牲了自己。这在梁辰鱼与罗贯中那里都得到了赞扬。在罗贯中笔下,貂蝉是一个集儒家美好品质于一身的女子,她在国家利益面前表现出了大义,在爱情面前克制了私欲,在王允的“美人计”中展现出来的是过人的智慧。同样,在梁辰鱼的笔下,西施的形象也无瑕疵,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对这个在国家危难之时奉献自己的女性形象进行了塑造,即便她作为政治手段而失身,作者也能对其抱有宽容的态度。从这点上看,罗贯中与梁辰鱼对于女性的看法较之他人要有着更多的先进性,他们用宽容的心态塑造了作为“谍者”的女性形象。
首先,二人皆是计谋中的直接施行者。西施是“美人计”的直接施行者,貂蝉是“连环计”的直接施行者。其次,二人姿色俱佳。夫差作为一国之主已见过无数美女。董卓也是政坛上手握重权者。西施和貂蝉以其超出常人的美貌,成功地迷住了她们想要迷惑的男人。第三,二人皆成功完成了任务。西施迷惑了夫差,越国最终战胜了吴国。貂蝉离间了董卓和吕布的关系,除掉了残暴、满怀私欲和野心的董卓,改变了东汉政权格局。
关于比较方法,黑格尔曾指出,“我们所要求的,是要能看出异中之同,或同中之异”[2]。因此,笔者在此着重论述二人的同中之异。
1.人物具有色艺双全的基本条件
《浣纱记》中的西施成长于越国诸暨若耶山下苎萝村,自小上山采苎麻,在若耶溪边浣纱。文中写道:“祖居苎萝西村,因此唤做西施。居既荒僻,家又寒微。貌虽美而莫知,年及笄而未嫁。”[3]3由此可知三点:一是西施最初是一名淳朴的农家少女,二是家境贫困,三是容貌很美。一直到入吴前始习才艺歌舞。貂蝉是王允府中歌姬,后被王允收为义女。尽管二人皆习歌舞,但貂蝉则是自幼享受优待的歌伎:“其女自幼选入府中,教以歌舞,年方二八,色伎俱佳,允以亲女待之”[3]65。可见,貂蝉近似于王司徒的亲女,生活自然是养尊处优,而西施最初成长过程中一直在农村为生活而辛苦劳作。
不同的生活环境自然会对人物产生不同的影响。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从文学艺术鉴赏(美感)来看,不同经济基础上的人们或者说出身不同阶级家庭的人,由于长期有关生活方式、教育的熏陶和影响,会产生很不相同的美感或艺术情趣。”[4]这说明通过对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成长背景的分析,可以更深地洞见人物的思想和秉性等特点,正所谓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成长环境是个体秉性形成的重要因素。这样看来,虽然两位作者给予了两个女性形象作为政治工具的基本素质,即:美貌与才干。但两者的形象表达上却有着不同。梁辰鱼笔下的西施出身平民,有着美貌与天生的聪慧,诸多美好素质集中于一人身上,这与当时的作者所在明代中后期的社会状况不无关系,面对着政治上的黑暗,作者将自己对美好事物的憧憬与期待集中于一人,而西施就是这个落笔点。而罗贯中笔下的貂蝉虽然一样美好,但却始终是儒家思想构架下的形象,所以她成长在官宦之家,少习歌舞,诗书俱佳,是一个严格按照儒家礼教成长起来的“美女谍者”。
总之,两个女性美貌与才艺形象的塑造虽展现出两位作者对于女性的尊重之意,但却因为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而使得两个形象的表达初衷有着些许不同。
2.政治动因的主动性与被动性
不论是在《浣纱记》还是在《三国演义》中,作者对于女性为国家利益奋不顾身的牺牲是给予肯定态度的。这相较于其他小说、戏曲中的西施与貂蝉作为祸国殃民的反面形象有着根本意义上的不同。此时两位作者对于女性地位予以了肯定,在作品中塑造出正面的形象,这是作者先进的女性观在文学上的一种体现。
两个女性角色在作者笔下均是能够以国家利益为先而投身到政治任务之中,但结合两位作者塑造形象时所处的时代文化背景,可见二者的政治动因却有着主动性和被动型的不同。
《浣纱记》中的西施先与范蠡相遇,初见定情,再见时范蠡却以国家为先而请西施献身。西施不允后,范蠡再次言辞恳切地乞求于她说,“国将遂灭。我身亦旋亡”,以自身的存亡来说服西施。西施“好苦楚人也”的感叹,真实地表达了她无奈而为之的心态。可见西施报效国家的意识并不是源于直接的主动,而是由他人循序引领,加以启迪,再加上大量情感因素的附加,可以说报国心与女子在爱情中的牺牲之心各有一半。
再看貂蝉,她是主动报主、乃至主动报国。《三国演义》第八回里貂蝉见王允忧愁多虑,主动积极地一再表示:“倘有用妾之处,万死不辞!”“但有使令,万死不辞”“妾许大人万死不辞”“妾若不报大义,死于万刃之下”[5]64-65。此四句回应王允皆是“万死不辞”。由此可见,貂蝉较之西施的主动性更突出,为国牺牲的决心也更坚决,作为罗贯中在儒家思想主导下而刻画出的女性形象,貂蝉的报国行为更加直接,更加彻底,缺少了西施的犹豫,这里边有着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子。
进一步比较,在计划完成的某件任务上,个体主动较之被动会增大任务的成功几率,能推动事件更快地接近成功。歌德的《浮士德》就塑造了这样一个人物,魔鬼摩菲斯特设置种种极具诱惑的环境引诱浮士德博士,但浮士德博士凭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都战胜了魔鬼。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动因的主被动性还可以显现出个体本身的价值取向和人格定位。爱因斯坦在《悼念玛丽·居里》一文中写道:“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6]从西施与貂蝉在政治动因方面的主动性来看,两者在爱国思想的觉悟性上有着明显不同,梁辰鱼对西施的塑造有着自己成长经历的烙印,西施在报国上是坚定的,但却有着私欲的存在,而对于信奉“仁义礼智信”的罗贯中来说,塑造的女性形象也必然是觉悟高尚的,以国家为重的,所以才出现西施与貂蝉在报效国家动因上的不同。
二、人物形象婚恋思想的同中之异
作为才貌兼备的西施、貂蝉二人在成为政治工具之前,均有着复杂的感情纠葛。《浣纱记》中梁辰鱼用尽美好之词描绘了西施与范蠡初识相爱的情景,这可见出作者对于女性婚恋自由选择的认可。而《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对于貂蝉的爱情观没有多着笔墨,重点在于描绘其周旋于王允、董卓、吕布之间的情感纠葛,从中可以看出貂蝉形象已经颠覆了封建传统的女性形象。这也是作者在女性观上的某种进一步发展。但仔细研究西施和貂蝉的婚恋观,两者又有着某些不同。
1.人物爱情纯粹度不同
通过《浣纱记》和《三国演义》的比较,西施形象较貂蝉形象在爱情上更生动。造成这种客观效果的原因在于《浣纱记》和《三国演义》的主题思想不同。《浣纱记》的主线有两条:一条是吴越两国的争战始末,另一条是西施和范蠡的美好爱情。而《三国演义》的主线只有魏蜀吴三国的争战,因此刻画貂蝉形象笔墨较少,亦没有对其情感给予更多的观照。
从主观原因层面看,西施和范蠡的爱情生活情景,描写最为详实的文本是《浣纱记》。范蠡“浪迹溪山”“问俗观风”和“寻真访道”之时,遇见“趁晴明溪边浣纱”的西施,对她一见钟情。然后交换定情物“溪水之纱”,互许婚嫁盟约后分别。从“赠纱订情”情节中可以看出作者对男女婚姻自主的肯定。这也是女性地位提升的表现。此后,范蠡因吴国攻打越国,不得不陪同君主入吴受辱。后范蠡因政治权谋需要,再次回访西施,请求她为国投吴,想以美人计为越国谋求政治利益。西施虽然百般不愿,但为了完成爱人的夙愿答应贡献出自己,愿意为了爱情牺牲自己。单纯从爱情观角度出发,西施爱的纯粹,她在爱情上有三个闪光点:一是用情之深。在与范蠡相遇后的第一次分别期间,西施因思念范蠡得了心病。这就足见西施感情的真挚和深厚。二是为爱而献身的魄力。为爱情将自己无私送给爱人,这已经是需要勇气了,而西施为了成全范蠡的理想,又将自己贡献给了吴王夫差,这就需要更大的魄力。三是在情感上超常的忍耐度。波伏瓦在《第二性》中谈到恋爱的女人时说道:“‘爱情’这个词对男女两性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这是使他们分裂的严重误会的一个根源。拜伦说得好,爱情在男人的生活中只是一种消遣,而它却是女人的生活本身。”[7]这就精辟地道出了女人比男人更为重视爱情。因此,女人也更难容忍在其他自己并不爱的男人身边生活。而西施到达吴国后,要隐藏起对范蠡的爱,与夫差生活在一起,这得需要多么大的忍耐力啊!《浣纱记》第四卷第三十四出《思忆》中西施道出了自己的心声:
明知勉强也要亲承受。乍掩鸳帏。疑卧虎帐。但带鸾冠。如罩兜鍪。溪纱在手。那人何处。空锁翠眉依旧。只为那三年故主亲出丑。落得两点春山不断愁。[3]103
可见西施为了范蠡的政治理想,一再压抑自己的真情感,只为了成全心爱之人的理想,这样的付出是真实的,所以容易受到伤害,但也是纯粹的,值得人们尊敬。在梁辰鱼笔下,拥有纯粹爱情观的西施形象也就具有了超时空的文化价值。
貂蝉的爱情对象为吕布。《三国演义》之前有的文本将其二人视为一对情侣。元杂剧《锦云堂暗定连环计》中,貂蝉对王允说:“灵帝将您孩儿赐与丁建阳,当日吕布为丁建阳养子,丁建阳却将您孩儿配与吕布为妻。后来黄巾贼作乱,俺夫妻二人阵上失散。”[8]在《三国志平话》中,貂蝉曾向王允自我介绍:“贱妾本姓任,小字貂蝉,家长是吕布。自临洮府相失,至今不曾见面,因此烧香。”[9]这表明貂蝉与吕布之间存在着爱情。而以《三国演义》文本作为落脚点,就可发现貂蝉的地位仅仅是作为一种手段或工具来推动政治格局的变化。这里突出了貂蝉的政治作用,弱化了貂蝉的情感,吕布与貂蝉起先并不相识,而是到连环计的第一环节,即王允将貂蝉引见给吕布,二人才相识,可以说在《三国演义》中貂蝉的爱情被弱化、被忽略了。这与小说的结构和作者的写作意图有关,没有考虑女性角色爱情维度,也从另一个层面看出罗贯中的女性观相较于梁辰鱼还有一段距离。从另一个角度看,貂蝉的爱情只存在于政治人物中,她忠于的是她的大义,爱情在她心中的地位并不突出,更谈不上有多纯粹。
2.人物形象与爱情对象精神统一程度不同
西施的爱情对象是范蠡,貂蝉的爱情对象是吕布。两名男子的共同点有二:一是从男子的身份来看,范蠡是越国大夫,吕布是汉末武将,二人皆是乱世中的佼佼者。二是从爱情的发端来看,范蠡与西施初相遇,即一见钟情;吕布第一次见貂蝉,毫不掩饰对她有情。从这一点来看,梁辰鱼与罗贯中均为两个女性形象铺垫出一条唯美的爱情开端,但爱情中能否与伴侣达成思想高度的一致就昭示了两个人物形象的同中之异。
(1)与爱人理想人格统一程度不同。西施与范蠡的爱情产生在实施美人计之前,尽管她的初衷是为了所爱之人而贡献出自己,但她在实行美人计的同时已经间接地提高了自己的人格高度,与范蠡一起拥有了志同道合的崇高理想。范蠡无疑选择国为先、家为后,虽然西施被动地跟随着范蠡这一思想,但这依然赋予了西施道德上的光辉。同时,这种共同的追求成为她与范蠡志同道合的思想纽带,并且赢得了范蠡的尊重,这些元素为最后范蠡决心与她共度余生增加了筹码。
反观貂蝉与吕布,吕布杀董卓的动机并不是为汉室除奸,而是因与董卓争貂蝉所导致的矛盾不可调和才愤而反主,他此前也杀过同为义父的并州刺史丁原。他为了一己私利,罔顾忠义,因而有“三姓家奴”之名。而貂蝉却为主分忧,为国担责。故吕布没有貂蝉的人格高度,二人不能站在同一个道德层面上,更不能达到精神层面上的统一。由此,西施相较于貂蝉无疑是幸运的,她最终拥有了与自己“并肩作战”的精神伴侣,而貂蝉却是“孤独行走”的“爱情弃儿”。
(2)男子付出的情感浓厚程度不一。范蠡第一次见到西施就倾心爱慕。但他后来却一再请求西施实施美人计,将心爱的女人献给其他男子。这虽然成就了范蠡的报国之愿,却在情感层面上减少了光芒。从结局来看,西施与范蠡拥有了归隐的幸福。但值得注意的是,范蠡在“泛湖”之前曾这样说:“功成不受上将军。一艇归来笠泽云。载去西施岂无意。恐留倾国更迷君。”[3]131他带走西施的意图在于担心国主勾践会被西施的美色所迷惑,而并没有说是为了爱情。从情感角度来看,范蠡的爱情程度尚处于较浅层次。
而貂蝉从一出场,作者就没有对她的个人情感作过多描写,她只是全力以赴去完成政治任务,在《三国演义》中不涉及她的主观情感色彩,但吕布对貂蝉的情感,书中的描述则较多。当吕布知晓貂蝉已侍奉董卓一夜,“布大怒”;在凤仪亭里,看到貂蝉哭泣时,“布羞惭满面,重复倚戟,回身搂抱貂蝉,用好言安慰。两个偎偎倚倚,不忍相离”[5]69。后董卓要载貂蝉去郿坞时,王允问吕布,为何在此长吁而叹,吕布答道:“正为公女耳。”[5]72吕布在王允安排下诛杀了董卓,急切地去郿坞寻回了貂蝉:“吕布至郿坞,先取了貂蝉。”[5]76可见,在吕布心中,将貂蝉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为她背叛了义父,是爱之深的体现。较之范蠡,更为动情。但值得注意的是,范蠡是文士,而吕布是武将。武将在情感的表达上较为直接,更为勇敢。而文士在谋略上较为智慧,并且有纵览大局之眼光。因此,二人的情感处理方式和用情程度有着较大的区别。结合各种因素来看,吕布与范蠡对于各自爱人的相爱程度不一,排除他们均带有的利己性因素,吕布的爱显得更加浓烈,范蠡的爱却显得较为平淡。
三、人物结局折射的文化内涵不同
在不同的文本中,西施与貂蝉的结局也有着诸多版本,也折射着结局背后隐藏的时代文化。而综合西施和貂蝉的母题研究情况来看,与结局不同随之而来的是世人各类各样的道德评价。《墨子·亲士篇》载: “ 西施之沉, 其美也。”[10]这里明确指出西施被沉的原因是美貌,但未道及其被沉的具体缘由。“后检《修文御览》,见《吴越春秋·逸篇》云:‘吴亡后,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终。’乃知此事正与墨子合。”[11]这就说明是越国主导了西施的生死。到《东周列国志》中:“勾践班师回越,携西施以归。越夫人谮使人引出,负以大石,沉于江中。”[12]这也是西施“沉江”,不过沉江行为的实施者已明确为惧怕她再亡一国的勾践夫人。这逐步丰富的西施被沉的经过,突显的是女子祸水论影响的扩展和加深。在《汉书·孝武李夫人》中有形容女人美貌的诗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13]女子的美貌不仅能使人折服,更可倾覆一个国家。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远古的神话传说、历史演义和民间故事,妺喜、妲己、杨玉环、陈圆圆皆是红颜祸水故事的主角,这是当时男权社会下,将男性的错误乃至失败归咎于处于弱势群体的女性的结果。而《浣纱记》中西施被礼迎返越,却受到了勾践、越夫人、范蠡、文种的“拜谢”。她虽然以美色魅惑君主,但她为自己国家作出了贡献,因此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优待。这不仅是女性地位的提升,也是对女性价值的公允评价。
《三国演义》中貂蝉在完成其政治任务以后,并没有得到当时英雄豪杰的认同。纵观貂蝉的结局,主要有三种,即不知所终、团圆、惨死。其中明人赵琦美《派望馆妙校古今杂剧》收录三国故事杂剧二十一种,其中就包括《斩貂蝉》一剧,剧中貂蝉的死因就值得注意。吕布败亡,张飞俘获貂禅,将她送给关羽。关羽夜读《春秋》,看到书中所写红颜祸水导致误国亡国的史事,便杀了貂禅。此戏后来演变成:关羽敬重貂禅,要释放她,可倚墙的青龙偃月刀自己倒下来,将貂禅误杀;或者是改成关羽以刀斩貂禅的影子以代其身,却失手致貂蝉死。其悲惨结局反映了世人对貂蝉这一“红颜祸水”的诟病,甚至忽略了她曾周旋于王允、董卓、吕布、曹操、刘备、关羽诸多风云人物之间的智谋与勇气。
西施和貂蝉的结局各有不同。《浣纱记》中的西施在完成报国大义后,与范蠡双双归隐。在《浣纱记》中,西施过的是一种田园归隐的生活,有着一丝丝的神秘感,也有着风浪过后的平静感,充满着理想主义色彩。这样的结局与作者梁辰鱼的入仕之路不顺、继而转向理想化的生活有关,所以作者尊重西施,就算其最终失身也能怀有宽容的态度给了她一个梦想的归宿。这也可视为作者先进女性价值观的体现。
《三国演义》对貂蝉形象的刻画主要集中在第八回和第九回里,貂蝉在完成报主大义后,虽跟随于吕布,但在吕布败亡后却下落不明,有人形容貂蝉为“儒家文化的牺牲品”,因为任务的失败,貂蝉在罗贯中笔下没有一个明确的结局,这不得不成为一个缺憾。究其原因,也在于男权社会的价值观,“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君臣之间尚且如此,更何况是处于卑贱地位的女性。罗贯中在女性观上较之梁辰鱼还是稍为逊色,他给予貂蝉一个悲剧命运也足以证明,在男权社会中,文人们虽然有着先进女性观的某种觉醒,但是真正能够彻底觉醒者却寥寥无几。
四、结语
自古有“红颜祸水”之说,但在古代小说中也存在一些“异类”,常常会给予女性形象一些宽容。作者这种宽容的女性观在当时社会文化背景下是十分可贵的。形成这样女性观的原因很多,大致可分为主观原因与客观原因两种情况。
客观原因:梁辰鱼与罗贯中为了其作品的架构,为了人物塑造、情节设置或者主题表达而为之。西施和貂蝉分别是两部小说中美人计得以实施的重要角色,给予她们更多展现自我情感和思想的机会是为了丰富整个小说的构架,实属角色需要。
主观原因:梁辰鱼的《浣纱记》把一个传统故事重新赋予了浓重的政治新意,将吴国的腐朽,越国的奋进,表达得淋漓尽致。这段历史是离不开西施的,但是给予其宽容的态度不是初始即有,特别是在作者早年所著《鹿城诗集》卷九里的《吴宫曲》中,他认为西施是使吴国灭亡的罪魁祸首,但是到了后期,由于他痛恨明朝后期的腐败与昏暗,自己的人生也经历了三次远游,这才使自己的女性观有了改变,从否定继而转向肯定。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虽然仅以有限篇幅描述了貂蝉,但是也从儒家角度赋予貂蝉深明大义、才貌双全、坚忍不拔的品质。
从中我们能够看出梁辰鱼与罗贯中对他们所刻画、塑造的女性人物均是有着尊重宽容色彩的,但是因为二者所处环境以及个体的差异,导致两人在具体文本描写中还存在着同中之异。相比之下,梁辰鱼的宽容度更高。从文本来看,西施在《浣纱记》中担任主角,因为作者对于女性的态度有从彻底否定到充分肯定的转折,而罗贯中对女性角色形象的描写则限制在儒家思想的框架下,单纯地赋予貂蝉仁义品格,在小说中仅有短短的出场,没有阐述更多的结局和评价,可见梁辰鱼的宽容度更深,更具有觉醒意识,更有反思的深度。
简而言之,梁辰鱼对于女性的宽容出于内心的感悟,自发性较强,而罗贯中对于女性的宽容虽然有着觉醒意识,但基于《三国演义》本身来看,更多的是为了完成小说构架与故事情节的丰富,女性的宽容观念虽然存在,但并不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