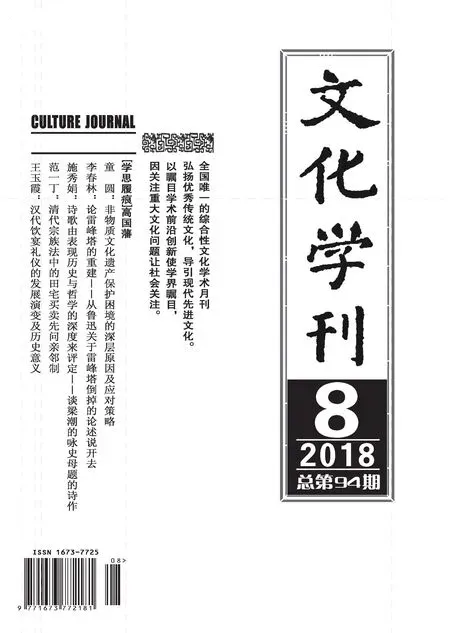解读抗日女英雄的成长之谜
——评徐光荣的《赵一曼》*
李 帅
(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辽宁 沈阳 110031)
徐光荣的英雄人物传记《赵一曼》出手不凡,开篇即以“赵一曼从哪里来”设置悬念,牢牢抓住读者的阅读心理和对赵一曼急于了解的心理需求,引领读者迅速进入女英雄赵一曼的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并通过破解赵一曼的身份之谜、成长之谜与忍受酷刑仍然坚贞不屈之谜将白山黑水间的抗日女英雄形象塑造得血肉丰满、栩栩如生。
一、档案追踪破解身份之谜
赵一曼的身份之谜来自两个障碍,一是赵一曼的工作性质决定的。作为一位伪满时期的抗日英雄,她必然要隐瞒身份与敌人周旋,以确保不暴露,假身份的使用在迷惑敌人的同时也使我们在追踪英雄的来龙去脉时增加了难度,甚至一度赵一曼的家人都不知其身在何处。二是敌伪档案的失实记载。徐光荣以先破后立的方法逐一拨开迷雾。比如对于敌伪报纸的报道,肯定了其中关于赵一曼信仰的可信性,批驳了关于她籍贯与经历的部分;对于敌伪档案中大野泰治和林宽重对赵一曼的审讯,也甄别其中的真实与虚假。这样的写法,一方面彰显了赵一曼所处环境的错综复杂,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她同敌人周旋时的智慧,在增添阅读兴味的同时,赵一曼的真实身份也逐渐水落石出。
而20世纪五十年代电影《赵一曼》的上映,使人们在赞赏赵一曼的英雄壮举之时,也急于了解她的身世经历。正当一切显得扑朔迷离之际,徐光荣交待了赵一曼二姐李坤杰的寻亲信函,年龄、经历、照片的逐一对照,终于认定李坤泰就是赵一曼,破解了数年前关于赵一曼身份的难解之谜。牢牢抓住读者心理而又顺应读者心理去追踪档案,增强了《赵一曼》的可读性,使年代久远的英雄故事有了现实感,缩短了读者与英雄人物之间的距离,赵一曼就不仅仅是一个传奇,反而如同我们身边的邻家女孩一般亲切自然。这种题外故事的设置,虽寥寥数笔,却消弭了时空界限,使纪念馆中的人物塑像、口耳相传的英雄故事、档案中的文字描述、亲人眼中的女儿、妹妹、爱人、母亲形象瞬间融会贯通,在人们心目中树立起全方位、富有立体感的人物形象,在伟大中见出平凡,在平凡中又烘托出伟大,血肉丰满的普通人的形象同坚贞不屈的英雄形象终于得到完满的融合。
历史人物传记的难点在于不能跟踪采访,只能通过档案、口述等现有资料和文学想象的结合加以还原,真实性是其突出问题。徐光荣解决这一难点的办法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有机统一。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是历史人物传记无法避开的一个问题。历史真实指的是基本史实的真实,如果把历史人物比作一棵大树的话,那么主干必须真实,而细枝末节可以虚构;艺术真实筑基于艺术虚构之上,体现了“虚写史实、实写精神”的原则,是舍弃细枝末节对人物精神的精准把握。历史真实重在大事件的真实,艺术真实强调人物精神的凝练与升华。这样,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就需要一个巧妙的切入点,而《赵一曼》这部小书之所以成为少年红色经典故事之一,就在于徐光荣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切入点——身份之谜。以电影《赵一曼》的热映带出赵一曼的身份之谜,以身份之谜带出两条线索:一条是赵一曼二姐李坤杰的寻亲信函(赵一曼的家人)以及原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部长何成湘和原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冯仲云的确认(赵一曼的组织关系);一条是原满洲国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大野泰治和伪警务厅长官、特务头子林宽重的审讯报告(赵一曼的敌人)。又由前一条线引出赵一曼的成长之路,后一条线引出赵一曼的英勇抗敌、不幸被俘、坚贞不屈的英雄事迹,由此奠定了这部传记的结构。
身份之谜的破解消弭了时间的界限,拉近了人们和英雄的距离。从出生到就义是生的历程,电影的热映、纪念馆的修建和后人的瞻仰是后世的影响,英雄的精神绵延不绝,赵一曼同志虽然牺牲了,但是她的精神不死,至今仍然是影响少年儿童的精神力量。正面描写和侧面烘托相结合以及首尾呼应、巧设悬念、环环相扣的小说笔法的运用,使赵一曼的英雄形象呼之欲出。
二、儿童视角破解成长之谜
尽管英雄的形象呼之欲出,徐光荣却放缓了叙事的节奏,并没有直接将赵一曼的英雄壮举加以描摹,而是将重点放在了英雄的成长轨迹上。这就避免了英雄人物传记的弊端——人物塑造的类型化和模式化。高、大、全的英雄形象塑造会削弱英雄人物的人格魅力,显得空洞而苍白无力,对英雄的人为拔高会使其脱离现实,将英雄神化又不符合历史的客观规律。因此,对英雄人物形象的尺度把握和分寸拿捏显得尤为重要,徐光荣巧妙地选用了儿童视角,并对赵一曼的成长历程浓墨重彩。
一个人物的成长,分为身体成长、心理成长和精神成长。徐光荣对赵一曼的成长描述兼具三者。关于身体成长,主要从童年的无忧无虑、自由自在、茁壮成长方面进行叙述,却并不平淡无奇,主要得益于儿童视角的选择。儿童视角是小说家根据内容需要所采用的叙事视角之一,指的是“借助于儿童的眼光或口吻来讲述故事,故事的呈现过程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的特征,小说的叙述调子、姿态、结构及心理意识因素都受制于作者所选定的儿童的叙事角度。”[1]作为家中的幺女,小时候的赵一曼同其他的儿童一样天真烂漫、顽皮可爱,也曾戏弄老师,与大自然的虫草为伴,度过无忧无虑的时光。黑花蝴蝶、蓝眼睛的大蜻蜓、在课堂上乱叫的知了、戏谑教书先生的螳螂充满着童趣。但是健康的身体成长却遭遇了传统习俗的戕害——被迫缠足。徐光荣没有直接言说缠足的危害,而是从一个孩子的切身体验和眼光去重新审视缠足,带着陌生化的视角重新看待这一古老的习俗,当一圈一圈裹脚布将健康的双脚缠裹变形,当赵一曼体验到钻心的疼痛,当她看到母亲因缠足而行动不便、以爬代行时,她的反抗意识和倔强性格开始逐渐彰显,在被迫裹脚时,她说:“不,我就不!”“你要再给我裹脚,我就不活了!”[2]这些简单、直接、稚气的语言描写,展现了儿童独特的话语表述方式,也展现了赵一曼骨子里的倔强,最终说服了爱她的母亲。
但当父亲病亡,接替父亲成为家长的大哥不但禁止她上学,还烧她的书,甚至希望她早日出嫁时,赵一曼口吐鲜血,烙下了病根。从儿童的思维方式看,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徐光荣在本书中不断在全知视角和限知视角间转换,少年时吐血为后文赵一曼健康状态堪忧埋下伏笔,也为她被俘后受到敌伪对其身体肆虐的摧残做了铺垫。心理成长是与身体成长相伴而生的。通过对缠足的抗争,赵一曼明白了旧习俗对女子的戕害,吐血的经历,让她领悟到旧家庭对女子的限制,正是因为她自己的切身经历,使她对中国妇女的不幸遭遇产生了深切的同情并愿贡献一己之力,这也是她走上革命道路的原初动力。徐光荣的儿童视角是一种叙事策略,不但充满生趣且真实自然,易于被少年儿童读者所接受,也借此透视赵一曼的心理成长过程,以此展开对英雄成长轨迹的追踪,揭开了英雄的神秘面纱,展现了赵一曼原生态的生命情境和生存世界。
三、关捩点破解忍受酷刑坚贞不屈之谜
如果说身体成长和心理成长在人的成长过程中是具有普泛性的成长阶段的话,那么赵一曼所获得的精神成长则是她成为英雄人物的关捩点。所谓精神的成长,指的是知识的学习和思想的启蒙,最重要的是树立远大的志向和坚定的信仰,从而提升一个人的精神境界。她的精神导师则是那个“奇怪的大姐夫”,引领她学习知识、启蒙思想、走上革命的道路,成为“扎根在心灵上的火种”,从而转化为一股强大的精神动力。除了赵一曼的精神成长,书中的另一重头戏就是赵一曼被捕后的坚贞不屈,面对敌人的非人性酷刑,赵一曼没有屈服,是什么让她能够死守党的秘密而忍受极刑?这与她成长历程中心中的“火种”密不可分,也与从小到大养成的倔强性格、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相关。
从传记文学的角度而言,这样的事实描述,就是一种“传记事实”。所谓“传记事实”,“狭义地说,是指传记里对传主的个性起界定性作用的那些事实。它们是司马迁所说的‘轶事’,它们是普鲁塔克传记里的‘心灵的证据’,它们是吴尔夫笔下的‘创造力强的事实,丰润的事实,诱导暗示和生成酝发的事实’。简言之,传记事实是一部传记的生命线。”[3]徐光荣准确地把握住赵一曼身体成长、心理成长与精神成长的生命线,将她成长为一名坚强的战士和优秀的领导者归因为成长期信仰的形成和信念的树立,也是她忍受非人酷刑而始终坚强不屈的关捩点,如果没有对成长历程的揭秘,很难使当代的读者对抗战时英雄人物的坚强意志加以理解。英雄的成长历程符合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也是徐光荣行文的内在逻辑,还与徐光荣的传记文学创作范式息息相关。纵观徐光荣的传记文学作品,无论传主是烹饪大师刘敬贤、科技帅才蒋新松,还是国宝鉴定大师杨仁恺,他总是侧重追踪传主的成长历程,并选取那些对传主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传记事实”加以浓墨重彩地描绘,从而写出传主的精魂。
《赵一曼》既是一部传记文学,又是一部儿童文学,还是一部英雄传奇,写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同时,又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养料。从接受心理学的角度讲,读者是一部作品得以成为经典的关键所在,而徐光荣显然抓住了受众的心理需求,让一部弘扬主旋律的红色英雄故事成为经典,同时成为畅销书,这不能不说是作者对传主精魂的准确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