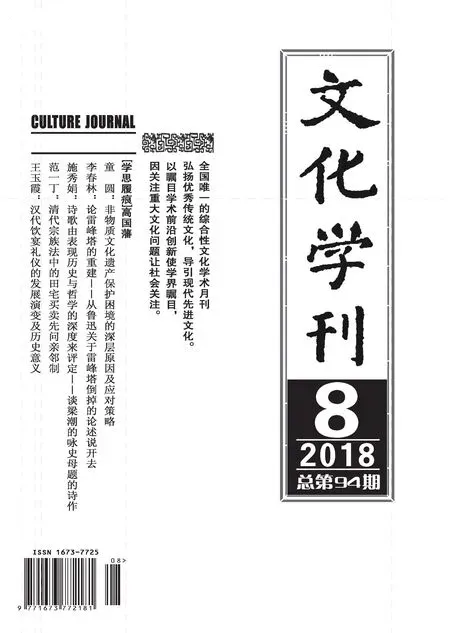论肖江虹小说中的底层叙事
孙晓楠
(辽宁师范大学,辽宁 大连 116033)
一、底层出身与独特的底层生活体验
底层意义的感悟是肖江虹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他“是在乡村完成了自己心灵的原始构建”[1]。肖江虹生于农村,他在贵州一个人多粮少的边远闭塞之乡整整生活了十五年,父亲是一个乡村教师,由于父母平时很忙碌,所以对他的童年约束的比较少,基本属于放养的状态,不受约束有不受约束的好处,肖江虹由此拓宽了自己的精神空间,他脑袋里总是会浮现出许多稀奇古怪的想法。放牛的时候会出现天马行空的想象,看见邋遢的人会引发近乎荒诞的想法,整日整夜地遍地乱跑,就让他和那片土地建立了质朴但日渐深厚的情感。如今,一旦空闲下来,肖江虹就会到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听老人们回忆往昔那段看似平淡却弥足珍贵的岁月,风不经意地掠过村庄,烈日下苦蒿的味道仿佛就在我们身边,他小说里的场景和人物,几乎都与那片土地有关,只要想到这些情境,他就特别来劲。因为肖江虹从小就生活在农村,他了解底层人物,热爱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的日常生活并能通过其作品传达底层人物的喜怒哀乐。正是这种独特的亲身经历,成了他心灵的原始构建和创作源泉,也给他的小说创作增添了底气和色彩,所以也使他的创作道路走得很畅通。
二、善良:底层人物的自我消解
世界性的文学母题之一:苦难,对当下众多底层写作中的故事人物做了定义和标记。“作家在创作中通过自己的情感,以及学到的知识,将其融合起来,形成作家自己对苦难的认识,在苦难中,人不光是苦难的载体,更是苦难的承受者,通常作家在文学的创作中,通过苦难者的形象,展现苦难者在面对困难时的态度,展现了苦难者的性格和苦难者的命运体验”[2]。但是有的作家在写底层人物悲惨命运时,会制造大量的凄惨故事或走温情路线感动读者,让读者读后落下两滴清泪,要么就站在高处,俯视底层人民生活的到底多么困苦,吃不上饭,穿不上衣,村里的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都缺少陪伴,既可怜又悲惨,这类的底层叙事大多会拿“苦难”当成一个亮点来吸引读者的关注,而这种写作态度不但不能给文学作品带来文学价值,而且也不会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最终被人们遗忘在历史的长河中。
肖江虹的作品同样记载了与底层人物息息相关的种种苦难,不过肖江虹是以一个全新的角度描述苦难。“他的小说也关注底层,也是写了些落伍或落难的人,但是他的注意力不是放在‘写苦难’上——这种‘写苦难’无非是表现‘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而改变的客观现实’——而是放在了写被苦难遮蔽的世道人心,写那种被忽略、被抹杀的‘主观的现实’——心灵的真相。”[3]他用人心的善良来包容悲剧的内涵,比如《当大事》中,松柏老爹去世,全村的老少出来帮忙,在这些小说中,肖江虹再现了底层人物的苦难生活,诠释了他们的悲剧命运。《天堂口》的故事发生在火葬场,这里的老火化工范成大每次都给客死他乡的人整理遗容,对死者充满了悲悯和尊敬,凭借着他的善良,把不受人尊敬的小事做成了“大事”。
在肖江虹作品中,善良是他故事人物面对苦难生活时表现出的一种自我消解式的态度。在《当大事》中他直接面对乡村的现实困境,描写了受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原本一个自给自足、充满朝气的村庄,荡然无存,年轻人纷纷涌入城市,村子里只剩下孤寡老人和小孩子,松柏老爹突然离世,把村里的老人给弄得措手不及,通知进城打工的松柏回来办理丧事,但松柏却以“假不好请,回来一趟,位置就没有了”,拒绝回来办理丧事,从小说中可以看到,传统的道德观念日渐淡薄,人伦关系的冷漠断裂,于是只能由村子里剩下的老者操办丧事,我们看到,六个老头艰难地把松柏老爹抬出来,由于松柏老爹身体变得僵硬,必须把身体放平才能盖上棺材盖,接着七个老者抬磨盘把松柏老爹身体压平,然后又有十多个老者移棺材,请来的道士班子,由原来的八个人变成了四个老头道士,四个年轻的道士也进城里打工了,松柏老爹的下葬地在一个山坡上,山坡上有无数的沟沟坎坎和满山的荆棘树,村子里的老人因为体力有限不能把棺材抬到下葬地,最终这些老者商量把松柏老爹在屋子旁边埋葬了。在这种种困难面前,肖江虹并没有表现出控诉和抵制现代城市文明的极端情绪,我们只看到了底层人物在遇到问题时,他们之间的互帮互助,感受到了他们善良而纯朴的人性光辉,原本充斥在文本中的苦难色彩被这种善良的品质给冲淡了。
三、丰富的底层叙事题材和叙事内容
肖江虹的小说不仅刻画了众多的底层人物形象, 而且蕴含着丰富的叙事题材与叙事内容。
《百鸟朝凤》这部小说以唢呐为线索,通过底层人民的视角展现了在时代的大环境下农村艺人的苦难形态。《百鸟朝凤》讲述了游天鸣向唢呐师焦师傅学习吹唢呐,在刚开始学习吹唢呐时并不顺利,游天鸣每天在河边用芦苇吸湖里的水,游天鸣的资质并没有蓝玉好,但是因为游天鸣的人品好,在未来更能守住唢呐这门手艺,所以师傅把班主交到了游天鸣的手里,学艺成功的游天鸣接手了焦家班,在无双镇开始了游家班的生意,好景不长,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西方洋乐队的进入,中国的传统手艺、价值观念被打击的一蹶不振,本土的唢呐队不受欢迎,游家班人心涣散,所以游家班有的人选择进城打工。游天鸣和游本盛不想游家班就这样解散,但仅凭个人的努力聚拢游家班,也无能为力,这是时代发展,是大势所趋。唢呐最后的悲剧,不仅仅是一个时代发展的悲剧,更是时代变迁的写照。由于受到现代文明的巨大冲击,我们甚至连传统的手艺都守不住,这正是一个时代的可悲之处。
都市化进程改变了大批农民的命运, 他们无法再按原来的轨道生活, 开始从农村走向城市, 寻找新的生存空间这一空间的转变不仅意味着生活方式的转变、身份的转变, 由此还带来了文化的转变、精神的转变, 生存的痛苦、寻找的艰难灵魂的麻木、被歧视被遮蔽的屈辱都成为“ 底层文学” 反复抒写的资源[4],在底层文学中都市仿佛是一个万花筒,它在向生活其间的人们提供无限可能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吞噬着人们的良知和道义,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乡下人进城”是一个非常显著地社会现象,进城的多是青壮年,农村中就留下一些孩子,孤寡老人,留在农村的这些底层人物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肖江虹的《蛊镇》就触及到了这些问题。蛊镇是个闭塞的村子,“在王昌林的记忆中老人常黑着脸告诫,不要轻易越过豁口,一线天那头有吃人的妖怪,红头绿面,口若血盆”[5],可胆子大的娃娃还是越过了豁口,走出了一线天,眼光和见识随着脚步一起开阔,原来一线天外面并没有祖先们说的那么可怕,相反外面的世界与农村相比很精彩,于是拿着蛇皮袋子进城的青年人就越来越多,他们抛弃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到城市中去追逐名利,在乡村中只留下一群没有劳动能力的孩子和一些孤寡老人。青年人王四维开始在城里出轨,他轻易就将自己对妻子的忠诚抛却脑后。而在当时还很封闭的中国农村,丈夫是天,天塌了,赵锦绣也只能通过她自己的方式挽救婚姻,于是她托王昌林制了“情蛊”,用来抑制丈夫的性欲,但是赵锦绣太过心急,用药剂量过大,导致王四维从此变成了“太监”。王四维最终被情人抛弃,心如死灰,从脚手架上掉下去摔死了。《蛊镇》这种关照底层的叙事,“总是在提醒我们故去的一切或许正以某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抚慰着现存的生命旅程而不至于遗忘了根脉里的那些朴素悠远的生存记忆,也正是在这个维度上,《蛊镇》中感性的乡土想象在其浪漫从容的审美意识之外兼具了观照现实的底蕴”[6]。
“他站在老百姓这一头,站在生活中的弱者这一头”[7],小说《我们》写了关于矿难的事情,哥哥徐老大曾被埋在矿洞中,虽然断了一条腿,但也成为那一次矿难的唯一幸存者,其弟徐老二为了生计也上了煤矿工作,平时弟弟都会在约定的时间给家里打电话,但现在已经几个月没消息,于是徐老大到煤矿去找弟弟,弟弟的矿友不敢说出实情,还在煤矿办公室把他毒打了一顿。在拉煤司机和其相好的照顾下,徐老大才免于一死。再后来,他找到矿老板在县城的家,徐老大是一个善良的人,他本意只是想询问弟弟的下落,并没有打算把矿老板一家杀害。当徐老大确认弟弟已经死后,他要求煤老板把弟弟的尸体挖出来,给母亲一个交代,没想到最终却被赶来的狙击手击毙。本来只是想要获得生存和正义,到头来他却连自己的生命都葬送了。
在小说《内陆河》中描写了底层妇女的生活困境。主人公琼花的男人在矿难中去世,家里只剩下公公婆婆,并留下一大笔抚恤金,琼花在家里没有主动权,连日常生活穿衣服买鞋都受公公婆婆的“限制”。丈夫去世后,作为一个正常的女性,琼花也渴望得到男人的呵护和关爱,但是公公婆婆的存在却让她无法成全自己,找寻新的幸福。于是她只能把所有的悲伤和无奈化解在繁重的劳动中,变成一种无声的反抗。“冷静的审视起来,崇尚仁义礼智孝风化、注重公序良俗的传统伦理,是无比残酷的,强权的甚至狰狞的”,以上种种,都对生活底层人民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肖江虹小说写出了众多底层民众。底层是他的人生的财富,在关注底层善意而温暖的写作情怀中,肖江虹把自己的文心和匠心相融合,肖江虹认为“无论文学作品还是影视作品,不管是描写黑暗还是歌颂光明,创作应是有温度的,做文学的人,一定要用善意的眼光看世界”[8],我们在他的作品中也确实感受到了这种温度,他的作品使我们对底层人物的生活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同时也丰富了底层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