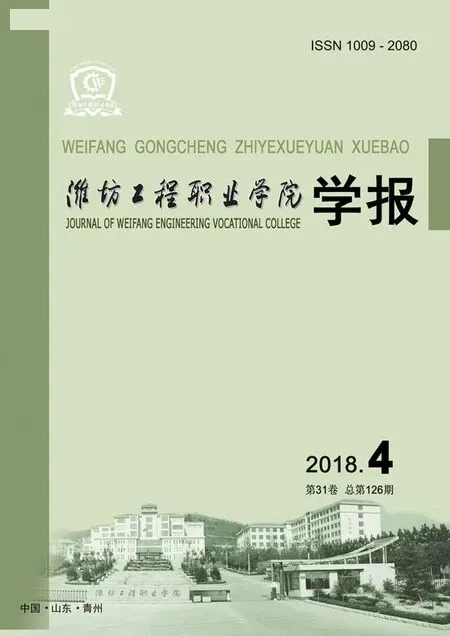从《古文辞类纂》所选曾巩文看桐城派对曾巩的接受及发展
陈 燕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昆明 650500)
曾巩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文章虽不像七大家流传广泛,但也备受朱熹、归有光等人的推崇。清代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把曾氏文章奉为圭臬。桐城派作为清代一个重要的学术流派,在中国学术史上影响深远,他们有自己的理论主张,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就是桐城派的理论实践,下面就从《古文辞类纂》对曾文的选取来看桐城派对曾文的接受及发展。
一、以文论道——义法接受及发展
道在古代文学中有多重解释。而曾巩文章体现的道主要是儒家所主张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古文辞类纂》中所选曾文主要是序体和记体散文,两种文体都有论道体现。
(一) 《古文辞类纂》所选曾巩序体散文中的论道体现
《古文辞类纂》所选曾巩序体散文大概有10多篇,集中体现了曾巩的先王之道。《〈战国策〉目录序》驳斥了刘向所认为的“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1]105的观点,进而阐述了儒家所尊的先王之道德因时适变,无疵无弊,远胜于战国游士之说。他还认为刘向肯定游士邪说是“惑于流俗,不笃于自信”[1]105的表现,而孔孟始终遵守先王之道是“不惑于流俗,笃于自信”的表现,通过两者鲜明的对比,也可以看出曾巩是尊于儒家正统思想的,体现了他“法”可异而“道”不变的政治观点。《〈战国策〉目录序》围绕先王之道无弊无害立论,首段简要叙述战国策的基本情况,随后见势批评战国之说的弊端,接着又花大段文字详说先王之道是本,接下来笔锋一转,大力列举战国邪说的害处,但也是为了阐明先王之道的尽善尽美,可谓详略得当,宾主适宜,最后再发出战国邪说应被极力禁止的号召。
其实不仅《〈战国策〉目录序》这一篇文章言说先王之道,《古文辞类纂》所选曾巩的很多文章都是以文论道的。《〈列女传〉目录序》对刘向的《列女传》进行辨别校正,说出刘向写《列女传》缘由,即正风俗,谏君王,进而阐发自己对女子与政治的思考。明代茅坤说:“子固诸序,并各自为一段大议论,非诸家所及,而此篇尤深入,近程朱之旨矣。”[2]234茅坤所言不虚,在宋明理学兴盛的影响下,宋代文章多议论,曾巩的文章也不例外,文章首先交代《烈女传》的基本情况,用的篇幅颇长,道出了作者对《列女传》亡佚深感惋惜,接下来第二段才是他的着力点,即列女之大功用——王政必自内始,内即列女。列女的善恶关乎国家兴亡,后面文字全部关乎此句,大力着墨来论述他的先王之道,可谓鞠躬尽瘁矣!自古提倡的儒家伦理道德也是程颢、程颐、朱熹所提倡的,所以茅坤说他文章的旨意接近程朱。
(二) 《古文辞类纂》里记体散文的论道体现
《古文辞类纂》里对曾巩的记体散文收录也比较多,共有10篇。很多大家也很推崇他的记体散文。孙琮在《山晓阁曾南丰文选》中说:“八家中,子固独长于学记。”[3]181《宜黄县县学记》道出了古人的学是为己之学,重在修身,康熙在《御选故渊鉴》说此篇“昌明博硕,无非经籍之腴润,诸学记中罕见其匹。”[4]301朱熹说“说得古人教学意出。”[5]3314康熙自幼对儒家学说充满浓厚兴趣,认为“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疲”[3]30,对曾巩的修身之文,自然赞赏。朱熹也是先王之道的阐发者,对曾巩的正道文章也极为欣赏。《墨池记》也是一篇以文论道的文章,从墨池故迹写起,指出王羲之的书法造诣并非“天成”而是“以自立自致”,最后推出学之不可少,要深造道德,学不可废。以墨池之水引出王羲之书法之妙绝,然意不在此,最后勉学先王之道才是文章的着力点,整篇文章如一幅画卷徐徐展开,笔法精妙,章法娴熟。《学舍记》中之前种种境遇,皆是为了后面一句“固予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1]636的落笔,可谓笔力惊鸿,说理透彻。这种积极的入世观和先王孔孟之道是非常契合的,这也符合桐城派讲究文统、治统和道统的观点。所以,曾巩的记体散文也多被选入《古文辞类纂》里面。
(三)桐城派在义法上对曾巩的接受及进一步发展
1.桐城派在义法上对曾巩的接受
方苞首先提出了“义法”。义指文章思想,法指文章形式要雅洁。刘大櫆在方苞“义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义理、书卷、经济”的说法,姚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相结合的主张。曾文“义出六经”,所以曾文的“理”诚然是胜过文辞的,姚鼐一直主张考据、辞章、义理并重。他的义理就是对曾文的先王之道和朱熹的性命之理的借鉴,既然要重“义理”,那么《古文辞类纂》中就得选入像曾巩、韩愈等人的论道文章。桐城派十分重视道德修养对创作的作用,姚鼐明确强调不可“以言行分为二事”[6]273认为只有做到“艺与道合,天与人一”[6]49,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
姚鼐在《古文辞类纂·序》中也说:“目录之序,子固独优。”[1]3方苞肯定子固序长于道古方面,道古就是弘扬传统的儒家先王之道,这些主张都是符合桐城派的文统和道统的主张的。《〈新序〉目录序》指出圣王之道为公学,周末后学为私学,并指出汉儒兴传而不兴经的弊端,从姚鼐《古文辞类纂》所选曾文偏重于序文这一方面可以看出姚鼐在“义法”上对曾巩文章的借鉴。
2. 桐城派在义法上对曾巩接受后的进一步发展
关于“文”与“道”的关系,李汉的《昌黎先生文集序》首先提出文是贯道之器,但是如何贯道,很难在韩愈的文章中找到具体的方法。宋代欧阳修把贯道提到立言不朽的高度,作了简单说明,曾巩则在《南齐书录序》和《寄欧阳舍人书》中从文章体裁方面作了比较明确的阐发。方苞的“义法”从“言有物”和“言有序”两方面进行了总结。姚鼐在方苞和刘大櫆的基础上提出了“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并重”的主张,这是对前人文论和同时代主张的经验借鉴和总结,在文道关系的探讨中建立了自己的体,对清代文坛影响深远。
(四)桐城派继承曾巩义法的原因分析
方苞的义法理论是和统治者的学术风气相统一的。康熙对程朱理学推崇备至,他认为:“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辨析心性之理,而羽翼六经,发挥圣道者,莫详于有宋诸儒。”[7]58-59康熙用御制、御选古文以正垂范,而方苞的《古文约选》即编选于雍正十一年,方苞在《进四书文选表》中提出了自己的编选标准:“故凡所录取,皆以发明义理,清真古雅,言必有物为宗。”[7]223-224其义法说的提出,明显受到统治者学术宗尚的影响。曾巩在《南齐书录序》认为“古之良史,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而一时偷夺倾危,悖理反义之人,亦幸而不暴著于世,岂非所讬不得其人故也?”[8] 187-188把文以贯道,文章立言有体,叙次得法以及文字的繁简问题作为评价良史的标准,从方苞“义法”说也可以看出对这些标准的借鉴。
二、语言典雅明洁——文法接受及发展
(一)桐城派在文法上对曾巩的接受及发展
1. 桐城派在文法上对曾巩的接受
曾巩的文章委婉含蓄,藏锋不露,节奏舒缓,语言浅显简洁,古拙朴质,形成古雅平和的风格特点。他寥寥数语,总能把琐事讲得明明白白。姚鼐在《古文辞类纂》里所选的曾巩文章明显是符合他们的雅洁要求的。《越州赵公救灾记》中赵在越州的救灾事宜繁多杂乱,而曾巩却能有条有理地写出来。首段即设多重问题,后面一一理清头绪,可谓运笔有方,胸有文法,文尽意明,含蓄委婉。曾巩“文辞雅洁、结构严谨、有法可循的创作正迎合了桐城派的古文理论追求。”[9]从《古文辞类纂》里所选曾文也可以看出桐城派的主张。子固的《寄欧阳舍人书》也被选入《古文辞类纂》里,历来评价颇高。先感动与惭愧并起,后以愧疚收束全文,结构前后呼应,先叙述撰写碑志之难,后顺势而转写欧阳修为先父所写碑诔之妙,行文灵活自然,指出了文章蓄德而后发的观点,充满阴柔之美。他的文章做到了气盛辞达,方孝孺《与舒君书》曰:“……道者,气之君;气者,文之帅也。道明则气昌,气昌则辞达。……唐之韩愈、柳子厚,宋之欧阳修,苏轼、曾巩,其辞似可谓之达矣。”[10]66曾巩文章多阐明先王之道,道明了所以文章之气就昌,文气昌则文辞达。因为他的文章朴实典雅,正统儒学气味浓厚,行文雍容平和,而且开合、转承、起伏回环都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符合了桐城派“义法”和“雅洁”的理论主张。
桐城派在文法上提倡雅洁。方苞首先对洁做了解释,他认为归有光的文章有司马迁的气韵,有欧阳修和曾巩的风格,而且方苞本人也模仿归有光的散文,并从他的文章里提出“雅洁”一词。他认为洁并不仅仅指文字简短,还要能正确表达思想,要求用词精炼,简明生动。“雅洁”是“义法”在文章风格方面的贯彻,文章要雅洁,还要义理醇正。
刘大櫆对文的探讨注重音节和神气。姚鼐在方苞和刘大櫆的理论基础上则更进一步,对散文艺术理论进行了相当全面的总结。他提出了“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之说和“阴阳刚柔”的论述。《古文词类纂序目》说:“所以为文者八,……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1]2文之精指的是文章的艺术规律和精神脉理,文之粗指的是文章的声律,先前曾巩、方苞等古文家多强调文章的神理而忽略了文章的声律。
宋文中、欧曾以阴柔为主,明台阁体继之,前后七子则鄙薄宋文,唐宋派专主曾文,方苞继唐宋派道路,标举“雅洁”,姚鼐高瞻远瞩,概括出文章存在刚与柔两种美的境界。
2. 桐城派在文法上对曾巩接受后的进一步发展
以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不满当时古文没落的社会现状,纷纷要求变革散文。他们继承唐宋派对曾巩的评价并从更全面的角度对其做了继承,他们从文法方面对曾巩进行借鉴,提出了“雅洁”一说。姚鼐“阳刚”“阴柔”之美的论说,是对他“神、理、气、色”和“格、律、声、色”的艺术概括。此论也为后来桐城派作家广为接受,曾国藩的《古文四象》对姚鼐的理论有很多继承。张裕钊以“神、气、势、骨、机、理、意、识、脉、声”与“味、韵、格、志、情、法、词、度、界、色”20字分配阴阳,都是对姚鼐刚柔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姚鼐的古文创作理论是继唐宋八大家以来最简洁、最全面、最具有概括性的,他把文章风格分为阳刚和阴柔两种类型。《清史稿·姚鼐传》说“为文高洁深谷,尤近欧阳修、曾巩”。[11]这种高洁深谷的文章风格也算是对子固文章雍容典雅的一种借鉴和发展。
(二)桐城派继承曾巩文法的原因分析
1. 受清代文坛风气的影响
方苞、刘大櫆、姚鼐分别生活在康熙初期到乾隆后期,清朝统治者在思想上尊崇程朱理学,文化上提倡考据学和八股文,“雅洁”一说也是为了顺应统治者文化政策的需要。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在告诫臣子以明代奏疏繁冗为诫,曰为文之法:“文章贵于简当,可施诸日用,如章奏之类,亦须详明简要。明朝典故,朕所悉知,其奏疏多用排偶,芜词甚成一二千言,每日积满几案,人主岂能见览?”[12]由于统治者推行“清真雅正”的文风,上行下效,所以方苞的“雅洁”以“简”为贵也和朝廷风气相应。 方苞又被朝廷任命主管十三经,二十一史等刊刻事宜,参与《四书文选》的编选,其编选的标准皆以发明义理,清真古雅,言必有物为宗。雅正是当时文章的主导,方苞的“雅洁”或多或少地受到影响。
“雅洁”说还是方苞为了挽救时文的文风之弊而提出的积极主张,时文即“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文,而当时的八股取试,早不习经义,经史只割取碎语,从事末节,章句失真,士罕通经,闹出以汉人为唐人,以家父为人父的笑话。而方苞从小学习了经书古文,自然能轻易地认识到时文的弊端,他的时文也写得极工,又贯通经史,成为统治者所需要的典型。他成功地把握住了当时康熙稽古右文和淹贯经史倡导,利用自己编选御文的时机,大力推行自己的理论。
2. 个人经历的影响
姚鼐生活在乾嘉时期,这一时期的学术发展是宋学向汉学转变的过程。汉学主要是汉儒以训诂、考据方法来治经。这样能就能把众多文人引入经典的繁琐考证中,实行清朝统治者的文化控制。这种学术转移对姚鼐造成了重大冲击,姚鼐早年正值尊崇宋学之际,自小以方苞的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作为立身准则,后来目睹了学坛风尚后又向考据倾斜,在追随戴震后也接受了一些考据训练,但是,它逐渐感到汉学的弊端,而卷入了汉宋之争。势单力孤的他被挤入学术边缘,政治前途一片黑暗。所以他以壮盛之年,告归于江南,以古文为业。他后半生都在学院教书,善于从教学中总结古文创作的规律,他懂得什么样的文章才能让门人理解,更多的是注重艺术规律的探讨而较少顾及官方意识形态。教材的选择必须要追求文从字顺,言简有序,清正雅洁,《古文辞类纂》就是这方面教材选文的代表。
结语
以上通过分析了曾巩文章注重以文论道和文章语言典雅明洁两个方面,阐释了他和桐城派的关系,他的文章符合桐城派的考据、义理和词章三者并重的要求,能够满足清代文化政策的需要,所以他的以文论道的文章风格被桐城派的方苞在创立“义法”时所接受。他文章行文简洁,纡徐不烦,简奧不晦的风格也被方苞和姚鼐等桐城派在创立文章写作理论方面所吸收后创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使得桐城派主盟清末文坛二百多年。
总之,桐城派吸收了曾文义理醇正、文章典雅明洁的一面,还借鉴了其他古文家的优秀文论,在创作、风格方面创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由于他们的理论主张符合统治者的需要,顺应了古文的发展规律,在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