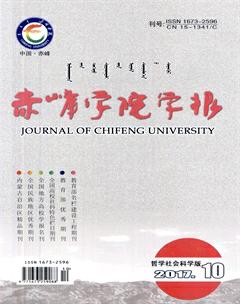广东省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肇始述论
江小娟
摘 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农村逐渐探索实施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开启了中国农村任重而道远的经济体制改革之路。广东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农民为解决温饱问题而自发启动并逐步得到政府认可、引导的历程。从改革前的生产困境到包产到户禁区的突破,再到政府与农民在曲折中共同探索,广东省逐步确立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分析阐释这一曲折前进的探索过程,以期丰富广东农村经济改革方面的学术研究。
关键词:广东省;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肇始;农民
中图分类号:G129;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10-0054-04
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主要包括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两种形式)是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当前学术界关于广东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改革原因、改革成果、改革阶段的划分等方面,对其肇始问题的探讨尚付阙如。本文依据所搜集到的资料,分析广东农民如何在与政府的博弈中敢于突破旧体制的束缚坚持包产到户,中央和地方政府逐渐解放思想、顺应时势发展确立了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实现了这一农民自发倡导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
一、改革开放前广东农村的生产困境
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农村进入了长达20余年的人民公社时期,广大农村实行统一经营、集体劳动、平均分配的人民公社体制,农民生产积极性低,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粮食和农产品短缺。1978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只有633斤,同1956年相比只多了19斤……农民人均分配收入只有70多元,全国约有1/3的农民(约2.5亿人)处在温饱都不能解决的贫困境地”[1]。地處中国大陆南端的广东,虽然拥有适于农作物生长的良好水热条件,但亦如全国其他农村一样,农业生产凋敝,农民收入较低,严重制约着广东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文革”的浩劫,农业发展缓慢。在“文革”极左思潮的干扰破坏下,在被扭曲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广东推广屯昌县“一批二干三带头”(批资本主义,干社会主义,干部带头批、带头干)的经验,把发展家庭副业、发展多种经营、开发集市贸易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限制历史上形成的圩(集市贸易)期,有的公社甚至组织民兵设卡禁止社员赶圩,扼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过度强调水稻生产,农业产量增长缓慢。“文革”十年,广东全省粮食和糖蔗年均仅增长1.8%,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每年增4.5元,生活水平较低[2]。
旧体制的阻碍,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中国仍处于“左”倾错误干扰的徘徊局面。在经营体制方面,广东农村继续实行“一大二公”、“政社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僵化的体制束缚着农民生产积极性,阻碍了广东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据统计,农业合作化的21年间(1957—1978年),全省农村生产队人均收入年仅增加1.6元,到1978年才达77.4元,其中人均年收入在50元以下的“三靠队”(吃饭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占全省生产队总数的1/3[3]。
二、包产到户禁区的突破
对于改革开放前后包产到户的发端时间及发源地点,学术界尚存在诸多争论。其中较有说服力的观点认为:新时期农村改革始于1977年;其“源点”并不是某一个村而是“多点开花”,是以“包”字为核心“多源汇流”的总体性成果[4],而广东亦是这“多点”中的一个。
面对食不饱腹的生活困境,广东农民急切要求冲破旧体制的羁绊,解决迫在眉睫的温饱问题。1977年冬,湛江地区海康县(1994年改为雷州市)北和公社谭葛大队在南村第五生产队试行联产到户,土地按人口、劳动力划分到户,工具、耕牛等凭价借给农户使用,规定谁种谁收,获得丰收。1978年春耕时,生产队土地、工具、耕牛等全部包给农户,当年早造大增产。从1979年上半年开始,整个大队全面实行包产到户,粮食总量达到61万公斤,比上年增产1倍多[5]。谭葛大队实行包产到户粮食大幅增产的消息传开,北和公社全社大部份生产队也随即实行包产到户。这一年(1979年)全社增产780多万斤粮食,增长45%[6]。谭葛大队作为广东包产到户的先行者,率先突破禁区,探索出了一条农民积极性高、增产丰收的路子,为广东其他农村地区的改革树立了良好榜样。
继北和公社之后,“包产到户”这种新型农村经营方式在广东农村悄悄地试行起来。1978年,海南岛(原名为广东省海南岛海南垦区,1988年升格为海南省)大旱,夏种时文昌县一些公社允许农民使用集体土地种植番薯,谁种谁收得以度过饥荒,随后文昌县经验在海南北部部分县区推广。1978年冬,惠阳地区紫金县上义公社有半数以上的生产队实行责任到户,获得大增产。同年冬,从化县江埔公社有3个生产队也尝试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同年广州市郊区杨箕村也搞起了包产到户[7]。
广东农民在生产关系领域也开始突破上级规定,出现了生产队分队的现象。自1978年8月至1979年10月,全省生产队从少于30万个增到38万个,增加25.3%,还有一部分暗队尚未计算在内。生产队总数增加最多的是梅县、惠阳、湛江3个地区,分别为50.3%、49.3%、47.3%[8]。全省包产到户的多地试行,各地连续出现的分队现象,表明以湛江、惠阳、海南北部等广大农村地区开始了一场突破旧体制的变革,包产到户的禁区逐渐被突破。
三、包产到户在曲折中前进
(一)政府坚持方向,农民坚持产量
十一届三中全会党和国家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调整了农业政策,放宽了对自留地、家庭副业和农贸市场的限制,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农民生产积极性由此提高,全国农村出现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但同时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明确提出“两个不许”,即不许分田单干和不许包产到户。落实这一农业政策,成为1979年全国农村工作的中心。endprint
湛江、惠阳、梅县等地区部分生产落后的社队自发实行包产到户,引起了省委领导的关注。中央特许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但鉴于两个“不许”的大方向,省领导的主导思想仍是反对包产到户。1979年4月,国家农委发布《关于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议纪要》,提出“三不许”,即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化小核算单位,不许分田单干。6月,广东省召开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和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12月召开省人大五届二次会议,多次批评包产到户“破坏集体经济,破坏生产力,是历史的倒退”,但省委同时强调要切实帮助这些地方克服困难,不能粗暴指责,更不能用政治运动的方法来批判[7]。在此形势下,广大农民群众突破旧体制的尝试举步维艰。
诚然如此,不少贫困地区的农民群众、基层干部,頂着巨大压力,自发实行包产到户。特别是在长期贫困落后地区,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呼声最高,实行包产到户后实际产量收益也最为明显。如湛江地区遂溪县附城公社信岭生产队,种植甘蔗78亩,其中由生产队统一排工不搞包产的41亩,总产34吨,亩产不到一吨;另有37亩包产到户,总产达到133.5吨,平均亩产3.6吨[8],是否包产到户对农业产量的影响差异明显。1979年,湛江全区3944个生产队包产到户,不少干部采取围堵的办法,通知不准分队、不准包产到户,派工作队到农村劝阻农民分队、合并已分的队,但工作队一走农民又分了队。为纠正这一现象,湛江地委1979年8月作出《关于纠正任意分队、分田单干的决定》,同时允许经济作物可联系产量责任到人。一些地方的农民又突破这一界限,把全部农作物都包产到户[9]。在1978至1979两年多时间里,政府坚持中央的大方向,主张统一生产经营,不许包产到户;部分地区的农民坚持产量,从实际出发,暗自实行包产到户,农业生产获得大丰收。
(二)中央拉引,群众助推
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定“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畜牧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10]。这就在包产到户问题上为广大农村农业生产提出了一种例外存在。“十一届四中全会以后,由于整个环境的改善,包产到户就不管平原山区,在全中国四处蔓延了”[11]。但在1980年初,全国关于包产到户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广东关于包产到户的争论也不绝如缕。1980年3月,习仲勋等省委主要负责人在湛江市海康县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谭葛大队党支部书记吴常胜介绍了该队包产到户的大丰收情况。习仲勋严肃指出“现在这种搞法,表面上是有些人解决了吃饭问题,但实际上是一种单干道路,贫富两极分化的道路,是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吴常胜解释道“过去搞到没饭吃才符合政策,现在搞到有饭吃又不符合政策”[12]。湛江部分地区包产到户后获得了增产增收的良好成果,但鉴于当时全国主流态度,省委主要负责人和大部分领导干部仍采取保守的态度。关于包产到户问题姓“社”与姓“资”的讨论这次座谈会后更为激烈:有的干部认为“辛辛苦苦三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有的干部主张包产到户是“右了、修了、偏了”;而群众坚持包产到户是解决温饱问题的一大法宝,有了它便可以“三摆脱”,即摆脱生产上的瞎指挥、分配上的大锅饭、“苛捐杂税”,认为“形势好不好,就看吃饱吃不饱”[12]。
鉴于一部分领导干部存在的疑虑,邓小平于1980年4月在经济发展长期规划会议上指出:“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贫困的地区……有的可以包产到组,有的可以包给个人……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13]。5月,邓小平赞扬了安徽省肥西县和凤阳县包产到户的做法,指出“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14]。邓小平一系列谈话充分肯定了包产到户,对于打破部分干部群众的僵化心理、克服“左”的偏见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中央对包产到户态度的逐渐缓和,广东省委于1980年4月25日召开常委会议,改变了对包产到户的反对态度,允许某些穷困地区部分“三靠队”在生产队统一经营管理的前提下实行包产到户,但必须阐明这是对特殊困难社队的临时措施[9]。尽管这一政策对包产到户有一定的限制,但政府允许贫困社队搞包产到户是一种较大的进步和突破,是中央拉引农民群众助推的共同结果。
(三)“分田单干”的拉锯战
1980年,省委印发《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一些地区的困难队可以实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办法,但必须坚持“四统一”(生产资料统一分配;种植计划因地制宜统一安排;定产内的产品统一分配;农田基本建设等所必须的劳动力统一调配)、“四不准”(不准拆散、破坏集体财产;不准破坏森林、果木;不准分掉公积金、公益金;不准在责任田上盖房子)。如果不坚持“四统一”、“四不准”,就有滑向单干的危险。对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要严格控制,由县委或地委审查批准。对于那些不是特殊困难队已实行上述办法的,县社要积极引导改正,按专业化分工的原则建立责任制[9]。只允许穷困社队实行有限制的包产到户,政府与农民的分歧亦由此展开。
“四统一”、“四不准”原则下的包产到户,束缚了农民的手脚,政府与农民关于“分田单干”问题展开了“拉锯战”。1980年5月,省委抽调230名干部分赴16个“分田单干”较严重的县,纠正“单干风”、“分队风”,很多地区包产到户受到制止,支持包产到户的干部受到了批评,然而“越扭农民越不接受,越纠搞‘双包到户和所谓单干的就越多”[15]。省农委副主任杜瑞芝于1980年6月到包产到户“重灾区”惠阳紫金县上义公社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到该县三次纠三次扩大,许多大队农民专门制定方案对付上级检查,大部分群众反映“搞了包上交后,增了多少产,可以吃饱饭了,不超支了”,从乡干部到县委书记都反映“从来没有看过群众插秧进度这么快、田间管理这么好”[12]。根据调查的实际情况,杜瑞芝向省委报告:包产到户不是单干,不应消极指责而应积极支持、加强领导。基于强烈的群众呼声以及农委干部的实际调查结果,习仲勋在1980年7月的地、市委书记会议上指出“对已经搞了包产到户的,要逐步把它引导到搞专业化分工协作的责任制”,一些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我们应当允许,不要因此去指责基层干部和党员,不要去硬扭”[9],政府态度由此迈开了重要一步。endprint
在“分田单干”的“拉锯战”中,政府逐渐认清事实支持包产到户,农民也由此减轻了思想上的负担,正大光明地实行包产到户。各地包产到户蓬勃发展,总体上最穷的队最先突破,其次是较贫困的地方,接着是比较富裕的生产队,支部较强的大队最后实行。1980年底,湛江全区大部分农村都实行了包产到户,全区粮食生产一举超过历史最高水平4.3%,13个市县个个增产。花生、甘蔗等经济作物,畜牧业、水产业等都大幅增产[8]。
四、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确立
1980年9月,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75号文),规定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强调“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管理形式,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17]這对于解决双包问题上的分歧、统一思想认识具有重大意义。1980年10月,广东省委发出贯彻执行中央75号文件的通知,允许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同时存在,由低级到高级逐步完善。各地市普遍贯彻执行中央和省委的文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广大农村得以推广,农民开始正大光明地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
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确立,突破了计划经济时代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模式,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经营权、劳动自主权,有效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改变了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的被动局面。据省农委1980年不完全统计,惠阳、湛江、梅县、汕头、海南5个地区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当年10月共为106945个队,占总队数的40%[12]。1980年底,广东省有40%以上的农户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省粮食产量比上年增产了11亿斤;农村人均收入达274元,比1979年增收51元,出现了盖新房子多、购置耕牛农具多、重视科学种田多的“三多”新气象[17]。广东农村经济状况得到较大改善。
广东新时期农村改革,从包工到作业组、联产计酬,再到包产到户;从边远山区、贫困落后地区再到平原地区、发达地区,经历了一场曲折而深刻的变革。在这一历程中,农民作为政策的实践者坚信包产到户是摆脱贫困的唯一出路,坚定不移地实行包产到户;中央作为改革的决策者,对包产到户经历了一个由排拒——认同——提倡的过程;地方政府随着中央态度的逐渐明晰,由中央政策的执行者逐步转变为包产到户的支持者。因此,广东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肇始过程,不同于以往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而是农民倡导下的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
参考文献:
〔1〕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资料选编(第二辑)[G].延安: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出版社,2006.
〔2〕广东省地方史编委会.广东省志·农业志[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
〔3〕广东地方史志办公室.当代广东简史[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
〔4〕武国友.新时期农村改革发端的再探讨[J].中共党史研究,2009(11).
〔5〕王涛,李秀珍,梁向阳.包产到户先行者吴常胜访问记[J].广东党史,2004.
〔6〕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广东改革开放决策者访谈录[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7〕《习仲勋主政广东》编委会.习仲勋主政广东[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8〕刘田夫.刘田夫回忆录[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9〕林若.八十年代初期湛江地区的农村改革[J].广东党史,1999.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1〕陈吉元、陈家骥:杨勋.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
〔12〕广东农村政策研究中心.广东农村改革发展史论[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
〔13〕张根生.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实[M].珠海:珠海出版社,2001.
〔14〕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5〕杜瑞芝.让子孙后代记住任仲夷这个名字[J].炎黄春秋,2007(1).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7〕《习仲勋传》编委会:习仲勋传(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 赛汉其其格)
Abstract: After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the national rural gradually explor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various forms of production responsibility, opened a long way in China's economic system reform.The reform of rural economic system in Guangdong was the process of farmers' initiative to start and solve the problem of food and clothing.From the production difficulties before the reform to the 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 and to the government and farmers to explore in the twists and turns ,the Guangdong Province had gradually established the household contract responsibility system.This paper analyzes and explains the process of exploration in order to enrich the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reform of rural economy in Guangdong.
Keywords: Guangdong Province; 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 Inchoation; Farmer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