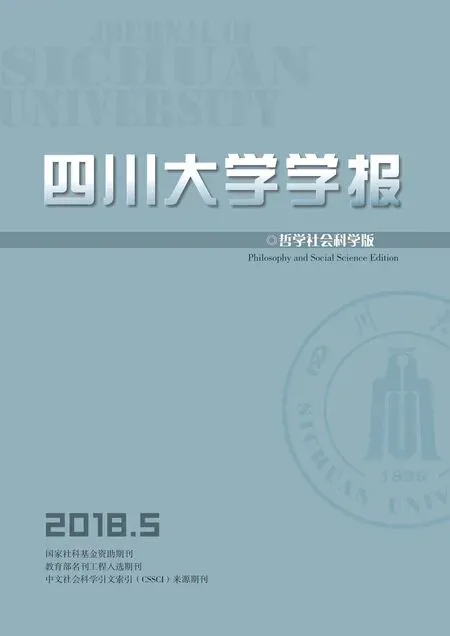明代朝鲜诏使诗世界观探析:以祁顺为例
文化交流史、全球史研究是目前世界人文领域最重要的研究趋势之一。透过彼此不同视角的观看与摹写,进而在文化实践活动中获得新生,自非一番顺境,而是要历经种种转折、误读、偏见、改编等复杂的交互作用,几乎可谓一场惊心动魄的旅程,居间穿针引线的中介人物,则常是隐而不显的一群。过去研究文化交流史,作为中西文化沟通重要媒介的传教士,夙为学界所重视,相关的研究不胜枚举,然大多侧重在传教士引入的天主教神学、科学技术等层面。近年来,种种新视角的研究方法大行其道,从物质文化(如茶叶、瓷器、颜料、火炮兵器)、艺术手法(如透视法、铜板画)、书写方式(忏悔录、第一人称、叙事角度、旅行书写)到翻译史等等不一而足,大大拓展了研究者的视野。
中西交流史研究尽管精彩迭出,东亚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进境亦不遑多让,相关研究胜义纷然。近年关于东亚内部的文学与文化交流也有重大的进展,此固有以致之,约有数端可说:(一)迩近韩国、日本、越南等大量汉文文献、数据集相继出版,例如《韩国历代文集丛刊》《燕行录》《琉球汉文文献》《越南燕行文献》《朝鲜通信使文献》《使琉球录》,日韩笔谈记录等等珍贵文献如今呈现在研究者面前,开启了一个缤纷多彩的世界。(二)研究视角的多元化与价值观念的再反思。例如日本京都大学的名誉教授夫马进、金文京对于东亚使节文化的提倡,中国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张伯伟教授鼓吹“域外汉籍”的研究,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葛兆光教授致力于推动“从周边看中国”的课题等。台湾中研院研究团队在石守谦教授的领导之下,结合文学、艺术、宗教、历史不同的研究取径,开创“东亚文化意象”,尝试就东亚文化交流互动寻求一个具有高度涵摄效力的解释模式。另一方面,面对过去习以为常的国族主义、世界史、主体性等概念,学界不同的研究视角成就了不同的学术成绩,其对此类研究大有推波助澜之功自不待言。(三)作为东亚共同沟通媒介的汉诗文,近年大有重新评价的趋势。明清以来的使节诗战,无法不令人想到当年《左传》赋诗言志的传统。中土使节与朝鲜、安南、琉球儒者、文人、僧人彼此唱和赠答不断,一如欧洲的拉丁文,汉诗文成为东亚知识社群彼此沟通情志最重要的媒介。透过共同的知识结构,虽然彼此观看视角与书写方式之间有所异同,仍旧构筑一个相互传唱的基础平台,而对汉诗文(乃至汉学)在东亚知识社群中的功能与角色省思,目前也是学界关注的焦点。
对于汉文诗,过去论者多侧重在其理想风格的呈现、文献真伪的考证或者异国风土的记述,但对于居间的中介人物,如使节、通事、海商、僧侣的身份与作用,却多存而不论。以使节诗为例,明代中叶以后,朝鲜方面就中土与朝鲜儒臣酬唱之作编成《皇华集》,自是该书在东亚知识社群中具有相当程度的典范作用,也引起中土批评家的注意。例如,明清之际的诗坛尊宿钱谦益曾经批评《皇华集》风格靡弱,他的说法招致朝鲜文人的反击,其中申昉就驳斥道:“钱牧斋《皇华集跋》谓奉诏诸公贬调就之,以寓柔远之意,尤可笑也。前后天使有文者,盖不多人,岂皆文章之士?而我之傧接必简一时之英,岂至使天使自贬调降格以见护也。”[注]申昉:《屯庵诗话》,赵钟业编:《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第6册,首尔:太学社,1996年,第99页。客观来说,钱谦益的说法并不能代表中土多数诗家的看法。从清初的王士禛、汪楫、徐葆光,到清代中叶的纪晓岚、翁方纲、法式善、洪亮吉,莫不对异邦汉诗人青眼有加,如洪亮吉就指出,“本朝文教覃敷,即异域人亦皆工于声律”。[注]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五,《丛书集成初编》,第259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6页。事实上,明代以来的使节,如祁顺、朱之蕃对于朝鲜汉诗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与赏誉,说明中土人士早就注意到异国汉诗质量俱佳。[注]关于这点,详参拙著:《从“搜奇猎异”到“休明之化”——由朱之蕃看晚明中韩使节文化书写的世界图像》,《汉学研究》(台北)第29卷第2期(2011年6月),第53-80页。而清代中叶朝鲜四家与中土士人维持良好的互动关系,已为老生长谈。朝鲜之外,清代中叶的批评家法式善对《中山诗文集》的琉球汉诗作者群,如周熙命、曾益、蔡铎等人的作品抱有良好印象,从其《梧门诗话》中的记述来看,[注]如“周熙臣新命与程宠文同为中山讲解师,著有《翠云楼诗笺》,颇为闽中士大夫传诵。录其《寄程宠文》。云:‘与子握手别,愁心绕故乡。驿亭花径冷,江路草桥荒。客梦随山月,溪声落雪堂。故人如问讯,万里一空囊。’”曾益“为中山文秀,好读书,尤长于诗。早岁登仕版,以陪贰来闽,晋秩正议大夫。与闽中陈昌其元辅称莫逆,陈为刻其《诗草》。《游西湖》云:‘西子湖头别有天,醉看花鸟尽嫣然。六桥柳色摇晴绿,三竺莺声带晓烟。走马客过桃叶岸,吹箫人上酒家船。飞来一片峰前立,为问林逋放鹤年。’”蔡铎“官中山正议大夫。康熙戊辰冬,奉贡至闽,亦与陈昌其友善。诗有‘十里柳堤双桨曲,半陂僧语一钟孤’、‘疏林孤磬凌空响,斜日轻鸥映水双’ 之句”云云。参见张寅彭、强迪艺:《梧门诗话合校》卷三、卷十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116、358-359页。不论抒情或写景,在法式善看来,琉球汉诗人与中土诗人颇能心意相通。以上诸人对东亚汉诗人的毁誉是否得宜先且不论,但有一点明清以来的中土批评家似乎皆未措意:东亚诸国的汉诗作者往往皆具有使节身份,至少相当程度参与使节的接待过程。[注]此处“使节”一词采用最广义的解释,包括非正式使节的从客、通事等。迩近数年,笔者于东亚使节诗学有所涉猎,希冀透过东亚使节诗作,尝试就诗人的异文化经验与世界图像有所发明。而在明清两代出使朝鲜的使臣文人当中,明代前期的诏使祁顺在中朝诗史上留下巨大的投影,本文即以祁顺为例,就其时空书写的精神特质加以阐析。
一、祁顺与《皇华集》
作为海东文物之首的朝鲜,诗论家对于使节的作用与影响始终未曾或忘,从高丽到朝鲜,韩国汉诗史上,出色的作者几乎皆多少具有相当程度的涉华外交经验。特别是《皇华集》中所记录的中朝诗人的互动,一直是韩国诗论家观看的重点。例如朝鲜后期的金渐就曾说道:“近代有《皇华集》,皆明使臣诗也。如倪尚书谦、陈祭酒鉴、张给事宁、金太仆湜、祚郎中嘉、董尚书越、王给事敞、龚祭酒用卿、华学士察、张给事承宪、唐太史皋、史给事道、许阁老国、魏给事时亮、朱太史之蕃、梁给事有年、姜合老曰广、王给事梦尹、熊行人化、刘学士鸿训辈,皆极一代之选。然兴象唐,理趣不如宋,是明人而已矣。”[注]金渐:《西京诗话》补录,《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第13册,首尔:太学社,1996年,郑炳昱教授藏本,第642-643页。按,《韩国诗话中论中国诗资料选粹》(邝健行、陈永明、吴淑铀选编,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20页)校勘记言似脱“不如”二字。这段话专从诗作的风格立论,《皇华集》中诗作往往近乎馆阁体,非唐非宋亦不在意料之外。但以唐宋判分优劣之前,朝鲜诗论家亦喜就中土诏使诗评次排比。如徐居正谓:“中朝使臣,前后来者皆文章节义之士。……陈给事嘉猷宽平正大,观其气象,知其为大人君子,文章亦平淡。张给事宁,其文章可伯仲于陈,而言行颇有强作处,然亦君子人也。金舍人湜工于七言四韵,笔法画格亦高妙,但节行扫地。张御史城有温雅气象,而无奇节。姜行人洁有大宽之量,而少文行。祁户部顺笃实有节行,文词亦纯正,其陈、张两给事之俦乎。张行人瑾文章操行不及祁,而在其范围之内耳。”[注]徐居正:《笔苑杂记》下,《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第1册,第557页。这一说法表明虽然明代诏使络绎于途,且其著作多收入《皇华集》,但彼此之间仍然存在极大差异,不应一以视之。与徐居正约莫同时的成俔对明代诏使的评价多有不同,但评骘科次的态度并无二致。[注]成俔:《慵斋丛话》,《韩国汉籍民俗丛书》,第7册,台北:万卷楼,2012年,第29页。其他如权应仁称“古今天使无高下,仆品题于湖阴,祁顺为首,倪谦、董越次之,金舍人湜七言律极好,张宁似为未熟”。[注]权应仁:《松溪漫录》上,《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第1册,第748页。尹根寿曰:“恭宪王朝,黄洪宪天使有先声,一日于经席问郑林塘惟言曰:‘我国诏使所著诗,谁为第一?’林塘对以祈(祁)顺,张宁次之。以今观之,张靖之诗,篇篇皆绝唱,合其第一,而林塘之对云然。何邪?”[注]尹根寿:《月汀漫笔》,《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第2册,第57页。李五峰谓“《皇华》诗,许国为第一,祁顺为第二,张宁第三”,而李睟光对此不以为然。[注]李睟光:《芝峰类说》,《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第1册,第299页。《菊堂排语》一书作者不详,其中有“诏使能文章者,倪侍讲、张给事之后,称祈(祁)户部云”等语。[注]《菊堂排语》,《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第3册,第229页。综观诸家言,不难看出,朝鲜诗论家喜尚殊途,然于诗文一道,大抵皆推祁顺、张宁为首。关于张宁,已有部分研究专著,且笔者亦将于别稿细论,本文先说祁顺。
祁顺(1434—1497),字致和,号巽川先生。广东东莞人。天顺二年,进士二甲二名及第。天顺七年拜兵部主事,成化二年,转户部,累迁本部员外郎、郎中。成化十一年建储,赐一品服,十二年,持节往诏朝鲜。成化十三年,任江西左参政,期间因事贬为贵州石阡府知府。后累升至江西左布政使。弘治十年,卒于官。享年六十四。著有《巽川祁先生文集》、《使东稿》(佚)、《宝安杂咏》(佚)。[注]关于祁顺生平,可参见郭文炳编:(康熙)《东莞县志》卷十二,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1994年据日本内阁文库藏清康熙刻本影印,第13页a。祁顺之名长久以来湮没不彰,相关研究寥寥可数。[注]笔者搜寻各种数据库,只寻获温建明:《祁顺及其〈巽川祁先生文集〉研究》,《东莞理工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第9-13页。
《皇华集》卷八载“成化十二年丙申颁册立皇太子诏使。正:户部郎中祁顺;副:行人司左司副张谨(字廷玉)。远接使议政府左参赞徐居正”。祁顺受命即行,据说其出使之际“关人故集士兵千余,土物万计,从而贸易。顺乃悉屏斥,惟匹骑从往”,[注]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余思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22页。且“惟一函诏、一箧衣,辽阳守臣如故事具供张,集夫力以俟,其富家奔走集货,夤缘求往者纷然,公悉拒绝。留信宿,即行。护送数十骑而已。朝鲜接待陪臣供张宴物如前,皆不纳,唯食常廪。至国中,虽礼馈物,一无所受”。[注]丘霁:《记朝鲜使事》,祁顺:《巽川祁先生文集》附录卷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7册,台南:庄严文化事业,1997年,据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二年在兹堂刻本影印,第 588-589页。祁顺以其清廉自持的高洁德行,被朝鲜方面誉为“中州凤凰”。弘治元年,遭风漂至中国的朝鲜人崔溥也与中国方面的士人就祁顺有过一番问答。其记曰:
荣曰:“我朝郎中祁顺、行人张瑾曾使朝鲜,著《皇华集》,国人赓和,徐居正居首列也。其诗有曰:‘明皇若问三韩事,文物衣冠上国同。’今见足下,诚千载一遇,蒙不弃,复承和诗,谨奉薄礼,少助舟中一膳,希目入幸甚。”臣曰:“祁郎中文章清德,人所钦慕,今为什么官职?张行人亦任什么职事?”荣曰:“祁郎中见贬为贵州石阡知府。”[注]朴元熇:《崔溥漂海录校注》,上海:上海出版社,2013年,第75页。
这段话说明祁顺在当时中朝两国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尤其在朝鲜,更是“文章清德,人所钦慕”,其著作有相当程度之流传,诗句亦脍炙人口。祁顺之所以名冠诏使,与其令誉清扬恐非无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方面的读者也注意到朝鲜方面与祁顺唱和的诗人徐居正。事实上,虽然明代诏使与朝鲜文人的酬唱无代无之,但徐居正与祁顺两人的连篇酬唱在中朝使节诗史中特别受到当代与后世的批评家的高度关注。
二、祁顺与徐居正之诗战
祁顺与徐居正二人的诗战,一直是朝鲜批评家津津乐道的话题,亲逢其盛的成俔就如是记述:
户部纯谨和易,善赋诗,上待之甚厚。户部慕上仪采,曰:“真天人也。”卢宣城、徐达城为馆伴。余与洪兼善、李次公为从事官,以备不虞。达城曰:“天使虽善作诗,皆是素构,不如我先作诗以希赓韵,则彼必大窘矣。”游汉江之日,登济川亭,达城出呈诗数首曰:“丈人逸韵,仆未能酬。今缀芜词,仰希高和。”户部微笑一览,即拨笔写下,文不加点。如“百济地形临水尽,五台泉脉自天来”之句,“倚罢高楼不尽情,又携春色泛空明。人从竹叶杯中醉,舟向杨花渡口横”。又作《江之水》辞。乘舟顺流而下,至于蚕岭,不曾辍咏。达城胆落,岸帽长吟而已。金文良舌呿不收,曰:“近来我不针灸,诗思枯涸,故如此受苦耳。”不能措一辞。人皆笑之。[注]成俔:《慵斋丛话》,《韩国汉籍民俗丛书》,第7册,第 29页。
成俔亲临现场的记述可信度极高,此段文字主要在推尊祁顺诗才之高以及徐居正不自量力的莽撞。不过由于徐居正与祁顺逞才竞胜之事脍炙人口,后日文人常于此添枝加叶,更发议论。例如金安老就如是说:
成庙朝,祁户部顺来颁帝命。道途所由,览物兴咏。远接使四佳徐先生以为平平,心易之。竣使事明日,四佳以汉江之游请。顺曰:“诺。在途酬唱,客先主人;明日江上,主人先客以起兴可也。”四佳预述一律,并录夙制《永川明远楼》诗韵,曰:“当竖此老降幡矣。”到济川亭,酒未半,于座上微吟,若为构思之状,索笔书呈一联,有曰:“风月不随黄鹤去,烟波长送白鸥来。” 顺即席走毫,曰:“百济地形临水尽,五台泉脉自天来。”顾四佳曰:“是否?”笔锋横逸,不可枝梧,四座皆色沮。乖崖亦预席,当和押,有“堆”字,苦吟思涸,攒眉顾人曰:“神耗意竭,吾其死矣。”久乃仅缀云:“崇酒千瓶肉百堆。”尔后又有“头”字押,乖崖云:“黑云含雨已临头。”顺曰:“可洗肉百堆矣。”乘舟放棹,顺流而下,江山役神,觞豆疲形,操觚沥精,不暇流眄。而西日半衔,夕波微兴,倚醺瞑目之顷,舟至蚕头峰下。户部开目曰:“是何地名?”舌者:“杨花渡。”即吟诗一律曰:“人从竹叶杯中醉,舟向杨花渡口横。”四佳次云:“山似高怀长偃蹇,水如健笔更纵横。”二公巧速略相似,犹两雄对阵,持久不决,奇正变化,莫不相谙。锋交战合,电流雷迅,揖让之风存乎旗鼓之间。虽堂堂八阵,举扇指挥;而仲达之算无遗策,亦未易降也。顺尝曰:“先生在中朝,亦当居四五人内矣。”行返到临津舟上,四佳先赋古风长韵,顺卷纸尾置案上,手批徐徐,览一句辄成一句,手眼俱下,须臾览讫,而步韵亦讫。步讫而笔犹不停,连书竟纸,飒飒风驰雨骤,而一篇又成。四佳心服之,顾从事蔡懒斋曰:“速矣!多矣!”额稍蹙然,即连赓两什,意思泉涌,浩浩莫竭。彼一再唱,而和必重累,以多为胜,此亦希世之捷手也。[注]金安老:《龙泉谈寂记》卷下,《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第1册,第656-657页。
《菊堂排语》的作者就此事说道:
正使户部郎中祈顺、副使行人张瑾来,颁册立皇太子诏。远接使:左参赞徐居正。正使《百祥楼宴席却妓》诗曰:“因缘旧愧风光曲,落魄空赢薄幸名。争似昌黎文字饮,醉来歌咏有余清。”游汉江日,徐居正以为天使虽善诗,皆是宿构,吾可先作,以试其才。仍投七言律:“楼中佳丽锦筵开,楼外青山翠似堆。风月不随黄鹤去,烟波长送白鸥来。登酬临唱三千首,宾主风流一百杯。更待夜深吹玉笛,月明牛斗共徘徊。”颔联乃丽朝蔡洪哲之句,而只改下数句,可谓发冢手也。正使即援笔次其韵:“楼前风卷白云开,坐看群山紫翠堆。百济地形临水尽,五台泉脉自天来。题诗愧乏崔郎句,对酒宁辞太白杯。花鸟满前春景好,不妨谈笑更迟徊。”《游杨花渡》诗曰:“倚罢高楼未尽情,又携春色泛空明。人随竹叶杯中醉,舟向杨花渡口横。东海微茫孤岛没,南山苍翠淡云生。从前会得江湖乐,今日襟怀百倍清。”又次副使韵,诗曰:“江头风景满楼船,花柳争妍二月天。帆影带将飞鸟去,笛声惊起老龙眠。山连两岸云林合,石激中流雪浪溅。莫怪东来好游赏,寻常诗酒贯相穿。”愈出愈奇,见者吐舌。诏使能文章者,倪侍讲、张给事之后,称祈户部云。[注]《菊堂排语》,《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第3册,第228-229页。
洪万宗也说:
天使祈(祁)顺尝出游杨花渡,舟中有诗曰:“倚罢高楼未尽情,又携春色泛空明。人随竹叶杯中醉,舟向杨花渡口横。东海微茫孤岛没,南山苍翠淡云生。从前会得江湖乐,今日襟怀百倍清。”徐四佳公以傧使和之曰:“风流江海十年情,坐待潮光拨眼明。山似高人长偃蹇,水如健笔更纵横。柂楼举酒日初落,官渡哦诗潮自生。更待明月扶醉去,杏花疏影不禁清。”两诗俱佳,祈诗似优。四佳每当酬答,蹙额有难色。祈公见四佳之作,甚奖诩。[注]洪万宗:《诗评补遗》,《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第4册,第147-148页。
综上诸家的说法,除了二人逞才竞胜之外,还有若干值得注意的地方:(一)和韵虽然无代无之,但徐居正以为中土使臣多是“宿构”,而非即景即事,祁顺的才情固然推翻了这种刻板的印象,却也说明历来使节酬唱,不独是文人雅兴的诗酒风流,更像是一场别具用心的特殊技能竞赛,虽然没有刀光血影,却也隐隐然感受到叩关叫阵的火苗。(二)徐居正主动出击,虽然最后仍然屈居下风,但说明他对个人才具的高度自信。从某个角度看,沈德符“朝鲜俗最崇诗文,亦举乡会试。其来朝贡陪臣多大僚,称议政者即宰相。必有一御史监之,皆妙选文学著称者充使介。至阙,必收买图籍。偶欲《弇州四部稿》,书肆故靳之,增价至十倍,其笃好如此。天朝使其国,以一翰林、一给事往。欲行者即乘四牡,彼国濡毫以待唱和,我之衔命者,才或反逊之。前辈一二北扉,遭其姗侮非一。大为皇华之辱。此后似宜遴择而使,勿为元菟四郡人所笑可也”[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三十,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786页。的说法,对于终落下风的徐居正并不完全适用,不过倘若当日所遇使臣才学非若祁顺精彩,徐居正旗开得胜亦不无可能,沈德符虽然年代较晚,但明代知识阶层显然对于朝鲜充使介者的好学能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汉江游赏之际斗诗竞胜一事,祁顺亦曾为文记之,但文字情调与朝鲜各家截然不同,其言曰:
朝鲜国城南十里许有水曰汉江,源出五台、金刚二山,合流入海。其景以幽胜闻而临江有楼可以登眺。故前辈自中朝至者咸往游焉。成化丙申春二月,余与行人司副张廷玉奉使于斯,甫竣事,有以游汉江请者,诺之。是月二十有六日,偕馆伴卢赞成思慎、徐参赞居正,自崇礼门出,历山蹊村径以达江浒,国王预遣都承旨柳轻、副承旨任士洪设宴楼上,而尹议政子云、金议政守温、任中枢元浚、成中枢任、李判书承召皆在焉,时宿雨新霁,山川明媚,天光与水色相连,二难与四美兼得,于是登楼纵观,举酒相酌,徐参赞赋诗二律,余即和之。既而相拉登舟,沿流西下,居人来观者,奔走争先,而沙禽野鸟飞舞渔舟烟水间,亦若乐睹光华徘徊不忍去也。宴设舟中,烹麟炙鹿,畅饮无筭。酒酣,余复作辞二章诗一律,廷玉有作又和之,数里至杨花渡,乃各道餫饷所聚之处,仓廪层出,与山势相高,又数里登龙头山,山瞰水涯,视群峰特出,隔岸之人家远近,海岛之风帆出没,毕入望中。时日迫暮而山上先已供张开筵,意不容拒,乃复酌数巡,赋诗一律而返。及抵城中更漏作矣。嗟夫!朝鲜去中国数千里,非王事不得至焉,则汉江之游,非偶然耳,然斯游岂特探奇览胜,留连诗酒而已哉。江之南,旧百济也;百济之东,古新罗也;而熊津都府又唐之遗址也。访其迹,思其时,盖有不胜怀古者矣。余念斯游之不可常,而恐其或忘也,于是乎记之。[注]祁顺:《游汉江记》,《巽川祁先生文集》卷十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7册,第530页。
祁顺之文平和冲淡,堪称记游佳构,其中“宿雨新霁”等句及“山瞰水涯”数句状景似画,如在目前。亦写燕集,“宴设舟中,烹麟炙鹿,畅饮无筭”,可谓融洽欢畅,几乎没有任何剑拔弩张的气氛,而是一场公余之暇的快意行旅。这一方面说明祁顺内心的优游自在,另一方面也说明中朝双方观看视角的异同。似乎对祁顺而言,沿途吟诗只是游赏心怀的恣意挥洒,与朝鲜诗人内心的高度紧张仍有一间之隔。客观来说,祁顺虽然奉命持节,但毕竟只是往告建储,公务性质相对轻松,远非倪谦、张宁之俦可比。更重要的是,祁顺虽然也有天国上使的格套,但却始终对朝鲜的风土人物抱持欣赏的态度。在为徐居正的文集所作的序文当中,祁顺就诗贯串不同时空中的人心的重要功能如是说道:
诗之道大矣,古今异世而诗无间也,中外异域而诗无别也。盖道之著者为文,文之成音者为诗。人有不同而同此心,心有不同而同此道,道同则形之言者,无往而不同矣。苟不于此求之而屑屑焉古今中外之较,岂知言哉?
这里,祁顺强调诗作应该构筑在普遍动人的价值根源之上,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由于具有共通的语文、审美标准以及价值信念,彼此情志沟通方为可能,这段话显示出相当程度的道学色彩,多少有些“文以载道”的倾向。然而,或许正因如此,祁顺引徐居正为同道中人,也因由此,祁顺对徐居正的诗学涵养推崇备至。如其接上言道:
朝鲜以文献雄东方,诗泒(派)相传,夙有攸自,逮际皇明,气化丕隆,声教沦浃,能言之士尤彬彬乎视昔有加。刚中博古通经,擢巍科,跻显仕,文学优赡,国人咸推重之。天顺庚辰,奉其主命入觐于朝,往还几八千里,上观乎都城之宏壮,宫阙之崇丽,车书文物之会同,礼乐典章之明备;下则睹乎山川之高深,道途之修迥,民风土俗之熙皞,鸟兽草木之咸若,凡其接于目、触于心者,悉于诗发焉。长篇短章沨沨乎其美盛也,渊渊乎其有本也,浩浩乎其不可穷也。推其所至,与中国之能声诗者,殊不相远。等而上之,虽古人亦岂难及哉。是固所谓心同道同而形之言者无不同也。[注]祁顺:《北征藁序》,《巽川祁先生文集》卷十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7册,第517页。
祁顺滞留朝鲜期间,想必已对徐居正于朝鲜一朝的重要性深有体会。徐居正除了文学特出之外,其赴华入觐往还中的见闻同样也对朝鲜时政、文化生活发挥相当程度的作用,而祁顺在强调他们两人心志相通的同时,也相当程度地强调“江山之助”,或者,至少是见闻阅历的重要性,这或许是出于二者经验类同,亦可视为祁顺之夫子自道。对祁顺而言,徐居正不仅可与中国当世名家比肩,甚且有超迈古人之处。与异国一代诗豪的邂逅与酬唱往还,想必也是祁顺毕生难忘的经历吧。
三、祁顺使东诗作的时空描写
诏使诗有强烈的纪行性质,前人言之已详,无庸词费。祁顺奉诏使朝,触目先见两国之同,对他而言,朝鲜与中华体现相同的价值信念,最明显的表征就是孔庙。在种种官方任务仪节之外,明清时期,由中国派往东亚各国的使节往往会晋谒孔庙。孔庙除了是中华文化的表征之外,也成为文明开化的判准。祁顺虽未入道学传,但其心中真诚崇奉儒学殆无可疑,他于汉城亲谒孔庙,有诗记其事云:
杏坛深处谒先师,曲阜云山入望思。荐罢芳芹留恋久,一番时雨遍东夷。
又云:
朝鲜诗礼独称雄,孔庙规模上国同。数仞门墙无路入,千年丝竹有神通。
斯文自与天长久,吾道常如日正中。四海车书今一统,典章何处不尊崇。[注]祁顺:《余与左司张君廷玉奉使抵三韩,同谒先师孔子庙。廷玉赋七绝一首,余因和之》《短句未足尽怀,再复一律》,郑麟趾等编:《皇华集》,第2册,台北:珪庭出版社,1978年,第693-694页。
“朝鲜诗礼独称雄,孔庙规模上国同”两句,文字略有异于《漂海录》所载,不过推尊之意更为强烈。由此不难看出,祁顺心目中的“道”,即是儒学。祁顺时,阳明学尚未抬头,中国儒生一意崇奉朱子,与朝鲜儒生可谓志同道合。入清以后,尊奉朱子学的朝鲜燕行使与中国的知识阶层每就彼此信念异同屡起勃溪,与此形成强烈对比。对祁顺而言,儒学就是普世价值的体现,朝鲜崇奉儒学自然让他觉得十分亲切。其言:“孔子之道,遍于四方,行于万世,而朝鲜能宗斯道,以雄于东,亦为知所重也已。《宋史》称其俗喜读书,庶贱之家,各于衢路,置局堂以相讲习,而国人金行成、崔罕、王彬相继就学于国子监,擢进士第而归,则诗书熏陶已非一日。我皇明文教诞敷,东渐尤近。朝鲜士人岁觐京国,耳闻目睹,所得尤深。宜其文物典章,不异中华而远超他邦也。”[注]祁顺:《谒孔庙诗序》,《巽川祁先生文集》卷十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7册,第517页。在祁顺看来,虽然就儒学的普及亦即中华文化的流播而言,朝鲜与中国山川草木有以异之,但对人伦道德的向往则并无二致。
祁顺在朝鲜孔庙,还披览朝鲜诸生功课,亦有诗记其事曰:
青袍济济列生徒,千里骅骝汗血驹。论秀远规周俊士,慕华同事鲁真儒。
功名自古非难事,道德由来是坦途。莫学隋唐昧根本,只将词赋费功夫。[注]祁顺:《坐中获睹诸生所作文赋,因赠以诗》,《皇华集》,第2册,第695页。
祁顺勉励诸生当以道德为本,切莫在词赋等枝微末节耗费心力,这样的说法于道学家屡见不鲜,祁顺的道学色彩再次获得证实。在他看来,词章末技非不重要,然儒者自当以修身为本,不应本末颠倒,刻意雕琢文辞,则有害道之嫌,如其言:“今诸生学圣贤之学,尚思蕴为道德,发为功业,以求高明远大之归,而不安于苟且卑陋之习,斯为善学者矣。若徒屑屑于词章末技,而弗究其本焉,则非中国所闻。”[注]祁顺:《谒孔庙诗序》,《巽川祁先生文集》卷十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7册,第517页。这种看法源乎朱子,朱子曾言,“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才要作文章,便是枝叶,害着学问,反两失也”。[注]朱熹:《论文上》,黎德靖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台北:文津出版社,1986年,第8册,第3319页。祁顺的儒者本色,于此又一次表露无遗。不过,祁顺并不迂腐,虽然对他而言,儒学具有普世价值,也带有文明启蒙的色彩,但他的使节纪行诗也不无异国闻见,例如《开城小咏》十首、《奉使出京》十七首、《朝鲜杂咏》十首,于鸭绿江、驿楼、土民家皆有吟咏。
祁顺在复命归国之际,献诗朝鲜国王,即《朝鲜杂咏》十首,于中颇能概括其此行心境,如:
诏下天门宠渥新,东藩人物入陶钧。唐虞声教覃荒服,孔孟诗书溢海滨。
百政修明夸令主,一心匡辅总贤臣。河山带砺今犹昔,应共皇图亿万春。[注]祁顺:《向辱国王饯别,尝奉小诗,而意犹有缺也。矧未别之前,承致赆礼甚厚,虽不敢祇领,而于盛德岂能少忘哉!途中怀仰日深,因辏七言律十章,用表惓惓之敬。倘不以为拙,时一展观,千里犹觌面也》,赵季辑校:《足本皇华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292页。(其一)
营州东畔古名区,耕有田畴读有书。果下尽乘三尺马,筵中多尚八梢鱼。
绿通长白江分后,红映扶桑日上初。自入圣朝文物盛,不应还比旧扶余。[注]赵季辑校:《足本皇华集》,第294页。《朝鲜杂咏》十首,见《足本皇华集》,第292-294页;亦收入郑麟趾等编:《皇华集》,第2册,第681-684页。以下不一一标注页码。(其九)
这些诗篇带有应制诗的气味,又有台阁体之风,圣君贤臣的唱叹先且不论,在传统的修辞当中,“海滨”往往是偏僻辽远、文教不兴的代称。不过,在祁顺看来,朝鲜虽僻处海滨,然君臣齐心推行儒教,文风鼎盛,人物郁秀。徐居正日后修《东国通鉴》不知是否受到祁顺的启发?“果下马”“八梢鱼”(小章鱼)是朝鲜风俗的特征,藉此说明朝鲜民风朴质淳厚。值得注意的是,祁顺来自广东东莞,使行途中,对于朝鲜海滨别有会心,题海之作为数不少,例如其六题途中所观之海岛云:
六鳌戴三山,千仞浮海面。昔人求神仙,可望不可见。徒令方外士,欺世逞夸衒。謇予获东游,海岛看欲遍。惊涛破万里,乘此天风便。麻姑笑相邀,错落开华宴。醉乎王方平,来问水清浅。
在中国传统诗词的修辞中,海洋往往伴随神仙想象,而此诗乃在此一修辞传统的延长线。诗中一方面嘲讽方外之士求仙的无稽,一方面又运用麻姑与王方平关于东海“沧海桑田”的典故以与中国神仙传说相连接。大海之外,祁顺对于神圣山岳也有一种恭仰崇敬之心,如其五写朝鲜圣山金刚山:
金岩接宝山,相去纔咫尺。林峦弄光辉,径路多赭色。坤灵孕富媪,所产辄奇特。既堪方丽水,亦可比垂棘。我闻古贤士,义利中不惑。外物虽足珍,视之犹瓦砾。而况治国家,轻重尤当择。九经次尊贤,贱货而贵德。
此诗先是表明金刚圣山的光华璀璨与物产丰饶,不过全诗后半则口气一转,以为治国仍须以道德为本。在《朝鲜杂咏》组诗当中,祁顺基本上把朝鲜设定成为滨海仙山,甚至世外桃源,至少具有“君子国”的理想形貌。不过形塑此一理想国度的依凭并不是渺茫的神仙信仰,而是儒家真诚的道德教化。换言之,祁顺等于间接歌咏大明文教(以儒学为表征)的开明宏猷。《朝鲜杂咏》组诗中,也有数首作品对过往的历史抱持反省的态度,如其三云:
平壤多流水,发卢河更清。有唐恣吞噬,将士频东征。李侯率偏师,来破新罗兵。俘囚余万计,历岁凡四更。徒因一朝捷,博此千载名。当时交刃处,古渡扁舟横。渔翁伴鸥鹭,终日两忘形。
此诗以历史为主题,大体本事于《新唐书》所载:“总章二年,徙高丽民三万于江淮、山南。大长钳牟岑率众反,立藏外孙安舜为王。诏高侃东州道,李谨行燕山道,并为行军总管讨之,遣司平太常伯杨昉绥纳亡余。舜杀钳牟岑走新罗。侃徙都护府治辽东州,破叛兵于安市,又败之泉山,俘新罗援兵二千。李谨行破之于发卢河,再战,俘馘万计。于是平壤痍残不能军,相率奔新罗,凡四年乃平。”[注]《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五《东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97-6198页。诗尾的今昔之感,映衬出战争的无奈与人民的悲辛。透过历史回顾与省思,祁顺或许在朝鲜国看到一个理想世界的可能性。《皇华集》中固然不乏怀古咏史之作,但《平壤怀古》一诗仍然十分特别。其云:
朝鲜有国临东海,箕子封来几千载。就中平壤是雄都,昔时形胜今犹在。冈峦迂郁田野平,
楼台雉堞空中横。秦初远作辽东徼,汉末新传王险城。何年并入扶余裔,复自丸都迁此地。
沃沮濊貊纷来归,渺渺东西六千里。隋兵三举空扰攘,可堪秘记唐符皇。天山得捷薛仁贵,
浿水成功苏定方。振衰继绝不旋踵,五代之余遭有宋。玄菟乐浪息纷争,使介联翩奉朝贡。
嵩岳迁都久已成,长安旧名治西京。鲁阳城古人非昔,马邑峰高地有灵。胡元不道图吞并,
分疆直抵慈悲岭。西京内属将百年,赢得腥风污边境。圣明德化覃八区,乐天字小古所无。
鸭江东畔平安道,还入朝鲜旧版图。居民熙熙事耕凿,女解蚕桑士知学。中华气习见染深,
文物衣冠宛相若。使臣奉诏天上来,登高揽胜襟怀开。不须吊古重惆怅,写景新诗聊尔裁。[注]祁顺:《平壤怀古》,郑麟趾等编:《皇华集》,第2册,第617-619页。
此诗前半回顾了平壤城兴废过程,借此汇整了朝鲜此前的历史,末尾将朝鲜描绘成一个理想世界的缩影,而沾染中华气习,特别是儒学的价值规范,则是朝鲜王国人民安宁生活的保证。面对过去,无须惆怅,应该勇敢面对新挑战,迎接新目标,全诗收之以旷达襟抱与无穷的希望。同时,祁顺在诗中对朝鲜王国的高度肯定也格外值得注目。
通过以上分析,从某种角度来说,祁顺可谓“文化主义者”,此次出使朝鲜,他不仅对于朝鲜王国的文化成就大感叹服,同时,对儒学的化育之功也别有会心。而他的诏使诗一方面有异国风物,一方面也呈现对于普世价值的追求;既有强烈的历史感,又时时将目光投向当下瞬间。
结 论
张其淦曾经如是形容祁顺其人其诗曰:
祈(祁顺)巽川方伯,历官中外,以清洁自守。却海外之遗金,留江西之公帑。所谓以清白吏遗子孙者,斯人良不愧也。钟云瑞谓巽川讲敬斋、白沙之学,立志于警非寡过,儒臣之宗也。袁昌祚谓巽川诗文其志洁,故其旨冲和。其行芳,故其词雅淡,可谓知言也。
今读巽川诸诗,古体洁净,不事雕饰,近体五言如“地寒尤有树,塞远不扬沙”……七言如“陇梅欲寄春无便,池草春生梦有香”……诸作,均有冲淡夷犹之致。[注]张其淦:《东莞诗录》卷八,东莞张氏寓园刻本,1924年,第76页b。
在明清两代,出使朝鲜的使臣文人当中,能诗之名或有过于祁顺者,但祁顺在中朝诗史上却留下巨大的投影,特别是其与徐居正的往来无间的相互酬唱,几乎成为诗界传奇,是为立言;持节王事,不辱君命,且祁顺任职贵州石阡知府期间勤政爱民,离任之际,百姓泣别不忍去,是为立功;又终其一生,祁顺始终维持高洁清廉的操守,纵使在最困顿艰难的时刻,也不改对于儒学信念的贯彻与提倡,严于律己,春风待人,可谓立德。然而,祁顺却是个被遗忘的名字。学界近年颇着意于东亚文化交流,《皇华集》中的作者,如倪谦、董越、龚用卿、朱之蕃渐渐重回世人耳目之前,但在中朝诗学交流上占有一席之地的祁顺仍少被学界提及,是以笔者不揣浅陋,就正方家。
后世的朝鲜批评家也注意到使节往往并非中国诗坛大家,柳梦寅曾谓:“《皇华集》非传世之作,必不显。于中国使臣之作,不问美恶,我国不敢拣斥,受而刊之。我国称天使能诗者必曰龚用卿,而问之朱之蕃,不曾闻姓名。祈(祁)顺、唐皋铮铮矫矫,而亦非诗家哲匠。张宁稍清丽,而软脆诬指,终于小家。”[注]柳梦寅:《于于野谈》,《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第2册,第501页。钱谦益也说:“本朝侍从之臣,奉使高丽,例有《皇华集》。……东国(朝鲜)文体平衍,词林诸公,不惜贬调就之,以寓柔远之意,故绝少瑰异之词。”[注]钱谦益:《跋皇华集》,《牧斋有学集》卷四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528-1529页。虽然同样都对《皇华集》诗格靡弱深致不满,但两者对所致之由看法不一,却都归咎于对方。严格来说,《皇华集》本近馆阁体,故有“软”“柔”之讥不在意料之外。诏使诗当然未必与中国主流诗坛同声响应,但代表着一种特殊的美感经验,特别是异文化接触的因素,可谓别辟蹊径。更重要的是,对于两国诗坛的沟通,使节几乎是最重要的媒介。从前述《漂海录》的说法不难得知,朝鲜一代诗豪徐居正于当时为中国读者所知悉,祁顺居间转介之功实莫能或忘。
祁顺诗作中的时空观念,从宏观的角度看,也相当程度体现出明代诏使诗的共通点:对异国山川草木民俗保有某种程度的好奇心,修辞、句式、用韵具有一定程度的套袭,而且特别强调中华文化观念的普遍化。由诏使诗亦可看出,在朝鲜一朝,儒学话语与价值观念的影响力可谓无远弗届,孔庙成为两国人士共同崇奉的价值符号。而透过历史观照,明代使臣往往特别强调两国交流的密切,或投射自身的想望,例如刻意形塑箕子作为朝鲜文化主体性的根源。诏使诗未必完全反映历史真实的情况,但至少是部分真实心境的反映。在祁顺的诏使诗中,中华文化与皇明之化自有一种高大巍峨的姿态,同时他对朝鲜王国的山川风光、纯朴民风、圣君贤臣亦青眼有加。祁顺的诏使诗基本上仍属盛世之音,时空观与价值观仍然维持其一贯的调性,于清雅平和的馆阁诗风之外,又多了一点道学气,此固然是个性使然,但同时也是时代精神的反映,或许朝鲜历来诗论家对于祁顺的推崇亦不无此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