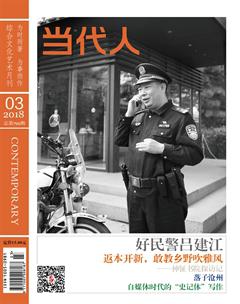城市的空间正义
彭秀良,历史学者、社会工作学者。著有《幽燕六百年:京津冀城市群的前世今生》《王士珍传》《段祺瑞传》《冯国璋传》《守望与开新:近代中国的社会工作》《一次读懂社会工作》。
何谓城市的空间正义?我的理解是,作为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统一体的城市空间,对于生活于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均质的或近乎均质的,人们不会由于生活的空间不同而产生被“隔离”或被“排斥”的状况。
故宫春色悄然去,无饰王冠只一端。
南下明珠三百箧,满朝元老面团团。
这是陈独秀诗集《金粉泪》中的一首。“故宫”是指故宫博物院,“春色”是指故宫文物,“无饰王冠”暗指王冠上嵌镶的珠宝被偷拆了。卢沟桥事变前,华北的形势越来越紧张,故宫博物院就着手将一些珍贵文物南运,陈独秀用此诗句讽刺国民政府高官对故宫财宝的侵占。虽然诗句带有讽刺意味,却也说明故宫已经成为公共空间,普通民众也可有权出入观赏文物,由此我想到了城市的空间正义问题。
北京城市空间的开放
北京作为元明清三个大一统朝代的都城,在城市布局和建筑方面有着严格的规制,这是中国两千年文化传统和政治传统的集中展现。尤其是清军占领北京后,内城汉人不论官民和职业,一律迁往外城,内城完全成为八旗驻地。后来又随着一系列措施的出台,内城变成了以紫禁城为中心,中央衙署为前导,八旗劲旅环卫的封闭的政治、军事结合体。
作为内城居民主体的旗民不农、不工、不商,只能从政当差或披甲当兵,他们是一群为君主专制政权服务的特殊群体,内城社会处于封闭状态。外城是非旗人居住区,同时这里也是城市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区域。外城的居民呈多样性的特点,他们不仅有名仕显宦,也有商贾匠作、佣夫走卒,同时还有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宦士子和沟通南北贸易的商人。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旗民分治”政策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被迫变通八旗制度,逐步以“旗民合治”取代“旗民分治”。 在上述背景和清政府政策的支持下,北京外城的民众不断涌入内城,内外城的居民结构变化十分明显。光绪初年,内城汉民不过3万余人,到宣统年间,内城汉民已增至约21万人。汉民定居内城以后,与旗人形成密切的邻里关系,增进了彼此的了解,有助于满汉民族隔阂的化解,促进商业活动的兴起和民间经济的发展。
不只是北京的内城空间对汉人开放,随着政治制度的变革,昔日的皇宫禁苑也开放为公共空间。1913年,天安门前的东西大道首先被打通,继而开辟南北池子和南长街两条贯通南北的大道,拆除大清门内的千步廊以及东西三座门两侧的宫墙,先后开辟南池子、南河沿、南长街等处的皇城便门。这样,天安门前形成了交通便利的中央广场。1914年,故宫前半部的武英殿先行开放。翌年,文华殿和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开放,并辟为北京古物陈列所。1924年,清废帝溥仪被逐出宫,故宫被政府接管。翌年,故宫博物院正式开放,成为东方最大的遗址性艺术博物馆。1914年,社稷坛被改造为中央公园,向公众开放,这是北京第一个近代公园。此后,太庙、天坛、地坛、先农坛、北海、中南海,以及西郊的颐和园等皇家禁苑相继开放,被开辟为市民文化、游艺和体育的活动场所,成为近代都市市民的公共空间。
北京城市空间开放的社会政治意义要远远超出北京这一座城市的范围,而具有全国性的示范作用。在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下,每一座城市的建筑规模和形制都与它的行政等级相匹配,因而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封闭空间,也就是“平头百姓”不许随便进入的地方。通常我们总以为,城市空间就是供人们居住、生活和工作的,其实这是很片面的认识,城市空间具有双重属性。
城市空间的双重属性
城市空间可分为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两种形式,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物质的城市空间是具体的、相对静态的空间,而社会空间是抽象的、相对动态的、渐进变化的空间。同时,城市空间既是社会性的,又是历史性的,这些都被看作城市空间的双重属性。老舍的名作《四世同堂》,开篇对小羊圈胡同的描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祁家的房子坐落在西城护国寺附近的“小羊圈”。说不定,这个地方在当初或者真是个羊圈,因为它不像一般的北平的胡同那样直直的,或略微有一两个弯儿,而是颇像一个葫芦。通到西大街去的是葫芦的嘴和脖子,很细很长,而且很脏。葫芦的嘴是那么窄小,人们若不留心细找,或向邮差打听,便很容易忽略过去。进了葫芦脖子,看见了墙根堆着的垃圾,你才敢放胆往里面走,像哥伦布看到海上有漂浮着的东西才敢更向前进那样。走了几十步,忽然眼一明,你看见了葫芦的胸:一个东西有四十步,南北有三十步长的圆圈,中间有两棵大槐树,四围有六七家人家。再往前走,又是一个小巷——葫芦的腰。穿过“腰”,又是一块空地,比“胸”大着两三倍,这便是葫芦肚儿了。“胸”和“肚”大概就是羊圈吧?
小羊圈胡同的形狀怪怪的,首先是物质性的存在,同时又是祁家人和其他五六家人家生活、交往的社会空间。老舍在一百多万字的长篇巨制中,设定的主要演出舞台就是这个狭小的、形状怪怪的小羊圈胡同,你方唱罢我登场,描绘出那个多灾多难的年代里的社会百态。小羊圈胡同的形状为什么怪怪的呢?老舍没有交代,也没有好事者作过考证,但是,我猜测是因为历经多少年的周边环境的变化使然。“小羊圈”坐落在北京西城的护国寺附近,最初可能就是一块空地,或者有些别的零散建筑。后来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便有了扩展居住空间的需求,空阔的“小羊圈”地区出现了第一批建筑,接着慢慢地增多,于是形成了老舍小说中所描写的奇特结构。城市空间的历史性,从我猜测的小羊圈胡同的形成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观察小羊圈胡同的形成过程,我们应该能够想象得到,那是居民自发建造房屋的结果,因为那个年代的北京(应该叫北平)还没有哪怕是粗疏的城市规划(即便有,也局促于非常有限的区域)。类似葫芦形状的小羊圈胡同,葫芦的嘴、脖子、腰、胸和肚等处都有住户,他们的活动构成了这一区域的社会空间,尽管各住户之间存在着社会地位上的差别,可这种差别不会太大,故而才能够组成一个朴素、平等的“小社会”。日军占领北平以后,“小羊圈”的居民结构发生了变化,原有的两家住户消失了,新迁来的日籍居民让胡同里的大多数原有居民感到压抑。是啊,在占领者的眼皮底下生活,生性谦和的北京人怎么受得了呢?小羊圈胡同原本和谐舒适的空间秩序遭到了破坏,放大尺度看,整个北平城的空间秩序都遭到了破坏,这又涉及到了城市的空间正义问题。
追求城市的空间正义
何谓城市的空间正义?我的理解是,作为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统一体的城市空间,对于生活于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均质的或近乎均质的,人们不会由于生活的空间不同而产生被“隔离”或被“排斥”的状况。可以这样说,追求空间正义,是近代以来国内外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
鸦片战争后北京城市空间的开放,属于时代剧烈变革中由政治因素而引发的城市空间变化,是城市空间正义的一个进展;《四世同堂》中小羊圈胡同的住户因日籍居民迁入而感到压抑,属于剧烈变革时期由军事因素引发的城市空间变化,是违反城市空间正义原则的。这两种情形都属于特例,在当代中国愈演愈烈的城市化进程中,如何最大限度地保证空间正义,才是最大的难题。
我的一位挚友,河北大学社会学系的林顺利教授,是以“城市贫困的空间研究”为研究方向而取得博士学位的。他选取了保定市的城区范围作为研究对象,以实证研究为依托,揭示出保定市的贫困空间主要集中在两个区域,一个是以火车站为核心的中心城区,一个是周边的“城中村”。他并且概括出造成这种格局的四种力量:经济体制改革、城市规划、土地商业开发以及居民的个人选择。我对这类实证研究是非常感兴趣的,因为城市贫困是城市空间正义损毁的最重要表征,我们采用什么样的城市规划模型和城市社会政策才能够确保城市的空间正义,必须给以足够的重视。对城市空间正义的追求,会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这从一位伟人的北京游记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1919年早春时节,青年毛泽东游览了故宫、北海等皇家宫苑。在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中,毛泽东深情地回忆说:
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可怜,可是在另一方面,古都的美对于我是一种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补偿。在公园里,在故宫的庭院里,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我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我看到杨柳垂在北海上,枝头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北庭冬树挂珠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激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如果昔日的皇宫禁苑没有开放为公共空间,青年毛泽东无从游览这些地方,他很可能就不会体验到“古都的美”了。对于仍处于高速城市化进程的当代中国来说,如何尽量减少封闭性空间、压抑性空间的出现,或许是追求城市空间正义的良好选择。
编辑:耿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