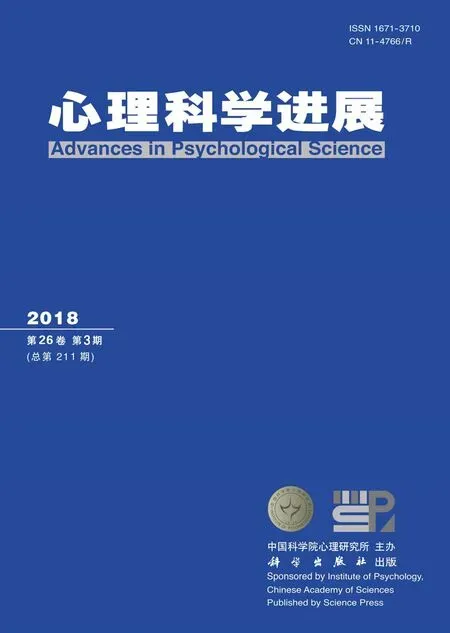动觉共情干预在舞蹈动作治疗中的应用*
阎 博樊富珉喻 丰
(1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北京100084) (2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西安710049)
1 引言
Rogers认为治疗师对来访者的共情是成功的治疗关系特点之一,也是治疗发生作用的充分必要条件之一(徐慧,侯志瑾,黄玉, 2011)。在舞蹈/动作治疗中(以下简称舞动治疗),以动作的方式表达共情是舞动治疗师经常采用的一种干预方式,称为动觉共情(kinestheticempathy)。动觉共情的目的是治疗师通过对来访者进行共情性地动作回应,与来访者建立起连接,以推动治疗进程(Berrol, 2006)。尽管上世纪60年代,舞动治疗临床工作者已提出动觉共情这一概念,但直到现在,动觉共情还没有形成明确的定义。在文献检索中我们发现,从1977年创刊的《美国舞蹈治疗期刊》至目前共刊出619篇文章,这些文章中包含“kinesthetic empathy”的有87篇,有关动觉共情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文章仅有9篇。国内已经发表的几篇舞动治疗综述(周红, 2004;陈丽, 2007;王雯晶, 2010;周宇, 2016),主要是从整体上介绍舞动治疗的源起、特点、发展现状及其局限。尽管有文章提到过舞动治疗中的共情(周红,2004;周宇,2016),但均没有展开叙述和讨论。作为一种干预方式,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动觉共情是舞动治疗研究及临床实务中的核心概念,也是舞动治疗产生疗效的主要贡献之一(Fischman,2009;Behrends,Müller,&Dziobek,2012),但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中,动觉共情研究却仍处于探索阶段。本文将简述动觉共情目前主要的理论研究成果,并探讨共情在舞动治疗中的应用及可能产生效果的原因。
2 共情中的行为成分
在介绍动觉共情内容之前,我们先引入一个与其联系十分紧密的概念——共情。共情也可被译为“移情”、“同理”、“替代体验”、“同情”或“投情”(肖福芳,申荷永,2010),主要是指一个人理解他人、试图去体会他人的内心世界、感受他人的感受,并做出恰当回应的能力(Stark &Lohn,1989)。德国哲学家RobertVischer最早使用Einfühlung一词用来表示人们把自己真实的心灵感受主动地投射到自己所看到的事物上的一种现象(引自郑日昌,李占宏,2006)。共情的研究持续了很多年,但由于其结构较为复杂,因而直到现在,共情尚未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心理学家Gladstein (1983)将心理咨询、发展心理学以及社会心理学中的共情内涵进行整合, 提出了两成分理论。该理论认为, 共情包括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两种类型, 其中情绪共情是指对他人情绪的感受, 认知共情是指对他人观点的理解。这一理论对共情研究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目前较新的观点认为, 单一维度单一理论并不能够有效地解释共情的内在机制, 共情应当是由个体认知、情绪和行为三个系统协调配合形成(刘聪慧, 王永梅,俞国良, 王拥军, 2009; 黄翯青, 苏彦捷, 2012)。从最初的单一成分构成, 到两成分构成, 再到加入行为成分, 可以看出人们对共情的理解和探索是在逐渐深入和丰富了。
实际上, 从开始探索共情内涵的时候, 就已经有研究者在思考动作、行为对共情可能产生的作用。提出“Einfühlung”的 Vischer以及将该词语翻译为“empathy”的 Titchener都认为动觉是共情重要的组成部分(引自Behrends et al., 2012)。Lipps在1923年就指出共情是主体间的、以动作为基础的过程, 对动作的内部模仿(inner imitation)是产生共情现象的重要原因(Behrends et al., 2012; 孙亚斌, 王锦琰, 罗非, 2014)。Allport (1961)同样认为共情的早期阶段就是客体行为动作层面的模仿。近几年, de Waal (2008)提出了共情与模仿的俄罗斯套娃模型(Russian doll model)。该模型的核心是知觉−动作机制(Perception-action mechanism,PAM), 这也是共情与模仿的基础。de Waal认为共情与模仿之间有着重要的相关关系, 当我们在体验共情的时候, 其实已经产生了相应的行为反应,但由于我们在意识层面没有及时感知到, 因此常常忽略了身体层面的参与。国内研究者也指出应当将行为成分纳入共情范畴, 从而提出了由情绪、认知和行为三个系统整合而成的共情动态模型(刘聪慧等, 2009)。
心理治疗和咨询领域对共情在行为层面带来的治疗效果也较早为人们所关注。Scheflen (1965)在研究谈话形式的团体过程时发现, 患者和治疗师之间特定的互动会以相似的形式和模式反复出现, 患者的非言语动作(如坐下、张望)和语言一样,对治疗效果产生重要作用。同理, 不同的臂部和腿部姿势会显著影响来访者对治疗师在温暖或共情维度的打分(Hudson, 1995; Smith-Hanen, 1977)。Ramseyer和 Tschacher (2011)在研究中随机选取了一些治疗师和来访者之间的互动片段, 结果发现, 高质量的非言语同步与治疗关系的质量和长程治疗结果呈正相关关系。国内学者赵春晓、江光荣和林秀彬(2016)等人对近些年心理咨询中的非言语行为进行了梳理, 并提出咨询师适当的非言语行为能够传达对来访者的同感, 建立起良好的咨询关系。
无论是共情研究领域内部还是与之有关的领域, 例如心理咨询和治疗等, 共情中行为成分的作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
3 动觉共情概念的发展
舞动治疗中, 共情的表现方式更多的是通过动作来表达, 也因此被称为动觉共情。动觉(kinesthesia)一词出现在 19世纪80年代, 泛指人们对动作和身体姿势的感知, 是对人们本体感受(proprioceptive)以及其他从内到外感官信息的整合(Behrends et al., 2012)。动觉与情绪感受紧密相关。20世纪初, 舞蹈家、舞动治疗师及相关研究者在心理生理学的影响下, 开始探讨动作与情感之间的联系。舞蹈家Laban和Martin等人从舞蹈动作的角度解释了两者间的关系(Behrends et al.,2012)。20世纪60年代, 舞动治疗先驱人物Marian Chace在 Sullivan的影响下提出了治疗关系的动觉共情(kinesthetic empathy)理念。她指出舞动治疗其实是关系治疗, 治疗师与来访者的关系由动作建立, 而动觉共情正是促进了治疗关系的发展(Fischman, 2009)。
对于动觉共情的概念和结构, 一些研究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早期的学者指出动觉共情是一种辩证的、螺旋式上升的结构, 从具体的角色采择观点和以身体为中心的技术上升为更加抽象的、高度情绪化的状态(Fraenkel, 1983)。有学者认为, 动觉共情是产生概念汇集的时刻。这一汇集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是由艺术、人文和科学以具身方式呈现出的特定文化现象组成, 另一部分是与共情密切相关的镜像神经元系统构成(Reynolds & Reason, 2012)。还有学者描述了动觉共情的内容, 即舞动治疗师在一定程度上共情并采纳来访者的动作, 有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吸收来访者表达出来的姿势或动作质感(Behrends et al., 2012)。而Fischman (2009)则指出, 动觉共情是一种动力性的治疗关系, 它包括了非言语交流、身体动作、舞蹈以及言语表达几个部分。总的来看, 研究者们有的是从对动觉共情的理解出发, 有的则从治疗过程出发, 提出了对动觉共情的认识, 但这些都是相对笼统地概括, 缺乏较为明确的定义。
4 动觉共情在舞动治疗中的应用——以镜像技术为例
动觉共情在舞动治疗中的具体操作技术包括镜像(mirroring)、见证(witnessing)和无领导者舞蹈(leaderless dance; Meekums, 2012)。目前, 舞动治疗相关文献中探讨最多的是关于镜像技术的内容(Berrol, 2006; McGarry & Russo, 2011; Eberhard-Kaechele, 2012)。
在谈话治疗中, 镜像是一种共情干预技术,这一技术也同样适用于舞动治疗。镜像作为动觉共情的主要干预技术, 是治疗师与来访者建立共情的第一步(李微笑, 2014; Fischman, 2009)。与谈话治疗不同, 舞动治疗中的镜像是指治疗师对发出者动作(也可以是面部表情或声音)质感进行的模仿, 包括动作背后的模式、动作质量以及情感基调等, 而并非仅仅仿效动作姿势(Berrol, 2006)。譬如来访者做出走路的动作时, 那么治疗师就要像镜子一样模仿其走路的形态, 以及走路时的精神状态和动作力度。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体验来访者当下的情绪和感受, 为后续的干预起到铺垫作用, 另一方面也让来访者感受到来自治疗师的关注和接纳, 有利于治疗关系的建立, 与此同时,还能让来访者在动作中对自己当下的状态有所觉察。
镜像技术有同步(synchrony)和回响(echo)两种具体表现形式(Fraenkel, 1983)。在舞动治疗中,同步是指治疗师和来访者或是团体成员在互动合作中, 使用同一时间/空间/内驱力(effort)执行某一动作或者改变某种姿势, (经过改变后)表现出来的动作可以相似也可以完全不同。同步有时间、空间和内驱力三种不同的同步方式, 双方可以有选择地进行同步。而回响则不需要双方的动作同步发生, 正如进行一场对话, 第一个动作和第二个动作之间会有延迟。这些干预或者动作变化的依据, 来自于拉班动作系统理论。该理论提出了非言语呈现的几个维度, 包括强度、持续时长、空间、节奏和/或者韵律(Berrol, 2006)。舞动治疗师可以选择上述一种内驱力(effort)或几种内驱力,与同步或回响结合, 通过动作、面部表情或者声音等非言语方式与来访者建立起互动。
镜像技术有助于增强治疗师和来访者之间的情感共鸣。Behrends等人(2012)发现, 与没有进行同步击鼓的搭档相比, 参与者会对进行过同步击鼓的搭档呈现出更多自发性的助人行为。Hudson(1995)指出, 对于精神病患者来说, 使用指定的节奏围成圆圈并保持同步动作, 可以促进患者之间关系的发展以及个体再社会化过程。在比较同步和回响哪种动作更让人感受到被理解的研究中,Fraenkel (1983)发现, 相比于同步而言, 回响更能让成年来访者体验到治疗师的共情。研究者猜测,这也许是因为回响是有延迟性的, 正如谈话治疗中的反馈, 给予了充分的反应时间, 这样的回应方式更能让他们体会到被理解。总之, 研究发现,镜像技术在个体治疗中可以增强个体的共情能力,在团体治疗中可以提升成员之间的凝聚力(Berrol,2006)。
5 动觉共情疗效的理论解释
5.1 镜像神经元理论
20世纪90年代, di Pellegrino等人利用单细胞记录技术在恒河猴的运动前区皮层下部边缘位置(F5区)首次发现了一些具有特殊属性的神经元,这些神经元在恒河猴自身执行目标导向手部动作或者观察同类执行相似动作时都被激活(di Pellegrino, Fadiga, Fogassi, Gallese, & Rizzolatti,1992)。由于这些神经元能像镜子一样映射其他个体的活动, 因而被命名为“镜像神经元”。镜像神经元的激活不仅体现在自我体验和观察他人方面,还体现在与情绪有关的内容上。研究者发现, 被试在模仿具有情绪化的面部表情时, 镜像神经元系统以及与情绪有关的脑岛和杏仁核会更显著地被激活(Carr, Iacoboni, Dubeau, Mazziotta, & Lenzi,2003; 胡晓晴, 傅根跃, 施臻彦, 2009)。情绪的脑区属于边缘系统, 而边缘系统参与并调节人类的基本情感(恐惧、愤怒、悲伤、厌恶、攻击等), 这表明当我们观察或亲身体验他人的情境时, 不仅激活了镜像神经元系统, 还激活了与情绪相关的脑区, 所以我们认为自己“共情”了他人的感受(Berrol, 2006)。Gallese (2005)认为这些与生俱来的镜像特性可以更好地解释社会、动作、情感认知或理解的机制。
通过上述镜像神经元的发展可以看到, 身体动作会对情绪、认知以及后续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在进行动作模仿的时候, 我们会在相似的脑区对他人的情绪化动作进行再创造, 体验他人情绪感受, 之后予以反馈(McGarry & Russo, 2011)。镜像神经元理论对理解动觉共情, 特别是对镜像技术的解释提供了理论依据。在镜像技术中, 舞动治疗师会与个体来访者一对一或者带领整个团体围成圆圈, 模仿他人的动作外形(shape)和动作质感。譬如, 当我们在观察到个体或者某团体成员很愉悦地做出快速抖肩的动作, 并对其动作进行模仿时, 我们自身的镜像神经元系统其实已经被激活, 同时被激活的还有边缘系统, 由于镜像过程受到情绪化动作反馈系统的调节, 因而使我们对快速抖肩这个动作产生了一种愉悦的感受。此时, 对方在看到我们对其进行动作模仿时, 镜像神经元系统和边缘系统受到了更强烈的激活。在这样的生物系统互动中, 成员彼此之间便产生了强烈的共情反馈(参见图1)。有研究者使用事件相关去同步化以及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的方法, 将专业舞者和非专业舞者进行比较研究, 结果发现,在呈现或想象与舞蹈动作有关的内容时, 专业舞者的脑区会产生比非专业舞者更强烈的响应或者激活(Calvo-Merino, Glaser, Grèzes, Passingham, &Haggard, 2005; Orgs, Dombrowski, Heil, & Jansen-Osmann, 2008)。因此有研究者提出, 如果对个体或者团体成员进行舞蹈技术层面的训练或者舞动治疗镜像练习的话, 将有助于强化他们的镜像神经元回路, 共情能力也许会随之增强(McGarry &Russo, 2011)。

图1 镜像神经元系统激活、镜像技术、边缘系统激活以及个体共情能力的关系图
5.2 依恋理论
从发展心理学视角出发, 共情由多方面组成,包括自我反省与自我感知、自我和他人的区分、(非言语)表达技巧以及社会互动身体层面的参与,任何一方面的缺失都可能会阻碍共情能力的全面发展(Behrends et al., 2012)。因此, 无论是(非言语)表达技巧还是身体层面的参与都是不可缺少的。
人类早期的联结建立在非言语沟通上, 早期的关系模式(母婴关系)会对孩子未来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Fischman, 2009), 而早期非言语经验会存留在来访者身体中, 有一些未经过深入加工的已知信息(unthought known)难以通过语言准确表达出来(Vulcan, 2009)。婴儿通过非言语沟通建立了对安全感或不安全感的感知, 以及对他或她自己的感知。如果在母婴关系中产生了失败和误解,便会形成相应的自我概念, 最后仅有部分自我得以发展或者形成一个虚假自我(false self; Wallin,2014) 。这也就是我们会在临床咨询或治疗中发现有的来访者将身体感知转换为情绪感受时有一定困难, 因此索性采取隔离或者解离感受的方式来避免体验以及整合这些情绪。久而久之, 情绪感受无法与身体知觉很好地融合, 致使在体验和表达自我情绪以及感受他人情绪上受到了影响。
基于早期关系具有的这种沟通特点, 舞动治疗师在治疗开始时会以非言语方式为主与来访者进行互动。治疗师将自身的情感以及身体层面的反应通过协调(attune)的方式(Jacobs, 1994), 与来访者建立起类似但不等同于母婴关系的治疗关系,例如会增加对来访者的积极接纳和抱持, 同时又会减少像父母一样对孩子的控制或教育。这种治疗关系正如谈话治疗中的反移情, 舞动治疗师在治疗中使用躯体反移情(somatic countertransference),即通过自己躯体的知觉与感受去理解来访者并对其做出回应(Vulcan, 2009)。由于舞动治疗是在关注双方关系互动中的行为, 因此, 治疗师不仅重视来访者在治疗过程中原始动作背后的情绪状态,还会关注来访者在互动中用怎样的动作模式回应治疗师, 以及这种回应模式背后的情绪和相关的心理议题(Eberhard-Kaechele, 2012)。
5.3 具身认知理论
具身认知强调身体在认知的实现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该理论认为, 认知过程的进行方式和步骤实际上是被身体的物理属性所决定的; 认知的内容是身体提供的; 认知、身体、环境是一体的,认知存在于大脑, 大脑存在于身体, 身体存在于环境(叶浩生, 2010)。Lakoff和 Johnson指出, 概念和语言通过隐喻的形式扎根于身体经验中, 从感官运动经验中获得, 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源自于自身身体的体验(引自Koch & Fischman, 2011)。
认知、身体以及环境是一体的, 因此当来访者进入治疗室后, 他们呈现的行为、举动往往都受到了过去经验的影响(Fischman, 2009)。此时,舞动治疗师会先通过镜像为主的技术, 通过模仿并感受来访者的状态, 建立治疗关系, 让来访者体会到被理解。慢慢地, 舞动治疗师会鼓励来访者关注一些之前没有注意到的动作模式, 使这些动作提升到来访者的意识水平。在进一步的治疗中, 治疗师还会鼓励来访者发展出新的语言及非言语层面互动模式, 促使他们产生与以往不同的思考内容和关注点, 从而扩展来访者对原有事物的认知(Koch & Fischman, 2011)。舞动治疗师发展出的动作和非言语交流方式正是融合了情绪与具身认知的理念。当来访者在治疗设置中体验到充分的心理安全时, 会有意愿体验不同于以往经验的动作, 而当这些新的动作融入成为来访者自发性动作的一部分时, 他们便得到了真正的改变(Fischman, 2009)。
6 未来的研究与展望
在以身体动作为导向的舞动治疗中, 治疗师鼓励个体关注身体自我以及在共享的动作空间(shared movement space)中呈现动作过程(Samaritter& Payne, 2016)。这些体验不仅有助于增强个体内部的自我联结, 而且能够促进个体在自我−他人知觉方面的改变, 进而提高信任和社会联结。在舞动治疗的过程中, 动觉共情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动觉共情理念的提出到现在, 这一概念就一直被研究者们认为是舞动治疗疗效的主要贡献之一(Behrends et al., 2012)。但是当前动觉共情研究中仍存在一些有待在未来继续探讨的问题。
6.1 还未形成明确的动觉共情概念
联系到共情定义研究, 有研究者在撰写共情文献综述的时候提到, 临床心理学家倾向于基于现象派哲学理解共情, 而实验心理学家在其操作性定义上则存在较多争论(陈晶, 史占彪, 张建新,2007)。这一现状与动觉共情的现状相类似。虽然临床实务工作者们提出了动觉共情的几种干预技术, 但是正如共情概念一样, 研究者的视角以及理论出发点不同, 因此至目前并没有形成统一明确的定义。在本文中,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 我们认为, 动觉共情是指治疗师透过来访者的动作表达理解其内心感受, 并通过以动作为主的干预技术(譬如镜像、回应、见证以及无领导者舞蹈等)回应其感受, 以此促进来访者对治疗师的信任,建立安全的治疗关系, 这有利于治疗过程进一步的深入。
6.2 缺乏直接有效地测量动觉共情的工具
当前对动觉共情的评估主要是以普遍测量共情的方法为主, 包括自我报告法、来访者报告法、观察者评价法以及生理测量法, 这些方法所采用的指标有语言指标、面部指标和生理指标(郑日昌,李占宏, 2006)。其他评估方法也有研究尝试在使用共情问卷的基础上, 结合拉班动作分析理论,加入了对来访者动作的编码分析(Fraenkel,1983)。由于动觉共情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情绪有唤起, 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 也可以考虑加入心理生理测量以及脑神经成像测量的方式, 使动觉共情的评估更具客观性。
6.3 缺少动觉共情的治疗过程以及治疗效果的研究
尽管动觉共情是建立治疗关系、促进团体成员关系的重要因素, 但是它的几种具体技术适用于哪些人群, 适用于哪一个治疗阶段仍然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加以了解。首先, 需要进一步验证基于动觉共情技术的干预效果。有研究者猜测, 治疗师在身体和情感层面与来访者进行动作协调(attune), 可以促使来访者的镜像神经元得到激活, 从而建立有力的治疗关系(Berrol, 2006;Mcgarry & Russo, 2011; Winters, 2008)。尽管一些临床案例描述了来访者的改善和症状有所好转,也有少量文章提到了动觉共情的干预过程和干预内容(Behrends et al., 2012; Behrends, Müller, &Dziobek, 2016), 但关于动觉共情干预效果的验证、治疗过程的评估, 以及动觉共情干预方案的研究则很少见。
其次, 增强对动觉共情的过程−效果研究, 以探究其在治疗过程中的作用。在精神分裂症团体中, 如果镜像动作被唤起的程度过于强烈, 治疗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Behrends et al., 2012)。因此研究者提出, 舞动治疗师在治疗过程中运用镜像技术时, 需要根据来访者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该技术使用的频率和强度。结合前文镜像技术的理论依据, 我们得到的启发是, 在了解哪些人群更适合镜像干预技术或者其他特定的动觉共情干预之外, 也需要关注在整个治疗过程中, 怎样的干预频率和强度更有利于来访者的改善。McGarry和Russo (2011)提出, 未来可以采用以镜像干预技术为主的舞动治疗方式, 对模仿能力或者镜像神经系统有缺陷的群体进行干预, 譬如自闭症群体,也包括镜像神经系统受损的脑卒中后或脑损伤患者。他们进一步提出假设, 镜像干预技术能够增强个体的共情能力, 而最有效的干预方式是在伴随音乐的动作干预之下产生的。因此, 除了上面谈到的研究干预技术的使用方式之外, 还可以探讨包括镜像干预技术在内的动觉共情技术在怎样的治疗设置情境中会产生更好的治疗效果。
最后, 从更多的角度和领域对动觉共情进行诠释。从当前已有研究进展来看, 对动觉共情的解释主要从镜像神经元的角度出发, 对其干预技术的探讨也以镜像技术为主。然而, 镜像神经元是从神经科学角度对动觉共情的部分解释, 镜像技术也只是动觉共情的一种干预手段。事实上, 动觉共情涉及的内容是一个交叉的领域, 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 可以利用丰富的临床实践指导研究的开展, 并且结合其他相关学科或领域加以考察。
陈晶, 史占彪, 张建新. (2007). 共情概念的演变.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5(6), 664–667.
陈丽. (2007). 舞动的力量——浅谈舞蹈动作治疗的内涵及其运用.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 54–57.
胡晓晴, 傅根跃, 施臻彦. (2009). 镜像神经元系统的研究回顾及展望.心理科学进展, 17(1), 118–125.
黄翯青, 苏彦捷. (2012). 共情的毕生发展: 一个双过程的视角.心理发展与教育, 28(4), 434–441.
李微笑. (2014).舞动治疗的缘起.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刘聪慧, 王永梅, 俞国良, 王拥军. (2009). 共情的相关理论评述及动态模型探新.心理科学进展, 17(5), 964–972.
孙亚斌, 王锦琰, 罗非. (2014). 共情中的具身模拟现象与神经机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2(1), 53–57.
王雯晶. (2010). 舞蹈心理治疗的跨文化研究述略.文学界:理论版,(5), 284–285.
肖福芳, 申荷永. (2010). 论empathy的翻译及其内涵.心理学探新,30(6), 18–20.
徐慧, 侯志瑾, 黄玉. (2011). 共情与真诚: 对罗杰斯三个不同时代案例的内容分析.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9(2),265–267, 202.
叶浩生. (2010). 具身认知: 认知心理学的新取向.心理科学进展,18(5), 705–710.
赵春晓, 江光荣, 林秀彬. (2016). 心理咨询中的非言语行为.心理科学进展, 24(8), 1257–1265.
郑日昌, 李占宏. (2006). 共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4), 277–279.
周红. (2004). 舞蹈治疗简介.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8(11),804–805.
周宇. (2016). 舞蹈治疗的回顾、现状与展望.北京舞蹈学院学报,(1), 80–84.
Wallin, D. J. (2014).心理治疗中的依恋: 从养育到治愈,从理论到实践(巴彤, 李斌彬, 施以德, 杨希洁 译).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Allport, G. W. (1961).Pattern and growth in personality.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Behrends, A., Müller, S., & Dziobek, I. (2012). Moving in and out of synchrony: A concept for a new intervention fostering empathy through interactional movement and dance.The Arts in Psychotherapy,39(2), 107–116.
Behrends, A., Müller, S., & Dziobek, I. (2016). Dancing supports empathy: The potential of interactional movement and dance for psychotherapy. In G. Hauke (Ed.),European psychotherapy 2016/2017: Embodiment in psychotherapy(pp. 99–131). Milton Keynes: Books on Demand.
Berrol, C. F. (2006). Neuroscience meets dance/movement therapy: Mirror neurons, the therapeutic process and empathy.The Arts in Psychotherapy,33(4), 302–315.
Calvo-Merino, B., Glaser, D. E., Grèzes, J., Passingham, R.E., & Haggard, P. (2005). Action observation and acquired motor skills: an FMRI study with expert dancers.Cerebral Cortex,15(8), 1243–1249.
Carr, L., Iacoboni, M., Dubeau, M. C., Mazziotta, J. C., &Lenzi, G. L. (2003). Neural mechanisms of empathy in humans: A relay from neural systems for imitation to limbic area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0(9), 5497–5502.
de Waal, F. B. M. (2008). Putting the altruism back into altruism: The evolution of empathy.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59, 279–300.
di Pellegrino, G., Fadiga, L., Fogassi, L., Gallese, V., &Rizzolatti, G. (1992). Understanding motor events: A neurophysiological study.Experimental Brain Research,91(1), 176–180.
Eberhard-Kaechele, M. (2012). Memory, metaphor, and mirroring in movement therapy with trauma patients. In S.C. Koch, T. Fuchs, M. Summa, & C. Müller (Eds.),Body memory, metaphor and movement(pp. 84–267).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Fischman, D. (2009). Therapeutic relationships and kinesthetic empathy. In S. Chaiklin & H. Wengrower (Eds.),The art and science of dance/movement therapy: Life is dance(pp.33–53). New York: Routledge.
Fraenkel, D. L. (1983). The relationship of empathy in movement to synchrony, echoing, and empathy in verbal interactions.American Journal of Dance Therapy,6(1),31–48.
Gallese, V. (2005). The intentional attunement hypothesis the mirror neuron system and its role 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In: S. Wermter, G. Palm, & M. Elshaw (Eds.),Biomimetic neural learning for intelligent robots(pp.19–30).Berlin Heidelberg: Springer.
Gladstein, G. A. (1983). Understanding empathy: Integrating counseling, develop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perspectives.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30(4),467–482.
Hudson, K. A. (1995).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the use of cotherapy in dance/movement therapy.American Journal of Dance Therapy, 17(1), 25–43.
Jacobs, T. J. (1994). Nonverbal communications: Some reflections on their role in the psychoanalytic process and psychoanalytic education.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42(3), 741–762.
Koch, S. C., & Fischman, D. (2011). Embodied enactive dance/movement therapy.American Journal of Dance Therapy, 33(1), 57–72.
McGarry, L. M., & Russo, F. A. (2011). Mirroring in dance/movement therapy: Potential mechanisms behind empathy enhancement.The Arts in Psychotherapy,38(3),178–184.
Meekums, B. (2012). Kinesthetic empathy and movement metaphor in dance movement psychotherapy. In D. Reynolds& M. Reason (Eds.),Kinesthetic empathy in creative and cultural practices(pp. 51–65). Chicago: Intellect.
Orgs, G., Dombrowski, J. H., Heil, M., & Jansen-Osmann, P.(2008). Expertise in dance modulates alpha/beta event-related desynchronization during action observation.European Journal of Neuroscience,27(12), 3380–3384.
Ramseyer, F., & Tschacher, W. (2011). Nonverbal synchrony in psychotherapy: coordinated body movement reflects relationship quality and outcome.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79(3), 284–295.
Reynolds, D., & Reason, M. (2012). Introduction. In D.Reynolds & M. Reason (Eds.),Kinesthetic empathy in creative and cultural practices(pp. 17–25). Chicago:Intellect.
Samaritter, R., & Payne, H. (2016). Being moved:Kinaesthetic reciprocities in psychotherapeutic intera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nactive intersubjectivity. In G.Hauke (Ed.),European psychotherapy2016/2017:Embodiment in psychotherapy(pp. 50–65). Milton Keynes:Books on Demand.
Scheflen, A. E. (1965). Quasi-courtship behavior in psychotherapy.Psychiatry-Interpersonal and Biological Processes,28(3), 245–257.
Smith-Hanen, S. S. (1977). Effects of nonverbal behaviors on judged levels of counselor warmth and empathy.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24(2), 87–91.
Stark, A., & Lohn, A. F. (1989). The use of verbalization in dance/movement therapy.The Arts in Psychotherapy,16(2), 105–113.
Vulcan, M. (2009). Is there any body out there?: A survey of literature on somatic countertransference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DMT.The Arts in Psychotherapy,36(5), 275–281.
Winters, A. F. (2008). Emotion, embodiment, and mirror neurons in dance/movement therapy: a connection across disciplines.American Journal of Dance Therapy,30(2),84–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