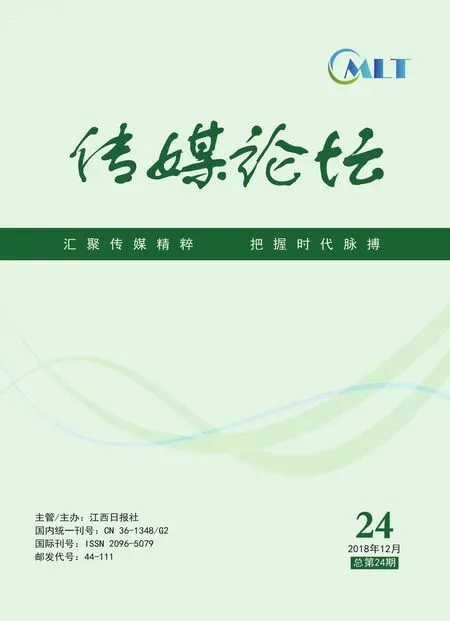《找到你》:“身份迷失”的母亲形象的建构
尹艳瑚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上海 200235)
一、引言
吕乐导演的电影《找到你》翻拍自韩国电影《迷踪:消失的女人》,经过本土化的改编后,叙事节奏更加紧凑,增强了悬疑性,内涵更为丰富,不仅书写了“爱不释手”的大写母爱,更是对不同阶层母亲困境进行了立体的揭示,这部聚焦现实女性问题的佳作具有强烈的现实质感。影片运用悬疑片的结构技巧讲述故事,从女律师李捷在垃圾堆疯狂寻女切入,通过对保姆孙芳带走多多案件进行追踪,刻画了三个女性不同职业身份的母亲角色:律政精英的白领李捷、外来务工的保姆孙芳、全职太太的朱敏。这三位母亲都面临“失婚” “失子”的问题,都处于对自我角色定位的迷失与婚恋困境之中。笔者认为导致她们“身份迷失”的主要有三重困境。
二、婚姻中女性面临的三重困境
(一)“精英”与“母亲”角色的权重取舍
在当今这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为了养育孩子,高学历女性组成的“全职太太”群体日益壮大,她们一方面过着享受着物质充裕的生活,分享着孩子成长的喜悦,另一方面也面临着一旦婚姻触礁,便可能“失业”的潜在隐患。更多的城市女性面对高房价、高成本、高消费、快节奏的生活挤压,选择投身职场,寻找安全感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追求给孩子提供更好的物质保障。
李捷和朱敏代表了大多数生活在都市的知识女性。她们面对职业和家庭的矛盾时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毕业于江城理工的大学的朱敏,从怀孕开始,为了更好地养育孩子,辞去工作,作了全职的家庭主妇,她以女儿的成长作为自我价值的替代和安慰,正如她对李捷所说的:“为了孩子我什么都付出了”。早在她怀孕的时候就发现丈夫在外面鬼混,为了孩子她选择了隐忍,因而抑郁多次去医院就诊。可是,她仍未能维系住名存实亡的婚姻,被迫离婚,在女儿被丈夫藏匿的情况下,她的精神大厦坍塌,选择了自尽。影片令人深思的是,一个精神缺乏稳定性的母亲,一个迷失自我的母亲,真的可以为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吗?
而李捷作为一个职业律师,靓丽干练,带有一点中产阶级的优越感。生活磨砺出她自私、冷漠的性格,她把自我价值的实现放在首位,成功地活出了女性主义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自尊、自爱、自强。当然,她并没有放弃母亲的角色,她期待自己的女儿“人生不能被爱情和婚姻定义,她应该活得比我们自由”。为了让女儿多多过上她认知中理想的生活,她全身心投身于工作之中,甚至要参加各种应酬、忍受异性骚扰,而把孩子交给了根本不知根底的保姆养育。虽然她挤出午休时间陪伴女儿,但她在幼小的女儿成长中多数时间处于“缺席”。保姆可以照顾孩子,但是可以教育好孩子吗?吕乐安排了这样的情节:多多把鼻涕蹭在保姆孙芳的衣服上,孙芳对此不以为然,对这种不礼貌的行为并没有加以教育制止,保姆对孩子的言行教育基本没有,如此的“放养”于保姆真的合适吗?
(二)“贤妻”与“弱夫”婚姻期待的错位
影片中对于三对夫妻的相处所给镜头极少,对于朱敏夫妇甚至没有认识的镜头,但是通过有限的镜头、当事人的讲述和第三方的回忆,已经把他们的情感冲突非常清晰地呈现在观者眼前。
保姆孙芳嫁给了城乡接合部一个开汽车修理铺的当地男人并且由此落户。但是在新婚之夜由于她不愿喝酒便被丈夫当众扇了耳光,丈夫不仅好赌输掉了汽车修理铺,还对怀孕中的孙芳继续施暴,然而她坚信“等孩子出生就好了”。为什么等孩子出生就好了?显然在婆家的观念中,女人应该给丈夫生下男孩传承香火,孙芳认为如果她完成了这项使命,作为外来打工妹的她可以被丈夫及家长更为看重。可是,她生下了一个患有先天性胆道闭锁的女儿,在小医院确诊后,丈夫就放弃了医治,也对自行去救治的孙芳和孩子不管不问。不仅如此,甚至在孙芳提出离婚的时候,除了勒索还意图侵犯。可见孙芳的婚姻是一种缺乏感情基础的浮萍式婚姻,在丈夫的认知中妻子只是他满足欲望和传宗接代的工具,全然没有为夫为父的责任意识,在这种婚姻中孙芳无法获得尊重和情感,成了一个异常艰难的患儿母亲。
现代婚姻中,背叛行为的泛滥,使脆弱的夫妻关系难以负重。朱敏的丈夫在妻子怀孕期间就已经出轨,接受过高等教育,知书达理的全职太太并没有满足他的婚姻期待,婚后他仍然出轨以致婚姻解体。他想的只是如何争夺女儿的抚养权,没有体恤妻子的付出,更没有想到缺失母亲家庭对孩子的成长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一切都以自我为中心,既有传统的夫权意识,但是却缺少了丈夫的责任意识,缺少了对全职太太这种身份的正确认知和尊敬,缺少了一个父亲的理性角色意识。
家庭的控制权成为婆媳争端的焦点,作为扮演儿子与丈夫双重角色的中国男人不仅要承受夹板气,还要有足够的协调能力。李捷的丈夫是个非常孝顺母亲的“妈宝男”,对母亲言听计从,作为个性独立的职业女性,李捷不愿受制于婆婆,更不能忍受丈夫对婆婆的情感倾斜,质问他:“你能像个男人一样自己做一回决定吗?”而田宁对作为律师的前妻也非常之不满,他不满于妻子的强势,也不满于妻子把孩子交给保姆而投身职场,他问李捷:“你觉得你还像女人一样吗?”他期待顺从婆婆,关心丈夫,照顾孩子,而李捷则更多的把精力投入工作之中,在家庭中少了忍让和牺牲,甚至有些强势。直到孩子走失,她在寻找的过程中才意识到:“对着孩子我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我觉得自己不配当一个母亲”。
当夫妻对于彼此婚姻角色的期待出现错位,家庭生活出现矛盾的时候,如何审视自己,如何化解矛盾,如何维系婚姻呢?这无疑是影片留给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
(三)“经济”与“精神”的双重贫困
影片中最为悲剧性的角色就是保姆孙芳,一个处于社会边缘的外来务工者。
由于老家穷缺水,她和同乡们来到了城市,相对充裕的物质生活,使她们不愿意回去。她希望在城市留下来,但是由于缺乏文化资本,无法实现阶层的上升,同时由于外来务工者的身份,使她在婚恋中处于边缘和弱势的地位,只能嫁给处于底层,不仅有赌博恶习,而且长期家暴的丈夫。她把美好生活的期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在片尾有个闪回镜头,怀孕中的孙芳无限温柔地对着腹中的宝宝说:“妈妈爱你,妈妈要把最好的都给你”。女儿的患病使她陷入精神的苦痛和经济的困境,为了筹集医药费,无助的她利用“身体”这一资本,陪酒、出卖皮肉、多次借高利贷,为了节省费用她从垃圾桶中捡拾别人吃剩的盒饭,可是由于巨大的开销,即使有医务人员的筹款帮助,最后仍然因为拖欠医药费太多而被强行出院。风雨交加之夜,由于住所的闭塞,错过了医治,她失去了一年八个月零两周的女儿。
绝望的境遇,使她产生了近乎疯狂的愤怒,失去了孩子的孙芳,好像变了一个人,她决定为女儿复仇,拐卖抢占女儿珠珠床位的多多。为此她陷害多多的保姆弄伤珠珠,贿赂李捷邻居阿姨,如愿当上了保姆。作为底层的保姆,她要为李捷清扫酒吐后的污秽,要谦卑地给女主人的脚脖后面贴上创可贴,可是在和李捷的关系中,她只是一个被雇佣者,她无人倾诉,把不知何所安葬的女儿尸体藏在李捷家的冰箱,请求情人张博放火焚烧她防卫过当杀死的丈夫,失女之痛,杀夫之惧,债务之压,活得艰难和死的恐惧,使她渴望身为律师、身为女人、身为母亲的李捷听她倾诉,为她指引,可是多次刚刚开口,就被李捷打断,无法挣脱困境的孙芳无暇顾及冰箱里的女儿,仓促之间决定远离这里,带走多多。她把视同女儿的多多带到向往的海岛,面对紧随而来的李捷和团团围住的警察,她跳向了广阔的大海,以死来换的最后的解脱。
孙芳一生是悲剧的,从小忍受经济的贫困,到了城市成为边缘人,成了家,没有感受丈夫的温情,而巨额的医药费再次把她推向贫困的深渊,唯一爱她的张博还因为她而负债累累,认知的局限,使她无法寻找解救女儿、解救自己的出路,面对“经济”和“精神”双重贫困,她唯有跳入大海,孤独地死去。影片以此结局,运用了慢镜头,给观者营建一种格外凄美而又悲伤之感。
三、“困境”背后的主题表达
吕乐导演的《找到你》获得了很高的口碑,除了对整体结构和叙事的精致打磨之外,更多还在于成功的现代“失婚”母亲形象塑造和深入的主题表达。
(一)婚姻关系的两性思考
通过“身份迷失”的三位母亲形象的塑造,既呼唤人们对全职太太身份的尊重,对职业女性工作家庭分身乏术的体恤,对底层女性经济贫困化、认识局限化、情感麻木化的同情,更引发女性对现代婚姻关系中的定位进行深刻思考。追求自我价值与教育孩子、关爱丈夫、照顾老人各应占有怎样的比重?当婚姻出现危机的时候,是以个人的情感感受为出发点,还是顾及孩子的成长理性处理?作为女性,如何兼顾幸福感与责任感,影片没有给出一个美好的形象以作样板,给女性留下很大的思考空间。
当然,走出婚姻困境不仅需要女性努力,也需要男性观念的更新,行为的调整。首先,家庭生活中,男性需要有婚姻的忠诚观念,增强自制力。三个丈夫,不仅王总出轨,而且从李捷说田宁:“如果到法庭,你是过错方,你将一无所有。”的话中,暗示观者除了“妈宝男”的问题,婚内出轨也极可能是导致两人感情破裂的因素。其次,要和妻子在家庭角色的分工上达成共识,并且对妻子的付出予以尊重。王总没有对妻子作为全职太太的家庭付出予以充分的尊重和认可,田宁与李捷各自忙于事业没有对婚姻角色的分配进行有效沟通,洪家宝把孙芳视为欲望和生育的工具,同时还要求她孕期工作。这些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只会导致婚姻关系的恶化、解体,使孩子失去快乐成长的原生家庭。当然任何一个家庭中的男性不可能是完人,但是可以调整自己刚毅性格下的柔韧性。
(二)家庭解体后的生存境况
影片中所聚焦的家庭问题值得我们警醒。在现代社会中家庭不仅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更是身体和内心得以抚慰的港湾,是社会新生群体成长的重要环境。现代社会高节奏、重效率、多压力的生存境况下,加之自我为中心思想的膨胀,婚姻关系更加脆弱,离婚率攀升。“无枝可依”的迷失者何处安放自己的情感?影片中的职业性女性李捷,长期隔绝社会的朱敏,底层保姆孙芳,各种失婚的女性无不面临着生存的压力和安全感的缺失,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家庭实体性的瓦解,并不意味着个体的解放,而是流放。
更为令人忧虑的是影片中所暴露的“缺席式”的抚育孩子现象。从留守儿童,到城市中的单亲家庭的儿童乃至父母全部缺席的儿童,占有相当比例,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公民,他们的情感空间,他们的责任意识,他们的道德教育又怎能不存在一定的隐患?
(三)不同阶层的包容与关爱
影片通过孙芳的双重困境,反映了外来务工女性婚恋生活中“无奈中的选择”和“选择中的无奈”,婚姻关系中被视为“生育工具”的客体性,社会关系中的卑微性、被失语性,从而增强了影片的深度和力度。
由于地域差异、城乡差异,贫困与“城市梦”驱使他们来到城里。他们的劳动力和身体已融入现代化进程,而社会身份和权利仍被现代化拒之门外。作为低收入、低学历的群体,常常被建构成为廉价、卑微、次等的社会身份,她们在阶层、城乡的社会分层结构下承受着歧视。她们的社会结构空间除了雇主外,只有同乡、外来务工者,情感上很难与城市中大多数群体进行沟通,产生共鸣,获得理解。所以很容易在遇到困境的时候,产生极端的仇视心理,从而影响社会和谐。影片结尾李捷的忏悔,无疑是一个很大的亮点,呼唤城市的市民对外来务工者予以更大的包容、理解和关爱。
四、结语
吕乐的《找到你》讲述的不仅是一个找到孩子的故事,还讲述了找到在婚姻生活中的自我定位,找到在生活中被忽略的底层“他者”的过程。这部现实主义的电影无疑和《我不是药神》《狗十三》等关注现实的作品一样代表了我国电影制作发展的一个新趋向。这种创作倾向,意味着更多的电影人在关注票房的同时,对电影社会教化功能的予以关注,正如著名学者厉震林所说:“许多伦理是通过文化娱乐形式形成的,例如通俗易懂的舞台艺术、口头文学,中国戏曲自古就有‘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的观念。因此,中国的伦理系统以及信仰高度,许多是通过文化形态而形成的,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就置换为一种宗教的功能,它承担着中国国民‘心灵养护’的责任。”电影现实主义创作的新趋向有利于推动社会观念的塑形,新型伦理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