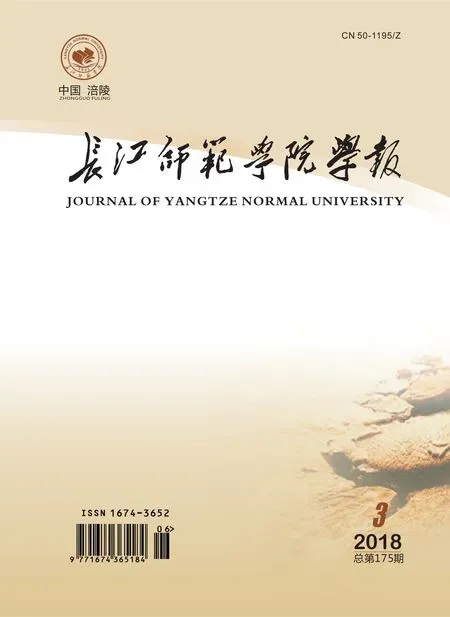冕宁土司制度探析
韩正康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36)
冕宁地区的土司政权成立于元朝,先后经历过明朝和清朝的“改土归流”,土司实力从明朝“改土归流”后开始大幅度削弱,到清朝“改土归流”后更是一蹶不振,到民国时期自行消亡。
一、冕宁概况
土司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在西南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统治制度。它效仿唐朝的羁縻制度,始建于元朝,完善于明清时期,在晚清和民国时期日渐衰落,直至民主改革时彻底废除土司制度。
冕宁县位于四川省西南部,东邻越西、喜德两县,南邻西昌市,北邻石棉县,西与九龙县为邻,西南与木里、盐源两县接壤。地处四川省西南部安宁河上游,中有牦牛山,东有小相岭,西面是锦屏山,安宁河和雅砻江自北向南横贯全境,形成“三山夹两河”的地理格局,自古以来就是四川到云南的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就民族分布格局而言,其西面是康巴藏区,东面属彝族聚居区,在辖区内除汉族外,藏族和彝族均具有较大的影响。
冕宁作为传统藏族聚居区的历史一直延续到民国初期。元朝时期,冕宁和许多地区一样都纳入到了中原王朝的管辖之下,并实行土司制度。就目前的土司研究来说,四川是相对薄弱的。就四川来说,土司研究主要集中在康巴藏区和嘉绒藏区,对凉山土司的研究相对来说较少,对冕宁土司的研究则更少。鉴于此,这里通过文献材料结合田野调查,对冕宁土司制度作一个力所能及的梳理,不当之处,还望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二、研究综述
涉及冕宁土司研究的文章不多,现简单归纳于下:方国瑜的《彝族史稿》依据咸丰《冕宁县志》总括了土千户、土百户和土目的数目,统计出各少数民族总的村寨数目,并将这些村寨与该《志》卷首的疆域图所载地名对照,发现“西蕃族在北部及东部,莫些族在西部,而倮亻罗族在南部泸沽附近,三族各为区域”[1]。何耀华对冕宁土司研究也有所涉及,他在《川西南藏族史初探》中罗列了咸丰《冕宁县志》中记载的土司,通过实地调查,并结合其他史料,证明了“大渡河以南至冕宁地区,自古为西番区域,但迟至唐代就有磨些与之杂居”[2]。龙西江的《凉山境内的“西番”及渊源探讨》[3],在介绍冕宁藏族的情况时,依据咸丰《冕宁县志》《四川通志》《邛嶲野录》等史料,将清代冕宁地区的藏族土司按不同汝都(部落)或不同支系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赵心愚的《咸丰〈冕宁县志〉的资料来源、篇目特点及纳西族史料价值》[4]一文,运用咸丰《冕宁县志》的史料,分析论述了瓦都、木术凹、瓦尾、耳挖沟、七儿堡5个土目及其属民的民族属性;认为土司司法活动在雍正改土归流后逐渐消亡。张晓蓓的《从冕宁司法档案看清代四川土司的司法活动》[5]一文依据冕宁的司法档案,认为一直到清末,冕宁的土司还在流官的管理下,参与地方的司法活动,活动内容涉及组织土兵维护治安、参与审判与调解、协助缉拿逃犯。袁晓文和韩正康的《多续藏族土司研究》[6]一文通过对咸丰《冕宁县志》及相关材料中有关多续藏族土司的记载,结合田野调查所得材料,说明了冕宁县多续藏族土司制度的沿革、运作和土司辖区文化的变迁,并对土司制度的消亡作过一些探讨。可见,对冕宁土司的研究还很薄弱,基本局限于清朝时期,对元明时期冕宁的土司制度很少涉及,一方面是由于缺少必要的文献材料,另一方面是因为留存下来的实物很少。
三、冕宁土司制度
(一)元朝时期冕宁土司制度
元朝是我国土司制度正式建立的第一个朝代,实行具有羁縻性质的土司制度,将土官纳入国家系统,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宣慰司,安抚司,招讨司,路、州长官司等行政机构,实行“土流共治”,根据不同官职给予不同品秩,实行由蒙古人或色目人为达鲁花赤而土人为土官的行政制度。这种治理模式被以后的朝代沿用下来,只是治理方式有所不同而已。
元朝时期,地处西南的冕宁地区被纳入到国家行政体系之中,属云南行省的罗罗蒙庆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管辖。当时冕宁境内的治理模式就是土司制度,但并没有设立达鲁花赤一职,这或许是由于在元朝藏族属于色目人的关系。据《元史》记载,元泰定三年八月辛丑“西番土官撒加布来献方物”[7]672。致和元年三月戊子“云南土官撒加布降,奉方物来献,置州一,以撒加布知州事,隶罗罗宣慰司,征其租赋”[7]686。这里的记载非常简略,除知道这个州属于罗罗宣慰司、知州为撒加布外,具体位于什么地方不清楚,州的名称是什么也不明确。《明史》记载:“宁番卫,元时立于邛都之野,曰苏州。”[8]8019-8020这样我们可以肯定元朝在1328年设立的以撒加布任知州的这个州就是“苏州”,其区域与明朝宁番卫的区域相当,则此州主要部分当在今冕宁县。对此,咸丰《冕宁县志》也有相应记载:“至元十二年置苏州,属建昌路。分其地置总管府,设罗罗斯宣慰司以统之。初属四川行省,寻改属云南行省。明洪武二十二年罢宣慰司,立苏州卫,二十七年改为宁番卫军民指挥使司,属四川行都司。皇朝初亦曰宁番卫,雍正六年罢卫改置冕宁县属宁远府。”[9]16从这则材料可以清晰地看到冕宁县建制的大致沿革:苏州—宁番卫—冕宁县,不同的只是辖区范围,但核心区是一致的。冕宁县原大桥镇所在的盆地中部偏西地区名叫“苏州坝”,正是元朝时期苏州土知府的治所所在地,20世纪末大桥水库建成后,“苏州坝”已沉入库底。宁番卫治所最初在元朝苏州治地,后迁现在冕宁县城所在地。
《元史》载至顺元年闰七月戊申,“罗罗斯土官撒加伯及阿陋土官阿剌、里州土官德益兵八千撤毁栈道,遣把事曹通潜结西番,欲据大渡河进寇建昌。四川行省调碉门安抚司军七百人,成都、保宁、顺庆、广安诸屯兵千人,令万户周戡统领,直抵罗罗斯界,以控扼西番及诸蛮部。又遣成都、顺庆二翼万户昝定远等,以军五千同邛部知州马伯所部蛮兵,会周戡等,从便道共讨之,发成都沙塘户二百九十人防遏叙州。征重庆、夔州逃亡军八百人赴成都。(八月)辛亥,云南跃里铁木儿以兵屯建昌,执罗罗斯把事曹通斩之。(九月)丙戌,邛部州土官马伯向导征云南军有功,以为征进招讨,知本州事。(十一月丙戌)罗罗斯撒加伯、乌撒阿答等合诸蛮万五千人攻建昌,跃里铁木儿等引兵追战于木托山下,败之,斩首五百余级”[7]卷34,763。不知此撒加伯是否是撒加布的异写,由于年代久远,已难考证,鉴于撒加布与撒加伯是同时代人,同属罗罗司管辖,是同一个人的可能性是有的。
元设苏州是州一级政权,并且下辖1县,但没有说明这个州是上州、中州还是下州,所以对撒加布所任品秩难以考订。据《元史》记载:“中统五年,并立州县,未有等差。至元三年,定一万五千户之上者为上州,六千户之上者为中州,六千户之下者为下州……上州:达鲁花赤、州尹秩从四品,同知秩正六品,判官秩正七品。中州:达鲁花赤、知州并正五品,同知从六品,判官从七品。下州:达鲁花赤、知州并从五品,同知正七品,判官正八品,兼捕盗之事。”[7]1551从其有辖县来判定,苏州属于下州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上州或中州的可能性较大;由于“以撒加布知州事”,说明撒加布是“知州”,而只有中州和上州的行政长官才是“知州”,所以初步认为苏州属于中州。如此,苏州土知州所辖居民应在6000户以上15 000户以下,而撒加布的品秩应是正五品。
(二)明朝时期冕宁土司制度
明朝沿用元朝的土司制度,设置的土司有宣慰使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等土司类型,另有“军民府、土州、土县,设官如府州县”[8]1876。据《明史·四川土司》记载:“宁番卫,元时立于邛都之野,曰苏州。洪武间,土官怕兀它(他)从月鲁帖木儿为乱,废州置卫。环而居者,皆西番种,故曰宁番。有冕山、镇西、礼州中三千户所。”[8]8019-8020
据《土夷考》载:“宁番卫,古苏州地。故名其蛮曰脱苏,其人凶犷强悍,刀耕火种、迁徙无常,不以积藏为事。自洪武初年,土酋怕兀他从月鲁帖木儿作乱,总兵徐凯奉檄征剿,后罢州治,废土官,改为指挥使司。遂将环居西番编为四图,责令办纳苏州驿铺陈、站马、廪给、差役,使之知向王化,而以四千户所钤束之。卫之东南、卫之东北,错居夷寨。若五宿,若结古、若热唧瓦、若扯羊、若纳纳碑,若马蝗沟等番,虽叛服不常,亦多驯挠听命……”[10]史,255-470
《明史》中记载的怕兀它就是《土夷考》中的怕兀他。由于元朝实行土官世袭制,“土官有罪,罚而不废”[7]2635,即使元朝时期反叛朝廷的撒加伯就是苏州土知州撒加布,其家族对苏州的管辖权也不会被剥夺,所以明朝初期跟随月鲁帖木儿反叛朝廷的怕兀他应该是撒加布的后裔。对于怕兀他,《明实录》载:“洪武二十一年冬十月……置四川苏州卫指挥使司,初以土官帕兀它(他)为知州,扶其夷民。至是,命羽林右卫指挥佥事陈起领军至苏州,筑城置卫以镇之。”[11]卷194,3
可见,明朝初期委任的苏州土知州,是由土著民族的首领担任,但此时朝廷“筑城置卫”,且目的是“镇之”,即对怕兀他保持一种武力威慑。这显然是对怕兀他的不信任,使怕兀他的统治受到威胁,这可能导致怕兀他的不满,加之当时明朝的驻军可能对土司及其属民进行欺凌和巧取豪夺,迫使怕兀他最终参与了月鲁帖木儿对明王朝的反叛。
明朝政府在平定叛乱后“罢州治,废土官”。洪武二十六年三月,“改苏州卫军民指挥使司为宁番卫,遣使赐指挥鲁毅钞三百锭,白金三百两,文绮八匹,授世袭指挥使,以守御有功也”[11]卷266。鲁毅虽然具有“世袭”的特权,但仍然属于流官,而不是土司,只是由于地处边疆,朝廷授予其世袭的权力,在当时朝廷驻扎宁番卫的屯军将领也同样具有世袭的特权。至此,苏州土司政权灭亡,怕兀他成为苏州最后一任土知州。明朝借助怕兀他反叛之机对苏州实行“改土归流”,史书称为“废土改卫”[12]563。这之后的明朝究竟还有没有在该地区设置土司,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首先,明王朝是想“改土归流”的,但能不能实现要看具体情况,“土官乘机宜革以救边民,夫边职之汉夷并设也,实番蛮杂处,非兼土司不能联属也,查先年宁番卫土酋怕兀他从裕噜特穆尔(月鲁贴木儿)为叛,太祖特命总兵徐凯征讨,遂废土改卫,止(只)将环居西番编为四图,听我羁縻”[12]560-563。就朝廷来说,革除土官是最佳选择,但有难度,只能“边职之汉夷并设”,实行土流共治,能够完成直接统治的只有宁番卫治所附近的“环居西番”,结合《明史·四川土司》提供的资料来看,将“环居西番编为四图”“以四千户所钤束之”。但对于边远一点的土著民族来说,由于“番蛮杂处,非兼土司不能联属也”。由于藏彝民族相互交错,民族关系复杂,只有设置土司才能有效管理。
《明实录》记载:宣德九年六月,“戊辰,四川宁番卫故土官作他子扒哥来朝贡马”“甲申……赐……四川宁番卫故土官舍人扒哥等钞金织纻丝罗绢”;《明实录》称“土司”为“土官”,作他子扒哥是宁番卫的故土官,而不是设立宁番卫以前的苏州故土官。封建社会的朝贡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贸易制度,这种制度对中原王朝来说,更主要的是具有象征性的政治意义。通过朝贡制度,既显示中原王朝的地大物博,也可以增强周边国家或部族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力。对“番邦”而言,主要是经济上的意义,中原王朝赏赐的物品,价值往往是其贡品的数倍乃至数十倍,这些赏赐有许多是土司辖区不能生产的物品。进贡的国王、土司或者其使臣,在路上的开支大都由沿途的地方政府负责,地位高的,皇室还要专门设宴款待。正因为此,中原王朝每年因朝贡需要数额庞大的开支,所以规定只有各国国王或土司才有资格进贡,并且规定了各藩国或土司按级别来确定几年进贡一次,每次只能带多少随员,级别越低间隔年限越长、随员越少。可见,凡有资格进贡者,均为明王朝承认其为某一国或某一区域具有合法统治权的国王或土司,作他子扒哥有进贡的资格,证明当时宁番卫确实设有土司。
据《钦定四库全书·四川通志》卷19记载,清雍正五年裁革的投诚土司就有一员是宁番安抚司[12]560-133,这也进一步证明明朝时期冕宁地区是设有土司的。同时,据咸丰《冕宁县志》记载,在康熙四十九年投诚授职,并在雍正五年裁革后尚有1员土千户、13员土百户、5员土目[9]116,这也证明明朝时期冕宁地区确实有土司存在。
“再查宁番卫原有安抚司一员安承裔,管辖土百户十一员:摆占田百户大咱、坝显百户沙家、白路百户倪姑、墟郎百户济布、河西百户那姑,系玀猡苗裔。耳挖沟百户达安、皮罗百户七儿、三渡水百户顺都、水墨岩百户韩雅、瓦尾百户卢沽、大水凹百户那咱,系獏狻苗裔。”[13]212明朝初期,怕兀他反叛朝廷遭到了镇压,为了继续对当地土著进行统治,需要任命新的土司,彝族安氏在平乱过程中立了功,所以被封为宁番安抚司,这也进一步证明明朝时期冕宁确实有土司存在。
从现在的民族构成来看,“玀猡”为彝族,“獏狻”和“西番”均为藏族。这里说摆占田、坝显、白路、墟郎、河西5个百户是彝族,耳挖沟、皮罗、三渡水、水墨岩、瓦尾、大水凹6个百户是藏族,而同一则材料同时记载墟郎、白路、河西3个百户“均系西番苗裔”,也就是说其民族成分是藏族。同样记载上述3位百户“均系西番苗裔”的尚有咸丰《冕宁县志》等史料。可见,明朝时期宁番安抚司安氏下设的百户大部分为藏族,也可以看出在明朝时期,冕宁地区的主要人口是藏族。安氏所辖区域为现在县城以南的安宁河以西、包括雅砻江流域的藏族和彝族居住区,安宁河以东及县城以北的藏族聚居区不在其管辖范围。马文中认为:“平定叛乱后,土知州降为千户所,领卫北原苏州治地为中心的北部番人,宁番卫治附近番人编为四图,纳入行政区划……后又封在平定月鲁帖木儿叛乱中有功的建昌卫土官安氏裔任宁番卫安抚司。”[14]81-82明朝时期经过调整,土著民族的管理分为3部分,一部分是安宁河以东及县城以北的藏族聚居区,由藏族土千百户管辖;治所周围地区纳入地方政府直接管辖;县城以南的安宁河以西、包括雅砻江流域的藏族和彝族居住区由彝族安氏管辖,而安氏下辖的土百户大都为藏族。
经过“废土改卫”后,由朝廷设立的宁番卫成为冕宁地区的最高政权机构,将治所周围的藏族地区纳入直接管辖之下,而其他地区设立土司进行管理。安宁河以西地区为藏、彝杂居之地,雅砻江流域为藏族聚居区,这些地区设土百户进行管理。在平定月鲁帖木儿反叛过程中,彝族安氏立有战功,故将安氏的安承裔委任为宁番安抚司,具体管辖上述土百户。治所以北和安宁河以东是藏族聚居区,设藏族土千百户进行管理。自此开始,冕宁地区再没有形成过统一的土司政权。
(三)清朝时期冕宁土司制度
清朝对冕宁土司制度的记载比元明时期要详细得多,但各材料的记述并不完全一致,这些材料可以相互佐证、相互补充。
康熙四十九年开始,清王朝镇压三渡水“生番”,也就是对现在冕宁县雅砻江流域的藏族用兵,目的是将三渡水地区纳入到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面对强大的清军及各地调动来的土军,原为明朝土司的众多土千百户为避免被剿灭的命运相继投诚,清王朝按原有土司级别予以授职,这就是康熙四十九年时期冕宁土司的来历。后在雍正五年对土司进行改土归流,雍正六年设冕宁县[15]116,16,这次改土归流主要是裁撤在三渡水战役中做事不力的土司,经过裁撤,最后授职的土司有:
县属土职,自雍正五年裁革外,现存土千户一员,土百户十三员,皆于康熙四十九年奉川陕总督殷为招扶,土司番蛮案内投诚授职,领有印信号纸,各员开列于左:苏州土千户姜文富,其祖姜喳,于康熙四十九年投诚授职,管西番寨落四处……架州土百户李正龙,其祖里五,管西番寨落六处……糯白瓦土百户李正隆,其祖纽哞,管西番寨落四处……苗出土百户罗成兴,其祖热即巴,管西番寨落五处……大村土百户马朝元,其祖也四噶,管西番寨落五处……大盐井土百户叶廷耀,其祖前布汪喳,管西番寨落五处……热即瓦土百户金得禄,其祖牙阜撇,管西番寨落五处……中村土百户马兴贵,其祖歪即噶,管西番寨落五处……三大枝土百户印玉龙,其祖甲噶,管西番寨落四处……现护窝卜土百户土妇伍朱氏,应袭土百户伍洪贵,其祖蓝布甲噶,管獏狻寨落四处……河西土百户杨世福,其祖那姑,管猓猡寨落四处……虚郎土百户沈应龙,其祖济布,管猓猡寨落十一处……白路土百户申有福,其祖倪姑,管猓猡寨落五处……阿得桥土百户杨世显,其祖募庚,管猓猡寨落四处……
以上土千百户14员俱系西番苗裔,外有瓦都等处土目四名,俱系獏狻苗裔,先世皆于康熙四十九年投诚授职者,雍正五年因征三渡水獏狻,违误军粮,参革充发,追缴印信号纸,其部落户口仍令该参员等后嗣世为土目管束,名列于左:瓦都土目安普氏,应袭土目安锡龄,其祖安承裔,管猓猡寨落五处……木术凹土目鄢成贵,其祖那咱,管西番(一示獏狻)寨落五处……耳挖沟土目达朝恩,其祖达安,管獏狻寨落五处……瓦尾土目卢成元,其祖卢沽,管獏狻寨落五处……外有七儿堡土目穆怀玉,其祖穆别,系西番人,于雍正五年从征三渡水硒踏路径有功,赏给世为土目,管獏狻寨落九处……
凡土千百户承袭,取具宗图各结详报咨部,换给号纸。土目则由县验充给委,所管堡寨,不必尽是一种,如獏狻部落,西番为多,举此可见。皆设有耆老伙头,通汉语,又有甲首轮户充当。各土职有设土兵者,如白路、虚郎,多者四名,少者二名,余设土差,多者十名,少者二名,以供传唤公务,稽查地方。[9]116-118
就材料分析,可以得出:
1.在清朝雍正五年改土归流后冕宁一直存在的土司共有土千户1员,土百户13员,另有土目4员。土千户、百户是由清朝中央相关部门颁发印信号纸,享有世袭权利,是名副其实的土司,而土目只是由县上发给任职执照,属地方行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不应该属于土司,但却享有诸如世袭等土司权利,所以从广义上来说也可以纳入土司系列。土千百户均为武职土司,而当时设置的几个土目,从《钦定四库全书·四川通志》卷19和咸丰《冕宁县志》等材料来看,也具有武职的性质。苏州土千户在归顺清朝时期辖地尚较为宽广,下辖苗出、大村、糯白瓦3个土百户,管辖番民1 516户,但到清朝咸丰年间,已经衰落到只管辖4个寨落,辖下的3个土百户也脱离其管辖。自此,苏州土千户只是名义上的千户。
2.以上各土千百户和土目共管辖藏族寨落71处,彝族寨落29处。可见,直到清朝咸丰年间,冕宁县的藏族人口要比彝族多得多,居住范围也要比彝族大得多。除此之外,藏族在明朝时期就有宁番卫直接管理的“环居西番”不在土司管辖范围,到清朝时期被纳入朝廷直接管辖的藏族村落应该更多。彝族地区迅速扩大、人口迅速增加,而藏族地区大幅度收缩、人口急剧减少的时间是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一直到整个民国时期,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大部分的藏族聚居区变为了彝族聚居区。
对冕山营所属的苏州土千户及8员土百户的记载,各史料是一致的,土司和属民均为“西番”。说明苏州土千户及架州、苗出、糯白瓦、大村、大盐井、热即瓦、中村、三大枝8员土百户以及他们的属民都是藏族。而据咸丰《冕宁县志》记载苏州土千户及13员土百户,以及七儿堡土目都是“西番”。除七儿堡土目外的4个土目均是“獏狻”,通过对文献的考订和实地的田野调查,“獏狻”是对藏族纳木依人的歧视性称呼[6],所以咸丰《冕宁县志》认为所有土司的民族属性均为藏族。这些大致是没有问题的,唯一有问题的是瓦都土目。瓦都土目安氏据《钦定四库全书·四川通志》记载,安承裔原是安抚司,在雍正六年被裁革,而嘉庆《四川通志》详细记载其被裁革的原因是“违误运粮”。安氏本西昌河西土司之旁支,现已完全融入彝族中,所以咸丰《冕宁县志》对瓦都土目所属民族的记载是错误的。
3.从材料上看,各土司土目必须按时按量向政府缴纳粮食或银两,表明朝廷对其管辖的有效性,但就内部的自治权利来说,各土司土目除能够自行安排生产生活及自行管理本辖区的宗教、教育等事宜外,还可以看出各土司权力的大小。冕山营河西土百户是所有土司中权力最小的,“有命盗事件归地方官审办”[17]3083,本身只有调解纠纷的权力,而靖远营的4个土百户、3个土目权力稍大,“有命案归地方官办理”[17]3084外,也就是说除“命案”以外均由土司自行管理,而权利最高者为冕山营的苏州土千户、8员土百户及泸宁营的七儿堡土目,几乎享有辖区内的一切权利。土司对辖区管理权的大小,反映出土司自治权力的大小,同时也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对各土司的权力没有采取“一刀切”的态度,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
4.关于七儿堡土目的问题,咸丰《冕宁县志》记载:“于雍正五年从征三渡水跴踏路径有功,赏给世为土目。”[9]118而嘉庆《四川通志》记载:“原设土司,于康熙四十九年投诚授职,颁给印信号纸,雍正五年因征三渡水獏狻违误运粮参革,追缴印信号纸在案,其部落户口仍设土目管束,住牧七儿堡。”[17]3084并管辖耳挖沟土目1名,《清史稿》也载:“七儿堡土目,原设土司,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雍正五年,降土目,管有耳挖沟土目。”[16]14240在《钦定四库全书·四川通志》中却没有关于裁撤七儿堡土司的记载,但在裁撤名单中有“皮罗木罗土百户七儿”[12]560-133,这有可能就是七儿堡土目的前身。从这些材料来看,咸丰《冕宁县志》属于孤证,而其他材料可以相互佐证,也就是说,七儿堡土目是由土司裁撤后设置为土目的可能性很大,而“原设土司”可能是土百户。
5.清朝初期裁撤了12个土司,其中4~5降为土目①鉴于各种文献对七儿堡土目是新设土目还是由土司降为土目记载不一致的缘故。,其余均完全撤销。完全撤销土司的地方就被收归政府直接管辖,清朝政府在这些地区设立了具有军事性质的塘汛,目的是对各土司土目保持军事威慑,同时也导致大量外地移民进入这些地区,与纳入政府直接管辖的“番民”杂居,这加速了当地土著民族融合的进程,同时使保存下来的各土司之间条块分割,不易联合起来反叛朝廷,经过长期治理,冕宁县境内的土司实力逐步衰落,最终在清朝末期到民国时期这一段时间逐步变为平民。
四、结语
从元朝开始,冕宁县境内设有实质意义上的土司,而撒加布是第一个受封建王朝册封的土司。从1328年建立苏州开始,直至明朝初期怕兀他起兵反明,被镇压后明朝废除了其家族统治整个苏州的权力,设宁番卫,将其地分设为安抚司及土千百户等众多土司,其家族对包括冕宁县大部及周边县域一部分的统治时间达60余年。
明朝初年彝族安氏因在平乱中有功而受封为安抚司,其权力及管辖范围没有明确记载,从清初“改土归流”的结果来看,安抚司被降为土目,全县地位最高的土司为苏州土千户,而苏州土千户为投诚授职者,说明苏州土千户可能是明朝时期的一个地位较高的土司,明朝初年镇压怕兀他之乱后,为维系对原苏州的统治而设立,考虑到对当地藏族的治理,可能同时设立了一些土千户和土百户,时间应该在1393年改苏州卫为宁番卫前后。
元朝中期到明朝初期的撒加布家族统治的结束,意味着统一的脱苏地方政权的终结。苏州土千户家族的历史,从明朝初期开始到民国结束,前后经历了500余年的时间,其统治范围也由明朝时期的苏州府所在地及其周边地区到后来的只有4个寨落,到最终变为平民。可以看出,冕宁土司制度的历史就是一部土司制度逐渐衰败的历史,也是当地土著藏族由盛转衰的历史。
从元朝设立苏州开始到清朝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可以看出中央王朝对冕宁地区的土司制度经历了一个由建立到逐步削弱的过程。元朝的苏州土司是统一的、有完整自治权的,明朝时期则设立了宁番安抚司及土千户进行分治,在安抚司及土千户之下设土百户。清朝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安抚司降为土目,一些土千百户被撤销,其辖地被纳入到政府直接治理之下,仅剩千户1员,百户13员,土目5员。并逐步取消千户管辖百户的制度,各土司最终被完全分割,土司制度彻底衰落。
冕宁是一个多民族、多族群的地区,所以一个土司所辖属民不一定是一个单一的族群,史书记载的往往是居于主体的族群。从明朝开始,政府直接管辖的地区逐步扩大,汉族逐步变为冕宁地区的主体民族,许多土司属民转为政府直接管理,土司辖地越来越小、属民越来越少,土司在当地政治经济文化中的地位也越来越低,一部分土著民族人口可能融入到汉族中。经过长期的文化磨合,各土著民族与汉族的居住格局逐步确定下来。随着清末朝廷对凉山地区大规模用兵,大量彝族家支越过小相岭进入冕宁境内,冕宁稳定的民族分布格局再一次被打破,新的民族分布格局出现。“改革开放”后,各民族互动频繁,大量藏族和彝族迁入汉族聚居区居住,民族分布格局再一次进入重新调整的时期。
[1]方国瑜.彝族史稿[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402.
[2]何耀华.川西南藏族史初探[M]//李绍明,刘俊波.尔苏藏族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324.
[3]龙西江.凉山州境内的“西番”及渊源探讨(上)[J].西藏研究,1991(1):26-39+85.
[4]赵心愚.咸丰《冕宁县志》的资料来源、篇目特点及纳西族史料价值[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158-163.
[5]张晓蓓.从冕宁司法档案看清代四川土司的司法活动[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45-52.
[6]袁晓文,韩正康.多续藏族土司研究[J].中国藏学,2015(2):114-120.
[7]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0.
[8]王鸿绪,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9]李昭,纂;李英粲,修.冕宁县志[M].冕宁县地方志办,校编.内部资料.冕宁:冕宁县印刷厂,1996.
[10]谭希思.四川土夷考·宁番卫图说[M].云南省图书馆藏旧抄本.
[11]明实录·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M].影印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82.
[12]张晋生.钦定四库全书·四川通志[M].西南大学图书馆藏影印本.
[13]四川省编写组.四川彝族历史调查资料档案资料选编[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212.
[14]马文中.川西南散居藏族[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5:81.
[15]清实录·雍正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6]赵尔巽,等.清史稿[M].西南大学图书馆影印本.
[17]黄廷桂.嘉庆四川通志[M].成都:巴蜀书社,1984.